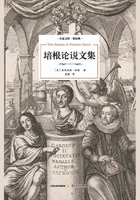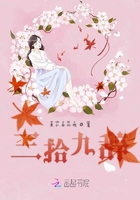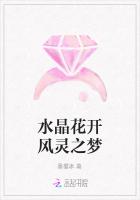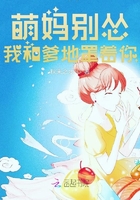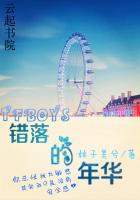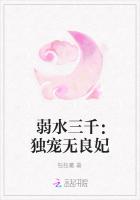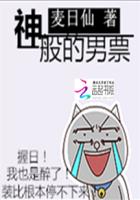孙文波
新近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90年代的诗歌状况;有人已经写出了洋洋洒洒的文章,对90年代的诗歌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章以自以为是的夸张言辞,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架子,将某种类型的诗歌说成是代表了90年代最高成就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与文章作者诗歌观念不同的诗人的作品统统指责为“伪诗歌”。其言论的霸道,所依据的理论的荒谬,都是近十年来罕见的,让人读到后不能不想到,即使在诗歌这样的领域里,要建设真正的写作的民主和自由,事情也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要消除某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思想,仍然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不过,就像纸永远包不住火,谁如果以为在面对历史的事实时可以玩弄瞒天过海的手法,靠诋毁别人就可以抬高自己,除了得不到一丝好处外,只能是自寻其辱。我不知道写出这种文章的人怎么连一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难道他真以为别人会连事实都不顾,光听他一说,就相信了诗歌在90年代的情况就像他说的那样了吗?
在90年代的最后一年,作为亲历者,我自认对一些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理解的90年代诗歌,它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相对与80年代,它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一种进步呢,还是有着其他的意义?
关于80年代诗歌,很多人写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总的看法是80年代是诗歌的革命时期,有着运动的性质,真正出现的有分量的作品不多。对这样的看法大体上我是同意的。今天回头看80年代,我看到的是文学革命的热情,对运动的热衷高于对写作的内部真正的探究。至于能够看到的,也是说法多于作品,宣言多于实干。因而即使是诗歌史家,他们谈论得最多的,也不是某些诗人的某些作品,而是某个派别、团体的某些行动。大家记住的是诸如“非非主义”“整体主义”“他们”,以及像什么“大学生诗歌宣言”“反文化”“前文化”“1986年两报诗歌流派大展”[106]这样的东西,很少能记住其他的、对于诗歌历史而言更重要的文本,而即使能够记住一些作品,也不过成为上述派别、团体存在的佐证。当然,就是这样,我个人认为80年代的成就还是不能抹杀的,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的意识形态禁锢后,诗歌的革命运动,无论怎么说也带来了对诗歌工具化造成的,写作的长期滞止的格局的破坏,改变了一代人对诗歌的阅读要求,和对诗歌本身存在的憧憬,而这一时期的写作作为学习训练,亦为以后的诗歌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为80年代的诗歌定位,我的定位就是:它的活跃的、激进的、夸炫的氛围,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少有些混乱的局面,为90年代的诗歌变化提供了可资总结的经验。这也是使90年代诗歌得以发展的先在条件。
大概很多人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在他们眼里,80年代是诗歌成就辉煌的时期,譬如就有人提到80年代是“朦胧诗”成熟的时期,也产生了海子这样的诗人,以及像韩东、杨黎、于坚、李亚伟、廖亦武这样的有影响的人物。的确,海子现在是相当受推崇的诗人了,韩东、于坚等也是某些写诗歌史的人要谈到的对象。只是在我的看法里,谈论他们的理由部分地出自对他们的诗歌文本的评价,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海子的死亡所带来的人们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一方面来自他的诗歌,以及诗歌抱负,另一方面则有缅怀,有对使他致死的因素的仇恨,和复杂的其他动机;但像韩东,人们如今谈论他,主要是由于他所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的理论,作为观点,它当然不失为一种关于诗歌写作的认识,对80年代的诗歌讨论亦产生过冲击性影响,但是,要说它使韩东(他的《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诗,其语言对认识事物的观念表达是清楚的)和接受了韩东观点的人,写出了与这一观点完全相符的诗篇,那又是大可怀疑的;而像于坚提出的“拒绝隐喻”的诗学观点,它所带来的却是更多的质疑,也许还有误解,这和他本人的写作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并没有让人看到他写出了哪些如他自己所说的,了不起的、真正拒绝了隐喻的诗篇(他的《关于一只乌鸦的命名》是对隐喻的拒绝吗?)。至于说像“消除语义”这样的更为极端的观点,其宏伟的抱负虽然可观,但要找到能够体现它的作品,则根本就只能是类似于攀天梯这样的幻想行为。(连语义都消除了,你凭什么希望人们阅读你的作品,并判断其是否有价值呢?)诗歌写作会受到写作者观念的支配,但要说有观念就可以产生经典作品,这样的等式却很难成立。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80年代是产生了少量的好诗人,而不是普遍的好作品的时代,曾经有过的,对某些作品的价值不是看错了,就是其真正的意义被夸大了,一代诗人的成熟还需要时间的打磨。革命之后的发展才更为关键。时代语境的总体性变化需要以新的方式来适应。所以,就利弊而言,80年代产生的问题多于为90年代提供的道路[107]。因为不同意“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你就必须回避它,或者说干脆对它提出质疑;不同意“非非主义”“整体主义”理论,亦要对之有所批判。如果说90年代,包括韩东、于坚等人的诗歌,产生了好作品,那么,它们的确不是由“诗到语言为止”“非非理论”“拒绝隐喻”和其他的什么理论滋生出来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人简单地认为是由于选择了什么“民间立场”后获得的。它们的产生,完全在于在放弃的痛苦和艰难的摸索中,找到了与90年代社会发展进程相关的话语方式,是这一新的话语方式下的产品。事实上,90年代的诗歌处境十分复杂。1989年后,中国的社会形势所发生的变化大得惊人。商业化潮流(包括政治、文化,甚至科学的商业化),以不可逆转之势改变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公众对诗歌的理解和兴趣亦日益萎缩。而通过对80年代诗歌的反省,不少诗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诗歌的存在所依赖的,除了其内部的发展规律而外,还与时代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或者说存在着某种相互刺激的共生关系。而任何单纯地将诗歌看作是可以不依据于任何东西就可以独立的事物,只要依靠对其内部有所把握,将之置于绝对化的人类精神活动范畴,就可以成就它的认识,除了显得十分幼稚,过于自恋和中心主义外,更像是关起门来的自我欺骗,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任何实在的收获。这样一来,除非不打算再写作,很多诗人也确实不再写作,还要写作,就必须重新理解一些基本问题,再次明确写作的性质、意义和目标,为自己选择或者说设计写作的方式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写作的最终成立建立在真实和恰当的基础上。
现在有人把这种重新开始看得很简单,仍然认为不过是将写作定位于对诗歌的功能的理解。因而在他们的文章里,所谈到的亦只是像什么“诗歌是自由的”“诗歌就是反对权势,是人类想象力的解放”[108],或者“诗歌来自于人的感官的直接悟性”“诗人是时间的原在”之类的话,好像只要在这样的说法的支配下,不要有所顾忌,放开手脚,让想象力驰骋,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诗篇。但哪有那么容易?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自由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也根本不存在让人绝对自由的条件。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由各种不同的思想支配的社会中享受到那种绝对的自由呢?同时,所谓的想象力,对事物的认识亦必然要受到时代环境、个人能力的诸种限制,并没有那种天马行空,将之放任到无边无界的可能性。而实际情况只能是:看清楚形势,对外部条件所给予的界限了解清楚,才能使写作获得真正的有效性。所以,我宁愿把90年代的诗歌写作看作是对“有效性”的寻找。而且我认为在一些诗人那里,这一点是找到了的。他们的确知道了,相对于“好”的写作,一个诗人在相关的时代里,写作的“有效性”更重要。它所包含的是“历史的这样”的事实而不是“历史的那样”的事实;它所决定的不仅是作品的价值,而且还有一个诗人以及诗歌在人类生活中为什么有必要存在的意义。为什么有些80年代很活跃的诗人到了90年代后,写作变得苍白无力,丝毫没有意义?就是因为这些诗人没有为自己找到新的写作边界,仍然以那种所谓的超越时代的幻想从事写作。
情况的确如此。进入90年代,一些诗人对体系化的理论不再热衷,当他们重新领悟了诗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并没有超验的自由,会被制度化地变为某种集体语言的牺牲品,并进而会使哪怕是充满激情、抱负的单纯性对抗写作失效时,提出了“个人写作”[109]的概念。有人后来对这一概念不理解,进而反对它,将之说成是假的诗学概念。其实,当初提出“个人写作”的诗人也并不是不知道它是临时性的诗学说法。诗歌写作,谁又不是一个人在写呢?只是,它具有针对性,针对的是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达和商业的发展把人们的思想强制性地拉向一边,意识形态又在制造所谓的“主流话语”,而且,一个“统一的话语场”根本不可能人为地分离出“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这样的两极对立形态。或者说只是提供着虚假而表面化的两极对立形态时,保持写作的独立性如果不被提高到与具体诗学相关的显著位置,并为之找到基本的品质保证,就没有可能写出“自己的”诗篇,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表达诗意的纯粹观念了。从今天的角度看,“个人写作”的提出是适时的,它使得一些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了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来自各个领域的权势话语和集体意识的警惕,保持了分析辨识的独立思考态度,把“差异性”放到了首位,并将之提高到诗学的高度,但又防止了将诗歌变成简单的社会学诠释品,使之成为社会学的附庸。因而,尽管“个人写作”从另一方面看,不再是强调代言,是诗歌的抱负的缩小,是在为写作建立起一个有限的,与个性和风格有关,而不是与无限膨胀的占有欲有关的范围,但它并没有因此放弃和无所承担,也没有自闭性地将写作放置在狭隘的、与其他人的交流隔断的境地。为90年代诗歌提供的亦是独立的声音。
当然,独立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作为诗歌是最好的声音。对诗歌的构成来说,还有很多因素是重要的,譬如说面对着诗歌的历史进程,存在着“怎么写”的问题;面对着时代的状况,存在着“写什么”的问题。虽然不能说这些问题80年代没有诗人去思考它们,但相对于80年代的思考,90年代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上,显得更讲实际,更有针对性,更强调它的“合成”因素的重要。就拿诗歌与人性,与时间的存在的关系这样的问题来说吧,80年代很多诗人更希望以纯粹的、直达核心的,甚至是超验的方式,对其做出阐述,因而产生出的诗篇很多都是直接性的,哪怕那些以结构庞大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诗篇亦是如此,像杨炼的作品[110],甚至在少数诗人那里,还出现了“新八股”迹象。但90年代,诗人们则更愿意在写作中呈现出这种关系在具体时间和空间中的样态,使之由景象、细节、故事的准确和生动来体现,力求做到对空洞、过度、嚣张的反对。而且正由于注重了“具体”问题,不单诗歌题材的选择更加多样化,进入了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产生诗意的领域。而且,构成诗歌的技术手段也变得多样化起来,就像有人已专门讨论过的那样,现在,构成诗歌的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正面的抒情了,不单出现了文体的综合化,还有诸如反讽、戏谑、独白、引文嵌入等等方法亦已作为手段加入到诗歌的构成中。这些东西的加入,无疑使诗歌脱离了“庸俗非理性”的吊诡,以及平面化的简单,提高了诗歌处理复杂题材的能力,尤其是复杂日常生活经验的能力,因而显得更丰满、更具有复杂性,也更具有表现力。同时,还不晦涩[111]。这样的情况,使那些总想从两个方面指责当代诗歌“简单”和“深奥”的观点,失去了意义。
而表面上看,这些就像有人所说,是因为90年代的诗歌选择了“叙事”,诗歌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变成了对现实的描摹。实际上,并非仅仅如此。“叙事”的确是现在不少诗歌作品的特征,但为什么“叙事”?叙了事就能带来作品内在的品质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不可能使诗歌达到“好”的标准。因为“好”是综合指数。所以,即使是“叙事”,还应该看到叙的是什么事,怎么叙的事。这样,如果将“叙事”看作诗歌构成的重要概念,包含在这一概念下面的也是:一、对具体性的强调;二、对结构的要求;三、对主题的选择。这样,同样的“叙事”,包含在这一概念里面的,已经是对诗歌功能的重新认识,譬如对“抒情性”“音乐性”,以及“美”这些构成诗歌的基本条件都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而我更宁愿将“叙事”看作是过程,是对一种方法,以及诗人的综合能力的强调。在这种强调中,当代诗歌的写作已经不仅是单纯地“写”,而是对个人经验、知识结构、道德品质的全面要求。可能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叙事”是“经验主义”的。虽然“经验主义”作为说法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将之看作是对创造力的扼制,但如果把它理解为对处境、遭遇的认识,甚至理解为能力、技术和态度,也可以说它是对的。诗歌与经验的关系不是简单摹写的关系。“叙事”在本质上是对处理经验的全面强调。人生活的世界上,面对着吃喝拉撒睡,面对着美与丑、爱与恶、生与死,经验当然是庞杂的。而庞杂兼有活力和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叙事”的选择实际上迎接了更大的挑战,包括对甄别能力和指责的挑战。
人们可以说80年代强调的也是方法,难道说“诗到语言为止”“消除语义”“拒绝隐喻”等不是这样的吗?不过,方法与方法有时候在实质上是不同的,相对于上面几种方法的强调,90年代对于方法的要求所具有的性质是具体的,就像“诗到语言为止”,怎么才算到语言为止呢?“消除语义”,怎么才算消除了呢?而“拒绝隐喻”,又怎么才算拒绝了呢?这样的笼统的说法在具体的写作中很难由作品来说明。但说到“叙事”,它却能具体到对一次谈话的记录,也能够具体到对一次事件的描述。像“日常经验”“诗意的扩大化”这样的所指,是能够容纳进去的。使一切具体起来,不再把问题弄得玄乎,一方面强调某种一致性,一方面注意依据自身经验使诗歌在结构、形式,甚至修辞方式保持独立性,这无疑是90年代诗歌的显著之点。很多作品也已经作出了证明,像萧开愚的《向杜甫致敬》、张曙光的《公共汽车上的风景》、臧棣的《书信片断》、王家新的《孤堡札记》、欧阳江河的《晚间新闻》等作品。这些作品尽管由于每一个诗人语言风格的不同,其在修辞、结构上各异,却都是清晰的。因此,那些把“叙事”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写作的风格的人,并没有真正了解到进入90年代后,对“叙事”的强调的真实含义,它绝不是有些人简单理解的那样,是将诗歌变成了讲故事的工具,而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体现着语言的真正诗学价值。其实,像于坚这样的诗人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诸多文章中,他亦从另一种角度反复谈到这类问题。只是,他好像并没有准确而仔细地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因而,在他的论述中,总是把来自与历史语境有关的变化看作是个才能使然的产物,和来自由地域提供的语音差异的产物,以为只要有了才能和说某种语音,就可以解决所有诗歌的质量问题,写出所谓的“本真”的诗歌。要是事情真那么简单当然好。但怎么能想象在当代诗歌的地理学中没有相对语境中的制度化压力,不存在由意识形态所带出的权势话语,能够出现他所说的写作的“民间立场”,和“非中心话语”呢?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对诗歌的认识,虽然表面上赋予了诗歌更神圣的价值,但由于它根本没有考虑历史语境有“现实性”,实际上是将之悬置起来,因而它也就更像来自一厢情愿的想象,或者说来自将自己放置到时代与社会生活之外的虚构。90年代以来,不少诗人谈论的“中国话语场”实际上包含了对这些问题的考虑。通过不断地在精神上与具体语境的强制性遭遇,他们意识到“现实的语言”与“语言的现实”,以及具体的社会生活,存在着制约诗歌写作的力量。任何诗人都不可能逃脱这样的约束。写作从来都是有限的写作。它虽然包含人类对于永恒的理解,但它绝不是抽象地体现所谓的永恒。因为没有对具体的把握,哪里又存在什么永恒呢?因此诗歌写作,永远是综合的“在场”,而不是对“在场”的遁匿。谁能逃匿?因而,它既不“本土”也非“非本土”,既不“边缘”也无所谓“中心”。它的无限只是由消失的时间给予的物质的事实。甚至,只是梦想。
但诗歌是为梦想存在的吗?从本义上讲是,但从写作的角度讲不是。进入90年代,抱有诗歌是梦想的想法的诗人越来越少。在物质的世界上,诗歌不能带来什么已越来越明确。就算如有人所说,它可以抵抗什么,这种抵抗也只是抵抗的行为本身。因此,不管是强调“知识分子身份”[112],还是“中年写作”[113],其意义都隐含了把现实看作诗歌赖以构成的前在条件——这种条件首先要求诗人将分析与批判看作自己的天职。一个诗人面对着这样的前在条件,必须意识到写作本身包含的对诸如道义、良知、责任、立场等人类价值的认知。它甚至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当代写作中,诗人必须选择“介入”或“非介入”,才能获得作为诗人的方位感,体现出向真理的趋近。而是一种写作与诗歌的双向“介入”。这样,与80年代不同,关于诗歌的神性,它使人获得某种带有绝对值的超人类价值的认识;关于语言的纯洁,它的不可动摇的绝对性,多多少少已被抛弃。离开了人类生活的具体事实,诗歌有什么意义?而语言,当它产生于复杂的善恶相混的世界,从来就不可能是纯洁的。这样一来,从另一种意义上讲,90年代的诗歌可以说是“世俗的”诗歌。“世俗的”,虽然不好听,但这是实际的。政治、经济、科学哪一样不是呢?人类生活的现实就是“世俗”的现实。诗歌讲述着人类的生活,以及精神上对于人类生活历史的认识。因而,它是一个返回而非脱离的过程。它通过语言,使人返回到与生活更紧密的,进而揭示其真相的关系中去,而不是想当然地勾画出一个所谓的“特权”领域,与什么“神意”“立法者”联系在一起。那种为诗歌划定“特权”领域的做法,在今天既显得自恋似的矫情,又不会有谁给予认真的承认。由此,哪怕是诗人无限地珍惜自己的劳动,并投入了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到了今天,他也再不会说自己与别人不同。不同的只是他选择了运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
这样,曾经萦绕于80年代的诗歌“纯”与“不纯”的纠葛,在90年代作为问题已不存在。人类都是不纯的,语言都是不纯的,而这一切又理所当然地共存在世界上,谁又能够真正地超越它们呢?因此,不管承认与否,90年代诗歌涉及的范围更广泛,对语言的选择自由度也更明显。只要是人类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是诗歌不应该去触及的。那些指责90年代的诗歌滑向了猥琐、凡俗、平庸,热衷于描写普通的事物,在词汇的使用上没有限制,是精神的下降而非上升的人,显然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这里面所包含的诗歌新认识:在语言的范围内,所谓的好词与坏词,抒情与非抒情,都已经获得了诗学观照,处于平等的地位,都可以成为诗歌确立的材料,都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最好的观照物,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人类生活的隐秘意义。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蕴含着诗歌因素的,重要的是,需要去发现、寻找、组织,并将之准确而生动地呈现出来。这同样是精神的探险的历程。如果我们说一个诗人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体现在他能够在任何地方发现诗意。世界上从来没有现成的诗意在那里等待着一个诗人。如果诗人不能做到从复杂的事物中找到诗意,那么他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一旦完成了诗意的构建,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是“纯”的而那是“不纯”的。这种分类在今天的确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对它的强调只能是人为地划圈诗歌的外沿。打破外沿,我们也可以说这是90年代诗歌所做出的最有力的努力之一。这样,尽管到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90年代诗歌在完成建立诗歌新形态的工作中,解决了全部问题,所有的作品都已体现出“满足”的文本质量。不过,说它们不再是单纯的、虚玄的、与生活无涉的,应该是成立的。当然,就像太阳下面无新事一样,人们也可以将这样的新认识说成是并不新的。《诗经》、唐诗、宋词,汉语诗歌传统中早就存在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但诗歌的传统不是修辞学的传统,诗歌的传统是变化的传统。90年代,同样也是对传统的修复的年代。上面提到过的“中国话语场”,以及对“具体”的强调,都是修复的表现。只是这种修复更注重精神的衔接,而非语言的外在的接受。同时,这种修复不等同于有人所说的“中国特征”的保持,当然也不等同于对它的放弃。在一个连政治也是既与信仰有关,又与利益的平衡有关的时代,特征绝不是保持在语言内部由单纯的词性所体现的。不可能出现语言的绝对独立这样的事情。有人说90年代的诗歌复杂,这种复杂是建立在对传统、现实的双重理解上的。
由此,也可以说,尽管90年代诗歌并不反对语言问题是诗歌的重要问题,但无论是“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甚或是换种说法:“诗从语言开始”,都不是作为中心问题进入到写作中来的。对存在了几千年的诗歌来说,虽然人类意识的发展在认识诗歌功能的问题上有所变化,作为“元艺术”的诗歌本身却要求不变。而写作始终要解决的,仍然是人类思维与认识世界的关系。是对包含在这一关系之下的全部问题——命运、苦难、光荣、幸福、制度——的探究。这样,相比之下,语言问题,尤其是将之看作唯一问题,以为它能够代替一切,是很难解决诗歌质量问题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90年代产生了影响的诗人,不管是强调个人的原始创造力、追求幻想的诗人,在文化的国际寻找差异性互补的诗人,注重挖掘日常生活经验的诗人,以及其他类型的诗人,都无不将写作与现实的关系作为自己必须考虑的因素,并在这一考虑中为自己找到了写作的出发点和诗歌写作技艺的全新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事实它使人看到:就像政治建立不起乌托邦,诗歌同样不能带来乌托邦。如果说写作是一种生涯,那么诗歌就是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当然包括了接受、交流、影响与幻想。它已经让人不得不接受如此的事实:单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永远不可能了。诗歌的语言也就是生活的语言。[114]
原载《诗探索》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