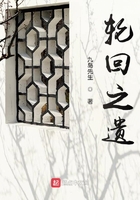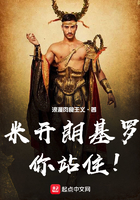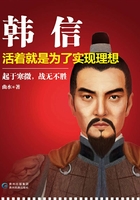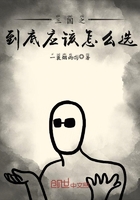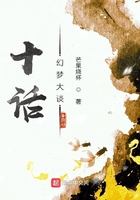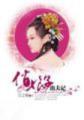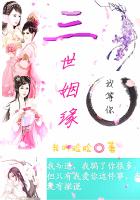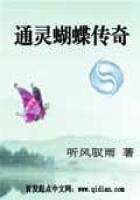1596年,利玛窦教授中国人建造记忆宫殿之法,他告诉人们,这个宫殿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希望记住多少东西:最有雄心的营建将由几百个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建筑构成。利玛窦说,“多多益善”,但又补充道,一个人并无必要上手就建一座宏伟的宫殿,他可以造一些朴实的宫室,又或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建筑,诸如一座寺观、公府、客栈,或是商人会馆。倘若此人希望从更小规模着手,则可建一个客堂、亭阁或是书斋。要是他希望这个处所更为私密,则不妨设想亭阁之一角、寺庙里的神龛,甚至是衣柜和座榻之类的家用物件。[1]
在总结这个记忆系统时,利玛窦说,这些宫殿、亭阁或座榻都是存留于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性建构,而非由真实的材料造成的实在物体。这类记忆的处所有三种主要来源:其一,它们可能来自现实,即人们亲身所处之地,或亲眼所见并在记忆中回想起的物体;其二,也可能是完全出于虚构,随意想象,不论形状和大小;其三,它们可能半实半虚,比如一座人们熟悉的房屋,但设想在其后墙新开一扇门,以作通往新空间的捷径,又如在同一座房屋正中想象出一条楼梯,以循此登入并不存在的更高层级。
在脑海中构想出这些建筑的真正目的,是为无数的概念提供安置之所,而正是这些概念构成了人类知识的总体。利玛窦写道,对每一样我们希望记住的东西,都应给予它一个形象,并给每个形象分配一个位置,使它能安然存放在那里,直到我们准备通过记忆的行动收回它。只有这些形象都各得其所,且我们能迅疾地记起它们的位置,整个记忆体系才能运作。鉴于此,为了便于记忆,显然最简单的办法是依靠那些真实的、我们了熟于心的处所。然而,按利玛窦所想,这也会导致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正是通过不断增加形象以及存放形象之位置的数量才能增强我们的记忆。那么中国人将纠结于这个烦难的任务,即创造无数虚拟的场所,将实和虚的场所混合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复习将其永铸于记忆之中,最终使那些虚拟的场所“与实有者可无殊焉”。[2]
中国人可能会问,这套记忆法最初如何出现在世间。利玛窦早预料到这个问题,将西方古典传统总结了一下:此传统将这种通过严格定位法来训练记忆的主张,归之于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正如利玛窦所说(他尽可能提供了与诗人名字发音最接近的中文名):
古西诗伯西末泥德尝与亲友聚饮一室,宾主甚众,忽出户外,其堂随为迅风摧崩,饮众悉压而死,其尸齑粉,家人莫能辨识。西末泥德因忆亲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记而别之,因悟记法,□创此遗世焉。[3]
按照其处所来记住事物的次序,这种方法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发展成一套记忆学说。到利玛窦的时代,人们已用此方法将自己的世俗和宗教知识条理化。由于利玛窦自己是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因此他期望,一旦中国人开始重视他的记忆能力,就会顺此向他问询西方宗教,正是后者使得此种奇事得以可能。
就为获得向中国士人听众展现这种记忆法的机会,利玛窦不远万里跋涉而来。他是意大利人,1552年出生在山城马切拉塔(Macerata)。1571年,利玛窦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一名初学修士,随即接受了神学、人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广泛训练。在印度和澳门度过了五年见习岁月之后,他于1583年进入中国,开展传教事业。到1595年,他已熟习汉语,并居住在东部省份江西的行政和商业中心——繁华的南昌。[4]在当年年底,利玛窦对驾驭新学语言已自信满满,用汉字写成了《交友论》,这是一本关于友谊的格言集,采自一些西方古典作家和基督教神父。他将这本书的手抄本献给了明朝皇室的建安王,这位亲王居住在南昌,经常邀请利玛窦来府邸参加酒宴。[5]同时,利玛窦开始与当地中国士人讨论他的记忆理论,并向他们传授记忆技巧。[6]翌年,他又用汉语写成了一本探讨记忆法的小书《西国记法》,对他构想的“记忆宫殿”做了描述。他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予江西巡抚陆万陔及他的三个儿子。[7]
利玛窦极力设法将记忆技法介绍给陆氏家族,该家族在中国社会里居于顶层。陆万陔本人是一位才智出众、家境殷实的学者,他在明朝官僚体系中出任过许多职位,熟悉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曾奉派管理过西南边陲,也在东部沿海和北方做过官,其职责范围也曾跨越司法、财政和军事各个领域,且功勋卓著。当时,作为一省的巡抚,陆万陔正值事业的巅峰,也准备让三个儿子去参加高等科举考试,二十八年前,他自己正是通过一层层科考取得功名。他和他的同时代人都很清楚,在中华帝国,科考的成功是通往名誉和财富最可靠的阶梯。[8]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利玛窦向巡抚的儿子们传授先进记忆技巧,是为了帮助他们更顺利地通过科考,而出于感谢,他们会利用新获取的功名来推进天主教传教事业。
然而,尽管巡抚的儿子们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十分优异,但这似乎并非因为利玛窦的记忆方法,而主要是靠中国传统反复背诵的办法,或许就是靠好记的诗句和朗朗上口的韵律,这些正是当时中国通行的记忆训练法。[9]利玛窦当年晚些时候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的信中就说,巡抚的长子仔细阅读了《西国记法》,但向其一个密友评论道:“这套理论确实称得上真正的记忆法则,但能利用它的人,首先得有非常出色的记忆力。”[10]在另一封写给最早和他一起将建造记忆宫殿的法则写出来的一个意大利朋友的信中,利玛窦说,尽管南昌的中国人“全都赞扬这套方法之精妙,但并非所有人都乐意克服烦难来学会使用它”。[11]
对利玛窦自己,建造记忆宫殿并没有什么奇怪或者特别困难的地方。这套方法伴随着他成长,并和许多别的技巧一道,把他研习的各种学问都熔铸于记忆之中。而且,这些技能是他在罗马耶稣会学院所学的修辞和伦理课程的基本内容。利玛窦学到的这套记忆宫殿理论,或许来自学者苏亚雷兹(Cypriano Soarez),后者编写的关于修辞和语法基本知识的教科书《修辞学艺》(De Arte Rhetorica),在1570年代是耶稣会学生们的必读书。[12]苏亚雷兹在书里不但教给读者古典语法和句法结构等基本知识,给出了比喻、隐喻、转喻、拟声、进一步转喻、讽喻、反讽和夸张等修辞法的例证,还介绍了西摩尼得斯的定位记忆的技巧,并将其称为“雄辩术的宝库”(thesaurus eloquentiae)。苏亚雷兹指明了这套记忆法是如何将事物和词汇都按次序定位,因此以其来记忆术语便可达到无穷的进境。学生们应尝试着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生动形象,并为它们设想出各自的场所——其中富丽的宫殿和宏伟的教堂堪称最佳。[13]
然而,这般含糊的说法并不能教给人们记忆技巧的全部,甚至连背后的基本法则也语焉不详。利玛窦或许是从其他几位作家那里学到了更详尽的记忆法,其中之一可能是普林尼,利玛窦在学院学习时曾读过他的《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并将其中有关历史上那些杰出记忆大师的段落译成汉语,编入他在1596年写成的《西国记法》当中。[14]其他的则可能来自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的一些著作,比如拉丁文修辞名著《致赫伦尼》(Ad Herennium),又或是昆体良,他在论演说术的小书中也探讨了记忆问题。这些著作都详尽阐述了如何构造记忆场所以及安置于其中的那些形象,《致赫伦尼》的作者就曾说道:
继而我们应该构造一些尽可能长久存留于记忆中的形象。如果我们希望形象与实物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我们想让形象既不繁多也不模糊,而是真正能有意义;如果我们想赋予这些形象超凡的华美或罕有的丑陋;如果我们想给某些形象戴上皇冠,穿上帝王的紫袍,以使它们更为醒目;又或许我们想以某种方式丑化它们,比如泼上鲜血,抹上泥巴,涂上红漆,如此这些形象就会更触目,或更有某种滑稽的效果——只要这样能使形象在我们记忆中更为牢固,那么,就去做吧。[15]
这番描述极具说服力,因为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视备受尊敬的西塞罗为《致赫伦尼》的作者。
昆体良也探讨了同样的话题,他还对人们作了解释,应当选用何种场所来存放他们选择的形象:
我们可以想象,最首要的思维形象会被安置在前厅,其次的则放在起居室,剩余的则按次序安置在中庭水池四周的房间,它们不仅被安排在卧室或会客厅,甚至可以考虑附于雕像等物之上。完成这些之后,一旦需要复苏关于某些事物的记忆,我们即可依次拜访所有场所,并将这些存放物从保管人那里取回,每看到一件物品,相应的细节就会重新浮现。因此,无论人们想要记起多少事物,都相互联结,如同手牵手的舞者一般,由于它们按次序前后排列,也就不会出错,而除了最初辟出记忆的场所安置它们的工作之外,也并无其他的麻烦事。前面所说的,还是在一座房屋里如此安置,在公共场所中也能有同样的效果,比如一趟长途旅程、城市的高墙堡垒,甚至是一些画。或者,我们干脆就自己来构想类似的地方。[16]
尽管有这样的说明,这套学说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仍然抽象而费解。但是,如果我们暂且离题,看一个现代的例子,或许就能拓宽视野,更好地理解利玛窦是如何通过建立这种形象和场所的联系,吸引中国人对他的记忆理论产生兴趣,这套方法通过概念的组合或是特定的助记法则,将在第一时间产生出人们需要的信息。
设想有一名现代大学里的医科学生,她正面临着一场口试,考查的是骨骼、细胞和神经方面的知识。这名女学生的头脑中有一整座记忆城市,放眼看每片城区、每条大道与小巷、每幢房子里,整齐地存放着她之前在学校里学到的所有知识。然而,医科考试将至,她完全不理会那些历史、地质、诗学、化学和力学的知识区域,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身体巷”(Body Lane)那幢三层的“生理楼”(Physiology House)。这栋楼里的各个房间,存放着她在每晚学习中所创造的形象,这些形象纷繁各异、生动鲜明、启人遐思,它们各居其位,分布在墙边、窗前,或是桌椅床榻之上。这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三个问题:人体上肢各块骨骼的名称、细胞减数分裂的各个阶段,以及头骨的上眼窝组织的神经次序。
她的思绪首先飞到二楼楼梯口的“上身骨骼间”,那里进门的第三个位置有一个加拿大骑警,穿着亮闪闪的鲜红外套,骑在高头大马之上,马尾还拴着一个手戴镣铐、神情狂乱的犯人。而瞬时间,她的思绪又飘到了地下的细胞室,壁炉边上站着一位身形魁梧、带有狰狞疤痕的非洲武士,尽管他硕大的双手紧紧抓住一位美丽非洲女郎的上臂,但脸上却带着无可名状的厌倦之情。接着,这个女生的思绪又很快飞抵顶楼的头骨室,那里,一个艳丽的裸体女子正斜靠在床头,床罩上绘的是法国国旗的条纹和色彩,女子纤小粉拳中正紧攥着一叠皱巴巴的美金钞票。
女大学生很快就有了前面三个问题的答案。皇家骑警和俘虏的形象让她想到一句话:“一些罪犯低估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能力”(Some Criminals Have Underestimated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按次序表示人体上肢各骨骼的名称:肩胛骨(scapula)、锁骨(clavicle)、肱骨(humerus)、尺骨(ulna)、桡骨(radius)、腕骨(carpals)、掌骨(metacarpals)和指骨(phalanges)。第二个形象,“倦怠的祖鲁人追捕黑人少女”(Lazy Zulu Pursuing Dark Damosels),则使她想起细胞减数分裂的各个阶段:细线期(leptotene)、偶线期(zygotene)、粗线期(pachytene)、双线期(diplotene)和终变期(diakinesis)。最后一个形象,“慵懒的法国妓女已预先脱光衣服躺着”(Lazy French Tart Lying Naked In Anticipation),则代表着头骨的上眼窝组织的神经次序:泪腺神经(lacrimal)、前额神经(frontal)、滑车神经(trochlear)、侧面神经(lateral)、鼻睫神经(nasociliary)、内部神经(internal)和外展神经(abducens)。[17]
在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晚期,类似的记忆法拥有不同的关注点,而其创制的形象也更切合于那个时代。我们看到,早在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就写道,赛琪(Psyche)在出生之时,收到了许多漂亮的礼物,其中包括“一架装有飞轮的车”——送这个礼物是墨丘利(Mercury)的主意——“尽管记忆之神把金链子绑在车上,使车子变得沉重,但赛琪依然能靠它飞速旅行”。这些金链子是记忆的链子,它代表着人类灵魂中使智慧和想象得以稳定的力量,而不是用作比喻任何静止不动的念想。[18]而且,在整整一千多年之后,卡佩拉所描绘的那个修辞女神(Rhetoric)的形象仍然在利玛窦和他的同时代人脑海中十分清晰,这个女神掌管着人类的记忆,她“拥有如此丰富的词句,储存如此浩繁的记忆”。
这是她公元5世纪时的形象:
一个身材高挑、自信无比的女性,拥有超凡的美貌。她头顶盔甲,还戴有圣洁的花环,手持光芒闪烁的武器,用来保护自己,或击伤敌人。她身披一件罗马式的长袍,袍上挂满了各式形制和图案的饰物,腰间还挽着一条缀满珠宝的腰带,闪耀奇光异彩。
她的长袍上的每一种装饰,光芒、图案、形制、色彩或珠宝,构成了修辞描述的各个方面,将让脑中印有此形象的学者们永世难忘。[19]况且,这位光彩照人的修辞女神形象,和偶像崇拜神(Idolatry)的可怕外表之间的对比是多么强烈呵,后者的形貌最初由5世纪时的神学家和神话学者富尔根蒂尤(Fulgentius)创造,后来又被14世纪的修士里德瓦尔(Ridevall)编成易记的拉丁文诗歌。由于偶像崇拜神被描绘成一个娼妓,她的头顶始终悬着一个高声鸣叫的喇叭,提醒人们她的到来。当偶像崇拜的话题被提及时,这个形象在人们心中就被唤起,她让人很快就想到神学教诲的关键点:她因为背弃了上帝,和邪异的偶像们私通,才会沦为娼妓;她既盲又聋,因为富尔根蒂尤曾说,最早出现的偶像,是奴隶们为了减轻丧子父亲的痛苦而模仿死去儿子做成的人像,而对于应该摒弃这类迷信的真信仰,她既看不见,也听不到。[20]
一个人头脑中的记忆宫殿里已经存储了多少这样的图像,它到底总共又能存储多少呢?利玛窦在1595年偶然写道,如果在纸上任意写下四百到五百个的汉字,他只要读一遍,就能按次序把这些汉字倒背出来,而他的中国朋友们则形容,他只要浏览一遍,就能把整卷的中国经典著作背诵出来。[21]然而,这种特长其实并不那么令人吃惊。与利玛窦同时代有一位长者——帕尼加罗拉(Francesco Panigarola),他可能在罗马或马切拉塔教过利玛窦记忆术,还写过一本讲记忆方法的小册子,其手稿至今还保存在马切拉塔图书馆。据他在佛罗伦萨的熟人们说,帕尼加罗拉头脑中存有十万个记忆形象,每一个都各就其位,任其择取。[22]而利玛窦则跟陆万陔说,根据他以前读过的讲记忆术的书,要让事物变得易记,最关键的是想象的建筑物中存放形象诸场所的次序:
处所既定,爰自入门为始,循右而行,如临书然,通前达后,鱼贯鳞次,罗列胸中,以待记顿诸象也。用多,则广宇千百间,少,则一室可分方隅,要在临时斟酌,不可拘执一辙。[23]
弗朗西斯·叶芝(Frances Yates)曾写过一本讨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记忆理论的著作——《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此书广博而精深,作者在书中深入探讨了“一种基督教化的人工构造的记忆究竟是什么样的”,但却遗憾地得出结论,“任何一篇讨论记忆术的论文,尽管总是给出了记忆的法则,但很少提供这些法则具体应用的例子,也就是说,它基本没法建立一个能存放记忆形象的体系”。[24]利玛窦的《西国记法》,这个中国版本的记忆法尽管无法完全弥补这个缺憾,但确实能让我们看到,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这种传统的记忆体系是如何被坚持下来的。
此外,利玛窦在《西国记法》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一组清晰的形象,每个形象都各就其位,按次序叙述。第一个形象是两个正在扭打的武士。第二个形象是来自西部的部族女子,第三个形象是正在收割谷物的农夫,第四个形象是一个怀抱婴孩的女仆。按照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用一种简单方式建立记忆体系,利玛窦选择把这些形象放置在某个房间的四个角落。这座房间是个大厅,面积相当之大,由立柱支撑。我将把它作为进入记忆宫殿的通道。陆万陔等初学者可以毫无困难地追随利玛窦开始这一个记忆的精神之旅。我们会看到他们一同向门走去,进入大厅,接着转向右边,逐个查看那些形象。[25]然而,一旦人们熟悉了这套方法,就没必要在一个建筑里构想出越来越多的厅堂或者房间,他可以在一个既定的场所放置更多的形象,以增加其记忆容量。唯一的危险就是,这个空间会变得相当杂乱,以至于头脑无法轻易从所有形象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不过,只要谨慎一些,他可以把更多家具搬进这个房间,或在某张桌上摆放金玉器皿,并把墙面涂上灿烂的色彩。[26]利玛窦说,人们还可以使用某些“图像”来唤起这些形象,就像昆体良在公元1世纪所要求的那样。同样,道尔齐(Ludovico Dolce)在1562年就曾建议那些对古典神话感兴趣的学生,只要熟记提香(Titian)某些作品那复杂精妙的细节,就能帮助他们学习神话。[27]利玛窦心里清楚,生动的插画对记忆有绝好的效果。从他的书信中看,他早就注意到了诸如纳达尔(Jeronimo Nadal)的《福音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Gospels)之类带有木版插画的宗教书籍,此书由耶稣会大量印刷,使信众对基督一生中每个重要的时刻都有鲜活生动的了解。他甚至还随身带着纳达尔此书的抄本来到中国。在他写给意大利友人的信中说,此书在他看来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28]
正如利玛窦在他的“记忆大厅”中存放了四个记忆形象一般,利玛窦还留下了四幅宗教图画,每一幅都有他亲笔写的标题,其中三幅还附有他的评论:第一幅画的是基督和彼得在加利利(Galilee)的海上,第二幅画的是基督与两位门徒在以马忤斯(Emmaus),第三幅画的是所多玛的人们在上帝派来的天使面前眼睛昏迷而倒地,最后一幅则是怀抱婴孩基督的圣母玛利亚。这些图画得以保存至今,应该归于利玛窦与程大约之间的友谊。程大约是一个出版商人和砚台鉴赏家,大约1605年在北京经朋友介绍与利玛窦相识,当时他正准备刊刻一部名为“墨苑”的中国书法与版画图集,非常希望在书中收入一些西方的艺术和书法作品,因此请利玛窦贡献若干。尽管利玛窦起初故意自谦地表示,中国士人学问广博,可能只会对西方文化的“万分之一”感兴趣,但他后来还是答应为之。结果,次年程大约刊刻出版精美的《墨苑》,收入了利玛窦所作的四幅画和评注。[29]我们可以确信,这些宗教画将《圣经》中这些生动的故事细节深深刻入中国读者的心灵之中,无论它们记录的是基督生活中的某些时刻,还是《创世记》中的片段。如果将这些画如同记忆形象一样精心排列,那么它们就能扩充记忆宫殿存储的数量,为它的建造添砖加瓦。
虽然利玛窦对他的记忆体系之价值确信无疑,但就在1578年他搭船远赴东方之前,这套体系在欧洲已经开始遭到质疑。学者阿格里帕(Cornelius Agrippa)尽管对魔法和科学炼金术很感兴趣,但他在1530年代出版的书《艺术与科学的虚幻和不确定性》(The Vanitie and Uncertaintie of Artes and Sciences)当中说道,记忆法中所捏造的“怪异形象”使得人们天生的记忆力变得迟钝,这种在人们头脑中塞入无止尽的信息碎片的尝试通常“不会使记忆更加深刻和确定,反而会引起疯狂和迷乱”。阿格里帕将这种炫耀知识的做法视为幼稚、好出风头。在1569年出版的英译本中,他这种厌恶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这是一件丢脸的事,这群无耻的人妄称要搞出一套新东西,但他们写的玩意就像商人处理货物,叫卖得越响亮,内心就越虚弱。”[30]诸如伊拉斯谟(Erasmus)和梅兰希顿(Melanchthon)这样的宗教思想家都认为,这些记忆体系其实来自早期修道士的迷信活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31]拉伯雷在1530年代也以极具感染力的讽刺手法,进一步质疑了这类记忆法。他在《巨人传》中描写了高康大如何在老师霍洛芬尼的教导下熟记了当时最深奥的语法著作,甚至还包括“捕风君”、“饭桶君”、“马屁君”等学者做的精深的全部评注。[32]结果是,拉伯雷郑重其事地写道,尽管高康大确实能将他读过的书“倒背如流”,“就像所有在炉中烘焙出来的人那样睿智”,但若有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一些机智的评论,那么“想从他嘴里掏出一个词来,比让死掉的驴子放屁还难”。[33]到了16世纪末,培根(Francis Bacon)本人对能够组织和分析资料的“自然的”记忆力量十分着迷,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种人为的记忆法作出明确批判。虽然承认这种记忆训练法所取得的效果在表面看来十分惊人,他称之为“非凡的卖弄”,但培根还是判定这类体系在本质上是“无益的”。“我没法估计出自己仅听一遍就能背诵出来的名字或者单词有多少”,他写道,“就像我没法知道自己会玩多少翻跟斗、走绳索之类的杂技把戏,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是身体上的,但都一样,奇异但毫无价值”。[34]
然而利玛窦时代的大多数天主教神学家,就像利玛窦一样,并没有被这些不敬的议论所劝服。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套体系的积极方面,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证实,早期记忆体系的关键性文本《致赫伦尼》并不是西塞罗所写,但他们无视这一点,依然将这本书作为他们课程的基本教材。[35]托马斯·阿奎那本人确信,记忆体系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先前人们认为的仅仅是修辞学的一部分。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中,阿奎那描述了“有形的比拟”——或称之为人像化的记忆形象——的重要性,因为它能防止“微妙的精神事物”脱离灵魂。而奇怪的是,当阿奎那试图强调使用记忆场所体系的必要性时,他指出西塞罗在《致赫伦尼》中曾说,我们“热切”需要我们的记忆形象。阿奎那将这句话的意义解释为,我们应当“胸怀爱慕地固守”我们的记忆形象,如此才能将其应用在虔敬的灵性事务中。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没注意到,《致赫伦尼》中说的是我们应该“单独”(solitude)选择我们的记忆形象,而不是“热切”(solicitude)。讽刺的是,阿奎那正是凭记忆引用了这句话,但他却引错了。这个错误却强化了将记忆技巧作为整合“精神意图”的手段这一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解释在当时传播极广。举例而言,只要明白记忆体系是用来“牢记天堂和地狱”,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乔托(Giotto)的肖像画,以及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叙述结构和细节。在16世纪出版的书籍当中,此类观念屡见不鲜。[36]
在阿奎那时代及之后两百年,有一类书籍撰述蔚为风潮,这类书通过激发信徒的想象力,增进其基督信仰的虔诚。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比如巴黎的威廉(William of Paris)在12世纪所写的《神圣修辞学》(Rhetorica Divina),其灵感就源于昆体良。[37]萨克森的鲁道夫斯(Ludolfus of Saxony)是14世纪一位极为虔诚的作家,他那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让后来的圣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为之深深着迷。鲁道夫斯竭力将他的基督徒读者带到耶稣受难的现场,将犀利的言语敲进读者的耳中,正如敲进耶稣身体的钉子:“当所有神经和血脉都被扭曲,骨骼和关节都被猛力拉拽而脱位之后,他终于被钉上了十字架。他的手脚都被粗糙而沉重的钉子戳穿,钉子刺透了皮肉、神经与血脉、骨骼与韧带,到处都伤痕累累。”[38]在这种情绪之中,“福音之声四处响彻”,鲁道夫斯教导信徒要“带着一种虔敬的好奇之心前行,感受通往主的道路,去触摸救世主的每处伤痕,他是这样的为你而死”,按鲁道夫斯征引的瑞典的布里吉特(Bridget of Sweden)的说法,耶稣身上的伤痕共有5490处。[39]作为天主教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的修士,鲁道夫斯倡导人们每时每刻都要将最活跃的想象力奉献于基督,“无论在行走或是站定,安坐或是躺卧,进餐或是饮酒,交谈或是沉默,独处或是群处之时”,都应如此。[40]到了15世纪中叶,在当时一本为奉教少女所写的书中,要求她们把《圣经》中的人物形象——当然不包括基督——与她们本人的朋友和熟人的脸一一对应起来,这样,她们就能将《圣经》人物深深铭记在心。作者还告诉这些年轻读者,要把这些形象放在她们心中的耶路撒冷,“为此建造一座你已熟悉的城市”。这样,每日她们“独自一人”在闺房中祈祷之时,《圣经》故事就会在她们眼前浮现,一幕一幕缓缓飘过。[41]
圣依纳爵·罗耀拉这个归信的西班牙军人在1540年创建了耶稣会后,为耶稣会成员们制定了一套宗教学习与训练之法,而这种生动的记忆重建正是训练法中的基本组成部分。他在写作《灵操》(Spiritual Exercises)一书早期的草稿时,就已经确定了这个观点,该书在八年后才定稿出版。为了使追随者能全方位地重演《圣经》叙述的场景,圣依纳爵教导他们,在凝思《圣经》情节之时,要充分调动五种感官的功用。在最初级的层次,从事这种操练的人们会在心中默想出某个特定事件发生的物理环境,或用圣依纳爵的说法,就是这个地方的“想象性重现”。[42]比如耶稣赴难途中走过的,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的道路,最后的晚餐所在的房间,耶稣被犹大出卖时所处的园子,耶稣受难之后圣母玛利亚等候的那间屋子,等等。[43]圣依纳爵说,在这些环境中,人们可以再加上听觉,从而进入更鲜明的画面,“听听,大地上的人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彼此交谈,在起誓,也在咒骂”,把他们的话与三位一体真神的言语比照,聆听真神的教诲,“让我们替大地上的人类赎去身上的罪”。在观看和聆听之后,人们可以在记忆活动里使用余下的感官,“闻闻那难以言表的芬芳,品尝那神性的无比甘甜吧,亲吻圣人们走过的路,紧贴他们坐过的地方,你们将从触碰中受益无尽”。[44]
如果说五种感官将过去的各个方面全部唤醒,并如原初的那样将其带到现实之中,那接下来就轮到记忆、理性和意志这三种能力登场了,它们要担负起将凝思的意义引向更加深入的重任,尤其当想象的主题在通常意义上是不可见的时候,更是如此,比如说“原罪的意识”等。于此,圣依纳爵说,“我们努力想象,制造出理念的图景:我的灵魂被囚禁在这个堕落的肉身之中,而我的整个自我,肉体与灵魂,都被判与这片大地上的禽兽们生活在一道,就如同流浪在异域他邦”(尽管这段话并不是专为传教士们所说,但我们能够推想,当利玛窦远离故土来到中国,难得寻到余暇来锻炼灵性修养时,这些文字一定给予他巨大的力量)。圣依纳爵又说,人们可以轮流使用这三种能力,但记忆应居于首位:
首先借助记忆,我会想起天使们的初罪;接着,我会运用我的理性对它进行思考;然后,我的意志将尽力回忆并思考,把我身上千千万万的罪恶与天使的初罪相比较:那原初的一重罪就使它们堕入了地狱,我满身的罪恶会受到何等的报应呵。一思及此,自己内心会激发出彻底的羞愧之情。记忆的作用,是让我们回想起天使们是如何满带荣耀被主创造出来,但它们却不愿全心全意地尊奉和顺从它们的创造者,它们的天主。它们沦为自身狂妄的牺牲品,从天堂一头堕入地狱,神的恩典离它们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满身的邪恶意志。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理性,我会更仔细地思考所有这一切;而借助于意志,我会努力唤起内心的高尚情感。[45]
每个从事这种操练的人,在反省自己的罪恶时,都会考虑最家庭化、最私密化的场景,比如思考自己不同时期在不同住所里的情况,考虑自己和所有他人的关系,反思自己在从事各种工作时的行为。这样,他就不仅仅是凝思天使们的初罪,而可以全景式地观看一场伟大的灵性战争,那就是基督和他的战士们对抗恶魔势力。[46]鲁道夫斯和圣依纳爵都极力主张,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将关于消逝的过去的“记忆”融入精神化的现实之中,这不仅呼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也合乎圣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思想,《忏悔录》在利玛窦出生前一千一百年就已写成,书中说:“我们恐怕得这么说:‘有三种现时:过去事物的现时,当下事物的现时,以及未来事物的现时。’”[47]然而,圣依纳爵同时代的天主教徒却在担心,圣依纳爵和他的追随者们祈求能获得一种洞察圣域的特别领悟力,这似乎有些过犹不及。巴伦西亚的主教就控诉说,《灵操》一书比“神秘货色的贩卖”好不了多少,它完全是在当时流行的光照派(Illuminist)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48]1548年,有六位神父宣称,通过这种灵性操练,他们已经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从而被宗教裁判所传唤审查:宗教裁判官很担忧,因这些神父声称“圣灵会降临他们身上,如同降临到使徒身上一样”。[49]到了1553年,有几名多明我会修士甚至攻击圣依纳爵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异端教徒”,这种指控激使圣依纳爵的友人纳达尔(即《凝思》一书的作者,利玛窦曾将该书介绍进中国)反驳道,圣依纳爵的思想直接来自《圣经》,而不是其他什么间接渠道。[50]利玛窦来华期间的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知晓这些争论,他更低调地对待圣依纳爵所说的“对感官的运用”,认为这是种“十分简单的状态”,无法和“凝思”及“祈祷”这些更复杂的形式相提并论。[51]
想在宗教经验和所谓的魔法力量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界线,从来都是很难的。近来有些学者认为,宗教与魔力之间的联系就存在于弥撒时的言辞和咒语当中,在于弥撒时的音乐、灯火、美酒中,在于人内心中的转变。[52]利玛窦在华的经历表明,在中国大众的心目中,很自然地认为他的记忆法来源于魔力。1596年10月13日,利玛窦从南昌给罗马的阿桂委瓦总会长写信,他在信中先是简要叙述,他进入南昌时,为了获准进城定居和购买房屋,与当地官员展开艰难谈判,然后又说道,有许多知名的中国士人蜂拥到他的住所表示庆贺。利玛窦认为,这些中国人到访主要有三个动机:他们相信耶稣会士能将水银变成白银,他们想要学习西方的数学,他们渴望学到利玛窦的记忆法。[53]
从当时欧洲的知识和宗教生活背景来看,利玛窦列出的这几项都是完全可信的。那时,记忆体系已经和命理学技巧以及半科学的炼金法术相结合,使得个中能手能获得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超越了惯常的宗教力量。我们应该记住,如果说,在某种层面上,我们要把利玛窦的事业置于天主教势力主动对抗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中,将其视为16世纪晚期依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枪炮推动的“欧洲扩张运动”的一部分,它才能获得意义;那么同时,我们还应该从一个更为古老的背景,也就是前文艺复兴时代的诸多方面来看待他的事业,这让我们回想起中世纪,甚至古典时代,回想起那个由基督教神父和懂得魔法、炼金术、宇宙学和占星术的“有智计之人”来共同抚慰人类心灵的世界。[54]
1545至1563年召开的特伦托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在教皇的授意下,对许多问题展开了漫长而复杂的讨论,其中或许解决了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是教会领袖们有感于天主教会的内部腐败以及新教对手的指责而提出来的。然而,这些“解决办法”只被一部分人接受,其他人依旧坚持己见。于是出现下面的情况便不奇怪:1584年,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磨坊主在被宗教裁判所审问时说道,上帝是在一片混沌中诞生的,而这片混沌中早已有了地、水、火、空气四要素。“那么谁在推动这片混沌?”审问者说。磨坊主的回答是:“它自己推动自己。”[55]磨坊主还说:“我的思想是崇高的,它期待着一个新的世界”,他解释说,自己信仰的动摇主要来自对世界其他地方和人们的了解,来自他所读的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的非洲和中国游记。[56]这个磨坊主尽管身份卑微,但仍可以作为例子,代表16世纪所有依赖自身寻求意义的人们。因为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的改革家们,都无法成功地解释世界起源的终极奥秘,也无法解释诸如强烈的精神消沉、灾难到来时人和动物的突然死亡、财产的散失和土地的歉收之类令人困惑的现象。[57]
因此,魔法和宗教之间的界线依旧很模糊。磨坊主更是发挥了他这套四要素理论:上帝为空气,基督是地,圣灵为水,而火则充盈着世界。[58]而他的一些同代人则更为可怜,他们梦想着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河流的堤岸是用意大利酸奶酪(ricotta)筑成,而天空中则雨点般落下意大利方饺(Ravioli)和杏仁糖。[59]至于利玛窦和他的友人,尽管他们否认任何施于事物之上的魔力,但却在1578年航经好望角遭遇狂风暴雨之时,把一个蜡质的小护身符抛进了海中,这个护身符的材料取自罗马复活节时的蜡烛。1601年,利玛窦在北京城外居住时,总是随身带着来自“圣地”的几粒泥土和一个小十字架,他坚信,这个小十字架是用当年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残片做成的。[60]而在已经公开“改革”新教的英国,热衷于耍弄魔法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有一个镇子里所有居民都住在离“魔法师们”十英里之内的地方。[61]
在那个习惯于从星空中寻找秘密的时代,人们对行星运行的每一个阶段、月亮的每一丝盈亏,以及每一颗新星的出现都尽力追踪,并仔细分析那会对人类的命运带来何等影响。有教养的男女尽管可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们的头脑中依然有一片区域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观念所占据,按某位史家所说,“未知的玄秘的影响力量”仍然在那里不时地“跳动”。[62]在此类观念之中,被视作理所应当的是,只要人们能够把宇宙的自然力与头脑中的记忆能力融合起来,便能获得特别的力量。即使在未受教育的穷人阶层中,在大部分以口头形式表达的文化里,超凡的记忆依然被视作理所应当的。例如,蒙田在1581年的意大利之旅中,曾经提到佛罗伦萨附近田野里的一群农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弹奏着鲁特琴,女伴们则立在一边,大段背诵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诗篇。[63]然而,在当时拥有超强记忆能力的人,马上会被周遭的人怀疑有魔力,就像发生在16世纪中叶法国南部的阿诺·杜·蒂尔(Arnaud du Tilh)[64]身上那样。[65]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对如何运用和增强记忆更是一点也不陌生。在哈姆雷特杀死了奥菲莉娅的父亲之后,奥菲莉娅跑到哥哥雷欧提斯面前哭道:“这株迷迭香能帮你牢记这一切,求求你,亲爱的,牢记这一切。”这并不完全是疯人之语,据当时许多关于记忆法的文献记载,迷迭香是增强记忆能力的灵药,奥菲莉娅希望借助它来坚定雷欧提斯复仇的意志。[66]
当利玛窦还是一名学童时,在他的家乡马切拉塔,有几名教士被指责玩弄邪恶的魔法,这或许和他们误用了记忆术有关,尽管我们并不了解这些人使用记忆术的详情。[67]但我们知道,整个16世纪,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等城市里,一些人投注了极大精力去创建“以占星术为中心的记忆法”,这些方法不仅在其家乡意大利风行,还被热切的首倡者们传播到了法、英等国。这些记忆法将宇宙间的所有力量都纳入“记忆的剧场”,或同心圆的图式,或是想象的城市之中,这样,这些力量能被直接利用,而操持这种技艺的人们则成为具有巨大潜能的“太阳占星师”。在1540年代,著名的意大利学者卡米罗(Camillo)这样布置他创造的“记忆剧场”:前台显眼的地方放着一堆小箱子,杂乱地堆着,里面塞满了西塞罗的所有著作。其后一直延伸到远处高台排列着宇宙万物的形象,正好表现“从创世到各色生灵的天地万物”,这样,剧场的主人就仿佛站在高山上俯瞰一片森林,不但看清每棵树木,也把握了森林的全貌。卡米罗解释道,“这种无与伦比的布置方式,不仅使我们能有恰当的地方存放事物、言语与行动,使我们在需要时立刻就能找到它们,而且也赋予我们真正的智慧。”[68]
这种智慧既不受限于言语的世界,也不受限于舞台。它在文艺复兴建筑的理论和实践当中都留下了自己的踪迹,它用“暗藏的线条”划分出空间,表达出庄重的感觉或是人类之爱的意味,为建筑物注入内涵,它用简单的石材表现出人像的完美比例与宇宙力量的结合。[69]它深藏在文艺复兴音乐的内心,记忆力量最初是通过字母系统和韵律来表达的,后来则被牢牢固定于旋律之中。在严肃理论家看来,这个过程会使得音乐在它的两种面目之间摆动,或是作为术数的神秘主义,或是作为科学。它既会在性别力量的领域发挥作用,也会成为一种特别的跨越国族的话语。所以,开普勒(Kepler)能够一面做着著名的关于行星轨道的探索,在神圣罗马帝国鲁道夫二世的宫廷里研究炼金术,另一面则提出新的音乐解释,即认为一段音乐中的大三度音程,代表着性爱中的男性角色,而小三度音程则代表女性。[70]而维琴蒂诺(Nicolo Vicentino)在1555年的一篇论文中,论述了他新制造的六键羽管键琴(archicembalo),他说,这种新乐器能够弹奏出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的声音,“世界上所有人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时,其音程变化不简单是一个或者半个全音,也有可能是四分之一全音,甚至更小,所以,用我们这种区分细致的键琴,就可以适应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发音”。[71]同样,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首先见到中国文字时,也被其所蕴藏的无穷潜能所震惊,这种潜能使其可以超越根植于语言中的发音差异。[72]
尽管这些事例纷繁各异,但都可说明在宽泛意义上的“反宗教改革”时期,有关记忆和记忆“力量”——无论是其本来的还是转换性的——的观念是何等多样。这使得我们很难相信,当利玛窦试图利用他的记忆法、西方科学知识以及深厚的神学训练来劝导中国人抛弃那种混合了儒教、道教和佛教的信仰之时,他会对同时代欧洲人由记忆法中得到的超越人类和自然的力量毫不在意。
在利玛窦著述中留存下来的这四个记忆形象,对于他的记忆宫殿里储存的无穷宝藏而言,其实只是吉光片羽。同样,他所绘制的四幅宗教画,也只是天主教圣像画传统的极小片段,这一传统在利玛窦努力想使中国人归信的天主教中具有核心地位。然而,既然利玛窦如此精心地选择了这些图像留之后世,而它们又奇迹般地流传至今,那么,现在我将使用这八块互不相干的碎片,来搭建起这部书。
1606年,利玛窦告诉程大约:“百步之远,声不相闻,而寓书以通,即两人者睽居几万里以外,且相问答谈论如对坐焉。”他是对的,正是通过这些偶然的遗存,我们得以进入他那个时代,我们深信,利玛窦也会赞同本书的写法,因为他曾这样和程大约说道:
百世之后人未生,吾未能知其何人,而以此文也,令万世之后,可达己意如同世。而在百世之前,先正已没,后人因其遗书犹闻其法言,视其丰容,知其世之治乱,与生彼世无异也。[73]
对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者而言,生活在伟大的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们是言行的典范。昆体良在那个伟大时代写下了他的记忆理论,而利玛窦则用两个扭打的武士作为第一个记忆形象,用加利利海开始他的图绘。这其中包含的相似性代表了利玛窦文雅的呼应:昆体良早就说过,通过矛和锚的形象,战争和大海应该成为人们最先记住的东西。[74]
当我们跟随利玛窦旅行时,应当牢记他那“古典的”过去和他的中国现实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最著名的罗马记忆法书籍曾提到,人们应该在自己创造的形象序列中做一些标注,或者说,每五个或者十个一组,设立一些标杆,比如说,一只金色的手可以提示我们数字“五”,而一个名叫德西莫斯(Decimus)[75]的朋友则能让我们联想起数字“十”。[76]利玛窦把这种教导融入他的中国形象的序列安排之中,并且将其与劝人归信天主教这一目标结合在一起,要知道,他的所有智慧与精力都倾注于这个目标。他取得了一种只有在汉语的书写体系中才可能产生的精巧成果。他建议中国读者,每十个记忆场所都应简单地标一个汉字“十”的记忆形象,而不是金色的手或者叫德西莫斯的人。[77]
这个想法的精妙之处在于,数字10在汉语中被写成“十”,中国人通常用它来表示两条线相交的物体或者场所,比如一个木架子或一个交叉路口。正源于此,最早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7世纪就来到中国,正是用“十”来称呼基督的十字架。到了13世纪,征服中国的蒙古人开始正式使用这一称呼,而在16世纪来华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也沿用之。[78]因而,当明代的中国人跟随利玛窦穿过他的大厅,欣赏过他的图画,逐步进入记忆宫殿的深处时,指引他们的并非只有十进制的记忆法则,还有十字架这个符号所代表的不容异己的神学象征。
注释:
[1]利玛窦:《西国记法》,第20-21页。现存唯一的《西国记法》版本将利玛窦列为作者,校订者是朱鼎瀚,编者包括高一志(Vagnoni,见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6位)和毕方济(Sambiasi,费赖之《列传》第40位)。关于撰写地点,参见《利玛窦资料》(Fonti Ricciane,以下简称FR)第1卷第376页,注6。朱鼎瀚是一位皈依天主的本土信徒,山西人,现存《西国记法》版本唯一的序文由他撰写。朱在序中说,“高先生”是利玛窦记忆术的主要传人,我假定这里的“高先生”即高一志。Vagnoni在1624年返回中国,居于山西某城,亦即朱鼎瀚所在之地,在那里他才开始用“高一志”这个中文名字。高一志早年成为见习修士后,曾在都灵教过五年修辞学,日后他成为一个杰出的汉语学者。他可能是在南京的时候抄录了一份利玛窦的手稿,之后在澳门作了修订,随身带到山西,并在1624年之后的某个时候拿给朱鼎瀚看。(参见费赖之《列传》第85与89页,其中关于高一志生平的详细介绍,应可支持此处推断。)从现存文本看,可以推测,高一志并没有改动利氏基础性的六章论述,但在第六章末尾,增加了较长篇幅的例证,见第28-31页(再版本第63-69页)。高一志或朱鼎瀚有可能在第四至第六章中也增加了一些例证,因为朱鼎瀚在序文中说,利玛窦的解释经常是不清楚的。由于两人同居绛州(译注:原文为Jinjiang,即“晋绛”,山西绛州),高与朱自然合作校订,但这里仍难确定具体时间。高一志逝于1640年,朱鼎瀚在一年后去世,因为文献中纪念作为秀才去世的他是在1641年(《绛州志》第8卷第29页)。毕方济在《记法》一书编订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并不清楚,他在1628年确实到过山西(费赖之《列传》第138页),但在绛州待的时间不会长,如果他去过那里。《记法》出版之许可是由阳玛诺(Emmanuel Diaz the younger)许可的,他在1623年被任命为中国传教区的副区长,1659年在杭州去世。
[2]《西国记法》第21-22页。
[3]这段文本见《西国记法》第17-18页。最后一句中有一字无法辨认。很明显,利玛窦此处是翻译自西塞罗著作De Oratore(2/86)中的著名段落,在Lyra Graeca(2/307)中也引到过。叶芝在其《记忆术》一书中也讨论过西塞罗的原文,见第17-18页。
[4]有关利玛窦生平行事的概要,英语文献中可以参看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所记,见《明代人物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以下简称DMB),第1137-1144页。而比较详细的论述可见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George Dunne,Generation of Giants)、克罗宁《西泰子来华记》(Vincent Cronin,Wise Man from the West)、哈里斯《利玛窦的传教》(Harris,“The Mission of Matteo Ricci”)。在法语中,费赖之的《列传》(Notices,第9位,第22-42页)依然是有用的,详细的考察可见裴化行(Henri Bernard)的《利玛窦神父传》。最近又有一个意大利语的利氏生平概要,还附有较好的参考书目,见Aldo Adversi的“Matteo Ricci”,载于Dizionario Bio-Bibliogra?co dei Maceratesi;而最详尽的意大利语传记还是FernandoBortone的P. Matteo Ricci, S.J.,其中附有地图、相片和插画。以上所有著作,主要利用的都是一个核心材料,即利玛窦的《中国札记》(Historia),此版最初由汾屠立(Tacchi Venturi)转抄出来,德礼贤(Pasquale d'Elia)修订后以《利玛窦资料》(FR)之名重刊。利玛窦《中国札记》的金尼阁(Trigault)版本(由Louis Gallagher英译)相较原文,充满了金尼阁的曲解、删改和添加,并不是利玛窦想法的忠实反映。中文世界里有林金水最近的论文《利玛窦在中国》,尽管不幸的是极为倚重金尼阁(Gallagher译)的版本,但对基本问题还是有周全的把握。有关当下台湾的利玛窦研究,在《神学论集》的专号(第56号,1983年夏季)收录有许多利玛窦中国传教的论文。
[5]有关《交友论》成书细节,参见利玛窦的书信,汾屠立编辑的《书信集》(Opere Storiche,以下简称OS),第2卷,第226页,1596年10月13日给阿桂委瓦会长的信。在信中利玛窦提到,编写该书是在“过去一年”(l'anno passato),并把这写作看做“一种修习”。由于在利氏1595年11月4日给阿桂委瓦的信中(OS,第210页)没有提到完成此书,成书应在11月或是12月。尽管原始资料证据清晰,但成书日期问题曾引起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参见德礼贤“Further Notes”,尤其是359页,方豪《利玛窦交友论新研》以及“Notes on Matteo Ricci's De Amicitia”;方豪指责德礼贤在语言能力上无法胜任研究(《新研》,第1854页),而德礼贤的反击认为方豪是明显的抄袭(“Further Notes”,第373-377页),后者即使没有获胜,至少也占了优势。
[6]见OS,第211页,1595年11月4日信。“我已经开始向许多人教授记忆体系法”。
[7]见FR,第1卷第376页。利玛窦在1596年10月13日写给阿桂委瓦的信(OS,第224页)中说,“对于当地的记忆法……我用他们的语言写了本小册子,做了些说明,我把这书送给了巡抚,给他的儿子用”(Per la memoria locale…feci in sua lingua e lettera alcuni avisi e precetti in un libretto, che diedi al vicere per il suo ?gliuolo),利玛窦在FR(第1卷第363页)中提到,巡抚实际上有三个儿子。
[8]陆万陔的传记可以参考他的平湖同乡过庭训所著《本朝分省人物考》,卷45,页32b至33b。有关他仕途和成就的更详细内容参见《平湖县志》第15卷第37页(再版第1431-1432页),《平湖县志》第13卷第5页(再版第1176页)所记表明陆万陔在1568年的进士考试中名列二甲第二十一名。
[9]关于陆万陔儿子们科举考试的成功,《平湖县志》第13卷页7a(重印本第1179页)记载其子陆键在1607年成为进士。陆家这代人其他几个的情况也见《平湖县志》和《嘉兴府志》(第45卷第75-85页,传记见第58卷)。有关炼丹术师、机械学、船只舵手和观星家记忆术的押韵诗篇,参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5卷第4部分第261页,第4卷第2部分第48页、528页,第4卷第3部分第583页。本书第五章会列举中国历史上的记忆名家。
[10]OS,第224页。1596年10月13日写于南昌。
[11]OS,第235页。1597年9月19日写给Lelio Passionei。
[12]Monumenta Paedagogica, p.350. 其中记载,“Cypriani修辞法”在每堂课上都被推荐。
[13]Soarez, De Arte Rhetorica, pp.58-59.
[14]将普林尼的《博物志》(第7卷第24章,Loeb版第563页)与利玛窦的《西国记法》(第14页)进行比较,Monumenta Paedagogica(1586年,第350页)表明,普林尼的《博物志》是耶稣会学院的一本指定读物。普林尼的这段话,在博尔赫斯的精彩故事《博闻强记的富尼斯》(Jorge Borges,“Funes the Memorious”)中发挥了跳板作用。
[15]Ad Herennium, p.221.
[16]Quintlian, Oratoria, 4/223. “大水池”(the impluvium)是罗马庭院中央一个大蓄水池。
[17]这里我使用的视觉词汇在文艺复兴传统中颇为常见,其中三种词汇记忆术在《记忆术辞典》(Dictionary of Mnemonics)中被当作例证,即“骨骼”(第18页,第1个),“细胞分裂阶段”(第21页,第2个),“神经”(第57页)。至于“祖鲁人”和“法国女人”我用的是单数,这可能是文艺复兴的记忆术中比较喜欢用的。
[18]Stahl and Johnson, Capella, 2/7, and n.18. Yates, Art of Memory, pp.63-65.
[19]Stahl and Johnson, Capella, 2/156-157(稍作改动)and p.156 n.13.
[20]Smalley, English Friars, p.114. 完整引用了里德瓦尔的短诗“Mulier notata, oculis orbata,/ Aure mutilate, cornu ventilate,/ Vultu deformata, et morbo vexata”,Yates, Art of Memory, p.241. 其中为Smalley引用里德瓦尔的这段话作了漂亮的注解。
[21]在OS(第155页)和FR(第1卷第360页,注1)中,利玛窦描述了自己的记忆本领。在OS(第184页)中利玛窦给出了记忆汉字的数目。亲眼见证的中国人包括李之藻,参见他给利玛窦《畸人十篇》作的序,第102页;还有朱鼎瀚,他在利玛窦《西国记法》的序文中引用了徐光启的说法。尽管《明史》中并无朱鼎瀚的传记,但在《绛州志》(1776年版本,第8卷第29页)中提到他是一个年长的秀才,1641年的岁贡生。
[22]见FR,第1卷页377n,这说明帕尼加罗拉是利玛窦的材料来源。参看马切拉塔的帕尼加罗拉稿本,Yates, Art of Memory, p.241 引到过一份1595年的佛罗伦萨手稿,论述帕尼加罗拉的记忆能力。
[23]《西国记法》,第22页。
[24]Yates, Art of Memory, pp.62 and 26.
[25]《西国记法》,第16-17页,第22页。我将汉字“室”翻译成“reception hall”。
[26]《西国记法》,第27-28页。
[27]《西国记法》,第22页。Quintlian, Oratoria, 4/223. 关于道尔齐,见Yates, Art of Memory, p.166.
[28]OS,第260和283页。有关纳达尔的著作,参看此书讨论:Guibert, Jesuits,pp.204-207.
[29]利玛窦:《利玛窦题宝像图》,第2篇第4页,程大约:《程氏墨苑》,卷3第2篇,Duyvendak, “Review of Pasquale d'Elia” pp.396-397.
[30]Agrippa, tr. Sanford, p.25 recto.
[31]Yates, Art of Memory, p.133.
[32]这三个学者是“Bangbreeze, Scallywag, Claptrap”,都是拉伯雷为了讽刺而虚构的人物。
[33]Rabelais, Gargantua, tr. Cohen, ch.14, pp.70-72. 还可参考此书丰富的讨论:Thomas Greene, Light in Troy, p.31.
[34]Bac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bk.2, sec.15, 2, in Selected Writings, p.299. Paolo Rossi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记忆术对于“新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第210-213页。
[35]Monumenta Paedagogica,1586年版仍然将其列入,第350页。最早否认此书作者为西塞罗的文献出现于1491年(Yates, Art of Memory, pp.132-33)。
[36]Yates, Art of Memory, pp.72-104. 尤其在第86页讨论到将“solitudo”误读为“sollicitudo”,还有第101页讨论乔托。Richard Sorabji在《亚里士多德论记忆》(Aristotle on Memory)一书中翻译了亚里士多德论记忆问题的原始文本,并做了精心注释。
[37]Guibert, Jesuits, pp.167-168.
[38]引自Bodenstedt的译文,Vita Christi, p.121.
[39]Conway, Vita, pp.38 and 127, Bodenstedt, Vita Christi, p.50.
[40]Conway, Vita, p.125 引到过。
[41]参看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 p.46. 其中引到过1454年“Garden of Prayer”。
[42]Ignatius of Loyola, Exercises, par.47. 在以下几页的段落中,我试图顾及Gilbert在Jesuits一书(第167页)中的告诫,Gilbert说,根据圣依纳爵·罗耀拉所倡导的方法去讨论他这个人,就像用外表颜色来定义一架火车头一样。我同样注意到Hugo Rahner的评论,参见Ignatius the Theologian, pp.181-183.
[43]Ignatius of Loyola, Exercises, par.192, 201, 220. Rahner, Ignatius, p.189. 后书把这些场所当做象征符号来讨论。
[44]Ignatius of Loyola, Exercises, par.107, 108, 124-25.
[45]同上,par.50.
[46]同上,par.56, 140-46. 关于圣依纳爵和感官能力,还有相反的评述,参见Barthes,Sade, Fourier, Loyola, pp.58-59.
[47]Augustine, Confessions, p.266.
[48]Rahner, Ignatius, p.158. Wright, Counter-Reformation, p.16.
[49]Rahner, Ignatius, p.159.
[50]同上,pp.161-62.
[51]同上,p.191.
[52]Wa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p.36 and pp.70-71 讨论魔法。Thomas, Decline of Magic, p.33.
[53]OS, p.223.
[54]Thomas, Decline of Magic, pp.178-80.
[55]Ginzburg, Cheese and the Worms, p.56.
[56]同上,pp.83-84.
[57]Thomas, Decline of Magic, pp.75-77. 这里引到的例子来自此书第14页,第8章以及第536页。
[58]Ginzburg, Cheese and the Worms, p.105.
[59]同上,pp.13-29.
[60]参见本书第三章及以下,讨论大海和护身符。FR, 2/121提到了圣物和这件十字架,后者由“带着基督祝福的多个十字架”(molti pezzi della Croce di Cristo benedetto)组成的。Thomas, Decline of Magic, p.31 曾谈到过历史上对于蜡质的神羔(Agnus Dei)法力之信仰。
[61]Thomas, Decline of Magic, p.247.
[62]同上,pp.333, 578.
[63]Montaigne, Journal de Voyage, p.349.
[64]这个Arnaud du Tilh,是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名著《马丁·盖尔归来》中冒名顶替马丁· 盖尔之人的真名。
[65]Davis,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p.37. 可以参看她对魔法和记忆的其他评论,第60、72、102、107页。
[66]Hamlet, act.4, scene 5, lines 173-74. 可以参看Grataroli在De Memoria一书(第58页)中提到的配方,还有Fulwood的1573年著作,英译本见E5页。
[67]Paci, “Decadenza,” pp.166, 194, and 204 n.400.
[68]Yates, Art of Memory, 引文见第147页,“记忆剧场”见第136页,作为“占星师”的卡米罗见第156页。也参见Wa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第141-143页讨论卡米罗,第206和236页讨论坎帕内拉(Campanella)和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Yates, Art of Memory第11、13、14章详细讨论了布鲁诺的体系。巧合的是,对布鲁诺异端的审判和对磨坊主Menocchio的审判发生在同一时间,前面已提到,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Cheese and the Worms)书中也注意到这点,第127页。
[69]Hersey, Pythagorean Palaces, p.84 讨论“暗藏线条”,pp.96-105讨论人像。
[70]Winn, Unsuspected Eloquences, pp.51, 58-59. Walker, Studies in Musical Science, pp.1 and 2, 53; 此书第67页分析了开普勒的Harmonice Mundi中的性别形象。
[71]Winn, Unsuspected Eloquences, p.167, 引文见pp.178-79.
[72]OS, pp.27-28, 见1583年2月13日从澳门给Martin de Fornari的信,有关Acosta在1590年的著述中将中国象形文字视作“天生就促进记忆的密码”,参看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1, bk.2, pp.806-7.
[73]利玛窦《利玛窦题宝像图》,第2篇,第1b至2页。还可参考Laufer, “Christian Art in China”, pp.111-12; Duyvendak, “Review”, pp.394-95.
[74]Quintlian, Oratoria, 4/221 and 229.
[75]decimus在拉丁语中意为“第十”。
[76]Ad Herennium, p.211; Yates, Art of Memory, p.23.
[77]利玛窦《西国记法》,第22页。
[78]FR, 1/112 n.5 and 113 n.6 当中给出了例子。Barthes, Sade, Fourier, Loyola, p.28. 其中讨论到,萨德以一种带讽刺意味的反转方式给经典排序,其中年老修女们以“十年”排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