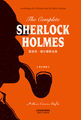诺里奇之行是一个转折点:它改变了一切。有关这次出行的行程我记忆寥落,只有通俗的福祉感觉,但这种福祉感像是往酒杯里添酒一样,似乎在我内心深处逐步聚集,不断升及更高的平面。平时,买衣服的过程让我恼火,因为我对我的外貌不怀什么虚荣,我也没有理由虚荣。我看上去那么热,竟成为人们逗乐的谈资,这才让我深信外貌对我十分要紧,我感到装束不可小觑。某种意义上说,我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就真的是什么样子,这个观念是对我的一个启示,而启示之初就叫我悔不当初。玛丽安告诉我某件衣服适合我而另一件不适合我(她从来没有过片刻迟疑),我意识到关于衣服,她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它们必须看着舒服而不是穿着舒服,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尽管这种感情很快就消失,但它的那种甜蜜我至今记得。我回来后,不仅觉得做我自己是件荣耀的事,而且私下里对我的相貌很是满意。
我们是在文瑟姆大街少女首领饭店吃的午饭,这对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机,因为即便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上饭店吃饭也被看作是莫大的奢侈:如果我们要出去吃饭,那也总是在某家寻常餐馆。
我们从布兰汉庄园出发得很早,赶在午饭时分我们几乎采购完了全部物品。我们把东西一包一包放进马车里,直到我们前面的座位堆得满满实实。我几乎不能相信它们大都是给我的。玛丽安问我:“你是想要现在就把自己装扮起来呢,还是愿意等到我们回到家?”我至今仍能记得这个问题给我造成的那种难决难断;最后,为了延长美好的期待,我回答说我要等。诺里奇那时间肯定酷热无比——因为当我们后半日去看温度计的时候,它依旧停在83度,之前比这还要高——但纵使我全副冬装,竟记不得有过热的感觉。
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至于留给我的印象是翅膀闪动和光芒闪现,像是鸟的飞翔带动空气流动,像是猛冲俯下又扶摇直上,像是模糊的彩虹缓缓地被白昼的清亮所包裹?
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她在场,而且,当午饭后她放我自便,要我在教堂里玩耍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的狂喜情绪仍在继续。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能见到她;然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我与周围环境如此和谐融洽,就好像整个建筑在奋力向上,升至它闻名遐迩的穹形屋顶,以表达我所感觉到的欣喜。后来,我离开教堂内阴暗的凉爽,走进户外的阳光和炎热,那里属于坟地巷,令我十分着迷的名字。我不断地伸长脖子,以便确定那个点,教堂的塔尖刺入天空的那个准确的点。
啊!高度!她要我在托马斯·布朗爵士的雕像旁与她会合;为了不迟到,我早去了一阵子;马车和拉车的两匹马停在那里,车夫扬起马鞭向我致意。我绕着雕像打转,心里想着托马斯·布朗爵士是什么人物;我又不好意思登上马车,坐在那里俨然一副车主的架势;然后,我远远地看见她在广场另一边。她看着像是在跟某个人道别,至少我对高高举起的礼帽有印象。她慢慢地朝我走来,在慢慢悠悠的交通涡流中穿行,直到很近很近了才看见我。接下来她挥动着她满是褶皱、满是泡沫边饰的阳伞,加快了脚步。
我的精神转变发生在诺里奇:正是在那里,我像一个正在破茧的蝴蝶,首次意识到了我的翅膀。我得等到喝茶时间才能让大家认可我自己的完美形象。我的出场赢得了高声的欢呼喝彩,就像这整个喝茶聚会专为这个时刻而鲜活。我的周围弹射起来的不是喷气火焰,而似乎是股股喷泉。我应要求站在一把椅子上,像一颗行星一样旋转,与此同时,我的整套新装,凡是可以让人瞧见的,都无一例外受到评判,或欣赏,或打趣。“领带你是从查洛店买的吗?”德尼斯大声嚷嚷,“如果不是从那里买的,我就不掏钱了!”玛丽安说了声是,而事实上,我后来发现那条领带上标着另外一个名字:我们进去过的店铺多了去了!“他看上去是个多帅气的顾客啊!”有人风趣地说;另一位说:“正是,就像一根黄瓜,是属于同一类别的绿色!”他们在讨论我的新衣服属于哪一种颜色。“林肯绿【13】!”又有一个声音说。“他也许就是罗宾汉!”那个叫法让我好高兴,我看到自己带着圣女玛丽安在绿林中走来走去。“你难道不觉得你不一样了吗?”有人问我,这问话近乎让人愤慨,好像我不承认似的。我高声宣称:“感觉到了,我觉得我成了另一个人!”——事实远远不光是这些。听了这话他们都笑。话题逐渐从我身上移开,像今天一样,议论不会总是围绕孩子们。于是我意识到以我为中心的时刻结束了,我很不自在地从我的椅座上移下来,但那个时刻是多么刻骨铭心啊。莫兹利太太说:“过来,宝贝,让我更近地瞧瞧你。”我局促不安地向她走过去,像一只虫子一样被她眼睛里射出的光束俘获,那是黑色的探照灯,压力和强度从不改变的探照灯。她在手指尖间拿捏搓揉着柔软轻巧的衣服面料。“我觉得这些烟灰色的珍珠纽扣很不错,你觉得是这样吗?是的,我觉得做得相当不错,我希望你妈妈也能这样想。”她转向她女儿,就好像我和我关注的东西对她不复存在。她继续说道:“你找到时机办我委托给你的那些小差事了吗——那些下一星期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办妥了,妈妈。”玛丽安说。
“你给你自己买了些什么吗?”
玛丽安耸了耸自己的肩膀。
“哦,没买什么,妈妈;我的可以拖一拖。”
“你不能拖得太久,”莫兹利太太平静地说,“我想你在诺里奇没有会见什么人吧?”
“连只猫都没见着,”玛丽安说,“我们一直在赶时间,对吗,利奥?”
“是的,我们在赶时间。”我回答,我太希望与她说一样的话,致使我忘了我在教堂里过的那一个小时。
夏天从我的敌人变成了我的朋友:这是我们诺里奇购物的另一个成效。我感到我可以在炎热里游刃有余,我在炎热里游来荡去,好像是在试探一种新的自然环境。我喜欢观看炎热闪着弱弱的光从地面升起,浓浓地挂在七月发黑的树梢上。我喜欢炎热所带来的,或者看似是炎热带来的,那种悬浮的动感,把自然界的一切都简化成无声无息的思索。我喜欢用手触摸它,在喉咙里感受它,体会它绕膝的感觉,我的两膝这时候已完全裸露待它拥抱。我巴望着要远行,更深入地走进热里,实现同它紧密的真实的接触;因为我觉得我经受炎热的经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循序渐进的,如果温度一味地变得越来越热,那才说明热有一个中心,是我应当到达的中心。
我的绿色套装,缀着烟灰色的珍珠纽扣,领口敞开,轻柔地依偎着我,我的薄薄的内衣用轻拂爱抚着我,我的长筒袜薄得几乎不足以保护我的腿免受划伤,我的低靿鞋是我特殊的骄傲——这一切我觉得只是我从物质形态上与夏天完全融合的第一步。它们会一项接一项地被我丢弃——以什么样的顺序丢弃,我对这个问题颇费心思,但决定不下来。我最终脱尽衣服全裸之前,哪一件衣服会成为我最后保留的呢?正像我所有关于性的意识一样,关于体面的见解,我思路不清,张冠李戴;尽管如此,我的想法已足够明确,足以使我渴望那种自由,将体面与衣服一道彻底丢弃,像一棵树或是一朵花一样,在自己与大自然之间无遮无隔。
这么多关于实现裸体主义的向往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也许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它们能否变为现实。与此同时,在我的意识的另一个层面上,我的新装束给我带来的自豪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与世界的关系。新衣服总是一层精神滋养,而我得到我的新衣服的情景使它们成了超级精神滋养。我自我感觉高大,我精心装扮自己,但我也不是怠惰于表达感激或敬畏,而这时间我的感激和敬畏两种情感都被唤醒了。礼物让我感激——当我受赐如此庄重的承诺和友好的赠予的时候,我的赞助人怎么可能不看重我呢?而我又怎么可能不看重他们呢?赠予方式让我敬畏:价格不菲的账单漫不经心地集聚,从一家店铺积累到另一家店铺,好像钱就不是钱!花费好比上帝;它属于另外一种状态的生灵,那个状态的生灵比我所熟悉的生灵更为富足。我的思维能力不能掌控它,但我的想象能力却可以随意摆布它;因为我的思维会把它所不理解的东西搁置一边,我的想象却与思维不同,它喜欢参悟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以类比的方式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我这里就有现成的想象的一例。这些辉煌的人们,因为有金币而金光闪闪【14】(我想他们有的是面值1.05英镑的基尼[11]),他们来了,住下了,又走了,显然他们不受家庭纽带和劳动关系的约束,他们是世界公民,他们把世界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他们可以放浪一笑让我痛苦,莞尔一笑让我快乐(我没有忘记这种经历),世界尽在他们的管控之中——这些人几乎不逊于黄道十二宫中令人崇敬的神话人物,他们离黄道十二宫中的人们只小小一步之遥。
我的服装中有一套泳装,部分地出于裸体主义的激励,部分地是因为我在遐想我自己穿上它(与玛丽安一起度过的那一天使我在许多方面有了自我意识),我非常想把它穿上。我承认除非有人挽着我,我是不会游水的,但玛丽安说她会安排这档子事。然而,恰在这时,我的女主人莫兹利太太果断阻止。我妈妈写信给她说我身体柔弱,容易感冒;她不会在未首先征得我妈妈许可的情况下负起让我游泳的责任。但当然,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观看其他人游水。
一场游泳聚会正在酝酿,我正好有时间写完信,然后下楼加入他们的行列。那是十四日,星期六——从气象学角度看是令人失望的一天,因为温度计(我这时候盼望它飙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示竟然不到76度。但这是一个只有我与马库斯还有他父亲分享的秘密,其他人对事态的真相毫不知情,大声抱怨着老天的酷热。我顺便带上我的泳装,以便不背离整个聚会的精神。马库斯也带了泳装以供使用,尽管他像我一样不会游泳。我遗憾地意识到我们俩的泳装都没有给裸体主义做出让步;我试穿上我的泳装,遮体太多,令人失望,马库斯的泳装也是这个样子。
之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大人们的游泳聚会。游泳聚会倒也没有什么新意,因为那个时候,游泳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人的消遣活动,同今天相比,那时候的游泳一词表示的是一种更为紧张激烈的经历。我那时对它充满好奇,又几乎是满怀恐惧——想到把自己置于从无涉足、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的包围之中。我对游泳的了解只是间接的,但我觉得我的皮肤有刺痛感,我的肠子在轻轻地下坠。
我们沿着小路结队而行,一行六人——玛丽安和德尼斯,还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的名字我记在日记里,但他们的相貌我想不起来了——我和马库斯殿后。时间大概是六点钟,但炎热依旧没有退却的意思,算不得骄阳似火,但赤日炎炎,温和而执着。我们穿过一个侧门进入一片林带。在炎热的日子里,我经常会从阳光下穿入树林;但我再也没有过类似这一次的酷热继以冰冷的印象。树木又浓又密,紧裹在我们周围;寂静也会互相感染,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我们来到了树中间的一条小路,沿路走一程,然后爬下一段陡峭的树木成行的河岸,走过一段台阶,进入一片草地。离这场经历又近了一步!在受到新一轮炎热的进攻的当口,我们又开始了交谈。马库斯说:
“特里明厄姆今晚就来了。”
“哦,他要来吗?”我回答说,不是对这人很感兴趣,而是在意我日记中要记入的名字。
“是的,但迟了,我们那时间已入睡了。”
“他是个好人吗?”我问。
“他是个好人,但相貌丑得可怕。当你看见他的时候,不要流露吃惊或是别的什么表情,否则会让他难堪的。他不希望你怜悯他。他在战争中受伤,他的脸没有复原,人们说那永远复原不了了。”
“倒霉。”我说。
“是倒霉,但不许对他本人这么说,也不许对玛丽安这么说。”
“为什么不许说?”
“我妈妈不喜欢这样。”
“为什么不许说?”我又问了一遍。
“答应我,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即便受到酷刑也不说出去。”
我答应了他。
“我妈妈想让玛丽安嫁给他。”
我在沉默中咀嚼这个消息,它让我极为难受。我嫉妒特里明厄姆,剧烈的嫉妒感。他是一名战争英雄,这个事实并没有赢得我对他的推崇。我父亲反对战争到了支持布尔人的地步。【15】我已经蛮有实力,可以放声高唱《女王的士兵》以及《再见了,多莉,我必须上前线》等歌曲,当听到烈女史密斯获释的时候,我激动得近乎疯狂;然而我相信我父亲是对的。也许特里明厄姆是活该破相。而为什么莫兹利太太想让玛丽安嫁给一个丑得可怕,甚至不配称先生的男人呢?
我们踏着一段凸起的堤道,穿过那片草地,去往一排弯曲排列的灯芯草丛,这条曲线是凹进的,我们要去的是凹进最深的那一部分。这里是诺福克的一处生长着沼泽棉的青苔湿塘地;尽管酷热难耐,万物萎靡,行人还须谨慎择路,以躲开那些水色微红、丛草半蔽的池地。咯叽咯叽,响声乍起,一股棕色的泥浆细流爬过了我的低靿鞋。
在我们前方有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满是横杠、竖杆、立柱,像一座绞刑架。【16】它辐射出一种恐惧感——也散发着强烈的孤独感。它像是一个不可靠近的东西,一个可能逮住你进而伤害你的东西;我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径直朝着它走,无所顾忌。我们几乎走到了,我都看得到它上面的沥青脱落得斑斑驳驳,且意识到这一定是多年无人理睬的结果,这时候,一个人的头和肩从灯芯草丛中出乎意料地伸出来。他背对着我们,没听见我们的声响,踏着台阶不慌不忙地走上了转盘和滑轮中间的平台。他走得很慢,沉浸在独处的欣喜当中;他抡圆胳膊,耸动双肩,好像是要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纵使他身上没有穿戴什么可以限制他活动的东西:有一阵子,我以为他是裸身的。
有一两秒的时间,他站着几乎纹丝不动,只试探着抬起他的双脚;接着他两手高举,舒张全身,展成弧形,随即消失。听到了水花四溅的声音,我才意识到河已近在眼前。
大人们在沮丧中相互瞪着眼睛,而我们又冷眼瞪着他们。沮丧演变成了恼恨。德尼斯说:“好没道理,我想整个这地方都是我们的,他应当知道他自己侵入了人家的领地。我们该怎么处置?责令他离开?”
“他不可能无所顾忌,他在这里自有他的道理。”另外那位年轻男子说。
“好吧,我们给他五分钟时间让他离开,可以吗?”
“我不管你们做什么,我要去换衣服了,”玛丽安说。“换衣服要花好长时间的。我们走,厄拉利(这是她朋友的怪怪的名字)。那里是我们的游泳操控设施——不好看但好用。”她指着灯芯草丛中的一间茅屋,跟许许多多茅屋一样,这一间也看着像个废弃的鸡舍。她们走了,留下了我们来面对眼前的情势。
我们彼此互相看着,拿不定主意,接下来不约而同地穿过灯芯草丛朝着河岸推进。到这时候,河依然是隐藏起来的。
忽然间,风景变了。河成了主角——我应当说是两条河,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不同的水流。
从我们立脚的水闸上游看,河是从那条林带的荫翳里流出来的。它流经杂草丛,流经灯芯草丛,时而发绿,时而发黄,时而金光灿灿;砾石闪着微光,看得见鱼在浅水中冲来奔去。水闸下游,河水开拓成了池塘,像天空一样蔚蓝。没有一根杂草污损它的表面,只有一样物件击破水面:入侵者一上一下浮动的头颅。
他看到我们了,便开始向我们游来;他两臂分水,上白下棕。很快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脸了,他的眼睛紧盯着我们,面带游泳人惯有的紧绷绷的表情。“哎呀!那是特德·伯吉斯,”德尼斯压低声音说,“黑土农场的佃农。我们不得对他动粗——一方面,河对岸就是他的地;另一方面,特里明厄姆不希望我们对他无礼。你们瞧瞧,我对他还必须尤其和善。作为一个农夫,他游水游得不烂,是吧?”德尼斯似乎庆幸没有当众大吵大闹;而我则感到失望,我一直是在企盼着有一场吵闹,并且我认为农夫不一定就是一个可以被轻易驱走的人。
“我就跟他打个照面问个好吧,”德尼斯说,“当然从社交角度说,我们是不认识他的,但我们一定不能让他认为我们高傲自大。”
这时候,伯吉斯几乎到了我们的正下方。一根老旧粗壮的柱子嵌在水闸的砖结构里面,伸出水外,风吹日晒使它的侧面沟槽遍布,顶端几乎剥蚀成了一个细尖。他抱住这根柱子,开始把自己拽上来。为了换一个蹬脚处,他蜷缩在尖头上,看上去他像是被钉在柱子上似的,然后他用手紧握住固定在砖壁上的一个圆环攀上了岸,水从他身上往下流。
“好险的登岸!”德尼斯说着把他的干手伸给农夫的湿手,“你为什么不从水闸的另一侧出水?那样会容易一点儿,我们在那里是修了台阶的。”
“我知道,”农夫说,“但我一贯是这样上岸的。”他的话带着当地的口音;这使他的言辞有了一种热度和质感。他低头看看脚下蓝色的砖面上逐渐聚成的水洼,因为在衣着齐整的人们面前几乎裸身,他突然显得不好意思起来。他满怀歉意地说道:“我不知道会有人来这里,收割才刚开始,我干活干得太热,我想我可以下来小游一程,毕竟今天星期六嘛。我不会游很长时间,再扎一头也就够了——”
“哦,请不要因为我们而把你搞得匆匆忙忙,”德尼斯插话说,“对我们来说,这没什么不妥,在布兰汉庄园,我们也热得慌。”他又补充了一句:“顺便告诉你一声,特里明厄姆今晚就来了:他有可能想要见你。”
“我乐意恭候。”农夫说,他给德尼斯鞠了个半身躬,然后沿着阶梯跑上了平台,在每一个台阶上留下了发黑的脚印。我们看着他跳水——足有10英尺[12]的俯冲——紧接着,德尼斯说:“我想我没有弄得他紧张吧,你说呢?”他的朋友点头附和。他们朝一个方向走去,我们走另外一个方向,为的是在灯芯草丛中找到掩隐的地方。灯芯草羽绒一样的毛穗频频点头。到了草丛中,我想我们可以看见别人,但别人看不见我们:这是教人脸红的秘密,不可声张。马库斯开始脱他的衣服,我也想脱,但马库斯说:“如果你不游泳,换作我,我是不会穿上泳装的,那看上去不伦不类。”于是我就按兵不动。
灯芯草窸窣作响,男人们走出来了,几乎是在同时,我们听到茅屋的门咯咯叽叽,还有女人的声音,他们一道全都走向水闸上方的台阶,我跟着他们,但感到不再是他们的同伴。从某种意义上说,看着他们衣着齐整,下水游泳,就好像他们穿着日常的衣服洗浴,这让人失望;我记得玛丽安的泳装把她裹得很严实,比她的晚礼服严实多了。他们在台阶上迟迟疑疑,顽皮地怂恿对方先下水。德尼斯和他的朋友相互把彼此拖进水里,被穿过水闸的激流冲走,而玛丽安、厄拉利和马库斯停留在上流只有腰深的浅水里;他们迈着大步,摇摇晃晃,来回蹚水,他们的脚踩在闪着金光的砾石上,脚被衬托得又软又白,他们扎入无人察觉的穴孔,相互泼水,放声尖叫,嬉闹地笑,豪放地笑。他们宽厚笨拙的衣衫开始紧贴住身体,表现出他们身体柔软的轮廓。现在胆大一点儿了,他们用力时可以带有目的。目标使他们的视域变窄;他们下颌上翘,缓缓划水,两手舒张,推水向后,继而再揽水入怀。逐渐地他们做这样的动作越来越自如;他们发出幸福圣洁的微笑,吸入深长的无比快乐的气息。
这很像看人家跳舞,自己又参与不进去。看他们看够了,我便转身向水闸较远的一边走去。在那里,德尼斯和另外的那个人在深水区仰面漂浮,时而把水踢成泡沫,时而凝目仰望天空,只有脸露出水面。正当我站在那里崇敬他们但不希望加入他们的时候,我听见从我下方传来声音;这是特德·伯吉斯正在攀住柱子,拖自己出水。他肌肉隆起,由于用力而面部紧绷,他没有看到我;而在那尊威力四溢的身躯前面,我几乎因惧怕而缩退,那尊身躯是在讲给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退入灯芯草丛,坐下;而他则躺在阳光下暖热的砖基上舒展自己。
他的衣服就放在他的边上;他没有自找麻烦,寻求灯芯草的遮蔽,现在也没有必要这么做。他相信别的游水人是看不到自己的,因而他让自己和自己的身体放纵于一种孤身独处的状态。他蠕动着自己的脚趾,使劲地用鼻孔呼吸,扭动着他依旧挂着水珠的棕色胡须,用挑剔的目光周身打量自己。这种审视似乎令他满足,或许真的使他满足。至于我,只跟正在发育的身体和心智打过交道,却在突然间与最为明白实在的成熟相遇;他所拥有的手、臂、腿、脚超越了健身房和操练场的需要,只为它们自己的力和美而存在。我想知道,成长为他会是什么感觉;我在想,他的四肢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生发自我意识。
就在眼前,他左手拿着一根车前草株干,轻轻地顺着他的右小臂揉擦汗毛;汗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颜色比胳膊灰暗,他的双臂至胳膊肘以上呈红木色。接下来,他把双臂高高伸起在胸脯上方,他的脖颈下面,太阳光给他晒成了一个古铜色的胸铠,除此之外,他的胸脯一片白皙,致人怀疑它有可能属于另外一个人;他对自己窃笑,一种亲密、惬意的微笑,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看上去会是童稚气十足的傻笑,但对他而言,则有一种羽毛长在老虎身上的效果——这则隐喻,意在对比,映照出的都是他的优势。
我说不清我是不是在刺探他的秘密,但我只要稍有动作就会暴露自己,况且我有一种感觉,打搅了他会有危险。
这段时间里,游水的那伙人一直很安静,但突然从河里传来了叫喊声——“啊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散开了,湿透了!干不了了!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我要出去了!”
农夫跳起身来,他不等自己干透。他把衬衣从头上套下来,把灯芯绒裤从湿泳衣上拉上去;他把脚塞进厚厚的灰色短袜里,蹬上靴子。紧接着先前的沉寂,他投入到这些动作中的富有爆发力的能量几乎吓着了我。他的皮带给了他最大的麻烦,他在扣上搭钩的时候急得骂粗话。然后他大步流星走过水闸。
过了一会儿,玛丽安过来了。她把她的长发卷握在身前。她的卷发有我所熟知的两道弯,它们属于黄道十二宫的处女座【17】。她很快就发现了我;她半是说笑半是恼火。“哎呀,利奥,”她说,“你坐在那地方看上去好洋洋得意啊,我应该把你扔进河里。”我想我听见那话的样子很惊慌,因为她接着说:“不扔,不真扔。只是你看你干燥得让人嫉恨,而我要过多长时间才能干啊。”她四周打量了一番说:“那人走了吗?”
“走了。”我说,能回答上她提的任何问题都总是让我开心。“他走开得匆匆忙忙,他名叫特德·伯吉斯,一个农夫,”我主动回答道,“你认识他吗?”
“我可能见过他,”玛丽安说,“我记不清了。但你还在这里,这就够了。”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但那意思听起来像是对我的赞词。她继续走路,去了茅屋。很快其他人陆续上岸:马库斯到我跟前给我讲游水多么快意。我羡慕他,他的泳衣似乎缩到了一半大小:我的未入水的泳衣好像一枚失败的徽章。我们等女士们等了好长时间,最终玛丽安出来了,托着她的发卷好让它不粘贴身体。“哎呀,头发永远干不了了,”她哭丧着脸说,“正往我的衣服上掉水呢!”看着她无助、无奈的样子,我觉得很好笑,她总是惯于把事情看得轻而易举,而面对像湿头发这样的小事却一筹莫展!女人就是很怪。就在这时候,我有了一个主意。这主意让我浑身欣喜。我说:“这是我的游泳服,它完全是干的。如果你把它系在脖子周围,让它从你的脊背垂下去,那样你就可以把头发铺到我的游泳服上,这一来,头发可以晾干,衣服又不至于弄湿。”我停下来,上气不接下气;那似乎是我做过的最长的演说,而我又非常担心她听不下去:小孩子们的建议被搁置一边,这是太常见的事儿了。我以恳求的姿态把衣服举起来递给她,以便她自己可以明了这衣服很适合那用场。她将信将疑地说:“也许管用,谁有别针啊?”有人拿出了别针;那衣服便绕着她的脖颈铺覆开来;人们称赏我的机智。她对我说:“现在你得把我的头发铺到泳衣上,小心,不要拉扯。噢,噢!”我惊诧地退缩回去;我怎么会弄疼她呢?我几乎没有碰触到她的头发呀,尽管我非常想那么做。然后我见她面带笑容,于是继续执行我的任务。那真是为爱辛劳,我的第一次为爱辛劳。
在各种不断加长的阴凉影子里,我随着她往回走,依然渴望着能成为她的“这就够了”,尽管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时不时地,她问我她的头发怎么样,而不论哪一回我摸摸她的头发,看看究竟,她都要假装出我拉扯了她的头发。她处在一种古怪的、自得的情绪中,而我也一样;而且我认为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俩这兴高采烈的欢态来自相同的渊源。我的想法罩住了她,她接受了我的想法:我就是那件上面铺着她秀发的泳衣;我是她正在变干的秀发,我是吹干她秀发的风。我有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描述的巨大的成就感。但当她把我的泳装还给我并且又一次让我触摸她的头发的时候,我感到了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我的泳装湿了,是因为我不想让她受潮湿所致,她的头发干了,是因为我所想到的干燥方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