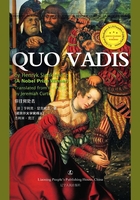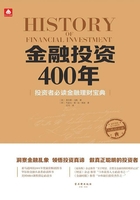两人出了茶楼,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照在身上。凉秋站在街头,环视一周,做了个深呼吸,回头对叶秋荻说:“好久没有这么舒畅地呼吸了!叶记者,敢不敢跟一个逃犯握握手呀?!”
叶秋荻便笑吟吟地伸过手去。凉秋一把握住,用力地摇了摇。
逃犯的手很粗糙,但一点不冰凉。
黄连诚很久没来纠缠秦小谨,秦小谨猜测,是那一小瓶硫酸起了阻吓作用。她有点后悔,不该亮出它来的,他不纠缠了,就没机会收集证据了。
但又一想,这不是歪打正着吗?她要的,不就是终止他的丑恶行为吗?
于是,秦小谨心安了。
换句话说,她被假象蒙蔽了。她放松了警惕,麻庳了心智,这天夜里上床前,竟糊里糊涂地忘记了一件每夜都做的事:将门反锁。
她的身心太疲惫了,早早地就上了床。她将收录两用的收录机放在枕边,听了一会音乐,睡意便如水漫来,刚刚来得及关掉开关,就朦朦胧胧地沉入了梦乡,对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她轻轻地打着鼾,常出现于她意念中的猫科动物蹑手蹑足到了门口,并将钥匙插进了锁孔,她却意识不到。
不,她的潜意识觉察到了,只不过,她以为这只是一个梦。她眼前迷茫一片,她依稀地看到,门无声地开了,一团模糊的影子变幻不已,向她飘移过来。她感觉到了莫名的危险,恐惧地蜷缩起身子,心里却安慰着自已:别怕,一个梦而已。
那团黑影到了床前,俯视着她。它和她如此之近!她直愣愣地瞪着它,发现它有两只小电灯泡一样的眼睛,还有一双半举起的毛茸茸的手。她喉咙紧涩,大叫一声滚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凄凉的月光透进窗来,映照着她和那个黑影。那黑影竟还拖着个影子,而且黑影的上部,嵌着一张熟悉的脸!秦小谨心里一惊,寒意立即渗透了全身。这时,黑影的轮廓愈发清晰了,这是一只巨大的猫,抖着一身肮脏的绒毛。猫爪子将她的被子揭开了,冰凉的风水一般从头流向她的双脚。接着,那猫抓住了她的内裤往下拉扯,她死死地捏着裤头,拚命挣扎,四肢却如冻僵了一般不听使唤。她哪里是猫的对手呵,内裤被慢慢地拉下去了,她最隐秘的部位暴露出来了……啊!她一声惊呼,终于喊出声来,也终于醒过来了!醒来之后,她才知道,这不是梦!她的内裤确实被人扯着,而黄连诚那张可恶的猫脸正浮在她的脸上方,朝她呼着带有强烈膻腥味的动物气息!
秦小谨的心蓦地缩成了一坨铁,但同时也极快地镇定下来。这是她收集证据的极好机会,是可怕的恶梦,也是天赐的良机。在那张猫嘴快要凑到她脸上之前,她及时地侧过身子,一只手下意识地摸到了录音机,摁下了录音键,接着,又拉了床头的电灯开关。
灯光顿时照亮了一切,但黄连诚并不惊慌,也没后退。她想爬起床来,黄连诚一把将她摁住,另一只手继续扯她的内裤。
秦小谨拽住黄连诚那只手,不让它动作,大声骂道:“黄连诚,你这个臭流氓!”
“嘿嘿,别固执嘛,只是玩玩嘛!”黄连诚压抑着嗓门,嬉皮笑脸的。
“你、你想强奸我?!”她喘着气,愤怒和寒冷让她瑟瑟发抖。
“哪能呢?早跟你说过了,这是两个人都快乐的事,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来吧,我们好好享受……”黄连诚抽出自已的手,抬腿上床,想搂住她。
“滚开!”她怒不可遏,腿一曲,一脚踢在黄连诚胸口上。
黄连诚没防备,呵哟一声滚下床去,但他马上就站了起来。他还想往床上去,秦小谨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床,抓过一件羽绒衣裹住自已,气呶呶地指着他:“你、你这不要脸的,你骚扰我几年了!你把我的家庭都破坏掉了,你还不甘心吗?你像个当领导的吗?你简直猪狗不如!”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只怪你老公太小心眼了,不像个男子汉!我又不想破坏你的家庭。其实,你那当工人的老公有什么好?要地位没地位,要长相没长相,一不小心就下岗了,饭都吃不饱!这样吧,我们先偷偷地好,以后你要是愿意和我结婚,我们再想办法。只要你对我好,我是不会亏待你的!”黄连诚说着又伸出两只爪子,企图拥抱她。
“你作梦!”秦小谨嘶叫一声,后退两步,“你要还不赶快滚出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噢,你还想对你的领导怎么样呵?”黄连诚涎着脸向她逼近。
秦小谨立即走到桌前,拉开抽屉,手忙脚乱地寻找那瓶硫酸。她有些心慌意乱,竟然没有找到。急中生智,她胡乱拿起一个小药瓶,对黄连诚举举说:“你要再不滚,我就把这瓶硫酸泼到你脸上去!”
黄连诚愣怔片刻,脸慢慢地白了,咬咬牙道:“你……好,好,算你狠!”一回头,快速溜出门外。他照例踮着猫步,一点声音都没有。
秦小谨坐在桌前,浑身疲软,手抚着胸口,很久才平静下来。
后来,她拿过录音机,倒带后听了一遍。所有的话语和声响都录在上面了,非常清晰。
她抓过桌上的电话,打了叶秋荻的手机。
“秋荻,你快到我这儿来!”
“有什么事吗?”叶秋荻问。
“刚才……我差点被黄连诚强奸!”
“啊?!”叶秋荻闻言大惊,“你没事吧?我马上过来!”
半小时后,叶秋荻风风火火地进门来,眼睛迅速地四处搜索一遍,关切地问:“小谨,你还好吧?”
“我还好。”秦小谨点点头,将刚刚发生的事叙说了一遍。
“好险,差点就让他得了手!”叶秋荻气愤之极,“竟然有这样的领导,简直禽兽不如!”
“这几天,我还以为他被硫酸吓住了,不敢骚扰我了呢,谁知他贼心不死……刚才要不是我又拿硫酸来吓他,只怕他不会罢手。”
“硫酸?哪来的硫酸?”叶秋荻问。
“我特意找康有志弄来对付黄连诚的。可刚才要用的时候,却找不见了,只好胡乱拿个药瓶蒙他。”秦小谨埋头往抽屉里翻着,少顷,拿出个小瓶子来,“奇怪,用不着的时候又找到它了,你看——”
叶秋荻朝秦小谨手中的小瓶子看了一眼,说:“小谨,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你拿硫酸烧了他,自已也犯了故意伤害罪,划不来!”
“我知道,可我心里那个恨呀,真想把瓶盖打开,一滴不剩地浇到他脸上去!”
“小谨,你不能留着这东西了,弄不好一冲动,就会做错事。交给我处理吧。”叶秋荻从秦小谨手里拿过硫酸瓶子,欲往垃圾篓里扔,想想不放心,就将盖子旋紧,把它塞进自已坤包的夹层中。
“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人一被逼急了,什么做不出来?狗还知道跳墙呢。只要能够惩罚他,我就是坐几年牢也值……不过现在我有了他骚扰我的证据,我可以告他了!”
秦小谨拿出录音机,放给叶秋荻听。
叶秋荻听后,却摇了摇头说:“没用。”
“为什么?”秦小谨忙问。
“昨天我在电话里与阳光律师聊过了,说了想用录音做证据的事。她说,凡没经过当事人同意而偷录的音、偷摄的像,法庭一般都不会作为证据采信。”叶秋荻皱着眉说。
“这是什么道理?”秦小谨急了。
“大概是出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考虑,才有这样的规定吧。”叶秋荻说。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我若征求黄连诚的意见,他会同意我录音吗?我能得到证据吗?为了保护他的隐私,就得让他对我进行人身侵害?天下哪有这样的理?法律究竟是保护好人还是保护坏人的呀?!”秦小谨胸脯大起大伏,眼里泛起了泪花。
“没办法,现时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叶秋荻悄悄叹口气,安慰地搂住秦小谨的肩膀,“只能想办法收集别的证据了。”
“这都不能算证据,还有什么能算?”秦小谨嗓子沙哑了,“难道一定要让他强暴我了,再让警察来找被他撕烂的内裤,收集他留下的精液吗?!”
“小谨,你别激动,别灰心,我们慢慢想办法!”
“连法律也不同情弱者,还有什么办法?看来唯一的办法,就只有用硫酸来保卫自已了。你把硫酸还给我!”秦小谨说着去拽叶秋荻的坤包,叶秋荻将她的手一把甩开了。
“你冷静点呵小谨!”
“你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这事要是摊到你头上,你还冷静得下来吗?”秦小谨眼都红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必须冷静,千万不要做出极端的举动来!”叶秋荻抱住秦小谨,一只手掌在她背上轻轻摩挲。
“我……实是被逼到死胡同里了,没有办法了。你替我想一个办法吧……”秦小谨无助地缩起身子,低垂着头,喉头一阵哽咽,轻微地颤抖着。
“小谨,总会有办法的……我一直想帮你的忙,想帮你摆脱恶梦,脱离困境。我觉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帮你,也是帮我自已……你可能想象不到,既使像我,也免不了受到骚扰和羞辱……我们必须找回女人的尊严。我在莲城早报上开专栏,对性骚扰开展讨论,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叶秋荻放低声调,眼睛望着窗外的夜色,目光迷惘,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可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顶多给人们增加了一点谈资罢了……骚乱在继续,羞辱也在继续,舆论难以形成,既使形成了也难对品质恶劣的人有所触动,法律对此似乎也无能为力……也许泛泛而谈,不指向具体的个人,就不能对骚扰者形成威慑,就无法阻止他们的丑行吧?也许,要把他们暴露在阳光下,展示在大众的目光里,才会让他们增加一点羞耻心,收敛起他们的爪子?我相信,正义和良心还是存在的,它会帮我们渡过难关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个人靠自已的无畏制止了丑恶,使自已不再遭受欺侮,我很佩服她。”
“谁?”秦小谨抬起头来。
“新农业示范园的周雅琴。”叶秋荻说。
秦小谨点头说:“嗯,我在你的文章里读到过她的事。”
“是的,不过因为篇幅的限制,我写得比较简略。”
叶秋荻稍作回忆,将周雅琴受骚扰和反骚扰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复述周雅琴在农场大会上说的那番话时,叶秋荻语调铿锵,两眼放亮,仿佛她就是周雅琴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