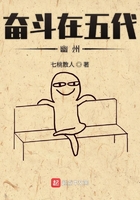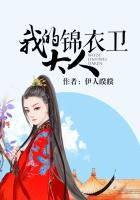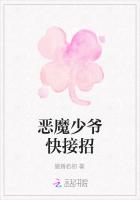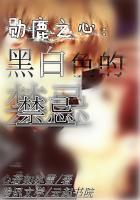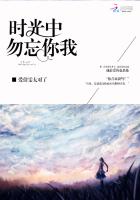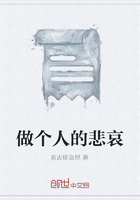第六辑
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和政治文明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此后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掲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然后由皇帝亲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黙诵讫,复再拜而出”。仪式庄重而神秘。碑中“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迷信观念极重的古代,第三条当然是极重的毒誓。但到北宋末年,金军攻破开封,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秘密就此公开。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勋向宋高宗转达重要口信,据曹勋向宋高宗上奏:
“(太上皇)又语臣曰:‘归可奏上,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在]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众所周知,唐太宗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是出名的,但这只属个人的政风,并未立下什么制度性的死规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不仅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也体现了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下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官员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古代的专制政治当然是残酷的,且不说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动辄遭杀身之祸。宋人谢逸在《读阮籍传》中说:“魏晋之交,王室不竞,强臣跋扈,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无所顾惮。一时名士,朝不谋夕,如寝处乎颓垣败屋之下,岌岌然将恐压焉。”其实,在整个中国古代,又何尝不是“杀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北宋末年,陈公辅上奏说:
“汉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尝杀戮大臣,然窜逐岭表固有之矣。”
南宋末年,黄震的《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说:
“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育天下三百馀年,前古无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
宋太祖誓约在北宋历代执行得相当严格,如大臣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也仅流放了事。在北宋后期的激烈党争中,大批反变法派流放岭南,变法派章惇、蔡卞制造冤狱,确实想将他们定为“大逆不道之谋”,而置于死地,但宋哲宗说:“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只有在宋钦宗时开了杀戒。宋徽宗认为宋钦宗诛斩王黼、朱勔、童贯等人“不祥”,故命曹勋传话,要宋高宗引以为训。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这是宋朝政治冤狱和文字狱最滥,正直士大夫受祸最烈的一代,主要也仅开三次杀戒:第一次是杀张邦昌、宋齐愈等降金媚敌者,第二次是杀害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第三次是杀害岳飞、张宪和岳云。秦桧得势之后,睚眦必报,杀心极重,但毕竟受到了皇帝的羁束,而在大部分场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约的羁束,对许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惩,也就是流放岭南或海南岛。
南宋第二个权臣韩侂胄得势时,“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仅是贬窜了事。为时不久,“伪党之祸寖解”,并未开杀戒。后韩侂胄在政变中被杀,宋宁宗最初并不知情。后有诏斩其同党苏师旦,才开了杀戒。苏师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当韩侂胄之“厮役”,属武官,在宋人眼里不算士大夫。第三个权臣史弥远为人阴鸷,他以谋反的罪名,杀害了武学生华岳和济王赵竑,但对许多名士,也仅是设法将他们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个权臣贾似道,对政敌和名士,“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也未开杀戒。贾似道最终流放到漳州,在木绵庵被县尉郑虎臣“拉杀”,即击杀,并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斩杀的,只有其幕僚翁应龙。
由此可见,陈公辅和黄震的说法是符合史实的。后世认为宋政“宽柔”,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来,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确是体现了“宽柔”的积极方面。当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总体制下,此种政治文明的进步毕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计过高。特别宋高宗不顾宋太祖毒誓,亲自下令的两次屠戮,即使在中华古史上也是罕见的凶残。
自宋以后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则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的专制淫威不断强化,政治过程的残暴化,动辄迫害和诛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视司空见惯。从珍视人命的现代人权和文明理念看来,这是理应被批判、谴责而唾弃的历史罪恶传统。
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
宋太祖建国后,由于是武人政变,黄袍加身的来历,又冀望自己创立的朝代能够长治久安,已显露出追求文治的倾向。如他曾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但当时五代重武之余习依然保留,在宋太祖开国第二年,因杜太后葬礼已毕,“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诸军、厢主军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进奉使于广政殿”。众多武将,包括官阶不太高者都有资格参加御宴,这在往后是不可设想的事。
严格意义上说,宋朝确立文官政治,是始于宋太宗时。一是当时科举入仕的名额剧增。宋太祖时,尚踵唐五代之旧,登科人数一般仅十多人,只有两次破例为百余人。然而宋太宗即位,最初即达五百人,最多一次达一千三百余人。二是开始在官场中强调出身,文官以科举登科为“有出身”,其他为“无出身”,更不论武官了。在魏晋南北朝,从官场到社会地位,最受重视者,无疑是门第。唐朝虽有科举制,但门第观念仍重,而宋朝取代门第观念者,是出身。《说郛》卷16《丁晋公谈录》记载,“吕丞相端本自奏荫”,“后苑赏花宴,太宗宣臣僚赋诗,吕奏曰:‘臣无出身,不敢应诏。’”表明到宋太宗时,无出身者在官场中已是低声下气。宋朝的宰相和执政大多是科举出身,即“有出身”,如吕端那样,是个别情况。这无疑是唐宋之际从官场到社会的一个变化。人们常引用文彦博说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其实就是与“有出身”者治天下。
宋朝以兴盛的科举制,造就了发达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国”,对政治稳定和文化发展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过犹不及”,一切事物超过限度,必然走向反面。宋朝厉行文尊武卑,在名分方面过分压制武将,南宋初的汪藻说:“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胡寅说,宋仁宗朝的“吕夷简为相日”,有高级武将“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阶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简上表求去,以为轻及朝廷,其人以此废斥,盖分守之严如此。”这与前述宋初的情况适成鲜明对照,在制度上保证武将在文官大臣面前必须低声下气。过分的崇文抑武,以压抑和束缚武将的军事才能与指挥权为快,又造成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军事的萎靡不振。
科举制本意是在公平、公正的学问考试竞争中选拔人才,然而与之相伴随的,则必然是考试作弊。尽管宋朝采取了诸如等糊名、誊录等各种措施,也不可能根本杜绝。宋代最出名的科举作弊案,是秦桧养子秦熺及其子秦埙的中举。秦熺参加殿试,在试卷中以“赋无天地,诗有龙蛇”八字为暗号,而被考官定为第一,秦桧又假惺惺辞免,宋高宗最后定为第二。秦埙参加两浙转运司解试时,最初就由秦桧的亲党疏通考官候选人萧燧,被萧燧拒绝。陈之茂出任考官,定爱国诗人陆游为第一,秦桧大怒,后在省试中将陆游黜落。殿试的考官全由秦桧提名。考官董德元按誊录字号拿到秦埙试卷,就兴高采烈地说:“吾曹可以富贵矣!”当时考官阅卷,必须闭门上锁,而另一考官沈虚中更命吏胥越墙飞报秦埙。宋高宗亲自阅卷,想抑制一下秦桧,就将张孝祥定为第一,秦埙改为第三名。秦桧又因此迁怒张孝祥,很快给他举办冤狱。秦熺参加殿试时,已荫补为正八品右通直郎,秦埙更已荫补为从四品敷文阁待制,但他们还是一定要力争从“无出身”变为“有出身”,也说明“有出身”对混迹官场和社会的重要性。
英国有保守党,在英文中当然不是贬义词,但现代中文的“保守”一词,已约定俗成,成了贬义词。文官政治并不意味着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最大特色,在总体上说则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讥评宋朝前百年的政治,说“因循苟且”,“侥幸一时”,“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不求振作有为,但求勉强维持,得过且过。保守的官场是个大染缸,宋朝的许多大臣在大染缸浸沉之余,往往没有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其小聪明有时适足以成就其大失策。他们在平时似乎高谈阔论,十分矜持,自鸣得意;一旦处于险局,就会充分暴露其庸劣,而束手无策。更有甚者,则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治国和救国全然无方;而钩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却又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这是“窝里斗”和“窝里横”的坏传统和恶劣士风。发展到了顶点,则是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
大致上说,宋朝文官政治的保守性,也是开创于宋太宗时。人们常引宋太宗即位赦,强调要继承乃兄的遗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专注于免蹈五代覆辙,堵塞各种政治上的漏洞,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保守。事实上,宋太宗最初还是有一股锐气,想有一番作为的,尽管他是个并不高明的政治家,特别是军事才能短拙,与乃兄不可同日而语。譬如他针对宋太祖包庇妻舅王继勋,而严惩其滥杀无辜之罪,就有革新庶政的意味。待到北边两次伐辽失败,宋太宗本人也中箭受伤,只能摆出消极防御、被动招架的态势,南面恢复唐朝对交州的管辖的企图又成为泡影,也就心灰意懒。但他也看准了边患不足以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宋太宗在位晚年,自我总结说:“朕承丧乱之後,君临大宝……朕执心坚固,靡与动摇,昼夜孜孜,勤行不怠,於今二十载矣。卿等以朕今日为治如何也?虽未能上比三皇,至於寰海晏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绝奸幸,固亦无惭於前代矣。”如“寰海晏清”等语当然是自我吹嘘,不符史实,他明知无法与大唐贞观之文治武功媲美,却仍以“昼夜孜孜”,保住已有的基业,不出大乱子而自豪。其实质还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乱的保守施政思想。
到第三代宋真宗时,武将的权位已压至出不了变乱的地步。人们对辽宋的澶渊之盟,已多所议论。当时辽朝大军倾巢而出,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其后夫汉人韩德让(当时名德昌,战后改姓耶律),另加辽圣宗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善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险棋,如果对手是个较高明的军事家,一方面避免硬拼,设法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又乘虚直捣燕云,对辽朝是非常危险的。辽的军事部署固然不高明,却遭逢了更糟的对手。事实上,杨延朗(后改名延昭)就提出此策,说“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奏入,不报”。 鼠目寸光的宋廷习惯于被动应战,根本不可能有此深谋远略和军事气魄。他只是一个战区司令,不能左右战略指挥。前沿总司令是败将兼庸将,北面都部署王超,他“阵於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宰相寇准排除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的“南幸”之议,只是力主亲征,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最终达成了对宋方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尽管如此,宋真宗其实认为此种和议是如天之赐,自此之后,宋廷进入文恬武嬉的状态。宋真宗为了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不惜装神弄鬼,尊崇道教,伪造天书,大事封禅,挥霍民脂民膏,虚饰盛世,“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宋朝的保守政治也就进一步深化。
四十年后,辽朝乘宋朝困于对西夏的战争,进行勒索,宋朝被迫增加岁币,富弼出使归来,非常痛切地上奏说:“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虏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鱼烂,梁之自亡耶?臣备位枢府,夙夜忧畏,恨未得死所,少纾国难。”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与范仲淹、韩琦都是改革派,而受保守派的排挤,离开朝廷外任。十年之后,富弼和韩琦先后回朝任宰相,却被保守的官场磨光了锋芒,依旧安常习故,不思变革。
辽宋与宋金的关系迥然不同,辽宋战争不过是宋的边患,而新兴的金朝却有灭宋的企图和军力。金军不同于辽军,不仅善于野战,也善于攻城,故能深入中原。北宋末年,当金军南侵之际,朝廷那群平时养尊处优、高官厚禄之辈乱成一团,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他本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又不懂军事,在仓猝之间,却临危主动请缨,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防御,因而陡然在朝野和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却引起那帮高官极重的妒忌。他们力主降金,使尽各种花招,“疾李纲胜己,同力挤排”,耿南仲进言:“欲援太原,非纲不可。” 唐恪说:“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宋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不知军旅,将兵必败”,“为大臣所陷”,“不宜遣”。李纲本人也有自知之明,“再拜力辞”,说自己“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宋钦宗却为之震怒,李纲不得不就任出行。太原之战是决定北宋皇朝命运的关键性一战。史实证明,保守派再进一步,必然变为投降派。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李纲并非在救援战中不尽己力,却在本来已是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又遇到朝廷的多方掣肘,终于在太原陷落后被劾下台,贬黜出京。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其实还是听信谗言的宋钦宗本人。
在蒙受靖康亡国奇耻深痛,并丧失半壁河山的南宋,保守政治的新特征,就是投降政治,甘愿忍受偏安的局面;而丧失重新大一统之志,也正是北宋保守和苟且的政风的延续。被某些史家称为“中兴贤相”的赵鼎是解州闻喜县人,他对家乡的失陷,国家的危难,曾有一阕《满江红》词,抒发其悲痛之心情:“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他初入中枢,也并非没有锐气,如谴责拥兵玩敌的庸将刘光世和张俊,举荐岳飞收复襄汉,面对金军大举进犯,力主皇帝亲征,也反对向金朝乞和。但几年之后,他又力主所谓“安靖不生事”,反对罢刘光世的兵权,伙同秦桧,将南宋“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以各种借口,主持对金屈辱讲和。
特别是在南宋时,有一条政治定律,不论某人以往的政治主张和表现如何,一旦转变为主守,特别是主和,就决不可能企求他真有卧薪尝胆、雪复仇耻之志。陈康伯和史浩两个名相也都是实例。
陈康伯在宋高宗绍兴末力主备战,抗金战争爆发后,“中外震骇,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独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临安诸城门扄鐍率迟常时,人恃以安”,处变不惊,确实起了好作用。但他在宋孝宗隆兴时,特别是著名的投降派汤思退复相后,却也倾向于和议。陈康伯与汤思退、周葵、洪遵四人联名上札子说,“群臣纷纷,乃谓臣等意欲讲和,以苟目前之安”。“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今日议和,政欲使军民少就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复。惟在陛下无忘今日之纷纷,而力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区区之愚,不专为苟安之事,以实议者之言”。其言虽辩,而观其实效,则是汤思退的降金阴谋在相当程度上得逞。
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在宋孝宗即位前,克尽献可替否之责,有“智囊”之称,故深得宋孝宗的倚信。绍兴末年,宋金再战,宋军败退,时为太子的宋孝宗不胜其愤,向宋高宗主动请缨,史浩得知后,力劝太子不可将兵,终于使太子避免了宋高宗的猜忌,而得以继位。故宋孝宗即位后,史浩立即升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他劝宋孝宗为岳飞昭雪平反。宋高宗当太上皇后,居德寿宫,纵容宦官开设酒库,犯榷酒之禁。有谏官袁孚上奏直言谏诤,宋高宗却为之震怒,宋孝宗只能下御批,将袁孚罢官。史浩出面调解,结果让袁孚主动辞职,宋孝宗又为之另加直秘阁的职名,给几方面都保留面子。史浩的聪明才智,表现在极善圆满地排解专制政体和官场的各种纠纷,但处置军国大事,却又是十足的庸劣。史浩对金只主张防守,宋孝宗听信其说,下令吴璘班师,招致了德顺之战的最终大败。宋孝宗最终明白:“此史浩误朕!”史浩对金朝早就提出“欲以弟侄之礼事之”, 无非仍是稍稍争取点体面,而忍辱苟安。他“既参知政事,(张)浚所规画,浩必阻挠,如不赏海州之功,沮死骁将张子盖,散遣东海舟师,皆浩之为也”。这当然也是误国失策的行为。史浩反对张浚用兵,并非没有道理,张浚虽然主战,从来是败事有余,而成事不足。表面看来,史浩属主守派。然而史浩后来再相,却找不出他有任何发愤图强、准备北伐的政绩,也证明他其实还是忍心于苟安。
著名的抗战派胡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议者乃曰:‘姑与之和,而阴为之备;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一溺于和,则上下偷安,将士解体,终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战乎?”南宋的史实证明了其评论的正确。
朱熹评论赵鼎说:“当国久,未必不出于和。”这是南宋保守政治的特点,具有某种规律性。“安靖”一词就成了保守以至降金乞和的代名词。程敦厚上书,赞扬宋高宗降金为“致安靖之福”。宋高宗等人给抗战派所加的罪名,就是“好作不靖,胥动浮言”,“唱为不靖”,“作为不靖,有害治功”,“务于不靖,以售其奸”之类。宋高宗特别强调:“其不靖害治者,显黜勿贷,庶知惩畏。”宋宁宗时,危稹说:“谋国者欲以安靖为安靖,忧国者欲以振厉为安靖,自二议不合,是以国无成谋,人无定志。”但主政的权臣,史浩之子史弥远其实是继承乃父的衣钵,“力主安靖之说”,他给边臣赵范书信,“令谕四总管各享安靖之福”。
朱熹评论赵鼎说:“看他做来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规摹”。爱国诗人陆游更进一步,“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东晋以建康为国都,建康亦名金陵,而赵鼎则力主将“行在”从建康后撤临安,其实就是无复北顾中原的象征。“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不望夷吾(春秋时的管仲)出江左,新亭对泣亦无人”。认为南宋的保守和投降政治还是在东晋的王导“规摹”、“新亭对泣”之下,这是准确的、中肯的评论。
总的说来,文官的保守政治一直伴随着宋朝,直至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