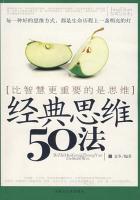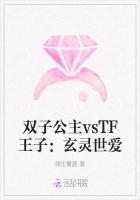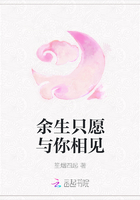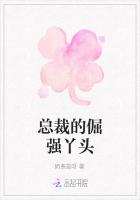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早年生活足够卓越,却也十分悲惨。他出生于1806年,父亲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是苏格兰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是功利主义先驱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追随者。边沁有句声名狼藉的名言:“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衡量对错的尺度。”[7]忘却历史,抛开传统:公共机构必须服务于受它们影响的每一个人的利益。任何不能让人们更幸福的事物,必须做出改变。
詹姆斯·密尔在1808年结识了边沁,并迅速成为边沁的拥趸。那时候,他的儿子约翰还不到两岁,但约翰的非凡人生就此起步。按照“好事始于家门”的原则,詹姆斯·密尔亲自为儿子设计了教育规划,要把儿子培养成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奋斗的人,让世界因他而不同的人。这次试验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来说,取得了“骇人的成功”。[8]称其成功,是因为约翰·密尔由此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英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称其骇人,则是因为他早年的茕茕孑立、与世隔绝。密尔被禁止与其他孩子交往,同时以惊人的步调接受教育:3岁学希腊语,7岁读柏拉图,8岁学拉丁语,11岁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少年时期学习逻辑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学,接着在15岁时学习边沁的理论和哲学。到了20岁,约翰·密尔已经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父亲的得意之子,却遭遇了精神崩溃。
在这样一本关于中年危机的书里讨论密尔,并尝试从他的经历中挖掘经验看上去有悖常理。他在《约翰·密尔自传》(Autobiography)中回忆,自己精神崩溃时还十分年轻。如同他在其他方面的经历一样,密尔经历的精神危机也是过早的。他的危机也可能是你面临的,是坚持哲学思考的典型。密尔试图去分析自己从崩溃到痊愈的经过,并为道德哲学提炼经验教训:我遵循的也是这一方法。
同时我得承认,密尔的一些遭遇并不只发生在中年。我们在这里分析密尔的不幸,实际相当于参加哲学伦理学速成班,好为本书余下的内容做好铺垫。我们将探索什么是幸福的本质,以及怎样追求幸福;我们将把中年危机拿来与跌入虚无主义的更彻底的崩溃做一番对比;我们将分析人类活动中不同类型的价值;而后,我们将在密尔的危机中找到可资借鉴的东西。我们可能不会拥有他那样的童年,但也许我们曾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重压以及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时间发过牢骚,也曾自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了吗?在下文中,我们将在密尔的帮助下着手回答这个问题。
密尔的叙事富有感染力,还有一个不祥的开头。他以荒凉和晦暗的笔触记录下自己的伤痛:
我陷入了神经麻痹状态,可能每个人偶尔都曾遇到过;我对享乐或愉悦的刺激失去了兴趣;快乐的事情曾带给我好心情,现在也枯燥乏味或平淡无奇……在如此情绪下,我不禁直问自己:“假如你人生的全部目标都实现了,你所追求的制度与观念变革都将立即生效:你会因此获得巨大的愉悦感和幸福感吗?”一个难以压制的自我意识立即回答道:“不!”[9]
玄妙之处在于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最深切的渴望和最宏伟的雄心终于实现,竟成了一件与己无关的事?问题出在哪里?
你也许会回答:确实出了好多问题。可怜的密尔,被他那专横的父亲驱赶着走上安排好的人生轨迹。这叫他如何能体会到对自己人生的掌控、自主意识和真实感?难怪后来密尔会写下《论自由》(On Liberty)这样一部探讨自治(self-government)和思想自由的作品。
其他症状还包括疏离感、社会联系脆弱,以及对亲密关系的渴求。至少从这方面看,密尔的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1830年,25岁的约翰·密尔遇见了他的一生所爱,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了,但他俩还是成了好朋友,密尔称这段关系为“我生命中最有价值的友谊”。[10]1851年,哈丽雅特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密尔向她求婚成功。在他的自传中,密尔称她实际上是该书的共同作者:“不仅在我们的婚姻生活期间,还有那之前,在我们亲密友谊的漫长岁月中,她对我发表的作品做出的贡献与我一样多,”包括《论自由》和《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然而“她的聪慧天分支撑着的,乃是我今生所见唯一最高尚且最平衡的道德人格。”[11]他们的才华和晚年生活堪称佳话。
尽管总体来说,这段关系对他发展的影响“具体地说,几乎是无穷大的”,[12]密尔并没有将他与哈丽雅特的关系当成治愈他精神崩溃的良方,或者将他发展这段关系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孤独。他也曾隐晦地暗示了自身面临的父子矛盾,直到“一缕微光驱散了我的阴霾,我很偶然地读到[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Jean-Fran?ois Marmontel)的《回忆录》(Memoirs),翻阅到讲述他父亲去世的那一段,他家庭的困境突然激发了他的勇气,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也使他的家人觉得,他将成为他们的一切——也将填补他们失去的一切”。[13]这或许是一则证实精神疗法功效的材料,但与密尔的自我诊断无关。相反,他为自己的危机归纳出值得关注的两个原因,每一个都具有哲学背景。
只为我自己
密尔从负面情绪中恢复过来以后,想法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的转变。第一个如下:
的确,我从未动摇过这一信念,即幸福是一切行为规范的检验标准,以及生活的目的。但我现在认为,只有不把这个目的当作直接目标,它才能够实现。(我认为)只有那些人会幸福,他们的心思都在自身幸福以外的事情上,在他人的幸福、人类的进步上,甚至在一些艺术追求上。他们不以这些为手段,而将其本身当作理想的目的。于是当他们把眼光放在别的事物上时,也顺便找到了自身的幸福。[14]
密尔通过这段话表达的见解有个名字:利己主义悖论(paradox of egoism)。它至少可追溯到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在伦敦罗尔斯教堂(Rolls Chapel)的布道,其内容在1726年结集出版。[15]作为英国国教的神父,巴特勒主教相信利己主义,或者说是对个人幸福的执着追求,将干扰甚至妨碍幸福的实现。就像密尔后来的转变,巴特勒认为幸福的关键条件是关心自己以外的事物。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转向利他主义。你所关心的也许是棒球、哲学,或者特定的某个人,如你的朋友、家人,而不是广义的人类。当你这样关心其他事物时,它不仅仅是你的一种自利手段,它本身就能让你感到幸福。所以这就是幸福的源泉,尽管它可能很脆弱。这正是密尔的观点。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想法。我们可以称之为预防中年危机第一定律:你必须关心自己之外的事物。假如除了个人幸福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你关心,假如你完全沉迷于自我,那么不会有太多东西让你感到幸福。当满足感难以获得之时,这个问题就值得好好琢磨了。把渴求幸福作为自己的目标是很自然的事,而可笑之处在于,你得做与之相反的事:关心其他事物。这并不是一个你可以直接采纳的建议,因为你没法热爱那些未能打动你的事物。但它也不是一无是处,你可以选择沉浸于那些你未来可能关心的事物,从而开始改变你的生活。谁知道呢,或许中年时读些哲学会激发你全新而持久的激情?我推荐这个,虽然你也可能找到其他的兴趣。
我们值得为利己主义悖论暂停前进的脚步,同样也值得停下来驳斥信奉人皆自私的人,他们认为世上不可能有那么多无私之欲。他们自认持有极其坦诚的现实主义观点,这些“心理利己主义者”坚持要重新解读那些表面上无私的行为,比如为保护并转移濒危文物而献出生命、[16]给陌生人捐肾,[17]他们将其视为通向幸福的秘密途径。这样一来,这些行为的出发点其实是“无私者”羞于承认的动机和信念。大多数情况下,那些为了他人而以身涉险的人并不相信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好。心理利己主义是关于人类动机的阴谋论,这基本可信。密尔自己就是个合适的例子,他从未将社会变革的愿望构想为利己的计划。但他坚持着这个愿望,尽管他同时坚信这愿望就算实现了也难以让他幸福。即使在最为绝望的时刻,密尔也不曾放下改变世界的渴望,不曾停止为之奋斗。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不管你怎么看利己主义悖论,它都很难适用于密尔。他的问题不是过分利己,非要说的话,恰恰相反:密尔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重要,除了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外,他一无所欲。他无须吃悖论的苦头。但危机还是来临了。密尔的第一个自我诊断尽管很有趣,但大错特错了。
或许很讽刺,但引用密尔精神崩溃的经历作为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悖论的例子可能更吸引人。这里的悖论并不是利他行为何以可能的悖论,而是指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的名言“生命唯一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他人的影响”[18]中隐含的我们还未提及的悖论。年轻的密尔或许会赞同这句话,但是其中的理念与他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借鉴道德哲学中终极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区分。工具价值是指一件事作为达成目的手段而具有的价值,例如赚钱或看牙医的价值。这些事当然值得做,可那不过是因为有钱或者做根管治疗之后的生活更好或更舒适。相反,终极价值则是一件事自身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让它成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它拥有非工具价值。想一想幸福的价值,就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来说,不考虑后果,幸福也是好的。
罗宾森的话暗示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只有工具价值:这些事的价值寓于它们对他人的影响之中。但是他人的生活,以及填满他人生活的活动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些价值也是工具性的,其价值取决于它们对于他人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价值同样取决于它们对于他人的影响,如此反复……价值实现就被无限地推迟了。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强调的,如果对价值的解释总是工具性的,“这一过程将趋于无穷,因而……对目的的渴求也就成了空洞”。[19]只有当人生自身变得重要,不需要依靠对他人的影响时,利他主义才有意义。只有当其他活动本身具有价值时,那些服务于这些活动的举动才有价值。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如果利他主义是唯一重要的事,那就没有重要的事了。人生也就不值得过了。
我这么说是不是对罗宾森不太公平?也许吧。他本可以指明构成重要性的特殊价值的含义,而不是只谈什么构成了美好人生。但我并不是唯一对曲解利他主义感到担忧的人,对利他主义的曲解会造成对利他以外一切事物价值的无视。想想奥登(W.H.Auden)那句嘲弄:“诗人能接受每一种自负,唯独忍受不了社工的那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帮助别人;至于别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我不知道。’”[20]〔这个掌故来自喜剧演员约翰·福斯特·霍尔(John Foster Hall)从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表演的《欢乐的牧师》(“the Vicar of Mirth”)。〕我们有理由推断,密尔的成长已经被一种自我否定扭曲,造成他对利他行为的积极目标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他就是奥登诗句里的社工。
但我不认为密尔的困境是利他主义悖论造成的。密尔对于满足人类需求这件事具有的终极价值不曾有过丝毫怀疑。社会变革的目的之一便是减轻人类的苦难,能让这个目的实现,本身便是具有价值的,不论其影响如何。密尔这位社工的计划绝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
如果密尔规避了利他主义悖论,那我们呢?我难以猜测你的性格,更不想因此有所冒犯,不过从我自己的情况来看,中年危机一定不会转变成狂热的无私,也不会转向虚无主义。即便在其最强有力的控制下,我还是知道我要关心我的所爱,要尽可能地做好我的工作,要让万物归位,要有责任感,要去帮助而非伤害他人。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价值。
无疑一些人的反应也许会更极端。列夫·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详述了自己的危机,他提出了一个令密尔感到震撼的问题,关乎人的抱负的实现:“好吧,很好,所以你会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更出名,比世界上所有作家都更出名,但这又如何呢?”[21]他自己也没有答案。托尔斯泰的恶性循环来得比密尔要晚(50岁才到来)且发展得更糟。“我的整个生命停滞不前,”他写道,“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当然这些事是我必须做的;但是生命不存在了,因为满足任何愿望在我看来都不合乎理性。”[22]也可以这么理解:没有什么事值得去做。但那并不是密尔的情况。我也没有经历这种感觉,并且希望你也不会。
典型的中年危机不会转向对理性或价值的普遍怀疑主义,也不会转向危及正常生活的哲学式怀疑。它们并不祈求一种广泛的虚无主义,而是期望对关于自身和世界的难以捉摸的概念有所把握,这就是它们在哲学上富有趣味的原因。找不到做任何事的理由,找不到追求更好结果的理由,这种无尽的空虚和中年危机带来的空虚不同,究竟是什么将两者区分开来的?这是个哲学问题。如果还存在终极价值,我们的中年究竟缺失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要求对具体价值予以区分,就像区分手段和目的那样,尽管这更加微妙、费解,也更为深刻。我们需要一块更好的伦理观念调色盘,以描绘中年的哲学肖像。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卖弄概念的方式倒可以解决中年危机的困扰。
所以密尔的问题出在哪儿?不是极度的利己主义,也非了无一事牵挂的结果。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利他主义悖论,以及这样一个观点:密尔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关照给他自己造成了对幸福认知的空虚,这种空虚会折磨所有人,包括你。这一点密尔自己也逐渐认同了。为了知道何以如此,我们必须以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密尔思想的第二次转变,重新诊断他的精神崩溃,这一次诊断像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悄然应和。
追求不朽
密尔所说的自己观念中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是“头一次,[他]在人类福祉的首要必备条件当中,为个人的内在修养找到了合适位置”。[23]他在此所指的是艺术鉴赏对人类情感的表达和完善。
密尔自己作品的美学价值仍值得推敲。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深受密尔的利己主义悖论影响,他在1872年这样建议一个朋友:“错过密尔的自传不会让你失去任何东西。我从没读过如此无趣的书……简直是蒸汽机的自传。”[24]但我们很难不被密尔的这段读书笔记感动,在经历了两年的精神危机后,他读了威廉·华兹华斯的诗歌。
华兹华斯的诗歌之所以成为医治我心灵状态的良药,是因为他的诗歌不仅叙述外在的美景,还有动人美景下蕴藏着的情感以及受其感染的思想。它们看上去正是我苦心寻找的情感沃土,在一行行诗句中,我仿佛从内在愉悦的源泉里吸取了养分,从富于同理心和想象力的快乐之源中有所收获,这些是全人类都能分享的;它们与挣扎或缺憾毫无联系,每当人类的物质或社会条件实现进步,它们就将更加丰富。从这些诗句里,我仿佛明白了,当人生中所有更可怕的邪恶被祛除后,究竟什么才是幸福的永恒源泉。当我从诗歌中汲取正面影响,我瞬间感到自己更加健康和幸福了。[25]
密尔尤其喜爱华兹华斯的《颂诗:不朽之光数少年》。他花了不少笔墨对比华兹华斯与自己的经历:“他也觉得,青春时期初次品尝人生欢愉带来的那种新鲜感不可能持续很久;但是……他寻找弥补的办法,而且找到了。现在他正在教我的,正是此中秘诀。结果是,我逐渐并彻底地从习以为常的沮丧中走了出来,再也未曾受其困扰。”[26]
我不嫉妒密尔的康复:对他管用就好。但他做的比较很是牵强。当华兹华斯歌颂着“欢乐和自由,童稚之信条”时,他怀念的可不是密尔那样的童年!关键的事实在于,他们的生活并不相似,但对于密尔,歌颂天性的诗歌正充当了独特价值和情感培育的源泉,这也是华兹华斯诗歌结尾的主旨:
全凭我们赖以生存的人类心灵,
凭它的柔情,它的欢乐和恐惧,
一朵摇曳的小花都能动我心旌,
牵起非啼泣所能尽的深沉思绪。[27]
人们也会挑剔华兹华斯的文字。密尔承认:“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一定有]更伟大的诗人。”[28]在密尔看来,华兹华斯是“不具诗意的诗人”,[29]同时他也坚称,“在那个时候,即使满怀着更深沉和高尚感情的诗句也无法像华兹华斯的诗那样给予我鼓舞”。[30]在华兹华斯的诗中,密尔“感受到了宁静的沉思中存在着真实而永久的幸福”。[31]对于天生不解诗意的密尔来说,这次体验算得上是惊人发现。
密尔从艺术的价值中到底获得了什么?他的所得对于深陷中年颓态的我们又有何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得更久远一些,直到亚里士多德这位最积极地为宁静的沉思摇旗呐喊的古希腊先贤。借助他的理论工具,我们才能推导出预防中年危机的第二定律。
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是柏拉图雅典学园的学生。柏拉图会开玩笑地昵称他为“努斯”(no?s),意为心智或神智。心智生活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扮演着一个奇妙的角色。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我之前提过两次的亚里士多德授课讲义集)令人费解的一点,是其花了九卷或者说九章来阐释实践德性,比如勇敢、节制和正义,而最末的第十卷,却通过贬抑实践生活来褒扬纯粹理性。一代代的读者被这个偷梁换柱的手法迷惑了,无数学者前赴后继试图为之辩解。
有趣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德性不满的原因与密尔为自己转而求助情感培育的理由非常接近。
实践德性活动体现在政治或战争事务中,但与这二者相关的行动看起来都没有闲暇可言,战争活动尤其如此。(没人会为了战争而挑起战争;任何出于征伐和屠杀目的对友邦悍然发动战事的人,都会被看作嗜血暴徒。)另一方面,政治活动也无闲暇,而且常常将目标瞄准政治活动之外的东西,比如专制的权力与荣耀,抑或不惜一切代价给自己及同胞带来幸福——这种幸福与政治活动不同,我们也无法在政治活动本身中找到它。[32]
就像密尔一样,亚里士多德担心实践德性的活动——发动战争、从政、变革社会——是靠“挣扎与匮乏”维系的。[33]这些活动的价值取决于它们致力解决的麻烦、难题和需求。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它们将百无一用。这就解释了悍然向友好邻邦宣战以制造大动干戈的机会为什么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密尔还可能会补充,同样愚蠢的还有为了给像他这样的改革家创造工作机会而延续人类苦难的行为。
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政治家的成就具有终极价值。它们“值得求取,既因自身,亦因他物”,“那是一种不同于政治活动的幸福,我们无法在政治活动本身中找到它。”[34]他没有花费九卷笔墨在牙科护理和一夜暴富这样仅仅是工具性的事情上,但是对他而言,政治活动的价值是缓和性的,是一种负负得正的价值:它回应不公、苦难和战争,致力于消灭这类恶。当然更好的情况是有一个这样的世界,在那里没有缓和的必要,没有损坏需要修复,没有伤痛需要治愈。这正是实践德性的局限和瑕疵,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实践德性被排除在亚里士多德构想的理想生活之外。就像密尔的社会工作和政治改革,他针对的是“挣扎或缺憾”的状况,而我们希望这些状况最好一开始就不存在。[35]除了缓和危害的作用之外,政治活动能不能有更积极的目标?或许我们的政治家资助了人文艺术、基础科研或是哲学本身呢?大概会吧。但是亚里士多德会抗议:无论我们从国家那儿获得了什么样的帮助,自给自足总比伸手求助要好。而仅仅修正我们的政治理论也无法让我们知道政治家应当支持什么样的活动。
这正是沉思进入我们视野的地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沉思不是为了解决理论难题,更不是为了将我们的理论付诸实践,而是为了反省我们已经得出的答案。这一活动“似乎仅因其自身就令人喜爱”,他写道:“因为除了沉思自身,它没有其他产物。而在实践性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会得到些行动以外的东西。”[36]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中,沉思的生活“毋庸置疑拥有终极价值”,“我们追求沉思从来都是因其本身,而非因他物”。[37]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就好像我们应该为沉思的无用而褒奖它。这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看重的不是沉思的无用,而是其完全正向的价值。沉思不回应麻烦、缺憾、苦难或冲突,它堂而皇之地扮演着一个多余角色。沉思不是为了阻止不公或伤害才有必要做的事情,即便在一个理想世界,我们也期望沉思。与政治活动不同,沉思是悠闲的,“[而且]幸福依赖闲暇;因为我们的奔忙是为了拥有闲暇,就像发动战争是为了得到和平生活”。[38]
尽管未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文字,但密尔一定读过《尼各马可伦理学》,还很可能是在10岁时读的希腊文版。如果你的改革抱负顷刻实现,你将有何感想?这个困扰着密尔的问题引出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区分,缓和性价值和沉思的正向价值是不同的。如果能将世界的不公连根拔起,如果能将人类的苦难彻底治愈,我们还剩下什么事可做呢?在精神崩溃前,密尔也没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尽管他的一系列活动具有终极价值,但它们并非最完善的,而只是回应人类可悲的需求。
在危机爆发后,一切都改变了。在诗歌中,密尔找到了“与挣扎或缺憾不相干的内在愉悦的源泉”。[39]它带来的快乐并非来自克服艰难的喜悦,而是“生活中那些更可怕的恶被祛除以后,留下常在的幸福源泉”。[40]密尔早年生活的困扰是,在减轻人类苦难的目的之外,他找不到一丁点线索来告诉他什么事情还值得做。如果我们最热切的希冀就是免于遭受苦难,过不那么糟的生活,那为何要费劲来人间走一遭?如果一切价值都是缓和性的,值得我们关注它本身的事物或许依然存在,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而非仅仅是手段,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并不值得过。既然如此,一开始就不存在于世间或许与这样活着一样好,甚至更好。
和我一样,你或许不是如此狂热地无私,或许也不是个雅典式政治家。但困扰着亚里士多德和密尔的问题,依然存在于现代生活中:现代生活有各种待满足的需求,需要支付的账单,需要喂饱的肚子,需要解决的困扰,盘踞着“挣扎和匮乏”。[41]想想那种除了睡觉别无所求的日子:暂时忘掉还有孩子要照顾,不用去做公司的救火员,无须绞尽脑汁讨好你的伴侣。别误会我的意思,这些事情固然都很重要。它们的价值也许是终极的,但本质上仍是缓和的。当你被绑着去完成这些事务,像推磨一样无聊,日复一日,也许就没有时间去做那些你想做却不是必须完成的事了。与密尔差不多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这样写道:
劳作、忧虑、艰辛和麻烦的确是几乎每个人的生活命运。可是,如果每个欲望一诞生就得偿所愿,人又该如何填满自己的生活,如何消磨时间?[42]
除了阻止事情恶化或者推动事情好转以外,还有什么是值得做的?如果对此你想法全无,叔本华提出的这个问题就会成为你的问题,它也是密尔问题的一个变体。“劳作、忧虑、艰辛和麻烦”诚然不可避免,但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了吗?
这种危机步步紧逼,有起有落。缓和性活动可能或多或少占据了你的生活,各种需求也是如此,你也许只有零星闲暇才能喘口气。但当这些需求不再占据你那么多时间(也许那时你的孩子已经长大),危机可能就会浮现:你开始感到空虚,你的日子不再被从前那些必须完成的事情填满,你却发现自己无事可做。
这也是中年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像密尔的精神崩溃一样,这不是一种虚无主义。造成危机的不是世俗价值的缺席,而是完成必要工作的折磨。这些工作的确值得去做,但有些事遗漏了。为了清晰描述遗漏之事,我们得在具有终极价值的活动中,把缓和性活动与不只有缓和性的活动区分开来。
尽管哲学家们热爱使用佶屈聱牙的行话,但他们尚未发明适用于这一区分的专用术语,所以我在尽可能长话短说的情况下还是不得不用这样冗长的辞藻。(“不只有缓和性”是一个三重否定:不只是去阻止或消灭一些不好的事物。)这可不是我的错。由于道德哲学忽视了我们之前对亚里士多德和密尔做的那种区分,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描述什么是“不只有缓和性”。既然它令生活积极向善,而非仅仅比原样好一点,这就解释了生活到底为什么值得过,所以我称这种价值为“存在主义”价值。由此我们得出预防中年危机的第二定律:在你的工作、人际关系和闲暇时光中,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活动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这听起来有点宏大,尤其因为关于存在主义价值我们最主要的例子是宁静沉思的价值。要获得这种价值,你是不是非得阅读华兹华斯,或是与亚里士多德一起思考世界的理性秩序?不见得。因为存在主义价值形式多样,也更接地气。尽管密尔和亚里士多德双双使用了“沉思”这个词,但他俩想表达的却完全不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的沉思是一种寓于科学探究之中的理解活动:它是对以神为目的因[43]的宇宙结构的思考。引发密尔沉思的则是诗歌鉴赏与更普遍意义上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著作中只提过一次“艺术的沉思”,用以说明某种你可以与朋友一起开展的活动。)[44]这些活动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的非缓和价值。一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打开一扇大门,寻得其他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活动。重要的是,即使人类生活的不幸都消失了,这些活动仍可以继续。例子很多,从研习哲学和高雅艺术,到讲幽默故事、听流行音乐、游泳及帆船运动,还有与亲友玩游戏等,都在此列。这些活动也许是对生活难题的回应,也许会让你从痛苦中分散注意力,或仅仅是为了消磨时光。但每一种都能成为没有挣扎和缺憾的“内在愉悦之源”,成为“生活中那些更可怕的恶被祛除以后”[45]幸福的永久土壤。
我们是否由宏大主题摇摆着坠落凡间了?由对神与自然的沉思转而拾起一个有趣的新爱好?既是,也不是。
不是,是因为并非只有兴趣爱好才具有存在主义价值。你也可以在工作中或是与他人的交往中,找到这样的价值。我有难以置信的好运气,能够找到一份让我一边领着工资,一边思考和写作的工作: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有存在主义价值的,至少有一点吧。(我猜当我写作本书时,或许就有机会减轻人类的痛苦。但这事说不准,而且我确信你不会这样评价我其他的书。)还有一些工作对于物质的或非物质的生产有贡献,亚里士多德会否认它们具有存在主义价值,因为它们不过是满足需求罢了。在理想世界中,家具和食物可以长在树上等人采摘。这与亚里士多德对艺术价值的漠视一脉相承,我们不必赞同他的观点。我们可以坚信,木工和烹饪也能成为理想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依赖于人类的需求,也不会是那种最好原本就不存在的需求。工作可以具有存在主义价值,友谊也是同理。这一点会让亚里士多德很费解,因为他坚信沉思是唯一存在主义的善。(最好的朋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有助于我们沉思的人,但如果可以离开朋友独自沉思,我们大概就应该这样做。)我们自己没必要那样想,即便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我们大概也会愿意与朋友们共度时光。
但另一方面,许多有价值的工作确实是缓和性的,如我们需要医生、教师和社工。而兴趣爱好的确可具有存在主义价值,比如中年正是开始打高尔夫的好时候,这是最具存在主义的一种活动了。你还可以去跳拉丁舞,或者弹钢琴。与其在向中年妥协的世俗生活中倍感消沉,不如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无聊的消遣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意义。亚里士多德批判实践德性的生活时,通过构想不需要缓和任何东西的神来阐释实践德性的缺点:“我们认为神最是享有福祉与幸福的;但神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公正的吗?如果众神间也有订立契约、欠债还钱一类的事情,看起来不是很荒谬吗?……节制的行为呢?既然众神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对他们节制的夸赞不是索然无味吗?”[46](可笑的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时常争吵,放纵,和凡人睡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们根本就不是神。)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活动与永生不朽相称:它们可归属于理想生活。当你与朋友玩“大富翁”或读书自娱,你正分享着神的生活。
请允许我说说哪些意味是以上分析所没有的,以便在此了结。它不意味着存在主义价值比其他任何事物更重要,或总是应当居于首要位置。尽管亚里士多德几乎持有这类危险的观点。
我们绝不该听信有些人建议的,人类就要思考人类的事情,凡胎就要思考凡胎的事情。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追求自身的不朽,拼尽全力过上与我们内心最美好的东西相配的生活。因为,尽管美好的东西为数不多,但其力量和价值却远远胜过一切。[47]
我不认同亚里士多德。当生活的需求非常迫切,紧急到不能忽视的时候,终日执迷于沉思、读华兹华斯或打高尔夫就大错特错了。凡胎还是要想凡胎的事。
但如果你失去了与存在主义价值的联系,如果你无法为神性活动(那些令你的生活开始值得一过的活动)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空间,你就面临着与约翰·密尔无异的中年危机风险。有时候,你应该抓住机会,追求自身的不朽。
牢房的阴影
我们从密尔身上学到了什么?像密尔这样的人,危机已经在路上等着他们了:他们的生活缺少存在主义价值,最渴望的事物不过是缓和伤害,对他们来说,消除痛苦很好,和有这样的痛苦等待消除一样好。这真是一种极度悲观的看法。只有像密尔那样的童年,才会遮蔽诗歌带来的欢乐,掩盖满足他人需要以外其他事物的价值。
还有更多司空见惯的危机,尽管它们不像密尔的危机那样黯淡,仅仅表现为存在主义价值的相对缺席(不足而非全然没有)。工作和家庭的重压令人不想做其他任何事情——如果这就是你的生活,那么你就得为具有存在主义价值的活动腾出时间。这些活动相比做好你的工作或确保孩子们衣食不愁或许不那么重要,但它们的价值是全然不同、不可替代的。
我在前文说过,中年危机有很多种类。受约翰·密尔的启发,我们已经讨论了其中的一种,即关于不可避免性的危机(a crisis of necessity)。这里有些讽刺的是,教会密尔解决早年危机的那位诗人自己也遭遇了危机,他没有密尔那样的乐观心态。密尔引用了《颂诗》作为自我治愈的指引,可能想起的是这些诗句:
袭上我心头,曾有愁思几缕,
及时排解,未积成胸中块垒,
又同前,身心壮健。
泻瀑自悬崖正把号角吹起。[48]
但号角似乎吹早了,因为下一节诗这样结尾:“哪去了,空灵的焰,梦幻的辉?/哪里还有那般梦境,那种瑰丽?”这还真治愈啊!怀旧与失落的氛围不断地重复,正如华兹华斯的诗歌一次次企图回归到被社会的“牢房”束缚住的童真和自由。
那么最后四行诗句[49]怎么样呢?它们是像密尔所想的那样,在颂扬被自然启迪的情感吗?不,实际情况要暧昧得多。牵起我们深沉思绪深的是啼泣,而非微笑。“牵起非啼泣所能尽的深沉思绪”这句诗扮演了思想深度的角色,这一深度只能通过语言笨拙地表现出来,这句诗同时也承担了“社会规范”的角色,雕琢和压迫诗歌的其余部分,就像诗人的感受必须符合格律。甚至诗歌本身也已经被文明的障眼法(它就像是社会牢房墙壁上的胡写乱画)耽误了。
华兹华斯没能从他的中年危机中恢复过来。在35岁完成《序曲》(The Prelude)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后,他便江郎才尽,在余下的40年生命里几乎没写什么文字。没有什么能够“唤回过去的时光/那早已零落的花卉的芬菲”。你无须像华兹华斯一样相信灵魂不朽,化身重生,“曳着光辉云彩……/我们从天帝那儿来,那是我们家园的所在”,并深深怀念那青春年少时的广袤天地、锦绣前程和无拘无束。尽管再没有回头路了,但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究竟在怀念人生定型之前那段时间里的什么东西。那是35岁或50岁,对乔治·奥威尔而言,到了50岁“每个人都有了他应得的那副面孔”。[50]拥有选择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接受错失机会的现实?我们能否“在有了哲人般的心灵之后/从留在身后的时光里”汲取力量?在下一章,在小说家和哲学家的帮助之下,我们将试着解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