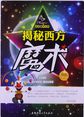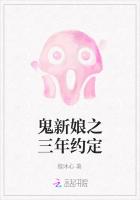大歌剧[12]从根本上说是归属于19世纪的形式,今天我们的歌剧院有如博物馆,典藏着瓦格纳、威尔第的作品,供20世纪的人们观赏。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不过,还有一点同样毋庸置疑:有些19世纪的曲目在当时就已经是反动之作,还有一些则在音乐与剧场领域引领革命。无论如何,19世纪的表演始终与当时的文化及美学实践紧密关联,这种关联充满活力并且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比如作曲家威尔第、瓦格纳、普契尼总是在现场引导并直接介入、影响自己作品的最终呈现,观众及演出者通常了解歌剧所使用的语言,而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使用一种共通的音乐语言。
今天,人们很难拥有19世纪的感受。比如,在我们看来,本质上属于保守之作的《阿依达》与《女武神》这样的革命之作,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有一回,一个爱说笑的人提到大都会歌剧院的一场《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演出时称:“四个胖子摸黑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唱,并且不知所云。”这句话稍加改动,几乎可以套用在大都会上演的所有歌剧身上。如此昂贵、分量十足的饕餮大秀理应讨观众的欢喜才是。而事实上,大都会每一个稍有名气、能吸引人的歌者简直都可归入“怪物”的行列——他们用大家不熟悉的语言歌唱,展现过时的音乐风格,夸张的戏剧表演毫无说服力。至于那些服装设计和导演,他们大多只是让歌手穿上古怪的衣服,叫他们一脸严肃、煞有介事地在台上走来走去。
冒着得罪众多歌剧爱好者的风险,我还要再加上一点,今天的问题很多来自意大利剧目本身。意大利剧目大多是些二流货色,罗西尼除外,他是真正的天才。像帕瓦罗蒂如此怪异的风格确与意大利歌剧琴瑟和鸣,如今他声名显赫、受世人追捧,这本身就是对意大利歌剧的控诉。这些歌手将歌剧表演的智慧贬低到最少,把要价过高的噪音推到最大。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剧场标准以及同样低标配的音乐性及导演堪比雪上加霜:这一切所构成的环境必然是反理念、反审美的。
之所以把话说得这么极端,是因为我在纽约市立歌剧院看了一场非凡的现代歌剧,安东尼·戴维斯(Anthony Davis,1951— ,美国作曲家、爵士钢琴家)的《X》(原名《马尔科姆·X的生活及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Malcolm X])。而就在《X》上演前后,我恰好看了两场大都会的演出。这两场演出都极有问题,一出是大都会乐季开幕首夜大戏《女武神》,另一出是《阿依达》。即便戴维斯的作品与大都会这两部歌剧在时间上不撞车,我依然会觉得大都会在拼命规避有意思的当代作品,这真令人恼火。事实上,今日常演剧目有百分之八十被诸如《波西米亚人》《托斯卡》《弄臣》《拉美莫尔的露琪亚》《诺玛》等剧包办,但这并非我要表达的重点。我反对的是,大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演出19世纪的剧目,其主导观念好像抄袭了193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歌剧逻辑——男女主角清一色又矮又胖、大嗓门、一副蠢相,并且歌如其人。就连19世纪的先锋革命之作都没能逃过无精打采、死气沉沉的命运,在现代人的演绎下,它们听上去似乎与保守派作品半斤八两。就算演出剧目范围狭隘,也没有理由剥夺剧目的可能性,令一切变成拙劣的滑稽。
以《女武神》为例,此剧是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歌剧中的第二部,被选来为大都会全新的指环全集打头阵。大都会找来贝伦斯(Hildegarde Behrens,1937—2009,德国女高音)饰演布伦希尔德,她可以胜任此类角色,有时也会有出彩的表演;奥特迈耶(Jeannine Altmeyer,1948— ,美国女高音)塑造了一个热烈非凡的齐格琳德;豪格兰(Aage Haugland,1944—2000,丹麦男低音)饰演洪丁,声音尚稳,不过却总是有种奇怪的隔阂,也许这是他最不该演的角色。此外,大都会的管弦乐团的确是一线好团,不论是准确性、音调语气、质感上的精致文雅或者声音的灵敏度都比纽约爱乐更胜一筹。但瓦格纳需要的不只是几个好歌手和一支优秀的管弦乐团,更需要大都会歌剧院在制作中注入自己的美学。遵奉威尔第的人歌颂他的“天真”,可瓦格纳不一样,因为瓦格纳也是哲学家(据某些人的说法,他从不曾停止过怀疑),更重要的是,他是音乐和美学领域的先驱。1870年,当威尔第创作《阿依达》时,瓦格纳的影响已传遍欧洲。正如威尔第自己所承认的,瓦格纳的影响力鼓舞着歌剧写作朝更精进、更关注细节、更强调反思的方向迈进。反讽的是,如今大都会演出《女武神》的构想却更多地遵循、依赖《阿依达》的影响,朝保守派靠拢,恰恰是一种本末倒置。
迄今为止,《指环》依然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歌剧构想。瓦格纳有意借由这套作品,从历史/神话的角度解读现代文化,并且,尼采的读者都知晓,这套作品是以古希腊的阿提卡悲剧为原型。瓦格纳的音乐知性深广,德奥音乐传统从巴赫、亨德尔,经由维也纳古典主义再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正是瓦格纳关于乐团、人声以及艺术建构的理解将德奥音乐带入极盛时代。对20世纪歌剧院团而言,另有两点使得演绎瓦格纳极具挑战。其一,在歌剧的诠释上,至今没有哪一位歌剧作曲家比瓦格纳拥有更多的理论与实践,部分原因来自拜罗伊特(作为瓦格纳学的中心,拜罗伊特由瓦格纳亲自设计,它的建立为一切有关瓦格纳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参照),再者那些献身于瓦格纳音乐的音乐巨匠们功不可没。莱文此生头一回指挥演出《女武神》时,想到冯·彪罗(Bülow,1830—1894)、尼基什(Nikisch,1855—1922)、施特劳斯、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克纳佩茨布施、索尔蒂(Solti,1912—1997)、布列兹这些指挥过该剧的前辈,他恐怕要紧张恐惧,这绝不是什么令人豁然开朗的作品。
关于瓦格纳作品还有第二个难题值得人们深入探究,即他的创作模式就本质而言是叙事体式的,虽然并非绝对。我想,若是真要拿他与谁相比较,最有效的不是那些同时期的歌剧创作者,而应当是福楼拜、詹姆斯、托马斯·曼以及普鲁斯特(后两位几乎被瓦格纳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叙事一如《尼伯龙根的指环》,是循环式的、充满反思的。阴郁的、不断重复再现的主题就此展开:每个事件都指涉先前所发生的一切,而先前的一切又印证了后来的种种结果和命中注定的劫数。致密的音乐线条一往无前,同时也左腾右挪、纵横决荡,整个过程不断蓄积压力与张力,直到循环终了,一切死锁不能动弹,沉重且具有强大自觉意识的音乐再也不堪自身重负而崩塌:瓦格纳似乎延伸了弗洛伊德的“多元决定论”[13],或者说将其应用于音乐写作中,并对半音风格与复音音乐大加发挥,甚至制造出魔性的效果。这无异于在理论层面将调性体系赖以维系的清晰、理性炸个粉碎。
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演出《指环》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工程——最近一次具备勇气与相应智慧的尝试是在十年前,布列兹与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ereau,1944—2013,法国歌剧与电影导演、演员)的合作。显然,大都会找不到这等人才来演《女武神》,不过,就因此有理由把这出歌剧做得如此毫无方向、漫无目的吗?
首当其冲的是莱文的音乐构思问题,他与奥托·申克(Otto Schenk,1930— ,奥地利歌剧与戏剧导演)的戏剧呈现完全无视战后瓦格纳作品演绎的所有进展与成果。他们的合作中没有丝毫象征意味,没有哪怕一点点荣格、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成分,只有生发于1900年前后的北欧式“自然主义”风格呈现,这种风格之下的所谓戏剧性就是以激动的姿态从舞台中央跑到门边,再从门边跑回舞台中央。饰演齐格弗里德的彼得·霍夫曼(Peter Hofmann,1944—2010,德国男高音)身着过于简单的服装,容光焕发,金发飘扬,正是以此等“纯粹自然”的风格手法来诠释人物的(他无法胜任G或A以上的音域,不过在第一幕中,高音区表现尚佳,唱得还算像样)。
第二个难点,演出瓦格纳的作品必须密切留意随即发生的戏剧性发展。《指环》中包含许多大段的吟诵,用以推动剧情叙事并揭露人物的性格;在这些段落里,演员与导演必须有能力传情表意,使观众意识到一些意义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第二幕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个部分,沃坦细述早年生活的故事:如何降临尘世,如何强暴爱尔达生下布伦希尔德,如何与法夫纳、法索特结约,如何与阿尔贝里希相争。如今,身为神明的沃坦犹如被禁锢的囚徒,他想方设法欲将自己从承诺与法则交织的网中挣脱出来(这个办法便是利用英雄齐格弗里德)。沃坦的叙述是《女武神》的核心;借由沃坦的叙述,一种得以自由创造的意识显露了出来,它呈现出文化与政治的困境并加以戏剧化。不过根本的矛盾在于,意识摆脱不了它的创造,却又要无止境地寻求新手段以实现超越道德范畴的、全新的自由。这或许是最具德国本性的表达,骇人的恐怖与狂热的欣喜一应俱全。这样的作品只有才智卓绝的艺术家能够胜任。此外,还需要一名聪明的指挥,他才不会将管弦乐声部大段的沉寂单纯地视作空洞无物的峡谷,偶尔来声巨响,打破静默。可以听听汉斯·霍特(Hans Hotter,1909—2003,德国低男中音)的录音,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瓦格纳大家之一,在四十分钟的宣叙吟唱里,他的张力、技巧造诣,他对于词句与乐谱的理解,皆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都会版的沃坦由西蒙·艾斯特斯(Simon Estes,1938— ,美国低男中音)扮演,这是个不错的轻量级男低音,唱过一些《指环》以外的瓦格纳角色。然而,沃坦是个威严伟岸的角色(霍特身高大约六英尺五英寸[14],且台风威仪凛然),艾斯特斯缺乏威严之感;他略显细小的嗓门能够得着中、高音区,但低音部分明显吃力。他的宣叙调内心戏深度不够,唱法与表演部分亦看不出有任何主导概念或观点。更糟糕的是,艾斯特斯(包括其他歌手)所唱的是复杂的、诗一般的词句,无人能懂。大都会坚持不准备唱词字幕,实属可笑。观众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东西?人们会花费一百块美金看一出表演低劣、使用世界语的莎士比亚戏剧吗?
退一步说,至少莱文在指挥过程中对于音乐方向的把控还算流畅,乐团敏锐地回应了他的要求:在冬天的暴风雨场景中呈现出温暖,在女武神的骑行里表现出喧闹的声势,在魔火场景里传递极富有诗意的浩瀚辽阔。然而,总体而言,他对这部作品的音乐构想更像是快笔速描,准备来日再充分发挥似的。最令人气愤的是,莱文是如此有天赋,却不知怎的,总是忽略音乐里最具反思意义、最知性的层面,唯有经过深思熟虑、不断反思才有可能触及的层面。
似乎是出于某种精明,他将《阿依达》留给不如他的人去处理。表现抢眼的格蕾斯·班布丽(Grace Bumbry,1937— ,美国次女高音)饰演安奈瑞斯一角,火爆的安奈瑞斯一举扫灭情敌,即那个可怜的、如今再不能开口说话的女奴阿罗约。除了班布丽,这场演出简直就是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威尔第在《阿依达》这部作品里的失算之处在于——谱曲部分过度发展,而故事情节部分发展不足,他在作品中对东方主义埃及学的观照死气沉沉、毫无趣味,作品虽为开罗而写,但作曲家对那个地方却显出冷淡疏远——这一切弱点,在大都会时而趾高气扬、时而结巴踉跄的演出中愈发突显,叫人痛苦不迭。壁饰与浮雕在你眼前腐朽剥落,一个意气风发、权势鼎盛的法老王庭为何一定要以废墟示人,只有天晓得。
幸好这不是世界末日,还有《X》!作品由安东尼·戴维斯担纲作曲,剧本由杜拉妮·戴维斯(Thulani Davis,1949— ,美国剧作家)根据克里斯多夫·戴维斯(Christopher Davis,1950— ,美国作家)的原著改编而成。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政治上毫不妥协,音乐风格虽谈不上统一连贯但相当有趣味,至于戏剧层面的表现堪称精彩绝妙。诡异的是,如此剧目竟能在这个极端保守的年代公演。整部歌剧基于《马尔科姆·X自传》一书生发而成,故事情节与原著紧密贴合。全剧分为三幕,每幕分别有三、四、五个场景,涉及马尔科姆1931年到1945年的早期生活,先是父亲于兰辛(Lansing)逝世,他本人混迹波士顿街头以及锒铛入狱的经历;接下来是1946年到1963年的中期,马尔科姆皈依伊斯兰,成为以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的弟子;末段,我们看到他的麦加之旅、他与以利亚·穆罕默德分道扬镳,最终遇刺身亡。
情节背后皆是巧妙的历史典故:贾维主义[15]风尚,黑人分离主义与黑人穆斯林的兴起,肯尼迪遇刺,泛非主义[16],迈德加·埃夫斯(Medgar Evers,1925—1963,美国人权活动家)与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925—1961,非洲政治家,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遭谋杀,等等。此外,这部歌剧通过刻画为数众多、设置巧妙的角色呈现出各类黑人群体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整体效果类似史诗戏剧、古典歌剧以及爵士乐表演的混合。马尔科姆时而领导受压迫的族群,时而化身受压迫族群的代表。显然,他与同族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紧张感,但在我眼中,这是意味颇丰的冲突。霍尔特(Ben Holt,1955—1990,美国男中音)饰演的马尔科姆,举手投足间带着克制,又流露出不羁的人格力量,恰是角色深陷两难困境时活生生的体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946— ,美国抒情男高音)风格大胆的表演,他分饰两角,一个是带点浮夸的街头悍将斯特里特,一个是爱说教的、隐约散发危险气息的以利亚·穆罕默德。如此交相辉映的一对角色,如此有力的诠释,实在难得。
《X》剧中最有冲击力的部分无疑是规模庞大且多样化的爵士乐队表演,尤其在第一、第三幕。狱中场景的表现力较弱,第二幕中相当一部分段落同样欠缺足够的强度与力道。这些地方常常把话题铺得过开,东拉西扯、散乱无章,在马尔科姆对肯尼迪遇刺喊出“作恶者必自毙”那句臭名昭著的难听话前,我们的剧作者便急于想先将一大堆有关马尔克姆皈依伊斯兰的信息塞给观众。第三幕的独特力量来自于马尔科姆与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对峙,以及他在麦加的二度皈依。在麦加这场戏中,戴维斯安排了一长段严格遵循宗教礼仪的“法谛哈”(fatiha),即《古兰经》首章开端的祈祷,相当成功。将这两个场景前后衔接,是十分有利于戏剧性呈现的恰当手法,因为马尔科姆在伊斯兰教中臻于自觉与他从种族排他主义的所有束缚中解放自己,两件事背后指涉的是同样的意涵。马尔科姆的孤寂,以及他最终对于伊斯兰普世主义的接受,似乎受到勋伯格《摩西与亚伦》的影响,虽然这之间有些许差异:“神怒”主题在勋伯格笔下表现为“神—人”关系,上帝的愤怒加诸摩西身上;而《X》剧则替换为单方面的视角,通过马尔科姆的历史及其身处的时代环境来呈现:“一股浪潮在你背后升起,你被卷走,随它而去。”此外,戴维斯在剧中明确地将马尔科姆的自我解放与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甚至南非的自由战士相关联,马尔科姆的救赎观及他遇刺牺牲也因此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市立歌剧院制作的《X》剧,美妙地配合了戴维斯的音乐、故事及剧本。演员水平整齐划一、训练有素,表演敏锐有力,由此可见这部歌剧是多么贴合当代需要。我不是说唯有当代政治题材歌剧值得做。不过,歌剧制作必须包含能勾连当下、映射整体的重要概念,我们的确需要一些本身具备历史感,或者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相关的歌剧。虽然安东尼·戴维斯的音乐传递似乎充满间接迂回,我们必须意识到为《X》此类现代且感人的作品配以音乐语汇的艰难。克里斯托弗·基恩(Christopher Keene,1946—1995,美国指挥家)的指挥调度得当且极有掌控力。不过,我也意识到十二音列体系与爵士乐是两种相互交战的音乐语言,它们并不能完美融合。另一方面,戴维斯的韵律节奏处理很连贯,手法纯熟,生动、切题,不拘于美学,并非纯反射式的套路写作。《X》因而令人着迷。不过其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戴维斯诉诸政治话题进行铺陈而并不采用任何明显可见的音乐模型,以及他终究未能在写作过程中生成一种音乐风格(他偏重有力的戏剧性陈述)。一边是十二音列的严谨,一边是即兴式爵士的自由流动,两者构成《X》不可分割的两面,当戴维斯在两种不同音乐语汇中摇摆不定时,这些短板就尤为明显。
《X》是一部真正重要的原创歌剧,当然,它仍然有许多外部障碍需要克服。其一,作品与当下主流相对立;马尔科姆本身就不是白人观众容易接纳的角色。其二,此剧演出成本昂贵,至今看不到继演的计划。其三,钱都被普契尼与马斯卡尼抢走了,肯花时间学习这么困难的音乐的歌手寥寥无几。类似柏林剧团能够鼓舞制作精益求精的歌剧团队毕竟是极少数派。那些总是演出固定剧目的歌剧院应该多一点冒险精神,比如,从演《X》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