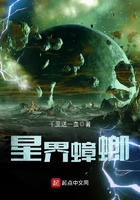汪曾祺:我事写作,原因无它: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
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理,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黄油烙饼
文/汪曾祺
萧胜跟着爸爸到口外去。
萧胜满七岁,进八岁了。他这些年一直跟着奶奶过。他爸爸的工作一直不固定。一会儿修水库啦,一会儿大炼钢铁啦。他妈也是调来调去。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长高了。
奶奶不怎么管他。奶奶有事。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给他接衣裳,接褂子,接裤子,接棉袄,接棉裤。他的衣服都是接成一道一道的,一道青,一道蓝。倒是挺干净的。奶奶还给他做鞋。自己打袼褙,剪样子,纳底子,自己绱。奶奶老是说:“你的脚上有牙,有嘴?”“你的脚是铁打的!”再就是给他做吃的。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他整天在外面玩。奶奶把饭做得了,就在门口嚷:“胜儿!回来吃饭咧——”
后来办了食堂。奶奶把家里的两口锅交上去,从食堂里打饭回来吃。真不赖!白面馒头,大烙饼,卤虾酱炒豆腐,焖茄子,猪头肉!食堂的大师傅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帽子,在蒸笼的白蒙蒙的热气中晃来晃去,拿铲子敲着锅边,还大声嚷叫。人也胖了,猪也肥了。真不赖!
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
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渣子,拉嗓子。人也瘦了,猪也瘦了。往年,撵个猪可费劲儿哪。今年,一伸手就把猪后腿攥住了。挺大一个克郎,一挤它,咕咚就倒了。掺假的饼子不好吃,可是萧胜还是吃得挺香。他饿。奶奶吃得不香。她从食堂打回饭来,掰半块饼子,嚼半天。其余的,都归了萧胜。
奶奶的身体原来就不好。她有个气喘的病。每年冬天都犯。白天还好,晚上难熬。萧胜躺在炕上,听奶奶喝喽喝喽地喘。睡醒了,还听她喝喽喝喽。他想,奶奶喝喽了一夜。可是奶奶还是喝喽着起来了,喝喽着给他到食堂去打早饭,打掺了假的小米饼子,玉米饼子。
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他每年回来,都是冬天。爸爸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土豆是他分的;口蘑是他自己采,自己晾的;黄油是“走后门”搞来的。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营养”,叫奶奶抹饼子吃。土豆,奶奶借锅来蒸了,煮了,放在灶火里烤了,给萧胜吃了。口蘑过年时打了一次卤。黄油,奶奶叫爸爸拿回去:“你们吃吧。这么贵重的东西!”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奶奶把黄油留下了,可是一直没有吃。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黄油是个啥东西?牛奶炼的?隔着玻璃,看得见它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他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扑痱子。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油汪汪的,很好看。奶奶说,这是能吃的。萧胜不想吃。他没有吃过,不馋。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儿。奶奶跟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说:“只怕是过得了冬,过不得春呀。”萧胜知道这不是好话。这是一句骂牲口的话。“嗳!看你这乏样儿!过得了冬过不得春!”果然,春天不好过。村里的老头老太太接二连三地死了。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原来打家具、修犁耙,都停了,改了打棺材。村外添了好些新坟,好些白幡。奶奶不行了,她浑身都肿。用手指按一按,老大一个坑,半天不起来。她求人写信叫儿子回来。
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
爸爸求木业社把奶奶屋里的躺柜改成一口棺材,把奶奶埋了。晚上,坐在奶奶的炕上流了一夜眼泪。
萧胜一生第一次经验什么是“死”。他知道“死”就是“没有”了。他没有奶奶了。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
奶奶给他做了两双鞋。做得了,说:“来试试!”——“等会儿!”吱溜,他跑了。萧胜醒来,光着脚把两双鞋都试了试。一双正合脚,一双大一些。他的赤脚接触了搪底布,感觉到奶奶纳的底线,他叫了一声“奶奶!”又哭了一气。
爸爸拜望了村里的长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把一些能应用的锅碗瓢盆都装在一个大网篮里。把奶奶给萧胜做的两双鞋也装在网篮里。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装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萧胜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他跟奶奶过惯了。他起先不说话。他想家,想奶奶,想那棵歪脖柳树,想小三家的一对大白鹅,想蜻蜓,想蝈蝈,想挂大扁飞起来咯咯地响,露出绿色硬翅膀低下的桃红色的翅膜……后来跟爸爸熟了。他是爸爸呀!他们坐了汽车,坐火车,后来又坐汽车。爸爸很好,老是引他说话,告诉他许多口外的事。他的话越来越多,问这问那。
他对“口外”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他问爸爸啥叫“口外”。爸爸说“口外”就是张家口以外,又叫“坝上”。“为啥叫坝上?”他以为“坝”是一个水坝。爸爸说到了就知道了。
敢情“坝”是一溜大山。山顶齐齐的,倒像个坝。可是真大!汽车一个劲地往上爬。汽车爬得很累,好像气都喘不过来,不停地哼哼。上了大山,嘿,一片大平地!真是平呀!又平又大。像是擀过的一样。怎么可以这样平呢!汽车一上坝,就撒开欢了。它不哼哼了,“唰——”一直往前开。一上了坝,气候忽然变了。坝下是夏天,一上坝就像秋天。忽然,就凉了。坝上坝下,刀切的一样。真平呀!远远有几个小山包,圆圆的。一棵树也没有。他的家乡有很多树。榆树,柳树,槐树。这是个什么地方!不长一棵树!就是一大片大平地,碧绿的,长满了草。有地。这地块真大。从这个小山包一匹布似的一直扯到了那个小山包。地块究竟有多大?爸爸告诉他:有一个农民牵了一头母牛去犁地,犁了一趟,回来时母牛带回来一个新下的小牛犊,已经三岁了!
汽车到了一个叫沽源的县城,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一辆牛车来接他们。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碌碌,骨碌碌,往前滚。他仰面躺在牛车上,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蓝天。牛车真慢,还没有他走得快。他有时下来掐两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车。
这地方的庄稼跟口里也不一样。没有高粱,也没有老玉米,种莜麦,胡麻。莜麦干净得很,好像用水洗过,梳过。胡麻打着把小蓝伞,秀秀气气,不像是庄稼,倒像是种着看的花。
喝,这一大片马兰!马兰他们家乡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大片马兰!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像是在一个梦里。
牛车走着走着。爸爸说:到了!他坐起来一看,一大片马铃薯,都开着花,粉的、浅紫蓝的、白的,一眼望不到边,像是下了一场大雪。花雪随风摇摆着,他有点晕。不远有一排房子,土墙、玻璃窗。这就是爸爸工作的“马铃薯研究站”。土豆——山药蛋——马铃薯。马铃薯是学名,爸说的。
从房子里跑出来一个人。“妈妈——”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妈妈跑上来,把他一把抱了起来。
萧胜就要住在这里了,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了。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
萧胜的爸爸是学农业的,这几年老是干别的。奶奶问他:“为什么总是把你调来调去的?”爸说:“我好欺负。”马铃薯研究站别人都不愿来,嫌远。爸愿意。妈是学画画的,前几年老画两个娃娃拉不动的大萝卜啦,上面张个帆可以当作小船的豆荚啦。她也愿意跟爸爸一起来,画“马铃薯图谱”。
妈给他们端来饭。真正的玉米面饼子,两大碗粥。妈说这粥是草籽熬的。有点像小米,比小米小。绿盈盈的,挺稠,挺香。还有一大盘鲫鱼,好大。爸说别处的鲫鱼很少有过一斤的,这儿“淖”里的鲫鱼有一斤二两的,鲫鱼吃草籽,长得肥。草籽熟了,风把草籽刮到淖里,鱼就吃草籽。萧胜吃得很饱。
爸说把萧胜接来有三个原因。一是奶奶死了,老家没有人了。二是萧胜该上学了,暑假后就到不远的一个完小去报名。三是这里吃得好一些。口外地广人稀,总好办一些。这里的自留地一个人有五亩!随便刨一块地就能种点东西。爸爸和妈妈就在“研究站”旁边开了一块地,种了山药,南瓜。山药开花了,南瓜长了骨朵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吃了。
马铃薯研究站很清静,一共没有几个人。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几个工人。工人都有家。站里就是萧胜一家。这地方,真安静。成天听不到声音,除了风吹莜麦穗子,沙沙地像下小雨;有时有小燕吱喳地叫。
爸爸每天戴个草帽下地跟工人一起去干活,锄山药。有时查资料,看书。妈一早起来到地里掐一大把山药花,一大把叶子,回来插在瓶子里,聚精会神地对着它看,一笔一笔地画。画的花和真的花一样!萧胜每天跟妈一同下地去,回来鞋和裤脚沾得都是露水。奶奶做的两双新鞋还没有上脚,妈把鞋和两瓶黄油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这地方大得很,没遮没挡,跑多远,一回头还能看到研究站的那排房子,迷不了路。他到草地里去看牛、看马、看羊。
他有时也去侍弄侍弄他家的南瓜、山药地。锄一锄,从机井里打半桶水浇浇。这不是为了玩。萧胜是等着要吃它们。他们家不起火,在大队食堂打饭,食堂里的饭越来越不好。草籽粥没有了,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现在吃红高粱饼子,喝甜菜叶子做的汤。再下去大概还要坏。萧胜有点饿怕了。
他学会了采蘑菇。起先是妈妈带着他采了两回,后来,他自己也会了。下了雨,太阳一晒,空气潮乎乎的,闷闷的,蘑菇就出来了。蘑菇这玩意很怪,都长在“蘑菇圈”里。你低下头,侧着眼睛一看,草地上远远的有一圈草,颜色特别深,黑绿黑绿的,隐隐约约看到几个白点,那就是蘑菇圈,长得溜圆。蘑菇就长在这一圈深颜色的草里。圈里面没有,圈外面也没有。蘑菇圈是固定的。今年长,明年还长。哪里有蘑菇圈,老乡们都知道。
有一个蘑菇圈发了疯。它不停地长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是有鬼,看着都怕人。附近七八家都来采,用线穿起来,挂在房檐底下。家家都挂了三四串,挺老长的三四串。老乡们说,这个圈明年就不会再长蘑菇了,它死了。萧胜也采了好些。他兴奋极了,心里直跳。“好家伙!好家伙!这么多!这么多!”他发了财了。
他为什么这样兴奋?蘑菇是可以吃的呀!
他一边用线穿蘑菇,一边流出了眼泪。他想起奶奶,他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他现在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越来越不好吃,因为掺了糠。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他恨这种掺糠的红高粱饼子,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他还是到处去玩,去瞎跑。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起先是拉了一牛车的羊砖来。他问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羊砖。”——“羊砖是啥?”——“羊粪压紧了,切成一块一块。”——“干啥用?”——“烧。”——“这能烧吗?”——“好烧着呢!火顶旺。”后来盘了个大灶。后来杀了十来只羊。萧胜站在旁边看杀羊。他还没有见过杀羊。嘿,一点血都流不到外面,完完整整就把一张羊皮剥下来了!
这是要干啥呢?
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
“啥叫三级干部会?”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
大队原来有两个食堂,南食堂,北食堂,当中隔一个院子,院子里还搭了个小棚,下雨天也可以两个食堂来回串。原来“社员”们分在两个食堂吃饭。开三级干部会,就都挤到北食堂来。南食堂空出来给开会干部用。
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吃了三天饭。头一天中午,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第二天,炖肉大米饭。第三天,黄油烙饼。晚饭倒是马马虎虎的。
“社员”和“干部”同时开饭。社员在北食堂,干部在南食堂。北食堂还是红高粱饼子,甜菜叶子汤。北食堂的人闻到南食堂里飘过来的香味,就说:“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好香好香!”“炖肉大米饭,好香好香!”“黄油烙饼,好香好香!”萧胜每天去打饭,也闻到南食堂的香味。羊肉、米饭,他倒不稀罕:他见过,也吃过。黄油烙饼他连闻都没闻过。是香,闻着这种香味,真想吃一口。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他问爸爸:“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他们开会。”
“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
“他们是干部。”
“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
“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萧胜的妈忽然站起来,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启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了一把莜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和南食堂里的一样。妈把黄油烙饼放在萧胜面前,说:“吃吧,儿子,别问了。”
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
妈妈的眼睛里都是泪。
爸爸说:“别哭了,吃吧。”
萧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汪曾祺的美食
汪曾祺丰富的阅历加之美食家的品味力,各地的饮食文化在汪曾祺笔下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胡同文化》把老北京的家常小吃写绝了: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要求并不高,有窝头吃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了。虾皮熬白菜来了,嘿!
《故乡的野菜》为故乡注入了宁静的诗意: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场小雨之后,就可听到叫卖枸杞头的声音。卖枸杞头的多是附近郭村的女孩子……女孩子也不把这当正经买卖,卖一点儿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成。
《故乡的食物》中体悟着普通百姓的生活情趣:蚬子是我所见过的贝类里最小,只有一粒瓜子大。蚬子是剥了壳卖的。剥蚬子的人家附近堆了好多蚬子壳。蚬子炒韭菜,很下饭。这种东西非常便宜,为小户人家的恩物。
《豆腐》可谓知上知下,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让人进入了豆腐大观园。从北豆腐、南豆腐、豆腐脑、豆花、水豆腐到臭豆腐、豆腐干、拌豆腐、烧豆腐、扬州和尚豆腐、麻婆豆腐、昆明小炒豆腐、砂锅豆腐及家乡的“汪豆腐”,而文中那句“从苏州上车,买两包小豆腐干,可以一直嚼到郑州”,读来更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汪曾祺还创作了《萝卜》《咸菜与文化》,萝卜、咸菜虽是各地都有的食物,却写出了各地特有的风情。
一个可爱的老头
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头,跟他在一起很温暖,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人间送小温”。
——高洪波
汪曾祺摒弃了宏大叙事的主题,平凡人日常衣食住行也可入文为传,以吃吃喝喝为文眼或主线也并不显得平庸,反而非常健康,是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钟晔
汪曾祺是个有“饮食境界”的人。他以委婉风雅的文笔娓娓道来,写得很有“情趣”。汪曾祺的吃,是平民的吃、家常的吃,始终怀抱着对底层民间的亲和力。汪曾祺的美食文章,无不显现出对民间饮食情趣的挚爱。汪曾祺美食美文的雅韵独步,能让人联想到明清小品的意蕴,如同古典的水墨画,淡雅脱俗,这是一种真正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感悟。诚哉,妙哉!
——付秀宏
与“汪老”做邻居啥感觉?
讲述:杨乔
我总觉得,与汪老一家处邻居是一种缘分。
1996年春,报社分房,我家乔迁福州馆宿舍,与汪曾祺一家正好在同一层楼,我们成了邻居。
其实,早在14年前,我就认识汪老了。
那时,我还没有调来北京,来京探亲期间,老公陪我上医院看病,一连串的排队等候,让我这个病人既烦躁又无可奈何。好在老公善解人意,让我坐在一旁看书等候。书是《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老公给我推荐了其中一篇《黄油烙饼》,看后很难过,也很压抑。书中主人公小胜子(萧胜)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一下觉得,自己就是小胜子,他的奶奶就是我的外婆。自那以后,我特别喜欢看汪老的书。去书店时,只要见到有汪老的书,必买。汪老在书中曾说过:“……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汪老那平淡而精彩的文字,常将我们带入那样的境界。
“文如其人”,读了文章,还想见作者。这下我们同住一层楼了,几次路过想举手敲门去看一眼我们尊敬的老先生,可又怕打扰,始终未敢。还是我在经济日报社的同事、老先生之子汪朗善解人意,刚搬新居不久,汪朗就托我将报社发的5斤鸡蛋给他父母送去,我说:“我不敢。”汪朗咧着嘴慢悠悠地笑着说:“这不是找个由头让你去见见老爷子嘛!”记得那天下班后,我提着鸡蛋,还未来得及回家,便按响了汪老家的门铃,第一次走进了405的门,第一次见到了汪老先生和老太太。我向他们自我介绍:“我姓杨,住401,同汪朗在一个单位,也是朋友,以后有什么事,请不用客气,随叫随到。”到了第二个月,又去问汪朗,还送不送鸡蛋呀?其结果当然又是提着鸡蛋,随着405音色响亮的咪哆咪哆的门铃声,又一次迈进了他们家门。
“一回生,二回熟”,从此,我们家同汪老一家开始有了来往。没过几天,老太太就叫老爷子画了张画给我们送来。画面是用淡墨和淡蓝、淡黄三色点染的几枝古藤,仿佛在淡淡的月光下,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上面题字:满屋明月梨花白——国枢乔勋同志饰壁,1996年春。
没过多久,老太太又让老爷子送来一个包装十分精美的木鱼石茶杯,老先生说,用这杯子泡茶,几天不会馊……
作为家庭主妇的我,比较爱烹饪,总愿将生活中的五彩缤纷在餐桌上体现出来。正好汪老又是文坛著名的美食家,我曾看过不少他写的美食小品,既亲切又馋人!除了如法炮制便是前去请教。一次,老公在农贸市场上见到卖大排,勾起了他对读大学时清苦生活的回忆:在上海,大排叫“大扒”,虽说只花两毛几分钱就能吃一块,可也只能偶尔为之,打打牙祭。我决定做大排,又从没做过,便去向老先生请教。老先生告诉我:大排在红烧之前要先用酱油、葱段、姜片腌上一个小时,味就进去了。我是在上班路过他家门口时匆匆向他请教的,老先生说,我去替你买回来,在你下班之前一个小时给你腌好,回来下锅就行了。我怎么好如此打扰老人家呢?于是赶忙跑到楼下去买回一斤大排,提前腌好。等我下班时,老先生已事先用黄酒泡了干贝,叫小阿姨小陈给我送来。老先生说,烧大排再加点黄酒干贝,更鲜。我如法炮制,果然。
汪老曾在昆明念西南联大,在那里他认识了恩师沈从文、妻子施松卿,他称云南是第二故乡。正好前门大栅栏有个云南商店,是我同老公常去的地方,回来后便给老先生捎回一些他在文章中多次描述过的东西:云南米线、鸡棕、牛肝菌、韭菜花……这些也是我们在四川凉山州第二故乡非常熟悉的东西,是老先生用他的笔唤起了我们对往事的美好回忆,我们给他捎回这些东西也算是一种“回报”吧。
记得刚搬到福州馆宿舍不久,发现在出大街拐弯路边的房角下,长着一丛一丛绿色的野菜,这不是老先生文章里提到的灰菜吗?于是,马上拿出塑料口袋,将那灰菜一点一点地选掐下来,洗净后给老先生送去,他高兴地大声说:“这是好东西,裹面蒸,好吃!”但胡同里的灰菜毕竟有限,我突然想起原来住回中宿舍时,楼下草丛里有一片灰菜,再给老爷子奉献一次吧!于是,星期天叫上老公坐6路车到牛街下车,奔到回中一看傻了:一片空地,一棵灰菜也没有!扫兴而归。
今春,市场上又卖起螺蛳,过去没在意,楼下小齐做好请我品尝,一下又吊起了我的胃口,心血来潮,买回两斤,如法炮制。老公说:“全北京就数你做得最好吃。”虽是恭维,倒也入耳。于是立即给老先生送去,怕他吃了不消化,只端了一小碗。老先生一看,二话没说,转身就往里屋走,以为他对此不感兴趣,没想到他是去拿牙签,把螺蛳放在面前,坐在他常坐的客厅沙发上,用牙签一个个仔细地挑来吃,那神态简直像一个贪吃美食的孩子!我突然想起有人撰文形容汪老先生:“酒至微醺状态,他会变得尤为可爱。”这下我可看到老先生那可爱的状态了,回家对老公说:“以后到老先生家,最好带个相机,随时都有好镜头。”
老先生虽是美食家,毕竟年事已高,已少见他亲自下厨了。有天下班还没走到405,就听见老先生用他那独特的响亮的大嗓门在叫“小杨”,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只听老先生说:今晚少做点菜,我给你们做了两道菜。
6点半左右,小阿姨小陈把老先生做的菜送过来了,一道叫百叶结,我以为是牛百叶,实际是用质量较好的东北豆腐皮代替牛百叶,一个一个地打上结,用肉汤煮,放小虾米和笋丝,清淡、味美。另一道菜是麻豆腐,是等我回来后才炒的:用羊油加麻豆腐和青豆。麻豆腐我吃不来,但是,能吃到77岁高龄的汪老为我们安排的菜,不能不说是我这个邻居的独有福分。
4月的一天,我同老公到汪家,看望久病卧床的汪老太太。后来坐在前厅同老先生闲聊,那天他兴致很高,刚画完画,便叫我们品他的画,我指着其中一幅说:“这幅好,有生命。”老先生说:“拿去吧。”我说:“不要,以前您已送过我们一幅了,拿了第二幅,就叫‘索画’了。”他说:“这有什么呀,这是画画裁下的边角,墨汁也刚好快完,顺手一画。”老先生说:“我再给你写两个字吧。”便从常坐的沙发上撑着站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到屋里,写好,盖上章,给我。那是淡淡的两枝荷花,衬着淡淡的两片荷叶,上面飞着一只红蜻蜓,左下方落款:芳邻小杨玩。
5月11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同老公一早经过老先生的门口,见他穿着浅灰色的西装,笔挺;一双新的黄色皮凉鞋,很精神的样子。我说:“老先生有什么外事活动?”他十分高兴地说:“香港回归前50天,作协要搞个活动,非叫去不可。”我说:“那你又得去画幅画啰?”老先生说:“早就画好啦,那么多人围着,画什么呀!到时再写几个字就行了。”买菜回来,看见老先生还在门口,等着车来接。中午,我同老公去西单,看见老先生正从大门往院里走来,我说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记错了,是明天。”
明天,他再也去不了啦!
当晚10点半,我们正准备休息,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是小陈!她说:“爷爷吐血了!”我同先生急忙跑到405,可吓坏了,老先生正倒在卧室里,大口大口地喷血,床上、地上全是。老公急忙打120叫来急救车,又叫来几位邻居,一道将老先生送到了友谊医院,那真是一场生死搏斗啊!
在整个过程中,老先生没有惊慌,没有呻吟,没有痛苦,他是我们最大的镇静剂。
他的女儿汪明后来告诉我们:“老先生说,见到我们,他就踏实了。”
是的,老先生是平和的,从不张扬,即使是病危,也怕给别人添麻烦,心静如水。
那几天,老先生的女儿常过来告诉我们汪老病情稳定的消息,说他需要休息,不能兴奋,所以我们一直未去打扰。那几天,我做饭,煎鸡蛋,一连几个都是双黄蛋,这是从前未有过的事情。我同老公都十分高兴,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16号下班回来,听到了老先生过世的消息。我们都不相信。汪老的几个子女,像汪老一样,平和不张扬。父亲突然而平静地离开,虽然接受不了,但他们把悲伤埋在心底,用这样的方式来悼念父亲——
老先生的书房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他的书、他的笔、他的纸、他的画,一切依旧。
老先生的卧室里:床上铺得整整齐齐,枕边放着一堆他平时常看的书。桌上放着那张人们熟悉的抽着烟的巨大黑白相片,栩栩如生,双眼炯炯有神,是在与别人谈笑风生?还是老爷子又要“下蛋”了——他的孩子们又要这样为他而挪窝了。桌子上还放着最近出版的《汪曾祺散文选集》和《独坐小品》两本书;还有他多年戴习惯了的老花眼镜,常抽的云南玉溪烟和红塔山烟各一包,一个打火机;中间放着那个外面包着羊皮的不锈钢扁酒壶,里面一定还散发着聂华苓给他盛过威士忌的醇香;新沏的龙井茶一杯,一切依然!
只是你抬头看见桌上的那盘圣桑的“天鹅之死”录音带,那悲哀的音乐又将你带到5月28日八宝山送别汪老的时刻;
只是你看见老先生常戴的那只手表,手表的秒针还嘀嗒嘀嗒地摆动,你才感到,它的主人的心脏已于5月16日停止了跳动;
只是你看见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率孩子小虎和小龙送来的插满了百合、菊花、月季和勿忘我的悼念花篮,黑色的绸子上写着黄色的“曾祺贤契永垂不朽”的挽联,你才会相信汪老真的离开我们了。
不!老先生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是随他的老师沈从文,到天国写书去了。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
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庠、王土序寺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胡同文化》
前好几年,春节后数日,我到沈从文老师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饭,师母张兆和炒了一盘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两片茨菇,说:“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认他这话。吃菜讲究“格”的高低,这种语言正是沈老师的语言。他是对什么事物都讲“格”的,包括对于茨菇、土豆。
——《故乡的食物》
豆腐最简便的吃法是拌。买回来就能拌。或入开水锅略烫,去豆腥气。不可久烫,久烫则豆腐收缩发硬。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此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
——《豆腐》
荠菜大都是凉拌,炒荠菜很少人吃。荠菜可包春卷,包圆子(汤团)。江南人用荠菜包馄饨,称为菜肉馄饨,亦称“大馄饨”。我们那里没有用荠菜包馄饨的。我们那里的面店中所卖的馄饨都是纯肉馅的馄饨,即江南所说的“小馄饨”。没有“大馄饨”。我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馆吃过这一家的一道名菜:翡翠蛋羹。一个汤碗里一边是蛋羹,一边是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绿,绝不混淆,吃时搅在一起。这种讲究的吃法,我们家乡没有。
——《故乡的野菜》
自报家门(节选)
文/汪曾祺
京剧的角色出台,大都有一段相当长的独白。向观众介绍自己的历史,最近遇到什么事,他将要干什么,叫作“自报家门”。过去西方戏剧很少用这种办法。西方戏剧的第一幕往往是介绍人物,通过别人之口互相介绍出剧中人。这实在很费事。中国的“自报家门”省事得多。我采取这种办法,也是为了图省事,省得麻烦别人。
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我的小说。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已经订好了飞机票。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把机票退了,好跟我见一面。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上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在运河的旁边。
运河西边,是高邮湖。城的地势低,据说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因此,常常闹水灾。县境内有很多河道。出城到乡镇,大都是坐船。农民几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阴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
我的家庭是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我的生母姓杨。杨家是本县的大族。在我三岁时,她就死去了。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他还练过中国的武术。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本县读的。
小学在一座佛寺旁边,原来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几乎每天放学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将、四大天王、释迦牟尼、迦叶阿难、十八罗汉、南海观音。这些佛像塑得生动。这是我的雕塑艺术馆。
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初中原是一个道观,还保留着一个放生鱼池。
我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毕业,教国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学问,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
我读的高中是江阴的南菁中学。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我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相合。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写了和尚的生活。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问我当过和尚没有。我没有当过和尚。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沈先生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学生都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这样有时甚至会使人物疏远。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须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
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
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到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
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有一位年龄略低我的作家每谈小说,必谈结构的重要。他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在谈结构的前面加了一句话:“苦心经营的随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在国内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
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琢磨,去思索,去补充。
短篇小说可以说是“空白的艺术”。办法很简单: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这样一篇小说的容量就会更大了,传达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这是很划算的事。
第一关
招摇山寻“迷谷”
1.爸爸回来看奶奶,带了什么吃的?( )
A.一袋土豆 B.一串口蘑 C.两瓶黄油
2.奶奶死后,萧胜第一次到爸爸妈妈所在的“马铃薯研究站”,妈妈给他做了什么吃的?( )
A.掺假的玉米面饼子 B.草籽粥 C.鲤鱼
3.萧胜第一次吃到“黄油烙饼”时怎么了?( )
A.咧开嘴痛哭 B.开怀大笑
通过此关,你便可获得“迷谷”的力量!
迷谷 招摇山的一种树,形状像谷树,有黑色纹理,光华四射,做成饰物佩戴在身上可以不迷路。
“招摇山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
——《山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