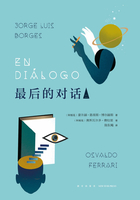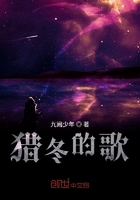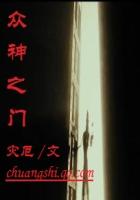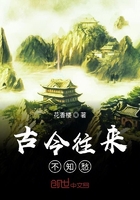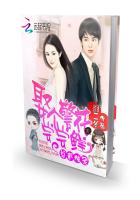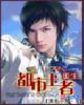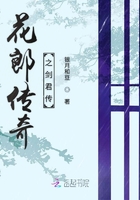薛昭曦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这一年4月,《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的要搜集民歌的意见,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由此,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群众性、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民间民歌搜集、创作和研究的运动。在这场以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运作代替自下而上的民间自觉的全民狂欢中,少数民族民歌的搜集与创作一直以来都未引起关注。以《红旗歌谣》为例,粗略统计,里面搜集了十几个民族较为典型的新民歌作品。作为“大跃进”时代“新民歌运动”的产物,《红旗歌谣》的民间身份,近几年来不断受到关注与研究。由郭沫若和周扬选编的《红旗歌谣》集中展现1958年那场声势浩大、全民参与的大众民歌采风运动的情况。“我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与实干精神相结合为特色,淋漓尽致、生动如画地反映在这些民歌当中。”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罕见的新民歌采风运动,它“全面推动了各个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然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现象,长期以来,对《红旗歌谣》的价值评判一直停留在“民间性”、“集体化”的维度,而少有将其中的“少数民族民歌”作为独立的部分进行考察,更不曾关注“作为整体审美存在的新民歌中的富有生命力且不无独特性的抒情因子”。1958年“新民歌运动”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起的,在搜集和研究民歌工作中,毛泽东特别指出“对各兄弟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要加倍重视”。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很少有人过问;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七年”时期,在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发掘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新民歌运动”中“各民族搜集出版了大量的的各民族民间文学传统作品;搜集出版的新民歌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在“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族民歌同样出现了繁荣的搜集、创作景象。同时在少数民族中还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名气很大的民间歌手,如蒙古族的爬杰,傣族的康朗英、康朗甩等。这说明在这场运动中,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已经开始成型。同时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民歌的研究者,如钟敬文、佟锦华、天鹰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布的“建国十年以来优秀创作”目录中,《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兄弟少数民族作家诗歌合集)也赫然位列榜中。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新民歌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民歌的搜集与创作,乃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一个重大的事件。应当重视“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族民歌的话语言说与表达方式的研究,借此得以洞见“十七年”中少数民族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本文就是试图通过对“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族民歌的解读,得以窥见这些民间言说中所建构的“国家神话”的想象方式。
当我们阅读“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族的民歌时,不应当只看到它作为一种单纯的颂歌形态,而更应该关注这种颂歌形态背后的“民族性”的言说方式和审美表现方式,同时也更应该留心这种颂歌背后所体现的少数民族人民对于当时的国家、政党乃至领袖的想象方式。这些不能不说体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对于“国家”的想象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国家神话”作为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运作,已经渗透到民间民歌的抒情话语中。国家得到了大众的情感拥护。正是由于现实意识形态的需要,再加上领袖的倡导,使得这场运动走向扩大和深入。民间歌谣式的生产口号,对调动劳动热情、推动农业生产,激发人们与天斗、与地斗改造自然的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诗人、政治家毛泽东,更是希望借群众文化创造的宝贵力量,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人民大众不再作为享有文化的主体,更是作为创造文化的主体走上文艺创作的前台。对于新民歌的关注和提倡实际上也就成为国家对于崭新的共和国文化建构的设想。“国家神话”在文化策略上的建构,同样也急于把少数民族兄弟纳入到“我们”这一集体话语中,从而以“大众化”、“同一性”的面目,为政治话语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提供合法化的地位。同时,作为一种情绪表达工具的民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的节日化和狂欢化推波助澜,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规约了这种“国家神话”的表达。作为一种抒情话语,仍有自己崇尚个性的表达功能,这种表达的诉求在集体声音面前虽然显得弱小,但是却表达了隐蔽的对抗性。当集体的声音将雄壮夸张的姿态赋予抒情时,个体的声音也在内部寻求欲望的突破。在这些民歌里我们看到了民间言说与国家神话的双重互动。民歌作为“表达现实生活、思想情感和心里愿望的有节奏的音乐性的”口头语言艺术,由于它简单易制、传播快捷的特性,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宣传其政策、方针、口号的重要工具,借此激励广大工农大众投身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的地位和身份得到了合法化,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和团结的政策,同时积极帮助兄弟少数民族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帮助他们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各族人民生活中产生了强大的推动。这些有利的鼓励性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树立和加强了他们的“国家意识”。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改变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前进。因此在这场“新民歌运动”中,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加入了集体大合唱,在各族民歌的相互影响下,各族新民歌创作形式不断丰富。各族歌手在传统民歌基础上,大胆探索、推陈出新,固定的套语、陈旧的手法和语言为新鲜活泼的形式所代替,那些柔软的、缠绵的调子也因为表现崭新的革命内容而变得健壮有力了。而这也正是国家所愿意看到和听到的来自兄弟民族的热情颂扬。
那么,这些少数民族民歌具体又是如何表达对于国家、政党以及领袖的想象呢?我们以《红旗歌谣》为例,考察少数民族民歌在其中的分布,很明显地发现,这些民歌集中出现在“党的颂歌”这一部分(《红旗歌谣》分为四部分: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保卫祖国之歌)。由此可见,这些民歌在搜集选编之初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选择的。“人民与国家是一体的,因此民歌不仅是人民的声音,同时还代表国家发言”。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民歌便是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抒情形态出现的。它的民间言说在政治规约下走入了“国家神话”之中。民歌的民间品格使得它不仅成为抒发集体乐观情绪的理想工具,也使得“国家神话”在叙述范围和传播范围上大大扩大。郭沫若曾认为,这些民歌“把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干劲,英雄人民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非常充分”。国家叙述和民间叙述同时出现在民歌的言说之中。并且国家叙述在抒情主体背后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例如,“只因为有了共产党/布依山区换新装/刀耕火种成过去/梯田变成水汪汪/只因为有了共产党/山区电灯亮堂堂/儿童琅琅把书读/妇女灯下缝衣裳/只因为有了共产党/山区到处办学堂/千年万载睁眼睛/如今提笔写文章”(云南布依族)。这一类的民歌在“党的颂歌”部分占了一定的数量,它集中表现了党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因此为了表达感激,少数民族民歌不可免俗地加入“同声合唱”之中。
其抒情的背后显然受到了国家叙述的利用和规定。同时,少数民族民歌之中,对于领袖的想象,同样也逃不出当时统一的想象,例如“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是草原上不落的太阳”(甘肃藏族);“在金碧辉煌的北京城/有耀眼的金光万道/那不是天上的太阳呵/那是毛主席的光辉闪耀”(四川康定藏族),对于“太阳”的情感不仅为汉族人民所拥戴,也进入到少数民族民歌言说之中。此外,这场“新民歌运动”还带有国家政治的节日狂欢性特征,少数民族民歌中也不乏对这一特征进行表现的作品。如云南哈尼族人民创作的《哈尼人唱跃进歌》中唱道:“今年的新年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咱们大伙来围在红彤彤的火塘旁边/唱一支新年的歌/尽情地倾诉我们心里的欢乐……我们就唱新年的歌/唱尽我们世世代代的苦难/却唱不完毛主席给我们的欢乐。”“新民歌运动”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全民性、仪式性、等级消失的狂欢节特征。它使得现有的制度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肯定现有的社会制度、政治秩序和等级关系,给节日注入了沉重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新民歌运动”中拥有特殊“政策倾斜”的少数民族诗歌,大部分言说还是不得不按照国家规格“被整合”到当时统一的叙述话语中去。“民歌有条件的被训练成制度化的抒情话语”。国家神话虽赋予了民歌某种“情感的巫术功能”,以使得民歌言说方式必须服从于国家神话的统一安排。同时在这场追求现代化,完成现代性文化建构的过程中,由于理性精神的片面化和偏至化,国家对原本是自发的、野性的民间民歌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和规训,使文化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结果使得世俗的现代化设想演变为狂想,在文学领域民族文化审美现代性的缺失,使得整个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原本那些基于现代性追求的民族国家想象步入到了激进现代性的岔道。正是由于这场运动中历史理性片面张扬,使得现在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回首这场运动时,因为无法看见其中隐蔽的人文理性的价值而采取了全票否决态度。但是,“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族民歌的民间言说,却能因着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为自身腾挪出部分空间,在表达民族经验的外壳下迫使强势的“国家神话”得到收束与缓冲。而且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民歌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少数民族民歌创作、流传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时国家政策的特殊照顾和要求在各个少数民族实际的民歌改编、创作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独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价值,这一独特性正是当时离奇夸张的政治乌托邦想象与纯真的、自为的原始情愫共同催生的。而这些正是今天的研究所不曾关注过的暗角。
在“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族民歌的搜集、创作数量丝毫不亚于汉族地区的民歌搜集、创作。据天鹰《扬风集》统计,当时的呼和浩特市决定三至五年内搜集五十万首民歌,内蒙古自治区则要求在五年内搜集一千万首民歌。各个少数民族生活的集中地区,也同样受到了“新民歌运动”的政策感召,掀起了海啸般喷发的民歌搜集、创作运动,成立了采集民歌的专门机构,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和民歌研究小组。同时,当时的各种刊物也为少数民族民歌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阵地。《民间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民歌的主要阵地,大量发表了各个少数民族搜集、创作的新民歌,成为“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和阶段。同时,《人民文学》、《诗刊》、《歌谣》周刊、《红旗》杂志以及各类地方性的文学刊物,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的文学刊物如《边疆文艺》等,都开辟了专栏或是有意选登少数民族的新民歌作品。甚至在国家文艺最高领导层编辑出版的堪称“诗三百也要显得逊色”的《红旗歌谣》中,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占有了一定的数量。可见,当时的少数民族民歌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传播载体上,都有一定的政策保障。同时,各个少数民族在“新民歌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新民歌创作的代表作家。如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康朗甩的《傣家人之歌》、潘俊龄的《金色的芦笙》等,虽然不完全算新民歌创作,但在诗篇的创作中仍然可以看到审美表达方式的选择与新民歌中的颂歌形态,存在某种极其相似的暗合。
各族的新民歌是各族人民思想感情、作风气派、心理特点和欣赏习惯的艺术表现,集中反映了各个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生活特点,在“新民歌运动”中,这些民歌表现出了多样的民族形式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当我们抛开固有的意识形态观念,单从民歌的具体文本分析“新民歌运动”中汉族民歌和少数民族民歌的言说与表达。我们很自然地发现,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民歌作为“国家神话”的特别关注对象,其集体抒情的言说方式除了渲染当时的政治气氛、情绪和激情外,还具备自身独特而有别于汉族地区民歌的审美特征。在高度统一化和强势的语境中,这一类民歌的出现,带来的不仅是民族风味,更是审美上对于“爱”和“美”的追求,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这些都是民歌中最宝贵的部分。笔者试将这些独特性归纳如下:一是,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体现。所有的民族形式,如蒙汉调、宴席曲、花儿、酒歌、箭歌、弦子、堆谐、车加、弹唱、飞歌、打歌笛子歌、盘歌、勒脚歌、笔管歌、僮欢、白族调、西山调、欢乐调等等都为表现新时代服务。在民族风格上,新民歌中也出现了不同特色的民族风格。苗歌和瑶歌古朴坚实,藏歌和傣歌光艳优美,蒙古族民歌则曲折悠扬,黎歌和畲歌委婉清脆。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民歌淳朴浑厚,粗犷有力。僮族的双声部民歌和朝鲜族的三拍子民歌,也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甚至同是花儿,由于不同条件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这些民族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它们以歌颂时热情奔放,抒情时深沉健美,叙事时鲜明有力表现出了有别于汉族地区民歌的审美独特性。例如:“一条洁白的哈达/凝结着翻身农奴的深情/千里雪山,万里草原/手捧哈达上北京/一条洁白的哈达/凝结着翻身农奴的心意/潜力奖和,万里流云/手捧哈达献给毛主席。”其艺术的完美、想象的丰富、构思的奇妙,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二是,对于中国传统民歌表达的自觉延承。例如,“没有好马走不了千里路/没有好鹰捉不着狐狸/没有好草养不了肥羊/没有人民公社/草原哪能变得像天堂。”(新疆哈萨克族)“太阳一出满天下红/顶天的松/一年四季长青/擎天一柱的毛泽东/灯塔的灯/万寿无疆日月长明”(回族)……从这些民歌中,生动有趣的比拟代替干巴单调的口语,不直接呼喊,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民歌中的“比兴”传统,通过在语言运用、结构方式、音韵格律和表现方法(比喻、夸张、起兴、对偶、谐音双关等)上精心结撰,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格,从而建立起了感情丰富、色彩多样的颂歌形态。这一类的民歌在各个少数民族民歌中可以经常看见,因其表达艺术化而超越当时口号式、标语化的民歌。
三是,本民族特色的景物、风俗的展现,带来了原始、野性的审美对象。例如,“葡萄”、“马兰花”等意象在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中的反复出现,“马”、“羊”、“大草原”、“胡麻”在蒙古族民歌中的展现,“雪峰”、“珍珠树”“雄鹰”在藏族民歌中描写,还有云南哈尼族在民歌中表现的嫁娶、歌舞、狩猎、祭祀等风俗场面,这些无不向我们展示了少数民族的生活地域的自然风光和风俗习惯。少数民族民歌中大量的带有本民族地域特色的山川草木和民族风俗场面描写,使这类民歌有了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在审美上获得了相对的成功。同时这一类新民歌是自觉借鉴少数民族传统民歌的结果,带有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这些传统少数民族民歌的鲜明特点。
四是,爱情的言说在少数民族诗歌中占了大多数,这一类“情诗”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原始的生命意识和野性欲望,并“不为道德和学问所拘泥”。在当时强势的政治语境中成为一抹温暖的色彩。例如,“哥住山南红梅庄/妹住山北桃树村/想唱山歌叫哥听/高山挡住不透音/想采鲜花送给哥/翻山越岭人人问/今年成立高级社/山南山北一家人/早晚能见情哥面/心里话儿听得真”(壮族),类似的爱情言说大量地出现在少数民族民歌之中,“利用和倚赖调侃加调情的直白形式,爱情中的所谓不正当性情愫表达被赋予了某种政治形式的合法性”。情歌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反映了青年男女之间的纠葛,借助对于爱情生活的描写,表现出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内心真善美的追求。而正是这一类爱情言说和表达使得少数民族的民歌有了超越于一时一地之文学的可能。朴实、真率、幽默、夸张、含蓄的种种表达方式,使得这一类情歌具有感人的魅力,并在当时与大跃进的劳动竞赛紧密结合,呈现出了一种崭新的思想面貌。这些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征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言,“均为同一种腔调和声音,同一种比赋结构模式”,“在纯粹的政治话语基础上嫁接了民间爱情歌谣叙事模式,抽空了生命的‘原发’质感”。这样的价值判断可能忽视了“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族诗歌在“新民歌运动”中审美的特殊性。当然,这些民歌的价值取向在当时统一地指向了“颂歌”,然而存在于它们表达之中的种种审美性还是很容易发现的。“国家神话”的强大意图在这些少数民族民歌中发生了松动。抒情话语以其强大的情感功能软化了政治话语,并在其鞭长莫及的地方继续动情地歌唱。如果有了这样的视角,那么也就不能轻易说,当时的民歌都是泥沙俱下,随意粗率的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新民歌在某种程度上向着传统意义上自下而上的、崇尚个性、审美、性情的民歌的某种艰难的回归。总之,这些来自少数民族的民歌,表现了独特的“民族性”言说方式和审美形态,有别于当时单纯的口号式颂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况且,作为“国家神话”在兄弟少数民族中的言说方式,“新民歌运动”中的这些民歌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时代语境之间复杂的关系也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其实,看到“新民歌运动”中少数民歌言说的特殊性,就是发现统一的时代语境背后,个体抒情话语的差异性。而正是这些差异性,表达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自觉追求。不论其多少,这些少数民族民歌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穿越当时集体情绪,发现爱和美空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