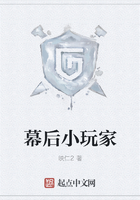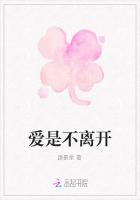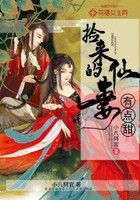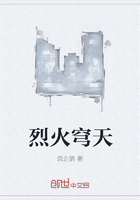【原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张居正直解
述是传旧。作是创始。窃字解作私字。比是仿效。老彭是商时的贤大夫。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传先王之道,以教万世。然犹不敢以作者之圣自居,乃谦逊说道:“大凡天下之事,有前人已为,而后人传之者,谓之述;有前人未为,而自我创始者,谓之作。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也。我今虽有所修为,只是传述先王之旧,或考之方册,而重加发明;或闻之故老而更为裁定,实未尝重新创造而有所作也。盖天地间的道理,哪一件不是古人说过的?就中讲求,自有无穷的妙处。我则深信而笃好之,惟日孜孜,不能自已,故但见其可述,而无容于复作也。然此岂我之独见哉?比先商时贤大夫有老彭者,他能信古而传述,我尝慕其为人,今我所为不过私自仿效我老彭耳!”夫孔子于古之贤人,犹不敢显然自附如此!其德愈盛而心愈下,盖可见矣!
【原文】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张居正直解
默是不言,识是记。诲人是教人。孔子说:“人之求道,如徒务口语而不能存之于心,则闻见虽多,终非实得。必须沉静简默,只在心上去理会。凡所闻所见的都不费辞说,而自无所遗忘,然后能深造而自得也。人之为学,若只是始初奋发,到后来便厌烦了,则工夫间断,岂能有成?必须深信义理之无穷,而实用其力,自始至终都只是这等勤学,无一毫厌怠之意,然后谓之好学也。人之设教,若不能尽心开导,到费力去处,便都倦了。则私意未忘,岂能成物?必须真知物我之无闻,而有教无隐,随人问难,都因材而造就之,无一毫倦怠之心,然后谓之善教也。这三件都是成德之事,而我之尝所致力者。然反而求之,何者能有于我哉?”夫圣人会道全体而曲成不遗,乃犹自以为不能,其谦己诲人之意至深切矣!
【原文】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张居正直解
义是理之所当为者。徙字解作迁字。孔子说:“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闻义能徙而后善可积,不善能改而后恶可去。这四件是切实紧要的功夫。凡欲为圣贤者皆当用力于此也。今我之于德,未能省察克治,以涵养其本源;我之于学,未能讲习讨论而研究其精奥;义有当为的,未能闻斯行之而迁徙以从其新;不善当改的,未能务于决去而惩创以革其旧。则是德有不成,学有不明,善不能积,恶不能去,将日流于污下,而不可进于高明矣。岂非吾之深忧者乎?”夫孔夫子之圣,非真有所不能也,亦非自知其能而故为是言也。盖其好学无已之心,自视常若有不能耳!然此四者,在人君尤为切要。古之帝王或懋敬厥德,终始典学,或取人为善,改过不吝皆是道也。欲法古帝王者,宜三复孔子之言。
【原文】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张居正直解
燕居是闲居无事之时。申申是舒畅的意思。夭夭是和悦的意思。门人记说:凡人在闲暇之时,有怠惰放肆的,便自亵其威仪;有矜持矫饰的,或反过于严厉,皆非盛德之气象也。惟吾夫子在闲居无事之日,以四体则从容舒展,而略无拘迫,何其申申如也!以颜色则融和润泽而自然愉悦,何其夭夭如也!盖德性极其纯粹,故容貌合于中和者如此!门人此言可谓善形容有道气象者矣。
【原文】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张居正直解
衰是血气既衰。孔子发叹说:“凡人年有老少,则血气有盛衰,甚矣,我血气之衰也。如何见得?盖我当强壮之年,常常梦见周公,恍然若与之相遇。到如今来,许久不复梦见周公矣,则吾之衰岂不集乎?”盖孔子生于周时,一心要做周公的事业。方其精力壮盛,寤寐不忘,故常形之于梦。及其既老,则自谅其力不能为,无复是心,而亦无复是梦矣,故其发叹如此。可见贤才之生于世,其可以有为者,每在其强壮之时。而人君之用贤,亦当趁其强壮而任之。若精力既衰,则事功所就,已不能副其初心矣,况于终不用乎?然则孔子之自叹其衰,固为可惜,而当时之君不能及时用之,以再见周公之化,而使之卒老于下位,则尤为可惜也。
【原文】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张居正直解
这一章是孔子示人为学之全功。志是心之所向。据是执守。依是依止。游是游衍玩习的意思。孔子说:“学莫先于立志,而道乃人化事物当然之理。志不于是,则趋向差矣!故必以道为终身之准的,而专心致志以求之。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行此道而有得于心,叫作德。德而不据,则持守之功不继,能保得者之不失乎?必拳拳服膺,务使此德常有诸己,而日积月累,不至于若存若亡而后可;体此道而心德纯全,叫作仁。仁而不依,则私欲有时复萌,能保全者之不亏乎?必念兹在兹,务使此仁存养愈熟而周流贯彻,无一毫间断错杂而后可。夫志道、据德、依仁,是本之在内者,无不尽矣。至于礼、乐、射、御、书、数之事,虽艺文之末,非德行之本,然亦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亦必游息于藏修之余,从容而玩味其理,用以收敛身心,调养性情,而成其道德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而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学之全功,何以加此?然此章之旨,不但是学者所当知,在人君尤为切要。盖道、德、仁,乃人君修身治天下之本,必当深造其极,方可无歉,而凡游心于艺文者,又须务求实用,始为有益。古之帝王所以学古有获,道积厥躬,德修罔觉者,正是如此!善学者当以圣言为法程可也。
【原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张居正直解
脩是脯,乃干肉也,十艇为一束。古人初相见,必执贽以为礼。一束之脩乃其至薄者。自行束修以上,言随其厚薄之不同也。诲是教诲。孔子说:“无不善者,人之性;而无不欲其人于善者,吾之心。但人不知来学,吾固无往教之理。苟知求教,自行束脩以上之礼而来者,即是可与为学之人,吾则未尝不教诲之焉。”盖天生圣人,非徒使自圣而已,正欲其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为时人之耳目也。所以圣人教人之心,倦倦无已如此。使其得君师之位,则必能大行其政教,使人人皆为君子而后已。惜乎不得其位,但能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也。
【原文】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张居正直解
愤是心求通而未得的意思。启是开其意。悱是口欲言而未能的模样。发是达其词。隅是四方转角处。反是反复问难。复是再告。孔子说:“君子之教人,固当尽言而无隐,然必其人有受教之地,而后可以施吾造就之方。且如人之求道,有用心思索而未能即通者,谓之愤。愤则有可通之机,吾因而为之开其意,彼将豁然而无疑矣!若未至于愤,则在彼本无求通之心,我何从而开之乎?此所以不启也。有心知其意而口未能言者,谓之悱。悱则有可达之势,吾因而为之达其词,彼将沛然而莫御矣。若未至于悱,则在彼本无欲言之心,我何从而达之乎?此所以不发也。至于我之所启发者,又看他了悟如何。若能于我所言,触类旁通,因此识破,我举其一隅,而彼即能以三隅反。譬如提起东方一角的事,他就并西、南、北方的道理都晓得了,提起西方一角的事,他就并东、南、北方的道理都晓得了,一一回答将来,相与质证。这等的人是其机圆而不滞,其心通而无碍,然后详以告之,则彼此相契,而其言易入矣。若示之以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复问难,则是资禀庸下,而不能推测,意见凝滞而未能旁通,虽谆谆而语之,亦终茫然而无得耳。我何为而强聒乎?此吾所以不复告也。”夫以孔子之诲人不倦,犹必因人而施如此!然则学者可不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哉?
【原文】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张居正直解
侧是边傍。哭是吊丧而哭。歌是咏歌。盖古人以歌咏养性情,遇心有所乐则歌也。门人记说:“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自已。如人有死丧之事,而夫子食于其侧,则未尝饱。”盖临丧哀,故食之而不能甘也。又如夫子于是日吊丧而哭,则其一日之间不复咏歌。盖余哀未忘,而自不能为乐也。然此乃是不忍之心,古之帝王见百姓之饥寒困苦流离死亡,则必为之减膳、撤乐,急急救恤,即是此心。有天下者能推此心以仁民,则无一夫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
【原文】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张居正直解
行是出而行道。舍是不用。藏是隐而不出。昔颜子深潜纯粹,学已几于圣人。故孔子称许他说:“吾人出处进退,只看时之所遇何如?或以仕为通,而至于枉己徇人,固不可;或以隐为高,而务于绝人逃世,亦不可。惟是人能用我,时可以有为,则出而行道,以图济世之功;人舍我而不用,时不可以有为,则隐而不出,以全高尚之志。或出或处,无一毫意必于其间,这才是随时处中的道理。此惟我与尔为能有之,在他人则不敢以轻许也。”盖孔子为时中之圣,自然合乎仕止久速之宜。颜子具圣人之体,能不失乎出处进退之正。观孔子有东周之志,而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有为邦之向,而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盖可见矣。然以大圣大贤,而皆不过于春秋之世,则岂非世道之不幸哉!
一万二千五百人叫作一军。大国则有三军。暴虎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冯河是不用舟楫而徒步涉河。子路见孔子独美颜子,乃就问说:“用舍行藏,夫子固与颜回共之矣。设使夫子统领三军,而行战伐之事,则将与谁共事乎?”盖自负其勇,意夫子行军必与己同也。孔子答说:“君子之所贵者,在于义理之勇,而不在于血气之刚。若是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无怨悔,这是轻举妄动、有勇无谋的人。使之用兵,必然取败,吾不与之行三军也。必是平昔为人不敢轻忽以误事,亦不敢苟且以成事,但事到面前常有兢兢业业、凛然危惧的意思。又好用计谋,预先斟酌停当,然后果决以成之,这才是持重详审、智勇兼备的人。使之用兵,必能全胜,吾方与之行三军耳!亦何取于徒勇哉?”子路好勇而无所取材,故孔子以是抑而教之。其实行军之道,亦不外此。故赵括好谈兵而致长平之败;充国善持重而收金城之功。任将者当知所择矣。
【原文】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张居正直解
这是孔子设词以警人的说话。执鞭是贱者之事。孔子说:“人之所以役役焉以求富者,意以富为可求也。若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之,则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盖执鞭虽贱者之役,而苟足以致富,则亦无不可为者。但人之富贵贫贱,莫不有命存焉,决非人力所能强求者。如其不可强求,则在我自有义理可好。吾惟从吾所好,而安于命耳?何必终日营营,为是无益之求,以徒取辱哉?”夫孔子之圣,非真屑为执鞭之士也,特见当世之人,多自决其礼义之防,而甘心于苟贱之羞,故甚言以警人之妄求耳!所以他日又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观此,则自修者固不当愿乎其外,而取人者尤必先观其所守可也。
【原文】
子之所慎:齐、战、疾。
张居正直解
齐是将祭时斋戒。战是统兵而行战阵之事。疾是疾病。门人记说:“夫子之所最谨慎者有三件事,其一曰斋,盖斋以交神,苟有不慎则志意涣散,神必不享。所以夫子之于斋也,内秉寅恭,外敦俨恪,务致其精诚,而后承祭以交于神焉。其一曰战,盖战者众之死生,国之存亡系焉。苟有不慎,则机宜不审,何以能胜?所以夫子之于战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务出于万全,而不敢轻率以取败焉。其一曰疾,盖疾乃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慎,能无伤乎?所以夫子于无疾之时,则薄滋味,寡嗜欲,时节其起居,而不敢宴游无度;和平其性气,而不敢喜怒过当。不幸有疾,则加意调养,审择医药,而不敢有一毫之忽略焉。”盖圣人无所不慎,而此三者关系尤大,故谨之又谨如此。
【原文】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张居正直解
《韶》是舜乐名。不图是不意。古者圣王作乐以象德,帝舜以至圣之德,当极治之时,故所作《韶》乐最为美盛。舜之后封于陈,犹传其乐,至陈敬仲奔齐,而《韶乐》遂在齐矣。夫子周流至齐,得闻其音,乃从而学之,至于三月之久,一心只在乐上,虽当食之时,有不知肉味之为甘者。盖不特习其声容节奏之末,而其契合之深,就如亲见虞舜之圣,身在雍熙之时者矣。遂不觉发叹说道:“吾向也但知《韶》乐之美,犹未能得于亲闻;今也始得闻而学之,不意其所作之乐至于如此之美也。”盖夫子中和之蕴本自与舜合德。故一闻《韶》乐而叹息之深如此!他日又称其尽善尽美,而颜渊问为邦,则以韶乐告之,其上嘉于虞舜者至矣。
【原文】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张居正直解
为字,解作助字。卫君名辄,是灵公之孙、世子蒯聩之子。诺是应答之词。昔卫灵公时,世子蒯聩得罪出奔,灵公薨,国人遂立蒯聩之子辄。及晋人送蒯聩归国,辄拒之不受。当时卫国之人都说道:“蒯聩得罪于父,于义当绝。辄以嫡孙嗣立,于礼为宜。未有明言拒父争国之非者。”那时孔子在卫,冉有疑孔子亦以为宜,乃私问子贡说:“卫君之立,国人固皆助之矣,不知夫子亦以为当然而助之否乎?”子贡即诺而应之说:“吾将入见夫子而问之。”盖未能深谅孔子之心,而不敢遽答冉有之问也。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长子叫作伯夷,第三子叫作叔齐。孤竹君曾有遗命,要立叔齐为君。及卒,叔齐又逊伯夷而不肯立。伯夷说父命不可违;叔齐说伦序不可乱,两人互相推让,都逃去了,这是兄弟逊国的事,正与卫君父子争国的相反。子贡不敢直斥卫君,乃入而问孔子说:“伯夷、叔齐是何等人也?”子贡之问是要看孔子之取舍何如。若以争国为是,则必以让国为非。若以让国为当然,则必以争国为不可矣。孔子答说:“二子逊国而逃,制行高洁,是乃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说:“二子固是贤人,不知让国之后,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子贡之意,盖以让国之事人所难能,若贤如二子者,尤出于一时之矫激,而未免于他日之怨悔。则不可概责之他人,而卫君犹或可恕也。孔子答说:“凡人有所求而不得则怨,今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只要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所以求尽乎人也。今既不违父命,不悖天伦,是求仁而得仁矣。求之而得,则其心已遂,又何怨悔之有乎?”夫孔子之于夷、齐,既许其贤而又谅其心如此,则让国之事乃孔子之所深取也。以让国为是,则必以争国为非,而其不为卫君之意不问可知矣!故子贡出而谓冉有说:夫子不助卫君也。盖惟孔子为能谅夷、齐之心,惟子贡为能谅孔子之心。一问答之间,而父子兄弟之伦,昭然于天下矣。为国者可不以正名为先乎?
【原文】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张居正直解
饭是吃,疏食是粗饭,肱是手臂。孔子自叙其安贫乐道之事说道:“人生日用之间,无不欲饮食充足,居处安逸者。我所食的不过是粗饭,所饮的不过是水,其奉养之菲薄如此!夜卧无枕,但曲其肱而枕之,其寝处之荒凉如此!贫困可谓极矣!只是我心中的真乐,初不因是而有所损,亦自在其中焉。若彼不义而富且贵,苟且侥幸以得之,虽胜于疏食饮水,以我视之,漠然如浮云之无有,何尝以此而动其心耶!”盖圣人之心,浑然天理,故不以贫贱而有慕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如此!
【原文】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张居正直解
加字,当作假字。五十字,当作卒字。假是借,卒是终。《易》即是如今《易经》所载的道理。孔子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凡天道之吉凶消长,人事之进退存亡,都具载于其中,学者所当深察而玩味也。但其理深奥精微,我尝欲学之而尽其妙,然今则老矣。天若假借我数年,使我得终其学《易》之功,或观其象而玩其辞;或观其变而玩其占。凡道理精微的去处一一都讲究得明白,则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我皆能融会于一心。由是见诸行事,必能审动静之时,得趋避之正。虽未必全然无过,而亦可以无大过矣。”夫圣人全体易道,行不逾矩,岂待假以数年而学《易》,亦岂待学《易》而后能免过?正谓易理无穷,欲人当及时以勉学耳。欲寡过者当以讲学穷理为先。
【原文】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张居正直解
雅字,解作常字。执是执持。人能事事循礼,才有执持,所以叫作执礼。门人记说:“夫子之设教,固必因人而施。然平日所常言者,则有三件:一是《诗》,盖《诗》之为言有美有刺,美者可以劝人为善,刺者可以戒人为恶。吾人所以养性情者莫切于此。一是《书》,盖书之所载有治有乱,与治同道则无有不兴;与乱同事则无有不亡,吾人所以考政事者莫切于此。一是执礼。盖礼主恭敬而有节文,既可以防闲其心志,又可检饬其威仪。吾人欲养其德性,使有所执持者莫切于此。这三件都是切实的道理,紧要的功夫。故夫子常以为言,欲人念念在此而不忘,时时用力而不懈也。”夫以孔子之圣犹汲汲于学易,而于诗、书、执礼则雅言之。可见圣人之道具在六经,学者必讨论讲习,乃可以明理。人君必体验推行乃可以致治,读者宜致思焉。
【原文】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张居正直解
叶公是叶县的令尹,僭称公。奚字,解作何字。愤是急于求通之意。昔者叶公问孔子之为人于子路,子路不对。盖圣人之德未易名言,故子路不敢轻对也。孔子闻而教之说:“叶公之问盖欲知我也,而汝之不对,何也?汝何不说:‘其为人也,惟知好学而已。方其理之未得,则发愤以求之。虽终日不食,有不知者。愤而至于忘食,是其愤至极也。及其既得,则欣然自乐,虽事之可忧有不知者。乐而至于忘忧,是其乐之至也。然天下之义理无穷,未得而求之以至于得,则愤者又未尝不乐也。有得而尚有所未得,则乐者又未尝不愤也。二者循还,曰有孜孜,而无所止息,虽老年将至,有不自知焉者,是乃我之为人也。’汝何不以告叶公乎?”这是孔子自言其好学之笃如此!然其全体至极,纯一不已之心,于此亦可见矣。欲学圣人者,其可不以勤励不息自勉哉?
【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张居正直解
古是古人的典籍。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说:“天地间的道理,凡精粗小大,哪一件不是吾人之所当知。但人之气禀不同,有天生上智,自然知此道理者;有必待学习然后能知此道理者。我今虽有所知,岂是聪明睿智,生来自然能知而不待学习者乎?只是见得这个道理,都具于古人之典籍,若非心里喜好,则志向不专,非上紧讲求,则功夫有间,所以笃信好古,汲汲焉勉力以求之。将古人的言语,字字去体认;将古人的行事,件件去思索,就似饥之求食,渴之求饮一般,惟日孜孜,不敢有一毫之懈怠。是以学力至到,义理固然贯通,而能有所知耳,岂真生而知之者哉!”此虽孔子自谦之辞,其实学问之功,虽圣人亦不能废。故尧、舜舍己从人,大禹不自满假,成汤之得师,武王之访道,皆不敢自恃其聪明,而必从事于学问也。傅说说学以古训,逊志务时敏,正与好古敏求之言相合,为人君者不可不知。
【原文】
子不语:怪、力、乱、神。
张居正直解
语是言语。怪是怪异。力是勇力。乱是悖乱。神是鬼神。门人记说:“夫子教人,固无所隐,然亦有所不语者,怪、力、乱、神是也。”夫怪者诡异无据,虚诞不经,最能骇人之听闻,惑人之心志者也。力者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专用血气而不顾义理者也。乱者臣子叛君父,妻妾弃其夫,乃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者也。鬼神者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其感应之理幽远而难测者也。前三件非理之正,后一件非理之常。言之,则有以启人好奇不道之心,渺昧荒唐之想,故夫子绝不以为言。其所雅言者不过《诗》、《书》、执礼,其所立教者不过文、行、忠、信而已。
【原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张居正直解
师是师范。孔子说:“学无常师,随在有益。人能存心于为己,斯无往而非进德之地,便是三人同行,亦必有我之师范存焉。盖人的所为非善则恶,而师也者,所以引人为善,教人去恶者也。今三人虽寡,而观其所行,岂无合于义理而为善者乎?亦岂无悖于义理而为不善者乎?善者我则景仰欣慕,取法其善而从之;不善者我则反观内省,恐己亦有是恶而改之。夫择善而从,则足以长吾之善,是善固我之师也。见不善而改,则足以救我之失。是不善亦我之师也。所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人且如此,则天下之人无往而非师矣!人能随处而自考,触类以求益,进善岂有穷乎?即此推之,可见人君之学,尤须广求博采,凡臣下之忠言嘉谟,古今之治乱得失,盖无非身心治理之助者,诚能以圣哲为芳规而思与之齐,狂愚为覆辙而深用为戒,是谓能自得师,而德修于罔觉矣。
【原文】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张居正直解
桓魋是宋之司马。如予何,是说没奈我何,言不能害己也。昔孔子周流四方,行到宋国,那时宋国的司马有桓魋者,忌孔子而欲杀之,门人都惧其不免。孔子晓之说:“人之死生祸福皆系于天。若天无意于我,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则我之命,天实主之,必将佑我于冥冥之中矣。桓魋亦人耳,其将奈我何哉?盖必不能违天而害我也。”然孔子虽知天意之有在,而犹必微服过宋以避之,则可见天命固不可以不安,而人事亦不可以不尽。故知祸而避,则为保身之哲,以义安命,则为乐天之仁。观圣人者于此求之可也。
【原文】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张居正直解
二三子指众弟子说。隐是隐讳而不言。与字,解作示字。昔孔门弟子专以言语求圣人,以为夫子之道本自高深,而其教人则甚平易,必有秘而不传者。故以有隐为疑。孔子乃教之说:“二三子之学于吾门久矣,其将以我为吝教,有所隐讳而不言乎?不知吾之于尔初未尝有所隐也。盖道理在人,本自明白简易,固不待言而显,亦不可执一而求。我今一动一静、一语一默,凡身之所行都依着道理,这是二三子所共见共闻的。则是以身立教,无一事不以昭示于二三子者,此乃丘之为人也,何尝有隐于尔哉?二三子不能随处体认,而徒以言语求之,非惟不知我,抑亦不善学矣。”然孔子之道,不但晓然昭示于门人,而亦灿然大明于万世。善学圣人者若能反之身心之间,而不徒泥于言语之末,则何圣道之不可及哉?
【原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张居正直解
文是《诗》《书》六艺之文。行是体道于身。尽己之心叫作忠。待物以实叫作信。门人记说:夫子以成就后学为心,其为教虽无所隐,然大要不过四件。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盖天下之义理无穷,皆载于《诗》《书》六艺之文,使不有以讲明之,则无以为闻见之资,而广聪明之益,故夫子每教人以学文也。然道本于身,使徒讲明,而不一一见之于躬行,则所学者不过口耳之虚,而非践履之实,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然道原于心,使发乎己者有不忠,应乎物者有不信,则所知所行皆为虚伪,而卒无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发于心者肫肫恳至,而无一念之欺;教人以信,使其应乎物者,慥慥笃实,而无一事之诈。苟能此四者,则知行并尽,表里如一,而德无不成矣。为学之道,岂有加于此哉?此夫子所以为善教也。
【原文】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张居正直解
圣人是神明不测之号。君子是才德出众之名。善人是志仁无恶的人。有恒是存心有常的人。亡字即是有无的无字。虚是空虚。盈是充满。约是寡少。泰是侈泰。孔子说:“天下之人品等第,每有不同,而随其才器造诣,皆可上进。彼神明不测,大而化之的圣人,乃人之至者,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才德出众而为君子者,斯亦可矣。然君子去圣人不远,岂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见,至于天资粹美、志仁无恶的善人,吾亦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存心之有常者,斯亦可矣。夫有恒者之与圣人,高下固为悬绝,而实为入德之门,然谓之有恒,不过质实无伪耳。盖天下之事,必有其实,乃能常久,若是存心虚伪,本无也,却做个有的模样;本空虚也,却做出个盈满的模样;本寡少也,却做个侈泰的模样,似这等虚夸无实,虽一时伪为以欺人,而本之则无自将不继于后,欲其终始如一,守常而不变,岂可得乎?所以说难乎有恒矣。夫无恒者如此,则所谓有恒者可知。人若能纯实无伪而充之以学,则固可由善人而为君子,由君子而为圣人,不止于有恒而已,此吾所以思见其人也。”然《中庸》言达道达德,九经而归本于一诚。先儒说:诚者圣人之本。孔子此言,岂徒以引进学者哉?要其极则参赞位育之化,亦不过自有恒之实心以充之耳。欲学二帝三王者,宜体验于此。
【原文】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张居正直解
“钓是钓鱼。以大绳系纲,截水取鱼叫作纲。弋是以丝系矢而射。宿是鸟之栖者。门人记说:吾夫子在贫贱时,为奉养、祭祀亦尝取鱼、鸟以为用矣。但常人都有贪得之念,而夫子每存好生之心。其取鱼也只用钓饵以钓之而已,不曾以大绳系纲拦截水中而尽取之也;其射鸟也,只以丝系矢,射其飞者而已,如鸟之宿者,则未尝出其不意而射取之也。”盖于取物之中,而寓爱物之意,圣人之仁如此!古之圣王网罟之目,必以四寸,田猎之法,止于三驱,皆以养其不忍之心,而使万物各得其所也。人君能举斯心以加诸民,则人人各遂其生而天下治矣。
【原文】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张居正直解
不知而作是不知其理而妄有作为。识字,解作记字。孔子说:“天下之事,莫不有理,必先知得此理明白,然后处事停当而无有过差。今天下之人,盖有不知其理而妄有所作为者,若我则无是也。然吾所以无不知而作者,岂是生来便晓得许多道理?盖我以天下之义理无穷,非闻见广博,则无以开聪明而扩智虑。于是多闻天下之理,择其善者而体之于身,务使有得而不敢不勉;又多见天下之事,不论善恶皆记之于心,以备参考而不敢遗忘。夫闻见既多,而又有所抉择参考,则得于人者无穷,而裁于己者有据,虽是闻见之知与生而知之者不同,然自此进之,则智虑日广,义理日明,亦可次于知之者矣。知之既明,则处之自当,又何妄作之有哉?”夫圣人本生知安行,而其自谦之词如此。则知学为圣人者,必先造其理,而后可以履其事。此讲学穷理之功,不可一日而不勉也。
【原文】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张居正直解
互乡是地名。昔孔子时,有地名互乡者,其人都习于不善,难于言善。那时有道之君子皆恶而绝之。一日有个童子,慕孔子而求见,孔子许其进见,不加拒绝。门人都疑惑说道:“君子持身贵正,疾恶贵严。今互乡童子乃不善之人,夫子何为见之?”此所以疑而未解也。
与字,解作取字。洁是舍旧从新的意思。往是前日。孔子因门人之惑而晓之说道:“君子之处己固当谨严,至于待人也要宽恕。今互乡虽不善之俗,而童子之求见,是乃向善之心,我今特取其进而求见耳,非取其退而为不善也。若因其习俗而峻拒之,则太甚矣。我何为而绝人于己甚乎?盖凡天下之人,不患其旧习之污染,而患其终身之迷惑。若能幡然悔悟,舍旧从新,而洁己以求进,这就是改过迁善可与人道的人,但取其能自洁耳,不能保其前日所为之善恶也。盖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君子待人之道,固当如此。今互乡童子正洁己以进者,我又何为而拒之?二三子亦可以无疑矣。”当时,教化陵夷,风俗颓败,孔子欲化导天下之人,以挽回天下之风俗,故其不轻绝人,不为己甚如此!惜乎有志未遂,非惟时君莫能用,而门人亦莫能尽知也。
【原文】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张居正直解
仁是本心之全德。孔子因人不肯用力于求仁,故言此以勉之说道:“世之惮于求仁者,盖将以仁为远于人也,自我观之,仁之为德也,果远于人乎哉?不远也,何以见其不远?盖凡物之远者,求之或未必得,得之或未必速。若夫仁者乃心之德,有此人即有此心,有此心即具此仁,本非在外之物也。人但迷于私欲而不知反求,故遂流于不仁,而视以为远耳。我若欲仁,反而自思曰:仁在吾心,不可失也,而求以得之,则一念方动,本体具见,仁固即此而在矣,何远之有?”夫以仁本不远如此,则人而不仁者,岂非自离其仁也哉?然仁具于心,至之虽甚易,而失之亦不难,必须于既至之后常加操存之功,则心德渐以纯全,而可造于中心安仁之地矣。此又求仁者所当知。
【原文】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张居正直解
陈是国名,司败是官名,即司寇也。昭公是鲁君。昔者鲁昭公习于威仪之节,当时以为知礼。陈司败以昭公娶同姓为夫人是失礼之大者,而乃负知礼之名,有所不足于心。故问于孔子说:“人皆以鲁君为知礼,果知礼乎?”孔子答说:“知礼。”盖人臣与君,称美不称恶,而陈司败亦未显言所以不知礼之事,故夫子直以知礼答之。
巫马期是孔子弟子,姓巫马,名施,字子期。党是庇护的意思。孟是长,子是宋国的姓。陈司败因孔子以昭公为知礼,心中不以为然。及孔子既退,适遇其弟子巫马期在前,乃迎揖而进之,与他说道:“吾闻君子之为人,平心直道而公其是非贤否于人,不私其人而为之党也。由今观之,君子亦阿党于人乎?何以言之?盖周家礼制,同姓不得为婚姻。吴,泰伯之后,鲁,周公之后,同是姬姓,而鲁君乃娶吴国之女为夫人,正犯此礼。却乃假辞遮饰,不称之曰吴孟姬,而称之曰吴孟子,夫子是宋姓也,娶吴国之女而冒宋国之姓,其能掩乎?是其任情越礼,明知故为,鲁君之不知礼甚矣!若君而可谓之知礼,则人人皆可谓之知礼矣,谁为不知礼者乎?”夫君不知礼,而夫子以知礼与之,是私之而为掩其过也,非党而何?司败品评昭公,固为确论。但疑孔子为党,则圣人用意之忠厚,彼盖有所不知也。
巫马期述司败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既不可自谓讳君之恶,又不可以娶同姓为知礼,乃自引以为己之过失说道:“这委实是我说差了。然凡人有过不得闻,则过无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可谓幸矣,苟有过失,人必知之。既知于人,则得闻于己,而可以改图于后日矣,岂非幸乎?”夫善则称君,过则归己,本理之当然。然孔子既自任以为过,则昭公之不知礼亦自有不可讳者。一则不昧天下是非之公,一则不失臣子忠厚之至。圣人一问答之间,真可以为万世法矣。
【原文】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张居正直解
歌是歌咏。善是歌得好。反是反复再歌。自歌以应人之歌叫作和。门人记说:“夫子好善之心无穷,不惟取人之善,而又以助人之善。如与人同歌,而其人之所歌,或辞意相协,音律相和,是歌之善者也。此时夫子之心,与之契合,要与之相和而歌,然不遽和也。必使之反复再歌,凡其辞意音律所以为善处,皆审察而详味之。既得其善矣,然后自歌以和之,使彼此迭奏,而同声相应焉。盖不但取彼之善为我之善,而又以我之善助彼之善矣。”夫孔子一咏歌之间,而气象从容,诚意恳至如此。其心与舜之取人为善,汤之用人惟己一般。此其所以为至圣也。
【原文】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张居正直解
言语成章叫作文。莫是疑词。犹人是说犹可以及人。孔子说:“人之所以为君子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世间有能言的人,或讲论道理,或敷陈政事,焕然有文采之可观,这不过在言语上求工而已。我虽未能过人,而犹或可以及人也。惟是身体力行,事事都实有诸己,而不为空言,这乃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则全未有得,虽欲勉焉以求至,而力有所不及矣。”观孔子此言,可见言易而行难,文在所缓,而行在所急。进德者固当先行而后言,用人者尤当听言而观行也。
【原文】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张居正直解
大而化之叫作圣,心德浑全叫作仁。抑是反语辞。公西华是孔子弟子。昔孔子至圣至仁,当时必有以是称之者。故孔子谦说:“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浑化的圣人与那心德纯全的仁人,则吾岂敢当乎?只是以仁圣之道而为之于己,则孜孜焉以求之,未尝以少有所得而遂生厌足之心;以仁圣之道而教诲于人,则谆谆焉以语之,未尝以劳于开导而或萌倦怠之意,这便是我之所能,不过如此而已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乎?”门人中有公西华者,闻夫子之言,乃仰而叹之说:“夫子辞仁圣之名,而自任夫不厌不倦者,岂以不厌不倦为易能乎?殊不知这正是弟子不能学处。”盖为之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至诚无息者,孰能无厌乎?诲人可能也,使非全体仁圣,而善与人同者,孰能无倦乎?然则夫子虽欲辞仁圣之名,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矣。昔祗德如大禹,而不自满假;缉熙如文王,而望道未见。孔子之心即禹、文之心也。圣人且然,况其他乎?欲学为圣人者,诚不可以自足矣。
【原文】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张居正直解
祷是祈祷。诔是哀词。上下神祇是天神地祇。昔孔子曾有疾病,门弟子都以为忧。于是子路请命于孔子,欲祷祀鬼神以祈福佑。盖疾病行祷虽弟子事师迫切之至情,然不达于人鬼之理,而溺于祸福之说,惑亦甚矣。孔子不直斥其非,乃先问说:“疾病行祷,果有此理否乎?”子路对说:“于理有之,吾闻诔词中有云:‘祷尔于上下神祇。是说人有疾时曾祷告于天地神祇,欲以转祸而为福,则是古人有行之者矣。’今以病请祷,于理何妨?”于是孔子晓之说:“夫所谓祷者,是说平日所为不善,如今告于鬼神,忏悔前非,以求解灾降福耳。若我平生,一言一动不敢得罪于鬼神,有善则迁,有过即改。则我之祷于鬼神者,盖已久矣。其在今日,又何以祷为哉?”盖圣人德于天合,虽鬼神不能违,岂待于祷?至于死生修短,则有命存焉,虽圣人亦惟安之而已,祷祀亦奚益乎?观孔子晓子路之言,可见当修德以事天,不必祷祀以求福。当用力于人道之所当务,不必谄渎于鬼神之不可知矣。
【原文】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张居正直解
奢是奢侈。孙字与逊顺的“逊”字同。不孙是僭越不循理的意思。俭是省约。固是鄙陋。孔子说:“先王制礼自有个中道,不可加损。若专尚侈靡而过乎中者,谓之奢。奢则意志骄盈,纵肆无节。虽理之所不当为者,亦将僭越而为之,其弊至于不孙。若专务省约,而不及乎中者,谓之俭。俭则悭吝鄙啬,规模狭小,虽理之所当为者,亦将惜费而不为。其弊必至于固。这不孙与固,皆不免于失中。但就这两样较来,则与其为不孙也,宁可为固。”盖奢而不孙,则越礼犯分,将至于乱国家之纪纲,坏天下之风俗,为害甚大。若俭而固,则不过鄙陋朴野而已。原其意犹有尚质之风,究其弊亦无僭越之罪,不犹愈于不孙者乎?盖周末文胜,孔子欲救时之弊,故其言如此!然俭,乃德之共,奢,乃恶之大,二者之相去岂特过与不及之间而已哉?帝尧茅茨土阶、大禹恶衣菲食而万世称圣,汉之文帝、宋之仁宗皆以恭俭化民,号为贤主。至如骄奢纵欲,横征暴敛,以败坏国家者,往往有之。然则去奢崇俭乃帝王为治之先务,有国家者所当深念也。
【原文】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张居正直解
坦是平坦,荡荡是宽广貌。戚戚是忧愁不宁的意思。孔子说:“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观其心术气象自然不同。盖君子心循乎天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故仰焉不愧于天,俯焉不怍于人。利害不能为之惊,毁誉不能为之惑,但见其坦然荡荡,无适而不宽舒自得也。小人心役于物欲,行险侥幸,惟日不足,故非切切以谋利禄,则汲汲以干名誉。其未得也,患得之;其既得也,患失之。但见其长是戚戚,无时而不忧虑愁苦也。”夫坦荡荡者,作德心逸日休也;长戚戚者,作伪心劳日拙也。一念既差,而人品遂顿殊矣。可不慎辨之哉!
【原文】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张居正直解
温是和厚。厉是严肃。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庄敬。安是安舒。门人记说: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气质各有所偏,故其见于容貌者亦偏。惟夫子则容貌随时不同,而无有不出于中和者。如人之温者难于厉也,夫子和厚可亲是固温矣。然和厚之中自有严肃者在,可亲也,而不可犯也,又何其厉乎?温而厉,是温之得其中也。人之威者易于猛也。夫子尊严可畏,是固威矣,然尊严之内自无暴戾者存,可畏也亦可近也,何至于猛乎?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人之恭者难于安也。夫子庄敬自恃,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迫,自然而非勉强,盖周旋中礼而有忘其恭者焉,又何其安乎?恭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盖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欲取法其盛德之容者,当先涵养其中和之蕴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