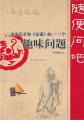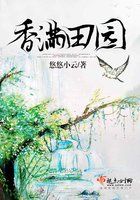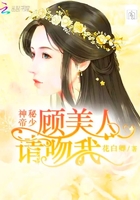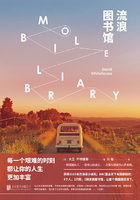【原文】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张居正直解
公冶长是孔子弟子。女嫁与人为妻,叫作妻。缧,是黑索。绁,是拘禁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系之于狱中,叫作缧绁。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谓之子。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伦莫重于婚姻,匹配莫先于择德。吾门弟子,若公冶长者,可以女配之而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虽曾为事拘系于狱中,乃是被人连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则固无害其为贤矣!”于是以所生之女而为之妻焉。此可见圣人之于婚嫁,不论门族,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非独谨于婚姻,亦可谓明于知人者矣!
【原文】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张居正直解
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宫縚,字子容。废,是弃而不用。戮,是杀戮。门人又记,孔子曾说:“吾门有南容者,尝三复白圭之诗,平日素能谨言慎行,是个有德的君子。若遇着国家有道,君子进用之时,他有这等抱负,必然人人荐举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于废弃而不用也。遇着国家无道,小人得志之日,他既言语谨慎,不致取怨于人,亦可以全身而远害,必不陷于刑戮之祸也。处治处乱,无所不宜,则其贤可知矣!”于是以其兄之女配之而为妻焉。前章以己女妻公冶长,此章以兄女妻南容,皆择贤而配,圣人致谨于婚配之礼如此。
【原文】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张居正直解
子贱,是孔子弟子宓不齐,字子贱。斯字,解做此字,上一个斯字是说此人。下一个斯字,是说此德。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之为学,都要学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门若宓子贱者,他的学力已达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贱所以能为君子,虽是他自家向上,有志进修,亦由我鲁国多君子,人才众盛,故得以尊师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鲁没有许多君子,则虽要尊师,而无师之可尊;虽要取友,而无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闻而已,将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可见自修之功固不可废,而师友之益,又不可无也。然师友之益,不但学者为然,古之圣帝明王屈己下贤,虚心访道,尊崇师保,而资其启沃,慎择左右,而责之箴规,无非欲严惮切磋,养成君德而已。古语说:“师臣者帝,宾臣者王。”然则人君欲成其德者,当以好学亲贤为急。
【原文】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张居正直解
赐,是子贡的名。器,是器皿。瑚琏,是宗庙中盛黍稷的器,以玉为之,夏时叫作瑚,商时叫作琏。子贡平日好比方人物,因见孔子以君子许子贱,故以己为问,说道:“赐也学于夫子,亦尝有志于进修,但造诣之浅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试说赐之为人何如?”孔子答说:“人之为学,以致用为贵,如世间器皿,以适用为宜,汝能告往知来,料事多中,既达于政事,又长于言语,是个有用的成材,就如器之适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贡又问说:“器有贵贱之不同,夫子以赐为器,不知是何等样器?”孔子答说:“器中有瑚琏者,陈之于宗庙,而饰之以玉,最是贵重而华美的。以汝之才,试之于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观,而足以为邦家之光,岂非器中之瑚琏矣乎。”然则子贡虽未能如君子之不器,其亦器之贵者矣。
【原文】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张居正直解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春秋之时,人皆以口才便利为尚。而冉雍为人,重厚简默,与时俗不同。故或人谓孔子说:“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论其为人,可谓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素性简默,无有口才,而不能为佞也。”或人之言,非惟不知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御字,解作挡字。譬如说,抵挡人一般。给,是取办。屡,是多的意思。憎,是恶。孔子答或人说:“汝以冉雍为不佞,是必以佞为贤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己,亦何用于佞乎?盖佞人所以应答搪抵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办一时。那甜言巧语,高谈阔论,外面虽似有才,其中都没有真实的意思,被人看破,却是个邪佞的小人,不足以取重,而徒多为人所憎恶耳,亦何益之有哉。今汝以雍为仁,我固不知他仁与不仁。但说他不佞,正是好处。要那口才何用乎!然则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由孔子之言观之,可见学者当用力于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只可憎,为害甚大,盖其言足以变乱黑白,颠倒是非,或逞其私智,以纷更旧章。或巧为谗言,以中伤善类,人君若不知而误听之,未有不败坏国家者。故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覆邦,皆所以垂戒于万世也。用人者可不以远佞于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见于三宅之心,这正是得知人之可信而后用之,所以能收得人之功。可见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审其所长,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所蕴也。
【原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张居正直解
桴,是木筏。由,是子路的名。材与裁字同,是量度的意思。昔春秋之时,上无贤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叹说:“吾之周流四方,本欲得位行道,以致君而泽民。今人不见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于天下矣!虽居在中国,亦何为乎!不如乘着木筏,浮于海中,可以绝人而逃世。吾门弟子中求其可以从我远去者,其惟仲由欤?”盖仲由勇于为义,是个临难不避的人,故孔子许其从己。然这说话也只是孔子自伤其不遇而假设之词,非真有浮海之意也。子路闻之,以为夫子不许他人而独许己,遂信以为实然,心中喜悦。盖过于信人为急务哉!
【原文】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张居正直解
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开。仕,是出仕做官。斯,指此理说。信,是知之真的意思。说,是喜悦。门人记,孔子使其弟子漆雕开者,出仕而为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开对说:“人之为学,须是于这道理,实得于心,知得十分透彻,深信不疑。然后出而居其位,行其志,才能事事停当。今我于这道理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是自己心里还有信不过处,正该力学以充之,岂可便出而治之乎!”观开此言足徵他所见者大、所期者远,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于精微之极,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闻而喜悦,盖深嘉其笃志于学,而将来成就有不可量也。求之于古,如伊尹乐道畎亩,便自任以天下之重。傅说身居版筑,便一出为王者之师,这正是他信得过处,所以能成辅相之业。夏禹迪知忱恂师,而暗于事理者矣!故孔子教之说:“凡人懦弱者,多惮于涉险,由也不以浮海为惧,而以得从为喜,这等好勇岂不胜过于我乎!然海岂可居之处,吾岂人海之人,不过伤时之意云尔,而由也遽以为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宜矣。由也可不思所以进于是哉!”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此可见圣人虽有伤时之意,而终无忘世之心,但当时之君,不能用其言而行其道耳。以孔子之圣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终于乱也。
【原文】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张居正直解
孟武伯,是鲁大夫仲孙彘。仁,是本心之全德。孟武伯问于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轻许,故答他说:“仁具于各人之心,难以必其有无,仲由之仁与未仁,我所不知也。”
千乘之国,是诸侯大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的。赋,是兵。古者军马都出于田赋中,故叫作赋。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若师。子路之仁,夫子岂有不知的,故又以为问。孔子答说:“由也好勇而果断,便是千乘的大国,若用他管理那兵赋的重事,必能训练倡率,不但使军旅强盛而有勇,抑且使亲上死长而知方,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室,是家。邑,是县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车百乘的。邑长家臣,通叫作宰。孟武伯又问夫子之门人若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答说:“求也多才。虽是千家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做邑长,必能修政于其邑,而使人民无不安。用他做家臣,必能修职于其家,而使庶务无不举,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束带,是着礼服而束带于其上。宾客,是四方来聘的使臣。孟武伯又问:“夫子之门人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为仁人矣乎?”孔子答说:“赤也知礼。若使他束带立于朝廷之上,应对那四方来聘的宾客,必能通两国之情,达宾主之意,而不至于失礼。其才之可见者如此。若其心之仁与不仁,吾不得而知也。”盖仁之为言,必纯乎天理,而无一私之杂,始终惟一,而无一息之间,才叫作仁。其心之纯与不纯,有非行事所可见,他人所能识者。故夫子于三子皆许其才,而未信其仁。盖以发于外者易见,而蕴于心者难知也。有志于求仁者,当省察于吾心独知之地而后可。
【原文】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张居正直解
愈字,解作胜字。昔孔子因子贡好比较他人的短长,而或暗于自知,故问之说:“你与颜回同游吾门,你自家说,比他所学,孰为胜乎?”
子贡对说:“人之资质有高下,悟道有深浅。赐也何敢指望到得颜回。盖回也是生知之亚,资禀既高,工夫又到,其于天下的义理,听得一件,就晓得十件。从头彻尾,无不默识心通,盖闻一以知十者也。赐也学而知之,资禀既庸,工夫又浅,其于天下的义理,听得一件,只晓得两件,比类思索,因此识彼,不过闻一以知二而已。”即此观之,回胜于赐远矣!赐也果何敢望回乎!
与,是许。孔子因子贡之言,遂激励引进之说道:“汝自谓不如颜回,此言非虚,汝委实不及他。但人莫难于自知,而亦莫难于自屈。今汝自以为弗如,则是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矣。夫能自知,则必不安于所已知,能自屈则必益勉其所未至,今日之不如,安知他日之终不如乎?我诚取汝这弗如之说也。”其后子贡终闻性与天道,不止于闻一知二而已。岂非夫子激励造就之欤!然这弗如之一念不但是学者上进的机栝,若使为人君者能以古之帝王为法,而自视以为不如,必欲仰慕思齐而后已,则其进于圣帝明王也不难矣!
【原文】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张居正直解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昼寝是当昼而睡。朽木,是腐坏的木头。雕,是刻。墙壁上盖着泥粉,叫作杇。诛,是责。何诛,是说不足怪责。昔孔门设教,只是要人好学。盖能好学,则志气精明,工夫勤密,然后可以人道。宰予学于孔子之门。一日当昼而寝,这便是昏昧怠惰,不肯好学的人。故孔子责之说:“凡木之坚者,然后可雕。若朽腐之木,虽欲雕刻成文,必然坏烂,岂可得而雕乎?凡墙之固者,然后可杇。若粪土之墙,虽欲饰以泥粉,必然剥落,岂可得而杇乎!譬如人必有志向学,然后可教,今予之昏惰如此,就似那朽腐之木、粪土之墙一般,虽欲教之,而无受教之地矣!然则我之于予,又何用于责备乎!”言不足责乃所以深责之也。夫宰予以一昼寝之失,而孔子责之严切如此,可见人当以勤励不息自强,以怠惰荒宁为戒。故禹惜寸阴,成汤昧爽丕显,文王日曼不遑息,孔子发愤忘食,此皆生知之圣人,其勤如是。况未及圣人者乎!学者不可不深省也。
宰予平日每自言其能学,今乃当昼而寝,志气昏惰,则行不及言甚矣!故孔子又警之说:“听言甚易,知人甚难。我始初与人相处,只道会说的便会行。故听人之言,就信其行,而不复疑其素履之何如。如今看来,凡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若闻言便信,未免为人所欺,故自今以往,听人之言,必观其行,而不敢遽信其言,行之相顾也。夫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则虽善为词说者,无所用其欺,而可免于轻信之失矣。然我所以能改此失者,只为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我起初曾信其行,而今日始觉其非,故以此为戒,而改我之失耳。”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宰予,使之惕然而悔悟也。夫师弟子之间,朝夕相与,其为人贤否易见,而孔子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盖人之难知如此,况人君之于臣下,尊卑之分悬殊,接见之时甚少,欲尽知其心术之微,得其行事之实,岂不难哉!盖敷奏必以言,而明试必以功,此即听言观行之法,用人者所当加意也。
【原文】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张居正直解
刚,是坚强不屈的意思。申枨,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枨。欲,是贪欲。孔子说:“凡人立身于天地间,须是有刚强之德,乃为可贵。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见有刚强者。”孔子之所谓刚,不但是血气强勇而已,是说人得天地之正气,而又有理义以养成之,其中磊落光明,深沉果毅,凡富贵贫贱,祸福死生,件件都动他不得。然后能剖决大疑,而无所眩惑,担当大事,而不可屈挠,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人之所易及者,故孔子叹其难见耳。或人不知其义,止见申枨血气强勇,就以为刚。乃对孔子说:“夫子之门人如申枨者,其为人岂不刚乎?”孔子答说:“凡刚强的人,必不屈于物欲。枨也多欲,不能以理义为主,则凡世间可欲之事,皆足以动其心。其心一动,则意见必为之眩惑,志气为之屈挠矣,焉得谓之刚乎!”观孔子此言,可见有欲则无刚,惟刚则能制欲,凡学为圣贤者,不可以不勉也。然先儒有言,君德以刚为主。盖人君若无刚德,则见声色必喜,闻谀佞必悦,虽知其为小人,或姑息而不能去,虽知其为弊政,或因循而不能革,至于优游不断,威福下移,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欲求致治,岂可得哉!然则寡欲养气之功,在人君当知所务矣。
【原文】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张居正直解
子贡自言其志于夫子说道:“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礼之事,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的心,也是不欲的。若以己所不欲者而加之于人,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之所为也。赐则视人犹己,视己犹人。凡我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以此而加之于人。”夫观子贡此言,固是他志量高处,然此乃仁者之事,子贡之学尚未能到此地位。夫子恐其自许太过,而行不逮言也,故呼其名而抑之,说道:“最难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凡己之所不欲者,即不以加之于人,则是视天下为一人,而略无形骸之间,以万物为一体,而溥其兼利之仁,这非是心德纯全,而己私克尽者不能。汝之所学,岂能遽及于此乎?所以说非尔所及也。”然孔子此言,不是言难以阻人之进,盖欲子贡知其难而加勉也。
【原文】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张居正直解
文章,是德之见乎外者,指威仪文词说。性,是人所受于天之理。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体。子贡说:“凡人学力有浅深,故其闻道有难易。吾夫子平日,凡动作威仪都有法度,言词议论都有条理,这是德之著,见乎外的,所谓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无所隐秘,故不待深造者而后闻之。凡浅学之士,从游门墙者,皆可得而闻也。若夫仁义礼智,禀于有生之初的,叫作性。元亨利贞,运于於穆之中的,叫作天道。夫子亦尝言之矣。但道理极其微妙,言语难以形容,若不是学力既深,可与上达的人,决不轻告。故不但浅学之士,不得而闻,虽久于门墙者,亦不可得而闻也。”盖子贡晚年进德,乃始得闻性与天道,故叹之如此。然圣门教人,循序渐进,于此亦可见矣。
【原文】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张居正直解
这是门人记子路之勇于为善,说道:“人固贵于闻善,然闻而不行,与不闻同。行而不力,与不行同。惟子路之为人,有兼人之才,负刚果之气,每闻一善言,必即时行之而后已,若或未之能行,则此心惕然不宁,惟恐复有所闻,而前闻者,或壅滞而不得行焉。”曰惟恐有闻者,非不欲后闻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闻,而预待其所未闻耳。观未行而惟恐有闻,则既行而惟恐不闻可知矣!子路之勇于体道如此。
【原文】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张居正直解
孔文子,是卫国的大夫,姓孔名圉,谥文子。敏,是聪敏。下问,是问于在下的人。古时生有爵位者,没必有谥。人有贤否,则其谥有美恶。孔圉得谥为文,是个美谥。子贡疑其为人不足以当之。乃问于孔子说:“卫大夫孔文子者,不知何以得谥为文也?”孔子答说:“凡人资性明敏的,便恃着他的聪明,不肯向学。孔圉虽有明敏之资,他却不敢自是。凡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一一讲习讨论,而无有厌心,其勤学如此。爵位尊显的,便看得自己过高,耻于下问。孔圉虽居大夫之位,他却不敢自亢,凡事有未知的,一一访问于人,虽下僚之卑,小民之贱,也虚己问之,而不以为耻,其好问如此。盖谥法中有云:勤学好问曰‘文’。今孔圉之行,正与之相合,此其所以得谥为‘文’也。”然勤学好问,不但是卿大夫之美行,虽古帝王之盛节亦不外此。盖人君有聪明睿智之资,尤易于自用;居崇高富贵之位,尤难于自谦。然不学,则义理无由而明;不问,则闻见无由而广。故虞舜好问好察,所以为圣。高宗逊志典学,所以为贤,真万世人君所当法也。
【原文】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张居正直解
子产,是郑大夫公孙侨,字子产。恭,是谦逊。敬,是谨恪。惠,是恩惠。义,是裁制经画,事事都有条理的意思。昔孔子尝称说:“郑大夫子产之为人,有君子之道四件,何以见之。彼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产之行己也,则有善不矜,有劳不伐。推贤让能,退然恭逊以自居,是有君子之道一也。敬以事君,君子之道也。子产之事上也,则内修国政,外睦诸侯,小心尽职,始终敬谨而无怠,是有君子之道二也。仁以育民,君子之道也。子产之养民也,则利必为之兴,害必为之去,件件都替百姓留心,而有厚下之深恩,是有君子之道三也。义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产之使民也,则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事事都有个限制,而无姑息之弊政,是有君子之道四也。”子产备这四美于上下人己之间,是以能尊主庇民,而郑国赖之,岂非春秋之贤大夫欤!然郑以区区小国,能用子产,故虽介于晋楚二强国之间,而竟能杜其侵陵之患,若人君以天下之大,任用得人,则其长治久安之效,又当何如哉!此用人者所当加意也。
【原文】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张居正直解
晏平仲,是齐大夫。姓晏名婴,字平仲。善与人交,是说能尽交友之道。孔子说:“朋友五伦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则善与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起初皆知相敬,至于既久,则习狎而怠忽矣!怠忽则必生嫌隙,嫌隙既生,交不能全矣。平仲之与人交也,始固相敬,至于久而亦然,不以其习狎而生怠忽之心,故交好之义,始终无替,此平仲之所以为善与人交也。”
【原文】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张居正直解
臧文仲,是鲁大夫,姓臧名辰,谥为文仲。素以智名者也。居,是藏。蔡,是大龟,用以为卜者。以其获之于蔡地,遂名为蔡。节,是柱头斗拱。藻,是水草。税,是梁上短柱。孔子说:“人都以臧文仲为智,然明智之人必然见理不惑,试举他一事言之。且鲁之有大龟,虽所以为占卜之用,然不过以决疑示兆而已,非能司其祸福之柄也。文仲乃为屋室以居之,又将那柱头斗拱上,都刻为山形,梁上的短柱,都画上水草,真若大龟居处于其中,而能降福于人者,斯不亦大惑矣乎。”盖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当尽,而神之理,则幽昧而不可知。惟尽其所当务,而不取必于其所难知,斯可谓智矣。今文仲不务民义,而谄渎鬼神如此,则是不达幽明之理,而惑于祸福之说,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谓之智乎?夫文仲之智,人皆称之。夫子独据实而断其不然,这正是众好之必察焉者。所以为人物之权衡也,观人者宜取以为法。
【原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张居正直解
令尹,是楚国执政的官。子文,是楚人。仕,是进用。已,是罢官。愠,是怒意。子张问于孔子说:“楚国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进用而为令尹,人都羡他尊荣,他却无喜悦之色。及至三次罢官,人都替他称屈,他也无愠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他既罢了令尹,又把旧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与新任的令尹。略无猜嫌妒忌之心。其物我无间如此,这等为人,夫子以为何如?”孔子答说:“凡人患得患失,妒贤嫉能者,都是只顾自己,不为国家,此乃不忠者之所为也。子文这等行事,是不贪恋朝廷的名爵,只要干济国家的政事,是个实心为国的人,可以为忠矣。”子张又问说:“制行如此,人所难能,亦可谓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说:“仁在于心,不在于事。子文之行虽忠,然未知他心里如何,若有一毫修名为人之意,便是私心,而非纯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便信其为仁矣乎!故不敢以轻许之也。”
崔子,是崔杼。陈文子,是陈须无。都是齐国的大夫。马四匹为一乘,十乘是四十匹。违,是去。犹,是相似。子张又问说:“当初齐大夫崔子弑了齐君,那时也有同恶相济的,也有隐忍不去的。独有陈文子者,恶其为逆,不肯与之同列,虽以大夫之官,有马十乘之富,飘然弃而去之。略无贪恋顾惜之意,及到他国,见其臣皆不忠,便说道:‘这就与吾国大夫崔子一般,不可与之共事,遂违而去之。’又到一国,见其臣亦不忠,又说道:‘这也与吾国大夫崔子一般,亦不可与之共事。’又违而去之,其审于去就如此。夫子以为何如?”孔子答说:“凡人与恶人居,便要污坏了自己的名节,清者不为也。今陈文子不恋十乘之富,不居危乱之邦,是个洁白不污的人,可以为清矣。”子张又问说:“制行如此,人所难能,亦可谓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说:“仁在于心,不在于事。文子之行虽清,未知他心里如何?若有一毫愤俗自高之意,而后来不免于怨悔,这也是私心,而非纯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遽信其为仁矣乎!故亦不敢轻许之也。”大抵人之行事易见,而心术难知。其念虑之纯与不纯,存主之实与不实,有非他人所能尽察者,故虽以文子之忠、文子之清,而夫子犹未肯以仁许之。观此,则仁之所以为仁,其义可知,而人之有志于仁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张居正直解
季文子,是鲁大夫,名行父,谥为文子。三思,是思了又思,展转无已的意思。再,是两次思量。昔鲁大夫季文子者,是个用心周密的人,每事必反复计虑,思了又思,展转数次,然后施行。孔子闻之说道:“人之处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过思。故凡事到面前,造次未可轻动,从而仔细思量一番,及思之已得,犹恐见不的确,又平心易气,再加斟酌一番。如此,则事理之可否从违,裁度已审,行出来自然停当,斯亦可矣!何必三思为哉!”盖天下之事,虽万变不齐,而其当然之理,则一定不易,惟在义理上体察,则再思而已精,若用私意去揣摩,则多思而反惑。中庸教人以慎思者,意正如此。善应天下之事者,惟当以穷理为主,而济之以果断焉,则无所处而不当矣!
【原文】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张居正直解
宁武子,是卫大夫宁俞,谥武子。知,是明知。愚,是昏愚。盖世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又有一等明知之深,韬光用晦,权以济变,反似昏愚的,则所谓大智若愚者也。宁武子能然,故孔子称之说:“宁武子之为卫大夫也,当国家有道,治平无事之时,则明目张胆,知无不为,直道而行,无少委曲,他的才能智识,都昭然可见,真是个明智的人。及至国家无道,危急存亡之日,则韬晦隐默,不露形迹,而卒以济艰难之业,成国家之事。他的才能智识都暗然内用,却似个昏愚的人。夫观人者,但据其迹而未窥其深,则必以愚不如智矣。自我而言,治平之世,公道昭明,君子可以行其志,但有才能的都会干济,有见识的都会主张,武子之智犹或可得而及也。至于昏乱之朝,则国势倾危,人心疑忌,忠君为国之深意,既难以自明,扶危定乱之微权,又难于先泄,最人之所难处者。武子之愚,乃能上济其君,下保其身,正是他善藏其用的妙处,非天性忠义,而才足以运之者,不能如此,人岂可得而及哉?”盖处常易,处变难,用其智以立功者易,藏其智而成功者难。所以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自人之分量而言,知固不如愚,然时乎无道,乃使君子不敢用知而用愚,则岂国家之幸哉!
【原文】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张居正直解
陈,是陈国。党,是乡党。小子,指门人之在鲁者说。狂简,是志大而略于事的意思。斐,是有文采。裁,是裁正。昔孔子周流四方,至于陈国淹留既久,知道之终不能行,乃发叹说道:“吾之初心本欲行其道于天下,今周流至此,而竟不一遇,是世终无用我者矣。我其归于鲁国欤?我其归于鲁国欤?然我之道虽不行于当时,犹当传于后世。今吾乡党后生中,尽有识见高明,志趣远大,不拘于小节的人,看他规模体段,已是斐然有文理之可观。但其志愿太高,学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时出于规矩之外耳。若就其才性之所近者,因而抑其过,矫其偏,以归于中,则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寄吾欲行之心,又何必栖栖遑遑以求用于世哉!此吾之所以欲归也。”是可见圣人为当时计,固欲其道之行,为后世计,又欲其道之传,其心真有视天下为一家,通古今为一息者。此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教万世无穷也欤!
【原文】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张居正直解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之二子。长曰伯夷,幼曰叔齐。念,是追念。怨,是恨。希字,解作少字。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至清介者也。大凡清介的人,疾恶太甚,其中多褊狭而不能容物,故人亦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齐,持身虽介,处心甚平,人有不善,固尝恶而绝之矣。然只是恶其为恶,而非有心以绝其人也。若其人能改而从善,则止见其善,而不复追念其旧日之恶,其好恶之公,度量之广如此,所以人皆尊敬而悦服之,就是见恶的人,亦乐其后来之能恕,而谅其前日之无他。怨恨之心,自然少矣。”此可见疾恶固不可以不严,而取善尤不可以不恕。古圣贤处己待人之道,莫善于此。若人君以此待下,尤为盛德。盖凡中材之人,孰能无过,惟事出故为,怙终不悛者,虽摈斥之,亦不足惜,然或一事偶失,而大节无亏,初时有过,而终能迁改,以至迹虽可议,而情有可原,皆当舍短取长,优容爱惜,则人人乐于效用,而天下无弃才矣。虞舜宥过无大,成汤与人不求备,皆此道也。此可以为万世人君之法。
【原文】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张居正直解
鲁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见称于时。人但慕其名而不察其实,故孔子举一事以断之说:“人皆以微生高为直,如今看来,谁说他是直人。盖所谓直者,必诚心直道,有便说有,无便说无。无一毫矫饰,而后谓之直。今微生高者,人曾问他求醋,其家本是没有,却不肯直说,乃转问邻家求来与他,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矣。即此一事推之,则其心之私曲,行之虚伪可知,焉得谓之直乎?”夫微生高之直,人皆信其行,而孔子独断其非,所谓众好之必察焉者如此。然当时似是而非,虚名无实者,不止一事,利口之人乱信,乡愿之人乱德,孔子皆深恶而痛绝之。盖欲人致谨于名实之辨也,然则用人者岂可徒采虚名而不考其实行哉!
【原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张居正直解
巧言,是言词工巧。令色,是颜色和柔。足恭,是过于恭敬而不中礼者。左丘明,是当时贤人。耻,是羞愧。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孔子说:“人莫善于诚心直道,莫不善于谄媚奸险。盖人之相接,词色体貌,本自有个正礼。若乃巧好其言,务以悦人之听,令善其色,务以悦人之观,足过其恭,务以悦人之意,是谄媚之人也。左丘明为人方正,尝耻之而不为,我亦耻之而不为焉。人之相交,恩怨亲疏自有个真心,若心里本是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面,佯与交好,是奸险之人也。左丘明存心诚笃,尝耻之而不为,我亦耻之而不为焉。”夫观此二者为圣贤之所共耻,学者可不省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哉!然此等人不止可耻,尤有害于国家。盖谄媚之人,阿谀逢迎,非道取悦,人情易为其所惑。奸险之人,内怀狡诈,外示恭谨,人情易为其所欺。若不识而误用之,则其流祸有不可胜言者,所以古之圣王,远佞防奸,如畏鸩毒而避蛇虺。盖为此也。
【原文】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张居正直解
盍,是何不。志,是心之所向。昔颜渊、季路尝侍于孔子之侧。孔子向他们说道:“二子学于吾门,都各有个志向,何不各言尔之志于我乎!”
衣,是着衣。裘,是皮服。敝,是坏。憾,是恨。子路因孔子问其志,遂对说道:“人不可以自私,且如乘的车马、着的轻裘,虽是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当为天下用之,不得专之以为己私也。我若有此车马轻裘,则愿与朋友共之,虽至敝坏亦无所恨焉。”盖子路勇于为义,识见高明,不屑为鄙吝之事,故其言如此。
伐,是矜夸。善,是有德。施,是张大的意思。劳,是有功。颜渊因孔子问其志,遂对说道:“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虽有善可称,然亦不过复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不欲矜夸于人,而自以为善焉。人能立功,虽有劳可表,然不过尽吾职,分之所当为而已。我若有劳,不欲张大于人,而自以为劳焉。”盖颜子几于无我,气象浑厚,无一毫满假之心,故其言如此。
安,是安逸。怀,是抚恤的意思。子路问于孔子说:“吾二人之志,已各言于夫子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愿有闻焉。”孔子答说:“吾之志无他,只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盖天下之人不同,有老者焉,有朋友焉,有少者焉。老者当安,吾愿养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逸。朋友当信,吾愿与之以信,而使之各全其交。少者当怀,吾愿抚恤之以恩,而使之各适其性。随其心之所欲得,而与之以理之所本然。此则吾之志也。”合而观之,子路公其物于人,而有难于兼济。颜子忘其善于己,而犹出于有心。惟夫子之志兼利万物而不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见其迹,真与天地之量一般,又岂二子之所能及哉!使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则时雍风动之化,当与尧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原文】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张居正直解
已矣乎,是绝望之辞。内自讼,是心里自家悔责。孔子说:“人不能以无过,而能改则可为君子。然必自知其过,而内自讼责,则即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我尝以此望于天下之人,自今看来,凡人有过,不是饰非以自文,便是委靡以自安,并未见有自家知所行的不是,而内自悔责者也。然则欲求其能改过,岂可得乎!昔之所望于人者,今则已矣。”这是孔子欲人悔过迁善,故为是绝望之辞,以激励天下人的意思。大抵悔之一字,乃为善之机。《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故终为有商之令主。然能居敬穷理以预养此心,则自然邪念不萌,动无过举。圣人所以能立无过之地者,其要在此。若待其有过而后悔之,不亦晚乎?孔子之言,盖为中人以下者发也。
【原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张居正直解
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资质纯实,可进于道者。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说:“人之造道,固在于天资,而尤须乎学力。我之得闻斯道,非徒以资质之美而已,实由好学以成之也。若但以资质言之,则岂必天下之广,就是那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纯朴笃实,可进于道如我者焉。则天下之如我者,可胜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质,不如我之勤敏好学以扩充其资,所以不能闻道,而有成者鲜也。”夫人乃不咎其学之不至,而徒诿于资之不美,岂不过哉!盖美质易得,至道难闻,故君如尧舜,必孳孳于精一,圣如孔子,犹汲汲于敏求,况其他乎!欲法尧舜孔子者当知所以自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