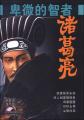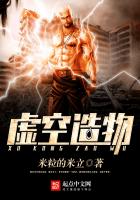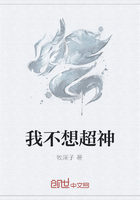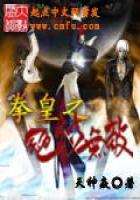光绪的心思
杨锐一直潜伏在皇权中心。宫廷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及时密报张之洞。这也是张之洞一直没有同维新派撕破脸皮的原因,他清楚地知道,光绪皇帝以及帝党分子一直在支持维新运动。他还知道,因为他对维新派的慷慨资助和大力扶持,光绪皇帝已对他表示出深切的好感和倚重之情。
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光绪皇帝就对他充满了这份情意,但因为翁同龢等顽固守旧派的阻挠和打压,光绪皇帝无法向他表白什么,只好把这份情意深埋在心底。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光绪皇帝更加敬重张之洞。因此,当张之洞上奏《吁请修备储才折》后,他立即批准推行。但心里话还是没说出去,他一直在等待,他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再向张之洞表白。
张之洞的判断
光绪皇帝的心思,张之洞根本不用猜。因此,他一直在坐观事态的发展和变化。但维新派这帮人,大多都是60后、70后的年轻人,张之洞又不得不防。在他们身上,张之洞似乎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激进、愤青、二愣、冲动,说话胆大包天,做事不计后果。
在他看来,这帮年轻人绝对比当年的清流还清流,当年的清流主要是上书言事,参劾权臣;而这帮年轻人,却要改革政治,参劾皇权,真是胆大包天。
对此,他真的想不明白:社会发展变化就是再快,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就是再潮,也不能拿政治和皇权开玩笑吧?难道他们就没读过历史吗?远的不说,就说近代的清流党吧,在清流党,除了我张之洞早早地转型,成功做了洋务派首领外,其他人哪个有善终?
上书言事都没有好下场,改革政治、参劾皇权还不得掉脑袋?更何况,清流派的上书言事,其宣传范围仅限于朝廷内部;而维新派的改革政治、参劾皇权,却通过报纸满世界地发,这事可就闹大了。
这事绝对要掉脑袋,甚至株连一大片。且不说历史曾无数次证明,就说慈禧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能容忍这帮年轻人如此兴风作浪?
维新派的思想是先进,是新颖,政治改革也可以推行,但凡事总有一个过程,要循序渐进,不断发展,千万不要激进、不要冲动,冒冒失失总会撞墙。
等着吧,这帮年轻人早晚会吃亏的,一场血光之灾很快就会降临!
潜伏成功
正是有了这种老到敏锐的意识,以及洞若观火的判断能力,张之洞在扶持维新派的同时,又打压、控制他们,并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而且,他还指示绝对服从于他的儿子张仁权、门生杨锐、幕僚汪康年等人:头脑要冷静,立场要灵动,不能绝对维新,也不能一点儿都不维新,要在帝、后两党之间摇摆,做帝、后两党都倚重的红人,这样即使出了事,也不会殃及自身。
姜还是老的辣,杨锐等人对恩师的教导深以为然,并作为行动指南。凭借在维新派中的影响和张之洞的操纵,杨锐很快接近了光绪皇帝。这源于一件事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强占山东青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为期99年的租界条约,并取得了山东境内的铁路修筑权和矿产开采权。在德国的影响和带动下,俄国、法国、英国群而起之,纷纷强租了广州、威海、旅顺和大连等重要港口城市。至此,中国更进一步沦为帝国列强的殖民地,在帝国列强的侵占和瓜分下,中国甚至有一种亡国灭种的气息。
值此危难之际,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变法图强。这次上书,他还提到了开国会、定宪法的政治主张。光绪皇帝深以为然,于是令康有为详细陈奏变法事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建议光绪皇帝效法日本明治天皇,领誓群臣,诏定国是,推行维新变法。作为康有为的搭档,杨锐表现得十分卖力。三月二十二日,他和康有为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从而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极大关注。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同时召见康有为、梁启超,并授予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门办理新政,实施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农历戊戌年)。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办事人员,相当于军机大臣的助理,被称为“小军机”。虽然只有四品衔,却能掌握实权和朝廷机密。
与其说谭嗣同和杨锐等四人是军机大臣的助理,还不如说他们是光绪皇帝的助理。因为在此之前,光绪皇帝根本没有什么实权,凡事都要请示慈禧。可是自从变法之后,很多事情他都敢擅自做主了,有什么旨意就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办理,直接绕过了慈禧及其后党官员。
光绪对这四个人的重用,深深地触动了慈禧,这个权欲熏天的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皇帝小儿长大了,翅膀也硬了,他想架空我,没门!我得对他留一手,哼!
请注意这四个军机章京,除了谭嗣同是坚定的维新派外,杨锐是张之洞的心腹门生,刘光第是张之洞托陈宝箴举荐的维新人士,林旭曾在中日战争时期做过张之洞的幕僚。
也就是说,在这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是张之洞一手安插的,可见他当时的势力和对维新运动的影响有多大。而杨锐能够入军机,且成为光绪皇帝的助理,除了他设身处地靠近皇权中心的原因外,也有张之洞四处活动保举他的因素。但张之洞的身份太敏感,他不能直接干这事,而是密令陈宝箴出面保举。
无论怎样,杨锐终于完成了张之洞交给他的潜伏任务,正是通过杨锐的卧底和努力,张之洞一直游刃于帝、后之间,而且他始终都是帝、后倚重的红人。
入参军机流产
戊戌变法前,慈禧和光绪同时作出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决定:召张之洞进京,入参军机!
促使慈禧作这个决定的人是大学士徐桐和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荣禄等人。徐桐(1820—1900年,汉军正蓝旗人)早年加盟南清流党,因为同样受到慈禧的倚重,他对张之洞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二十七日,徐桐等人奏请朝廷调张之洞入参军机,充军机大臣,得到了慈禧和光绪的一致同意。
慈禧同意张之洞入军机的原因很简单:张之洞是她钦点的探花,是绝对效忠于她的疆臣和心腹,这次提拔重用他,他会更加效忠自己。再说无论是名望、资历,还是能力,张之洞都有资格入军机,只要有他在朝廷,她就可以放心地休养。另外,慈禧特别讨厌光绪身边的翁同龢,调张之洞入军机,正好可以打压、制衡他,何况他俩素有矛盾。
较之慈禧,光绪皇帝同意张之洞入参军机的原因则有点复杂。
首先,他知道张之洞是慈禧的人。即使他不同意,慈禧也会同意。只要慈禧同意,他就是不同意,也得同意。因此,不同意还不如同意。何况事实上,他很同意。
其次,他敬重张之洞,早有倚重之意。后来见张之洞一直扶持资助维新派,他就觉得张之洞是“言新者领袖”。他还觉得,张之洞要是振臂一呼,就足以呼风唤雨。
如果调张之洞入参军机,主持维新变法的话,那他肯定能担当统领大任,压倒各方,从而有力地推动维新事业。因此,在光绪皇帝看来,张之洞是主持新政的不二人选。
第三,调张之洞入军机,可以借助他和慈禧的深厚关系,调和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融洽两党之间的关系。只要两党关系融洽了,帝、后也就一条心了,那么新政也就能顺利推行了。光绪皇帝很明智,这年四月,他非常痛快地下了一道诏令,令张之洞进京“辅翊朝政”!
张之洞接到朝廷的晋升令后,欣喜万分,感慨万端:我都61岁啦,终于当上军机大臣啦,太不容易啦!虽然我一向自命清高,只推崇干大事,没把虚头巴脑的军机大臣放在眼里,可这毕竟是位极人臣的职位啊,谁不向往?谁不惦记?
俗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臣子:不想当军机大臣的臣子不是好臣子。原来,我只推崇干大事,办洋务,搞实绩。可现在我不办洋务了,我要去办国务。国务大于洋务,我张之洞应当大材大用才是。再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这就往高处走了。
就这样,张之洞立即收拾行装,把湖广总督一职交给谭继洵署理,而他则踏上了赴京任职的征程,他兴致勃勃,信心满满。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刚刚抵达上海,就接到了朝廷的又一道诏令:湖北沙市发生教案,你回湖北处理去吧,不必来京了!
张之洞当即傻眼了:朝廷这不是拿我张某人开涮吗?难道这是愚人节的玩笑?让我上来就上来,让我下去就下去,以为我是电梯啊?太不拿我当回事了,这叫啥事啊?
那一刻,他的心拔凉到了极点。从来没有人如此伤透他的心,这太让他跌份儿了。
那一刻,他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愚弄,哭笑不得,而又非常无语。但朝廷的诏令又不得不执行,于是他只好返回湖北,处理沙市那桩见怪不怪而又非常蛋疼的教案。
翁同龢使坏
回湖北的路上,张之洞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光绪皇帝突然变卦令我打道回府,绝非偶然,也绝非是他的主意,这肯定是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擅长公报私仇的翁同龢从中作祟。
除了他,没有别人。张之洞猜得没错,就是翁同龢坏了他的好事。
原来,光绪皇帝的诏令下达后,翁同龢心里一直不安,他担心人气正旺的张之洞入参军机后,会抢占他的风头和位置,于是再三怂恿光绪皇帝,把张之洞支回去。起初,光绪皇帝的立场还很坚定,可他大小事都听翁同龢的,架不住翁同龢的一再磨蹭,他也就违心地借沙市教案,真把张之洞支了回去。
张之洞第一次入参军机就这样流产了。他郁闷极了,但很快他又庆幸极了。
慈禧的行动
张之洞惨遭翁同龢算计,心里自然很难过,但慈禧很快给了他一个巨大的安慰。就在光绪皇帝诏定国是的第四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就以“揽权狂悖”为由,迫令翁同龢开缺回籍!
慈禧此举颇耐人寻味。她是给失意的张之洞一个安慰,替他打击报复翁同龢吗?
是,也不完全是。慈禧一直讨厌翁同龢,早就有让翁同龢收拾铺盖卷走人的想法,一直没动他,主要是考虑他位高权重,且主管内政,动他不易。虽然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有他在,至少可以制衡各方,比如可以用他来制衡李鸿章,还有其他朝臣和疆臣,当然也包括张之洞。
慈禧现在动翁同龢,主要是他成了帝党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加上他向来能左右光绪皇帝的思想和决定,因此必须得动他。动了他,顺便也给了张之洞一个安慰,好让他更加记住她的好。
慈禧此举,真可谓是一箭三雕:把翁同龢“雕”走了,把帝党的势力“雕”下去了,把张之洞的心“雕”来了。
不难想象,张之洞得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消息后,肯定会拍手称快:“苍天啊,大地啊,慈禧姐姐给我出了一口恶气啦!这太给力了,也太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