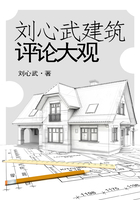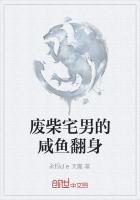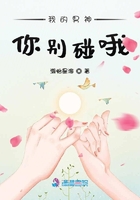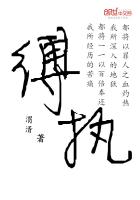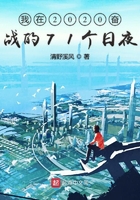创作散文
自报家门
不才李文俊,有名无字,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八日出生于上海。(我母亲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三女出生于一九三〇年[庚午]属马旧历十月十九夜十一时三刻。”)父亲名为李廷芳,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月与日为旧历,下同)生,一九九四年去世。母亲梁冠英,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五日生,一九八七年去世。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大哥比我大三岁。二姐大我一岁,很可惜已于十四年前殁于美国。妹妹小我五岁。六弟小我七岁。八弟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生。小时听母亲说还有一个四弟,最最聪明乖巧,可惜很小就夭折了。另外还有一个七弟,也未能在世界上存在多久。
父亲原籍广东香山(现为中山)石岐茅湾村,不过我少年时曾见到家中保留的一本家谱,上面说我的始祖(名字似为李东源)是从安徽迁到广东去的,因为辈数不是很多,我想应是“长毛之乱”时的事情吧。父亲幼时即随父母从香山老家到苏州居住。祖父曾在苏州火车站西餐厅工作。我小时候还见过他的工作服,并且试穿过,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它有点像童子军制服。当时我因为家中拿不出钱给我做一套制服,未能参加学校组织的远足活动,不大高兴。父亲和祖父母在苏州时住在一条靠小河的街巷上,房东叫“老杨(羊?)妈妈”。在苏州话里后二字是读作“miemie”的,想来就是形容羊叫的“咩咩”声的那两个字了。我小时(大约三岁吧)曾随父母兄姐去看过“旧居”,对那位殷勤热情、语音悦耳、见了小孩喜欢不已的老太太还依稀有点印象。我祖父嗜酒,似乎常常被酒友们架回家中。这样便自然逝世较早。我父亲一生不抽烟不沾酒,想来是与他年幼时的所见所闻与所受到的刺激不无关系的吧。我父亲由我祖母(我们用粤语叫她“阿婆”)一手拉扯大。祖母自然吃了不少苦。父亲在贫穷状态下读完了苏州的粹英中学。后来通过一个在怡和洋行工作的长辈亲戚李殿邦的关系,来到上海,进入那里的茶叶部,从学徒一直做到部门经理。当然,他上面还有真正掌权的英国“茶师”。据我了解,他那个部门所做的业务,就是从祁门一带把红茶收来,装入木箱,销到英国去。我父亲一到茶叶店或是百货公司的茶叶部,总喜欢将缸子、箱子里的红茶捞起一把,凑到鼻子前狠狠地吸气嗅闻,沾得满鼻子都是茶叶。店员见他西装笔挺,倒也不敢拦阻。怡和洋行茶叶部所做的应该都是正正经经的合法外贸生意,与其前身“东印度公司”的贩卖鸦片并不是一回事。
我记得在他工作满四十年时,茶叶部“老番”茶师Mr.Norton(还是Naughton?)还送给了他一支黑色的派克钢笔(是钢笔头包在里面露出一个小金色尖头的那种,当时很流行,型号好像叫“派克51”)。爸爸把笔转送给我用,却让我在上复旦大学时不小心弄丢了。
苏州外婆家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由洋行领导从上海调去香港分行工作的。起先,他定期汇钱回家,还托人捎回来一些衣物。我记得其中有一件是枣红色的夹克衫,上面镶有皮子,那款式很“港”,上海是没有的。大哥穿了,在弄堂里出足风头。当时大哥手里零用钱颇多,小伙伴都敲他竹杠。他也很大方,完全不像后来那么擅于计算。我也领到过一件“皮”夹克,但穿了没多久,便裂了很多口子。而且越到冬天越不暖和。显然,那是塑料一类材质(广东人把这类人造品叫“化学”东西)做的。可见,我爸爸收入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当时有些女邻居总要在我母亲跟前嘁嘁喳喳,让她当心父亲在香港另外找女人。我母亲总是坚决表示,她相信也深知父亲是决不会这样做的。
前面写到,我幼年时,爸爸妈妈曾把小孩们带到苏州去。全家出行,除了访问父亲旧居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妈妈的娘家当时仍然在那里,那宅院似乎就是在观前街一带。我印象中最最深的就是院子里的那口水井。因为外婆家的用人早已把西瓜扔在井水里浸泡,等我们这些客人来后便捞起来切开给我们吃。西瓜又甜又凉,好吃极了。这口井能映出人影,水一动人影也变化莫测。大概我的艺术细胞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得以分裂与繁殖滋生的。那次应该算是母亲的“归宁”了,不过我不记得见到过外公,他大概已经去世了。
外公曾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苏州的第一家照相馆“兴昌照相馆”便是他开设的。另外,他还开了“兴昌大药房”。这些店在武汉、郑州等处都开有分店,后来因为用人不当,店产一点点被账房先生蚀空,家道逐渐中落。我母亲认为,中落的主要原因是儿子太小,帮不上忙。我大外婆没有生育,外公很晚娶了妾,即我的小外婆,这才有了一女二子。但大娘舅很年轻就去世了。听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据说,“紫雪糕”这一名称,还是他应“美丽牌”冷饮公司之征,想出来中了奖而被采用的,直到不久之前,出“光明牌”的公司似乎还在用这三个字。
至于我与大舅父的关系,好像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一岁左右时,大舅父把我抱到住房晒台上去晒太阳。他从兜里摸出一枚银圆来给我玩,殊不知我一扬手竟把银圆扔到外面马路上去了。急得大舅父赶紧跑下楼冲出门去捡,好在当时并没有路人经过。大舅父年纪轻轻便染上肺结核去世了,有一遗孀住在广东南海乡下,很久不通消息,现在怕也不在人世了吧。多年后我曾重访旧居,见到那儿的阳台就在二层,离地面确实是很近的。
外公看来是个干练的人。听母亲说,有一回他出外办事遇见持刀的暴徒要抢他手中的包。外公一边拼命奔跑,一边用英语大声呼叫:“Police!Police!”(“警察!警察!”)(母亲学给我听时用的就是这个英语词。)好不容易总算逃脱,但大褂上还是被划了一个大口子。
由于外公开过照相馆,我家旧照片不少。大多数照的都是少女时代的我的母亲。在见到的照片里,母亲梳着民国初年的发式,似是在脑后盘一个髻,穿了旧时时髦女学生穿的长裙短褂,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pose)。背景则是画出来的风景。照片所附的硬纸片亦相当精美,大都在“文革”时精简掉了。我母亲那会儿也算得上是个美貌女子呢。
鸿德堂乞讨
儿时的印象还有:和姐姐、哥哥一起在虹口公园(今之鲁迅公园)玩耍。当时我们住在北四川路(现称四川北路)横浜桥,离公园很近。不过,这印象也许是得自家中所藏发黄的老照片。另一件有点印象的事情是:我三到五岁时曾独自一人,去到附近的一所礼拜堂,向站在教堂门口散发宗教宣传品的阿姨索要一张。阿姨说:“侬小人看勿懂。”我用生硬的广东腔上海话(因家中通常只讲广东话)反驳说:“拿番去被我姆妈睇。”意思是:拿回去给我妈妈看。传教的阿姨只好给了我一张。这件事后来我母亲反复讲,用以说明我是个聪明的孩子,还说我还会临时改用上海话(当然很不地道)讲,说明我有“应变能力”,真是不简单。不久前我重游虹口,在多伦路上见到一座鸿德堂,那儿门口的形状与我印象中儿时所见差不多。我虽然没有调查,但我猜想横浜桥一带不可能再有另一座教堂的。因此这里必定就是我七十多年前乞讨宗教纸片的地方了。
另外我小时候皮肤比较白。母亲说,我还很小时,有一天躺在床上,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个小姐姐,看到我,喊出声来说:“系(是)靓仔喔!”但我长大后相貌平平,要让那位小姐姐见到,怕是会失望了。这事我也不是直接记得,是听母亲讲的。我母亲是个感情丰富,有些艺术细胞的女子。她说起话来总是有声有色,还带点表演的手势与动作。她字写得很秀丽但软中有硬(像是《星录书词》的那种字体),我记得她曾在我练毛笔字时站在我身后把着我的手教我写。可惜到现在我的字还没有她的好。母亲的文笔亦算得上生动老练,还爱夹用些文言词语。她还保留着念初中时的几篇作文,我只记得其中一篇的主旨是鼓吹“好男要当兵”。足见她曾受到富国强兵思潮的影响。“文革”时她写给我的一封信里哀叹时局,还用了“夫复何言”这样的话,让我伤感了好半天。对于遣词用字,她也比较挑剔。记得有一回见到某小学的公告里有“学生中有奇峰突出者,当……”这样的文字,便觉得好笑,认为是装腔作势。她写信一定要用上好的带蓝线的正规道林纸信笺(她习惯于把纸横过来竖写),还一定要用那种插上鸡心形钢笔尖的蘸水钢笔。她不打稿,也从不涂改,但下笔前总要沉思片刻。这就是在打腹稿了。她还喜欢作画。她年轻时初中毕业后曾考取苏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是颜文梁。她告诉我们,她去上学的第一天,一看,全班只有她一个女生,第二天就不敢去了。我小时,家中大衣柜顶上,还放有一卷她年轻时作的水彩风景画静物画,有时兴致来了,她便会取下展开给几个儿女看,一边怀念已逝的青春岁月。有一次她还教过我唱京戏,唱的是《四郎探母》里“一马离了西凉界”那一段。下面还有“青的山,绿的水,花花世界”等唱词。当然,她也就是轻声哼哼,没有用老生腔大声吼叫,而且是在亭子间里关上了门,很神秘的样子。我现在想,那一定是当时她心情很郁闷了,必定也是觉得“我好比笼中鸟、南飞雁与浅水龙”了。这大约是在日军占领香港,我父亲音信全无家里生计难以维持的日子里的事情。那个阶段里,每当我向她要一些零用钱时,她总是说:“石子里榨不出油呀。”我还自作聪明地顶嘴说:“不是有石油吗?”不过我母亲的经济头脑是不行的。她不大会也不大愿意计算,整天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难怪小菜场里的菜贩给她起了个外号:“快活大小姐。”我从来没听到过她骂人。真的遇见一个她很鄙视的人了,她才从嘴角发出一声:“法利赛人!”
我记得母亲较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严格地说仅仅是轻声哼唱。只有我父亲的结拜兄弟来我家时,她才会与他们一起一本正经地合唱英语歌曲,想必都是在教会中学里学会的。我只记得他们唱的歌里有一首叫A Spanish Cavalier(《一位西班牙骑士》)。她最爱唱的歌里的一首是《秋水伊人》。最近,我在报上见到贺绿汀所作的这首歌的歌词全文,现在抄录如下,因为我感觉它与我母亲当时的气质、心境有些相关: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梦魂无所寄,空有泪满襟。几时归来呀,伊人哟!几时你会穿过那边的丛林?那亭亭的塔影,点点的鸦阵,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你的女儿哟!已长得活泼天真: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另外,有一首叫《初恋》的歌,依稀记得我母亲也哼唱过。歌词是:
我走遍了漫漫的天涯路,我望断遥远的云和树,多少的往事堪重述,你呀,你在何处?我难忘你的哀怨的眼睛,我知道你沉默的情意,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个梦中忘记你。啊,我的梦魂遗忘的人!啊,受我最初祝福的人!终日我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
当然,记住全部的歌词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福克纳在小说《喧哗与骚动》里让班吉这个弱智儿童说得出父亲讲过的拉丁语“Et ego in Arcadia”[1],译到这里我总觉得别扭。这里引录的歌词,我也是从有关资料里查找出来的。不过,母亲当时哼唱的那种气氛,我却是深深感受到并且记忆犹新的。现如今,有一班小女子成天瞎吵吵“小资”什么的。其实,最老最纯的小资恐怕还是我母亲那一代人吧。
母亲的艺术气质传给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如大哥的过于自信与想法特多,大姐的热情有余却有些马马虎虎和不负责任,还有我的对外国文艺的爱好与妹妹的喜欢观察与分析周围的人与事。是母亲一开始便坚持让姐姐学钢琴,这才使我们家有好几个人以及下一代好几个人都走上弄音乐与文艺的这一条路。
“八岁离开广东”
前面讲了不少母亲方面的事,现在再来说说我印象中的父亲。我想先在这里引用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我家世的情况。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你在九月二十五日曾来信问我,想到茅湾去看看老家,问我有什么熟人。我收到信后,真是没有办法讲出来!
我从八岁离开茅湾后,已有八九十年了,老的已经过世了,年轻的都不认识!我的房子一共有两间,一间给张润婆住了,还有一间给他(她)儿子、媳妇等住了!而且房子都很小的,房子后面有菜园及禾场、果园等,到现在已经大大变动了,或者归公了!
我的母亲是乌石乡人士(氏)。她一家有很多人,有四姊妹、两兄弟:大舅父叫郑惠贞早年出国美洲,在那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后来叫他的儿子阿山继续他的位置,惠贞独自回乡下;在抗日期间,我在香港渣甸洋行任职,惠贞舅父曾与我通过信,来叫我帮助他孙子交学费。关于二舅父惠回,早年已过世,他的孙子阿佩在一九五〇(疑为一九三〇)年左右来上海曾在怡和洋行栈房做过工作,后来日本侵略期间不幸去世。
听说阿佩的母亲也住在茅湾村,对于我的房子等情况,她都知道的。
其实茅湾村离开澳门是十分近,一望就可以看到澳门。
我父亲木讷寡言,言语表达能力较差。他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嗓门特大,这是因为他耳朵有点重听的关系。他身材高大挺拔,走起路来步子跨得又大又快。母亲和他一起出去,过上一阵总要叫一声:“廷芳,等一会儿呀。慢点儿呀。”父亲皮肤黝黑,很有点运动员的风度。他也的确爱好运动。我记得住虹口时每到星期天早上,他总去参加长跑。家中还保留有他和朋友浸在水里仅仅露出脑袋的照片,那说明他是会游泳至少是喜欢游泳的。他也喜欢旅游,我见到过他在南京明孝陵拍摄的照片。他星期天常带我们上公园去玩。我们兄妹们当时是很以他为骄傲的,认为他比别的孩子的父亲新派,而且在洋行上班,那么英文必定是水平很高的了。我手中原来还保留有一封他写给我的英文信,是他去世前不久写的。他大概是希望他的三儿能和他用英语通通信,让他过上用英语写作的瘾的。可惜我当时偷懒,没有想到应该顺从他的意愿。没过多久,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日,父亲去世了。虽说他活到九十四岁也算是长寿了,但我总排遣不去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奈之感。至于我的母亲,则走得更早一些。她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去世后,我们在她记“豆腐账”的一个练习本上发现她写下的这些话:
“无病而终,倒也十分痛快,聊尽人事,以俟天年,对生死等闲视之。”其实她是有病的。不过她的洒脱态度在老年人中还是不多见的。
我家住横浜桥时,有天早上父亲去上班。好像是他在北四川路上等有轨电车时,一辆汽车开歪了,撞上路边的黄包车,黄包车又撞上了在等车的父亲,使他跌倒并且昏迷,住了一段时间医院总算康复。对于目击的熟人跑来通知母亲,母亲急匆匆冲出家门的情景,我好像还有点印象。我幼年时的印象除了这件事之外,还有到外白渡桥去看夜景的事,那天因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上海英租界热闹非凡,黄浦江边与桥上张灯结彩,使我眼花缭乱。我查了一下大百科,那天应是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
家中曾经有一幅照相馆拍摄的照片,是布纹相纸贴在美术硬纸板上比较讲究的那种。上面是五个头发往后梳涂了不少凡士林皮肤黝黑的广东青年。他们是结拜兄弟,大哥是我父亲,老二姓唐,老三姓陈,老四姓梁,老五姓汤。这位汤先生后来与一富家小姐结了婚,与兄长们不大来往,所以我对他的情况也不甚了了。他长年住在静安寺路平安大戏院西边一个当时挺洋派的叫作“沧州饭店”的旅馆里,所付房租必定不赀。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我至今仍然不解。家中人走过“沧州饭店”时,总要朝那边指指点点。这家饭店我后来居然也去住过一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单位几个人出差去沪,没有地方住。还是同行的一位女同志靠了她老首长陈沂的关系,我们几个人才能住进去。结果发现那儿已是部队的一个招待所(似叫江陆饭店了),乱得很,好多人住一个大房间,显然成了复员军人的中转站。门口管进出登记的小房间窗前坐着一位女工作人员(也穿军服),长得挺漂亮,竟成天有几个军人在窗口外跟她纠缠不休,他们涎皮赖脸,一点不像我心中已经定型的解放军战士。我在大房间里与一批复员回家的老兵油子住在一起,那里一整夜直到天亮灯都亮着不关,半导体收音机亦兀自响着,我这个容易失眠的人哪里还睡得着。第二天一早,我就躲开这个没有三八作风的军事招待所,跑到姐姐家里,和外甥一起睡到他们家的顶楼上去了。
父亲的二弟唐先生相貌堂堂,留两撇小胡子,说话声音深沉洪亮。我后来看了大仲马的《三剑客》,总把他跟小说里那位胖胖的颇多士连在一起。我家逃难搬至法租界时,唐叔帮我们买来一架Watson牌电风扇,风扇翼子是黄铜的,光闪闪的十分神气。唐叔叔帮我们在一根木柱上安了个座架,把风扇固定在上面,插上扑落(英语plug的音译),打开开关,风扇不但送来凉风,而且金光四射,十分壮观。唐叔叔战前是英租界“万国商团”的一名“义勇军”。那是保安队一类的组织。可能是他有点亲英美吧,他的看法与流行的都不大一样。我记得他在讲到沈崇案件时用了一个英文词:“induced”(诱使)。说到《资本论》时用的是德文词“Das Kapital”。显然想表示他对“这一套”是门儿清,心里有数,别人休想拿什么大道理来蒙骗他。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被临时派到北京来做外贸翻译。他住在当时新建的“和平宾馆”。他很看不起这幢新盖的建筑物,说是厕所里居然还要让人将大便纸放入边上的字纸篓,简直是“太土”了。他说他不理这一套,仍然将用过的手纸丢在马桶里。
陈叔四十年代时在一家私营银行当襄理,大哥到钱庄去当练习生好像还是他介绍的。他先后把周家都很漂亮的两姐妹都娶到家里,一大一小。当时,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已经不作兴这样做了。父母都觉得他这样做未免太过分,有点放纵,而且也不够新派。陈叔、梁叔后来都去了香港,五十年代初陈叔还代表银行到北京来开过会,我与佩芬去看他,在前门外一家老字号饭庄,好像就是“鸿宾楼”,请他吃了一顿饭。他说我现在算是“翻译官”了吧,我听了暗暗觉得好笑。梁叔送给爸爸一件“Arrow”(箭)牌白衬衫,爸爸转送给了我。很肥大,像是电影里击剑手们穿的。我在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开始搞业务时见到过一本香港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译本,让爸爸去信请陈叔寄一本给我。过了一段日子我收到海关一张通知,说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不宜进口,已退回”。这使得我怅怅然大失所望。
再记弄堂
还是从我小时所住的弄堂讲起。说起来,它与文化界还有点儿关系呢。曾看到有人回忆,三十年代时,茅盾、黄源等人组织的一个什么团体,就设置在这里。四十年代,白穆、孙景璐、王丹凤等演艺界人士都曾在这里住过。与拉都路相交的辣斐德路路口,有一家饺子馆,北方来的演员,以石挥为首,常聚在这里喝酒聊天,喝多了酒酣耳热,声音自然一点点大起来。那些道地的北方话便与酒气、大蒜味混合着从店门口飘出来,听起来就是与白云之流的“奶油小生”(当时这一名称尚未出现,我们会用“娘娘腔”这类说法)说出来的不一样,让人听了精神为之一振。他们大多住在这一带弄堂的某个亭子间里。王丹凤(她倒不是北方人)住在靠襄阳路的一个二层楼里。隔壁的孩子胆子比较大,曾带我从后门进去爬上扶梯去请她签名。严格地说是为他签名,我不喜欢也不敢这么做。
里弄住的都是和我家差不多的市民。我家在其中还算是景况好一些的。这里住的大都是江浙人,以宁波人居多,他们天生有一副大嗓门,因此弄堂里一早就响起了不很悦耳的宁波话。听起来就像好事者为取笑他们而编造出的那段笑话:什么“啥棉纱线杜来啦,蓝棉纱线杜来啦”,等等,那首谐音歌的最后的结束语是“勿杜”(意思是“不去取”)。
弄堂里也住着几家从虹口搬来的广东人家。一家住在靠马路过街楼房子的三层。我的外甥小时候曾托养在那里,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孩子瘦得好像一只小猫,显然是缺乏营养。附近住着的一家姓简,是弄音乐的,父亲好像是钢琴调音师。一个女儿在上海交响乐团拉小提琴,我哥哥和她有些来往。她眼睛大大的,面孔轮廓线条比较硬,就是一副广东姑娘的英爽模样。那样的脸是不会出现在“那妮”无锡女子的身上的。
弄堂里的外国人
弄堂里还住了几家外国人。弄堂口大约也是沿马路的房子里,就住了一家“罗宋人”。他家小孩不少。大一些的女孩即是与吴家姐姐吵架的那位了。有一个男孩年纪和我差不多,但个子要比我大得多,名叫“谢里克”,后来我读了俄语,才知道原来就是俄苏小说里常见到的“谢尔盖”了。中国小孩和他打架,三四个一起扑上去他也不怕,我趴在他背上,他一甩,就把我甩下来了。多年后,我翻译到福克纳的《熊》里人、狗、熊激烈格斗那一段时,就不由得想到当年与小罗宋打架时的情景。不过我们当时打架也不是真打,双方都不使出狠劲,不下狠招,不会往对方柔弱的部位,如胯下、脸面特别是眼睛下手。我们不过是在玩一种比较凶狠的游戏而已。双方不能用言语沟通,但心里倒是很有默契的。我还曾从罗宋小孩那里初次见到外国的“小人书”,那种竖开本的comics(连环画),才知道原来外国也是有小人书的。
弄堂里居住的另一种外国人是吉卜赛人。在我们南面两条支弄一幢房子的灶偏间(厨房间)里,就住有一家吉卜赛人,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挤住一起,也不知他们是怎样烧饭和上厕所的。有一次,大家都说,吉卜赛人结婚了,快去看呀。我跟别人去到那里的门口,只见里面一屋子的吉卜赛人,都在唱歌跳舞。女人家穿着纱衣裙,一转身便飘飘然的,皮肤虽然黑一些,但还是挺漂亮的。吉卜赛人眼睛特别亮,熠熠有神,头发则微带波浪形,身材也都苗条矫健,可以算是比较好看的。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水兵来到上海的不算少。我常见到他们搂着吉卜赛女人的腰,走在林森路(霞飞路一度叫这个名字)上,而吉卜赛少年则成了给他们的姐姐嫂嫂拉皮条的,躲在街角落里跟水兵套近乎,问:“嗨伙计,想要漂亮妞吗?”但是还不等解放大军开进上海,这些流浪者又不知悄悄地漂流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里去了。
“Very good皮鞋带”
在辣斐德路、亚尔培路一带,住的外国人就更多了。不过还是以俄罗斯人和南欧(西班牙、葡萄牙)人居多。只要看到屋子有百叶窗和白纱帘,就知道里面住的是外国人了。我到一位姓江的同学家里去,他父亲是个从哈尔滨来的医生,出资在辣斐德路拉都路口路北底层街面开了家“马迭尔皮鞋店”(马迭尔是英语“Modern”的音译)。他家住三楼,朝马路对面看去,那里的三楼里就住着一家俄罗斯人。因为天热,女人上身只穿一副奶罩,我当时见了不免有些吃惊。在这附近的一家二三轮的“上海电影院”看电影的外国人也多半是俄罗斯人。当时他们都很爱穿美军剩余物资里的那种深绿色的卡其布工作服。
有一次我看到辣斐德路海关大院靠马路的几棵玉兰花一朵朵大白花开得很好,便爬到高处去采,我小时候爬树的本事可不小。此时,下面有一位洋太太经过,仰起头来看我摘花,并且做出想要的样子。我便摘了几朵下树送给她。这算是我生平第一次当了一回骑士吧。不过,会跟我要花的大概也是俄罗斯人。真正有钱的英美大班都住在虹桥路那边。富有的法国人则住贝当路(今称衡山路)一带的高档公寓里。我们家附近住的都是二等白人,要不就是犹太人,他们是逃避德国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中国的。他们虽然穿的也是西服革履,但总透出一股寒酸气。我有一次走到雷米路小菜场附近,遇见一位瘦瘦小小的外国人,手里拿着一只当时小学生用的长方形皮书包。小个子外国人见到我,把书包举起打开,只见里面放的是一束束的皮鞋带,他让我买他的货,说:“Very good皮鞋带。”那个“鞋”字是用上海话发音的,作“a”声,因此,“biata——”连在一起念非常顺溜,活像是一句英语。一副皮鞋带能值多少钱呢?足见他买卖的规模也够小的了。
拉都路北端近霞飞路处路西,抗战胜利后也盖起了一座犹太教堂(synagogue),大门上方饰有一只六角星。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大卫之星”了。
海格路与St.John's大学
前面所说的是我念中学时爱去的一处地方,另一处则是霞飞路海格路(华山路)一带了。那里有一些木框架结构外露的英式建筑,那些尖尖的红瓦屋顶、山墙以及顶楼上的牛眼窗,都让我十分着迷。路拐弯处慢慢驶来发出叮叮铃声,显得十分从容自在的有轨电车,使我觉得这儿的世界远离战争与苦难,连太阳光在这里也似乎格外温煦、灿烂呢。
我去海格路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领略异国情调。海格路上开有好些家专卖西书的旧书店,我可以不花钱站在店堂里看上小半天。有时也会买上一两本。那里的服务很是周到。倘若选中什么书又嫌太重自己不好拿,或是钱没带够,尽可以把地址留下让店里送货到家然后交书费。我有一次就以这样的方式买了一本大词典。我回到家不久书店的小学徒就骑车把“货”运到了。后来我去北京工作,我父亲还托我姐夫坐飞机把词典带来,至今还在我家里柜顶上垫古玩呢。
海格路往北,就是静安寺与愚园路一带了,再往西北,是兆丰公园与圣约翰大学。我曾随年纪稍大一些的小朋友“潜入”St.John's校园去玩。我只记得那里有一棵很大的大树,枝杈分得很开,布下很宽阔的一片浓阴。我们几个孩子走累了,便在树干周围躺下,看着绿茵茵的大片草地和远处的红瓦屋顶,那里好像还有钟楼。当时心想,倘若能来这里上大学,那真是最好不过了。我家隔壁家的几个哥哥都在圣约翰大学念书。他们进学校过不多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举一动都斯斯文文的,说话不但不带脏词儿,虽然仍然是说上海话,但是连土一些的“侬”和“阿拉”也都不用了。我问过一位哥哥,他若是要对大学老师提问该怎么称呼。他说,先要叫一声“sir”。这使我觉得大学跟中学就是不一样。这位哥哥还说,他参加了约大的一个“团契”,经常练习和表演合唱,唱的自然都是宗教歌曲。听他一说,这些赞美诗真的是世上最纯最美的音乐了,而他们合唱队的水平又是高级高级了。他用来形容的一个最高级的说法,我记得,就是“har(harmonic,和谐)得不得了”。我中学时去杭州旅游,参观过之江大学,那里在江边山坡上的一幢幢西式建筑也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高中毕业我考大学时,报考了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结果复旦正式录取。于是我便上了复旦,始终未能在教会大学里受陶冶,直到近四十年后因学术交流来到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天主教会的学院,我记得那是以一位圣徒名字命名的St.Michael学院。在教师餐厅吃早饭时,一位神父教授还问我你们的于斌主教(台湾教区)近况如何,让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