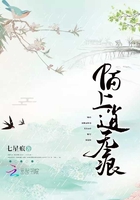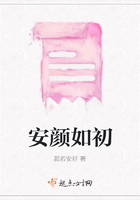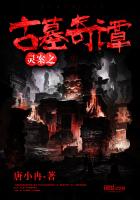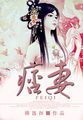【1】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注释】
[1]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官至刑部主事,王阳明的学生。
【译文】
我问:“主一的工夫,如果读书就专心在读书上,接待客人就专心在接待客人上,这样可以看做是主一吗?”先生说:“好色就专心在好色上,喜好财货就专心在喜好财货上,这样可以看做是主一吗?这是所谓追逐外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心于天理。”
【2】问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1],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注释】
[1]美大圣神:语出《孟子·尽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意为那些好处充满他本身叫做“美”,充实并且光闪耀人地呈现称之为“大”,既能够光闪耀人地呈现,又能够融会贯通,便叫做“圣”,圣德扩充却不能测度的境界便叫做“神”。
【译文】
请问立志方面的问题。先生说:“只要一心想着存天理,就是立志。能够不忘记存养天理,时间长了自然心中凝聚,就像道家所讲的心中形成了圣胎。时常保存着天理的想法,逐渐达到孟子所说的‘美大圣神’,也就是从这一想法去涵养扩充。”
【3】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译文】
平常日里工夫,感觉纷扰烦乱就去静坐,感觉懒得看书,就专门去看看书,这就是对症下药。
【4】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译文】
朋友之间相处,务必要互相谦让,才能受益,互相争上,就会带来损害。
【5】孟源[1]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源从傍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先生曰:“尔病又发。”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注释】
[1]孟源,字伯生,滁州(今安徽滁县)人,王阳明的学生。
【译文】
孟源有自以为是且喜好名声的缺点,先生常常责备他。一天,刚刚警告他不久,一个朋友陈述自己近日来的工夫,请先生指正。孟源从旁边插话说:“这正是找到了我以前的病根。”先生说:“你的病又犯了。”孟源听后脸色立变,想要进一步辩解。先生说:“你病又犯了。”并跟他讲:“这是你一生的最大病根。比如方丈土地内,种一棵大树,雨露的滋养,土壤的肥沃,却只养好了一个大根。四周即便要种一些五谷,但上面被树叶遮盖,下面又被这个树根缠绕住,怎么能长得好呢?必须要砍掉这棵树,一点根须都不要留下,才能种好五谷。不然的话,任凭你耕种培育,也只是把这个根养好了而已。”
【6】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译文】
问:“后世著述很多,恐怕会扰乱正统学问?”先生说:“人心与天理本来是浑然一体,圣贤的著述,就像描写肖像表达人的神情相貌,不过把一个大概的形状展示给后人看,使别人凭借着画像去寻求真人面貌。而真人的精神气质,谈笑举止,本来就不可能完全通过肖像画来传达。后世著述,则是把圣人所画的东西,模仿誊写,然后随意地加以分析,添枝加叶,以表现自己的技能,因而也就越来越失真。”
【7】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1]者,其言何如?”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注释】
[1]语出朱熹、吕大临合编的《近思录·道体》,意为宇宙混沌虚寂无形,没有任何踪迹可循,而万事万物已经兴盛繁茂地生长起来。
【译文】
问:“圣人对于各种问题都能应变不穷,是不是预先都做过一番探究呢?”先生说:“怎么能探究那么多?圣人的心就像一块明镜,就是完全的明澈,随所感知到的事物而应对,一切事物都在它的普照之下;不存在照过的事物之形态还在镜子中,而没有照过的事物之形态预先出现于镜子中的情形。而后世学者们所讲的,恰好是这样,这就与圣人之学相违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此化成天下,都是圣人所能做到的,尧舜为什么不做完这些事,而要等到周公呢?孔子删订《六经》以教导后人,这也是圣人所能做到的,周公为什么不先做完这个事,而要等到孔子去做?由此可知,圣人处在那样的时代,才有那样的事业。只怕镜子不明澈,不怕事物来了照不到。探究事物变化,也是属于照镜子时的事情。然而学者必须先有一个追求心灵明澈的工夫。学者只要担心内心不澄明,不必担心事物的变化不能穷尽。”问:“那么所谓的‘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种说法本来不错,但是如果不正确理解,也就有问题。”
【8】“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1]’?”
【注释】
[1]语出《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意为周文王看待百姓好像他们受了伤害一样,追求大道却又似乎未曾看见。
【译文】
“义理没有限定在某一处,也没有穷尽。我跟你谈论,不能因为略有所得,便认为义理只有所讲的这些。再探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不能穷尽。”改天,先生又说:“像尧、舜这样的圣人,然而尧、舜以上,善没有尽头;像桀、纣这样的恶人,但桀、纣以下,恶也没有尽头。假使桀、纣没有死,难道恶就到此为止了吗?假使善有尽头,文王为什么会发出‘望道而未之见’的感叹?”
【9】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1]。”
【注释】
[1]语出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二:“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意为所谓本性的安定,是指遇事行动时能定得住,安静时也能定得住,没有送往迎来,没有内外之分。
【译文】
问:“静下心来时,觉得自己的想法挺好,可是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怎么办?”先生说:“你这是仅仅知道静中涵养,而没有用克己的工夫。如果这样,遇到事情就会把持不住。人必须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站得稳,才能做到‘静亦定,动亦定’。”
【10】问上达[1]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注释】
[1]语出《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意为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备人,学习人事活动中的各种知识,以求向上通达天命。知道我的,只有上天罢!”
【译文】
有人问上达工夫。先生说:“后世儒者教人,刚刚涉及精微之处,就说上达不能学,还是说下学。这是把上达和下学分为两截了。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口可以说话,心可以思考,这些都是下学。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口也说不出,心也不能思考到,这就是上达。就像对树木进行栽培灌溉,这是下学,至于日夜生息,枝叶畅达茂密,这是上达。人怎么能参与到树木的生长力之中?所以凡是可以用功、可以说出来告诫别人的,都是下学,上达只是在下学工夫中。凡是圣人所说的,虽然很精微,都是下学工夫。学者只要在下学里用功,自然就能上达,不必另外去探寻一个上达的工夫。”
【11】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1]之功:无二说也。”
【注释】
[1]明善即诚身:语本《中庸》第二十章:“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意为使自己真诚是有方法的,不明白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
【译文】
问:“‘惟精惟一’,是怎么用功的?”先生说:“‘惟一’是‘惟精’的主导,‘惟精’是‘惟一’的工夫,不是说在‘惟精’之外还有一个‘惟一’。‘精’字是‘米’字旁,姑且以米来打个比方:要使米干净洁白,这是‘惟一’的意思,然而不通过舂米、簸撒、筛米、挑拣这些‘惟精’的工夫,就不能实现米的干净洁白。舂米、簸撒、筛米、挑拣是‘惟精’的工夫,然而也只是要实现米的干净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惟精的工夫,而目的在于追求惟一。其他的,如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都是这个道理。”
【12】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译文】
良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良知的完成。圣人之学只有一个工夫,知行不能分为两截。
【13】漆雕开[1]曰:“吾斯之未能信。”[2]夫子说之。子路使子羔[3]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4]。”曾点[5]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
【注释】
[1]漆雕开,名开,字子开,孔子的学生。
[2]语出《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3]子路,即仲由,字季路,孔子的学生。子羔,即高柴,孔子的学生。
[4]语出《论语·先进》。
[5]曾点:曾晳,曾参之父,孔子的学生。曾点言志,见《论语·先进》。
【译文】
漆雕开说:“我对这个还没有信心。”孔子很高兴。子路派子羔去当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别人家的孩子!”曾点谈论自己的志向,孔子赞许他,圣人的志向由此可见。
【14】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1]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注释】
[1]语出《中庸》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下文的“已发”、“未发”、“中”、“和”均源于此。意为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发动的时候,内心平静,没有偏倚,这种状态就叫做“中”,喜怒哀乐的情感发出来都符合礼仪规范,没有过头和不及,这种状态就叫做“和”。
【译文】
问:“宁静存心时,可以认为是‘未发之中’吗?”先生说:“现在人们讲存心,只是定住气。当他们处在宁静时,也只是气息宁静,不能认为是‘未发之中’。”问:“情感没有发出来就是中的状态,莫非是求中的功夫?”先生说:“只要去除人欲,存养天理,就是功夫。宁静时一心念着去人欲,存天理,行动时也一心念着去除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如果一味追求宁静,就不仅会逐渐养成喜欢宁静、厌恶行动的弊病,中间还有很多病痛潜伏着,始终不能彻底摒除,一旦碰到事情就依旧滋生。以遵循天理为主导,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导,则未必能够遵循天理。”
【15】问:“孔门言志:由、求[1]任政事,公西赤[2]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3],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4],曾点便有不器[5]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之。”
【注释】
[1]冉求,字子有,孔子的学生。
[2]公西赤,字子华,孔子的学生。
[3]意必: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为孔子没有四种毛病: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
[4]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琏瑚也。’”
[5]语出《论语·为政》:“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像器皿一样,只有特定的用途。
【译文】
问:“孔子门人谈论志向,子路、冉求任政事,公西赤任职礼乐,这些工作或多或少还实用。等到曾晳说他的志向,却好像是游玩一类的事,圣人却赞许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曰:“子路等三个学生是有意向和执着,有执着就会偏向一边,能够做这个事未必能做那个事;曾点的言谈则没有执着,因而可以‘在自己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当做的事情,不希望做本分之外的事情’、‘处在未开化的夷蛮之地,就做处在未开化的夷蛮之地应当做的事情,处在患难的地位,就做患难的地位应当做的事情。君子守道而行,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自得’。子路等三人所谈的都是孔子所说的‘你好比是一个器皿’。曾点则有不愿意像器皿一样的想法。然而三个学生的才能,各自富有文采,不像世上那些浮夸不着实地的人,所以孔子也赞许他们。”
【16】问:“知识不长进如何?”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1]。仙家说婴儿[2],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3],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注释】
[1]语出《孟子·离娄下》:“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意为有本源的泉水滚滚地往下流,昼夜不息,把低洼之处注满后再往前奔腾,一直流入大海。
[2]婴儿:语出《老子·第十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3]语出《中庸》第一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文】
问:“知识没有长进怎么办?”先生说:“求学必须有一个本原,必须从本原上努力,然后才能逐渐前进。仙家使用的婴儿比喻很好。比如婴儿在母亲肚中时,只是纯精气,哪有什么知识?等到从母体出生后,才能啼哭,继而能够笑,然后能够认识自己的父母兄弟,再接着能够站立行走、持拿背负物品,最终天下之事无所不能。这都是因为他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日益强壮,智力日益开启,不是从母体出来那一天起便能探求推寻得到的,必须有一个本原。圣人达到天地各安其所、万物各遂其性的境界,也就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逐渐培育而来。后世儒者不明白格物的学说,看见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便希望在刚一下手时探究透彻,哪有这种道理?”又说:“立志用功,就好比种树。当它是树芽的时候,还没有树干,等到有树干时,还没有枝条,有枝条然后才有叶子,有叶子才有花和果实。刚开始种树根时,只管去栽培灌溉,不要想着枝条、树叶,也不要想着花和果实。空想有什么用?只要不忘记栽培的工夫,还怕没有枝条树叶、鲜花果实?”
【17】问:“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译文】
问:“看书看不明白怎么办?”先生说:“这是因为只在文辞句意上穿凿探求,所以有不明白之处。这样的话,还不如先前的那些学问家,他们倒还读得多,理解得清楚。只是他们在学问上虽然理解得极为透彻明白,但终身没有真正的心得体会。必须在心体上用功,凡是理解不清楚,实行不顺畅的,必须返回到自己内心上体会,然后才可以通达。《四书》、《五经》,也不过是探讨这个心体,这个心体就是‘道’,心体澄明了,也就明白了‘道’,再没有其他的解释。这才是做学问的关键。”
【18】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1]。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注释】
[1]语本朱熹《大学章句》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王阳明借用朱熹的注,进行了改造。
【译文】
心灵明亮澄澈,万物之理包含在其中,万事由心主导而施行。心外不存在天理,心外没有事物。
【19】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1]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注释】
[1]语出朱熹《大学或问》。
【译文】
有人问:“晦庵先生说:‘人之所以做学问,是因为有心与天理。’这句话怎么样?”先生说:“心就是性,性就是天理。说一个‘与’字,恐怕难免把心与理看做两个事物。这就要求学者正确地去理解。”
【20】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译文】
有人问:“人人都有这个心,心就是天理,为什么有人为善,有人为恶呢?”先生说:“恶人的心,丧失了其本体。”
【21】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1],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注释】
[1]语出朱熹《大学或问》:“析之极精不乱,说条目功夫;然后合之尽大无余,说明明德于天下。”
【译文】
问:“‘天理可以通过分析达到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的程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统括天下事物而没有遗漏’,这句话怎么样?”先生说:“恐怕还没有完全说清楚。这个天理怎么能分析开呢?又何必要凑合起来呢?圣人说精一,就已经讲得很完备了。”
【22】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译文】
省察是有事的时候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23】澄尝问象山[1]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2]。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注释】
[1]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自号存斋,江西抚州人,曾讲学于象山,学者称象山先生。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倡导心学,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齐名,史有“朱陆之辩”。
[2]语本《象山全集》:“复斋家兄一日见问云:‘吾弟今在何处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
【译文】
我曾经就陆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的主张请教先生。先生说:“除了人情事物,就没有任何事情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到富贵贫贱、患难死生,都是事物变化。所有事情变化也都体现在人情中。关键在于达到中和的状态,而达到中和状态就在于‘慎独’。”
【24】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1],是性之表德邪?”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注释】
[1]语本《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译文】
我问:“仁义礼智这几个名称,是因为本性呈现出来之后才具有的吗?”先生说:“是的。”另外一天,我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性所体现出来的品德吗?”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人的本性所呈现出来的品德。本性只有一个,从它的形体而言称之为天,从主宰人的行为而言称之为帝,从它流行扩散而言称之为命,从赋予到人之中而言称之为性,从主导人身而言称之为心。人心发动,奉养父亲就称之为孝,侍奉君主就称之为忠,以此推导,名称没有穷尽,但只是一个人性而已。就好像一个人,对父亲而言称之为子,对子女而言称之为父亲,以此推导,名称没有穷尽,但还是那一个人。人只要在本性上用功,把性字看清楚,那么一切道理都豁然开朗。”
【25】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1],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2]时在。虽曰‘何思何虑’[3],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注释】
[1]槁木死灰:语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2]端拱:端坐拱手。
[3]语出《周易·系辞下》:“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意为天下有什么需要去思考的呢?天下殊途同归,思虑万千却终归于一致。天下有什么需要去思考的呢?
【译文】
一天,讨论为学工夫。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开始学习的时候,心猿意马,思虑不定,所想的大多是人欲方面的,所以应该教他静坐,平息思虑。时间长了,等他的心思稍微安定。但一味静守,就好像槁木死灰一样,也没有用。还得教他反省自身,克制私欲。这种反省克己的工夫,片刻不能间断。就好比清除盗贼,必须有彻底清除的决心。没有事情的时候,将贪慕美色、财货、名声等各种私欲,逐一追究搜刮出来,一定要彻底清除这个病根,使它永不再萌芽,才是要紧的事。就如猫抓老鼠,一眼看见了,一边耳朵听着,才有一丝欲念萌发,就立刻除去,斩钉截铁,绝不让它存留片刻,不能藏匿,也不能放它出去,这才是真正用功,才能彻底扫除干净。到了没有私欲可以清除的时候,自然有端坐拱手的那种状态。虽然有‘何思何虑’之说,但这不是初学者的境界。初学者必须思考反省克己,也就是思考至诚,只思考一个天理。等到了纯粹天理的状态,就是‘何思何虑’了。”
【26】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1],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子莘[2]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注释】
[1]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意为浩然正气是通过长期积聚正义感而形成的,不是行为偶尔符合正义便可获取。
[2]马明衡,字子莘,福建莆田人,官至御史,王阳明的学生。
【译文】
我问:“有人晚上怕鬼,怎么办?”先生说:“这是因为平常不能集义,内心有愧疚,所以害怕。如果平日行为合于神明,有什么害怕的呢?”马明衡说:“正直的鬼不必怕,就是担心邪恶的鬼,不管人是善是恶都来侵害人,所以难免害怕。”先生说:“哪有邪恶的鬼能够侵害正直人的呢?就是这种害怕,表明心有邪念。所以那些迷误的人,不是鬼侵迷了他,而是内心迷蔽了自己。如人喜好美色,就是被色鬼迷上了;贪好财货,就是被财货鬼迷上了。在不当发怒的时候发怒,就是被怒鬼迷上了;害怕不当害怕的东西,就是被惧鬼迷上了。”
【27】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译文】
心之本体恒定不移,这就是天理,动静只是就心所遭遇事情的时机而言。
【28】澄问《学》、《庸》同异。先生曰:“子思[1]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注释】
[1]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相传为《中庸》的作者。
【译文】
我问《大学》、《中庸》的异同。先生说:“子思把《大学》一书的主要含义概括为《中庸》的首章。”
【29】问:“孔子正名[1],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2]。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
[1]孔子正名:语出《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2]此春秋时事,《左传》有记载,据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
[3]语出《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译文】
问:“孔子正名的具体主张,先儒说是向上禀告天子,向下告知各诸侯国,废掉辄的国君之位,而重新确立郢为国君,这种说法怎么样?”先生说:“恐怕很难这样去做。哪有别人真心实意地礼待我去帮他治理国家,我就先去废除他的国君之位的做法?这岂是人情天理?孔子既然赞同辄主持国政,必定是他能够尽心治理国家,对于各种意见都能听得进去。圣人德性高尚,以至诚之心,感化卫君辄,使他知道不孝顺父亲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辄必将痛哭前往迎接他父亲回来。父子之间的情感,出于天性,辄能够如此真诚地忏悔,蒯聩怎能不感动呢?蒯聩已经回国,于是卫君辄交出国君之位,并请求惩罚。蒯聩已经被儿子的真情所感化,又有孔子的至诚之心在中间调和,绝不肯接受君主之位,仍然命令儿子辄为君主。群臣百姓又必定想要辄继续做他们的国君,卫君辄坦诚自己的过错,请示天子,通告诸侯国,一定要让父亲当国君。蒯聩和群臣百姓都赞美辄的悔悟和仁爱孝顺之情,请示天子,通告诸侯国,一定要让辄继续做他们的国君。于是各方面的要求和任命集中于辄身上,使得辄继续当卫国的君主。辄不得已,按照后世奉养太上皇的做法,率群臣百姓尊崇蒯聩为太公,以丰厚的物品奉养他,然后才告退继续做国君。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次性解决,并且可以治理天下了。孔子的正名,或许是这样。”
【30】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1]。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2],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注释】
[1]语出《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2]语出《礼记·丧服四制》:“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意为父母之丧,三天以后就可以喝粥,三个月后就可以洗头,一年后就可以改戴练冠,这期间虽然身心痛苦,但并不会损害人的身心性命,这体现了不因为死者而伤害生者的道理。
【译文】
我在鸿胪寺居住,忽然接到家书,说自己的儿子病危。我内心十分忧郁,不能忍受。先生说:“这个时候正适合用功。如果这个时候放过,平常空闲时讲学有什么用?人正是要在这个时候来磨炼自己。父亲疼爱儿子,本来是最真切的情感。然而天理也有一个中和的状态,过头了就是自私。人在这种时候常认为天理应当忧虑,于是一直忧愁苦恼,却不知道这已经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了。通常人有所感触而发出七情,多数情况下都过头了,很少有不及的。才过头就已经不是心之本体,必须调整适中才能实现。好比父母的过世,作为子女谁不想哭到死去活来,才能快慰于心?然而《礼记》却说‘毁不灭性’,不是圣人强制要这么做,天理本体原本有一个限度,不能过头。人只要认识了这个心体,自然不能增加或减少分毫。”
【31】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1],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注释】
[1]语出程颐《周易程氏传·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译文】
不能说一般人都具备“未发之中”的状态。因为“体用一源”,有这样的体,就有这样的用。有“未发之中”的状态,就有“发而皆中节之和”的状态。现在的人不能达到“发而皆中节之和”的状态,可知他“未发之中”的状态也没有完全实现。
【32】《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译文】
《周易》的爻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周易》的卦象是初爻的象,《周易》的变化,是围绕象而变化,《周易》的占卜,是运用爻辞。
【33】“夜气”[1]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
【注释】
[1]夜气:语出《孟子·告子上》:“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
【译文】
孟子的“夜气”说是针对普通人而言。学者如能用功,那么不管白天有事无事,都是这个气汇聚与发散之时,圣人就不必说“夜气”了。
【34】澄问“操存舍亡”章。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1],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注释】
[1]语出《孟子·告子上》:“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意为孔子说:“抓住它就存在,放弃它就亡失。出出进进没有一定的时候,也不知道它何去何从。”这是说人心吧?
【译文】
我问孟子“操存舍亡”这一节。先生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这虽然是针对普通人而言,但学者也必须认识心的本体原来就是这样,则操持存养的工夫才没有弊病。不能说‘出’就是亡失,‘入’就是存养。如果说本体,原本无所谓‘出’和‘入’。如果说‘出’‘入’,那么思虑运筹的时候是‘出’。然而心这个主宰时常昭然存在,哪有什么‘出’呢?既然没有出,哪有什么入呢?程子所谓的‘腔子’,也就是指天理。虽然整天应酬交际,但都不外乎天理,都是由天理在主导。如果超出了天理,那就称作‘放’,称之为‘亡’。”又说:“出入只是讲动静,动静没有终始,哪有方向呢?”
【35】王嘉秀[1]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2],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知者见之便谓之知,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3]。仁、知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注释】
[1]王嘉秀,字实夫,王阳明的学生。
[2]科、贡、传奉:分别指古代入官的三种途径,即分科考试被录取入官、乡党推荐入官、内官安排入官。
[3]语出《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译文】
王嘉秀问:“佛教以脱离生死来引诱人们入道,道教以长生久视引诱人们入道,它们的本意也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致,也是只看到圣人之道的上一截,不是圣人之道的正途。如今进入仕途的方式有分科考试被录取入官,乡党推荐入官,内官安排入官,一样都可以做到大官,但终究不是做官的正路,君子不走这条路。道教、佛教修炼到极处,和儒者略同,只是有了上一截,遗漏了下一截,终究不像圣人之道那么完整。然而他们的上一截是相同的,不可否认。后世儒者往往又只得到了下一截,分开后就失真了,流变为背诵记忆、词章、功利、训诂之学,最终也不免沦为异端。这四门学问,终身劳苦,对于身心却没有丝毫益处。和道教佛教徒的清心寡欲,超然世外,不为俗世所牵累相比,反而有所不及。如今学者不必先去排斥道教佛教,应当确定从事圣人之学的志向。明白了圣人之学,则道教佛教自然泯灭。不然的话,现今所学,恐怕佛道们都会轻视,反而想要他们诚服,不是很难吗?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看法,不知先生认为如何?”先生说:“你所讲的大致不错。但是说上一截、下一截,这是人们观点有偏激才如此划分。如果讨论圣人的中和至正之道,上下彻底贯通,哪有什么上一截、下一截呢?‘一阴与一阳相互作用的规律叫做道’,但是对于这种规律,‘仁者有仁者的看法,智者有智者的看法,而百姓每天都运用着这种规律却毫无知觉,所以真正全面认识这种规律的人很少’。仁和智难道不可以称之为道?但是认知有偏差,也就有弊病。”
【36】蓍[1]固是易,龟亦是易。
【注释】
[1]蓍:古代用以占卜的草。
【译文】
蓍草诚然是周易占卜之法,龟甲也是周易占卜之法。
【37】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1],恐亦有不满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没,毕竟如何?”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注释】
[1]语出《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为舜时的乐曲名,《武》为周武王时的乐曲名。孔子评论《韶》说:“美极了,而且好极了。”评论《武》说:“美极了,却还不够好。”
【译文】
问:“孔子认为周武王没有尽善,好像对他有不满的地方?”先生说:“在周武王的时候也只能这样去做。”问:“假使文王没有死去,最终会是怎么样?”先生说:“文王在世的时候,天下已经有了三分之二归附于他。如果到武王讨伐商纣的时候,文王还活着的话,或许不至于兴兵讨伐,必定这剩余的三分之一也来归附了。文王只是善于与纣王相处,使他不能放纵自己的恶行而已。”
【38】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1]。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注释】
[1]语出《孟子·尽心上》:“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意为子莫这个人主张持守中道,持守中道就差不多了。但如果持守中道没有灵活性,就和执着于一点一样。
【译文】
问孟子所说的“执中无权犹执一”。先生说:“中就是天理,就是变易,随时变易,怎么能执着?必须因时制宜,很难预先确定一个规范。像后世的儒者,要将道理逐一说得没有一个漏洞,确定一个格式,这正是执一。”
【39】唐诩[1]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2],只是志到熟处。”
【注释】
[1]唐诩:江西人,王阳明的学生。
[2]语出《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为七十岁的时候随心所欲而不会逾越规矩。
【译文】
唐诩问:“立志是要时常保存一个善念,要去为善去恶吗?”先生说:“心存善念时就是天理。此刻的念头就是善,哪还有什么其他的善?此刻的念头不是恶,哪还有其他的恶要清除?这一念头就如树木的根芽,立志的人长久保存这个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志向成熟的境界。”
【40】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译文】
精神,道德,言说行动,大都是以收敛为主,发散开来是不得已。天地万物与人都如此。
【41】问:“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1],惜其蚤死。”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曰:“续经亦未可尽非。”请问。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2]。”
【注释】
[1]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2]语出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王阳明引此,意为王通续经,颇费心思,自知其苦,难为他人言。
【译文】
问:“文中子是什么样的人?”先生说:“文中子差不多大体接近圣人,只是没有那么博大精微而已,可惜他死得太早。”问:“为什么他会在编撰经书这事情上遭人非议呢?”先生曰:“编撰经书也不能完全否定。”请问原因。过了很久,先生说:“更觉良工心独苦。”
【42】许鲁斋[1]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注释】
[1]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元朝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力倡程朱理学,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贡献很大。他曾说:“学者治生最为先务。”
【译文】
许衡认为儒者应当以治理生计为首要的任务,这一说法容易误导别人。
【43】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译文】
问道家关于元气、元神、元精的学说。先生说:“这三者是一体的,就其畅通流行而言称之为气,就其凝聚结合而言称之为精,就其奇妙的作用而言称之为神。”
【44】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译文】
喜怒哀乐的本体原就是中正和谐的。只要掺杂自己的私意,就有过头和不及,就是自私。
【45】问哭则不歌[1]。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注释】
[1]语出《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译文】
请问先生为什么孔子哭泣就不再唱歌。先生说:“圣人的心体自然如此。”
【46】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译文】
克己必须把私欲彻底扫除干净,丝毫不留才行。如果有一毫私欲存在,那么很多恶念就会接踵而至。
【47】问《律吕新书》[1]。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2]。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注释】
[1]《律吕新书》:南宋蔡沈著,上卷《律吕本原》,下卷《律吕辨证》。
[2]古人通过律管飞灰来测定节气。具体做法是:将芦苇茎中薄膜烧成灰,放在不同律管里,置案上,密封门户,等到某一气节来临时,相应律管里的灰就会自行飞出,以此测定几时几分气节至。
【译文】
请问《律吕新书》方面的问题。先生说:“学者应注重当务之急。就算熟知律吕,也未必有用。必须心中先具有礼乐的本体才可以。并且像书上所说,多用律管来测定气候。然而到了冬至那一刻,律管上的灰飞动时,有先有后,片刻之间,怎么知道哪一个律管上的灰飞动时恰好代表的是冬至那一刻呢?必须要心中先知道冬至那一刻才可以。这就是讲不通的地方。学者必须先在礼乐本体上用功。”
【48】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译文】
徐爱说:“心就好比镜子。圣人之心好比明镜,常人之心好比昏暗的镜子。近世的格物学说,就好比拿镜子来照物,只知道在照的行为上用功,不知镜子还是昏暗的,怎么能够照呢?先生的格物学说,就好比让人先去磨镜,让镜子明亮起来。在磨的行为上用功,等到镜子明亮了,也没有放弃照的工夫。”
【49】问道之精粗。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
【译文】
询问道的精粗问题。先生说:“道无所谓精粗,人理解的道有精粗而已。比如说这一间房,人刚一进来,只看见一个大致的规模,待久了,就连柱子墙壁之类的东西都一一看得清楚。再待久些,就连柱子上的花纹雕饰都能看清楚。但只是一间房而已。”
【50】先生曰:“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
【译文】
先生说:“近来诸位很少有疑问,这是为什么?人如果不用功,无不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为学只要循规蹈矩就可以了。却不知道平常的私欲一天天积累,就如地上的灰尘,一天不扫,就积累一层。踏踏实实地用功,就明白道没有终点,越探究越深奥,必须达到精粹清澈没有一毫不符合道才行。”
【51】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译文】
问:“知至了然后才可以讲诚意,如今都没有完全了解清楚天理人欲,怎么去用克己的工夫呢?”先生说:“人如果踏实地用功不间断,那么这个良心所蕴含的天理精微都能够日益洞察,对于细微的私欲,也能够每天见得更清晰。如果不用克己的工夫,整天只是空谈而已,天理最终不能自己呈现,私欲最终也不会自己呈现。就如人走路一样,走一段才认得一段,走到岔路口,有疑问就问路,问清楚了再走,才能逐渐到达想去的地方。现在的人对于已经知道的天理不肯保存,对于已经知道的人欲又不肯摒除,而只是担心不能完全知道天理人欲。只空谈一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姑且等到自己没有私欲可以克制了,再去担心不能完全知道天理人欲,也还不迟。”
【52】问:“道一而已[1]。古人论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无方体,不可执着。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注释】
[1]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夫道,一而已矣。”
【译文】
问:“道只是一个。古人谈论道往往不同,探求道有没有关键呢?”先生说:“道本没有形体方位,不可以执着。如果拘泥于文辞句意来探求道,则反而远离了道。就如现在的人只说天如何如何,其实何尝看见过天呢?不可以把日月风霜之类的气象说成是天,也不可以把人物草木等说成是天。道就是天,如果理解了,何处不是道?人们往往因自己的一孔之见,认定道只能如此,所有观点各有不同。如果反躬自求,看得自己的内在心体,则随时随地都是道。从古至今,无始无终,哪有什么异同?心就是道,道就是天,认识了心体就认识了道,认识了天。”又说:“各位要真实理解这个道,必须从自己内心上去体认,不需要向外探求来获得。”
【53】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1]。”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2]之乐,稷[3]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注释】
[1]语出《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2]夔:传说是舜的乐官。
[3]稷:周人的先祖,尧舜时主管农事的官。
【译文】
问:“事物名称、规则、标准等,也必须预先研究吗?”先生说:“人只要造就自己的心体,各种作用就在心体之中。如果涵养心体,确实有‘未发之中’的状态,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的状态,自然无论什么行为都会恰当合适。如果没有这个心体,虽然预先研究了世上许多事物的名称、规则、标准,但与自己本不相干,只是一种临时的装饰点缀,自然并不能真正实行。也不是说完全不去理会各种事物的名称、规则、标准,但要知道先后轻重,才接近道。”又说:“人要随各自的才能来成就自己。才能是个体所能做的,如夔是乐师,稷是主管农事的官,这都是他们各自的资质禀赋适合做这一行。成就他们的资质,也就是要他们的心体达到纯粹天理的状态。他们的作为,都是由天理主导所致,然后可以称之为才能。等到行为完全符合天理时,也就不再是专门的人才了。假使夔、稷换个职业去干,应当也可以承担。”又说:“像《中庸》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都是不成为像器皿一样的人。只有涵养本心的人能做到这一点。”
【54】“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时先生在塘边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学云。
【译文】
“与其打造几亩没有源头的池塘,不如打几尺深但有源头的水井,这样生机无限。”当时先生正在池塘边坐,旁边有一口井,所以拿这个比喻求学。
【55】问:“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
【译文】
问:“世道越来越衰败,太古时候的气象怎么能再次看到?”先生说:“一天就一元。人早晨起来,没有接触事物时,内心清明的景象,就像在伏羲时代游历一样。”
【56】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1]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
【注释】
[1]六卿:明代六部分别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均设尚书。
【译文】
问:“内心追逐外物,怎么办才好呢?”先生说:“君主端正坐着,清静肃穆,六部各安其职,天下由此得到治理。心统帅五官,也要这样。如今眼睛要看时,心就追逐美色。耳朵要听时,心就追逐声音。就像君主选择官员一样,一定要亲自到吏部,要调动军队时,亲自去兵部,如果这样,不仅君主这一主体失去了,六部也没法各就其职了。”
【57】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
【译文】
善念产生时内心知道,并且充实它,恶念萌发时内心知道,并且遏制它。知道、充实与遏制,这都属于人的意志,是人生来就具备的。圣人也就是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学者应当存养这一点。
【58】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1],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2]。”
【注释】
[1]语出《周易·系辞上》:“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2]语出程颢《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二:“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
【译文】
我说:“喜好美色、喜好财利、喜好名声等心思,本是私欲,像闲思杂虑,怎么也称之为私欲呢?”先生说:“毕竟都是从喜好美色、喜好财利、喜好名声等根源上兴起的念头,自己去寻找这个根源就可以看得到。就像你心中必定没有做盗贼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你原本就没有这个心思。你对于财货美色名声利益等心思,一切都和不做盗贼的心一样,都消灭掉,仅仅只有一个心的本体,看有什么闲思杂虑?这就是‘寂然不动’,就是‘未发之中’,也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59】问“志至气次”[1]。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2]之偏,故如此夹持说。”
【注释】
[1]志至气次: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意为人的思想意志主导着意气情感,意气情感是充满于体内的力量。思想意志一彰显,意气情感也就随之呈现,所以说坚定自己的意志,不要放纵意气情感。
[2]告子,名不害,战国人。他提出性无善恶论,并有“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的论点,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
【译文】
问“志至气次”。先生说:“这是‘志之所至,气亦至焉’的说法。不是‘极至次贰’的说法。持守志向,则养气就在其中。不放纵血气,就是持守志向。孟子补正了告子思想的偏激,所以这样混着说。”
【60】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1]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注释】
[1]语出程颐,见《河南程氏外书》卷三。
【译文】
问:“程颐说:‘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这种说法怎么样?”先生说:“不对,这样说乃是作伪。圣人就如同天一样,无处不是天。日月星三光之上是天,九层大地之下也仍然是天。天何尝降低自己到卑微地位呢?这是孟子所谓的‘大而化之’。贤人就如同山一样,守住它的高度而已。然而百丈高的山不能提升到千丈,千丈的不能提升到万丈,因此贤人也没有拔高自己而自我标榜,有意拔高和自我标榜是作伪的表现。”
【61】问:“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1],延平[2]却教学者看未发之前气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3]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
【注释】
[1]语出程颐,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2]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今福建南平人。程颐三传弟子,朱熹曾从游其门下,并编撰其语录为《延平答问》。
[3]语出《中庸》第一章:“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为君子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要警戒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要敬畏持守。最幽暗不明的地方就是最容易看见的,最细微看不见的事物也就是最容易显现的,所以君子要在独处时谨慎。
【译文】
问:“程伊川所说的‘不应当在喜怒哀乐之情没有流露出来的时候去探求一个中和的状态’,李延平却教学者去体认喜怒哀乐之情没有流露时的状态,这怎么解释?”先生说:“都对。程伊川担心人在喜怒哀乐之情流露之前去讨论中和,把中和看做一个固定的事物,就像我以前把气息平定时看做中和的状态,所以他只教人在涵养省察上用功。李延平担心人不知道如何下手做工夫,所以教人时时刻刻去追求喜怒哀乐之情流露之前的状态,使人端正眼睛去注视是这样,倾耳去听也是这样,这就是《中庸》所讲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这都是古人不得已开导人的说法。”
【62】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有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时一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1]。”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曰:“天理何以谓之中?”曰:“无所偏倚。”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虽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既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注释】
[1]语本《中庸》第三十二章:“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所倚。”
【译文】
我问:“喜怒哀乐的中和状态,其整体状态一般人确实不能持有,比如一件应当喜或怒的小事,平时没有喜怒之心,等到应对事情的时候,也符合礼仪,这可以称之中和吗?”先生说:“在一时一事上,确实也可以称之中和,但是不能称为大本达道。人性本善,中和是人人都具有,怎么能说没有呢?但常人的心智往往有所蒙蔽,因而其本体虽时时发现,终究是时明时暗,不是本体的全然发用状态。无时无处不符合中道,然后才可称之为大本;无处不和谐,然后才可称之为达道。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确立天下的大本。”我说:“我对于‘中’字的含义尚未明白。”先生说:“这个必须要自己的内心去体认出来,不是通过言语所能讲清楚的。中只是天理。”我说:“什么是天理呢?”先生说:“摒除人欲,就知道天理。”我说:“天理为什么称之为中?”先生说:“因为它没有偏倚。”我说:“没有偏倚是什么气象呢?”先生说:“就好像一块明镜,全体晶莹透彻,没有一丝灰尘沾染。”说:“偏倚是有沾染,比如说染在喜好美色、喜好财利、喜好名声等事情上,才可以看得见偏倚。如果喜怒哀乐之情没有呈现时,美色名利都没有沾染到心。那么怎样才知道它有偏倚呢?”先生说:“虽然没有附着,然而平日的喜好美色、喜好利益、喜好名声的心思原本没有放弃,既然没有放弃,那就是有,既然有这个心思,那么就不可以说没有偏倚。譬如患了病的人,虽然有时候不发作,但是病根却没有除去,所以也就不能称之为没病的人。必须把平日喜好美色、喜好利益、喜好名声等私心全部一并清除干净,没有毫发保留,而此心的全体廓然大公,纯粹是天理的状态,才可以称之为喜怒哀乐之情没有呈现时的中和状态,才是天下之大本。”
【63】问:“‘颜子没而圣学亡’[1],此语不能无疑。”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其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2],是见破后如此说。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3],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
【注释】
[1]语出《王阳明全集》卷七,《别湛甘泉序》:“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
[2]语出《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意为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一定的礼节来约束我的行为,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
[3]语出《论语·子罕》,意为想要继续跟着前进,又不知怎样走了。
【译文】
问:“‘颜回死了后,圣人之学开始消亡’。这句话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先生说:“体认到圣学全貌的只有颜回,看他的喟然一叹可以得知。颜回所谓‘老师循循善诱地教导我,让我广博地学习知识,以礼仪来规范我的行为’,这些都是看破之后才这样说。博文约礼怎么是善于诱导人呢?学者必须思考这个东西。大道的全体,圣人也难以告诉别人,必须是学者自己修养自己觉悟。颜回所说的‘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也就是文王‘望道未见’的意思。追求大道却没有看到,才是真正领会了大道。颜回死后,圣学的正统没有得到完整的流传。”
【64】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为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译文】
问:“身的主导是心,心的灵明知觉是良知,良知之发动是意念,意念所接触的是事物,是这样的吗?”先生说:“也可以这样讲。”
【65】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译文】
只要存养心体,使之时常被知觉,就是学问。过去和未来的事情,想多了有何益处?只会把心放逐于外。
【66】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
【译文】
说话颠三倒四,以此足可以看出他的心体没有存养。
【67】尚谦[1]问:“孟子之‘不动心’[2]与告子异。”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注释】
[1]薛侃(?—1545),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人,正德二年(1507)进士,官至行人司司正,王阳明的学生。
[2]语出《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
薛侃问:“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同。”先生说:“告子是强行把捉住这个心,要他不动。孟子则是通过集义达到自然不动心。”又说:“心的本体原来是不动的。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天理,性本来不动,天理本来不动,集义就是要恢复心的本体。”
【68】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译文】
天地万物兴盛繁茂之时,也就是宇宙混沌空寂无形之时;宇宙混沌空寂无形之时,也就是天地万物兴盛繁茂之时。宇宙混沌空寂无形的状态,是专一的开始,天地万物兴盛繁茂的状态是精粹的开始,专一中包含着精粹,精粹中包含着专一。
【69】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
【译文】
心之外没有事物。如我的心发出孝顺父母的一个念头,孝顺父母就是一个事物。
【70】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1]的工夫。”
【注释】
[1]义袭而取: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意为浩然正气是通过长期积聚正义感而形成的,不是行为偶尔符合正义便可获取。
【译文】
先生说:“如今跟我学习格物学说的人,很多还只是停留于口耳相传。何况那些专门口耳相传的人,能够超过他们吗?天理人欲的精微之处必须时时刻刻反省克制,才能逐渐有所见识。如今交谈之间,尽管只讲天理,但片刻之间,不知内心已经有了多少私欲。有偷偷流露出来而自己还不知道的,虽然用力省察,仍然不容易看清,何况只是口头上讲的人,可以认清全部吗?如今只知道讲天理,却把天理停放着不遵循,讲人欲的也停放着不清除,这怎么能算是格物致知的学问呢?后世之学,达到极致的,也只是做了个‘义袭而取’的工夫。”
【71】问“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译文】
问格物的学说。先生说:“格是正的意思,纠正不正确的,以恢复到正确的状态。”
【72】问:“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译文】
问:“知止就是知道至善只在我的内心,本来就不在心外,然后志向才能坚定吗?”先生回答道:“是的。”
【73】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1],是动静皆有事。”
【注释】
[1]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意为一定要使心处于清醒与自觉状态,但不要抱特定目的和意图,时刻记住,但不去违背规律地帮助它生长。
【译文】
问:“格物是在行动处用功吗?”先生说:“格物的工夫本来没有动静间隔,静时也有事物在。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表明不管动静都是有事的状态。”
【74】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
【译文】
工夫的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这也就是诚意的工夫。意念既已真诚,大多时候心也就自然端正,身也就自然修善。但是正心修身的工夫,也分别有用力的地方,修身是意念发出来的状态。正心是意念没有发出来的状态。心端正了就达到中,身修了就达到了和。
【75】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注释】
[1]语本程颢,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译文】
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只是阐述“明明德”。即便是“亲民”,也是属于“明德”的内容。明德是人心的德性,也就是仁。“具有仁德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体的存在”,如果有一个事物不当其位,那就是我的仁德没有完全扩充开去。
【76】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译文】
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就和道教佛教的主张相似了。
【77】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译文】
至善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本来没有一毫恶,所以说是至善。止于至善,就是恢复人性的本然状态而已。
【78】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译文】
问:“知道至善就是我的本性,我的本性内在于我的心。如果我的心就是至善的最后归宿,那么就不会因为过去的纷纷扰扰而向外探求,志向更为坚定了。坚定了就不会再纷纷扰扰,而是保持宁静,静心而不妄动就是安,安定则一心一意只在至善上。千思万想,务必追求达到至善,这就是思考之后而有所得。这样说对吗?”先生说:“基本差不多。”
【79】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1]反不得谓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注释】
[1]墨氏兼爱: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称之为墨子。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反对儒家繁礼厚葬,提倡薄葬非乐。有《墨子》一书传世,为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
【译文】
问:“程子说:‘具有仁德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为一个整体。’为何墨子的‘兼爱’说,反而不可以称为仁呢?”先生说:“这也很难说。必须由你们自己去体认才行。仁是造化生生不息的天理,虽然弥漫周遍,无处不在,然而它的流行发用,也只是渐进,所以才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产生,必定从一阳开始,然后才逐渐发展到六阳,如果没有一阳的产生,又怎么有六阳呢?阴也是如此。由于有渐进的过程,所以就有一个发端的地方,有个发端的地方,所以才能产生。唯有生长,所以不停息。譬如树木,它刚开始抽芽,就是树木的生机发端处,抽芽然后再发干,发干然后再生长枝叶,然后是生生不息。如果没有树芽,怎么会有树干有枝叶?能够抽芽,必定是下面有一个根。有根才能生长,没有根就会死去。没有根从哪里抽芽呢?父子兄弟之间的爱,就是人心的生机发端处,就像树木的抽芽。从这里开始仁爱人民,进而热爱事物,就是长出树干、生长出枝叶。墨子的兼爱没有差等,把自己的父子兄弟看成和路人一样,这是自己埋没了发端处。不抽芽,就知道他没有根,也就不会生生不息,怎么可以称作仁呢?孝悌是仁的根本,仁这个天理就是从孝悌这个根里生发出来的。”
【80】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1]。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是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注释】
[1]语出李侗《延平答问》,指既合天理又没有私心。
【译文】
问:“李延平说‘当理而无私心’,符合天理与没有私心,怎么分别呢?”先生说:“心就是理,无私心就是符合天理,不符合天理就是有私心。如果把心和理分开来讲,恐怕也不好。”又问:“佛教对于世间的一切情欲私欲,都不执着,好像是没有私心。但是放弃人伦,就是违背天理。”先生说:“这也就是一回事,都只是成就了他自己的一个自私的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