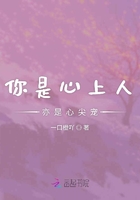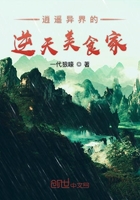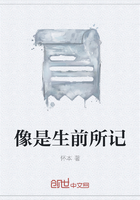一个凡人越难解放他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我们的人性。
——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
像在上一本三部曲《三大师》中一样,在这本书里,我再一次将三位作家的肖像在一种内在共同性的意义上联系起来;但这种内在的统一性将不再是一种比喻上的共同性。我不想探寻任何思想家的公式,只想刻画思想的形式。如果说我在书里总是有意识地把几个这样的人物安排在一起,那这恰如一种某些画家所采用的方法,即喜欢给他的作品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光线和反光互相交织、互相作用,通过对照将不同类型之间的那些原本隐匿着、现在却很显著的相似之处展现出来。我一直觉得对比是一个起推动刻画作用的因素,我喜欢以它为方法,因为使用它时没有强制性。公式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贫乏,对比就在多大程度上使对象变得丰富。它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反射来照明,用空间的深度来做独立作品的画框,从而提高了画作的价值。最早的语言肖像画家普鲁塔克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塑造的秘密,在他的《对比列传》[1]中,总是同时对一个希腊人物和一个罗马人物进行类比式的描绘,以便使他们个性背后的精神投影,使他们的类型显得更加清晰。我试图在一个相近的精神领域,即文学-性格学领域达到与这位传记-历史学领域赫赫有名的前辈所取得的相似的效果。这两本我想题为《世界大师——精神类型学》的书,只是即将产生的一个系列中最早的两本。但我绝不是想为天才人物的世界强行建立一个生硬的体系。作为一个富于激情的心理学家、一个渴望去刻画的刻画者,我只是将我的肖像艺术运用到这种艺术本身驱使我到达的地方,只是以那些我感到自己与之密不可分的人物为对象。这就从我内心里为任何完备配套设定了限制,而我对这一局限丝毫不感觉遗憾,因为这种必要的断片形式只会吓着信仰创作的系统性的人,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精神的无限世界可以被挖空心思地想象得面面俱到。然而这个庞大的计划吸引我的却又正是这种两重性,即它既触及了无限,又给自己设置了边界。就这样,我用这双令自己也感新奇的手缓慢而充满激情地继续建造这座始于偶然事件的建筑,一直建到高悬于我们生活之上的那一小片不确定的时间的天空。
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这三位英雄人物在生活的外部命运上就具有不容忽视的共同性: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星相方位。三个人都被一种极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力量驱赶出他们温暖的存在,卷进了一个毁灭性的激情旋涡中,过早地终结于可怕的精神错乱、致命的感官迷醉以及疯狂或自杀中。他们与时代毫无联系,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如流星般闪耀着短短的光芒迅疾地冲进了他们的使命的暗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意义,因为他们只是从无限驶向无限:他们生命中的跌宕起伏几乎从不接触现实世界。某种超乎人性的东西作用于他们内心,这种力量超越了他们自身的力量。他们感觉到自己完全陷入了它的控制中:他们不是听命于自己的意志(在少数几分钟自我清醒的时刻,他们恐惧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变成了依附奴隶,成为一种更高之力——魔鬼之力下的中魔之人(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
“魔鬼性”这个词从古代神话宗教的原始观念进入现代,已经经历了如此众多的意义与解释,所以很有必要赋予它一个我个人的解释。我用“魔鬼性”一词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使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似乎自然将它从前的混乱中的一个不可转化的不安定部分留给了每颗心灵,这个不安定的部分总是兴奋而激越地试图返回那个超越人性、超越感官的本原之乡。魔鬼就像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酵母,一种膨胀着的、折磨人的、紧张的酵素,发酵了所有危险过度、心醉神迷、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东西,而排斥了其他的安静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上,心灵中的这个宝贵而危险的部分很快就枯竭耗尽了;只是在极少数的短暂时刻里,在青春期危机中,在由于内心世界的爱情或生殖欲望而激动的时刻,这种跃然体外、热情奔放和自我牺牲的东西才会充满预感地控制了市民式的平庸生活。但在其他时候,稳重矜持的人们却压抑住体内浮士德式的欲望,他们用道德的氯仿来麻醉它,用工作来压制它,用秩序来阻挡它:市民永远都是混乱之物的天然敌人,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他们自己心里。但在更高层次的人,尤其是创造性人物的身上,不安定却作为一种对当前作品的不满足而创造性地继续起着作用,它赋予人一颗“高贵的、痛苦着的心灵”(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质疑的精神,这种精神超越自身,渴望进入宇宙。所有那些以探寻和冒险精神推动我们超越自身的天性和个人利益而进入探寻之险境的东西,都应归功于我们自身中那一部分魔鬼似的精神。但只有在我们能控制它、在它服务于我们的紧张和激动时,这个魔鬼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旦有益的激动变为过分激动,一旦心灵陷入煽动性的欲望和魔鬼性的强烈爆发中,那么它的危险性就开始出现了。因为这个魔鬼只有通过毫不留情地破坏有限之物、世俗之物,也就是它所寄居的躯体,才能回到它的故乡、它的本原之乡,即回到无限之中:它发端于扩充,却趋向于破裂。因此它占据了那些不知及时束缚它的人,它用可怕的不安定实现他们魔鬼的天性,粗暴地从他们手中夺去意志的控制力,致使他们这些毫无意志的被驱使者在风暴中迎着命运的险礁跌跌撞撞地前行。生命的不安定永远是魔鬼性的第一个征兆,血液不安定,神经不安定,精神不安定(因此人们也把那些散布不安定、厄运和破坏力的女人称为魔鬼)。在魔鬼周围永远萦绕着危险的、胁迫生命的暴风雨天气,永远萦绕着悲剧的气氛和厄运的呼吸。
因此,每个精神的人、有创造性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与他的魔鬼的斗争中,这种斗争永远是一场英雄的斗争、一场爱的斗争,也是人类最壮美的斗争。有些人屈服于魔鬼那激烈的攻势,就像女人屈服于男人一样,他们愿意被它强大的力量所强暴,为自己能被这种多产的元素所穿透和淹没而感觉幸福至极。有些人约束魔鬼,将自己冷峻、果断、目标明确的男性意志施加于它热烈颤动着的本性上:这种充满敌意的感情和满怀爱意的搏斗交织缠绕,常常贯穿生命的始终。这种伟大的搏斗在艺术家的心里和他的作品里同样的生动:在他创作的每个细枝末节都颤动着热烈的呼吸,这是精神与它的诱惑者在新婚之夜的感性颤抖。只有在创造者身上,魔鬼才能走出感情的阴影,努力变作语言和光明。在那些被魔鬼操纵的诗人身上,我们能够最清楚地认出它的激情特征。在这里,我选择了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这三个人作为这类诗人在德语世界最有意义的代表。因为如果魔鬼独断专横地统治诗人,那么在火焰般迅速加剧的兴奋中将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类型:迷醉艺术。极度兴奋狂热的创造,痉挛般洋溢着的精神振奋,抽搐和爆发,放纵和沉迷,希腊人的μανια,即那种神圣的、一般只存在于预言者和神话人物身上的疯狂。漫无节制、夸张过度永远是这种艺术的可靠标志,这是一种永恒的超越自我的意念,它渴望达到极点,渴望进入被魔鬼性奉为最原始的自然状态而竭力回归的无限之中。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就属于这种非凡的类型,他们激烈地撞破生活的边界,反抗地打破各种形式,在过度的狂热中毁灭了自身。在他们的眼睛里明显地闪烁着魔鬼那种陌生的、不安的目光。魔鬼还借他们之口说话;甚至当他们的喉咙变哑了,他们的思想消散了,它还借着他们支离破碎的身体说话。只有当他们的心灵在强大的张力下被痛苦地煎熬、被撕碎时,人们才得以透过一个裂缝窥视到那里面魔鬼栖居的深渊;除此以外的任何时候,他们本质中这个可怕的客人都不会更轻易地被感觉到。恰恰是在他们的精神衰落之时,这种平素隐藏着的魔鬼之力在这三个人身上都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这些受控于魔鬼的诗人的神秘本质,更清楚地揭示魔鬼性自身,我忠实于我的对比方法,给这三个悲剧英雄设立了一个看不见的对照人物。但是,这些魔鬼附身的诗人的真正对立面绝不是那种没有魔鬼性的诗人:没有魔鬼性,没有从世界的原始乐音中流淌出来的词句,就不会有伟大的艺术。关于这一点,没有人能比那个一切魔鬼性的死敌、那个在克莱斯特和荷尔德林的生活中坚决地站在反对立场上的歌德证实得更清楚了。他在对艾克曼谈及魔鬼性时说:“任何最高类别的创造,任何出色的总览式描述,都不在人力范围内,而是超越尘世力量的。”没有灵感便没有伟大的艺术;而所有灵感又都源于一个无意识的彼岸世界,一种高于自身之清醒的知觉。作为那种过度兴奋的、被洋溢的激情夺去了自我的诗人,即那种对自己漫无节制的诗人的真正对立面,我选取了懂得节制的诗人,他能用尘世赐予他的意志来约束他所具有的魔鬼之力,并使之具有明确的目标,因为魔鬼性虽然是最美妙的力,是一切创造之母,但它却是完全没有方向的;它唯一的目标是回到无限,回到它来源于其中的混沌中去。如果一个艺术家用人性的力量控制这种原始的力量,如果他给予它尘世的标准和自己所选择的方向,如果他像歌德那样“支配”诗歌,将“不可测度”的东西转化成有形的思想,如果他成为魔鬼的主人而不是奴隶,那么就会产生一种高贵的、毫不逊色的魔鬼性的艺术。
歌德,这就是那个作为截然相反的类型提出来的名字,这个名字将象征性地贯穿全书。歌德不仅作为自然科学研究者和地质学家,是一个“火山爆发的反对者”——在艺术中,他也推崇进化性而不是火山爆发性,以一种他少有的、非常激烈的坚决来对抗一切粗暴痉挛的、火山爆发的,简而言之,一切魔鬼性的东西。而正是这种对抗时的愤怒比其他东西更好地使歌德泄露出,与魔鬼的斗争也曾是他的艺术中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那些在生命中遭遇过魔鬼的人,只有那些见过它那美杜莎一样的眼光而不寒而栗的人,只有那些体验过它的全部危险性的人,才会如此般把它当成一个可怕的敌人。在青春的灌木丛中的某个地方,歌德一定曾经在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时与这个危险的家伙遭遇过——维特可以证明这一点,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他把克莱斯特的命运预见性地从自己身上排除了;塔索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通过他,他也把荷尔德林和尼采的命运先见地从自己身上排除了。经过那次恐怖的遭遇之后,歌德对他的这个强大的敌人的致命力量终生怀有愤怒的敬畏和不加掩饰的恐惧。在任何形象和变形中,他都能以一种神秘的目光认出他的死敌: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在克莱斯特的《彭提西丽娅》中、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他后来再也不敢翻开莎氏的悲剧:“它会毁了我”)。他越是关注形象塑造和保存自身,就越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他知道把自己交给魔鬼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因此他保卫自己,因此他徒劳地警告他人。歌德为了保卫自己而要花费的力量与魔鬼为了挥霍自己要花的力量一样多。对于他来说,这场搏斗也涉及一种最高的自由:他反抗无节制,为节制而战,为他自身的完善而战,而那些人却仅仅是为无限而战。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而不是在竞争的意义上(虽然生活中确有这一竞争),我把歌德的形象作为这三个诗人兼魔鬼仆人的对立面提出来:我相信我需要一种强大的反面声音,使我在描写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时所推崇的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激昂、狂热与强劲的东西在价值意义上不会作为唯一的或最崇高的艺术而出现。在我看来,正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对立构成了最高级别的精神两极的对立。因此,如果我把这一对内在的反命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做稍许变动,使之变得一目了然,就似乎不是多此一举了。因为这种强烈的对照以近乎数学公式般的准确贯穿了从广泛的形式到感性生活中最微小事件的全部:只有将歌德与这些极具魔鬼性的对手进行比较,这一比较才能作为一种精神的最高价值形式的对比而照亮问题的最深处。
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身上最不容忽视的特点首先是他们与世界的缺乏联系。魔鬼抓住了谁,就把谁从现实中拖拽出来。三个人都没有妻子儿女(就像他们的手足兄弟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一样),都没有房子和财产,都没有长期的工作和稳定的职务。他们的天性是流浪的,他们是尘世的流浪汉,是格格不入的人、怪异的人、受歧视的人,过着全然不为人知的生活。在尘世间他们一无所有,无论是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还是尼采,都不曾有过一张自己的床;什么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坐在租来的椅子上,在租来的桌子上写作,辗转于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房间。他们从不曾安家立业,连爱神也不愿长期眷顾他们这些把自己献给了善妒的魔鬼的人。他们的友谊脆弱易碎,他们的地位丧失殆尽,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他们永远处于虚空之中,又永远只落得虚空。他们的生命像流星,像不安地旋转着、坠落着的那种星;而歌德的生命却划出了一道清晰、完满的轨迹。歌德稳稳地扎下根来,这根越扎越深,越伸越广。他有妻子、有儿女,众多女性环绕装点着他的生活,为数不多但却忠诚的朋友们充实着他的每一小时。他住在宽敞富裕的房子里,房子里摆满了珍奇的收藏;他生活在温暖地簇拥着他的荣誉里,这荣誉环绕他的名字,有半个多世纪。他有地位有身份,是枢密顾问和大臣,世间所有勋章都在他宽阔的胸前闪闪发光。在他身上,人间生活的重力不断增长,正如在那三个人身上精神的飞翔力不断增长一样,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本质变得越来越牢固和稳定(而那三个人的本质却变得越来越飘忽,越来越不稳定,他们像被追捕的野兽一样在大地上奔逃)。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他自我的中心,同时也是民族的精神中心;他稳稳地、安定人心地统领着世界;他与世界的联系不仅限于与人的联系,而且还扩及植物、动物和石头,并由此创造性地致力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位魔鬼的主人都强有力地生活在自我中(而那三个人却像狄俄尼索斯[2]一样被自己的恶魔撕得粉碎)。歌德的一生是唯一一种对世界的战略性胜利,而那三个人却在虽富有英雄精神但却毫无计划的战斗中被世界所威迫,不得不逃进无限之中。为了能够超凡脱俗,他们必须用暴力挣脱尘世的束缚——而歌德不用离开尘世一步就可以到达无限:他慢慢地、很有耐心地把它拉近自己。因此他的方法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他每年都存储相当一部分经验作为精神收益,年底时,他像个精细的商人一样将之整理登记到“日记”和“年鉴”中,他的生命赚取利息,就像田地收获果实。而那三个人管理收支时却像是赌博者,在一种对待尘世的极其漫不经心的态度中,用他们的全部生命、全部存在孤注一掷,无止境地赢,无止境地输——魔鬼最恨那种慢吞吞的储蓄罐式收益。经验对于歌德意味着生存中最根本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却毫无价值:所以他们从痛苦中除了愈加强烈的情感外什么也没学到,他们像是幻想家,像是神圣的局外人一样迷失了自己。但歌德却是个不断学习的人,生活之书对于他就像不断铺展开的新作业,必须认真地、一行行地用勤奋和锲而不舍来完成。他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直到后来才敢于说出那句神秘的话:“我已学习过生活,神呵,限我以时日吧!”
而那三个却认为生活既无法学习也不值得学习,在他们看来,对于更高一级的生存的想象要比所有对旧感觉的依恋和感性的经验更重要。天资没有赋予他们的东西,他们自然不能拥有。他们只从天资那光芒四射的内容中取得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只允许自己从内心里被狂热的情感所激动和兴奋。火变成了他们的基本元素,燃烧变成了他们的行动,而这种鼓舞了他们的似火激情则摧毁了他们的一生。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在生命终结时比开始时更加孤独、遗世和寂寞,而歌德的每一分钟都比上一分钟更加富有。在这三个人身上,不断强劲起来的只是魔鬼,不断增加的只是占据了他们的无限:这是一种美丽的生活之贫瘠,又是一种不幸的贫瘠之美丽。
天才们虽然具有最内在的相似性,但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却使他们对现实采取不同的价值评判。每个具有魔鬼天性的人都蔑视现实,认为它有所欠缺,他们始终都是——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现有秩序的反抗者、叛乱者和叛逆者。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将自己的毫不动摇与毫不妥协坚持到死亡,坚持到毁灭。他们由此而成为(壮美的)悲剧人物,他们的生命则成为一场悲剧。相反,歌德却——他是多么明显地超越了自己啊!——对策尔特[3]透露道,他觉得自己天生不是个悲剧作家,“因为他的天性是妥协的”。他不愿像那三个人一样永远斗争,他想要——作为一种“持久的、平和的力量”,他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获得平衡与和谐。他带着一种人们只能称之为顺从的感情臣服于生活,将生活看做是一种更高的,甚至是最高的力,一种在任何表现形式和任何阶段中他都尊崇的力(“生活,不管它是怎样的,它总是好的”)。对于那些被痛苦折磨的人,那些被追赶者、被驱逐者,那些被魔鬼拖出尘世的人来说,给现实以如此高的评价,甚至哪怕有一点好评,都是再陌生不过的事情:他们只认识无限,以及通达这一无限的唯一道路——艺术。因此他们认为艺术高于生活,文学高于现实;他们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穿过千千万万的大石块,狂怒地、阴郁地锤锤打打,怀着越来越狂热的激情,穿过自己生命中的昏暗坑道,奔向那块闪闪发光的、他们在梦境深处感觉到的石头。而歌德(像列奥那多一样)却觉得艺术只是一个部分,只是生活的千千万万种美好形式的一种,这种形式对于他虽然像科学、哲学一样珍贵,但终究只是部分,只是生活中起作用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魔鬼性的人的表现形式变得越来越内敛,而歌德的表现形式则越来越外张。他们的本质越来越向一种极端的片面性和一种偏激的绝对性转化,歌德的本质则越来越向一种广泛的多面性转化。
由于对生活的热爱,在反魔鬼性的歌德那里,一切都以安全、明智的自我保护为目标。由于对现实生活的蔑视,在魔鬼性的人那里,一切都变成游戏、变成危险、变成暴力式的自我扩张,并且在自我毁灭中走向了终结。正如在歌德身上所有的力都是向心的,是从外部向中心点集中的,在那些人身上,一切力都是离心的,是从生命的内部向外扩张的,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将内核撕裂。这种外溢,这种向无形的宇宙空间流溢的愿望,在他们对音乐的偏爱中得到了最显见的升华。在音乐里,他们能够完全无边无际、无拘无束地从自己的本原中流溢出来。正是在跌落的过程中,荷尔德林和尼采,甚至连强硬的克莱斯特都陷入了它的魔力之中。理智完全化作迷狂,语言成为节律:魔鬼性的精神崩溃之时,总是(在莱瑙那里也是如此)有汹涌的音乐萦绕。相反地,歌德却对音乐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他害怕它那能将意志拉入空洞之中的诱人力量,所以在自己最坚强的时刻强制性地抵制它(甚至包括贝多芬的音乐);只有在虚弱、病痛和恋爱之时,他才对它完全敞开。他真正的本原因素是绘画,是雕塑,是所有那些能提供稳定的形式、能给模糊无形以限定、能阻止物质四溢流散的东西。如果说那些人喜爱无拘无束、通向自由、回归混乱情感的东西,那么他明智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则去抓取一切能提供个人稳定性的东西,去获得秩序、标准、形式和规则。
人们还可以推演出对魔鬼的主人和仆人这对创作上的矛盾体的上百种对比,而我只想再选择那种永远都最清楚明了的几何对比法。歌德的生活公式是一个圆:闭合的线,生存的尽善尽美,永远回归到自身,从确定不移的中心到无限总是相同的距离,从中心向外全面地扩展。因此在他的生命中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巅峰,他的创作也没有任何顶点——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方面,他的本质都在圆满地向着无限生长。相反,魔鬼性的人的表现形式是一条抛物线:快速、强劲地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升,骤然地转变,急剧地跌落。他们的至高点(无论是创作还是生命中的时刻)已濒临跌落点:就是这样,后者神秘地与前者汇合在一起。因此,魔鬼性的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跌落是他们的命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只有跌落才能完成他们的心灵肖像,就像只有下落才能使抛物线这一几何图形得以完成。而歌德的死却只是已完成的圆上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微小部分,对他的生命肖像并无本质的影响。事实上他也不像他们一样死得很神秘、很有英雄的传奇色彩,而是死得平凡安详,像一个德高望重的族长(民间传说徒劳地发明了那句“多一点光”以赋予他的死亡一种睿智的、富有象征性的色彩)。这样的生命结束了,只是因为它已实现了一切,而那些魔鬼性的人的死亡却是一种跌落,一种燃烧的命运。死亡补偿了他们生活的贫瘠,而且还赋予他们一种神秘的力量:谁有悲剧式的一生,谁就有英雄般的死亡。
热情地付出,直至在自然中消亡;热情地保留,在一种塑造自我的意义上——这两种与魔鬼斗争的形式都要求心灵具备最高的英雄主义,两者都带来了精神上的伟大胜利。歌德式的生命之圆满与魔鬼性诗人的创造性跌落——两者都完成了精神个体的相同的、唯一的任务:向生命提出无限的要求,只是不同的类型在各自不同的塑造意义上。如果说我在这里把他们的性格对立地放在了一起,那只是为了通过象征使他们双重的美更加清晰可见,而不是为了引出一个裁决,更不是为了推进那种目前还在流行的、非常乏味的医学解释,说什么歌德是健康的,那些人是病态的,歌德是正常的,那些人是反常的。“病态”这个词只适用于不具备创造性的低等世界,因为一种创造了不朽的病态已不再是病态,而是过分健康、极度健康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使魔鬼性处于生活的最边缘,并且已经探身出去,探进那不可触及且从未被触及的领地,它也仍是人性的内在主体,也仍在大自然的范围之内。因为就连大自然本身,这个几千年前就已经算定了种子生长的规律和胎儿在母腹中的期限的大自然,这个万法之宗,也一样有这种魔鬼性的时刻,也一样有感情的爆发和洋溢,在这种时候——在雷雨中、在旋风中、在泛滥的洪水中——它的力就会危险地扩张,最后到达自我毁灭的极致。连它也会偶尔——当然是在很少有的时刻,就像魔鬼性的人在人类中那么的少有!——中断自己平静的进程,但只有在这种时刻,只有在它的过度之中,我们才能看到它的适度。只有这稀有的时刻才扩展了我们的思想,只有面对强力时的战栗才提升了我们的情感。因此,不同寻常永远是衡量所有伟大事物的标准。而且——即使是在各种混乱的和危险的形象中——创造性也永远都是一切价值之上的价值、一切意义之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