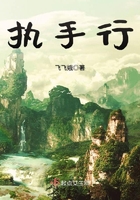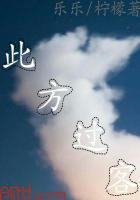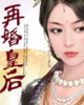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从春秋末期李悝制订第一部系统法典《法经》六篇起,自秦汉以迄明清,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成文法典,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唐律》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最为后人所称道。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渊废除了隋炀帝的《大业律》,命裴寂、刘文静等人依照隋文帝的《开皇律》,修订了一部新律令,并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式颁行,是为《武德律》。《武德律》虽然对《开皇律》有所损益,但基本上一仍其旧,没有太大发展。所以李世民即位后,立即着手对《武德律》进行完善。他采纳了魏徵“专尚仁义,慎刑恤典”(《贞观政要》卷五)的建议,依据儒家的仁政思想,进一步加强“德主刑辅”的立法原则,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法律,积十年之功,成一代之典,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式颁行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法典——《贞观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领衔,以《贞观律》为蓝本,修订并颁布了《永徽律》。稍后,鉴于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李治又下令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的解释。这些内容称为“律疏”,附于律文之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律疏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部法典当时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简称《唐律》)。
《永徽律疏》是唐高宗秉承李世民遗训,在贞观立法原则的指导下,按照《贞观律》的基本精神修订的。直至唐玄宗时,人们仍然认为《贞观律》与《永徽律疏》是“至今并行”的。由此可见,《唐律》实际上是定型于贞观时期,而完善于永徽年间。
《贞观律》和《永徽律疏》的制订和颁行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们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并且影响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各国,乃至在世界法律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大法系。
自唐以降,五代、宋、元、明、清各朝莫不奉《唐律疏议》为圭臬,虽代有损益,但终不敢越出其规范之外。元代律学家柳赟说:“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诏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唐律疏议·序》)
清代律学家吉同钧也说:“论者谓《唐律疏议》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诚确论也!”(《律学馆大清律例讲义·自序》)
由此可见,定型于贞观时期、完善于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在后世法学家的眼中确实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文法典。
(一)皇权与法权
在古代中国,法律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因为它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它头上还有一个最高权威——皇帝。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皇权绝对高于法权。法律之所以被皇帝制订出来,并不是用来约束皇帝本人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臣子和老百姓。正所谓:“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韩非子也说:“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明太祖实录》)
总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民主与法治”的社会。此可谓确论!
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总设计师,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的关系的呢?
对此,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卷五)
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作一种“防民之具”和“辅治之术”,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
不过,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肺腑之言,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从下面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是性质却很严重。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
说白了,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很多将吏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就出台了“恩荫”政策,让烈士后代能够承袭先人官爵。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以此骗取朝廷恩荫。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企图走一条加官晋爵的捷径。
上述这些现象就叫作“诈冒资荫”。有关部门难辨真伪,对此大伤脑筋。针对这些现象,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
敕令颁布后,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后,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
戴胄原本只是兵部的一个郎中,因有“忠清公直”的美誉,不久前刚刚被李世民破格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相当于从一个国防部的小司长突然晋升为最高法院副院长。皇恩如此浩荡,按理说戴胄应该知恩图报、事事顺着李世民的脾气才对,可秉公执法的戴胄却在柳雄这件案子上狠狠地触逆了龙鳞。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种罪最多只能判流放,所以戴胄便对柳雄做出了“据法应流”的判决。这个判决结果虽然是依法做出的,但显然违背了李世民的敕令。
李世民勃然大怒,对戴胄说:“朕早就颁下敕令,不自首就是死路一条,你现在却要依法改判,这岂不是向天下人表明,朕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面不改色地说:“陛下如果直接杀了他,臣无话可说;可陛下一旦把案件交付法司,臣就不能违背法律。”
李世民悻悻地说:“你为了让自己秉公执法,就不惜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戴胄说:“陛下的敕令是出于一时之喜怒,而国家的法律却是布大信于天下!陛下若以法律为准绳,就不是失信,而恰恰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假如不这么做,臣只能替陛下感到遗憾。”
李世民沉默了。
他知道,如果他执意要杀柳雄,谁也拦不住,因为他是皇帝,而且早有敕令在先。可问题是,这么做虽然足以体现帝王的权威,但无疑会大大损害法律的权威。而法律的公信力一旦遭到破坏,朝廷的威信和人君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
思虑及此,李世民立刻转怒为喜,当着群臣的面对戴胄大加褒扬,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贞观政要》卷五)
这是贞观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上富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凸显了皇权与法权的冲突,并且以皇权的妥协告终,最后使得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体现出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对法律的尊重,以及对司法独立的尊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
“柳雄事件”之后,史称“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泉涌;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贞观时代吏治清明、执法公正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要说“天下无冤狱”,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一个王朝拥有像戴胄这种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法官,并且拥有像李世民这种善于妥协、尊重法律的皇帝时,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贞观时代即便不是历史上最少冤狱的时期,起码也是最少冤狱的时期之一。
(二)对生命的尊重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刑法。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刑法,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待死刑的态度。
贞观法治之所以被后人津津乐道,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宽仁慎刑”的理念,以及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
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就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立法思想,以诏令的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了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死刑)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在这种“宽仁慎刑”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的治安形势。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才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因此,对死刑的滥用就是对生命的蔑视和人权的践踏。
相反,对死刑的慎重自然就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刺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
张蕴古被杀不久,李世民经过一番冷静的反省之后,深感后悔。他对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
李世民之所以责怪大臣们没有及时谏诤,正是因为他认识到:即便张蕴古确有徇私,论罪也不至于死,自己显然是在盛怒之下办了一桩错案。
为了汲取教训,杜绝此后类似错案冤案的发生,李世民随即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复奏”。(《贞观政要》卷八)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两天内五次复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
此举是对“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随后,这项“五覆奏”的死刑复核规定就被纳入了《永徽律》,成为正式的成文法。后来的《唐律疏议》对这条法律的执行进而做出了详细解释和严格规定:凡是“不待覆奏”而擅自处决死刑犯的官员,一律处以“二千里”的流刑;即便经过了覆奏,也必须在上级的最后一次批复下达的三天后,才能执行死刑;若未满三日即行刑,有关官员必须处以一年徒刑。
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唐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之严,及其对待死刑的态度之慎重!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在做出“五覆奏”的规定后不久,发现许多司法官员在审判中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文,即使是情有可原的案子也不敢从宽处理。虽然如此执法不失严明,但李世民还是担心这样子难以避免冤案,于是他再次颁布诏令,规定“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贞观政要》卷八)也就是说,门下省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凡是发现有依法应予处死、但确属情有可原的,应写明情况直接向皇帝奏报。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制订一部严明而公正的法律需要执政者具备一种卓越的政治智慧的话,那么在执法过程中既能贯彻“法理”、又能兼顾“人情”,就不仅需要执政者具备卓越的智慧,更需要具有一种悲悯的情怀。
在李世民身上,我们显然就看见了这种悲悯。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又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是把这种难能可贵的悲悯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纵囚事件”。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十二月末,年关在即,李世民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时,想到春节将至,而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顿时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
相信在当时,肯定有很多官员为此捏了一把汗。
因为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时间一到自动回来受死,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这批囚犯的人数足足有三百九十个,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回来,各级司法部门就要忙得四脚朝天了。况且,在把他们重新捉拿归案之前,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不会再次犯案,这显然是平白无故又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欣慰地笑了。
他当天就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
这个“纵囚事件”在当时迅速传为美谈,而且成为有唐一代的政治佳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就有“死囚四百来归狱”之句赞叹此事。
然而,也有许多后人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李世民为了树立自己的明君形象而表演的一场政治秀。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说李世民此举纯粹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他说,这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只能“偶一为之”,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那么“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所以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圣人之法”,“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也就是说,真正好的法律必须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没必要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也没必要用违背常理的手段来沽名钓誉。
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这种“纵囚”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纵囚”。平心而论,“纵囚事件”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刑罚”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已然之罪”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未然之罪”进行预防。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当那些死囚都能遵守“君子协定”,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具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而且整个社会,上自执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义务挽救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其实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于此。当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简单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后者绝对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李世民的“纵囚”举动,实际上就是凸显了上述理念,只不过他采取的是一种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复制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见,“纵囚”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宽仁慎刑”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宽仁慎刑”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废除死刑”的结果。
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
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法治的精神,一度废除了绞刑和斩刑。他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中强调,这是为了“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册府元龟·刑法部》)。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安史之乱”而中辍,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而日本此举,无疑正是受到了唐朝的影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曾经说过:“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
时至今日,限制死刑、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与理性程度的标志。
自从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人权运动的发展,限制并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据有关学者统计,截至2001年,在全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中,在法律上废除死刑和事实上停止死刑适用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占总数的64%;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71个,占36%。在欧洲,“废除死刑”甚至成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此外,美国联邦法律虽仍保留死刑,但已有12个州废除了死刑。
在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中,虽然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废除死刑,但是在“少杀、慎杀、防止错杀”这一司法原则上无疑具有普遍共识。而我国同样是将“慎用死刑和逐步减少死刑”作为刑法的改革方向,并且已经有很多法学家提议,希望我国最迟能在20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实现死刑的全面废除。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尽管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直到今天,“宽仁慎刑”的贞观法治精神无疑仍旧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而这种精神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