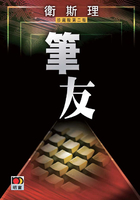迈克尔的父母每年会从莫里斯敦开车来看他们一次,他们是模范客人:逗留的时间从不会太长,也不太短,拿捏得刚好让人舒服;他们不会去找托纳帕克的奇怪之处,或拿这里跟拉齐蒙的家比较,也不会问令人难堪的问题。他们目的明确:来这里看孙女,而劳拉也真心喜欢他俩。
可是露茜的父母却没那么让人放心。除了潦草的圣诞贺卡和劳拉生日时偶尔的一点礼物外,可能两三年音讯全无;然而也可能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他们便不期而至——两位漂亮、夸夸其谈的有钱人,他们的每个眼神、每个手势似乎都透着有意的冷漠。
“原来你们躲在这里,”夏洛特·布莱尼从一辆极长而干净的汽车里钻出来大声说。她在草坪上停下来,四处打量,然后说,“嗯,它有点——不同,是不是?”他们正要进房间时,她说,“我喜欢你们这个小小的螺旋型楼梯,亲爱的,可是我不太懂它有什么用?”
“是个谈话间,”露茜告诉她。
迈克尔觉得岳父比上次见面时老了很多,能人斯图尔特·布莱尼可能还在玩激烈运动,市内玩壁球、乡下打网球;他可能还会高台跳水,在游泳池里游上几圈;但是他一脸迷惑,似乎无法想象这些年时光都哪儿去了。
据说他曾经对露茜说过一次,他觉得迈克尔拒绝她的财产“可敬可佩”;不过,此时,他坐那里,眯眼看着手中兑水的波旁酒,显然想法变了。
“嗯,迈克尔,”他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你那本零售杂志怎么样了?它叫什么来着?”
露茜代他回答了,随意的浅笑让迈克尔心头一热。
“噢,我们差点把它给忘了,”她说,接着解释迈克尔当了自由职业者,听上去仿佛一两个月他几乎无需为《连锁店时代》费心,然后,在意味深长的停顿之后,她说“他又有一本诗集快完稿了”,以此结束了谈话。
“哦,那真不错,”布莱尼先生说。“剧本怎么样了?”
这次迈克尔自己回答的。“嗯,我的剧本运气没那么好,”他说,事实是他的剧本根本没运气可言。早期的几个剧本还在一些非百老汇制作人的桌子上或一叠文件里,但最大的那个剧本,那个三幕悲剧,耗费了他许多心血的那个剧本,只换来经纪人一封草草的收稿信,现在正“四处给人看”——一条漫长而希望渺茫的路。那年夏天,他有时候甚至想把这个剧本交给托纳帕克剧场来演出,但他每次都抑制住自己的这种念头。这年巡回演出公司的导演是个神经兮兮、慌里慌张、没有决断的人,让人没有信心;演员要么是群没有教养、为了资质认证不顾一切的孩子;要么就是些不合格的老演员,年纪总太大,演不好他们的角色。再说,如果他们看了剧本却拒绝的话,那更让人受不了。“戏剧是件非常、非常棘手的事。”他结束道。
“噢,我知道是这样,”布莱尼先生说。“我是说,我想它肯定是的。”
这时,劳拉放学回来,迈克尔知道这意味着这次拜访快要结束了。斯图尔特和夏洛特自己很少承担为人父母之职,所以也别指望他们会对下一辈的孩子表现出多少兴趣。他们假意惊呼一声之后,似乎便没再理这个害羞的大眼睛女孩。劳拉衣服上还沾有青草汁,她就站在他们膝边,离得太近,害得他们为了安全起见,只好高举威士忌酒杯,可笑地伸长脖子从劳拉的这侧换到另一侧,尽量继续大人们的谈话。
布莱尼夫妇刚走,迈克尔紧紧地搂着妻子,感谢她替他回答了她父亲的问话。“你真是帮我解了围,”他说。“太好了。当你——你这样帮我时,真是太好了。”
“哦,”她说。“我这样做既是为你也是为我自己。”他怀中她的身体似乎硬邦邦的,可能是他的手臂有些僵硬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他踩着她的鞋子,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快便分开。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笨拙的一次拥抱。
一个秋日,水泵房门口传来敲门声,汤姆·尼尔森笑着站在门口,穿着那件GI坦克手夹克。
“想不想出去打野鸡?”尼尔森问。
“我没有猎枪,”迈克尔告诉他,“也没有狩猎许可证。”
“见鬼,弄这些又不难。你花二十五块钱便可以买到一把像样的猎枪,许可证更容易。这几天早上我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有个伴更好。我想一个老空中机枪手要打飞鸟肯定了不得。”
这个想法不错——当然也是奉承,所以汤姆·尼尔森一路从金斯莱来到这儿告诉他;迈克尔带他回家,让露茜也开心。他们参加过尼尔森家的好些聚会,尼尔森夫妇也经常到他们家来坐坐聊天;即使这样,任何能保证尼尔森夫妇是他们朋友的事都能让她高兴。
“打鸟?”她说。“这主意好吗?”
“打猎传承古风,夫人,”汤姆·尼尔森说,“而且它能让你走出户外,这是种锻炼。”
一天一大早,迈克尔忸怩地扛起他新买的便宜猎枪,穿过金黄的田野,朝尼尔森所描述的“自然景致”走去,他兴致慢慢提起来了。他玩拳击是出于某些更复杂的原因,除此之外,他很少从事或喜欢过其他什么体育运动。
但是当他们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上坐下来后,迈克尔发现汤姆关心的不是野鸡,他需要的是有人作伴,他想聊的是女人。
上次聚会时,迈克尔可曾留意到那个黑发姑娘?那甜美的嘴、那迷人的胸,真是为她而死都值得!她跟耶鲁大学那个搞艺术史的混蛋同居——难道那不让人心碎吗?最糟的莫过于她似乎还很喜欢那个糟老头。
哦,天啊,再说说伤心事吧:两三周前,汤姆在现代博物馆里逗留好久,想跟那个漂亮可爱的小东西套近乎,她刚从莎拉劳伦斯学院或类似学校毕业,媚眼流波、长腿甜美,他刚说到他是个画家。
“她说‘你是说你就是托玛斯·尼尔森?’可是狗娘养的,那个该死的同性恋馆长偏偏挑了这个时候从房间那头喊我,声音跟笛子一样响:‘噢,托玛斯,过来见见自然博物馆的布莱克·谁谁谁。’老兄,我极不情愿地走了过去。我敢肯定,她以为我是同性恋。”
“难道你不能过后再回头来找她吗?”
“伙计,吃中饭啊,我得同自然博物馆的混蛋一起吃中饭。后来我花了半小时四处找她,可她已经走了。她们总是走掉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的问题是结婚太早,我不是太挑剔:这是家,是家庭,要稳定什么的。”他在两腿间的石头上掐灭了烟头。“可是这些姑娘——这些姑娘真是太那个了。想不想干掉一两只鸟?”
他们真心实意地想打鸟,只是一只也没找到。
转眼就到了猎鹿季节。在帕特南县,散弹猎枪是唯一合法的猎鹿枪支,不允许使用步枪——那些散弹枪的枪管钝钝的,从包得很紧的纸枪筒里戳出来,看着极其残忍,以致许多猎人在跟踪他们的猎物时难以专心。迈克尔和汤姆甚至连三心二意都谈不上,清晨他们在树林间主要是闲谈漫步,或者把枪搁在膝盖上长时间的休息。
“你有没有收到过喜欢你的诗的读者写来的崇拜信?”
“没有。从没发生过。”
“不过那样真好,是不是?某个好女孩爱上你,给你写封让你呼吸急促的信;你回信,约好在哪里见面,精心安排好,要那样可真不错。”
“是啊。”
“我差一点就有这么一次经历,我是说差一点。有个女孩看了我的画展后,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我觉得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也许我们彼此都有话要说。’我处理得很酷,我做得很好。我回了封信,向她要张相片,事情就是这样。相片上的她好像给树叶阴影遮住了半边脸,我猜她是想让自己看上去有点艺术气质,但是她的小眼睛、撅着的嘴、卷曲的头发还是藏不住——我不是说完全像条狗,但至少有一半像。真是失望,老兄,如果我脑子里没有这姑娘的另外一副形象,感觉也不会那么糟。天啊,想象真是捉弄人!”
另一天,尼尔森抱怨说好些日子没有出过远门了,只有一次《财富》杂志派他去画些插图。“通常我很喜欢这类工作,这种工作很轻松,我也喜欢旅行。去年他们派我去南得克萨斯州,为那里的钻井平台画些草图。工作是没问题,麻烦的是有两个家伙负责开吉普车领我四处走走瞧瞧。你知道,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他们一直叫我做‘艺术家’。有一个是这样说话的:‘嘿,查利,要不要带艺术家去五号工地?’或者‘你觉不觉得艺术家今天够累的了?’后来,有一次我们三人在货车休息站之类的地方吃中饭,他们谈起他们的家庭,我无意中提到我有四个儿子。”
“哇!你真应该看看他们的脸,他们的下巴都要掉了!仅听我说有‘四个儿子’,一切马上天翻地覆。问题在于,你知道,很多这种人觉得‘艺术家’一词就等于‘同性恋’,你没法怪他们。不管怎样,从那时起,他们对我好得不能再好。晚上给我买酒,叫我‘汤姆’,问我关于纽约的各种问题,对我讲的笑话大笑不已。我觉得他们甚至打算给我找个姑娘,可惜没时间了,得去赶该死的飞机。”
猎鹿季节的最后一天,他们回家吃早饭时,像疲惫的步兵双肩扛着武器保持平衡一般慢慢吃力地走着,汤姆·尼尔森说:“啊,我真搞不懂我小时候怎么回事,我发育太迟。看书、打架子鼓、玩那些锡兵——那时候我本该外出找女人做爱的,可我却在干那些事。”
一天晚上,露茜洗碗的时间比平时要长,当她从厨房里出来进了客厅后,她将一缕耷拉下来的头发抚到脑后,这模样说明她有个困难的决定要宣布。
“迈克尔,”她开口道,“我想好了,我该去看心理医生。”
迈克尔的心揪了起来,就像完全接不上气。“哦?”他说,“为什么?”
“有些事情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对他说。“如果可以解释,我会解释的。”
他又模糊想到以前在波士顿博物馆里讨论抽象—印象派画作时她的不耐烦。“如果他真能说出来,那就没必要画它了。”
“好吧,但我想问,主要是因为婚姻吗?”他问,“还是另有其他问题?”
“它是——各种问题都有。有目前的问题,还有些是自我小时候起就有的问题,只是我现在觉得我需要帮助而已。金斯莱有个叫费恩的医生,应该还不错;我已经跟他约好了这个星期二见面,我想一周去两次。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有点可笑。噢,当然没必要为费用担心,我会用我自己的——你知道——我自己的钱。”
于是,星期二的下午,他只好站在窗前看着她开车离去。可能她很快就会回来,被心理医生的问题或态度弄得很不开心;更大的可能是,从现在开始,她每周二、周五都会消失在一个秘密、不便告人的世界;她会离他越来越远,她会蒸发掉,他会失去她。
“爸爸?”有一次就他和劳拉两人在家时,劳拉问他,“什么叫困境?”
“哦,它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比方说,你可能想出去跟安妮塔·史密斯玩,可是电视里有很好看的节目,你又有点想待在家里看电视,那你就处于某种‘困境’之中,明白了吗?”
“噢,”她说。“是的。这个词不错,是不是?”
“肯定啦,你能在很多事情上用到它。”
帕特南县下了最大的一场雪,安·布莱克用了四五天才请人把车道打扫干净。在这种清晨,迈克尔和劳拉手牵着手,一路哆嗦着、笑着,吃力地在积雪中穿行,走到校车停靠的地方。他们总是有哈罗德·史密斯和他的孩子们作伴。哈罗德背着他的脑瘫儿子基斯,说“你一点没轻,还这么死沉,伙计”,女儿们跟在后面。他俩把孩子们在车站上安顿好,孩子们沾着雪花的围脖、僵硬的连指手套、橡胶靴,看起来一副凄凉景象。然后该哈罗德挥手说再见了,他大步朝一里半外的火车站走去——如果那天碰巧是去《连锁店时代》的日子,迈克尔会跟他一道走。他们走得很快,偶尔停下弯腰,在雪中擤擤鼻子,他们像两个共患难的同志在交谈。
“婚姻很搞笑,迈克,”有一次哈罗德说,大风把他说话时哈出的热气横扫开来。“你跟她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却不知道你娶的这个人到底是谁。真是个谜。”
“你说得没错,”迈克尔说,“真是这样。”
“当然,大部分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关系:你混日子,一直混到孩子们出生、长大,转眼间,你能做的只有尽量让自己别睡着,到该睡觉时再去睡。”
“是啊。”
“有时候,你看着这个姑娘、这个女人,你想: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我?”
“是啊,我懂你的意思,哈罗德。”
到1959年春天,迈克尔觉得他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他出版的第二本诗集让人失望——评论不多,仅有的几个评论也不冷不热——但是现在他开始着手写的新诗集,看上去会是极为出色的一本。
有几首新诗很短,但分量并不轻,结构也很紧凑。他独自一人在水泵房时,大声朗读好一些的几首诗,觉得很快乐。有时候,他为它们而哭,丝毫不觉难为情。这本诗集最后的那首长诗、那首浓郁而激情洋溢的长诗——可跟戴安娜·梅特兰说她最喜欢的那首《坦白》相提并论——离写完还早,不过他已写下强有力的开首几行,对接下来该怎么写心中也大致有数。他自信只要这个夏天进展顺利,到九月底就能写完。刚开始节奏可能缓慢,随着纷繁复杂渐增,节奏也越来越快。这首诗探索的是时间、变化与衰亡,最后,于隐约微妙中,暗示着一段婚姻的破裂。
每天晚上他从小棚子走回家时,当露茜在蒸汽迷漫、香气四溢的厨房里忙碌,他端着威士忌坐在客厅里时,脑子里都没停止过寻章觅句。
唯一令他分神的是咖啡桌上摆着的一本鲜艳的紫白色书。这书摆在这儿好几天了,书名叫“如何爱”,作者是德瑞克·法尔,看封底的作者照,原来是个秃头男,双眼热切地直视镜头。
“这是本什么书?”当露茜走进来布置饭桌时,他问。“性爱手册?”
“才不是,”她告诉他。“是本心理学著作。德瑞克·法尔是哲学家,也是职业心理医生。我觉得你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是吗?为什么是我?”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天,客厅里所有的声音、活动都覆盖在星期天的报纸下了。迈克尔从《纽约时报书评》中抬起头来说,“露茜?你知道那个叫德瑞克·法尔的家伙连续二十五周保持在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吗?”
“我当然知道。”她在房间那头翻着时装广告,然后望着他说,“你觉得畅销书全是垃圾,是不是?你向来这样看。”
“嗯,不全是。不对,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不过,当然大部分这类东西都是垃圾,对不对?”
“我觉得根本不对。如果一个人写的东西能吸引无数人;如果他的思想、他的表达方式正是许多人想要的,或需要的——难道这不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吗?”
“哦,得了吧,露茜,你知道得很清楚。问题是从来就不是人们‘想要什么’或‘需要什么’——而是他们愿意忍受什么。同样讨厌的商业法则决定了我们在电影、电视中能得到什么,低级趣味主导着大众品味。天啊,我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他抖抖报纸,回到看报状态,清楚地表明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沉默了十到十五秒后,她说:“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一直都了解你对一切的看法;那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从来不同意你的看法——从来没有过——而最可怕的是直到最近几个月我才发现。”她腾地站起来,一副挑衅的样子,但同时又奇怪地显得很害怕。
迈克尔站起来,书评版滑落到地上,“喂,等等,他妈的等一下,”他说,“这就是你跟费恩医生这些个舒服的亲密会谈得出的结论吗?”
“我就知道你会得出这么龌龊的结论的,”她说。“正好相反,你完全错了——我甚至拿不准还要不要去见费恩医生——可是随你的便,你爱怎么想怎么想。现在你能闭嘴吗?”
她飞快走进厨房,而他紧跟其后。“我会住嘴的,”他对她说,“要等我他妈的想闭嘴的时候才闭嘴,不是现在。”
她转身面对他,上下打量一番。“噢,这可真奇怪,”她说。“可真够有意思的,我是说真够吃惊的。我发现我原来一直讨厌听你那套《肯雍评论》[15]般宝贵的精英言论——天啊,说我现在不想听你谈‘诗歌’或‘戏剧’,可能言之过早——但现在我只知道我讨厌的是你的声音本身。你听懂了吗?我再也受不了你的声音,再也不想看你那张脸!”她拧开水池上方的两个水龙头,拧到最大,开始洗碗。
迈克尔走回客厅,在洒落一地的星期天的报纸中踉跄踱步。没有比这再糟了;这已糟至极点。以前吵嘴时,有时他会尽量留点时间让她一个人待着,让她在沉默中慢慢恢复,觉得抱歉,可是这条老规矩不再管用了,而且,他还有话没说完。
她弯腰对着热气腾腾的泡沫水,他在她身后站定,保持一段距离。“你从哪里弄来的‘宝贵’?”他问道,“从哪里弄来的‘精英’?又从哪里弄来的《肯雍评论》?”
“我觉得我们最好马上住嘴,”她告诉他,“劳拉会听到的,她可能在楼上哭了。”
他摔上厨房门,走出家来,一路经过本·杜恩那夸张的花田,但在书桌前坐下后,他已无法握笔,什么也看不清。他只能把半只拳头塞在嘴中,鼻子喘着粗气,努力去理解真相已经大白。结束了。
他三十五岁,一想到将再次独自一人生活,他怕得像个孩子。
露茜也不好受。她在水池边洗完碗,将湿洗碗巾往墙上的钩子上用力一搭,钩子却从墙上掉下来,廉价的灰泥墙上露出四个可笑的小伤疤。这间凑合着用的厨房里没有一样东西好使;在整个将就凑合的家里,在这个二手的、二流的地方没有一件东西对头。
“我还要跟你说件事,”她对着墙壁恶狠狠地低声说。“当诗人就该像狄兰·托马斯,当剧作家——哦,天啊!——当剧作家就该像田纳西·威廉斯[16]!”
打记事起,劳拉·达文波特就想要个妹妹。有时候,她想,如果要她在有个弟弟或干脆什么也没有之间选的话,那弟弟也行,但她最想要、连做梦都想要的是有个妹妹。她甚至很久以前就给她取好了名字——梅丽莎——她经常跟幻想中的妹妹说上几小时的话。
“你准备好吃早饭了吗,梅丽莎?”
“还没。我还没梳好这讨厌的头发。”
“哦,过来吧,我来帮你。我最会梳打结的头发,只要一秒钟就好。喏,好些了吗?”
“啊,是的,好多了。谢谢你,劳拉。”
“不客气。嘿,梅丽莎?吃完早饭后,想不想去史密斯家?要不你就在这儿玩洋娃娃?”
“我不知道,我还没想好。我待会儿告诉你,行吗?”
“行。你知道,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干点别的。”
“什么?”
“我们可以去野餐的地方,看看我们能不能爬上那棵大树。”
“你是说那棵真正的大树吗?喔,不行。我害怕,劳拉。”
“怎么会?你知道我也在那儿,如果你脚滑掉下来的话,我会接着你的。为什么你总是怕呢,梅丽莎?”
“因为我没有你那么大,这就是为什么。”
“你甚至怕学校里的那帮孩子。”
“我没有。”
“你怕的——二年级学生不过是群娃娃;人人都知道。如果二年级的你都怕,我简直不敢想象你到四年级该怎么办。”
“那又怎么样?我打赌你怕四年级的学生。”
“这可是我听过的最可笑的话了。我有时候是有点害羞,但那并不是害怕。害羞与害怕完全不同,梅丽莎,记住了。”
“嘿,劳拉?”
“什么?”
“我们别再吵了。”
“嗯,好的。但是你还没说你今天想干什么。”
“噢,没关系。你说了算,劳拉。”
还有些时候,原因不明,一连好几天或好几周梅丽莎消失不见了。可能是劳拉在想些有意思的新东西,准备告诉梅丽莎,或者在计划些新事情,要跟梅丽莎一起做;她甚至可以一半以梅丽莎的身份,小声问问题答问题,但在那些时候,她不由自主地、难为情地发现,她这是在自言自语。而且一旦梅丽莎离开,似乎再也不会回来。
劳拉九岁那年,一个温暖的九月下午,事情这样发生了。放学后,她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仔细梳着一个小洋娃娃长长的褐发,露茜站在楼梯脚下,叫她:“劳拉?你能下来一下吗?”
她抱着洋娃娃和梳子出来,站在楼梯顶端问:“为什么?”
露茜奇怪地有点局促不安。“因为我和你爸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亲爱的,要跟你讨论,这就是为什么。”
“噢。”劳拉慢慢走下来,进了客厅,她开始明白这准是件极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