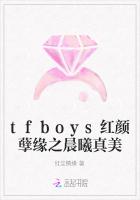不,事情开始变得可怕。今天早上大约十点,格雷高瑞尤斯太太又站在了我的房间里。她看上去苍白而凄惨,眼睛大大地瞪着我。“出什么事了?”我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小声地回答:
“昨夜他强奸了我,跟强奸能做的一样。”
我坐在写字台边,手指拨弄着一支钢笔和一页纸,似乎打算写下一个处方。她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可怜的孩子,”我说,仿佛自言自语。我找不到其他可说的。
她说:“我生来是被蹂躏的。”
我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开始陈述。他在半夜里弄醒了她。他睡不着,他哀求、痛哭。他说他的幸福在危险之中。如果她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他不知道究竟还将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做这事是她的职责。职责先于健康。上帝会帮助他们,上帝总会让她恢复健康。
我呆坐着,惊得说不出话。
“那么,他是个伪君子吗?”我问。
“我不知道。不,我想不是。但他有这习惯,凡事都拿上帝来说话,这对他最合适。他们总这样,我自然认识好多牧师,我恨他们。但他并不是伪君子,相反,他总是认为他的宗教的正确显而易见,他倾向于认为那些拒绝宗教的人是骗子和恶人,故意说谎来给别人带来毁灭。”
她平静地说着,只是声音中带了小小的颤抖。她说的这些某种程度上让我吃惊;此前我不知道这小女人思考过,不知道她能判断一个男人,如她在谈论的这样的男人,这么清晰的、局外人般的,虽然她对他定然是感到致命的仇恨和深深的厌恶。我感觉到了那厌恶和仇恨,在她声音的颤抖里,在每一个她吐出的字眼里;并且这也传染给了我,当她述说完事情的全部:她想起身,穿衣服,走出去,走到大街上待一整晚,直到天明;但他死死抓住了她,他力气大,他不让她逃脱。
我感觉自己在发热,太阳穴突突直跳。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几乎害怕会大声说出我的念头,一个声音在齿缝间摩擦:当心,牧师!我答应了这小女人的,这有着明亮丝绸般头发的女人花,我会保护她抗拒你。你给我小心,你的命在我手里,我愿意,我也能够在你祈求前送你到极乐天地。当心,牧师,你不了解我,我的意识和你的一点不同,我是我自己的裁判,你根本就没察觉过有我这样一种人存在!
她是果真坐在那里,听见了我隐秘的念头吗?我打了个寒颤,突然听见她说:
“我但愿能杀了他。”
“亲爱的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我带着一丝微笑回答,“自然,这只是一种惯用措辞。但即便如此,像这种话还是不该采用的。”
我的话是到了嘴边的:“绝不能说这样的话。”
“但是,”我几乎是一口气地说下去,以便转换话题,“告诉我,您究竟是怎么会嫁给格雷高瑞尤斯牧师的呢?来自父母的压力,还是坚信礼时期的一点狂热?”
她摇摇头,像打寒颤似的。
“不,全不是那样,”她说,“一切来得很怪,全不是您能猜测和理解的。我当然从没爱过他,一丁点也没有。连少女对坚信礼牧师通常会有的爱慕也没有——全不是那样!但我会试着告诉您,解释全部。”
她在沙发的角落里蜷得更深,耸着肩像个小姑娘,目光越过我,迷茫地朝着外头不确定的什么,开始了叙述:
“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非常快活。当我回想那段时光,一切跟童话似的。大家都喜欢我,我也喜欢大家。然后就到了那段年龄,您懂得的。起初并没有变化,我还是特别开心,甚至比以前更开心——直到我二十岁。一个年轻姑娘也有对性的渴望,这您能懂,但在青春的早期,这带给她的只是快乐,至少在我是如此。血液在我耳里歌唱,我自己也唱——不停地唱,在家做杂务时唱,走在街上我也总轻轻哼着曲子……并且我总是坠入情网。我生于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但我没觉得被亲吻是什么了不得的罪。假如我爱上了某个小伙子,而他亲了我,我就随他去。我知道还有另一件事是得小心的,那是罪,但那对我来说模糊得很,还离我很远,我并没受什么诱惑,不,一点没有。我甚至不明白,那怎么就能诱惑人呢,我以为那只是人结婚后,又想要孩子时必须服从的,那事儿本身并没有意义。但当我二十岁时,我深深爱上了个男人。他模样俊,人也好——至少当时我觉得是,现在当我想起他,我还是这么认为。是的,他一定是那样的——后来他和我年轻时的女友结了婚,他让她过得很幸福——那是个夏天,我们在乡间遇见的。我们接了吻。有一天他把我带到林子的深处,在那里试图侵犯我,他几乎就得了手。哦,如果他得了手,如果我没挣脱着跑开,一切会和如今多么不一样!也许我就和他结了婚——至少我决不会同我现在的丈夫结婚。我兴许有了孩子和一个家,一个真正的家;永远不需要成为一个偷情的妻子——但我因害怕和羞耻而完全发狂,我挤出他的双臂,跑开了,拼命地跑了。”
“接下来的是段可怕的日子。我不愿再见他,不敢见。他送我花,写了一封接一封的信求我原谅。但我以为他是坏人;我不回他的信,将花儿从窗口扔了出去——但我想他,不停地想。这时我想的已不只是他的吻了,这时我知道了什么是诱惑。我感觉好像自己已发生了变化,虽然什么也没做。我幻想人们能在我身上看出什么来。没人知道我受的煎熬。在秋天,当我们回到城里,有一天我独自走在黄昏里,风在房子周围打转,有雨点儿不时地飘落。我拐进了那条街,我知道他住那儿。经过那幢房子,我停下脚步。能看见他的窗户点着灯,他在灯下,埋头看一本书。这像磁铁般吸引了我,我想,和他一起待在屋内该有多好。我闪进大门,上了台阶,走到一半,在那里我回转了身。”
“如果那些天里他给我写了信,我是会回答的。但他已疲于写那始终得不到回音的信了,然后我们再没见面——好多年都没见到。当然那时一切都已变得那么不同。”
“我自然跟您说过,我是在虔诚的宗教氛围中被教养的。现在我更是完全陷在宗教里,我成了护士学生,但又不得不中断,因为我变得有些虚弱;我就返回了家,跟从前一样做些家务,梦想着,期待着,并且祷告上帝将我从梦想和期待中解脱出来。我觉得那发生过的一切难以忍受,必须有些改变。于是有一天,我从父亲那里得知,格雷高瑞尤斯牧师已请求过我做他的妻子。我站在那里,完全惊呆了。牧师从没有以这种方式接近过我,让我感觉到什么。他和我们家来往很久了,母亲崇拜他,而父亲,我想父亲有些怕他。我进了自己房间哭了。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我一直觉得牧师身上总有些什么让我很排斥;我相信一定是这使我决定说同意。没人强迫我,没人劝说过我。我以为这是上帝的意愿。人们让我学会以为,上帝愿意是这样,上帝的旨意总和我们自己的相悖。就在前一夜,我还在床上祷告上帝给我自由和安宁。如今我相信,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以他的方式。我觉得上帝的意愿清晰地在眼前闪现。我想和这男人在一起,一定能熄灭我的欲望,消除我的梦想。我感到,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上帝将这一切安排给了我。并且我确信,他一定是个好人,因为他是牧师。”
“一切和料想的自然完全不同。他并不能消除我的梦想,他只将它们弄脏。他慢慢摧残了我的信仰,这是唯一我可以感谢他的事,因为我并不想回归信仰。信仰,当现在回想这一切,我只觉得可笑。所有人们向往的,觉得愉悦的,都是罪。一个男人的拥抱是罪,如果人向往这,喜欢这;倘若遇到丑陋和讨厌的,灾祸、折磨、恶心事——假如人不愿接受那些,那是罪!格拉斯医生,您说,这难道不古怪吗?”
说了这么多,说得她灼热和激动。我透过眼镜朝她微微颔首:
“这确实古怪。”
“或者您告诉我,您是否认为我现在的恋爱是罪?这不仅仅是快乐,或许更多是苦闷,但您是否以为那是罪呢?如果那是罪,那我所拥有的一切全是罪,因为我不能在我所有的一切中找到比这更好、更有价值的。——但或许您对我感到吃惊,坐在这儿跟您说这些。我当然有另一个人可以说。但当我们见面,时间是那么短促,他跟我说得很少。”——她突然脸色绯红,“他很少和我谈这些,而这是我考虑得最多的。”
我平和地默不做声地坐着,我把头埋在手中,透过半合的眼帘看她,那里,她坐在沙发的角落,茂密的金发下是盛开的玫红,处女般柔滑的脸颊。我想:如果她是对我有了那样的感情,那我们也不会有多少时间来说这些。她再开口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径直走过去,用一个吻来封上她的嘴。但她现在默默地坐着。通往候诊室的门半开着,我听到了走道上我的女管家的脚步。
我打破沉寂:
“但是告诉我,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您就没想过离婚吗?您并不是因什么经济上的需要和您丈夫捆在一起——您父亲给您留了财产,您是他唯一的孩子,而您母亲还健在,境况不错。不是吗?”
“哦,格拉斯医生,您不了解他。离婚——一个牧师!他永远不会同意,永远!不管我做了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他情愿‘饶恕’我七次和七十次[1],挽救我,或尽其他一切的可能……他甚至会在教堂里为我祷告。——不,我生来就是被蹂躏的。”
我站起来:
“那么,我亲爱的格雷高瑞尤斯太太,您现在希望我为您做什么呢?现在我看不到其他的出路。”
她茫然地摇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别的。但我估计他今天会来您这里,看心脏,昨天他提起过。您不能跟他再说点什么吗?但您自然不能让他觉察我今天来过这儿,和您说到这事?”
“那么,看情况吧。”
她离开了。
她走了以后,我拿了本医学杂志来转移思路。但这是徒劳的。我看见她一直在我眼前,耸着肩蜷在沙发的角落里,讲述她的命运,讲述事情怎么会到了这一步,她走偏了路,到了这世界疯狂的边缘。这是谁的错?是那在某个夏日,在森林里想引诱她的男人的错吗?唉,在这世上,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使命,除了引诱还能有什么,可能在森林,可能在新娘床上,然后全面地帮助她、支持她,像遵循诱惑一样。这到底是谁的错——是那牧师的吗?他不过对她有了欲望,像成千的男人对成千的女人有了欲望,对她的欲望是另外奉送了原则和光荣的,用他滑稽的术语来说——而她没弄明白也并没理解,只被她成长于其中的古怪而混乱的想法左右着,就同意了。她跟他结婚时并不清醒,她在睡梦中做了这一切。梦里自然会出现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虽然在梦里,它们以完全自然和平常的姿态出现。但当人醒来,记得梦里的一切,人是震惊的,不是笑出声来,就是怕得发抖。现在,她醒了!而她的父母毕竟知道婚姻是什么,竟同意了,也许他们甚至是觉得高兴和受宠若惊的——他们当时清醒吗?至于那牧师本人:他就一点不觉得,自己的行为里有不自然、粗鄙和不体面的成分?
我从没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伦理道德不过是只旋转木马。我其实从前就知道这一点,但我总以为这旋转的时间会是几百年或几万年——现在这时间在我看来却只有几分甚至几秒。一道微光在我眼前摇曳,就像女巫舞蹈中唯一的指引,我又听见一个声音在我的内心,一个声音在齿缝间摩擦:当心,牧师!
完全正确,诊疗时间里他果真来了。从开着的房门看见他在候诊室,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隐秘的喜悦。在他之前只有一个病人,一个老妇人要更新处方——然后就轮到他进来了。大衣下摆铺展着,他以沉思的体面姿态坐在沙发角落,就是几小时前他妻子蜷缩过的地方。
和往常一样,他自然是从谈论一堆琐事开始的。他一直和我谈圣餐问题,心脏病简直是顺便提及。我得到个印象,似乎他果真要知道我作为医生对圣餐的看法,是否那有害健康。近来所有的报纸都在讨论圣餐,作为讨论了大湖怪兽后的一点变化。我没跟踪这场讨论,时不时地,我也浏览过一篇半文,但远未达到对这话题了解的程度。于是,牧师得把问题给我摆出来。如何对付领圣餐时的感染——这是问题所在。牧师非常遗憾这样的问题会被提出,但问题既已提出了,那就得回答。有好多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最简单的是,每个教堂准备些小杯子,教区执事在每次领圣餐后在圣坛里清洗。——但那一定很贵,或许钱少的乡下教区就不可能拥有足够多的银杯。
我随意地评论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宗教的兴趣正稳步增长,既然大量的银杯被用在每场自行车赛上,要找到用于宗教目的的特制银杯,不该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我可想不起来圣餐制度里有什么和银相关的字眼,但这点意见我保留给自己。“人们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牧师接着说:“就是每一个领圣餐的人自己带杯子来。但如果有钱人带了艺术装饰的银杯,而穷人带了喝烈酒用的玻璃杯,那看起来像什么呢?”
就我而言,我以为那看来丰富多彩,但我保持沉默,让他继续说下去。“然后,”他继续说,“有一个摩登牧师,自由思考的那种,他建议受难者的血可以用胶囊方式来饮用。”开头我以为我听错了,“胶囊,像蓖麻油?”“是的,一句话,用胶囊。最终,一个皇室牧师发明了一种绝对新型的圣餐杯,拿了专利,成立了一家合资股份公司。”牧师对我解释了这发明的细节,那似乎多少是沿着和魔术师的杯子、瓶子同样的思路来设计的。至于格雷高瑞尤斯牧师,作为他,他是正统的。他一点也不是思想自由开阔的人。因此这些消息全都给他带来深刻的疑虑——“但这么着不也还是有细菌,那该怎么办?”
细菌——听他吐出这个字眼,我心头突然一亮。我完全清楚地记得这语调,我记得以前听他谈起过细菌,显然,他患着一种叫“细菌恐惧症”的毛病。清晰地,在他眼里,细菌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立于宗教和世界的伦理秩序之外。这是因为它们是那么新。他的宗教则是古老的,大约一千九百年之久,而世界的伦理秩序,至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初,从德国哲学和拿破仑的垮台开始。但细菌,在他的老年来攻击他,完全毫无准备。照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并不是直到最近,细菌才开始了它们肮脏的行动,当然他此前从未被卷入。从我们能判定的来看,在客西马尼园最后的晚餐的饭桌上传递的陶罐里,也一定有大量的细菌。
无法断定,他更多是一只绵羊还是一头狐狸。
我转身背对着他,任他说下去,同时整理了一点仪器橱里的东西。我随意地叫他脱了大衣和背心;关于圣餐的问题,我没再多加思考,决定选择胶囊法。
“我承认,”我说,“刚开头这方法连我也觉得抵触,虽然我没法夸口自己是特别虔敬。但再仔细一想,所有的疑虑也就全部自行打消了。不错,圣餐的精髓并不在面包和葡萄酒,甚至也不在教堂的银餐具,是在信仰。而真正的信仰自然不可以被诸如银杯或胶囊这样外在的事物影响……”
说着最后一句话,我将听诊器放在他胸部,要他保持平静,并听了会儿。我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只是心跳不太规则,年纪大些的人若是晚饭习惯于吃得比需要的多,爱在沙发上躺着打个盹,有这样的症状是常见的。兴许有一天会来个心脏病发作,这谁也说不准,但这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不是特别有威胁的可能。
可我已拿定主意,要把这诊断弄成一桩严肃的事情。我听了比需要的要长得多的时间。我移了移听管,敲了敲,又听下去。我察觉到这一切是如何让静静地被动坐着的他开始焦虑——他当然习惯于不间断地说话,在教堂、社团、他自己的家里。他明显有那才能,不难推想,正是这小小的才能首先引领他走向了他的职业。他有点怕诊断,也许他情愿继续关于圣餐的讨论,然后突然看看时钟,冲向大门。但我已将他按在了沙发的角落里,我不放他走。我听了,保持着沉默。自然,我听的时间越是长,他的心脏就越是不好。
“严重吗?”他终于问道。
我没立即回答,我来回踱了几步。一个计划在我内部发酵。计划本身很小、很简单,但我不习惯于诡计,所以我犹豫着。我犹豫还因为,这计划全部或部分地立足于他的愚蠢和无知——他是否真的够蠢,我究竟敢不敢?这是否过于粗暴?他会看穿我吗?
我停止了踱步,用我非常锐利的医生的目光朝他注视了几秒。那灰白的胖短脸打着懦弱、虔诚的褶皱。但我捕捉不到他的目光。他的镜片上只反射着我的窗户、窗帘、印度橡胶树。我决定要大胆。他可能是绵羊,也可能是狐狸——我想,但一只狐狸也到底比一个人要愚蠢许多。人可以不担惊受怕地和他玩那么一会儿吹和骗——他喜欢吹和骗的方式,明摆着的事;我在他询问后的苦思状踱步和长时间沉默已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已经软下来了。
“真奇怪,”我终于嘀咕道,就像自言自语。
我再次靠近他又听了一次:
“对不起,”我补充道,“我得再听一会,以便确定我没搞错。”
“嗯,”我终于说道,“据我今天听到的,牧师的心脏可不那么好。但这不是通常所谓的不大好。今天这情况是由一些特别原因引起的!”
他匆忙地试图在脸上做出一个疑问的表情,但这没奏效。我立即看到,他的不好的自我感觉已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动了动嘴巴,要说些什么,也许要问我,是什么意思,但他说不出,只咳嗽了几声。他也许想避免进一步的说明——但我现在可不肯。
“让我们彼此坦率,格雷高瑞尤斯牧师,”我开口道。这样的开场白让他绝望。“牧师一定没忘,几星期前我们有过的谈话,因为您太太的健康问题。我并不想提什么不文雅的问题,关于牧师在我们的谈话后如何做了处理。但我只想说,如果当时我知道牧师的心脏状况,我会说出允许我提那建议的更重要的理由。对您太太来说,这牵涉到她的健康,但对牧师自己来说,这牵涉到性命。”
我说这话时,他看来很可怕——有那么种颜色涌在他脸上,不是泛红,是绿和紫。他那样子太丑陋了,简直不堪入目,我不得不转开视线。我打开窗,好让肺里进点新鲜空气,但外头几乎比里头更压抑。
我接着说:
“我的处方是简单和明了的:就是分房睡。我记得牧师不喜欢这样,但这没办法。不仅仅是在这一场合的终极快乐会导致严重的危险,避免一切会让欲望兴奋的事也十分重要。——是的,是的,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会说您是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个牧师,但不管怎样,我是个医生,我有权利坦率地和病人说话。并且我不觉得我在越过理性的界限,如果我指出,对一个年轻女人的持续接近,特别是在夜间,这对一个牧师和对其他平凡男人的效果是一样的。我在乌普莎拉学习过,我在那里接触到不少神学人员。我并没有获得这样一种特别的印象:对神学的学习比其他更适合于帮助年轻身体抵御欲火。至于年龄,对了,牧师多大了?五十七岁。这是个临界的麻烦年龄。在您这年纪,欲望和从前差不多大,但满足度却在报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当然,我承认,看待人生的方式多种多样,价值观也多种多样。如果我是和一个老浪荡子说话,我自然会准备好从他那儿听到,在他是很合乎逻辑的回答:操他妈的!光为保命放弃给生命带来价值的东西一点没意义。但我自然知道,这样的论调对您的世界观来说是完全奇怪的。作为医生,我在这种场合的职责是指明和警告——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我确信现在牧师已明白这有多严重,这是全部所要做的。我很难想像如已故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或更近些的菲利·福尔总统[2]那样倒毙会是牧师您的趣味……”
我说这些时避免看他。但当我说完,我看见他坐在那里,用手遮盖着双眼,而他的嘴唇在动。我猜到,多过听见他在说:我们的父,那在天堂的、神圣的、您的名字……不是将我们带向诱惑,而是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
我坐在写字台边,给他开了点洋地黄。
把处方递给他时,我补充道:
“在这么个大夏天里一直待在城里对牧师您可不利。一个六周的水浴旅行会很有好处,泊拉或者热内比[1]。但那样的话,当然,牧师得一个人去。”
注释:
[1]圣经中有人问耶稣,原谅一个得罪他的兄弟七次是否足够,耶稣说,是要原谅七十个七次。
[2]弗朗索瓦·菲利·福尔(Francois Félix Faure,1841—1899),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六任总统(1895—1899)。1895年在意料之外当选法国总统,使左派人士大挫。1899年2月16日猝然逝世。
[3]泊拉(Porla)和热内比(Ronneby)都是夏天的度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