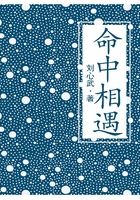一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1940年5月24日生于列宁格勒维堡区图尔教授的医院[1]。按东正教历书,5月24日是创造斯拉夫字母的圣徒基里尔和梅福季的纪念日。不过,成长于被同化的犹太人家庭的诗人到成年时才知道,而这时他早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亲爱的基里尔字母”联系在一起了。
彼得堡是世界大城市中最北边的。布罗茨基一生怕热,夏天喜欢去北方,那里有松树、花岗岩、苔藓、灰色的天和灰色的水。他总是渴望在靠近大河或大海的城市生活。
大战开始,父亲参军以后,母亲带着一岁的儿子离开父亲在环形排水池与瓦斯大街(旧彼得戈夫大街)交会处的家,迁往离自己亲族较近的地方,住在主显圣容大教堂后面。布罗茨基母子在那里住到1955年。布罗茨基已是少年的时候,他们迁往主显圣容广场斜对面的装饰成“摩尔塔尼亚”风格的很大的出租屋。布罗茨基住在他后来所描写的“一间半房间”里,直至1972年离开俄罗斯。潘捷列伊莫诺夫街通往布罗茨基生活和成长的主显圣容广场。这条街的起点是夏园附近的小喷水池,那里有一座桥,栏杆装饰着佩尔修斯的盾牌和墨杜萨·戈尔贡的脸。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儿童读物中讲了佩尔修斯的故事。墨杜萨·戈尔贡的头上是一大堆蠕动的蛇,那就是她的头发,样子太恐怖了,人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不过佩尔修斯不但勇敢,而且很狡猾。他迫使墨杜萨看到她自己在打磨得像镜子一样的盾牌上的映像。童年时读神话就像读童话故事:有趣、快乐、可怕。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神话实际上是在阐述生活,暗示在神话的表面下所隐藏的内涵。“……桥上戈尔贡的铁铸的脸/在我看来是那些地方最正直的面孔”(《五周年》),——多年后布罗茨基在远离故土的地方这样回忆道。那时他已是作家,“可怕的镜子”的主题经常出现于他的诗作和随笔。
布罗茨基对诗感兴趣较晚。大约是十七岁开始写诗。他的诗开始表现出独创性特征时,他已经二十岁出头了,但此后他就非常迅速地提高了写作的技巧。写于1961年还充满了青春期的模糊冲动的长篇叙事诗《游行》(“神秘剧”),写的是居住着文学人物的城市。在列宁格勒秋天的街道上漫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梅什金公爵,勃洛克的阿尔列金和科隆宾娜,亚历山大·格林而非茨维塔耶娃的克雷索洛夫。
此时这些不朽的人物形象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白银时代的彼得堡文学的抒情主题和哲学题材一起,被逐出允许阅读的范围已有三十年:城市像一座迷宫,失去上帝的人们在其中迷失了方向;城市的虚构性;城市作为世界性的恶的化身。与彼得堡传统的决裂之所以发生,众所周知,与其说是文学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文学演变被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警察措施所打断。俄罗斯优秀文化的自由发展在20年代中叶彻底中断,因而斯大林后的第一代人把过去的三十年看作祖国历史中的一个巨大的窟窿,于是很自然地力求重建不同时代之间的联系。年轻的布罗茨基多半是直觉地这样做了。他的作为的真正意义,老一辈人从一旁看得更清楚。在巴黎的文学批评家В.В.魏德列在长篇概论《彼得堡的诗学》的末尾有一段话讲到布罗茨基:“我知道,他生于1940年;他不可能记得。然而在看他的作品时,我每一次都在想:不,他记得,他透过生生死死的迷雾记得1921年的彼得堡,基督1921岁时的彼得堡,在那个彼得堡,我们埋葬了勃洛克,却未能埋葬古米廖夫。”[2]
在苏联的社会结构中,布罗茨基的家庭属于“职员”范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罗茨基(1903—1984)是摄影记者,玛丽亚·莫伊谢耶夫娜·沃尔佩特(1905—1983)是会计。约瑟夫是他们晚来的独子。
物质条件“和大家一样”。住得很挤,一家三口挤在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里,后来住在另一套几家合住的住宅,略微宽敞些——父母住较大的穿堂房间,儿子住小间的前部,而父亲在后部的立柜后面洗印自己的照片。两个房间里堆满了不同风格的旧家具。他们穿的是旧衣服,时常要缝补和改做[3]。家人没有挨饿,可是经常缺钱用,父母的收入不多(“……家里,从我记事起,因钱而起的争执就不曾停过”[4])。布罗茨基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正赶上艰苦的年代——1941—1945年的战争、战后物资匮乏的1945—1948年。他太小,不记得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惨状,不过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童年只记得勉强不致挨饿的穷苦生活。
布罗茨基从童年起,尤其在青年时期,是非常敏感的,往往不能经受冲突甚至只是情绪激动的生活场景。他本人很直朴地说,在这样的时刻“情绪会低落”。他那时患有恐怖症,尤其怕孤独。这种恐惧以及内心同它的斗争,他在其诗作《芥菜园里》以自我观察的高超能力作了描述。成年后他喜欢援引芥川龙之介的话而略加改变:“我没有信念,我只有神经。”[5]——承认自己有变态人格(或精神分析学术语中的“神经官能症”)的特征。众所周知,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是与艺术天赋有密切关系的。青年时期,据学校的正式鉴定可以断定在童年也一样,布罗茨基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喜怒无常、心灵易受伤害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养成了自律的习惯,面对致命的疾病时表现了难得的坚强,而且在年轻的时候,即使遭遇危机,例如1964年在法庭上,他也能在内心找到自制的力量。在危急关头精神坚定,拥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善于将庞大的创作计划进行到底、追求完美,这一切都说明,他的性格远比典型的“喜怒无常的神经过敏者”复杂。他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克服了生物学所注定的结果。
布罗茨基的自觉生活开始于战后的列宁格勒。他在回忆的随笔中写道:“如果真有人从战争中获益,那就是我们——战争之子。我们除了生存下来之外,还获得了浪漫主义想象的丰富素材。”[6]每一步都有轰炸和炮击所遗留的家园的废墟使人想起战争。刚刚结束的战争和胜利的鲜活感受与帝国的神话融为一体,正如城市街道上不久前的战争的累累伤痕与彼得堡所富有的后古典主义风格的象征意义不可分割:这个小男孩从自己房间的窗口看得见主显圣容大教堂用缴获的大炮建起的围墙,而在佩斯捷利街(潘捷列伊莫诺夫街)的另一端是为纪念俄国舰队的胜利而建造的潘捷列伊莫诺夫教堂。剑、矛、镖枪、钺、盾、头盔、古罗马扈从的插着小斧头的束杖装饰着横跨喷水池的大桥,正如也装饰着帝国旧都的其他很多围墙和建筑物正面。
建筑物的新古典主义装饰风格不仅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应该说,这些建筑物的正面和柱廊——它们的古典主义、现代派、折中主义的风格及其圆柱、壁柱、神话中的兽首和人首的雕塑,它们的图案装饰和支撑着阳台的女像柱、正门壁龛里的躯干像使我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了解多于后来的任何一本书。”[7]关于女性裸体的最初想象来自夏园的大理石雕像,正如较抽象的美学观念——对称、景观远近的正确配置、部分和整体的协调来自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艺术。孩子在尚未充分自觉的幻想中构建着理想祖国的神话般的形象,它的光荣和强大不可思议地与暴力和死亡无关,生活建立在匀称、和谐的基础之上。在个人的这种乌托邦和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关于后者童年的布罗茨基不曾多想,而在成年后对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抱着毋庸置疑的蔑视态度。他想象中的帝国的象征是白底和“大海的”蓝色斜十字架,而不是拜占庭“帝国的可恶的双头鸟或共济会似的镰刀斧头”[8]。正是童年培养起来的对理想国家的乌托邦幻象与过早衰朽的苏维埃帝国的丑恶现实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他的作品的内在悲剧,如?Anno Domini?、?Post aetatem nostram?、《大理石》以及其他作品。
彼得一世所设想的彼得堡是真正的“第三罗马”,然而牢固地植根于20世纪彼得堡知识界的意识中的历史参照物却是亚历山大:这个城市所拥有的高雅文化别出心裁地将希腊化时代和基督教结合在一起,是建立在东方世界边缘的一座辉煌的古典城市,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这个城市将遭到野蛮人的入侵,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彼得堡的现代神话是末世论神话,预示着这个城市是必遭灭亡的新的亚历山大,那么战后幸存的彼得堡人就不得不面对新的现实:野蛮人来了,周围是废墟,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纪元之后”。这个题材将以各种各样的变体出现于布罗茨基的创作:仿古风格的叙事诗?Post aetatem nostrum?、诗作《矫揉造作》、剧作《大理石》、诗作《发扬柏拉图精神》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把未来表现为往日的“永恒的回归”(尼采语),像野蛮时期的经常回归那样。这个题材也表现于布罗茨基为他的生身城市彼得堡而作的随笔(《关于一个改了名字的城市的手册》)。想必一个不算太冒昧的推测是,对废墟中的城市的印象注定他会把哀诗确定为他的创作的中心体裁。
他按规定于1947年七岁上学,不过1955年就退学了。苏联的学校从来不是以确切意义上的教育为宗旨,而且那几乎是苏联国民教育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历史和文学课完全服从于对未来的苏联公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任务。历史、文学甚至地理教科书都是用贫乏无味的语言写成的,并且塞满了宣传。孩子的自尊心受到压抑。通常会因为没有学好功课或顽皮就当众羞辱、责骂、侮辱孩子。
虽然得了些2分,其中包括英语课(一个将成为公认的英语随笔大师的孩子),布罗茨基还是较好地掌握了学到的知识。当然,这首先是指他对俄语语法的卓越理解。他对自己的母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一封信保存了下来,这封信是他在1963年写的,与当时改革正字法的倡议有关。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向学识渊博的改革派语言学家们解释说,正字法的划一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言说者心理的贫乏:“语言的复杂不是缺陷,而是——这是首要的——创造它的人民内心丰富的见证。因而改革的目的应该是探索更充分、更迅速地掌握这笔财富的方法,而绝不是简单化,实质上简单化就是对语言的盗窃。”[9]
离开学校,从而突破常规是不平常的决绝之举。与官方对工人阶级的颂扬相反,日复一日地要孩子们牢记,没有高等或中等教育,他们便注定要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混日子。对于城市中等文化家庭的少年而言,离开学校就意味着与别人不一样了,被社会抛弃而处境更糟。
离开学校后,几乎立即达到了一定的年龄,按照法律的许可,布罗茨基又试图继续正规的学业——在夜校注册就读,作为旁听生在大学学习。不过,他终于成为有广泛文化教养,并在某些知识领域达到高深造诣的人,是由于不倦地自我教育。他早在年轻时就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和波兰语,后来可以凭借词典阅读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又开始学习中文。布罗茨基本人曾半开玩笑地说,他获取知识是“by osmosis”(英语,用耳濡目染的方法)。对这种自我教育应严肃地看待。在他亲密的朋友中有杰出的语言学家、文艺学家、艺术史学家、作曲家、音乐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而布罗茨基广为人知的一个特点是就其感兴趣的学科非常仔细地向专家求教。很了解布罗茨基的А.Я.谢尔盖耶夫写道:“约瑟夫能在空气中抓到无数的东西。他如饥似渴地捕捉每一个新出现的item(英语;此处的意思是:资料),竭力记下此项收益,在诗中加以运用。可以说,什么也不会白白放过,一切都用得上,其惊人的技巧是难以想象的。”[10]
布罗茨基出生和成长于苏联的那个历史阶段,反犹太主义几乎成了政府的官方政策,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也在市民中复活了,扩散了。他跻身其中的那些人,与周围的大多数人相比,人生的机遇显然是有限的,这样的认知同母乳一起被布罗茨基吸收了,早年在他的同龄人中扩散的日常生活中的反犹太主义又加强了这样的认知。“在学校里作为‘犹太人’意味着经常要准备自卫。人们叫我‘犹太佬’。我握紧拳头冲上去打架。我对类似的‘玩笑’的反应是很过分的,认为受到了人身侮辱。他们触犯我,因为我是——犹太人。现在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侮辱的意味,但这种理解来得较晚。”[11]不过从布罗茨基在诗歌、随笔和答记者问中全部自传性的言论来看,很清楚,他在成年后的生活中较少为反犹太主义而感到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十五岁离开学校后,布罗茨基从不追求功名,否则他会碰到通常的障碍——对犹太人升入高校和踏上仕途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很早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在青年时代就为自己立下规矩,绝不贬低自己与国家政体和社会制度发生冲突,因为支撑它们的是简单粗暴的意识形态,而反犹太主义不过是它很多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布罗茨基是俄罗斯人,至于身份的自我认同,他在成年时期形成了一个简明的公式,并一再使用:“我是犹太人、俄罗斯诗人和美国公民”。按性格特征来说,他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按美学见解而言,是人格主义者,他排斥任何按种族或民族准则划分的联合会。其实进入布罗茨基文化视野的犹太因素仅限于它融入西方文明的程度,即如同基督教西方所接受的《旧约》。值得玩味的是,在叙事诗《以撒和亚伯拉罕》冗长的宗教哲学冥思中,虽然含有对散居异乡的犹太民族的悲惨命运和大屠杀的隐晦暗示,不过对基本情节,对亚伯拉罕的牺牲的解释,显然是以两位哲学家的著作对这部《圣经》的片段的阐释为中介,其中的一位是基督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另一位是脱离犹太教的俄罗斯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
叙事诗《以撒和亚伯拉罕》与犹太人问题只是多少有些联系,除此之外,在布罗茨基的全部庞大的诗歌遗产中只有两首以犹太人为题的诗。第一首是《列宁格勒附近的犹太人墓地》(1958),年轻的布罗茨基显然是在模仿老一辈诗人鲍里斯·斯卢茨基非法出版而风行一时的诗《关于犹太人》(“犹太人不播种粮食……”),布罗茨基本人从未将《……犹太人墓地》收入自己的诗集。第二首是《列伊克洛斯》(维尔纽斯犹太人区一条街道的名称),被收入组诗《立陶宛的余兴节目》(1971),是以选择命运为题的幻想:布罗茨基在其中似乎把自己置于维连家族某个祖先的地位。
这里还要提一提布罗茨基对消失的中欧文化世界的怀旧。这表现在他热爱波兰语和波兰诗歌、罗伯特·穆齐尔和约瑟夫·罗特源于奥匈帝国生活的长篇小说,乃至好莱坞关于鲁道夫大公和他的恋人玛莉亚·韦切尔男爵小姐双双自杀的伤感主义传奇剧《马耶尔林格》。这个消失的文明的南方前哨是“在荒野的亚德里亚海深处的”的里雅斯特,它曾是另一位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官邸的所在地,布罗茨基的诗《墨西哥的余兴节目》两首是献给他的,而东北方的前哨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边界上的加利西亚人的小城布罗德,在该地出生的约瑟夫·罗特在长篇小说《拉杰茨基进行曲》中记述了这座小城。这个祖先发祥地的曲调只是隐秘地回响于布罗茨基的几首诗[《丘陵》、《第五牧歌(夏季)》],只有一次他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大声说了出来“(波兰)这个国家,对它——不过,这样说也许很无聊——我所体验到的情感,也许,甚至比对俄罗斯更强烈。这也许是由于……我不知道啊,看来是由于某种潜意识,毕竟,归根结底,我的祖先,都是来自那里——那是布罗德啊,——我们的姓就是由此而来……”[12]。
二
青少年时代是在各个阶段交替中度过的,每几个月就是布罗茨基工作的一个阶段——在“兵工厂”做铣工的学徒,在州医院的陈尸房当解剖医生的助手,当过澡堂里的司炉、灯塔上的水手、地质勘探队的工人——到过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到过远东,到过雅库特以及里海东北的大草原[13]。
选择在冻土带、原始森林、草原从事无定额劳动,而非墨守成规的八小时工作日,在较晚的时期,人们会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斯大林之后的时代,俄罗斯脱离外部世界而孤立的状态依然如故,然而城市的年轻人有了在国内荒无人烟的广袤大地上游历的机会。无怪乎50年代下半叶列宁格勒最知名的大学生诗歌小组是矿业学院在Г.С.谢苗诺夫领导下的文学联合会。矿业学院的学生中出现了一批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例如:列昂尼德·阿格耶夫,弗拉基米尔·布里塔尼什斯基,利季娅·格拉德卡娅,亚历山大·戈罗德尼茨基,叶连娜·昆潘;他们的联合会还有“外来的”人才:格列布·戈尔博夫斯基和亚历山大·库什涅尔。弗拉基米尔·布里塔尼什斯基成功地出版了这个小组的第一本薄薄的诗集《探索》。诗集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地质”抒情诗及其组成部分:旅途、克服物质上的匮乏、男性的严峻的友谊。若干年后布罗茨基说,布里塔尼什斯基的诗是促使他在青少年时代拿起笔来的最初动因:“诗集的标题是‘探索’。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地质探索和一般的探索——探索人生的意义及其余的一切……我觉得,对这同一个主题可以写得更好些。”[14]马拉姆津本[15]的开篇几首作于1957年的短诗《别了……》、《工作》、《祝酒》完全掌握了“矿业学院学生”的诗学功课,不过逊色于作诗技巧的范例:
闯过一切障碍。
走遍一切沼泽。
翻山越岭。
去吧。
工作就是这样[16]。
按照时代精神,艰难跋涉是形成个性、“探索自己”的一种方式。1958年8月7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东北的彼尔沙湖镇写给校友Э.拉里奥诺娃的一封信里,探索——是关键词:“地球上有些人孜孜以求的是要使未来比现在更好些。这是一些真正的作家、真正的医生、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意思是创造者。我想在某个方面成为配得上的人。为此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我很后悔,我开始您所谓的旅行太晚了。毫无疑问,这两年没有白过。?……?我希望,你能正确地理解我。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探索。探索新的思想、新的形象,主要是新的表现形式。”[17]
在勘探队和后来在流放中的体力劳动——在野外翻掘岩石,集运木材等等——不仅不使他心情沉重,反而是那里的生活中最愉快的方面:“在那里我黎明起身,清晨六时左右跟随执勤人员去管委会的时候,我明白,此时在整个所谓的俄罗斯大地上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人民都在上工。因而我有权觉得自己是属于人民的。这个感觉太棒了!”[18]布罗茨基是20世纪俄罗斯唯一的大诗人,像普通工人一样开始自己的劳动生涯。
他与苏维埃政权冲突的一个难以置信的方面在于,当局向他提出了对漂泊文人的公式化的控诉,指控他不劳而获,不愿从事生产劳动。布罗茨基在其意识形成的年代,虽然有十分广泛的文化兴趣,但决不能归入“娇生惯养的青年”之列,锦衣玉食的知识分子那种漫无止境的内省,臭名远扬的“脱离人民”、假斯文与他是格格不入的。他对普通人的态度既不过分温情,也不全然是讽刺。他在很多方面都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
布罗茨基很早,几乎四岁就学会了阅读。正如人人识字的国家的所有儿童和少年一样,他在电视群众性的普及之前就读了很多书。书本知识与天赋的生动的想象力相结合,使这个年少的读者能识别不同的国家、时代和文化。学校教学大纲硬塞的等级阶梯激起了抗议,抗议之余便是对列夫·托尔斯泰(作为官方的等级阶梯上的“首要作家”)的讽刺态度,对涅克拉索夫、契诃夫的冷漠。布罗茨基拿来与托尔斯泰相对立的不仅有他所热爱的没有纳入苏联学校教学大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还有屠格涅夫。童年时期的圣像破坏运动的阴影表现在布罗茨基对普希金的态度上,不过他从未质疑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核心作用。“……我们在学校里惟妙惟肖地朗读《智慧的痛苦》和《叶甫盖尼·奥涅金》?……?。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乐趣。是关于学生时代的最愉快的回忆之一。”[19]他一生写的最后一封信是谈论普希金的散文作品[20]。他能背诵普希金的很多抒情诗和《青铜骑士》。关于《回忆》中的诗行:“在厌恶地阅读我的人生的时候……”——他说,从其中产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罗斯的全部散文作品。不过布罗茨基还是总想纠正俄罗斯传统上对普希金的崇拜而列举非常优秀的一代诗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卡捷宁,而首先是巴拉滕斯基。他非常了解和热爱18世纪的诗——从康捷米尔和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到杰尔查文和卡拉姆津。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无系统地阅读俄罗斯和世界(主要是西欧的)经典作品之后,年轻的布罗茨基的主要阅读范围是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主要是译作,50年代下半叶的青年对它有浓厚的兴趣。这一代人渴望弥补斯大林统治后期在严酷的文化孤立中所失去的十年。公立图书馆和家庭藏书遭到清洗后幸存的书籍在人们之间争相传阅:革命前出版的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苏联战前出版的О.哈克斯利、多斯·帕索斯、Л.Ф.塞利纳的长篇小说,海明威早期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托玛斯·曼的《魔山》,普鲁斯特的史诗,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翻译的《十九和二十世纪法国抒情诗选集》,米哈伊尔·津克维奇和伊万·卡什金的《二十世纪的美国诗人》,Д.С.米尔斯基的《英国近代诗选》[21],期刊《国际文学》载有《奥德修纪》章节的各期。这个期刊以俄罗斯化的名称《外国文学》于1955年复刊。其中载有散文作品以及翻译的诗歌。显然,它特别吸引年轻的布罗茨基。他学生时代的很多诗作是自由诗,这在俄罗斯诗歌中颇为罕见,而在《外国文学》中却是司空见惯的。对他来说,俄罗斯现代主义散文作品(别雷、扎米亚京、巴别尔、皮利尼亚克)在风格上,而罗札诺夫还在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恰在这时被重新发现的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布罗茨基认为他是20世纪的主要作家之一。稍后他了解了并高度评价列昂尼德·多贝钦、安纳托利·马里延戈夫,特别是康斯坦丁·瓦吉诺夫的散文作品。从1961年秋起,他就有机会在藏有私自出版物的图书室里了解很难接触到的俄罗斯侨民作家的作品,那都是青年学者С.С.舒尔茨收集起来的(摄影拷贝、打字翻印的书籍和巴黎期刊《现代纪事》中的某些作品)。其中有纳博科夫的全部俄文长篇小说,茨维塔耶娃、霍达谢维奇、Г.伊万诺夫的散文作品和诗歌[22]。
布罗茨基对俄罗斯高超的现代派诗歌(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赫列布尼科夫、奥贝里乌等)的认识不是开始于他的文学兴趣尚在形成的少年时期,而是开始于稍后的60年代上半叶,这时他已是一位积极从事创作的诗人。只有茨维塔耶娃是例外,他早在60年代初就读了她的叙事诗《山之歌》、《终结之歌》、《捕鼠者》的秘密翻印本。茨维塔耶娃立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毕生仰慕的诗人[23]。
与《外国文学》相比,有关西方精神和美学新风尚的资料在更大程度上是来自波兰的波兰文书刊。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版物不同,“人民民主主义”的波兰书刊在苏联是可以自由出售的。波兰的刊物可以订阅。“我读过的现代西方文学作品,大约有一半是波兰文的……”[24]——布罗茨基为了阅读加缪和卡夫卡的作品而学会了波兰文。和他的很多列宁格勒的朋友一样,他也是波兰周刊《观察》的忠实读者。在布罗茨基身边,偶然在《素描》这首诗中遇到诗行“月亮闪耀着刺目的光芒。/月亮下面,仿佛孤单的人脑——乌云……”,《观察》的老读者一定会想起达尼埃尔·姆罗兹的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版画,他曾不止一次描绘有人脑状的大朵乌云的夜景。总之,《观察》的画家和作者以五六十年代的先锋派(从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到比特尔斯的抒情作品)为取向的风格在布罗茨基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不过对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别重要的是了解波兰的诗。这是斯拉夫语族的诗,然而它与发源于古罗马的欧洲传统有着更深远、更有机的联系。波兰有过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鼎盛时期,以及对布罗茨基非常有吸引力的全球电视转播体系。俄罗斯的巴洛克风格大约迟来了一百年,不过布罗茨基也发现,康捷米尔、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和杰尔查文就有巴洛克风格的特点。他翻译过16世纪波兰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雷伊、沙任斯基的作品,也许还译过科哈诺夫斯基的作品。他们为他接受约翰·多恩和其他英国玄学派诗人作了准备。他还译了波兰浪漫派大诗人诺尔维德的作品,这位诗人的激情和悲剧性想象早于茨维塔耶娃,而且他的狂热的诗体也早于茨维塔耶娃——节奏异常的诗句中满是大胆的省略。他译了比自己年长的当代波兰现代派诗人加尔琴斯基、赫尔伯特、米沃什的作品。
吸引青年布罗茨基的那些作品在风格上相去甚远,却有一个美学的主导方向——现代主义。若是承认“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定义的相对性,就终究可以肯定,布罗茨基作为艺术家的形成要归功于现代主义的熏陶。现代主义有时被混同于另一种现象——艺术上的先锋派,大约从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到20世纪中叶,现代派在文学和艺术上占据着主要地位。尽管现代派作家的作品是多种多样的,却有一个基本的相似之处。他们全都基于由来已久的神话原型构建情节,现实的描写不合情理、不连续,在前辈力求发现和谐与逻辑的地方揭示混乱和荒诞的胜利,对所有的人来说,基本的哲学问题和叙事问题都是时代问题。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现代派诗人之一和最有洞察力的批评家艾略特曾指出,现代主义的美学和哲学与巴洛克风格在类型学上是相似的。
童年的布罗茨基没有读过学校教学大纲之外的诗歌。十七岁开始经常阅读诗歌。他很容易就能记住并兴味盎然地大段或全文援引自己心爱的诗——杰尔查文的《梅谢尔斯基公爵之死》,巴拉滕斯基的《秋》、《荒原》、《致一位意大利叔叔》,А.К.托尔斯泰的《波波夫的梦》,20世纪诗人的大量诗作(既有老一辈的诗人,也有他的同龄人),这足以说明,实际上所有这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是多么牢固而详尽地保存在他的持久的记忆里。
50年代列宁格勒的年轻诗人们从上一代的示范中受到教益。当然,我们讲的不是半官方性质的诗作,而是真挚的抒情创作。年轻的诗人们爱戴的老师是有才华却由于非政治倾向而很少发表作品的诗人格列布·谢苗诺夫(1918—1982)。谢苗诺夫特别强调诗歌的连续不断的世代传承关系:
然而普希金的星光在
窗外的严寒中闪烁。
然而丘特切夫的隐秘
透入心底而令我泪下。
然而勃洛克的疯狂
会使我永久地心酸。——
唯有这编织中的一条细线
惊动我午夜的听觉[25]。
从普希金到丘特切夫,从丘特切夫到勃洛克。要不是有书刊检查,谢苗诺夫就会在勃洛克之后讲到霍达谢维奇和阿克梅派诗人。在这个文学谱系中,随之而来的是列宁格勒1930—1940年的那一代诗人,格列布·谢苗诺夫本人也属于这一代。1921年被枪毙的古米廖夫或侨民霍达谢维奇,其姓名不再被当众提起,或在讨论中代之以其学生和追随者的姓名,主要是20年代至30年代列宁格勒的诗人们,如H. C.吉洪诺夫和别的一些人。培养的是具体的观察、情感的含蓄、简洁和洗练。这种文风不适合为领袖、党、政府、“共产主义建设者苏联人民”写赞美诗,不适合揭露美帝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宣传文章,按规定这样的文章需要华丽、冗长的雄辩术。另一方面,它本身不会激起意识形态检查官的气愤,因为避免使用隐晦(“人民不懂”)的词语,不会超越标准语的词汇规范。
为什么布罗茨基未能掌握列宁格勒的功课,原因很简单——他不曾在这个学校学习。我们知道,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读过诗,也不写诗。对他那一代的列宁格勒诗人来说,这是反常的。在那个时期,少男少女通常会渐渐地成长为诗人,从童年起便饱读诗歌并且自己作诗。在学校、文化宫、少年宫,与教孩子们学习摄影或制作航空模型的小组并列的是少年诗人小组。最有天赋的孩子被选入少年宫(涅夫斯基大街的阿尼奇科夫少年宫)的艺术学校。Г.С.谢苗诺夫曾在战后最初几年领导这个学校。学生们在那里很快就学会用扬抑格、抑扬格、抑抑扬格、抑扬抑格和扬抑抑格写诗而不破坏重音的次序,多少能准确地押上诗行的韵。等孩子们年龄稍长,再向他们说明,重要的并不是正确的诗律本身,它只是形式,而诗作的内容是思想,但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通过对生活情景的具体描写来表现的思想。这种描写的基础是对细节的精确观察。换言之,有高度文化教养的Г.С.谢苗诺夫是自觉的,而文化教养较差,在文学小组捞外快的文学家们则是由于修辞的惯性而教授阿克梅派的诗学基础。在那时,直接由于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政委们于1946年在文学界所造成的浩劫,“阿克梅派”这个词和创作了阿克梅派诗歌最纯粹的典范作品的阿赫玛托娃的姓名一样,是不能说出口的,然而阿克梅派精湛的美学依然是培养未来诗人的基础。在俄罗斯约定俗成的所谓“阿克梅派”,在英美称之为“意象派”。埃兹拉·庞德坚持诗歌应避免象征性的暗示、影射和一般的抽象(“自然的物体永远是最贴切的象征”),Т.С.艾略特随后在1919年为“客体的相关描写”下了内容丰富的定义:诗的表现力会加强,只要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对客体——事物、情况、事件——的相关描写来表现情感。这是现代派诗学的黄金律之一。1968年布罗茨基在其诗作《烛台》中写道:
无疑,艺术的感染力就
在于真实,而不是吹嘘,
因为艺术的基本规律
是细节的独立性,这一点无可争辩。
在意识形态的残酷压迫的条件下,客体的相关描写的方针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导青少年诗人的试笔避开保守的半官方的雄辩术,以及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的“仿效马雅可夫斯基”风格。不过这个学派也有不好的一面。这种“现实主义”在实践中往往会变成“形式主义”,因为一首诗只要能证实作者的观察力,就会得到认可。年轻诗人的老师即使自己铭记在心,但在那种条件下也不能开导自己的被监护人,成功观察到的细节在诗中的重要性不在于细节本身,而在于表现悲哀、希望、恐惧、绝望、爱,以及理性和玄学的探索。
布罗茨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没有人要他记住,被社会抛弃的诗人保持浪漫派的态度,直接探讨生死问题、有无宗教信仰问题,这是“愚蠢的爱好”,而文化史题材是“咬文嚼字”。他开始作诗已不是爱慕虚荣的孩子,为受到称赞而努力按规则写作,而是开始独立生活的青年,认真地关切这种生活的意义及其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性的美好和丑陋,贫困和失去自由的经常性威胁,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世界的自我肯定。在文学尤其是诗享有崇高威望的社会,他选择诗歌作为自我肯定的方法,同时也作为探索那些“棘手问题”的答案的方法。
布罗茨基的天性中有追求第一的渴望,正如也有所谓神授的超凡能力。他吸引同龄人的是真诚,广泛的兴趣,自然而非做作的新派作风,以及对人、对交谈、对抽象观念和日常事件的非常热心的态度。与这结合在一起的是茫然不知,在文学圈子里什么行为得体,什么行为不得体。他从不带着最初的试笔参加评论,却出席私人聚会和官方核准的文学青年的会见,为的是朗诵自己的诗作,显然对诗的优点满怀自信。他的朗诵照例比别人更响亮也更热情奔放,不过当时几乎所有的新诗都意在朗诵[26]。朗诵后往往独自或在朋友们的陪伴下离开,不留下来听听别人的朗诵。这一切不能不激起文学青年监护人的愤怒和担心。很多人都记得1960年2月14日在纳尔瓦河附近高尔基文化宫的“赛诗会”上的丑闻。十九岁的约瑟夫朗读了《犹太人墓地》。像往常一样,他的朗读博得大多数青年听众的喜爱,可是在大厅里的Г.С.谢苗诺夫大声表达了他的气愤。赛诗会的另一位参加者Я.Α.戈尔金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说明的:“崇高的诗人,在其多灾多难的人生中习惯于高傲的矜持、沉默的对抗,谢苗诺夫气愤的是约瑟夫所闪现的天真的反抗,似乎并非得益于才华的轻松自如。”[27]布罗茨基朗诵《有题词的诗》,以回应激烈的责备。题词是一句拉丁文的俗语:“朱庇特可以做的,公牛不可以。”小冲突酿成了大丑闻。丑闻不仅在不满的文学青年中,而且也在有责任监视这类青年的人们之中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1960年布罗茨基第一次与惩罚机关发生冲突。一年前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生亚历山大·金兹布尔戈私自出版诗刊《句法》。第三期《列宁格勒专辑》有布罗茨基的五首诗,其中包括《犹太人墓地》和《朝圣者》,后者也许是他初期诗歌中最风行的一首。《句法》是第一本私自出版的刊物,广为人知。它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传播,国外对它也有所了解,苏联报刊对它大肆抨击:《消息报》发表诽谤文章《无赖们爬上了诗坛》[28]。1960年7月金兹布尔戈被捕,判处羁押集中营两年。
《句法》中包括布罗茨基在内的诗人们的作品,作为个人主义或悲观主义的诗作,在意识形态上是苏联书刊检查机关所不可接受的,但这些诗歌并没有直接批判苏维埃制度,也没有号召推翻它。尽管如此,一些年轻人还是被传唤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受审,以残废和坐牢威吓他们,要是不知悔悟的话。从这时起,即使不是更早,布罗茨基便处于列宁格勒克格勃注意的范围。
1962年1月29日布罗茨基被捕,在什帕列尔纳亚的克格勃内部监狱羁押了两天。对布罗茨基的两个熟人亚历山大·乌曼斯基和奥列格·沙赫马托夫的案子进行调查,有可能也对布罗茨基提起严厉的控诉。
奥列格·沙赫马托夫当过空军飞行员,是有才华的音乐家,是一个有冒险秉性的人,大约比约瑟夫年长六岁。1957年他们在列宁格勒青年报《接班人》编辑部偶然相遇,两个人都是来投稿的。从童年起就爱好航空的约瑟夫与他颇为相投。沙赫马托夫介绍他与亚历山大·乌曼斯基相识[29]。乌曼斯基是有广泛天赋的业余爱好者。他谱写钢琴奏鸣曲,撰写关于基本粒子的文章和政治哲学专著,醉心于神秘主义科学,认真研究印度教,还练习瑜伽。据熟人的回忆,乌曼斯基很有魅力,在他周围总是有一个青年小组,吸收那些想在官方意识形态框框之外讨论“永恒问题”的人们,以及新派的画家和音乐家。
1960年12月布罗茨基去撒马尔罕探望在那里的沙赫马托夫。两个朋友忽然想出一个不切实际的逃往国外的计划。多年后布罗茨基这样描述那个计划:买票登上小型支线飞机,起飞后击昏飞行员,由沙赫马托夫驾驶,飞越边界进入阿富汗[30]。买了撒马尔罕-铁尔梅兹航班的机票,可是在起飞前,布罗茨基耻于伤害无辜的驾驶员,因而计划作废(沙赫马托夫写道,只因航班被取消)。
一年后,沙赫马托夫因非法持有枪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受审时竭力想逃脱新的刑期,这次的刑期可能会很长,他供称在列宁格勒有一个“乌曼斯基地下反苏团体”,并供出几十个与乌曼斯基多少有点关系的人。还讲了和布罗茨基一起逃往国外的那个未能实现的计划。于是布罗茨基也被拘留,但因为没有犯罪事实,而且关于犯罪意图也仅有沙赫马托夫的口供,两天后获释。不过,1964年在法庭上给他在撒马尔罕的瞎折腾记了一笔账,从此他就处于克格勃的严密监视之下,直至被驱逐出境。
三
布罗茨基十八九岁写的诗,由于毅力和丰富的想象,偶尔会有很不错的诗行,但整体上毕竟还只是青少年的试笔。这些诗的作者像他这个年龄的很多人一样,醉心于空洞华丽的抽象概念,满怀浪漫情调而轻视平凡的世界。他喜欢华而不实的外来语,语无伦次地加以使用,几乎到了谵妄乱语的程度:
... начисто заблудиться
в жидких кустах амбиций,
в дикой грязи простраций,
ассоциаций, концепций
и — просто среди эмоций.
[?Стихи о принятий мира?,1958)[31]
他的想象用异域情调的小册子和电影的混杂堆砌创作华丽却不知所云的哑谜:
Мимо ристалищ, капищ,
мимо храмов и баров,
мимо шикарных кладбищ,
мимо больших базаров,
мира и воря мимо,
мимо Мекки и Рима,
синим солнцем палимы,
идут по земле пилигримы.
[?Пилигримы?,1958)[32]
麦加和罗马,作为国外神秘的豪华景象的象征的市场,随即是科学幻想中的蓝太阳和来自不喜欢的涅克拉索夫一首诗中的“朝圣者/太阳暴晒”。写丑闻的《有题词的诗》(1858)赋予抒情主人公以兽性和神性——神或牛,人性是被忽略的。在一定的年龄段,很多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写。莱蒙托夫在这个年龄就声称:“我——或者是神——或者什么也不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样的诗,又热情洋溢地以非同寻常的“琴弦般的”嗓音朗读,有浪漫倾向的少男少女都很喜欢。不同凡响的是,早期在同龄人中所获得的好评,未能诱使布罗茨基停滞在这个阶段,他另辟蹊径,很快就摆脱了矫揉造作的浪漫色彩。大约在十九岁他已经开始领悟到,诗作不是源于异想天开的幻想,而是源于现实生活。当他被带往克格勃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在受审时该怎样自持:
要牢记风景?……?
在工作人员办公室的窗外……
要牢记,
顺着玻璃慢慢流淌的浑浊的雨水怎样
扭曲了那些建筑物的匀称,
在那些人说明我们该做些什么的时候。
(《诗学的定义》,1959)[33]
日常生活的抒情,诗的俗语资源,善于在简单和平常的现象中发现超验的底细——布罗茨基学习了这一切,到1962年这一类严肃的诗对抽象的浪漫派诗歌开始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这个流派里布罗茨基是有老师的。后来他把自己年长的朋友叶甫盖尼·赖恩和弗拉基米尔·乌夫梁德称为老师。年轻时影响了他的还有这一代的其他卓越的诗人——斯坦尼斯拉夫·克拉索维茨基、格列布·戈尔博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布里塔尼什斯基。不过,那时他无疑是从阅读斯卢茨基的作品吸取了主要的教益。
Б.А.斯卢茨基(1919—1986)是战时一代最重要、最独特的诗人。这位勇敢刚毅的人物就其政治信念而言毕生是共产主义者,可是他的无情的现实主义诗歌完全不符合官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50年代下半叶是他的创作的极盛时期,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诗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亲身感受到他的影响。
К.К.库兹明斯基回忆,1959年冬他曾向布罗茨基出示自己最初的诗作。没有评价也没有忠告,布罗茨基向他朗读了斯卢茨基的《科隆的牢房》,意思是:就该这样写[34]。布罗茨基对斯卢茨基终生不忘。提起斯卢茨基,他照例会背诵《市场上的音乐》:
我在大市场长大,
在哈尔科夫,
那里只有几个垃圾桶
那里只有几个垃圾桶
干干净净地放着,
人们因为急于吐痰,
从不走近垃圾桶……[35]
斯卢茨基吸引布罗茨基的不是社会主义主题,尽管他本人也不无反资产阶级的倾向,吸引布罗茨基的是诗的力量。斯卢茨基在19世纪枯竭的诗歌形式和室内乐的纯粹实验之间打开了自由的空间。原来只要略微变化古典诗格,诗行就有了灵活性而不至于分崩离析。布罗茨基追随斯卢茨基,开始运用俄罗斯古典诗歌的原封未动的资源[36]。他也逐渐开始去掉或添加某个音节,使古典诗格转化为三音节诗格的变体。例如在《言语的一部分》组诗(1974—1976)中,郁闷、陈旧的抑抑扬格多半变了样。斯卢茨基表明,丰富而不显眼、不毫无必要地惹人注目的音韵资源还远没有用尽。动词韵尤其如此,有时会用韵前(重音前的)辅音(стояли-доставали,пили-били,кружился-ложился,而在звучала-изучала中同音异形接近于完全相同)。文学圈子反对动词韵聚集,形成贫乏的语法上的押韵。总之,斯卢茨基几乎伪装成散文的诗贯穿着连接其结构的诗学手法——同音重复、元音重复、头语重复、形似词错综、双关语等等。他教会布罗茨基利用诗的戏谑因素应对严肃而非戏谑性的任务,布罗茨基的叙事诗《以撒和亚伯拉罕》(1962年7月)的开头似乎在向这位老师致敬。这里令人印象深刻地利用了《圣经》中的一个名字Исаак(以撒)及其俄罗斯化的变体Исак之间的区别:“俄语的以撒(Исаак)少一个音,?……?以撒(Исак)本来就是蜡烛头,/以前人们都把那支蜡烛称为以撒(Исак)。”斯卢茨基有一首关于这个话题的短诗:
人们到处颂扬以撒(Исаак),
所有的教堂都在为他祈祷。
对待Исак却很不一样,
只许他在室内活动[37]。
布罗茨基从斯卢茨基学到的重要一课涉及怎样作诗,以适应诗的语义结构。斯卢茨基的《市场上的音乐》开始于以粗俗的语言讲述极其粗俗的场景,似乎不改叙事的风格,而以稍加掩饰地援引福音书作为结尾:音乐在鞭笞街头的小贩,好像把讨价还价的那些人赶出教堂的基督。布罗茨基也要在自己的诗里把肉欲的、庸俗的成分与抽象的哲学和玄学密切地结合起来。他笔下的新的但丁,作为从乌有创造宇宙的造物主,将一个词填在空白处,而这个关于宗教仪式的词(Слово)却与亵渎和粗俗的词“херово(叉开腿)”押韵(《波波的葬礼》,1972)。他往往从逼真地描写丑陋的现实——简陋的内部装修或恶劣的自我感觉——开始写诗,并引向精神上的发现,不过这种发现并不总是能让人得到安慰,抱有希望。他的短诗《我搂着双肩,看了看……》(1962)和长诗《静物画》(1971)都是这样的结构,不过抒情情节的直接的、“自下而上”的顺序更多地让位于较复杂的结构。
不过,布罗茨基师承斯卢茨基的,或者说,至少在斯卢茨基作品中所领悟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诗的基本情调,那种能表现作者对世界的态度的主要属性。布罗茨基曾在1985年谈到这一点:“斯卢茨基几乎是独自改变了战后俄罗斯诗歌的基本情调。?……?特有一种生硬、凄凉和冷漠的音调。像这样讲话的通常是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假使他们想大体上讲讲,他们是在哪里活下来的,此后又到过哪些地方。”[38]
在少年时期,布罗茨基回避官方“文学小组”泯灭差异、压抑想象力的学习方法,他独自学习诗歌遗产——不均衡,却是自由地学习。不过,正如任何一位初涉门径的艺术家,他感到有必要与某位亦师亦友的人经常地联系切磋。在50年代下半叶和0年代初,列宁格勒的年轻诗人向往前面提到的矿业学院文学家联合会,或希望结交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的文学家联合会多少有些联系的人。如果说矿业学院的诗人们有一位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老师Г.С.谢苗诺夫,那么语文系的文学家联合会却有几个官方派的学监,因而“语文系学生们”主要的诗朗诵及有关的谈论不是在联合会的会议上进行,而是在合住的一套住宅的几个房间里——在列昂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弗拉基米尔·乌夫梁德或写下这几句话的笔者家里。不过,在“语文系学生”的聚会上也时常能遇到“矿业学院学生”,在这两个团体之间没有严重的对立。不同的是美学取向。谢苗诺夫按照相当保守的传统培养自己的学生,而自行其是的“语文系学生”认为自己是30年代中断的俄罗斯先锋派的复兴者和继承者。这就决定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对两个团体的诗人的不同态度:严肃地看待“矿业学院学生”,尽可能帮助他们发表作品,而“语文系学生”的创作被认为是有点幼稚的游戏。不过“语文系学生”弗拉基米尔·乌夫梁德和谢尔盖·库勒的诗也以其独特的幽默得到老一辈知识界读者的赏识。布罗茨基不常介入矿业学院学生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上述与Г.С.谢苗诺夫的冲突之后。1959—1960年他结识了列昂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弗拉基米尔·乌夫梁德和米哈伊尔·叶列明,他们曾构成后来所谓的“语文系流派”的核心,不过这三个人中只有叶列明曾在语文系学习。布罗茨基与乌夫梁德交上了朋友,而且毕生喜爱他的讽刺性模拟和多愁善感的抒情水乳交融的诗。乌夫梁德毫不张扬,却非常机敏的作诗技巧也令他叹服,说到他后来把乌夫梁德称为自己的老师之一,那么这一点应该很具体地去理解:布罗茨基押韵的风格在很多方面重复并发展了乌夫梁德在50年代末所取得的成就。不过,那个时期在列宁格勒的年轻诗人中还有一位卓越而不同凡响的人物,诗人叶甫盖尼·赖恩,其文学观点使他与“语文系学生”和“矿业学院学生”都没有过于密切的交往。
布罗茨基写于1991年的关于赖恩的短篇随笔特别提出,哀诗是对赖恩的抒情作品起决定作用的体裁。“哀诗——追忆往事的体裁,也是诗中最常见的体裁。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人类的本质所固有的感觉,主要是在事后才觉得,存在渐渐地具有现实性的地位,部分地在于一个事实,即笔在纸上的运行本身,按时间顺序来说,就是一个回溯的过程。”[39]哀诗确实使赖恩在列宁格勒年轻诗人的圈子里脱颖而出。这个圈子所推崇的体裁是旧时所谓的“微型诗”、抒情小品,倾向于捕捉瞬间的感受、印象、观察、思想。有才华的诗人们在这种体裁的框架内写了形形色色的诗。矿业学院学生列昂尼德·阿格耶夫描绘苏联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微型画,米哈伊尔·叶列明根据各种资料形成隐喻,大多是根据科学资料,因而只有少数知情者才懂的八行诗,以及亚历山大·库什涅尔的心理复杂,然而措辞简练的内省,是难以对比的,但体裁的属性是相同的。这些和前面提到或不曾提到的其他有才华的诗人,在成功的诗作中记下了瞬间感受的极其丰富、细微的心理差异,不是“快乐”、“悲伤”等太笼统的词语所能表达的。比布罗茨基年长五岁的赖恩促使自己的朋友作出世界观的抉择,而非形式主义的抉择。哀诗实质上是怀旧的体裁,写的不是当下,而是过去,即与时间问题有关。任何诗歌创作只有在其他话语形式不适应的时候才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哀诗存在的理由来自维特根施泰因的著名论点:谈论死是不可能的,因为“死不是有生命的存在”[40]。在谈论无能为力的地方,抒情作品就是可能的。哀诗作品还有一个内情——语言和时间问题无法解决:任何书写都是“回溯的过程”。这个问题困扰着浪漫派作家,看来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与直接感受完全相符,因为作品总是“迟来的”;这里,困扰布罗茨基的,与其说是情感能不能表达的问题,不如说,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瞬间之永不停留”。
停下,这个瞬间!与其说
你完美,不如说你不可重复。
(《雅尔塔的冬日黄昏》)
由于幸运的巧合,大概就在他结识赖恩的时候,布罗茨基为自己发现了巴拉滕斯基。布罗茨基由于侨居国外与赖恩分别十六年之后,在1988年重逢,老朋友问他:“是什么把你推向诗歌的?”回答是:“1959年我乘飞机去雅库茨克。我在那里纵酒作乐,混了两个星期,因为天气不好。就在那里,在雅库茨克,记得我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溜达,顺便走进书店,碰巧买了巴拉滕斯基的作品——‘诗人文库’出版。我那时没有什么书可看,找到这本书看了以后,就全都明白了:现在该做什么。”[41]追随巴拉滕斯基“该做什么”,布罗茨基在关于这位诗人的札记中解释了自己对现代哀诗创作的理解:“……他从来不是主观的、自传性的作者,而是倾向于概括,倾向于心理的真实。他的诗——是结局、结论,是对已有的生活悲剧或精神悲剧的附言,而不是对悲剧事件的叙述,对情境往往是评论多于描述?……?。巴拉滕斯基的诗几乎以加尔文宗教徒的热忱追随自己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几乎总是——以自己为样本所描绘的远非完美的灵魂。”[42]
介绍布罗茨基认识阿赫玛托娃的正是赖恩[43]。这是在1961年8月7日。阿赫玛托娃关于布罗茨基个别作品的确凿言论,我们已知的并不很多[44]。我们知道,她指出在她1962年生日写给她的诗《公鸡们会高声啼叫,四处奔忙……》,是比期待于道贺体裁的更为深刻的作品,并以其中的诗句作为自己的诗《最后的玫瑰》的题词[45]。我们知道她非常重视叙事诗《以撒和亚伯拉罕》及其关于A音的诗行:“其实——这是可怕的喊叫/稚弱、悲伤,是临死的哀嚎……”——用作四行诗《名字》(最初的标题)的题词。阿赫玛托娃看了《献给约翰·多恩的大哀歌》后讲的一句话“您自己也不明白啊,您写了什么呀!”(布罗茨基和几位回忆录作者的引述略有差异)作为成人仪式的一个因素走进了布罗茨基个人的神话[46]。
尽管如此,这时布罗茨基已形成个人的风格,与阿赫玛托娃作品的基本取向——暗示性、言而不尽的诗风、语言倾向于质朴的诗意不仅不相似,而且在很多方面是截然相反的。布罗茨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他解释道:“我们去她那里不是要得到称赞?……?我们去她那里,因为她会使我们的心情活跃起来,因为有她在座,你仿佛会放弃自己,放弃自己在内心,在精神上——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说了——所达到的水平,放弃你与现实交谈的‘语言’,而选择她所使用的‘语言’。当然喽,我们谈论文学,当然喽,我们散布流言蜚语,当然喽,我们跑去买来伏特加、听莫扎特的音乐并嘲笑政府。可是回顾过去,我的所见所闻不是这些;从我的意识里浮现了出自《野蔷薇》的一个诗行:‘你不知道,人们已经宽恕你了……’它,这句话,与其说冲破不如说甩开了语境,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因为宽恕者永远比冒犯本身和冒犯者更伟大。因为对一个人说的话,其实是对全世界说的。它是——灵魂对生活的回应。我们向她学习的大概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作诗技巧。”[47]
阿赫玛托娃亲切地接待周围的年轻诗人,然而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态度却完全不同,把他既看作一个人,也看作一个诗人。毫无疑问,她最先认识到了布罗茨基诗歌天赋的潜在的、当时还远未实现的气派以及他个人的气魄。“须知布罗茨基是她的发现,她的骄傲”,丘科夫斯卡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48]。阿赫玛托娃对布罗茨基是平等相待的:“约瑟夫,咱俩了解俄语的一切音韵……”[49]。对她来说,Н. Я.曼德尔施塔姆也是年轻诗人,是“小奥夏”[50],表面上,举止风度很像自己伟大的同名者。显然,对阿赫玛托娃来说,相似并不只是表面上的。她在1963年的日记里写道:“另一个约瑟夫对我的态度令我想起曼德尔施塔姆”[51]。这也就决定了阿赫玛托娃出人意料地对年龄相差半百的布罗茨基平等相待的关系,他的言谈有时会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记和书信中她一再地重新回到布罗茨基的想法,认为诗中主要的是——构思的伟大。“又重新浮现了意义深远的话语:‘主要的是——构思的伟大。’”[52]有一天阿赫玛托娃写道:“《几页日记》的题词取自布罗茨基的一封信:‘……他(大写的人)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由时间、空间、精神?应当认为,作家在努力塑造大写的人的时候,就一定要写时间、空间、精神……’”[53](必须指出,布罗茨基关于“构思的伟大”的想法有一个文学上的起源——《莫比·狄克》第104章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提及“丰富宏大的主题具有使作品伟大的力量”。“我们自己会达到主题的程度,”梅尔维尔写道。“要创作伟大的作品,必须选择伟大的主题。”)[54]
布罗茨基在阿赫玛托娃身边所吸取的经验教训,不仅涉及个人的道德品质,还涉及诗学使命的品德方面。作为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者,作为原则上的“私人”,他明白,严肃对待自己使命的诗人不能不是人民经验的表达者,他是用他们的语言写作。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作家有“人民性”,而且人民性被理解为政治正确和审美简单化的结合。结果是知识界对“诗人和人民”问题本身形成了百折不挠的反感。因而20世纪对“纯艺术”和“象牙之塔”话题的沙龙式奇谈怪论被很多人信以为真。阿赫玛托娃对宣传鼓动是不予理睬的。她后期的创作,首先是Requiem'a的中心主题,是诗歌的代表性主题:她意识到自己的天职——她的声音是“一亿人民的呐喊”。布罗茨基的诗《安娜·阿赫玛托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也正是要肯定这一点——祖国的大地在用她的声音说话,幸亏有她,这片土地才“在又聋又哑的世界”获得“说话的能力”。
布罗茨基遭遇了不少非常事件和动荡——大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后来的威斯坦·奥登的赞许,还有逮捕、监禁、精神病院、法院审判、流放、驱逐出国、致命疾病的发作、世界性的荣誉和地位,不过对他本人而言,多年来他人生中的主要事件始终是与玛丽娜·(玛丽安娜·)帕夫洛夫娜·巴斯马诺娃的同居关系和决裂。在普希金的《先知》中,上天派来的六翼天使赋予诗人神奇的视力、听觉和声音。布罗茨基深信,对一个女人的爱在他心里引起了同样的改变:
这是你,热情洋溢,
给我创造了
左边的、右边的
耳壳,低声细语。
这是你,扯着窗帘,
往我湿润的口腔
注入频频
呼唤你的声音。
我简直瞎了。
你悄然出现
赐我视力。
(《我只是那个……》)
“献给М.巴斯马诺娃”的诗在布罗茨基的抒情诗中占有中心地位,不是因为优秀——其中有杰作也有很一般的——而是因为这些诗和投入其中的内心体验是一座熔炉,冶炼了他诗歌的个性。布罗茨基到了自己的晚年还谈到这些诗:“这是我一生的主要事业。”[55]在说明他怎么会基于“献给М.巴斯马诺娃”的诗写作《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引向与但丁《神曲》的比拟:“遗憾,我没有写一部《神曲》。看来永远也写不成了。而这里却在某种程度上写成了一本有自己题材的小书……”[56]
作者所说的题材是感情的培养,个性的形成过程。题材从相对平静的初恋发展而来(1962—1963年的抒情诗,这些诗在另一处被收入组诗《幸福的冬季之歌》;参见注释26)。这样的平静与对自己和女友的一种自然哲学观点是相符的(“你——是风,小友。我——是你的/树林……”)[57]。两人的关系是必然的,因为和大自然的变化过程——日夜交替、季节转换、潮起潮落不可分割。参与他们的生活的有树林、空气、大海、飞鸟,但完全没有提及另一种人形动物,直至他们不再强制拆开一双情侣(“在牢房的门闩发出/摆脱压迫的响声之后……”,1964)。不过,1964—1965年无论在流放地还是与爱人别离中所写的诗仍然基于自然界的隐喻,可是拆散一对情人的反常力量闯入了生存的正常进程:
我穿着敞开的大衣
世界穿过筛子落入我的眼睑,
穿过迷惘的筛子。
我有点聋,我,上帝啊,有点瞎。
听不见话语,还有整整20瓦
的月光。
(《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
结束这个时期的诗《预言》(1965)是——绝望的个人乌托邦的画面,在这个乌托邦自然界被压缩到海岸边的狭长地带,有一个菜园和牡蛎(这些在早期平静的诗作中也曾提到,如《天使之谜》和《蜜月片段》)。他人的世界,文明自我毁灭的后启示录世界被留在“海堤”之外。抒情题材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1967—1972年在彻底决裂的当时及其后所写的诗。自然哲学的梦想已经破灭:
从赫西奥德曾经颂扬的
那种傻气的旋转木马上
纷纷下来的,不是从座位那里,
而是在夜色就要降临的地方。
(《诗节》,1978)
这个时期的诗有哀诗《六年后》(1968)和《爱情》(1971)。没有自然界的中介而是人际关系及其心理和生活方式直接出现在回忆决裂的诗里。就是在这时布罗茨基开始在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的不朽形象中重新认识个人的悲剧——以直接比拟的方式(“我离开城市,像忒修斯——/离开自己的迷宫,让米诺陶诺斯留下/发臭,而让阿里阿德涅——留在/巴克科斯的怀里细语缠绵。”[《前往斯基罗斯岛的路上》,1967];“像雅各那样,/守护着从楼梯上跑下来的/美人。”[《近于哀诗》,1968]),以及仿佛以古希腊罗马为题材的寓喻形式(Anno Domin,1968;《蒂朵和埃涅阿斯》,1969;《奥德修斯对忒勒马科斯说》,1972)。在侨居国外头几年献给《М.巴斯马诺娃》的诗里,关于失去爱情的挥之不去的思念加强了更广泛的怀旧主题和戏剧性:“……我把枕头拍松,含糊地呼唤着‘你’,/身在海角天涯……”(《那里也没有人带着爱心来……》,1975—1976)。写于70年代末,后来收入《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的那些诗越来越具有冥思的抒情色彩,而在这本诗集编成的几年后所写的《亲爱的,今天很晚我才走出家门……》(1989)和《女友啊,容貌渐衰,你到乡下去定居吧……》(1992)读起来就像是对往日的悲剧的两句讽刺性的附言。不过,什么促使布罗茨基把自己与“М.巴斯马诺娃.”有关的诗说成自己的《神曲》呢?显然,作者本人会比读者更强烈地感受到,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悲剧是足以改变个性的特殊的内心体验。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三首诗:《哀诗》(《到现在想起你的声音,我还是会来……》,1982)、《燃烧》(1981)和《我只是那个……》(1981)。在《哀诗》中“失去女友的人”被比拟为“进化的产物”,即有质的不同的生物,好像一种海生动物爬上陆地,就要适应新环境的生活并学会另一样的呼吸。《燃烧》争辩性地模仿帕斯特纳克的文选诗《冬夜》的形象性,情欲被宗教仪式化,比拟为祭坛上的供品:
你号叫吧,颤栗吧,尽情
抖动你瘦削的肩头。
天上的父啊,
但愿你享用他的袅袅青烟。
三首诗中的最后一首的结尾将人间的爱情等同于宇宙之爱:
天体这样被创造出来。
创造后,往往就这样
让它们旋转,
滥用恩赐。
于是我们时而被抛进热浪,
时而是寒潮,时而一片黑暗,
地球在旋转,
在宇宙中消失。
这个尾声无非是《神曲》末尾诗行的迂回说法:“爱,推动着星星和天体”(俄译者М.洛津斯基)。
四
1963年深秋和1964年初的一个半月是布罗茨基生平最沉重的时期。和巴斯马诺娃的关系出现意外的变化,这种不幸完全控制了他的心情。然而正是在这个内心最脆弱的时期,由于情况的巧合而使布罗茨基成了警察局整治的对象。
在布罗茨基遭难的前一年,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自由化“解冻”时期达到顶点,1962年11月号的《新世界》杂志刊载了А.И.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作品不是对“某些缺点”的批评,而是关于苏联整个规划的反人道本质的寓言。《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后,随之而来的应该是真正的、广泛的自由化。但它的到来只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而1963年,恰恰相反,是意识形态反动的一年。党的高层意识到他们的制度的根基开始动摇,于是抨击自由思想,迎合自己的越来越任性乖戾的领袖。1963年6月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全会上彻底巩固了斯大林文艺政策的复辟。中央委员会抓思想的书记Л.Ф.伊利乔夫的报告论述了苏维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政策。伊利乔夫谈到“年轻、政治上不成熟,却又过于自信、受到无限吹捧”的作家们,他们不再“为人民的英雄业绩而欢欣鼓舞”[58]。谈到要特别注意对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因为“青年中还有懒汉、精神不健全的人,爱发牢骚的人”,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点头赞许下诋毁艺术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原则,而代之以懒汉和不学无术者的鸟话”[59]。伊利乔夫在报告的开头严厉地提醒全国:“在我国的条件下没有选择可言:我想劳动就劳动,想偷懒就偷懒。我国的生活及其法律不提供这种选择权。”[60]的确,尽管苏联宪法所宣布的只是含糊的劳动权,1961年5月4日与“不劳而获”作斗争的法令却从立法上规定,警察有权监督,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必须有固定的工作地点。
虽然布罗茨基落入彼得格勒克格勃及其党组监督人员的视野大约已有三年,起初他们未必在心怀不满的青年作家相当庞大的群体中把他定为最可恶的人物。那时布罗茨基并不比其他非官方的诗人和作家更适合于典型的整治对象这个角色。更准确地说,甚至比其中的很多人都更不适合于这个角色,因为在围场里的插曲之后,几乎认为意识形态腐化的一个必备的特征是形式主义(这意味着任何创新,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的任何背离),而布罗茨基的诗风是比较保守的。大多数年轻人,例如那个索斯诺拉,都更坚决地从事文学形式的试验。可是1963年列宁格勒的国家安全局和与它密切合作的共青团州委注意到,以前的那个小角色由于乌曼斯基和沙赫马托夫的案子而在本市知识青年中特别受欢迎。
11月29日《列宁格勒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依傍文学的雄蜂》。其中把布罗茨基称作“自信地攀登帕尔纳索斯山的侏儒”[61]。文章的标题听起来也是威胁性的:“雄蜂”——“寄生虫”的同义词。“他继续保持寄生虫的生活方式。二十六岁?原文如此!?的健康小伙子将近四年没有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62],——文章的结尾这样说。一个寄生虫,写一些形式主义的颓废的小诗,对西方奴颜婢膝,于是——依据伊利乔夫在六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一个离经叛道的概括形象出现了[63]。
严格地说,即使根据苏联的法律来看,布罗茨基也不是不劳而获。恰恰在这个时期他开始靠写作挣钱。1962年11月号的《篝火》杂志刊载了长篇《小拖船抒情叙事诗》。1962年秋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古巴诗选,有布罗茨基的两首译作,1963年他又有两首译作被收入南斯拉夫诗集,而且已经与这个声誉卓著的出版社有了新的翻译合同。
布罗茨基在“绳索厂厂长别墅”的莫斯科卡先科精神病医院迎来了1964年。朋友们安排他住院检查,希望精神失调的诊断能挽救他免于更坏的遭遇。这个计划是在阿尔多夫家有布罗茨基本人和阿赫玛托娃参加的“军事会议”上通过的,在几位相识的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下才得以实现[64]。布罗茨基当时就描写了这个新年:
在这里的六号病房,
我站到可怕的宿处,
在蒙着脸的白色王国
夜闪着泉水似的白色光辉
与主治医生平分秋色……[65]
最近几个月受尽神经紧张的折磨的布罗茨基害怕了,担心真的会“在蒙着脸的白色王国”丧失理智,几天后就要求朋友们把他从精神病医院解救出来,他们当初把他安排到医院里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1月2日[66]出院后,布罗茨基立刻就知道了玛丽娜已与前男友同居,于是赶往列宁格勒要求解释。几天后他曾企图切脉自杀(依据丘科夫斯卡娅1月9日的日记)。朋友和相识的人都以为,对布罗茨基的迫害和迫在眉睫的判决是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可怕事件,而对布罗茨基来说,此刻的悲剧是失去他视为妻子的女人,其余的一切只是加重这个悲剧的荒谬的环境。对他而言,1964年及其后的一年正是在爱情冲突,而非与体制作斗争的标志下度过的。不论在精神病医院,还是以后在被捕前的几个星期为躲避列宁格勒的警探而奔波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塔鲁萨之间,他都继续致力于抒情组诗《幸福的冬季之歌》的写作。这个标题并非自嘲——组诗渗透了对1962年冬幸福的恋爱时期的回忆。甚至注明1964年1月的诗,其履历的潜台词很可怕,却凸显了与世隔绝的伤感情调:
幸福的冬季之歌,
你就留作纪念,
要在旋律的进展中
回忆其中的冷漠:
你像小家鼠那样
急奔而去的地方,
不论如何称呼,
它都存在于旋律的韵脚里。
…………
就是说,这是春天。
是呀,静脉里的血
太满了:刚一切开
鲜血便潮涌而出。
在那样的现实情况下所创作的《幸福的冬季之歌》,在原则上甚至是挑衅性地不问政治。我们知道布罗茨基在什么条件下写完了《幸福的冬季之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略带讥讽意味的伤感的爱情诗,是关于大自然的诗意的沉思,是大体上淡然的口吻,这种口吻更适合于19世纪的英国乡绅或俄国地主,而不是逃避民警的苏联弃儿——这一切的解释在于自觉选择的道德观,争取内心的独立自主。
去一趟莫斯科回来后,2月13日晚布罗茨基在自家附近的街道上被捕。2月18日在捷尔任斯基区的法院审理布罗茨基的案子。女法官萨韦利耶娃的审问毫不掩饰地表明,她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判决布罗茨基不劳而获有罪。
“女法官:总之,您有什么特专长?
布罗茨基:诗人,诗歌翻译家。
法官:谁承认您是诗人?把您列为诗人?
布罗茨基:没有谁。(没有挑衅意味。)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法官:您学习过吗?
布罗茨基:学习什么?
女法官:学过作诗吗?没想过要进高校,那里有人培养……有人教……
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这要靠教育。
女法官:这要靠什么呢?
布罗茨基:我认为这……(惘然若失)来自天意……”[67]
辩护方的主要意图是争取从宽处理,莫斯科的朋友们为救援约瑟夫而设计的办法是拿到他有精神病的证明——对精神病人能怎样?——于是律师在初审结束时请求将布罗茨基送去体检。
这个请求得到了超乎预期的效果,不是像辩护方所要求的那样解除监禁进行体检,而是把布罗茨基关在“普里亚什卡”三个星期,即普里亚什卡河沿岸街的第二精神病医院,而且最初三天是在狂躁症患者的病房。那里立即开始为他“治疗”——半夜叫醒他,把他浸在冷水浴盆里,裹上湿床单,放在暖气片旁边。渐渐烘干的床单钻心地刺人。1987年有人问他,在苏联的生活中什么时候最痛苦,布罗茨基不假思索地提起在普里亚什卡河上所遭受的折磨[68]。不清楚为什么要让布罗茨基遭受中世纪的酷刑。须知惩罚机关并非要迫使他提供任何情报,根据一切情况来判断,也没有要求他悔过,承认自己误入歧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真的认为他是精神病患者,要用自己的方法治愈他,使他能接受审讯和判决,要么就是医务人员的施虐狂,关于这一点,后来世界从持不同政见者的叙述中了解到,他们都领教过苏联精神病医生的恐怖手段[69]。在列宁格勒没有碰到对布罗茨基怀有善意的医生,普里亚什卡河上的精神病医生作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客观的,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却是致命的:“他所表现的是变态人格的特征,没有精神疾患,就其神经心理的健康状况而言是有劳动能力的。”[70]
3月13日法院第二次开庭,决定要办成示范性的诉讼。诉讼程序分为三部分:审问被告;证人的发言和质询;社会控诉人和辩护人的发言。布罗茨基和法官萨韦利耶娃的对话还是以第一次开庭时的那种荒唐的方式进行。
А. Н.托波罗娃律师回忆道:“布罗茨基的最后发言很精彩。他说:‘我不仅不是不劳而食者,而且将是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诗人。’这时法官,陪审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71]
诉讼程序持续了近五个小时,到晚上很晚才结束。判决甚至使那些不希望为诗人辩解的人也大吃一惊。对布罗茨基的判决是按1961年法令所能判处的最重的刑罚——“从列宁格勒市移居专门划定的地区,为期五年,并在定居点从事义务劳动”[72]。
维格多罗娃无视女法官的威胁而写的布罗茨基庭审记录,不仅对布罗茨基的命运,而且在俄罗斯近代政治史上也是意义重大的文件。几个月里,这篇记录就在非法出版物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还出现在国外,西方报刊也加以援引。此前布罗茨基的名字在西方鲜为人知,而在1964年底,尤其是在法国?Figaro littéraire?、英国?Encounter?全文译载维格多罗娃的记录之后,这位受到凶恶、迟钝的官僚主义者摧残的青年诗人的富于理想的故事,已经完全完全没有苏联贫乏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政客作风的详情细节,这使西方的知识界深感震撼。对了解极权主义的性质的人们来说,对布罗茨基的审判是迫害帕斯特纳克之后的又一个证据,说明在赫鲁晓夫时代的苏维埃俄罗斯,正如在斯大林时代一样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而对很多左派人士来说则是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任彻底破产。
布罗茨基深知,从健全理性的视角来看,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十分荒谬的,同时也深知自己与国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正如他的辩护人所强调的那样,他从未写过任何反对国家的诗歌。他的国家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体制,因而更接近于柏拉图的极权主义乌托邦,而不是霍布斯的实用主义利维坦。“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十卷有一段著名的话,说诗人是扰乱社会秩序的疯子,应该逐出理想国:“?诗人?唤醒、培育、加强心灵中最恶劣的一面,毁灭心灵的理性本源;?……?他个别地向每个人的心灵灌输坏的国家体制,纵容心灵的非理性本源……”[73]布罗茨基在1977年写了《发扬柏拉图精神》,这首诗回忆群众怎样“在周围暴跳如雷,大声喊叫,/用劳累过度的食指戳着我:‘你不是我们的人!’”。维格多罗娃的笔记还记下了休庭时在法院大厅里的谈话:“作家们哪!把他们全都赶出去才好!知识分子!硬是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我也要开始写作,译诗呢!……”[74]
布罗茨基不喜欢回忆1964年3月的审判。记者对他生平的这个小插曲的过度关注引起了他的抗议:他希望被看作诗人,而不是制度的牺牲品。
据我们所知,布罗茨基在普里亚什卡没有写过诗,不过在2月13日被捕后到18日被送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前,他在牢房里每天都写,在以《囚犯须知》[75]为总标题的四首小诗注明写于14、15、16和17日。写于2月15日献给阿赫玛托娃的八行诗《二月里春天还远……》(即东正教的奉献节——阿赫玛托娃的命名日)也是一幅大自然的微型画(讽喻人到中年的女诗人的容貌),不过其余的短小诗句都基于监狱里的直接印象:牢房的寒冷、电灯的强烈光线、打瞌睡、在封闭的空间往返踱步。突然,第四首诗《在牢房散步之前》的末尾出现了与美化的神话的比较:作者置身其间的那种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与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一件大功绩——前往赫斯佩里得斯圣园获取金苹果的旅行。同样的对比,人身卑微的不自由和想象力的自由,监狱封闭的——就其本义而言——空间和无限的文化空间的对比,布罗茨基的两首八行诗抨击得更加尖锐,这两首诗布罗茨基写于自己的生日1965年5月24日,当时他被羁押在区民警局的禁闭室。他因为休假迟到而受到羁押几天的惩罚。
夜。禁闭室。监视孔
直刺我的瞳孔。
执勤的民警在咕噜咕噜地喝茶。
我觉得自己好像大街上的垃圾桶,
命运把成堆的垃圾倒进去,
每个垃圾都往里面吐唾沫
琴丝刺人的竖琴
在茅坑的后面。
沼泽地在侵蚀土坡。
而以天为背景的一名哨兵
完全就像福波斯。
你往哪里钻哪,阿波罗!
在对禁闭室和从监狱窗口看围着带刺铁丝的茅房的自然主义描写中,绕开戏剧性词汇,使用刑事案件的行话(“行窃的黑话”),这就强烈地突出了福波斯-阿波罗在诗末的出现。作者以注意细节的习惯审视着监狱的禁闭室和囚禁其中的自己。作者的立场是在禁闭室之外,总之是“在外面”,即绝对自由的立场。某种重要的情况发生于监狱的简朴的素描——布罗茨基诗学的哲学原理诞生了。受难被看作人类生存的条件,世界就是它本身的样子。“直插”这个不雅的词与福波斯-阿波罗邻近消除了不体面的性质,修辞的两极在作品中自然地相遇,作品不评论生活,不数落生活,而是描绘生活。狱中诗意味深长的是感情的持重,特别是没有那种普遍的狱中抒情主题——抱怨、自怜。这是原则性的方面。十五年后,布罗茨基开始以诗总结自己四十年的人生历程,回忆狱中的体验(“我代替野兽走进笼子,/像墙上的钉子熬尽期限和癔病女患者的狂叫……”),强调自觉地接受灾难(“我把押送兵发蓝的瞳孔放进了自己的梦里……”),严禁内心脆弱的表现(“我允许自己接连发出任何声音,除了哀号之外……”)。
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往往被称为“卡夫卡式的”,意思是缺乏法理逻辑、控诉的荒谬和令人憎恶的氛围。不过对布罗茨基来说,审判的确是卡夫卡式的,不过另有含义。须知卡夫卡的《审判》不仅涉及人会被审讯和处决而不明所以,还涉及人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审讯他,却还是觉得自己有罪。这种全人类的存在主义罪恶感不一定与犹太基督教的原罪观念有关,从来就存在于布罗茨基的诗和一般的精神生活。在布罗茨基的伦理学和诗学中,与罪恶的主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宽恕的主题。阿赫玛托娃的话:“你不知道,人家宽恕你了……”——他带在身边走过一生,作为护身符[76]。
五
四月中旬指派布罗茨基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关押解送犯人的监狱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诺什区的移民点。监狱、押解人员的侮辱是不小的考验,而流放地的生活却并不那么可怕。后来在西方,记者谈到布罗茨基的遭遇时提及“古拉格”和某些虚构的“流放北极地区从事劳动的移民村落”[77],这就可能使不太了解俄罗斯地理及其他实际情况的读者产生永久冰层和镣铐的想象。
流放不是日常的田园生活,时常思念家乡,时而会有完全被遗忘的感觉,但布罗茨基的回忆却不是这样:“……我生平最好的时期之一。有些时期也不坏,然而更好的——好像不曾有过。”[78]
流放犯要自己找工作。布罗茨基找到的工作是当“长工”,即国营“达尼洛夫斯基”农场的杂工。他碰巧要干的“杂工”是田间作业:
布罗夫——拖拉机手——和我,
农业工人布罗茨基,
我们在播种越冬作物——六公顷。
我在观察林木茂盛的地区
和有一条反光带的天空,
我的一只皮靴触及制动杆。
子粒在耙子下面扎煞,
发动机的轰鸣响彻四周。
飞行员在乌云间留下自己飞舞的笔迹。
面向田野,背朝震动,
我自己是播种机的点缀,
满身粉尘,好像莫扎特[79]。
在另几首诗里他提及当桶匠(《制轮匠死了,桶匠……》)、屋面工(《我代替野兽走进笼子……》)、马车夫(《踏上泥泞的道路》),而根据他本人的回忆我们知道,他曾在树林里集运原木和放牧小牛。
他在诺林斯卡亚村找到了住所。“那里有36栋或40栋木屋。不过只有14栋有人居住。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其余的居民,略微有些生存能力和力气的年轻人都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那里穷得可怕,是没有希望的地方。”[80]
虽然布罗茨基回忆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流放地的生活是自己生平最幸福的时期之一,却并不意味着他在诺林斯卡亚村的生活安然自得,无忧无虑。对来往自由的限制使他难以忍受,尤其是不能与巴斯马诺娃相见。1964年在流放地所写的诗(24首完篇或未完篇的诗)几乎有一半或献给不在身边的巴斯马诺娃,或干脆以离别为主题。其中只有一首《发扬克雷洛夫精神》描写田园牧歌似的场景,两人在一起悠闲地散步。翌年关于爱情和离别的诗——占三分之一。此外,1965年所写的叙事诗《费利克斯》把情敌讽刺地描绘成婴儿型的色情狂(СИБ-2,том 2,стр.154-160;这篇作品布罗茨基没有发表,到70年代才在小圈子里为人所知,这要归功于马拉姆津斯基的汇编)。布罗茨基的严厉的批评者А.И.索尔仁尼琴注意到出现于流放时期的诗句“……土地、一切在生长繁殖的植物、马匹和农村劳动起着使万物欣欣向荣的作用”。“甚至透过令人惊愕的埋怨声——大地、俄罗斯乡村和大自然的呼吸会出其不意地提供顿悟的萌芽。‘在乡村,上帝不是生活在某些角落,/像嘲笑者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无处不在……’”[81]这样说只是部分正确。俄罗斯的大自然,乡村生活白天和季节的一系列活动经常出现于布罗茨基的抒情作品,至少从1962年起是这样。由于多种原因的综合,这一类的诗排挤了早期抒情作品的城市主题和书卷气。其中既有市郊生活的直接印象,也有对巴拉滕斯基哀诗的爱好,也有对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的初步认识,从诗风的某些特点来看,还有帕斯特纳克晚年作品的潜在影响。
在流放地布罗茨基外于——或者说先于——其余的一切思索着诗歌艺术的原理。他曾在1965年6月13日致雅科夫·戈尔金的信中加以阐释。信里有两个基本论点。其一涉及创作的心理学,其二布罗茨基称之为“实践性的”,——涉及构造单个诗句或短诗的几个原则。在心理上,作者应该只遵循自己的直觉,不论直觉把你引向何方,要绝对独立于准则、规范,不必顾忌权威和假定的读者。“要独立。独立——在任何语言里都是最优秀的品质。哪怕会导致失败(蠢话)——这不过是你个人的失败而已。你要自己清算自己;要不,鬼才知道该清算谁。”[82]对作品的要求也起着毫不逊色的决定性作用。“在诗歌中最主要的是结构。不是题材,而是结构。这是不同的。?……?必须安排结构。例如:关于一棵树的诗。你开始描写你所见到的一切,从土壤起,往上描写到树梢。你请看,这就是伟大的作品。应该习惯于把画面作为整体来看……没有整体的部分是不存在的。?……?不是用逻辑,而是以心灵的悸动——只有你自己明白的悸动——把诗节连接起来吧。?……?主要的在于——这就是所谓的戏剧性原则——结构。须知隐喻本身就是——微型精细画的结构。我承认,我觉得自己更像奥斯特洛夫斯基,而不是拜伦(有时我觉得自己是莎士比亚)。”[83]抒情作品的戏剧性,作为作诗战略的结构——这实质上是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特纳克语义学诗体的基础[84]。
布罗茨基去流放地是一个诗人,而过了两年不到回来成了另一个诗人。改变不是瞬间发生的,但变得很快。流放第一年,即1964年所写的诗,基本上还是1962—1963年的那种表达方式。因此两者在诗集《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里是那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明显的例外只有上面讨论过的狱中组诗和年末所写的Einem alten Architekten in Rom(《致罗马的老建筑师》)。后者的标题接近于重复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诗题《致罗马的老哲学家》。早在同年秋布罗茨基还改动了拜伦的诗题《献给奥古斯塔的四行诗》——《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关于《我窗外,木窗窗外,有几棵树……》这首诗,布罗茨基说他是作为弗罗斯特的诗题《我窗外的一棵树》的变体来写的。他从前也读过译本,还想读原版英美诗歌,不过在诺林斯卡亚村才开始用心地领会英语诗的内涵。他手边有一本很好的英俄词典,有很多书,其中包括路易斯·安特梅尔和奥斯卡·威廉姆斯的诗选[85]。每到傍晚他就在村旁小河边的木屋里心无旁骛地在词典里查找与英语词准确对应的俄语词,缓慢地阅读英语作品。这样专心阅读的一个附带的效果是自然而然地对英文有了很好的了解,然而这时他感兴趣的对象已不是另一种语言,而是另一种诗。英语诗逐渐展现在他面前,不像俄语诗,也不大像他以前读过的那些译作。
布罗茨基究竟吸取了英美诗的哪些教训呢?初看似乎是英国的巴洛克诗体给布罗茨基的风格打上了最鲜明的印记。在诺林斯卡亚村他初次对最伟大的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创作有了充分的认识(他自己的《献给约翰·多恩的大哀歌》写于1962年,当时他对多恩的作品还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关于钟声的风行一时的引文,它“为你而鸣”)[86]。他曾译过多恩和马韦尔的作品,细心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们的诗意冥想往往表现于展开的(放大的)隐喻。这样的隐喻和比拟又称为“协奏曲”(来自意大利语concetto,“虚构”,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炼,想象的建构)。“协奏曲”是全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典型特点,不过布罗茨基潜心阅读的原作主要是英语作品,尤其是波兰语作品。17世纪玄学派诗人通常把感觉、心情比拟为物理客体及其功能,似乎与激动诗人的主题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不同于浪漫派动人的一次性比拟(例如,“少年的欢娱已逝,/如梦,如清晨的雾”),巴洛克风格的转喻的发展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允许作者闪耀想象和机敏的火花。安德鲁·马韦尔就在《爱的决定》中这样运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公设:
As lines, so loves, oblique may well
Themselves in every angle greet;
But ours, so truly parallel,
Tough infnite can never meet.
(好像直线,爱情也是这样,倾斜时
可以/从任何角度迎向对方;/
可我俩,就是真正的平行线,/
即使无限延伸,也永远不能相交)[87]。
布罗茨基曾在60年代的诗中试验类似的隐喻,悉数收入《美好时代的终结》:《纪念塔季扬娜·布罗夫科娃》、《纪念保卫汉科半岛的英雄的喷水池》(整首诗都是展开的隐喻),而极端的表现是长篇诗作《没有伴奏的歌声》,其中几何学的隐喻——被不可跨越的空间隔开的情侣的视线好像直角三角形的两条边,在天上相遇——在244行诗中所占的篇幅长达120多行。
众所周知,古典主义时期所排斥,浪漫派诗人所遗忘的巴洛克风格,是在现代主义中复兴的——先是复兴于19世纪末法国象征派诗歌,稍后是英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Т. С.艾略特所理解的历史性纲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决定性地影响了20世纪的英语诗。不过,玄学派的隐喻在新的体现中是以浓缩的形态出现的:以复杂的逻辑结构解释诗人怎样联接相距颇远的概念,而寄望于有准备的读者的领悟能力。例如,埃利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开头两行就是这样:
When the evening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the patient etherized upon a table.
(当暮色在天空蔓延的时候/被麻醉的病人正在手术台上。)
原则上相似的隐喻也是俄罗斯现代派的鲜明特点。例如,试比较马雅可夫斯基《裤子里的云》引自埃利奥特的比拟:“12点钟落下,/好像死刑犯的头颅滚落断头台。”或如帕斯特纳克关于情妇的诗《由于迷信》:“她带着椅子进来,/好像从隔板上拿下我的生命/吹掉上面的灰尘。”尽管有个人的各种差异,原则上同一类型的玄学派浓缩隐喻既是茨维塔耶娃也是曼德尔施塔姆的特点,很可能正是有鉴于此,布罗茨基才在致戈尔金的信中写道:“隐喻是一个微型结构。”60年代下半叶他也主要倾向于这种隐喻形式。1958年的诗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均见ОВП)。
在洗衣桥上,我和你曾
模仿刻度盘的指针,
指针在十二点相逢,此后
不是分别一昼夜,而是永别……
(《洗衣桥》)
只有倾盆大雨刺激着我昏昏欲睡的神智,
仿佛守财奴走进远房亲戚的厨房,
这时通过我耳鼓的:
还不是音乐,却也不是噪音。
(《近于哀诗》)
不过我们看到,布罗茨基不同于本国的上一代诗人,在尝试古代巴洛克艺术手法时,似乎是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演绎着现代派对现实的观感和与之有关的隐喻方式的前史[88]。他这样做有时不免有损于情感的表现力(只要比较一下《没有伴奏的歌声》和与之有关的传记题材《莎霍区》就能看出,情感的表达比后者更复杂,也更富于张力,就因为后者没有展开仿古的隐喻)。显然,由于某些内在的原因,布罗茨基感到有必要完成17世纪的功课,弥补俄罗斯诗史的缺口。不能说,俄罗斯诗歌完全放弃了巴洛克风格的诗学。布罗茨基喜欢推荐安季奥赫·康捷米尔的顿涅茨诗行,援引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的巴洛克风格的俄语诗和乌克兰语诗,并发掘杰尔查文甚至巴拉滕斯基对现实的巴洛克风格的反映,然而对巴洛克风格和现代主义同样典型的理智语言和情感语言的有机融合,他首先是通过在烛光下,在俄罗斯北方的木屋里深入研读英语诗而加以掌握——那里的环境从17世纪起就很少变化。
说布罗茨基诗体范围的急剧扩大就是开始于诺林斯卡亚村,未免停留在现象的表面。急剧的变化发生于诗的个性的结构,因而这个新“我”需要自我表现的新形式。像在列宁格勒的法庭上那样,回避自己和正在进行中的事态是脱困的良策,同样,布罗茨基在1964年和1965年之交认识到,作品的作者与作者的“我”异化会展现怎样的可能性。
……这是最好的方法,
可以拯救强烈的感情,以免弱势群体
介入。希腊的假面原则
重新流行。
(《再见,韦罗妮卡小姐》)
作者的新观点最鲜明地表现于诗的体裁,这种体裁在20世纪俄罗斯抒情诗中被视为陈旧的或处于过渡状态,正是由于在有故事情节的诗里没有更恰当的术语。19世纪“诗体故事”是相当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奥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А.К.托尔斯泰的历史题材的抒情叙事诗,以及这样一些有故事情节的诗,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莱蒙托夫的《将死的斗士》,涅克拉索夫的《毛发》——只是大量例子中的几个而已。到20世纪这种体裁过时了。写作和出版了大量有故事情节的诗,短篇和长篇的叙事诗都有。这样的作品“是民众容易懂的”,其实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化产品的思想检查官容易懂,当然,也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服务于宣传的目的。但高雅的现代派俄语诗几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节。于是早期马雅可夫斯基或茨维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诗,阿赫玛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文化学的冥思,也像安年斯基、勃洛克、帕斯特纳克、叶赛宁的抒情诗一样倾向于极其准确的自我表现。这种纯抒情诗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的同一性。这一类抒情诗总是充满激情,而且诗里的情感总是明确地表现出来。马雅可夫斯基的《长笛-脊柱》和《裤子里的云》,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歌》和《山之歌》表达了痛苦、绝望和对周围世界的蔑视和憎恨,或帕斯特纳克诗集《妹妹是我的生命》中的欣喜、对自然哲学的热衷,或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如《失眠。荷马。鼓起的风帆……》、《瓶子里流出蜂蜜的金色细流……》的激动人心的喜悦、对诗学思考的重要性的强调,而最常见的——从安年斯基和勃洛克到叶赛宁——是生活的寂寞和因之而起的自怜之感。从诗歌艺术的语用学观点来看,可以说这类抒情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充满好感的个人关系。诗人所体验到的感觉、心情包罗万象,因而很有感染力。正如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所说明的那样:“艺术是人类的活动,在于一个人有意识地以某种外在的符号把他所体验到的感觉传递给别人,而别人受到这些感觉的感染,也就能体验到。”[89]就抒情诗而言,这样以虚构的人物“别人”代替“我”,而且这个人物所处的环境与作者的生活环境显然不符,这就破坏了可信度。因此甚至俄罗斯现代派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内心的倾诉(上面提到的马雅可夫斯基和茨维塔耶娃的叙事诗、帕斯特纳克的诗集,其中的抒情自白压倒了故事情节,不论1905年的革命、施密特中尉的叛变还是玛丽娅·伊利英娜的传记)。俄罗斯现代派诗歌中的例外纯属试验性的作品(例如布留索夫或谢利温斯基的诗),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吉洪诺夫早期的通俗叙事抒情诗、巴格里茨基的某些作品都是,不过这些诗人也主要留在亲密抒情的传统轨道上。20世纪俄罗斯唯一以其主要创作摆脱这个传统的大诗人是米哈伊尔·库兹明。从早期的《亚历山大之歌》到稍后的诗体小说集《福雷尔破冰》,库兹明在抒情作品中采用的是“希腊的假面原则”,时而还写一些“像散文”的诗,即采取讲“别人的”故事的形式,其情节有时还相当复杂。
俄罗斯现代派诗歌中的例外,在那个时期的英语诗歌中却是典范。托马斯·哈代、У.Б.耶茨、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罗伯特·弗罗斯特、埃德加·李·马斯特斯、Т.С.艾略特、У.Х.奥登都同样地既写第一人称的诗,也写关于“别人”的诗。他们对虚构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描写,详细地描述他们的生活场景,往往在诗中使用直接引语。当然,这些诗使俄罗斯青年读者感兴趣的首先应该是,在放弃情感的直接自我表白的条件下,诗赖以达到感染效果的那个因素,抒情性。就其最一般的特征而论,可以说,尽管这样的诗往往很长,而且其中的描写也很详细,但足以感动读者的主要的东西,却是作品中所没有的。情感的感染力在于言不尽意,在于意味深长的潜台词[90]布罗茨基认为罗伯特·弗罗斯特是近代英美诗歌的中心人物,关于他的诗的艺术准则,布罗茨基是这样说的:“……弗罗斯特的叙事的主要力量——与其说是记述,不如说是对话。弗罗斯特笔下的情节照例发生在四壁之内。两个人彼此交谈(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在彼此之间什么话不说啊!)。弗罗斯特笔下的对话包含作者的一切必要的情景说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布景、动作。这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简直就是一出芭蕾舞剧。”[91]特别重要的是所指出的并非抒情艺术的古典范例,而是古希腊的悲剧(在那次谈话中布罗茨基还由于弗罗斯特而提及普希金的“小型悲剧”)。抒情作品的戏剧化(在前面引述的致戈尔金的信里他说:“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而不是拜伦”),利用“舞台”、“演员”,使他可以包罗万象地转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诞,而在浪漫主义抒情独白的传统形式中,存在主义悲剧很容易就被偷换成个人的抱怨。
这种沉思的结果是这样的一些作品,如?Anno Domini(公元)?、《致Z.将军的信》、《烛台》、《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1968)、《雅尔塔的冬日黄昏》、《献给雅尔塔》,组诗《选自?校园诗集?》和与之有内在联系的诗《处女作》、《品茶》(1969)、?Post aetatem nostram?(1970)、《致罗马友人的书信》(1972)等,沿着这个方向所跨出的最初几步见于这样的一些作品,如?Einem alten Akhitkten in Rom?(1964)、《预言》、《容器里的两个小时》(1965)和《喷水池》(1966)。这都是布罗茨基创作中驰名的诗,其体裁和风格在布罗茨基之前的20世纪俄罗斯诗歌中罕有相似的现象。不过,与此同时,布罗茨基也继续在传统的抒情方式上痛下工夫。最后,在英语文学的影响下出现的新动向与传统并非分道扬镳。在布罗茨基那里,最有成效的恰恰是折中主义的方法——从我-叙述到他-叙述、从中立的讽刺风格到隐秘的激情自由转换(例如《容器里的两个小时》、《预言》和《雅尔塔的冬日黄昏》)。到70年代中叶,这种折中主义产生了对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诗都非同寻常的结果,即作诗的“我”的结构战略——把自己作为别人来描写。“完全无足轻重”,“一个人/身披斗篷”在《潟湖》(1973)中初次登台,此后有一系列短诗,其中的“我”都处于孤立的个人空间,与世隔绝——往往是在咖啡馆的小桌边,在毫无特色的旅馆房间里或街心公园的长椅上,而且在平流层的“我(鹰)”也包括在内。诗中的这个角色与世界的联系——是目视的,是早期一首诗所说的“记住细节”的才能,是稍后的一首诗所说的要珍视“细节的独立性”。
在诺林斯卡亚村阅读英语诗时,布罗茨基有一次体验了宗教迷信所谓的瞬间顿悟。他是这样描述的:“……书(《英语诗集》)完全偶然地翻在奥登《回忆耶茨》的那一页……这首诗用四音步写成的第三部分中的八行听起来好像救世军军歌、出殡赞美歌和儿歌的混合体:
[Time that is intolerant
Of the brave and innocent,
And indifferent in a week
To a beautiful physique,
Worships language and, forgives
Everyone by whom it lives;
Pardons cowardice, conceit,
Lays its honours at their feet.]
[Время, которое нетерпимо/К храбрым и невинным/
И за одну неделю становится равнодушно/К кра-
cивой внешности, //Поклоняется языку и прощает/
Кажого, кем язык жив; /Прощает трусость, тщеславие,/
Складывает свои почести к их стопам.]
“记得,我坐在农村的小木屋里,一个正方形的窗户只有飞机的舷窗大,我望着窗外潮湿、泥泞、有几只鸡在走动的路,对刚才读到的东西半信半疑,该不是我的语言知识同我开了个玩笑吧。”[92]
在我们看来,在布罗茨基的意识里,就像拿书占卜时一样偶然出现的奥登的这些诗行,使他聚焦于这个时期内心最深沉的思考、怀疑、感受的两种倾向。首先是宗教道德对罪孽和宽恕的感受。布罗茨基被判处流放是无辜受害,然而存在主义的负罪感是他所固有的(所以后来他才把自己的感受称为“卡尔文主义”的道德)。正如我们所知,那时只有阿赫玛托娃理解了布罗茨基在流放中所感受到的这种道德危机,并把它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里的危机感。被看作神谕阅读的奥登的诗预示着宽恕,条件是真诚地献身于自己的使命:成为语言赖以为生的人之一。
其次,对布罗茨基来说,奥登的八行诗是魔法水晶球,他在其中找到了答案,回答了对他而言至关重要的语言和时间的本性问题。英国诗人朴实的话语使他确立了语言重于个人意识和集体存在的观念。这些想法弥漫于时代的氛围,好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萨丕尔的文化学,以及急剧扩大影响范围的符号学的辐射形传播。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一切存在都是符号体系,都是语言;生活表现为交际的网络——信息的传递、接收、曲解、不接收(正如布罗茨基在《与天人交谈》中以不可知的笔调所写的那样,甚至对上帝的信仰也“不过是一种邮件/单向的”)。萨丕尔把语言的结构比拟为留声机唱片上的纹路——人类的思维只能沿着这些纹路运行。海德格尔教导说,存在是在语言中实现的。对此奥登作了补充:语言需要诗人,使语言始终是鲜活的语言。当然,奥登是在重复旧的真理,布罗茨基已经听说过。归根结底,甚至词源本身也指明了这一点,“поэзия(俄语,诗)”——源于希腊语poeisis(诗)、“делание(创造)”,即以语言作为工具、创造以前不曾有过的东西。而在沉重的怀疑、近于绝望的时刻,奥登的话帮助布罗茨基确信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从一切迹象来看,与奥登诗行的那次至关重要的接触是发生在深秋,一月初布罗茨基从西方广播中获悉艾略特的死讯,在1月12日写完《艾略特之死》,首行在很多人看来是对三十一年后布罗茨基自己的预言:“他死于一月,在一年之始……”实际上这简直就是近似地翻译了奥登关于耶茨之死的首行:“他消失于隆冬……”(“He disappeared in the dead of winte ...”)这首诗大体上是模仿奥登哀诗的三部分的结构。第一部分展开诗与时间以及时间与海洋的比拟。时间是循环的——日、周、年的周而复始。诗也基于语音(尤其是诗行的末尾——韵脚)、有节奏的人物、形象、情节的有规律的重复,时间被描绘成海洋及其潮起潮落所形成的波浪的律动。(十年后他又在组诗《言语的一部分》中回到这种复杂的“玄学的”比拟,其中的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我生长于波罗的海沼泽地,靠近/铅灰色的波浪,波浪总是成双地涌流,/于是所有的韵脚——便由此而来……”)冬季节日后结冰世界的画面在电影平面图的交替中提供——从推摄扫出“门外的碎片”到从平流层向海洋和大陆的一瞥。形象是具体的、物质的,正如艾略特所要求的那样。然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其思想的成熟和表达的晓畅而言逊色于范例——奥登的哀诗。耶茨逝世时,奥登是比二十四岁的布罗茨基年长许多也远为成熟的诗人。布罗茨基还只是开始走上自己的路,写于1965年1月12日的这首诗只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个路标。
1965年1月初,被奥登关于耶茨之死的哀诗激起灵感的布罗茨基每晚在国营农场劳动后为艾略特之死写诗的时候,在莫斯科,维格多罗娃、丘科夫斯卡娅、格鲁季宁娜、阿赫玛托娃和诗人的其他辩护人孜孜不倦的斗争,他们踏破门槛、写信,对多少有些影响力的人物的劝说开始生效。布罗茨基于11月23日正式获得自由。
布罗茨基为获释而高兴,依旧为了与情妇的复杂关系而忧虑,写诗,而对一年半的磨难尽可能地少想。他所发生的一切使他感到惊讶的首先是自己的荒谬。“折磨的总和产生荒谬”,——几年后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下了这样的结论[93]。
六
1965年从流放中回来,1972年出国,这七年间布罗茨基在苏联社会的处境很奇怪:他获准自由生活,靠笔墨维持生计,却没有正式作为诗人而存在。
他仍然处于克格勃的视野之内,尽管直接的迫害停止了。审判和逮捕的丑闻使布罗茨基在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处境有了重大转折,新当选的理事会大体上是自由派,很赏识布罗茨基。使他成为协会会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但有一个附属协会的“职业小组”,这个小组团结了一些人,这些人从事文学工作,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成为协会的全权会员。布罗茨基回到列宁格勒,也立即被安置在这里。这样他的身份证就有了机关印记,这是他免于不劳而获指控的证书。他像被捕前一样,继续翻译写作儿童诗,有时在刊物《篝火》和《火花》上发表,并尝试其他与文学有关的工作,例如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外国电影配音译制片的文学加工。偶尔因为他在私人场合读诗而付钱给他,这是向听众收取的应得的报酬[94]。
安排与心爱的女人同居的尝试在流放后又持续了两年。他们时而同居,时而分开住。1967年秋玛丽娜和约瑟夫有了儿子安德烈,可是此后不久,在1968年初,也就是在初遇的六年之后,他们彻底分手。
我和她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我们用自己的身影
做各自的门——工作也好,睡觉也好,
却始终敞开门扇,
显然,我们就是穿过这些门扇,
走出暗道,奔向未来。
(《六年后》)
不能说,布罗茨基不在意他的诗能否出版。正如很多真正的诗人——不同于爱慕虚荣的业余爱好者,他对发表作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怕一旦发表作品会彻底脱离作者。诗歌创作——永远是心理宣泄的体验,他想延长这一过程。未发表的诗仿佛尚未完成,而发表了——就是永别。另一方面,布罗茨基在受审时关于他怎样看待自己的社会地位所说的并非空话。他自觉地认为,出版是必要的,早在60年代中叶,他的草稿中就有诗作目录——未来诗集的构成。他在那时的谈话中曾把诗集出版,自己的工作得到社会的承认,称之为“正义的胜利”,只有这过分夸张的表达方式才有开玩笑的意味。
1965年在布罗茨基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诗集《短诗和叙事诗》(СИП)在纽约出版。它主要是根据未经作者认可的非法出版物的抄本付印的,布罗茨基从来不承认它是自己的[95]。散见于侨民期刊,国内读者无缘得见的作品,以及开始出现的某些诗歌的外语译作,再要称之为“正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布罗茨基在列宁格勒作家圈子里的众多同情者,也像莫斯科的熟人一样,希望从流放地回来后能随即出版布罗茨基的诗,这方面的集体努力似乎会产生效果。1965年底或1966年初布罗茨基就按照有自由派倾向的编辑们的建议将诗集手稿交给苏联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他建议以“冬季邮政”为书名,不同于美国版的诗集,本书所收集的主要是1962—1965年的诗作。布罗茨基被蒙骗了整整一年,此后他向出版社要回了手稿。
他的第一部真正的诗集《在旷野扎营》1970年出版于纽约。这是大部头的书,其中有70首短诗,有叙事诗《以撒和亚伯拉罕》和《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书末还有译自约翰·多恩的四篇译作。《以撒和亚伯拉罕》和22首短诗(其中的15首写于1963年之前)与收入《短诗和叙事诗》的重复,但这部诗集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成熟的新作。所有幼稚、模仿性的作品一概淘汰,甚至包括《四行诗》(“连国家、乡村墓地也……”)和《列宁格勒附近的犹太人墓地……》那样曾风行一时的作品。各部分中诗的分节和顺序是作者缜密构思的结果。1968年6月布罗茨基在列宁格勒将手稿的主要部分交给其诗歌的译者美国教授乔治·克赖恩。对私带手稿出境的美国人,尤其是布罗茨基而言,这是一步险棋。在不久前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诉讼案之后,“将手稿交给西方”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间谍活动”或“叛国”。尽管布罗茨基的诗没有任何类似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政治讽刺内容,可是苏联的惩罚机关很容易就能将《玻璃瓶里的信》、《在旷野扎营》和《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某些章节解释成反苏维埃的。
《在旷野扎营》的结构的两大支柱是诗集之首的《以撒和亚伯拉罕》和卷末的《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在布罗茨基精神演变的道路上,这两部叙事诗标志着掌握《圣经》——《旧约》和《新约》的不同阶段。在其作诗的道路上则标志着其独特风格的形成和确立:结构手法、词语的形象体系(象征性词汇)、独创性的诗律。
《以撒和亚伯拉罕》是布罗茨基创作中第一部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是他的诗中唯一的经过提炼的《旧约》题材。在世界艺术中得到广泛反映的亚伯拉罕祭祀的故事(《创世记》,第22章),布罗茨基以前也不可能不知道,即使看过冬宫博物馆的伦勃朗的画,不过写作这部叙事诗正好是在他生平头一回阅读圣经的时候:“我简直在看完《创世记》的几天之后就写完了《以撒和亚伯拉罕》。”[96]也就是在那时,布罗茨基读了克尔恺郭尔的《畏惧与颤栗》。正是在这里,克尔恺郭尔在思考亚伯拉罕的祭祀时得出结论,宗教感情是超越理性的,“信仰的骤变”是必然的。由于这个缘故布罗茨基也了解了列夫·舍斯托夫的思想(《克尔恺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
关于布罗茨基在1963年5月怎样致力于《以撒和亚伯拉罕》的创作,Н. Е.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写道:“……他向我详细地——可以说是从结构方面——讲述了还是草稿的《以撒和亚伯拉罕》。例如曾讲到КУСТ——其中的每一个字母会有什么含义。一切都恰如后来出版的叙事诗,然而这是当时的讲述啊。这使我感到震惊:我不知道,而且至今也不大明白,诗还可以这样写,诗人早就成竹在胸,并拟订计划(但可以回忆一下普希金的写作计划)。”[97]
至于还有什么能使布罗茨基想到叙事诗的计划,А.Я.谢尔盖耶夫有这样的记述:“……他说,在分析罗宾逊的叙事诗《艾萨克和阿奇博尔德》时,他暗自把主人公改为‘以撒和亚伯拉罕’。”[98]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的《艾萨克和阿奇博尔德》(1902)几乎是田园牧歌。俄罗斯读者读着十二岁男孩和老人艾萨克(以撒——美国基督教徒常用的名字)徒步旅行去老人阿奇博尔德家做客的故事,会想起契诃夫的《草原》。罗宾逊的叙事诗的潜在情节是——生命的终端和开端的对比,是孩子关于死亡的最初的思考。《以撒和亚伯拉罕》与罗宾逊叙事诗的内容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过,应当考虑到布罗茨基的如下评语:“记得我曾与阿赫玛托娃讨论以诗体改写圣经的可能性问题。在美国这里,没有哪位诗人会做这种尝试。埃德温·阿灵顿·罗宾逊是愿意这样做的最后一个人。”[99]
有时《以撒和亚伯拉罕》被视为布罗茨基以犹太人为题材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操俄语的以色列批评家塞夫·巴尔-谢拉提出了这样一种极详尽的解释。他把这部叙事诗看作圣经的诗体诠释。诗人试图遵循喀巴拉的神秘教义,以以撒和亚伯拉罕的故事破解犹太人的使命,同时通过这次创作为自己解决阿多诺的悖论:“在大屠杀之后还能写诗?”[100]
如果说这位以色列批评家认为,布罗茨基以克尔恺郭尔为出发点而转向以色列人历史的玄学方面,那么在不列颠文艺学家瓦莲京娜·波卢欣娜的阐释中,作家布罗茨基却比克尔恺郭尔更具有基督教精神:“布罗茨基在自己的叙事诗中改变了视角,力求看透亚伯拉罕故事的含义。叙述的核心不是父亲,而是儿子。以撒像亚伯拉罕信任上帝一样信任自己的父亲。看完这部叙事诗,我们得出结论,也许,对阴森的上帝之谜的回答总是浮在表面上。归根结底,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只是上帝对自己的同样的要求: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儿子。”[101]
毕竟对布罗茨基未来的个人及其创作的命运而言,《以撒和亚伯拉罕》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掌握克尔恺郭尔的神学,至少是其神学的基本公设:绝望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人的本体论罪孽/人有罪并直接站在上帝面前(后来布罗茨基把这一切形容为自己的“加尔文主义”)。1965年5月14日致友人的信里有一句话说明了《以撒和亚伯拉罕》对布罗茨基精神形成的特殊意义,信里诗人对自己的全部创作给予了轻蔑的评价:“重要的只有《以撒和亚伯拉罕》。”[102]对作者来说,《以撒和亚伯拉罕》成了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工具,自我认同的工具,不是根据宗教、民族或社会特征的认同,认同的只是注定要在精神上永不休止地艰苦探索的人。
《以撒和亚伯拉罕》——也是布罗茨基语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词的形象是作品的内容丰富的核心,只有放在他的整个创作的语境中才能真正了解:荒漠/沙土,丘陵,灌木/森林/树叶,蜡烛/火光。使用“独立的细节”是构建标志的基本方法。对木板——一个真正的独立的细节——的描写就是这样,因为作者并不说明这是什么样的木板,在游牧的犹太人宿营地的几个帐篷中这块木板是从哪里拿来的。他描写宿营地、帐篷、向一个帐篷的里面窥视,仿佛是贴近一个裂缝看(木板的裂缝?),接下去是32行诗,这才说到“谁也不知道裂缝,是木板……”。这种描写的惊人之处在于,对近在眼前的东西的凝神观察(微型摄影)被覆上完全不同范围的画面。作者仔细审视木板被刀砍出的裂缝,他看得那么仔细,甚至注意到“在黑暗的细孔里残余的树脂蒙着一层灰尘”。接着他把木板中的这些微型空洞比作窗户。于是出现一栋屋子,屋子的墙边刮着低吹雪。在巴勒斯坦峡谷和另一些地方、另一种气候下的圣经场景并存。评论家们关于这块木板写道,它——(1)暗指圣像“板”,(2)棺材板,(3)木板上刀砍的裂缝在提醒有人企图消灭犹太人,镇压犹太人的反抗,(4)希伯来语的词“луах”(“木板”)还表示遗教碑,以及(5)刀砍木板就是克尔恺郭尔的“信仰骤变”。所有这些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与叙事诗的题材也很协调,而解读的多样性恰恰说明,布罗茨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象征性的形象,使它具有产生多种含义的无限潜力,不过布罗茨基《以撒和亚伯拉罕》的诗句有些地方还是过于复杂,而且作者在语言方面还不足以驾驭向他潮涌而来的幻觉的洪流。两三年后,他在创作另一部巨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期间才充分掌握了作诗的技巧。
布罗茨基晚年曾以怀疑的态度评价自己初期的作品,而在完成《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二十年后回忆时称之为“特别重要的作品”[103]。创作这部叙事诗的几年也许是作者生平最富于戏剧性的几年:警察的迫害、逮捕、审判、流放、从流放地回来、与情妇的不和、与她建立家庭的尝试、儿子出生、彻底决裂。这些经历所引起的极大的心理负担,以及与之有关的个性的改变构成了叙事诗的传记性的主要基础,而且《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完善过程本身也作为真正的自我完善的过程融入了这种内心体验的总体:第三章倒数第二诗节是一篇祈祷,在祈祷中,作者的alter ego(改变)就是请求至高无上的神赐予他“战胜沉默和窒息”作为经历的总结。
作为《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素材的外部生活环境,是布罗茨基两次在精神病院接受诊察:有几天在莫斯科郊外的“绳索厂厂长别墅”,然后在列宁格勒的“普里亚什卡河上”。拥挤、污浊的空气、寒冷、恶劣而缺乏营养的伙食、粗暴的态度,此外还有病人的友谊、医务人员的冷酷、迫使病人“认错”的原始的精神疗法,苏联精神病院所有的这些像监狱一样的特点,在叙事诗中都有现实主义的、而有些地方也有很离奇的描写。
年轻的诗人在那些年里的确有情感过分受刺激的特征,时而会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健康。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描写了由于剧烈的精神创伤而陷入二重人格的状态,无疑,他便以此自况:
癫狂已用翅膀
蒙着心灵的一半,
又拿很冲的酒灌它,
又引诱我去黑暗的深谷。
我明白了,我应该
把胜利让给它,
倾听自己的仿佛已是
陌生人的呓语。
《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深刻自省还起着内科治疗的作用:预防堕入“黑暗的深谷”。布罗茨基把自己最可怕的体验转化为艺术作品,而把互相冲突的声音转化为这个作品的人物。
寒冷恶臭的病房是时远时近的背景,而《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真正的活动场所是抒情主人公的意识、大脑(мозг)。要注意的是,在布罗茨基的诗里大脑往往代替往日相对有诗意的“心”。这明显地反映于词汇的频率数据的比较[104]。
诗人讲了个颇为典型的故事,讲的是他在初次做心脏手术前夕的想法:“我对自己说:‘是呀,当然啦,这是心……可毕竟不是大脑,这可不是大脑啊!’我这样一想,就轻松多了。”[105]
“我对自己说……”——这大概是了解叙事诗构思的关键。主要主人公的二重人格——不是精神分裂症的症候群,更不是“声音”幻觉的病态现象,像某些批评家所误解的那样[106],而是大脑两半球结构的人格化。“在任何最深奥的创作领域,不论数学还是音乐,最高成就主要与右半球的形象直觉有关,然而为了体现这种成就(首先是语言文字的体现,总之是利用离散个体的括字版,如自然语言的文字)还需要利用左半球的(言语)能力。”[107]最初对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描述就是这样:前者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姓氏,倾向于发展复杂的逻辑结构,如第Ⅲ章《戈尔布诺夫在夜间》的二进制概念,以收集离散的象征(小狐狸、岛屿、浮标)作为他的梦境的密码,而后者,其姓氏会激起读者的“普希金式的”联想,梦见的是富于感情色彩的具体画面(形象)——街景、自己的童年时光,而首先是音乐的印象(“演奏会、如林的弓弦……”),他的夜间独白,第ⅩⅢ章《戈尔布诺夫在夜间》与第Ⅲ章《戈尔布诺夫在夜间》对称,是几乎毫无联系的一连串激昂的传单,传单上有布罗茨基一般很少用的大量惊叹号(有29个,而第Ⅲ章只有1个)。叙事诗一再指出的正是戈尔布诺夫的言语因而也是思维的功能:“多么奇怪,戈尔恰科夫/说着戈尔布诺夫的疯话!”这也就决定了,照例是戈尔恰科夫提出问题,而戈尔布诺夫作出回答、解释。因为语言在布罗茨基的人类学价值等级中居于首位,我们在第Ⅹ章的结尾读到的是:“音调高些的时候——那是戈尔布诺夫,/哪里低些——是戈尔恰科夫的声音。”
叙事诗中只有一处会使读者怀疑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是一个人的两种身份。戈尔布诺夫在第七章说:“我生于五月,是孪生儿”——和叙事诗的作者一样。而且那里还说,戈尔恰科夫生于三月,白羊星座。这是在开玩笑的场合说的,用星相学解释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性格,然而在这里,更确切地说,问题不在于星相学,而在于胚胎学:人类的大脑是在出生前三个月开始形成。
抒情主人公相互冲突而又彼此离不开的两种身份的对称—不对称,类似区分大脑两半球的功能的对称,这种对称-不对称也表现于叙事诗的结构,表现于内容的平行现象和各章对称编排的鲜明反差。作者为强调《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这个重要的结构特点而使十四章标题的总和构成十四行诗一样的文本:
1. 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
2. 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
3. 戈尔布诺夫在夜间
4. 戈尔恰科夫和医生
5. 第三者的歌声
6. 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
7. 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
8. 戈尔恰科夫在夜间
9. 戈尔布诺夫和医生
10. 台阶上的谈话
11. 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
12. 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
13. 关于大海的谈话
14. 交谈中的谈话
叙事诗形式的对称很严格。实际上14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100行,第1章和第13章例外,是99行(总共1 398行)。所有“对话”的各章都用10行诗节,每节各有五个同样的对偶的韵脚(强调二重性的又一种方法,其实质是抒情的独白)。越出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对话的范围之外,也对称编排的第5章和第10章是例外,诗节更长,韵脚也不重复。
在叙事诗的正文中一再出现针对弗洛伊德泛性论学说的讽刺性抨击。布罗茨基与阿赫玛托娃和纳博科夫(但不是奥登!)一样,不承认精神分析。他说:“弗洛伊德从某一点看,是一位杰出的人士,他扩大了我们对自己本身的认识。但一般地说,这一切并没有给我留下特殊的印象。……这位先生愚蠢的一个简单的例证:他硬说创作的本质是情欲的升华。一派胡言,因为创作过程也好,情欲也好,怎么说呢,人的积极性其实是各自独立的,——并非一个是另一个的升华,两者都是人的创造因素的升华。”[108]
在《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之前,布罗茨基曾在《以撒和亚伯拉罕》和一些短诗中尝试对话的形式。我们记得,在诗中运用对话最使他感到惊讶的是罗伯特·弗罗斯特(参见上一章)。借助于对话,弗罗斯特营造了存在主义的荒诞、恐怖氛围。有趣的是,布罗茨基的对话文本照例没有情景说明,以确定谁在对答,甚至预定要搬上舞台的作品——剧作《民主!》(1990)和《树》(1964—1965);参见第Ⅸ章关于这些剧作的说明)也是这样。在《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中布罗茨基甚至采用怪癖的手法,将所有“他说”之类被省略的说明全都移入单独的一章——第5章《第三者的歌声》,然后又移入对称编排的第10章《台阶上的谈话》,给句子加上引号,这些句子不是对话,而是“作者”独白的一些片段(“这不也是谈话吗,/既然一切都是用语言来叙述?”)。不加说明可以增强对话内部化的印象,取消人物对话和抒情独白之间的差别。
对巴赫金关于对话主义,尤其是关于文艺创作不可能有“无对象的单声部语言”[109]的学说,《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堪称完备的例证,而写作《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时期恰逢巴赫金在苏联复兴之初。但未必说得上直接的影响。巴赫金的直接影响在这里是没有的,不过飘荡于空气中的对话论思想,特别是关于没有与他人的积极交际,便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在叙事诗中是有所反映的。注意:荣格,改为尤格!
……我觉得,只是在
有对话者的时候我才存在!
——戈尔恰科夫在第8章这样说[110]。
最后,阅读这篇叙事诗不能不注意到,它的时间与基督教的历法有关——这是大斋期的疯人院(戏谑或严肃地提及斋戒和此后的复活节,这在作品中是按时出现的)。大斋的宗教意义是“精神旅行,其目的——是把我们从一种精神状态引向另一种精神状态”[111],这也包含在《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情节里。叙事诗的十四章分为七双符合斋戒的七周(试比较另一首复活节诗《献给椅子》的基本类似的结构,那里的七个诗节符合狂欢周的七天——从周一至周日)。整个作品的关键是圣徒叶夫列姆·西林在大斋祈祷中的那广为人知(部分地要归功于普希金的转述)的一句话:“让我看清自己的罪过吧,不要惩罚我的兄弟。”在悔罪的大斋期间日益尖锐的肉体(出卖者的)和精神(被出卖者的)的对立还表现为与福音书的类比:戈尔布诺夫类似于注定要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而戈尔恰科夫则类似于不认基督的彼得,如果不是类似于叛徒犹大的话。在这个意义上说,布罗茨基的对话体叙事诗很像中世纪的神秘剧。“……我爱你,又出卖你遭受磨难”,——这是犹大-戈尔恰科夫在第8章的结束语。在这宗教礼仪的情节中,叛徒和被出卖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多么奇怪,十字架上的戈尔布诺夫/指望着下面的戈尔恰科夫”,——折磨戈尔布诺夫的医生们感到惊讶(第9章第八诗节)。在下一个诗节的末尾各各他的类比加强了。医生们问:“哎,戈尔布诺夫,您要咖啡吗?”(被改写为一碗加醋的胆汁)——对方用基督的话回答道:“你为什么背弃我!”
还有一个与救世主类比的潜在的暗示被置于第4章和第9章的标题《戈尔恰科夫和医生》和《戈尔布诺夫和医生》之内。在圣像画和西欧宗教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情节是图解路加福音第2章第46—47节:“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按西欧传统,教堂智者(在俄语中是“教师”)称为“医生”[112]。盘问戈尔布诺夫-戈尔恰科夫的精神病医生令人想起丢勒名画中盘问基督的怪诞而阴郁的医生们。
1964年后布罗茨基构思《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试图在荒谬得令人恐怖的亲身经历中找到意义[113]。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个宗教模式。心理变态者、“拿破仑们”和“爱品茶的人”在戈尔布诺夫-戈尔恰科夫的陋室里是没有的。在这个可悲的地方,癫狂不是病态,而是存在主义的不幸——亲人的背叛、人间的冷酷、自身在生物学上的脆弱。这种不幸无法忍受——这也就意味着“失去理智”,丧失自己的个性。抵抗不幸的人的孤独,被布罗茨基比喻为基督在各各他的孤独。叙事诗中还有与《旧约》对照的幻觉因素:
您等一等,我看见……一个人……瘦瘦的……
四周是——沙漠……亚洲……看哪:
沙土像鞑靼军队一样爬行,
太阳在熊熊燃烧,它怎么了?……在天顶啊。
天顶被敌对的气氛四面包围……
(第4章第5节)
这不仅是用俄语写的,而且是用布罗茨基诗作的象征性语言来写的,这里的“沙漠”、“亚洲”、“沙土”等字眼,比它们的词汇意义有更多的含义。我们可以在《以撒和亚伯拉罕》和作为书名的那首诗以及一系列其他作品中找到同样的一些词语形象。
这个片段所涉及的圣经中的约瑟夫,被他的弟兄们抛进井里,他居然从井里逃了出来,并在异乡获得荣誉和尊重。
七
布罗茨基喜欢说,诗“поэзия”和政治“политика”的共同之处只有起首的两个字母“по”。他的非政治倾向不是表现于回避尖锐的政治题材,而是表现在他把政治题材只看作亚种下面的一种。社会生活中善与恶的表现,对他来说不过是人性冲突的个别事件。在这方面很典型的是布罗茨基对奥登笔下恶的经典形象的再认识。这里讲的是奥登的诗《阿喀琉斯之盾》的一个著名的段落:
A ragged urchin, aimless and alone,
Loitered about that vacancy; a bird
Flew up to safety from his well-aimed stone:
That girls are raped, that two boys knife a third
Were axioms to him, who'd never heard
Of any world where promises were kept
Or one could weep because another wept.
(一个衣着褴褛的街头顽童,/独自无目的地/在这空地上走来走去;/一只鸟儿/飞起,躲过他瞄得很准的石头。/强奸那些小姑娘,两个少年会杀掉第三者,/对他来说这就是公理,因为他从未听说,/有哪个世界会信守承诺,/什么地方会有人因别人痛哭而呜咽。)
布罗茨基在《坐在阴影里》一诗中回忆奥登的这一段,在诗的序幕中说:
我看着在花园里
奔跑的孩子们。
他们欢快凶狠的游戏、
伤心的哭泣
会使未来的世界困惑不解,
要是它有眼能看的话。
还有下面的14诗节:
一个干瘦的顽皮少年,
街头的小天使,
嘴里紧抿着水果糖,
在花园里拿木把弹弓
瞄准一只麻雀,
不是想——“我要命中”,
而是坚信——“我杀了它”。
奥登笔下衣衫褴褛的少年无谓地作恶,因为他生长于赤贫和赤贫所产生的残忍的世界。布罗茨基笔下同样作恶的不是衣衫褴褛的少年,而是嘴里含着水果糖、在花园里游戏的顽皮孩子。布罗茨基曾说,上面引用的奥登的诗节,“应当雕刻在现存的所有国家的入口,而且总的来说,要雕刻在我们整个世界的入口”[114]。不过我们看到,他重新解读了这个诗节:孩子心中的恶不是由于社会经济因素,而是由于人类学因素。
与心仪的诗人的分歧,与基督教的伦理信条无关,而是与排外、战争、种族灭绝有关。到30年代末,奥登还多少持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革命起源的观点:“饥不择食”,他在《1939年9月1日》中这样写道。布罗茨基认为,经济不平等、饥饿和贫穷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
重要的是给许多人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
(这一点可以在霍布斯那里找到)。
(《话说洒掉的牛奶》)
在霍布斯看来,大部分人类都创造了不同形态的国家和这些利维坦,总算结束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不过在警察的保护下生活并填饱肚子也并不觉得幸福些。
布罗茨基有马尔萨斯人口论所启示的阴暗预感。
那么多人手的事业
不是毁于剑下,
而是毁于廉价的裤子
被气愤地扔掉。
未来是黑暗的,
不过是因人而起,
不是因为我
觉得它是黑暗的。
(《坐在阴影里》)
人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群众、军队、合唱向来敌视有个性的人。在《话说洒掉的牛奶》发表的二十年后,布罗茨基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是这样开始的:“对一个有个性,而且毕生偏爱这种个性胜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对一个在这种偏爱中走得相当远的人——其中也包括远离祖国,因为做一个民主制度下最大的失败者也好于在专制制度下做思想的受难者或主宰者——对这样的人来说,突然出现在这个讲坛上——深感困窘和沉重”[115]。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社会以私人的自由契约为基础;在与苛政不可分割的庶民政治中,有个性的人作为变节者和叛徒而受到迫害(参见《发扬柏拉图精神》),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处于边缘状态。过去这样,将来也永远这样:
在不久的将来,无疑,
人口会膨胀。雇工
像过去一样,在烈日下
挥锄。有一个戴眼镜的人,
将忧伤地在咖啡馆翻阅马克思的著作。
(《百科全书札记》)
有个性的人(布罗茨基的抒情主人公的政治身份)的梦想是和女友在海边定居,“凭借高高的堤坝/与大陆隔开”(《预言》),独自生活在一个偏僻省份的海边(《致罗马友人的书信》),但实际上他注定要生活在群众之中,目睹暴君喃喃自语,“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一只野山羊’。”(《发扬柏拉图精神》)布罗茨基关于私生活的梦想和被社会遗弃的主题,往往发生于虚构的国度、城市和时代的假设的情况,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空想的,不如说是理想的,因为可以反映现实的不同变体的实质、柏拉图的“理念”。苏联的实质就是一个帝国,苏维埃的大都会就是柏拉图的城邦。在这个集体主义国家,个人生活的理念就是凭借“高高的堤坝”与世隔绝。
布罗茨基经常把他所憎恨的政体称作苛政。在布罗茨基的诗中,暴君总是带着平庸的光环出现。在?Anno Domini?中,他受着肝病的折磨,在《致暴君》中——吃着美味的小面包,在?Post aetatem nostram?中——在厕所里使劲,在《官邸》[116]中——穿一件淡紫色的女式棉背心对着一行行数字打盹儿。这是一个不大聪明、不再年轻的病态的人。他的素质中最有人性的一点是他一定会死。
形容语“渺小”是布罗茨基的恶的问题中的关键词。“恶的平庸”最早出现于汉娜·阿伦特的经典作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1)。其含义当然不是说恶是平庸的,而是说恶的体现者、发起者是平庸的。平庸——是托尔斯泰笔下对拿破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对鬼机灵的卡拉马佐夫的主要评语。20世纪一再证实,大规模的恶行——,纳粹分子的灭犹,柬埔寨的恐怖统治,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等——其责任者都不是恶魔般的超人,而是平庸之辈。中等资质的人,有时有些精神变态,而有时也可能没有,会干出其规模之大匪夷所思的恶行。布罗茨基在个人经验的有限范围内也曾体验到这一点。迫害和折磨他的人无例外地都是一些平庸的人们。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原始的欲望和恐惧,思维能力由于被洗脑而僵化。这些人终于也像那些站在国家金字塔塔尖上的人一样,由于精神空虚、道德沦丧而作恶。恶的平庸所表现的是犹太基督教伦理学自古以来所阐释的恶的非实体性:恶填补空虚,恶的实现需要内心空虚的人。
在布罗茨基最初在西方写作和发表的一篇随笔[117],以及1984年在规模不大的威廉斯精英学院对毕业生的演讲中,关于恶的本性的直接论述都占有主要地位。布罗茨基向青年致临别赠言时还说:“对恶的最可靠的抗拒——是极端个人主义、独立思考、独创性,甚至可以说是——怪癖。”[118]这在较少挑衅性的文体中也可以称之为“批判性思维”或“脑力劳动”。不过,在布罗茨基的诗和随笔中经常有与恶的问题相关的主题,似乎有悖于他对个人主义甚至怪癖的肯定。诗人声称,他个人的主要成就在于“我的歌没有主题,/然而它不能合唱”(《我总是强调,人生如戏……》)——在考虑到使他的国家遭到历史性灾难的那些罪人时,他却坚持使用代词“我们”。
这个“我们”在《在旷野扎营》这首诗里是有特殊含义的:
现在列宁格勒的希腊人那么少,
所以我们拆了希腊教堂,
要在空地上建造
音乐厅。
曾经是彼得堡希腊正教团体的教堂的那座建筑物被列宁格勒当局勒令拆除,在它的原址上于1967年为迎接十月革命50周年而建造了一座音乐厅。诗的第一节讲的是新建筑物的丑陋。被拆毁的希腊教堂也并不以建筑艺术见长,不过布罗茨基的冥思与保护历史文物的问题无关,而是涉及此事的象征意义——俄罗斯抛弃了基督教,同时也就抛弃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给俄罗斯历史留下了极其丑陋而庸俗的特征。“我们”被布罗茨基选作冥思的主体,在诗的开头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决定拆除老建筑、建造新建筑的正是对诗人进行残酷迫害的列宁格勒的那些官僚主义者。但随着诗的进展,便渐渐地清楚了,这里讲的不是苏维埃制度的一系列反文化罪行,而是民族的集体失误,这个民族从自身中产生了这种制度并放弃了历史性的选择——接受古希腊的遗产及其不可分割的民主制度。《在旷野扎营》以尾声结束,尾声是一系列面向未来的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的不是“我”,在希腊教堂被拆毁时坐在壁龛废墟上的作者,而是“我们”。在诗的结尾“我”自然而然地转为“我们”:
今夜我望着窗外
在想,我们来到了哪里?
我们离什么更远:
是离东正教还是希腊化时代?
我们亲近的是什么?那里,在前面的是什么?
现在有另一个时代在等待我们吗?
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又是什么?
而我们应该为这个时代作出怎样的牺牲?
布罗茨基对祖国的历史罪行负责的主题,更尖锐地表现于个人倍感羞耻、屈辱。有人问,他生平是否有过什么时候强烈地想逃离俄罗斯,他回答道:“是的,在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记得,我那时很想随便跑到哪里去。首先是要避开耻辱。避开我属于一个干出这种事来的强国的现实。因为至少部分的责任总是落在这个强国的公民身上。”[119]他以讽刺诗《致Z.将军的信》回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诗中的主人公,帝国的一名老兵,拒绝战斗:“将军!现在我有寒颤。/不知怎么了:是由于羞耻?由于恐惧?”这种心情更直白地表现在为苏维埃国家最后一次帝国主义冒险而作的《1980年的冬季战役》:
光荣属于那些人,他们眼也不抬,
在六十年代走进人工流产手术室,
为了拯救祖国免于耻辱!
《在旷野扎营》发表两年后,布罗茨基在?Anno Domini?中明说,每个人对祖国历史的恶劣结局都错在哪里——错在随大流,盲目追求“与大家一致”,错在放弃个人主义。在苏联日常生活的用法中,“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布罗茨基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也是同样彻底的利他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这对他来说意味着精神上的独立,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个人不得不参加的集体行为承担道义责任。集体主义——这是拒绝上帝的定数(“离开了造物主的圣像”),也是拒绝生活本身:
所有人在棺材里都一样。
那就让我们在生前有不同的面貌!
(?Anno Domini?)
如果我们(“我们”)都选择无个性和无作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以裁判权换取平均量的安逸:
……我们不是祖国的审判官。审判之剑
将陷入我们自己的耻辱之中:
继承者和权力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好啊,船舶停航!
好啊,大海结冰!
布罗茨基60年代至7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祖国题材总是——交通停顿、生活麻木以及平均信息量的题材。“停滞”这个术语只是在20年后才进入他的同胞们的政论。以前的公民诗流行浮夸的言辞,在布罗茨基笔下,政治史题材是可见的、经过细节加工的画面,而其实是包含着隐喻的画面。这就是——《话说洒掉的牛奶》、《美好时代的终结》、《波波的葬礼》和直接以列宁格勒的现实为背景的其他一些作品中束缚城市生活的严寒。或是《致Z.将军的信》虚拟景色中的一条不可通行的沼泽小径:“我们大炮的炮筒扎进了污泥……”或是诗体小说?Post aetatem nostram?的一章《君主》中两个讽喻的激烈冲突:君主的残暴驱策和停滞的历史进程。
总之,现在一切都蹒跚而行。
帝国像一艘三桡战船
在对三桡战船而言太窄的运河里。
划船人用桨使劲敲击陆地,
石块剧烈地刮蹭着船舷。
肤浅的观点认为《在旷野扎营》是一篇朴实之作。是生平的写实:诗人认识年轻的鞑靼姐妹,从她们住宅的窗口看到已开始拆毁希腊教堂。由于这个缘故他对往事的思考是用五音步抑扬格写就的,似乎可以改写为散文而无损于它的内容。然而在似乎从容的独白中有一种戏剧性的紧张。这种紧张是逐渐形成的——布罗茨基有谋略地使思考往事与日常见解交替出现。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仅有有限的具体含义的词语,却由于贴近关于祖国历史的思考而暗示着其他的一些含义。
一切都起因于鞑靼人的交谈;
随后有一些响声搅进了谈话,
起初与话语声融成一片,
但很快就压倒了它。
挖土机开进了教堂的小花园,
吊杆上挂着铁制的重锤。
于是墙壁开始缓缓地倾斜。
这看上去好像并非隐喻,而是对事实的直接描述。诗中稍显突兀的是修饰语“鞑靼人的”。女主人未必会当着客人的面用他听不懂的母语交谈,也许这是布罗茨基常有的打趣的故作幼稚的用词手法(试比较:“惨无人道的,/更确切地说,行人稀少的十字路口……”或是“老太婆在一条牧羊犬的包围中——/意思是说,它围着老太婆/绕圈子……”见组诗《从二月到四月》)。“鞑靼人的”在诗中只是表示作者的对话者是鞑靼人而已。但在潜台词中是有情节的转变的。“一切起因于鞑靼人的交谈……”一切是指什么?指希腊教堂被摧毁?那么诗行“吊杆上挂着铁制的重锤”的最后一个词就会引起与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克里米亚鞑靼王朝的双关联想。揭示这个双关语的含义,在《在旷野扎营》这样的哀诗中听起来就太滑稽了,不过布罗茨基并没有加以揭示,让它留在潜台词中。同时在题材中引入了俄罗斯历史自觉的根本问题:欧洲还是亚洲?
对布罗茨基来说,欧洲从它的希腊化源头开始,就是和谐(结构性)、运动、生命。亚洲是混乱(无结构性)、静止、死亡。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亚洲的轮廓。
(《1972年》)
(在阅读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作品时,布罗茨基曾一再碰到“亚洲——死亡”这个形象的联想[120]。)
布罗茨基总是把地理(或地缘政治)主题表现于严格的对立模式的框架之内:亚洲——西方,伊斯兰教——基督教,树林——海洋,冷——热,以及进入政治流行词汇很久之前的停滞——运动[121]。1970年末布罗茨基写道:“今天我浑身感到热!我渴望迁走!”——即使在这种打趣的诗句中热和运动(“迁走”)也是与帝国停滞(这个词兼有冷和静止的意思)的形象相对立的:“那里的气候也是静止的,在那个国家……”(《献给约翰·多恩的大哀诗》)。
诗作《训诫》(ПСН;写于1987年)通篇把亚洲描绘成危机四伏的地方,在那里旅行者的每一步都潜伏着出卖和犯罪,人的生命分文不值。在这首诗中我们也能找到与布罗茨基的亚洲主题相矛盾的线索。细心阅读就会发现亚洲(更正确地说是中亚)现实中所特有的一些现象——宽颧骨、棕色眼睛、高山景色、淤泥堵塞的河流、沙漠、厩肥的气味以及典型的俄语词汇。如果说在第一行诗中读者前往亚洲(“在亚洲旅行,在陌生人家借宿……”),那么下面的第二行就准确地说明了亚洲的那些“陌生人家”究竟是什么样子,提供了如下的清单:乡村木屋,浴池,仓房在——圆木搭建的阁楼里。这里提及的四种类型的建筑物都与传统的罗斯有着牢固的联想关系,尤其是特意用破折号引出的古风的“用圆木搭建的阁楼”。这种混合运用独具特色的“亚洲”和独具特色的“俄罗斯”的策略扩散到了整首诗作。第二诗节(“你要防着宽颧骨……”)之后的第三诗节是描写居住着“农夫”和“农妇”的“乡村木屋”,如此等等。换言之,我们在《训诫》中所接触到的是俄罗斯——亚洲、欧亚大陆、索洛维约夫笔下的“薛西斯的俄国”令人生畏的形象,要是可以这么说的话。
布罗茨基的诗学思想不在于以19世纪作家的方式告诉我们:“你挠了挠俄罗斯人,却发现是鞑靼人”——而在于“亚洲”这个概念对他来说不是地缘政治概念,而是心灵主义概念。布罗茨基的亚洲神话题材成分在某种程度上既吸收了索洛维约夫的成分(亚洲——注定的危险敌人),也吸收了欧亚大陆的成分(亚洲——这就是我们),但布罗茨基对传统的俄罗斯-亚洲神话所作的改变,却着眼于其体现者的道义立场。布罗茨基不像索洛维约夫那样号召文明之间进行最后的决战,也不张扬不文明的亚洲,如勃洛克的大欧亚诗体宣言《西徐亚人》:“是的,亚洲人——我们……”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集体的、民族的正义感和自豪感:在索洛维约夫那里是由于我们没有像亚洲人那样“成为奴隶”,在勃洛克的《西徐亚人》中则相反,是因为我们具有西方所丧失的集体的、历史的生命力。布罗茨基愿意分担拆毁希腊教堂的集体的、民族的、我们的罪错,不过对他来说,积极的成果只能是在个人方面——个性的自由、个人的自律。
《话说洒掉的牛奶》以多样的风格激动地讲到布罗茨基的信条:
通常谁唾弃上帝,
谁就会首先唾弃人类。
我们知道,在无神论社会和不关心宗教的家庭受教育的布罗茨基,在青年时代热衷于玄学问题,而且对印度教和佛教原理的了解早于对犹太基督教的了解。初次读完圣经是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他是信教的人吗,如果是,那么他的信仰对基督教、犹太教、东方宗教持什么态度呢——或者那是同上帝的关系而与宗教信仰无关?利用布罗茨基的信仰或不可知论来投机是极为不妥的,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我们能找到的只是对后一个问题的明确无误的回答:“我不赞成宗教仪式或形式主义的礼拜。”[122]
不信仰东正教的仪式并不自动地意味着倾心于新教或福音派基督教,尽管布罗茨基会在诗里转向上帝:
低下头来,我有话要附耳低语:我
为一切而感恩……
(《罗马哀诗》,Ⅻ)
……对着上帝因为白日
的喧嚣而掩住的耳壳,
你只低声说了四个字:
——宽恕我吧。
(《立陶宛的余兴节目》)
布罗茨基的信仰的表现不是期望拯救自己于痛苦的深渊,而是感恩和请求宽恕,实质上是幸福心态的流露。“只要不用烂泥封住我的嘴,/嘴里响起的就只是感恩的声音。”(《我作为野兽走进笼子……》)关于阿赫玛托娃《野蔷薇》的一行诗:“你不知道,人们宽恕了你……”——布罗茨基说——“这行诗是心灵对存在的回答。”(“因为宽恕者永远大于伤害本身和造成伤害的那个人”)[123]
有两首诗最充分地表达了布罗茨基的摇摆不定的信仰——时而信仰上帝,时而是不可知论,这就是《与天人交谈》(1970)和《静物画》(1971;两者均见КПЭ)。布罗茨基说,圣经中给他留下强烈印象的是《约伯记》。《与天人交谈》的凄凉悲惨的声调正如约伯的怨言。但约伯确知在对谁说话,而且能听到他的回答。布罗茨基笔下与天人交谈的人,倒像是贝克特笔下等待戈多的人,既不能确定天上的状态,有时甚至也不能确定对方是否存在。这个戈多时而是天使,时而似乎是上帝(因为恩赐被还给了他),时而是“划过苍穹的玩偶之一”,这就导致了不可知的结论(“任何话语都是没有针对性的”),时而是存在主义的阴沉的宗教观:“一切信仰都不过是单向的邮件。”精神支柱、面对痛苦和死亡的“勇气”只能求之于己,而不是诉诸上帝。
《与天人交谈》和《静物画》相隔一年有余,然而《静物画》对于《与天人交谈》中没有答案的问题作出了肯定却很不平常的回答。《静物画》写于病中,在不那么严重的确诊之前被怀疑患有癌症。诗中提到病情引起的贫血症状:“我的血很凉。/它的寒气比/结冰结到底部的河更猛烈……”“两条大腿很凉,像冰。/静脉的青紫色/酷似大理石”。《静物画》中没有“心灵”这个词,但这首诗的戏剧冲突是——生物变为无生物,肉体变为大理石,人变为物。没有“心灵”这个词,却有从加缪的《西西弗神话》直接转入布罗茨基诗歌词汇的“荒诞”。加缪关于人类生存的荒诞的思想,布罗茨基也在被收入《美好时代的终结》的其他诗作中加以援引——《致Z.将军的信》(“痛苦的总和催生荒诞”)和《献给雅尔塔》(“须知这是——为荒诞辩护!对荒谬的颂扬!”)。加缪对荒诞的态度是有二重性的。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在于不可避免的死亡:“想法是‘我存在’,我的行为方式仿佛一切都有意义……这一切都被会死亡的荒诞性以令人头晕的速度所推翻”[124]。但加缪说,揭示荒诞性会给人带来悲剧性的自由,甚至带来幸福,这种揭示会“从此岸世界赶走上帝,他是带着对无益的痛苦的不满和偏爱潜入这里的”[125]。不过布罗茨基对加缪的这种英雄主义的无神论不予认同。面对荒诞的挑战,他在《静物画》中以肯定信仰来应对,而且具有诗风的非凡创意。
成熟期的布罗茨基向来以结构作为语义构成的重要因素。除了《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之外,各部分的对称/不对称也许在哪里也不像在《静物画》中那样起着特殊的作用。这首诗包含十个编号的部分,每个部分各有三个四行诗。前九个部分是作者的独白,类似于《话说洒掉的牛奶》,但聚焦于死的主题。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个主题表现为人/物之间的对立。就像契诃夫《樱桃园》中的加耶夫含泪赞扬“可敬的壁橱”不可动摇的存在,布罗茨基讽刺地把餐柜和人对立起来,餐柜如同巴黎圣母院的砥柱一样坚固,人却对死亡满怀可怜的恐惧。第1—3部分和第6部分讲到人、自己,都以“我”出现:“我坐在板凳上……”(1),“我准备开始……”(2),“我不爱人们……”(3),“我在大白天睡觉……”(6)。与第1—3部分和第6部分对称的是第9部分结构中的第4部分和第7—9部分。其中讲的是物:树、石头、灰尘,总之以物为对象。第5部分(《壁橱》)是整个结构的核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具体的物的观察,不过观察者也并未缺席,有“我”,尽管不是作为主语:“旧壁橱……使我想起……”这首诗的下半部物对人的优势确定了有机物麻木的主题,简直把“静物画”解释成“死的大自然”。在结束这个主题的第9部分直接讲到死神走近实际上已无生命症候的尸体,这具尸体只能像物——镜子一样反映死神的面容。
作者直接的独白至此结束。但《静物画》还没有完。在严格的对称结构之外,作为情节前后不连贯的陈述而出现第10部分——伪福音书的场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与马利亚的对话[126]。话题是战胜死亡而复活的秘密。
圣母对基督说:
——你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
神?你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怎么还能回家?
在跨出门槛的时候,
我不明白,不能确定:
你是我的儿子还是神?
就是说,不知你死了还是活着?——
他回答道:
——生或死,
妇人哪,没有区别。
儿子或神,我是你的。
生或死没有区别——这好像是克尔恺郭尔的“信仰的骤变”,不过在布罗茨基简练的诗行里还隐藏着对悲剧性二分法的这种回答的颇有诗意的合理化。只是在“Я твой(我是你的)”这一点上生死才没有区别。由于现代俄语语法也普遍省略动词—系词,我们会忘记,完整的语法结构应为“Я есмь твой(我是你的)”。被爱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人们суть,是存在的。在这种联系之外——homo homini res est(人对人是物)[127]。不论“荒诞中的人”(加缪语)的刚毅的孤独怎样令布罗茨基肃然起敬,对“决定性的问题”他毕竟还是遵循传统的基督教精神来回答。也不只是在《静物画》中。作为救赎的爱的主题贯穿于布罗茨基此后的所有作品。与“我不爱人们……”的挑衅相反,他后来写道:
许多人——其实是所有的人!——至少,在这个世界上值得爱……
(?Стрельна?)
不过,布罗茨基对善的肯定似乎在哪里也不曾达到那种隐喻的力度,像他在1980年圣诞节所写的一首诗《雪在下,把整个世界留在少数人手中……》:
仰望夜空,多少光塞满星星
的碎片!好像难民塞满了小船。
如果说圣诞节的星光——是纯粹的善的能量,那么这星光的量子在布罗茨基笔下就成了一艘小船,地球上最流离失所的人们在小船上逃避迫害他们的恶。小船上的难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或在报纸上读到:越南人、古巴人试图在破旧的、有时是自造的简陋的小船上逃避共产主义的暴君们。
八
苏联几乎密不透风的封闭在60年代末出现了裂缝,为数不多的公民获准离境,以便与国外的亲属会面。1972年春获准离境的人数激增,这是很容易解释的——莫斯科在期待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访。鼓励尼克松在以后提供粮食并执行“缓和”政策。
这时布罗茨基得到了“通知”——以色列当局认证的来自虚构的以色列亲属的邀请函,邀请他在祖先的土地上定居。他不愿按这次邀请采取行动。那时他还是认为,情况会发生变化,准许他短期出国旅行。布罗茨基有太多的依恋——依恋父母、儿子、朋友、出生的城市,太珍惜母语环境,不愿一去不复返。
不过,列宁格勒的克格勃对这个老当事人有自己的设想。有了适当的机会便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位不可预测的诗人。既不让布罗茨基好好准备,也不让他向亲友道别。1972年7月4日,布罗茨基在自己年满三十二岁的十天之后乘飞机从列宁格勒前往维也纳。
离开苏联侨居国外,在70年代对出行者和送行者都是不无悲剧成分的事件。人们相信这是永别,因而送行有点儿送葬的意味。对出行者何况还是从未离开过苏联国境的人来说,一去不复返地跨过边界也同样有刻骨铭心的悲哀,因为边界隔开了故土的熟悉的世界和不熟悉的外人的世界。
离开社会主义的列宁格勒飞行不久便来到资本主义的维也纳,最初只是感性层面的大为震惊。另一个世界刺眼的亮丽色彩,充耳是另一种言语。不过新现象的压抑减轻了,一切忙乱的令人惊愕的印象全都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布罗茨基在另一个世界的边境遇见了一个人,他对此人的敬重高于当代的任何人,这就是威斯坦·奥登,他关于语言的权力凌驾于时间的话是八年前在俄罗斯北方的乡村木屋里读到的,这句话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几乎是一次偶然的幸遇,对布罗茨基以后的人生具有极大的意义。
在布罗茨基出现于他的篱笆门边之前的两年,奥登读了他的诗的乔治·克莱因的权威译本,随即为这本译诗集写了简短的前言。这篇文章落笔谨慎——奥登一开始就指出,不懂原文,根据译文来评论诗人是很难的,然而前言是以同情的笔触写的,而且其中的一些见解相当透彻。
对奥登的直觉不能不给予应有的评价,他似乎猜透了这个用陌生语言写作的青年诗人的隐衷,对他满怀好感,并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克服在陌生环境里初期的紧张心情。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次见面称为平等的交流。首先,对俄国这名政治流放犯写的是什么诗,奥登缺乏真切的了解,何况从个人方面说,他也不可能对不会讲英语的布罗茨基作出真正的评价。不过对布罗茨基来说,与奥登的见面乃是天意。在俄罗斯,在文学之路的开端,布罗茨基有白银时代最后一位伟大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赠言,而在人生巨变的前夕,在西方的门口,受到了最伟大的英美诗人威斯坦·奥登的欢迎。在寻求话语感谢自己的两位享有盛誉的庇护者时,布罗茨基的感谢实际上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可以把这(指奥登的诗——洛谢夫注)叫作精神上的慷慨,但愿精神不需要在心里折射它的人。人不是由于这种折射而受人敬重,而是精神变得仁慈而容易理解。仅凭这一点——何况人生有限——就足以向这位诗人顶礼膜拜。”[128]在《安娜·阿赫玛托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这首诗里,同样的思想——伟大的诗人会找到神圣的词语“宽恕”和“爱”——有了迂回的写法:
……因为人生一世而已,这些词语出自必死者之口,
听起来比出自上空的云絮更清晰。
当然,并非完全的对称。布罗茨基与阿赫玛托娃有多年的密切交往,许多时间都是在交谈中度过,而和奥登的交流是短暂和单向的。回忆阿赫玛托娃的时候,布罗茨基强调的是她的道德典范的意义,在他和阿赫玛托娃之间作为诗人却很少共同之处。奥登则不然。是影响还是自觉学习或才气相近起了作用(也许三者都起了作用),总之,实际上布罗茨基的一切——从单个诗句的结构到对诗歌体裁的理解和一般的诗歌艺术观点——都能在奥登那里找到类似的现象[129]。从个人方面来看,在他们之间可以找到相似的特点,也可以找到根本不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才是实质性的——生于1940年的俄罗斯诗人的诗歌与他父母的同龄人的这位英、美诗人的诗歌惊人地相似。看来与奥登的见面帮助布罗茨基认清了这罕有的选择性相似的深度,这次见面之后,他便终其一生都完全自觉地以奥登作为典范来审查自己的诗作。
布罗茨基所移居的国度,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陌生。布罗茨基受过认识美国文化的长期函授教育。好莱坞和美国文学渐渐带来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家的大量文化信息。当约瑟夫年龄稍长,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陶醉于爵士乐的时候,他断定这门艺术的基础实质上正是个性独立、个人自由的原则。梅尔维尔的伟大的长篇小说,Э. А.罗宾逊、罗伯特·弗罗斯特、Э. Л.马斯特斯的诗暴露了个人主义的某些令人忧虑的方面。然而独自对抗世界的混乱和恐怖、“无所畏惧”的伦理观更具有吸引力,不像否认道德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自由是被认识的必然”)或叶夫图申科一首寓言诗中的人物所表明的无耻的相对主义:“真正的自由——我们没有,你们也没有……”[130]我们曾引用奥登《阿喀琉斯之盾》中的著名诗节,讲到一个人形的小野兽,他作恶,因为他从未听说“of any world where promises were kept”(“有哪个世界会信守承诺”)。其实奥登是在呼应20世纪美国更风行的(最风行的!)一首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驻足于雪夜的树林》,其结尾是: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不过我有必须信守的承诺,
我在睡觉前还有几英里的路要走,
我在睡觉前还有几英里的路要走。)
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布罗茨基怎样从潜心阅读美国诗歌而渐渐获得对一个社会的认知,在这个社会个人的责任感是显而易见的。
在旁观者看来,布罗茨基1964年生活中的主要事件是不公正的审判和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对布罗茨基本人来说——是一本英语诗集使他茅塞顿开。1972年也是这样——所谓的“文化休克”,改变居住地的创伤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对他来说,主要的是新的音乐开始响起,这在他的诗的焕然一新的音韵中得到了表现。富于隐喻的“诗的音乐”——有具体内容支撑的表达形式。在诗歌作品的所有成分中唯有它可以真正准确地描述和量化。这里讲的是语音结构和节奏。在诗集《在旷野扎营》中55%的短诗,连两篇长叙事诗和《学校诗选》在内,是用从容的五音步抑扬格写的,这是俄罗斯叙事体和沉思体诗歌的典型诗格。其中的少数短诗是用其他经典诗格写的(五首四音步抑扬格、五首抑抑扬格等)。近18%,69首短诗中的12首用的是三音节诗格的变体,即比五种经典诗格组织得更复杂、更不可预测、更个性化的诗格(“Теперь так мало греков в Ленинграде”是五音步抑扬格,而《再见,韦罗妮卡小姐》这首诗的音步:“Если кончу дни под крылом голубки ...”就是三音节诗格的变体)。从1970年起这个比例有了变化。《美好时代的终结》所收入的诗写于60年代末至1971年,三音节诗格的变体已占29%。但量与质的飞跃发生在《美好时代的终结》和《言语的一部分》之间。《言语的一部分》中用经典诗格写的诗是少数,占36%,多数是三音节诗格的变体。
只有与诗无缘的人才会认为,这样改变取向纯粹是技术性的。作品的韵律特征以及语音和节奏的组织——俄罗斯诗歌是由此起步的。亲切地回忆往日爱情的瞬间(“楼梯上跑下一位/盛装的美女,我像雅科夫一样,/在暗中守候……”)和窗外乍起的暴风雨的即时印象(“远处的雷声震耳……”)开始融入统一的抒情作品,布罗茨基在《近于哀诗》中记下了一笔:
这时通过我耳鼓的:
还不是音乐,也已不是噪音。
把失去意义的“噪音”,即不受控制的回忆、意识流、离散的观察和印象改造为传情达意的诗的音乐,这就是创作。韵律的选择,对布罗茨基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语言的表达,而且先于语言的表达。诗行的音步从纯粹物理学的声学的角度来看,是语音按一定顺序的交替,而这个顺序是由重音节之间的间隔的长度来决定的。这种间隔持续几秒或一秒的几分之几,但不管怎样,间隔是发生于时间之中。韵律是在时间中操控言语。“音步……不是单纯的音步,而是相当引人入胜的玩意,这是打乱时间进程的不同形式。任何一首歌曲,甚至鸟鸣都是改组时间的一种形式。我不想在这里发一些离奇古怪的议论,只是说,格律诗提炼着各种不同的时间概念”,——布罗茨基这样说[131]。因此诗的节奏结构的选择,对布罗茨基而言便有了哲理意义。不论诗的情节如何,节奏令人想起情节在其中展开的两种语境,——时间不顾一切的单调而等速的流逝和个人(作者、抒情主人公)试图打破单调性——延长、缩短时间或让时间倒退。从70年代开始在他那里占优势的三音节诗格变体比经典诗格更能使他以远为个性化的形式拟定时间概念。当然,在经典的俄语诗格的范围内也可能有节奏的细微差别,然而布罗茨基的三音节诗格变体是他自己为自己,为自己和时间的关系而创造的。
布罗茨基的三音节诗格变体的诗行是独具特色的。其中有三个强音甚至两个强音的诗行(强音指三音节诗格变体诗的强重音音节)。一个很早的例子——《丘陵》(1962;ОВП):“Вместе они любили/сидеть на склоне холма ...”可以根据这首诗的情节推测,它的节奏结构的来源是西班牙《歌谣集》的俄文译本(译者:马查多·洛尔卡)。很久以后,布罗茨基在组诗《墨西哥余兴节目》(1975;ЧР)的那些具有模仿风格的诗中以《墨西哥歌谣)》作为其中一首的标题,从而直接指明了这层渊源。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布罗茨基力求找到与奥登的节奏相当的俄语节奏。《静物画》(1971;КПЭ)不仅重复奥登《1939年9月1日》的情节结构(序幕:“我坐在公共场所,看着人们,可我不喜欢他们”;展开:关于这一点的哲理思考;结论:基督徒仁爱之心是必要的),而且重复奥登的三个/两个强音的三音节诗格的变体和清一色的阳性尾韵:
奥登: 布罗茨基:
I sit in one of the dives Я сижу на скамье
On Fifty-Second street в парке, глядя вослед
Uncertain and afraid проходящей семье.
As the clever hopes expire ... Мне опротивел свет.
(我坐在饮食店里,
在52道街上,
缺乏自信又受了惊吓,
离奇的希望在渐渐消失……)
但更有收获的是在另一个方面——带有长诗行的三音节诗格的变体。在1972年至1977年间的所有作品中,布罗茨基所珍视的无过于组诗《言语的一部分》。构成组诗的二十首短诗中有十五首是以抑抑扬格开始的:“Ниоткуда с любовью ...”,“Узнаю этот ветер ...”,“Это ряд наблюдений ...”,如此等等。抑抑扬格有某种伤感主义的语义光环,显然与华尔兹舞曲“三拍”的节奏有关。抑抑扬格在布洛克的抒情诗中并不罕见,不过曼德尔施塔姆把它贬低为有些庸俗的浪漫诗格。布罗茨基走的是另一条路,选择抑抑扬格作为他最看重的作品——爱情诗和怀旧诗的基本韵律。组诗《言语的一部分》的诗行对抑抑扬格而言太长(大体上是五音步和六音步),因而大多数诗行的抑抑扬格变成了最小限度的三音节诗格的变体,却彻底改变了原有的节奏:诗行的末尾“缺少”抑抑扬格的一个无重音的音节:“По-то-му | что каб-лук | ос-тав-ля- | -ет сле-лы |[这里少一个音节]---зи-ма”。这样长的类似于抑抑扬格的三音节诗格变体的诗行,在俄语诗中几乎不曾有过。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布罗茨基拉长诗行是要创立相当于爵士乐的即兴诗(《从郊区到市中心》直接谈到了这一点:“郊区的爵士乐向你们致意……”),那么《言语的一部分》的作者只是在言语的噪音中倾听时间的节奏(“帝国的兴衰和言语的噪音相关……”,《科德角的摇篮曲》)。
让我写下这些话的不是
爱情也不是缪斯,而是降低
音速,寻根问底的平淡的噪音……
(《切尔西区的泰晤士河》)
“寻根问底的平淡的”嗓音所强加的时间节奏毁了作品。要使分行符合语法上的划分,就该这样分:
让我写下这些话的不是爱情也不是缪斯,
而是降低音速,
寻根问底的平淡的噪音……
跨行的诗句从70年代初开始,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布罗茨基的笔下,而且越来越走极端[像上面引文中的否定语气词не(不是)的隔离]。埃特金德这样讲到布罗茨基:“这是一位具有深刻的哲理思维的诗人,他的哲理思维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表现于对言语的句法的执著追求:平静淡然、学者般广泛涉猎的句子一往无前,无视格律—诗节的障碍,这样的句子似乎从不参与任何‘文字游戏’。然而这是不对的,——它不仅参与这种游戏,它本身就是诗的躯干,而诗赋予它以形式,并与它一起投入悖论关系,或者不如说是讽刺关系。”[132]诗律和句法的冲突,其结果是跨行,埃特金德认为,这种冲突在布罗茨基那里也像在茨维塔耶娃那里一样,都是哲理因素。这种哲理冲突是布罗茨基成熟期全部诗歌的基础,冲突的内容就在于他所选择的诗律:被置于冲突关系的是人和节奏,是个人的、有限的、必死的生命和无始无终、从容流逝的时间。难怪既在布罗茨基早期的作品《从郊区到市中心》,也在他最后写就的诗《八月》(ПСН)中会出现来自普希金的引喻“年轻的、陌生的一代”,这个情节远比对它的平常解释凄惨。同样可以说,布罗茨基作为其诗学基础的韵律特征和话语的冲突,乃是普希金的形象、普希金的“游戏人生”和“冷漠的大自然”的冲突的抄本。只是要懂得,普希金的“равнодушная”这个词不是用于平常的意思“无所谓”、“漠不关心”,而是用它的本义——像拉丁文aequanimis的仿造词。讲的是自然界的平均性,自然界没有个性,没有善恶之分,生也不比死好。布罗茨基经常用自己诗行的格律使人想起这一点。在他那里也能找到公开的声明,以一种佛教徒精神宣称,必须完全接受这些生存条件,“与神融为一体,如同与风景融为一体”(《与天人交谈》,КПЭ)。
在《美好时代的终结》和《言语的一部分》的诗行中他既成功地模拟时间(通过节奏),又并不成功:他提高嗓门,怒不可遏,满腔热血。于是诗行中出现了希腊人所谓的两种元素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便没有戏剧。
卡尔·普洛菲尔打算出版写于《在旷野扎营》问世后的新诗诗集,或诗人移居美国后不久的诗选。不过布罗茨基不急于出版。推迟的主要原因是创作方面的——作者对写于1970年之前的“旧作”不再感兴趣了。而新作,他在1973年和1974年觉得还不足以凑成一本书。发表于1975—1976年的组诗《言语的一部分》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在母语环境外创作潜力会枯竭的担心没有应验,可以考虑出书。组诗的标题应该也就是书的标题。关于书的构成问题,诗人和他的朋友出版家有过争论:布罗茨基真正想出版的是1971年后的新诗,但这样一来,在俄罗斯写于《在旷野扎营》之后的那些优秀作品就被排除在诗集之外。终于决定——出版相互衔接的两本诗集,而不是一本。不过,布罗茨基对这个计划作了重要的修正。他原则上不愿拿《1972年》这首诗作为第二本诗集的开卷之作,也就是说,不愿在写于国内和国外的诗之间划一条界线。正如他拒绝承认,审判和流放是自己人生中的特殊的、命运攸关的事件,被驱逐出境、移居美国,他也认为不过是“空间的延续”。如果说他的生活和诗作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是发生在1971年和1972年之交,而不是在五个月以后。后来他说:“……1972年是一条界线——至少是苏联的国境线……但绝不是心理上的界线,尽管我在那一年从一个帝国跨进了另一个帝国。”[133]《致暴君》、《波波的葬礼》、《素描》、《致罗马友人的书信》、《纯真之歌,它是——阅历之歌》、《奉献节》、《奥德修斯对忒勒马科斯说》写于1972年冬、春的俄罗斯。《1972年》、《蝴蝶》和《古典芭蕾是美的囚笼……》是在国内开始写的。
在准备出版时,布罗茨基对《言语的一部分》所表现的兴趣远大于对《美好时代的终结》的兴趣。他感到自豪的是书名和收入其中的同名组诗。布罗茨基倍感珍惜的思想是:作为人的创作,他的《言语的一部分》大于作为生物个体或社会一分子的人。后来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有代表性的诗选用的也是这个书名(Часть речи. 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0)。
和布罗茨基所有的诗集一样(只有《献给奥古斯塔的新四行诗》例外),《言语的一部分》开卷就是圣诞节的诗《1971年12月24日》。收尾的是《佛罗伦萨的12月》,这首诗几乎是在诗集准备付印时才加上去的。两个“12月”之间显然有主题上的呼应。列宁格勒的诗的开头“包围货摊的”群众,回忆起来很像佛罗伦萨的诗末尾的“包围有轨电车场的”群众。
《言语的一部分》与布罗茨基其余诗集的区别在于单篇的诗(16首)较少。主要部分是四部组诗(《致罗马友人的书信》、《致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十四行诗二十首》、《墨西哥余兴节目》和《言语的一部分》——总计56首),还有一些结构近似组诗的诗,如《波波的葬礼》(分为四个部分)和《纯真之歌,它是——阅历之歌》(两个部分各有三首诗),最后还有叙事诗《科德角的摇篮曲》(布罗茨基称之为“诗”,不过看来是用于其广义,指诗体作品)。严格地说,《……摇篮曲》及其特殊的抒情题材,与组诗之间的体裁差异已被磨灭,然而这改变不了总的情况:在1972年至1977年这个时期,诗人倾向于创作系列性的风格相似、题材多少有些联系的抒情作品。
九
布罗茨基在西方的生活,简略地说就像沿着成功的阶梯上升。名牌大学教授职位的相当可观的薪酬。文学家所可能获得的一切最高的奖项和奖金,其中包括1981年的“天才奖”、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的美国桂冠诗人称号。布罗茨基是耶鲁、达特茅斯、牛津的荣誉博士,弗罗伦斯和圣彼得堡的荣誉市民,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如此等等,诸如此类。
不相等的两半在人生的“黄金分割”中所大致折射的反差很大的对照,只是呈现于局外人的肤浅的观感。自然,采访记者经常会问,移居西方对他有什么影响,布罗茨基耐心地、时而气愤地回答说,这不过是“空间的延续”。在《科德角的摇篮曲》第四章他列举了与“改换帝国”有关的生活特征:
改换帝国,以致人声鼎沸,
以致讲话时唾液四溅,
以致栖身的陌生角落无数,
以致平行线相交(通常在极地上)的机会
慢慢地越来越多。而这,
帝国的改换,还与劈木柴有关……
在陌生的角落生活很不习惯,经常要讲外语,甚至还要劈木柴,在列宁格勒是不必做这些事的,可这里有壁炉。不过,归根到底
……笔
急切地要讲述
相似的故事。因为你们手里拿的
还是从前那样的笔。小树林里
长的还是那些植物。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常生活中的祸福同样地干扰着布罗茨基,因为两者都会卷进来使他分心,不能专注于唯一的要务——写作。1964年1月当民警冲进来进行恐吓时,他在想,要是能把他的诗《穿棉袄的园丁,像一只鸫……》写完就好了。
《美好时代的终结》和《言语的一部分》问世后,到他出版下一部诗集《乌拉尼亚》过去了十年。乌拉尼亚在希腊神话中不仅是司天文的缪斯,还是阿佛罗狄忒·乌拉尼亚(“天上的缪斯”),是两个阿佛罗狄忒之一。另一个是阿佛罗狄忒·潘婕莫斯,即“全民的缪斯”,或如А. Ф.洛谢夫所译“庸俗的缪斯”。1988年出版的诗集的英译本,其结构与俄语的《乌拉尼亚》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不过英语的书名有些改动,不是《乌拉尼亚》,而是《致乌拉尼亚》,这澄清了一个思想:《致乌拉尼亚》——是布罗茨基内心传记的矢量。
1992年布罗茨基曾向采访记者解释诗集的名称,他说:“我觉得,(但丁)好像曾在《炼狱》……向乌拉尼亚恳求帮助——帮助他把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改写成诗。……我曾想把书名改为《迈向乌拉尼亚》,仿效奥登的《迈向克利奥》……”(Brodsky 1992)。
书名也与布罗茨基特别喜爱的巴拉滕斯基的诗《最后的诗人》(1835)有关,不过,像布罗茨基的暗中援引所常有的那样,他的援引是争辩性的。巴拉滕斯基笔下歌唱“天赐激情”的诗人与“冷的乌拉尼亚的崇拜者”是对立的。相反,布罗茨基确定自己的缪斯是“冷的”司天文的缪斯、司地理的缪斯,广义的解释也就是不以激情为转移的客观创作的缪斯。《乌拉尼亚》是最直接意义上的冷书。七十三首诗中有二十四首,几乎占三分之一,讲的是冷、冬天和秋天,讲春夏的只有十首。《乌拉尼亚》中有一些热爱生活的作品,如《马泰广场》、《罗马哀诗》、《燃烧》,不过占优势的是顺从天意的主题,追求冷漠、恬淡的格调。把《乌拉尼亚》和主题相似的早期作品比较一下,这一点就特别明显。像《致Z.将军的信》(ПКЭ)、《1972年》(ЧР)这样一些诗的政治热情变成了《1980年冬的战争》和《五周年》的忧郁的冷嘲热讽。热情洋溢的寻神(《与天人交谈》、《静物画》、КПЭ)变成了讽刺性的不可知论(《献给椅子》)。1968年的《斯特洛弗》(“分手时悄无声息……”,ОВП)讲到与心爱的女人分手:“死后的遭罪,/生前就已降临”,——而1978年的《斯特洛弗》(“好像一只杯子……”)是这样写的:
真的,叶子上的黑色
污垢积得越厚,
个人对往事,
对未来的空虚
就越不在意。
下一个诗节是:
若问我去“哪里”,
你听不到回音,
因为放眼四方
都是冰雪统治的世界。
关于生存于生死之际的两首长诗(颂诗)《蝴蝶》(ЧР)和《苍蝇》(У)形成了特别强烈的对比。蝴蝶是灵魂、死而复生的传统象征。《苍蝇》所歌颂的是传统抒情诗中不可能有的东西——一个萎靡、肮脏、垂死的昆虫。然而正是歌颂,而不是令人震惊和厌恶的描绘,像波德莱尔之后的诗所常有的那样。诗人在苍蝇身上找到了蜕变、死而复活的新的象征,它正在“光线昏暗的灯”下的“无色的尘埃”里爬行。
布罗茨基在《乌拉尼亚》中有目的地创作了一种没有先例的东西——单调的日常现象、生活寂寞的抒情诗。
布罗茨基出国时已是完全成熟的人,能阅读英语,但没有积极主动地掌握它。他从不认为自己是英语作家(“我是俄罗斯诗人,美国公民……”)。他在英语世界的作家声望首先基于他用英语写了(或用英语自译了)数十篇随笔、文章、公开讲演,其中的四十篇被编辑成书:《小于本人》(?Less than One?,1986)、《水印》(?Watermark?,1992;俄译本见《绝症患者的沿岸街》)和《悲伤与理智》(?On Grief and Reason?,1995)。他还写了一定数量的英语诗,并且勤奋地把自己的诗译成英语,不过,如果说他的随笔基本上受到好评,那么英语界对他作为诗人的态度就远非一致的了。他本人对自己的英语诗的态度也并不单纯。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自己的英语诗的次要的甚至消遣、游戏的性质。对于他是否认为自己是双语诗人这个往往会提到的问题,他对采访记者说:“这样的奢望我是完全没有的,尽管我能写出相当不错的英语诗。不过,当我用英语写诗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更像是游戏、下象棋,不妨说是玩拼图方块。……但成为纳博科夫或约瑟夫·康拉德——这样的奢望我压根儿就没有。”[134]另一方面,他顽强而又年复一年越发勤奋地继续写英语诗,并非总是轻松的体裁,而是抒情的、哲理性的和涉及当代悲剧主题的诗作。不仅如此,他还越来越信不过英语诗人和翻译家所翻译的他的俄语诗。在他逝世四年后出版的五百页英语诗集(CP)中没有作者不曾参与完成的译作。其中的诗是布罗茨基亲自用英语写作和翻译的或有布罗茨基的参与。至于“参与”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布罗茨基的朋友、诗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沃尔科特回忆道:“但实情是,与自己的所有译者共事时,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约瑟夫亲自完成的,甚至在节奏上,甚至在押韵上”[135]。
显然,充分了解外语诗的体裁特点和修辞手段可以丰富母语的创作。这种情况曾发生在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诗人之间。我们已经说过,英美诗怎样影响了布罗茨基作品中作者的“我”的作用和隐喻的结构等。但诗歌作品的更深层次——韵律、诗对语法的运用、不同言语风格的冲突的语义处理等——都取决于民族语言的典型特点,因而是不可译的[136]。不可译的鲜明例证是押韵的次数(押韵就其性质而言,首先是语音现象)。譬如说,三重韵(aaa),在俄语诗中罕见,而在英语诗,尤其是奥登的诗中却相当普遍,布罗茨基曾令人印象深刻地加以采用,如《五周年》(У),?Fin de siècle?(法语,世纪的终结),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的序幕以及《矫揉造作》(ПСН)。看来将这些作品译成英语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押韵的这个模式英语诗也曾用过。可是英诗大师如德里克·沃尔科特却说:“英语中的三重韵aaa有了讽刺的意味,如拜伦,甚至滑稽可笑的意味。在英语中很难为这样的尾韵辩解,因为其中有喜剧性或讽刺性的俏皮话……我想:试图用英语达到布罗茨基原作的这种语音效果会导致对诗句结构的极大破坏。”[137]布罗茨基英语诗的批评家,不论是否怀有善,对广泛使用阴性韵也有这样的反应。诗行的阴性结尾(即重音在倒数第二音节,而不是在最末音节)在俄语诗中就像阳性结尾一样平常,因而各自在修辞上是中立的。而当代英国人听起来就觉得滑稽可笑——阴性韵适合于搞笑的儿歌或轻歌剧的咏叹调,而把严肃的作品变为讽刺性的模拟。实际上不可能在英语诗中复制俄语诗的节奏结构。原因很清楚:俄语词大多是多音节,英语词大多是单音节。另一方面,俄语任何长度的词都只有一个重音节,而英语的多音节词却有一个强重音和一个弱重音。如果在英语作品中模拟俄语的节奏,就会给英语读者留下讨厌的“击鼓”的印象。然而与自己的诗的英译者合作时,布罗茨基首先坚持的恰恰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原作的节奏结构和韵脚。在这方面使他的诗英语化的尝试,他断然拒绝,认为太“流畅”[138]。
布罗茨基由于其随笔而在美国,很大程度上也在整个西方确立了作家的声誉。正是由于随笔西方才能理解和评价布罗茨基的才华的真正水平。1987年授予诺贝尔奖便是对这种才华的承认。
他极其认真地写了获奖讲演,力求在讲演中以最简洁的方式陈述自己的信念。这是我们从布罗茨基以往的全部创作中所了解到的那些主题,不过在这里陈述得特别坚决:他首先谈到艺术的人类学意义,然后是语言在诗歌创作中的首要意义。
在公开讲演和访谈中,布罗茨基时而会语惊四座,声称“美学高于伦理学”。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漠视艺术的道德内容,更不意味着艺术家有权成为非道德主义者。这是席勒和浪漫派的传统论题,在俄罗斯文学史上,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曾给予最详尽的论证。1981年格里戈里耶夫曾这样写道:“艺术作为对本能的生活之本能的自觉反应,作为创作力和创作力的活动,不屈从也不可能屈从于任何千篇一律的东西,包括伦理道德在内,不应该以任何千篇一律的东西,因而也不能以伦理道德来评判和衡量艺术。好吧,我要根据这个观点走向匪夷所思的极端。不是艺术要向伦理学习,而是伦理要向艺术学习(而且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说真的,这个怪论并非那么不道德,像初看时或许会有的印象……”[139]
关于艺术(布罗茨基认为艺术的最高表现是诗)陶冶情操,矫正性情,使人变得更优秀,并赋予他力量,以反抗敌对的、消灭个性的历史力量的思想,是有传统的。布罗茨基本人也牢记柏拉图将美与善和理性等量齐观的三位一体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美拯救世界”——还提及其他一些经典作家的名字。他根据这些一般性的论述作出文学的意义大于文化或文明的结论。艺术——是人类学的(试比较格里戈里耶夫的“本能的”),因为艺术改变着人作为一个种类的天性本身。在布罗茨基看来,只有读书人是有个性的人和利他主义者,不同于集体群居的人形动物。布罗茨基仿佛提出了他自己的人类进化论的版本。他的更优秀的人是不同于社会主义乌托邦“新人”的个人主义者,也不同于尼采的超人的人道主义者。两种情况使这些论述具有强烈的尖锐性——一种情况在正文里有所表述,另一个情况蕴涵于正文之中。布罗茨基从时代的悲惨现状出发谈到阅读伟大文学作品的必要性。20世纪是人口爆炸的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规模空前、惨无人道的行为:纳粹的大屠杀[140]。布罗茨基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功绩是没有让斯大林主义彻底毁灭人们的心灵并延续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进程[141]。这样的文化的美育效果对布罗茨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对熟读狄更斯作品的人来说,以任何思想的名义对和自己一样的人放一枪,比不读狄更斯作品的人要难得多。”因此“美学乃伦理学之母”[142]。在讲演中没有直接说出来,但含有对相对主义的偏见和流行于西方有教养阶层的知识分子习气的批判。布罗茨基没有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缺点视而不见,但直言不讳地宣称,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实验,首先是自己祖国的实验,乃是新时期最可怕的恶。然而西方知识分子圈子里大谈两种社会制度的各种缺点而又等量齐观,不加区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性抨击,以及一般地以善恶范畴评价政治制度一概被斥为反动。文学是道德进步的工具的观点即使不被斥为反动,也被视为陈腐和幼稚。这个观点的前提是作者写入文学作品的某种一致的内容,如但丁、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在相对不长的讲演中布罗茨基列举了二十多位作家和哲学家的名字)。但知识界占优势的风气是宣布“作家死了”,而后现代主义的公设之一是任何作品都有无限的多义性。因而布罗茨基在瑞士科学院的小礼堂所说的一切,用他惯用的说法,对很多听众都是“逆耳之言”。
苏联报刊只是在两个半星期之后的11月8日才第一次在《莫斯科新闻》上提及诺贝尔奖[143]。《文学报》到11月18日才有了报道。不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已刮起自由的微风。《新世界》杂志诗歌栏编辑奥列格·丘洪采夫(他早在1987年就在美国与布罗茨基有过交往)终于获准在12月号发表新出炉的获奖者的诗选。看来并非故意,但入选的作品大多是“信”——组诗《致罗马友人的书信》、《致明朝的信》,以及《奥德修斯对忒勒马科斯说》和《从哪里也没有人怀着爱心……》[144]这在记忆中唤醒了20年前所写的诗行:
……风,
像回到父亲家里的浪子,
立刻就收到了所有的信。
(《来自K城的明信片》)
十
1972年离开俄罗斯的时候,布罗茨基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祖国。从苏联侨居国外,只是单向的不归路。受惩罚的不仅是被流放的政治犯,而且家庭也不能幸免。布罗茨基的父母十二次提出申请,要求准许他们一起或单独去看望儿子,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拒绝的理由是毫无道理的:当局认为出国“没有合适的目的”。布罗茨基的母亲死于1983年3月17日,父亲在一年多后也去世。他们终于没有见到儿子。
戈尔巴乔夫当权后开始解除国家的封闭状态。记者越来越频繁地问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否准备回国。他起初回答说,等国内开始出版他的书就回国[145]。在1987—1989年报刊的最初报道之后,他的书终于在1990年开始出版[146]。随着出版的书越来越多,而刊物有关布罗茨基的文章和文学评论又潮涌而来,形成雪崩之势[147],疑虑支配了布罗茨基。他对祖国,尤其是对生身城市所怀有的感情是复杂而隐秘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回去势必会伴随着庆贺、电视和新闻界,要与生疏的人群会面。渐渐地他以玩笑的口吻来搪塞回国的问题,说什么他不该回到犯罪现场,也不该回到当初谈恋爱的地方。
对戈尔巴乔夫的苏维埃制度自由化的尝试,布罗茨基抱着怀疑的态度。他颇有洞察力地看出,这并不是和平的民主主义革命,像他的很多朋友和相识所理解的那样,而是俄罗斯政体习以为常的突变——官僚主义的帝国利维坦在变化的世界中适应新的生存条件。就在那时,在80年代末,他开始写作独幕剧《民主!》[148](完成于1990年),又在1992年写了第二幕,以回应前苏联事件的发展。布罗茨基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没有)写过真正的政治讽刺体裁的作品。甚至直接回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作品《致Z.将军的信》(1968,КПЭ)也是以一名疲惫而绝望的帝国士兵独白的形式写的,讽刺和抒情融为一体。然而《民主!》是纯粹的讽刺,是一幅政治漫画。就像早期带有政治讽喻成分的作品?Anno Domini?(1968,ОВП)和《帝国,傻子的国度》一样,剧情不是发生在首都,而是在帝国的一个省份。不过?Anno Domini?和《帝国,傻子的国度》中的帝国是假定的,而《民主!》讲的就是苏联,而某省指的是一般化的某个波罗的海共和国[149]。
另一篇直接呼应苏联事件的作品是《仿贺拉斯》(ПСН)。更正确地说,这首诗应称为《反贺拉斯》。贺拉斯的颂诗《致共和国》警告“国家之舟”在航行中会遇到可怕的危机,要谨慎。布罗茨基却完全相反,号召向未知的世界猛冲:“飞吧,小舟!”——这是诗的中心思想。“别怕呀!”——重复了两遍。这是——快乐的诗。展开贺拉斯的经典隐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布罗茨基选择了剽悍、肆无忌惮的格调,听起来剽悍而快乐,因为诗里高度集中了乖张的,其实是游戏的笔法。半数诗节都全部或部分地采用半谐韵,其中包括第一诗节:
Лети по воле волн, кораблик.
Твой парус охож на помятый рублик.
Из трюма доносится визг республик.
Скрипят борта.
破浪飞驶吧,小船。
你的帆像一张揉皱的纸币。
从船舱传来加盟共和国的尖叫。
船舷吱吱作响。
由于缩短每个四行诗的第四行,诗就显得仓促。作者似乎没有时间找到合适的词而以不合格的“еённый”塞入韵脚,没有时间顾及用形似词错综格拉近“неотличай горизонт от горя”是毫无意义的,也没有时间质疑同音异义双关语“Гиперборей—Боря”的性质。
如果说布罗茨基真的在某处模仿贺拉斯,那就在于他以可见的具体形象发展了对贺拉斯而言已是古老的“国家之舟”[150]的隐喻。诗的力量在于尽管诗行简短、“仓促”,一再出现头语重复,而诗的内容却并不局限于号召冒险地破浪飞行。寥寥数语,布罗茨基就让我们看到了多得惊人的现象:
肋骨两侧的衣缝声声撕裂。
舵手闲聊着凶残的鱼类。
甚至最勇敢的人们
也在大口地呕吐。
但小船的飞驶只是勉强跟得上诗人想象力的飞扬。横跨第五诗节和第六诗节的不完整的七行诗勾画了嵌入其中的整个短篇故事的轮廓:
他们就这样发现了列岛,
后来那里闪着海员们的白色十字架,
一个世纪之后,那里
有人向您出售系着细绦带
的书信,令人讶异的是
与土著妇女私生的可爱的孩子
那双惹人怜爱的蓝眼睛。
布罗茨基最后五年的生活恰逢俄罗斯和世界的巨变。他真正被卷入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时而以俄语,时而以英语的诗歌、文章和公开讲演回应重大事件。在这五年他总是前所未有地忙碌着:继续教学工作,参加各种广场集会。在美国到处奔走,时常漂洋过海。在美国获奖诗人的岗位上发起全美诗歌宣传运动。又开始了另一个活动,目的是在罗马创立俄罗斯科学院。
1990年9月他娶了意大利女子玛利亚·索查妮(按母系是俄罗斯人),享受着不曾有过的家庭生活的乐趣。1993年他们有了女儿安娜。
这个时期也是他从年轻时起在文学上最多产的时期。90年代他创作和翻译了一百多首诗、一部戏剧和十篇长篇随笔。这时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
易发心血管疾病想必是遗传性的。“26年不间断的颠簸,/生计的窘迫,法庭的惩罚”也起了作用,已知的局部贫血和心理上的应激反应是有关系的,不过从未搞清楚,是应激反应引起了心绞痛发作,还是疾病引起了心理的不稳定。在乡村饮食恶劣的条件下过于繁重的劳动,以及侨居岁月安排不当的单身汉生活也损害了健康。
在其漫长的成年生涯中,布罗茨基始终在他意识到的死亡的威胁下写诗。他不是忧郁症患者,有能力把日子过得充实,甚至快乐,尽管有病,尤其是在病情缓解的时候。他没有写于1997年的诗,即第一次动心脏手术后的那一年,但可以猜测,这是由于手术后的心情抑郁,个人性格上的某些原因,或希望不再像过去那样写作[151]。的确,《乌拉尼亚》和最后一本诗集的诗体有了不少新的变化,不过作者对生的(对死的?)感受也有了变化。只要布罗茨基意识到他的寿命多么有限,似乎他那阴郁的听天由命的情绪便会消失,这种情绪曾表现于1979年之前所写的作品,如《切尔西区的泰晤士河》(1974;ЧР)、《五重奏》(1977;У)、《诗节》(“好像玻璃杯……”;1978;НСКА)。相反,出现了一些不能不称之为朝气蓬勃的作品。那就是——《乌拉尼亚》中关于意大利的诗:《皮亚察·马捷伊》(1981)、《罗马哀诗》(1981)和《威尼斯诗节》(1982)。稍后,在收入《洪水泛滥的风景》中的成果丰硕的最近七年的诗中,与哀诗或讽刺性作品一样,也有很乐观的(《西班牙舞女》、《云》、《仿贺拉斯》和?Ritratto di donna?)。最后一本诗集与以往的所有诗集相比,喜剧的成分更多。幽默在一些诗中占优势,如《肯陶洛斯》(全部组诗)、《兰德维尔运河,柏林》、《你不会对蚊子说……》、《矫揉造作》和《墨尔波墨涅神庙》,当然,还有近乎滑稽的《演出》,不过在基调比较严肃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搞笑的地方[152]。在他最近的诗中有一首是《科尔涅利·多拉贝拉》(1995年秋),以悲剧性的、庄严的诗行结尾:“大理石使我的主动脉变窄”——对器物的硬化煅烧被重新理解为投身万神庙,在那里当之无愧者获得大理石雕像的永生。不过,这首诗的开头把身披托加的大理石罗马人比作从莲蓬下跳出来,仓促地变为一条毛巾的人。
“先知通常都不大健康”,布罗茨基早在1967年就这样写道(《再见,韦罗妮卡小姐》,ОВП)。他不是把疾病理解为反常现象,而是理解为创作的必要条件,即使一般地说并非人性的必要条件。关于经常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会使人生更有意义的想法并不新鲜。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CXLVI结尾的一个诗节里就表现了这个想法:
So shalt thou feed on Death, that feeds on men,
And Death once dead, there's no more dying then.
(亲爱的,你就以死亡为食吧,死亡是以人
为食的,/一旦死亡死了,便不会再有死亡)
布罗茨基的列宁格勒朋友亚历山大·库什涅尔也在其早期的优秀诗作之一(《即使在最轻松的日子……》)中写到心灵以死亡为食,把经常想到死比作有毒的植物籽粒:
可是没有这种籽粒,
就不是那个味儿,不想喝酒了。
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在《星期天的早晨》(1923)这首诗中以简洁的笔触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想法:“死乃美之母……”
与迷信的恐惧格格不入的布罗茨基曾在1989年的一首诗的开头就说:“世纪很快就要结束,而我会死得更早。”(?fin de siècle?,ПСН)在阳光的《罗马哀诗》中他也忘不了迫近的死亡,然而这种思量和为生活的欢乐而感恩的主题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罗马哀诗》的结尾是布罗茨基所有的六部诗集中唯一的向上帝的直接诉求:
低下头来,我有话要向你附耳低语:我
为一切而感恩;为鸡的脆骨
也为剪子连续而急促的声音,它已为我
剪破黑暗,既然黑暗——是你的。
甚至在《马太广场》的热情奔放的诗节中也会偶尔出现“残躯”和“躲到幕布下偷闲”(黑体表示着重号——洛谢夫)。这里有普希“在黑暗的无底深渊岸边”的陶醉,但某些人处于存在主义绝境而发生的“信仰的骤变”,在布罗茨基那里却毕竟没有发生。然而在他后期的诗歌中,在为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感恩的同时,还有挑战命运、不顾肉体的死亡而自我肯定的主题(《科尔涅利·多拉贝拉》,Aere perennius;ПСН)。的确,圣诞节的诗大多写于面对死亡的最后十年[153],不过索尔仁尼琴说得好,在布罗茨基那里“……圣诞节的主题好像被装上镜框放在一边,就像被温和的光线照亮的正方形”[154]。在诗人喜爱的大地存在的要素——海洋、江河、街道、女性美、心爱的诗人们的作品——之中还有圣徒家庭的基督教神话成分:生于岩穴,婴儿和星座的关系,逃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扎营。不过他对福音书题材的喜爱与个人得救的信仰无关。据其他诗作来判断,布罗茨基所承认的死后存在的唯一形式是作品,“言语的一部分”,他的贺拉斯式的纪念碑。诗人的笔比伪君子的全套家什更可靠:“由于有笔世世代代的犁沟会更长,/你们带着手提香炉永世待在犁沟里也是枉然。”(Aere perennius)
除了“exegi monumentum”,我们还在布罗茨基那里找到了其他一些传统主题,涉及诗人关于死的冥思,即纪念逝者的主题:“逝者把自己的一部分留给我们,让我们保存它,并继续活下去,使他们也能继续存在。归根结底,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55]。还有,另一次说得更简练:“我们就是他们啊。”[156]我们可以在很多《纪念……》(《追忆……》)的诗里找到这个主题的变体。仅在《洪水泛滥的风景》里就有六个:《安娜·阿赫玛托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157]、《纪念父亲:澳大利亚》、《追忆根纳季·什马科夫》、《威尔廷努斯》(纪念詹尼·布塔伐瓦)、《纪念Н.Н.》和《纪念克利福尔德·布劳恩》。
这个领域还有一个传统主题,即作者死后有机生命仍在延续。普希金的这个主题“年轻的一代、生疏的一代”的变体见于布罗茨基的诗《从市郊到市中心》(ОВП)、《1972年》(ЧР)、Fin de siècle(ПСН)和最近完成的《八月》(ПСН)。他还有该主题的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变体——生命的延续是腐烂、分解:“动物的尸体是——脱离笼子而自由,脱离整体而自由:是分解的微小粒子的封神仪式。”(“只有灰烬才知道,焚毁是什么意思……”;ПСН)尽管是自然主义,这首诗里讲的却不仅是有机体。未来考古学家所发掘的动物尸体也就是“被埋在土里的激情”。
除了传统的主题之外,布罗茨基还有他自己的与死亡问题有关的主题。正是这个主题极其广泛地表现于他的诗作,尤其是在晚年,不过早在《致罗马友人的书信》(1972,ЧР)中就已初露端倪。这个主题就是“我身后的世界”。
书信所寄予的罗马友人名叫伯斯图姆。像布罗茨基的另几首诗一样(参见《发扬柏拉图精神》中的福尔图纳图斯),收信人名字的含义是拉丁文的Postumus——“后人”,这是给父亲死后出生的孩子取的名字。贺拉斯也在颂诗《致伯斯图姆》中饶有趣味地表现了这个名字的含义:“噢,伯斯图姆,伯斯图姆!岁月如梭/转瞬即逝……”(颂诗,第2卷)[158]《致罗马友人的书信》与贺拉斯的著名颂诗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人生苦短的主题,而且还在于两篇作品的结尾都是生活场景在继续而不见作者(抒情主人公)的身影。相似之处得以强调,还在于布罗茨基追随贺拉斯,在末尾提到了柏树——古罗马人墓地上的树。在初稿(РНБ)中这个“死后的”情节是没有的:
大海在黑色的松木栅栏外闪着波光
谁家的船在岬角旁与风浪搏斗
我跪在摇椅上——老普林尼
黑鸫在柏树茂密的枝叶间啁啾[159]
定稿中“信”的结尾与草稿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闪动的月桂的绿叶。
大开着的门,满是尘土的小窗。
被遗弃的椅子,被遗留的床。
纺织品吸收着正午的阳光。
黑海在黑色的松木栅栏外喧嚣。
谁家的船在岬角旁与风浪搏斗。
在干裂的长椅上的是——老普林尼。
黑鸫在柏树茂密的枝叶间啁啾。
其实两段结尾之间的区别是原则性的。定稿中没有“我”。被遗弃、被遗留(这些词挤在一个诗行里是不无深意的)的世界的物理属性依然如故,它依旧是动态的,把自己呈现于生动的感知:月桂的有光泽的叶子在灿烂地闪动,纺织品因为有太阳而炙热,海在喧嚣,船在与风浪搏斗,黑鸫在啁啾。却没有人由于难以忍受的闪光而眯起眼睛,在太阳地里取暖,倾听大海的喧嚣和鸟鸣,目送远方的帆船并接着把书看完。顺便说一说,未看完的书——就是作家反映那个世界的书,《博物志》,老普林尼试图提供对整个自然界的百科全书式的叙述。
在这方面布罗茨基想象力的发挥特别富有成效。对他来说,任何地方的特点都是以前到过那里的人们此刻的缺席:“每一家在有供暖设备的同时/还有一个缺席系统”(《每一家在有供暖设备的同时……》,ПСН),“一片空地,我们曾在那里相恋”(《你忘记了被遗弃在沼泽地里的那个乡村》,ЧР)。在描写夜间噩梦般的四个房间时他说:
第三间——到处积着厚厚的灰尘,好像
空心的油脂,因为这里从未有人住过。
我喜欢这一点,胜于父亲的家,
因为以后到处都是这样。
(《这个房间散发着破烂和生水的气味……》,У)
关于这些诗行М.Ю.洛特曼写道:“总之,对布罗茨基而言,空即使不是超验的,无论如何也是彼岸的,它也就被纳入近似于宗教仪式上的圣像之列(“我信仰空”,如此等等)。空是全部物质世界的基础,它包含在物质之内,构成其实质——或不如说——构成其绝对的剩余部分。正是由于空物质才不是有限的。”[160]这是正确然而过于谨慎的见解。布罗茨基在有些作品中有意识地将空神圣化:
空。不过想起它
你就好像突然见到了无源之光。
(《1971年12月24日》,ЧР)
布罗茨基从年轻时起就对宗教学说很感兴趣,在这些学说中乌有、空是与存在和神性联系在一起的:佛教、喀巴拉、雅各布·波墨的神秘主义等。
从物理空间向观念的、玄学的空间转化的形象出现于《人们把一切都归咎于我,只把天气除外……》(1994)这首诗的末尾,布罗茨基打乱顺序,以这首诗作为自己最后一部诗集的末篇。他在《人们把一切都归咎于我,只把天气除外……》之后还写了不少诗。可是恰恰希望这首诗被看作他的valediction(告别辞):
……也许,一般的虚无之保留
会珍惜将它变为筛子的尝试
并为筛孔而感谢我。
在这首告别诗中,空间的洞孔与星融为一体,在布罗茨基的诗中还有一个固定的神奇形象源于福音书和《旧约》,也源于奥维德(在奥维德《变形记》第15卷中尤里·恺撒死后成了天上的星)。在同一年的另一首诗《在下一个世纪》中这样讲到星星:“因为对它们来说光速是灾难,/它们的在场是缺席,而存在只是不存在的结果”,就是说,布罗茨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以天文学资料为基础的一个隐喻,该隐喻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叙事诗《放开喉咙》中是以否定的形式来表现的:“我的诗一定会到达……不像死去的星星的光那样永远在途中。”[161]当然,根本的区别在于物体的不存在、缺席在布罗茨基那里成了存在的观念形式。
М.Ю.洛特曼在《诗人与死》一文的开头写道:在布罗茨基那里,“……话语侵入沉默、空、死的领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在敌人自己的领土上与之作斗争”[162]。当然,“与窒息作斗争”(《我总是强调,人生如戏……》,КПЭ),“言语的一部分”战胜死亡这个中心主题来到布罗茨基的诗里,不仅是作为普希金和贺拉斯的传统,也是作为古代的印欧传统[163]。洛特曼所引用的“我信仰空”只不过是《波波的葬礼》末尾的反题语境中的正题(ЧР):
已是周四。我信仰空。
在空里像在地狱里,不过更糟。
于是新的但丁向一页纸弯下腰来
在空白处写下一个词。
反题——词填充了空,黑填充了白[164],空白被消灭了。布罗茨基对空白问题,对缺席的情节的兴趣,首先毕竟不在于教条主义哲学,而在于艺术。
归根结底,对
这些空白处,对它们的
空洞的画面感到好奇才是艺术。
(《新生活》,ПСН)
尽管布罗茨基撇开创作过程,把创作过程时而归结为在纸上写下一个空泛的“词”,时而甚至简单地归结为用黑填充白色空间(他写字不用圆珠笔,总是喜欢用自来水笔,而且墨水一定要用黑的),不过,读者关注的当然不是“什么白在黑的上面”(《致Z.将军的信》,КПЭ),而是信的字符所描绘的诗人的想象。他的想象确实容不得空。无论如何,全球性的启示录、个人的死亡都不能使世界成空。切斯拉夫·米沃什有一首诗《世界末日之歌》,其实质在于,审判日当天和以后生活的因循守旧都在继续:“而另一个世界末日是不会有的!”这近似?Post aetatem nostram?(《我们的时代之后》)和剧作《大理石》[165]里所发生的情况。《大理石》从情景说明开始:“我们时代之后的第二个世纪”,——不过布罗茨基的一系列其他诗作仅限于未来学的某个细节或捎带提及的观察:《预言》(ОВП)中的堤坝,《官邸》(У)中伪装成列柱的军用火箭筒,《天气预报附注》(ПСН)在第一诗节末尾插入的更确切的说明——“甚至在未来已降临的此刻,/要保存一位女宾的雕像”(黑体表示着重号。——洛谢夫)。对布罗茨基而言,历史不是单向的过程,像一神教、黑格尔或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但也不完全是循环,而更像是镜子:过去反映于未来。整首诗《正午的房间》都与此有关:“在未来就是在混合体中,是在被反映的昨天……”——接下来是:
我们不会死,在期限到的时候!
而是一个孩子
用指甲把我们
从混合体上刮掉!
在成年的布罗茨基那里,1965年后怕死的主题从诗中渐渐消失。如果说对他喜爱的斯多葛派而言,哲学是死亡的练习,那么对他来说,这种练习就是诗。对死的恐惧让位于专注甚至愉快地关心丰富多彩的激流般的人生,让位于去“我们身后的世界”旅游的想象,冥思空的问题(缺席——在场)和斯多葛派哲学,后者有时被表现为粗鲁几乎是地痞无赖的形式。我指的是诗《悲剧的画像》(ПСН)。
这首诗注明的时间是1991年7月,开篇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一组戏剧”。书中在《悲剧的画像》之后是为上演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而作的诗《矫揉造作》和《墨尔波墨涅神庙》。引人入胜的是设法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布罗茨基将《悲剧的画像》这首篇幅不小,而且无疑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诗挤出了记忆。由于个人生活迎来了一个幸福的时期?由于彻底摆脱了这个题材?对此我们却一无所知。
《悲剧的画像》具有总结性,在这方面不亚于?Aere perennius?和《人们把一切都归咎于我,只把天气除外……》,可以在其中发现布罗茨基过去三十年所有诗作的基本主题的概要。例如星星的主题。
紧贴悲剧的面颊!紧贴戈耳戈涅斯的黑色鬈发,
从圣像的后面紧贴粗糙的木板,
像驶往东方的列车一样
带着从颧骨上滚落的
星星……
在布罗茨基的诗里星星也是被分开的恋人在天上相会的地方(《没有伴奏的歌声》,КПЭ),是上帝慈父般的眼神(《圣诞节的星星》,ПСН),也是绝望的泪水(《在湖区》,ЧР),也是挤满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小船(《雪在下,把整个世界留在少数……》,У)。星星——是人间苦难和宇宙之爱的交汇点。此时星星就是从颧骨上滚落的泪水,也是比喻的第二部分的驶向东方的列车,那些列车正把古拉格的几十万其他受难者送去遭受曼德尔施塔姆的折磨和处死。
这个片段的韵脚(指俄文的韵脚)以前也有过。布罗茨基在《五周年》(У)中说:
……我不爱酗酒,不亲吻圣像,
而一座桥上的戈耳戈涅斯的铁脸
我觉得是那个地方最正直的脸。
显然,这个韵脚的确含有深意,只能在《五周年》中加以揣测:圣像的反面是——佩尔修斯的盾牌。从圣像后面看着信徒的是天界,而从相反的方面看的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蠕动着的混沌的化身,它的目光是致命的。
佩尔修斯之盾——是一面镜子。诗的开头要人注视悲剧的脸,而布罗茨基首先看到的是他自己:
我们看一看悲剧的脸吧。看到的是她的皱纹,
她的鹰钩鼻子的侧影,男性的下巴。
首先投入眼帘的是皱纹。接下来在诗里出现的是疾病和肉体腐烂的越来越引起反感的细节。诗的词汇也与这些细节相适应:“打耳光”、“蹬腿”、“摇尾巴”。而在以往的年代悲剧“是美丽的”。在索福克勒斯和拉辛的世界,悲剧是人奋起反抗天命、反抗命运的摆布。在贝克特和布罗茨基的世界,悲惨的是人的肉体本身在其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和腐烂的路上。亚里士多德把悲剧描述为一切体裁中最体面的。它应该是理智的(《诗学》第6章)并回避低俗的语言表达(《诗学》第22章)。“悲剧的画像”及其长寿,若非阿拉伯式的尸恋,那就有伤大雅了。
我们倒在悲剧的怀里,准备寻欢作乐!
陷入她的并不年轻的肉体。
把她顶穿,直抵床垫的弹簧。
布罗茨基笔下的悲剧不用“崇高的语言表达”,只是极其不雅地发出牛鸣声:
在喉咙发出的元音中
你要选择蒙古人臆造的“ы”(呃)[166]。
使它成为名词,使它成为动词、
副词和感叹词。“ы”——普通的吸气和呼气
我们由于利害得失而声音嘶哑地发出“ы”音,
或带着“出口(выход)”的牌子冲向门口。
但站在那里的是你(ты)瞪着凸出的眼珠子。
与呻吟着“ы”的悲剧的丑恶性交暗示着俄罗斯人的淫秽——隆吉诺夫的《骠骑兵入门课本》:“Ы,是不用于词首的字母。/‘Ы!’——荡妇的呻吟,在快要结束的时候。”[167]这就是布罗茨基笔下的悲剧所比拟的情况,整首诗就是挑战婚姻的混乱和解体。这是充分展开的隐喻,即使最短促的音响听起来就像冲着死神的脸说:“Fuck you!”
很可能疾病会使布罗茨基渐渐地成为不能工作的残废,而他将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或手术台上。可是“……死神像贼一样向他走来,/突然偷走了生命”(杰尔查文)。1996年1月27日星期六傍晚,他把自己久经风霜的皮包塞满了手稿和书籍,准备第二天带着去南荻。星期一新学期就要开始了。他向妻子道了晚安说,他还要工作一会儿,便起身来到自己的书房。早晨她就是在那里发现了他——躺在地板上。他衣着整齐。书桌上与眼镜和一支不曾点燃的香烟并排放着一张白纸和一本打开的书——《希腊诗选》。
布罗茨基葬在威尼斯古老的圣米凯尔墓地,在墓地的新教地区,因为禁止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葬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地区[168]。不大的地方很像乡村墓地,不过在砖墙外威尼斯的潟湖惊涛拍岸。简朴的大理石墓碑上刻着普罗佩提乌斯哀诗的字句:Letum non omnia finit[169]。
列夫·洛谢夫
注释:
[1] 布罗茨基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一点(РНБ;略语表见注释)。
[2] 见Н. Гумилев.文集第4卷。华盛顿: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жного магазина Victor Kamkin,Inc. С. ⅩⅩⅩⅤ-ⅩⅩⅩⅥ。
[3] СИБ-2. Т. Ⅴ С. 318.
[4] РНБ.
[5] Н.费尔德曼的译文是:“我没有良心,我只有神经。”(Акутагава Рюноскэ. Новелы. 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74. С. 539)
[6] 《胜利的见证》(经作者А.苏梅尔金认可的译本)(СИБ-2. Т. Ⅵ. С. 8)。
[7] 《小于本人》(译者В.戈雷舍夫)(СИБ-2. Т. Ⅴ. С. 8)。
[8] СИБ-2. Т. Ⅴ. С. 329.
[9] Гордин 2000. С. 140(Я.戈尔金的书里全文引用了这封信)。
[10] Сергеев 1997. С. 436.
[11] Иытервью 2000. С. 123.
[12]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328.布罗茨基到过布罗德吗?我从未听他说去过乌克兰,估计他只是在去克里米亚或敖德萨的途中,从列车的窗口看到过乌克兰。不过布罗茨基从米兰寄给父母的没有注明日期的明信片(现收藏于彼得堡阿赫玛托娃博物馆)谈到他顺路去看了列奥纳多的《最后的晚餐》,又补充道:“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工作晚餐’这幅画是在姆林,在一座有很美的黄色李子的花园里”。“姆林”就是“磨坊”,在乌克兰往往被用作地名。有一个居民点就叫这个名字,而且离布罗德不远。
[13] 1963年秋,《列宁格勒晚报》有一篇文章宣称布罗茨基是寄生虫,他在答辩中写道:“我曾在地质队工作,到过雅库特、白海沿岸、天山、哈萨克斯坦。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的劳动手册里。”(引自Гордин 2000. С. 171)布罗茨基在地质勘探队一共出差五次:1957年和1958年去白海,1959和1961年去东西伯利亚、雅库特,1962年去哈萨克斯坦。1961年夏,他在雅库特的尼尔坎村被迫无所事事期间(由于没有驯鹿而不能继续前行)发生了神经性疾病,获准返回列宁格勒(参见:Шулъц 2000. С. 76)。
[14]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141;另参见:Волков 1998. С. 34。
[15] 作者审定并自费出版的布罗茨基五卷本文集,是马拉姆津于1972年至1974年准备就绪的;这是此后历次出版的布罗茨基1972年前的作品的主要来源。以后的作品,见МС。
[16] МС. Т. 1. С. 3.
[17] 引自Э.拉里奥诺娃提供给胡佛研究所的复印件。角形括号表示删节的部分。
[18] Волков 1998. С. 85.
[19]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150.“……在列宁格勒拿起笔来的任何一个作者,不论他多么年轻而又缺乏经验,都会这样或那样地把自己与和谐的学校生活联想起来,校名是普希金起的”(Волков 1998. С. 133)。
[20] 参见:Труды и дни. С. 21-24。
[21] 出版时没有米尔斯基的署名,他在本书出版的1937年被捕(书中作为编者署名的是译者之一М.古特纳)。这本书在布罗茨基的朋友圈里获得很高的评价,М.Б.迈拉赫于1963年赠予布罗茨基作为生日礼物(Мейлах 1997. С. 159)。
[22] Шульц 2000. С. 77.
[23] 参见: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417。
[24]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325.
[25] Глеб Семенов. Прощание с осенним садом. Л.: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С. 112.
[26] “特别受欢迎的是Г.戈尔博夫斯基、В.索斯诺拉、Α.莫列夫、Κ.库兹明斯基、Н.鲁布佐夫、И.布罗茨基的诗朗诵。这类诗歌有时被称为‘舞台诗’或‘声乐诗’。诗人与观众的视听接触影响了诗的韵律特征——诗的选音配韵和节奏的组合。”(Иванв Б. 2003. С. 548)在1950—1960年代之交,最受欢迎的列宁格勒青年诗人的名单应加上И.赖恩、Е.叶夫图申科(莫斯科的)、Α.沃兹涅先斯基和Б.阿赫马杜琳娜,他们以怪僻的朗诵风格为其特征。
[27] Гордин 2000. С. 134.
[28] 1960年9月2日;作者是Ю.伊瓦先科。
[29] 关于乌曼斯基小组的资料我主要得自Г. И.金兹布尔戈-沃斯科夫。另参见:Шахматов 1997。
[30] 参见:Волков 1998. С. 66.
[31] СИБ-1. Т. 1. С. 20(未收入СИБ-2)。
[32] СИБ-2. Т. 1. С. 21.
[33] СИБ-1. Т. С. 30(未收入СИБ-2)。
[34] 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зьминский.《杜鹃花奖》获得者//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1987,30 октября. № 3697. С. 11。正文中错为1958年。
[35] 最初发表于Знамя. 1957. № 2。
[36] 这在1972年之前的一个时期首先表现于非常多样化和富于独创性的诗节。详细的述评参见:Шерр 2002。
[37] Борис Слуц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3-х т. Т. 1. 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91. С. 71.就在这首诗里,斯卢茨基以前置词押韵(Немногое от — господ),这成了布罗茨基的“名牌”手法。
[38] 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London). № 4285(17 May 1985). P. 544。
[39] Евгений рейн. Избранное. М.; Париж; Нью-Йорк: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1993]. С. 6.
[40] Ludwig Wittgentein. Notebooks: 1914-191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 75.
[41]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Евгений рейн. 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 Человек в пейзаже//Арион. 1996. № 3. С. 34.赖恩曾为一部未完成的文献片采访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提到的那本书是:Е. А. аратынсн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Л.: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57。“布罗茨基和巴拉滕斯基”这个主题在叶菲姆·库尔干诺夫的论文《布罗茨基和哀歌艺术》中有所阐述,见Иосиф Бродский:ворчество,личность,судьба. С. 166-185。
[42] An Age Ago. P. 159.
[43] Рейн 1997. С. 73.
[44] 参见:Лосев 2002。
[45] Ахматова 1996. С. 234, 390.
[46] 参见:例如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174。
[47] Волков 1998. С. 256.
[48] Чуковская. Т. 3. С. 208.
[49] Волков. 1998. С. 256.
[50]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ью-Йорк: Изд. им. Чехова, 1970. С. 205.
[51] Ахматова 1996. С. 523.
[52] 同上,С. 588,601,637。
[53] 同上,С. 724。
[54] 《莫比·狄克》最早的俄文本是1961年出版的И.伯恩斯坦的译本(我们的引文纠正了译者的一些错误)。Г. И.金兹布尔戈-沃斯科夫告诉我,布罗茨基当时就非常热情地向他推荐这本书。《玻璃瓶里的信》、《新的儒勒·凡尔纳》和《你,缠满蛛网的吉他状的东西……》都有《莫比·狄克》中的类似表现。
[55] Волков. 1997. С. 317.
[56] 同上,正如托马斯·文茨洛夫给作者的信所指出的那样,更正确的做法,不是把НСКА比拟为《神曲》,而是要比拟为但丁的另一部作品?Vita nuova?(《新生活》)。
[57] СИБ注明的日期1983年是错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写这首诗的确切日期,不过那是在1963—1964年。除了修辞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情况足以说明:作者在НАСК中把这首诗放在最前面,即放在组诗《幸福的冬季之歌》里。
[58] Л. Ф. Ильичев.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партии//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18-21 июня 1963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4 г. С. 58-59.
[59] 同上,С. 36。
[60] 同上,С. 26。
[61] 引自:Гордин 2000. С. 159-163。
[62] 同上,С. 163。
[63] 半年后,伊利乔夫独断地核准了布罗茨基的案子,与А.А.苏尔科夫谈话时把诗人称作“社会渣滓”(Чуковская 1997. С. 217)。
[64] 参见:Loseff 2004。
[65] СИБ-2. Т. 2. С. 11.
[66] 1964年2月18日在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布罗茨基说他是在1月5日出院的(Гордин 2000. С. 182.)。这要么是维格多罗娃的笔误,要么是布罗茨基的口误,因为出院证明上写的是1月5日。实际上1月3日布罗茨基已回到列宁格勒。
[67] СИБ-2. Т. 2. С. 181-182.
[68] 参见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279。
[69] 几年后经历过“精神病医生的惩罚”的人中有一个是纳塔丽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她是诗人也是布罗茨基的朋友。关于实行惩罚的医生以及刑具湿床单,参见Bloch,Sidney and Reddaway,Peter. Psychiatric Terror:How Soviet Psychiatry Is Used to Suppress Dissent. New York:Basik Books,1977。关于在普里亚什卡河上的经历怎样成了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的素材,详见Loseff 2004。
[70] Гордин. 2000. С. 186.
[71] Якимчук 1990. С. 23.
[72] Гордин 2000. С. 187.
[73] Платон. Сочинения. М.: Мысль. 1971. Т. 3. С. 435.
[74] Эткинд 1977. С. 170.
[75] 初次发表时又补充了16行,是一年多以后在另一个禁闭室写的,组诗的标题更具讽刺意味——《禁闭室里的音乐》。
[76] 引自她的诗《你别怕,我还很像……》,这首诗被收入组诗《蔷薇花开(录自焚毁的笔记本)》。写于1962年7月,也就是在布罗茨基已经与阿赫玛托娃经常见面的时期,她想必正是在那时给他读了这些诗句。
[77] 参见:例如Disch 1980,Kirsch 2000. P. 40。
[78] 参见:Волков 1998. С. 89。
[79] 这个细节似乎是简朴的“写生”,处于意味深长的对比之中。飞行员在天空的飞行使人想起作者童年当飞行员的梦想。飞行员没有当成,甚至在播种机上抖动着,“满身”灰尘的他也“好像莫扎特”。作者恰恰对农业的实际情况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播种机变成了耙子(这是不同的农具,尽管拖拉机手会把播种机上的中耕机梁架叫作“耙子”)。“子粒……扎煞”听起来很奇怪。显然,由于这些原因这首诗在全集出版前未能发表。
[80]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433.
[81] Солженицын 1999. С. 182.
[82] 引自Гордин 2000. С. 137。
[83] 引自Гордин 2000. С. 137。
[84] 这种诗学也称为阿克梅派诗学。不过帕斯特纳克的日常文学活动与阿克梅派小圈子是没有联系的,他的诗学原则上与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是在这里引述的布罗茨基的信里所提及的方面。戈尔津在自己的书中引用的帕斯特纳克关于结构的特殊意义的论述,与布罗茨基的思想很相似(同上,С.138)。
[85] 一再出版的The New Pocket Anthology of American Verse from Colonial Days to the Present(edited by Oscar Williams)就有那些“黑白方框”——布罗茨基在纪念奥登的随笔中所回忆的那些诗人的肖像(СИБ-2. Т. 5. С. 263)。
[86] 参见: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154;Волков 1998. С. 159-161。
[87] 布罗茨基多次重复这个平行线情节。交叉的平行线作为抗议的象征,反对认为世界完全可以理解的纯理性主义观点,交叉的平行线是布罗茨基继承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别雷、帕斯特纳克、纳博科夫、华莱士·斯蒂文斯这样的作家(详见《美好时代的终结》的注释)。
[88] 对布罗茨基隐喻形式的详细分析,参见:Polukhina 1989;Полухина,Пярли 1995。
[89]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е:В 22-х т. Т. 15. 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3. С. 80.
[90] 我们在这里所作的总结,只能用于描述俄语诗和现代派英美诗之间的本质区别。谈的是倾向,而非绝对的事实。例如,暗示的潜台词也是阿赫玛托娃抒情诗的明显特点,而且在其他俄罗斯诗人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对暗示法的有效运用。这样的诗学大师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有的,不过他不是诗人,而是作家——契诃夫。参见“о‘чеховском’” у Ахматовой и Бродсуого:Лосев 1986,Loseff 1995。
[91] Волков 1998. С. 98.这是真实谈话的笔记,布罗茨基的话不完全正确:弗罗斯特笔下的情节远非“照例”发生在房间里。
[92] СИБ-2. Т. 5. С. 259-260(译文是经过校正的)。
[93] 《致Z.将军的信》。
[94] 参见:Сергеев 1997. С. 440-441。
[95] 关于СИП的出版经过,参见:Клайн 1998;Кузьминский 1998。
[96] Kline 1973. P. 228.
[97] Горбаневская 1996. С. 16.
[98] Сергеев 1997. С. 432.
[99] Волков 1998. С. 101. Е.彼得鲁尚斯卡娅推测,这部叙事诗的构思与斯特拉文斯基为男中音和室内乐队而作的叙事曲《亚伯拉罕和以撒》有关。1962年斯特拉文斯基来过苏联,曾在公开讲演中谈到这部作品的写作情况。布罗茨基经常关注斯特拉文斯基(Петрушанская 2004. С. 40-41)。
[100] Бар-Селла 1985. С. 213.
[101] Polukhina 1989. P. 264.
[102] Сергеев 1997. С. 428.
[103] Волков 1998. С. 318.
[104] Патера 2002;A Concordance to the Poems of Osip Mandelstam/Edited by Demetrius J. Koubourlis. Ithaca [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Словарь Языка Пушкина. М.:Государc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словарей. Т. 2. 1957;Т. 4. 1961.
[105] Волков 1998. С. 195.
[106] 参见:Проффер 1986。
[107] Вяч. Вс. Иван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ств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асимметрия мозга и образ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a//Текст и культура.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ⅩⅥ.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Тарту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ыпуск 635. Тарту, 1983. С. 12.
[108] Интервью 2000.С.567-568.可以设想这就是荣格在叙事诗中的回声——大海作为荣格所谓的无意识的主要象征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叙事诗的第13章(《关于大海的谈话》)。
[109] М. М. Бахтин.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79. С. 288-289.
[110] 试比较《静物画》的结尾——参见第7章的有关部分。
[111] Прот. А. Шмеман. Великий пост. Париж: YМСА-Press, 1986. C. 91.
[112] 帕斯特纳克以类似基督的主人公日瓦戈医生阐明了“医生”一词的这个含义。
[113] 马拉姆津注明1964年5月的叙事诗初稿:“睡在窗边的是戈尔布诺夫,而戈尔恰科夫就躺在他身旁。”(РНБ)
[114] СИБ-2. Т. 5. С. 264.
[115] СИБ-2. Т. 1. С. 5.
[116] 布罗茨基写《官邸》(1983)指的是苏联当时的统治者Ю. В.安德罗波夫(参见Рейн 1997. С. 194-195)。
[117] 《作家——孤独的旅行者……》(СИБ-2. Т. 7. С. 62-71)。
[118] 《临别赠言》(СИБ-2. Т. 5. С. 275)。
[119] Волков. 1998. С. 182.
[120] 布罗茨基很了解В. С.索洛维约夫的创作,不是仅凭布罗克豪斯和耶夫隆的百科辞典的词条。从流放中回来后,他手边有了一部复印的索洛维约夫全集,是有人从国外的朋友那里带来的。
[121] 关于这一点详见拙作?Home and Abroad in the Works of Brodsky?(Loseff 1992)。
[122]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95.记者问他,听说他已经正式信奉东正教了,这是真的吗,布罗茨基回答道:“这绝对是胡说八道!”(С.219)
[123] Волков 1998. С. 256.
[124] Альбер Камю. 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вобода. М.: Радуга, 1990. С. 66.
[125] 同上,С. 108。
[126] 福音书没有这个情节。很可能他是受了阿赫玛托娃《安魂曲》的影响,《安魂曲》也是分为十个部分的结构,其中的第10部分也与前九个部分没有明显的联系。第10部分《钉上十字架》是两个福音书场景,前一个场景引述了基督对马利亚所说的话:“别为我悲伤,母亲……”(引自东正教复活节前的圣餐仪式第九首伊尔莫斯颂歌。)
[127] 关于《静物画》另参见:Loseff 1989以及本书对这首诗的注释。
[128] СИБ-2. Т. 5. С. 274.
[129] 关于这一点参见上面涉及在诺林斯卡亚村阅读英美诗歌的章节。“布罗茨基和奥登诗体”这个题目不属于这里的概述范围,需要认真地研究。
[130] ?Сенегальская баллада? (1966); Евгений Евтушенко.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х т.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4. Т. 2. С. 96.
[131]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396.
[132] Ефим Эткинд. Материя стиха. Париж: Institut d'études Slaves, 1985. C. 114.
[133] Волков 1998. С. 313.
[134] 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118.
[135] Полухина 1997. С. 303-304.
[136] 为了公正起见,我应该说,布罗茨基曾激烈地否定这个看法,尽管毫无根据。我最初是在《英国的布罗茨基》一文中提出这个看法。
[137] Полухина 1997. С. 303.
[138] 参见:Myers 1996. P. 35.关于布罗茨基的自译参见:Weissbort 2004。
[139] А. А. Григорьев. Искусств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6. С. 264.
[140] СИБ-2. Т. 6 С. 52.
[141] 试比较魏德列关于布罗茨基恢复了两个时代的联系所说的话(见本书第2页)。
[142] 同上,第55页。我们不必犹疑,布罗茨基的这个警句是与他所喜爱的克尔恺郭尔相矛盾的,克尔恺郭尔将美学置于伦理和信仰之下,称之为享乐主义。
[143]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87, 8 ноября. С. 14.
[144] 除了“信”还有《新的儒勒·凡尔纳》和《小城的秋日黄昏》(Новый мир. 1987. № 12. С. 160-168.)
[145] 参见Интервью 2000. С. 223;Newsday. 1989,December 28. P. 57。
[146] 1990年出版了《鹰的秋啼》(Л.:IMA Press)、《诗集》(Л.:СП Алгa-фонд)、《诗集》(Библиотечка журнала Полиграфия)和有代表性的集子Часть речи.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ихи,1962-1989(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47] 据不完全统计(Указатвль 1999),献给布罗茨基的作品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年有近千篇。
[148] СИБ -2. Т. 7.
[149] 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也可以将《公元》(?Anno Domini?)解读为把前往波罗的海苏维埃共和国立陶宛的旅途印象移入了想象(参见:Венцлова 1998)。
[150] 熟悉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布罗茨基知道,这个比喻早就出现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那里,伊奥卡斯忒将国家元首比作在暴风雨中掌舵的舵手。
[151] 据档案材料的初步研究可以推测,布罗茨基在1979年写过诗,不过想必是觉得一无是处,认为这些作品需要继续琢磨。
[152] 布罗茨基将早在俄罗斯写的四首旧诗中的两首《高领衫之歌》和《伊万诺夫的浪漫曲》收入ПСН,这两首诗都是诙谐的讽刺性模拟作品。
[153] 我们说的是直接以圣诞节为题材的诗歌,而不只是与日历上的圣诞节有关的诗歌。后者有《圣诞节浪漫曲》(1962)、《绳索厂厂主别墅的新年》(1964)、《送客》(1964)、《话说洒掉的牛奶》(1967)、?Anno Domini?(1968)、《岸边的第二个圣诞节……》(1971)和《潟湖》(1973)。
[154] Солженицын 1999. С. 190.
[155] 引自在纪念卡尔·普罗费尔的晚会上的讲话(Beinecke;原文是英语)。
[156] 与阿廖什科夫斯基谈话时讲到自己的梦,这个梦诱发了随笔《致贺拉斯的信》(阿廖什科夫斯基当时就把这篇随笔转交给我们了)。
[157] “……形式上这是献给诞辰周年,内容对布罗茨基而言却是典型的‘悼亡诗’”(Лотман 1998. С. 196)。
[158] Квинт Гораций Флакк. Оды. Эподы. Сатиры. Послания.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0. С. 112. Пер. з. Морозкиной.
[159] 遗憾,我们只有最后一个诗节的草稿。
[160] Лотман 1998. С. 201-202.“很喜欢……更好了”,因为诗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民间的俗语作品。
[161] 布罗茨基的诗与马雅可夫斯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隐喻也指明了相似的主要因素之一:两位诗人都着迷于未来和时间问题[参见:Кристина Поморска. Маяковский и время. (К хронотопическому мифу русского авангарда)//Slavica Hierosolimitana. 1981. Vol. Ⅴ-Ⅵ. C. 341-353]。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是不亚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Ю.卡拉布切夫斯基是对的,他曾探索他所厌恶的两位诗人之间极为相似的特点,不过他还写道,布罗茨基“不仅比马雅可夫斯基无可比拟地更有教养,而且也比他聪明得多”(Карабчиевский 1985. C. 273)。参见布罗茨基与托马斯·文茨洛瓦谈话时罕有然而意义重大的自白:“我向马雅可夫斯基学到了太多的东西。”(Интервью 2000. C. 349)
[162] Лотман 1998, стр. 189.
[163] 同上,С. 194。
[164] 布罗茨基早就掌握了白色和黑色的象征意义:试比较青年时期未完篇的《百年战争》中的“‘土地是黑的’——‘噢不,它是白的……’”等等,《献给雅尔塔》(КПЭ)中白色世界的幻影,“白的在白的上面,作为卡济米尔的幻想(《罗马哀歌》,Ⅺ),雪被是空间最好不过的外貌(《我不是疯了,是夏天太累……》;ЧР),创作自我实现的不变情节是黑的在白的上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用过同样的意外情节:……黑的在白的上面还不算多,须知黑的在白的上面是不可改变的”(致А.迈科夫的信,1867年8月;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30 т. Т. 28 (Ⅱ)。Л.:Наука,1985. C. 205;黑体是着重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有的)。
看来很有可能,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莫比·狄克,或白鲸》第ⅩLⅡ章《关于鲸鱼的白》对年轻诗人的想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一章是关于白色的象征意义的专论:白“是精神本源的意味深长的象征,甚至是基督教的神自己的真正的帡幪,同时又加剧了人类所恐惧的一切的可怖。……不信神的一切色皆无色,而不信神是人力所不及的……”(赫尔曼·梅尔维尔《莫比·狄克,或白鲸》的俄文版.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67. C. 227-228)。试比较“与光学所教导的相反,在布罗茨基那里白并不意味着颜色的丰富多彩,而是颜色的完全缺失”(Лотман 1998. C. 204)。
[165] 在布罗茨基早期的诗作中还会遇到更传统的科学幻想等题材,例如他的诗《致阿赫玛托娃》(ОВП)和未完篇的叙事诗《百年战争》(Звезда. 1999. № 1. С. 130-144)。
[166] 1997年我在安阿伯向布罗茨基转述有关俄语史的资料,也谈到一种猜想,说俄语中的ы音是突厥语影响的结果。很可能布罗茨基也看到了巴秋什科夫对俄语的看法:“语言本身嘛,不怎么样,有些粗野,散发着鞑靼人的气息。什么是Ы?什么是Щ?什么是Ш,ШИЙ,ЩИЙ,ПРИ,ТРИ,ТРЫ?”(К. Н. Батюшков Нечтоопоэте и поэзии. М.:Современнк,1985. С. 252;引自Н. И.格涅季奇在11月27日—12月5日期间收到的一封信)。试比较Д. И.彼得罗夫斯基《宗旨》的著名诗行:“我们把后缀引入动词,/把前置词引入副动词,/为了让蒙古人不能/这么快就学会我们的表达技巧。”(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ский. Галька. М.:Круг,1927)
[167] 布罗茨基(Beinecke)凭记忆在工作笔记本里记下了《骠骑兵入门课本》的一些片段。
[168] 1974年布罗茨基寄语安德烈·谢尔盖耶夫,戏称想葬在威尼斯:“不过没有知觉的尸体/在哪里腐烂都一样,/被剥夺故乡的黏土,/在伦巴第峡谷的冲积层/腐烂也愿意。因为/自己的大陆上也是那些同样的蛆。/斯特拉文斯基长眠在圣米凯尔……”(Сергеев 1997. C. 453)
[169] “死去不是一切都完了”(普罗佩提乌斯《哀歌集》,4. Ⅶ)。碑铭是诗人的遗孀选定的,她知道布罗茨基爱好普罗佩提乌斯的作品,特别是这首哀歌,人们有时将它更名为《肯提亚之死》。这行诗也是布罗茨基给予崇高评价的康斯坦丁·巴秋什科夫的哀歌《朋友之死》(1814)的题词。与巴秋什科夫这首哀歌的呼应可以在布罗茨基晚期的诗《致西莫·希尼》(ПСН)中看到。也许阿赫玛托娃与布罗茨基谈起过普罗佩提乌斯的这首哀歌,那是在1965年秋他们交往密切的时期,因为正是在那时她曾向他反复朗读这首诗,并且说:“普罗佩提乌斯是一位优秀的哀歌诗人。”(Роман Тименчик.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в 1960-е годы. М.;Toronto:Водолей Publishers —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2005. С. 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