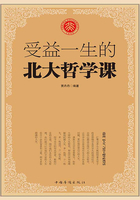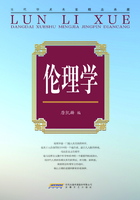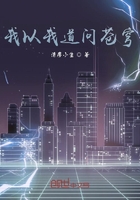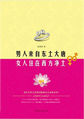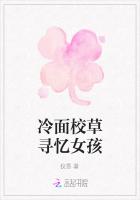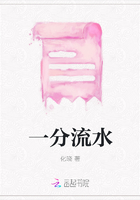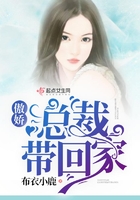人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使用的“诗性喻象”解决这个问题,正如《老子》中的“母亲”喻象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样。就像庄子的“言语”
(words)一样,喻象说出了某种东西。母亲和女性在《老子》的整个通见中占有中心的地位,这一喻象被用来指称非存在与存在互动的神秘领域。
在这个例子中,“诗意”和“喻象”不是“主观虚构的”(subjective)。事实上,这一喻象很可能与那个时代的一场辩论有关,这场辩论发生于当时伟大的思想中心稷下学宫,是在名叫“季真”和“接予”的两位学者之间进行的。关于他们,我们仅知道如下的情况。季真与这种学说有关:“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制造了它”(莫为);接予则与这一立场有关:“某人或某件东西制造了它”(或使)。问题似乎是:事物是如何诞生的?第一种回答似乎是符合常规的道家答案,即它们是通过“无为”的自然过程而诞生的,除了“出生”或生长这样的自然过程以外,它们的特殊现象没有任何特定的原因,它们只是自然而然地从“道”之中产生出来而已。后一种观点有可能反映了墨家的观点。它致力于根据直接的、可以言说的和特定的原因解释事物,在这个案例中,它似乎指某种有目的的造形或成形能力。这种思路在《吕氏春秋》中有生动的描述。“当春天的‘气’到来之时,草和树木就生长起来;当秋天之‘气’到来之时,草和树木就会凋零。
既然生长和凋零都是由‘某种东西或某人’[或使,与接予使用了同一个短语]所造成的。那么,它们就不是自发的[自然]。当那种导致了它们产生的东西在场的时候,每件事物都能起作用;当这种原因不在场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起作用。”(《吕氏春秋·孝行览》:“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当然,也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春天以及反常的夏天。这里很明显是针对国家统治者的作用以及他们所接受的特殊政治哲学而发的。好的国家并不会自发地“产生”。这一论辩似乎还对“无为”观念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攻击。统治者符合道德的努力意图起着关键的作用。
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庄子或者他的弟子们会选择季真的“莫为”学说。但事实上,在一段无疑属于庄子本人的文字中,他似乎并不明显地偏向于任何一方,尽管他清楚地表明整个讨论严格地局限于语言能够适用的领域。他不太愿意说单是靠引用一句“没有任何人制造了它”(莫为),就能打发“鸡鸣犬吠”这个事实。
有一种观念认为,和我们通常与人造物品相关联的特定造型及创造活动一样,自然也是与之同类的特定造型及创造活动;这样的观念,不见于中国思想中,可是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eus)或者某些印度思想模式中同样是缺少的。某些人对下述观念表示了明显的不满:对世界上的无数“事物”,不顾它们各具不可还原的而且独特的个性,统统用“自发生长”来简单地加以解释。正如上文已经说明过的那样,事物可以根据两种角度加以考察:一种是,根据它所具有的分立的、可感的存在(实),例如像“我面前的捆扎起来的马”;另一种是,根据它的“虚空”(虚),例如一匹马,它被分解为一百个部分,而每个部分又都可以继续分解直至“虚空”的状态。庄子似乎想说,“有人导致了它”的观点过分强调了以独特个性的面目显现的事物具有可感的、具体的、偶然的实在性(reality)。
“没有人制造了它”(译者按,莫为)的观点则过分强调了它从根本上讲是短暂的和“虚空”的。当庄子把注意力集中在独特的设计、繁华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所具有的令人惊讶的独特性的时候,这种“道”——是“造物者”或“创造力”,而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这种能力与事物的独特个性是关联在一起的——的喻象终于浮现到了脑海里。“鸡鸣犬吠”这类的事实似乎要求某种特殊的创造性。人们感觉到,这里存在的并非“科学的”兴趣,因为后者只关心“事物是如何制造的”;这里存在的大概是从美感艺术的角度出发,对于在当下起作用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创造力的欣赏态度。艺术创造力是神秘的:它既包含了自觉行动(为),又包含了“无为”
的成分。情况似乎是,当处理多元化的自然(有)领域时,庄子甚至乐于将“无为”与“为”之间的对立,连同所有其他类似的二元对立,都看成是相对的。实际上,关于特定的“创造性”原则或者“造物者”的观念,即使在后代也必将继续成为大部分“有机主义”思想的显着特征。它甚至还可见于朱熹的新儒学,在他那里,“造化”、创造性原则、转化现象的创造者等术语,经常与生殖原则或自发的生长原则一起使用。
人类领域与《老子》一样,在《庄子》中,正是在人类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麻烦。那种被称为人的特殊被造物是如何与“道”产生分离的呢?在《庄子》中,问题似乎的确要比在《老子》那里展开得更为深入。在《老子》中,当人们从高等文明的扭曲环境中解脱出来之后,就很有可能恢复到“道”的不需反思的生活状态。尽管与《老子》一样,《庄子》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致命的“有为”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但在《庄子》思想中,人们可以说,人类意识的病态对于整个物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深深扎根于人心(heart/mind)自身。我们因而发现,这里并不存在着任何“原始主义”的解决方案。这种形势并不能因为出现了道家的圣贤统治者而有所逆转。尽管避而不用“性”(人类本性)这个术语,但正像葛瑞汉坚持认为的那样,在《庄子》思想中有一个术语,其意思是某种使得人类成为人类的“本质精华”(essentialnature,情)的东西,而正是由于这种东西的存在,使得人们与“道”分离开来。事实上,使得人类与“道”相分离的并不是感情(feelings)。快乐、愤怒、愉快以及其他感情全都起源于“道”,就像“蒸汽凝聚成为蘑菇”[蒸成菌]一样,或像狂风怒吼时从各种自然洞穴中发出的不同声响一样(译者按,《齐物论》上谈过“地籁”,并云“万窍怒号”)。它们是人类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人类有机体又是由全宇宙的“真正主人”支配的。
然而,在这种特殊的有机体之中,人“心”(心/心灵)这种器官却具有一种致命的能力,它谮称能赋予自己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完全个体化的实体属性(attributes),这就是“彻底完成的或个体化的人心”(成心);通过一种自我封闭手段,它就能建立一种只属于自身的自我,从大“道”的流行之中分离出来。“成”这个词被用来指称如下的一般过程:藉助于这个过程,自然的事物能够变成自我封闭的事物或过程,它们具有只属于自身的自我;这个词自始至终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任何事物与过程,一旦完全地将自我封闭起来,与大“道”的流行分离开来,都意味着对于“道”的伤害。一个令人好奇的例证是,音乐家昭氏完成了完美无缺(成)的琵琶表演;正是其音乐的完美无缺——作为一种自我封闭的实体——反而割断了它与无限的、更高的音乐之“道”的联系。人心通过把注意力凝聚于变幻无穷的周边世界中的某些方面,试图把它们作为我们固定的目标或思想的对象加以凝固,从而去肯定人心的自我存在本身,这就使得它们绝对化了。人们的喜好和厌恶,既通过沉迷性的、占有性的激情,也通过涉及到“对”与“错”的固执意见,而变得固定起来,即使与此同时他本人就如同一切有限而短暂的被造物一样正在无情地朝死亡迈进,也仍然执迷不悟。“他们对于自己遇见的每一件东西都变得缠绵不已;他们日复一日地与他们的心灵作斗争……有时四处飘荡,有时深入探索,有时又精于计算……在小的恐惧之中,他们容易焦急,在大的恐惧之中,他们垂头丧气。在对‘正确’与‘错误’作判断时,他们的心灵就像弓箭上的弹丸一样飞射出去。他们坚守他们的意见,就好像他们发过郑重的誓言一般。他们像秋天和冬天一般地衰退……当我们相互指责和相互争夺的时候,我们的种族却像无人能够制止的奔马一般地趋于灭绝,这难道不是可悲的吗?我们终生劳累,但却没有见到任何成功……这难道不可悲的吗?光说我现在还活着,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身体衰朽了,心灵也随之衰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悲哀吗?”(《庄子·齐物论》:“与接为构,曰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祖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这里所说的既是普通人的生活,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
无论是为财富、权力而争斗,还是坚持人们固定化的意见和学说的正确性,全都在加固他们完全个体化了的心灵(成心)。悲剧并不在于存在着生死现象,而在于那种佛家称为坚持并凝固了世界之多样性的东西(译者按,执)。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出现一位能将人类高等文明的外在环境打扫干净的“圣贤君王”就可以拯救这一形势,因而我们发现,对于政治秩序(即便是《老子》意义上的)的拯救功能,这里持有激进的否定态度。人们也许会说,文明就其自身而言是完全个体化的人类的“基本性质”(译者按,情)的“自然”结果;人们还感到,庄子敏锐地注意到,在《老子》的圣贤观念之中存在着矛盾,圣贤有意识地设计了方案,从而引导人们远离文明的状态。
当然,尽管对于权力、财富或是感性满足的固定化的目标被抛弃了,但主要关注目光仍然投向了知性的领域。庄子对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冲突表示十分的失望,儒家和墨家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这类冲突的典型。当然,大自然中存在着大量的“自然”差异,但人类却具有这样的能力:只需要依靠相互贬斥对方为“错误的”,就能对同一件事拥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然而在“道”之中,又有什么东西能是“正确”或“错误”的呢?《庄子》提出了一个柏拉图在《智者篇》也曾提过的问题。“凭藉着什么,‘道’就被隐藏了起来,而我们就有了真实与虚假?凭藉着什么,语言就被模糊,而我们就有了正确与错误?‘道’怎么就会消失并且不存在了呢?言语怎么就会明明白白地在场,却不被接受呢?”(《庄子·齐物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柏拉图曾经谈及:“任何人在说任何东西的时候,必须说出某种东西;一个在说着那种不成其为某种东西的人,毫无疑问,根本就没有说出任何的东西。”当儒家和墨家就同一事态作出不同判断的时候,对一方来说是错误的东西,对另一方却是正确的。尽管柏拉图相信,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关于辩论的知性能力,并能通过推理最终将他引向关于实在的真实图画,可是毫无疑问,庄子会很惬意地(gleefully)思考亚里士多德作出的相反断言,后者发现柏拉图是错的。当用于特定场合的时候,孔子或墨子的观点也可能包含了某些真理;然而,他们试图用他们本人的“正确性”去包容无穷多样的环境和视角,在每一个地方都想发现道德的“错误”和思想的“错误”,他们的努力就像专制君主的偏执野心一样,是固执己见和孤立之“心”的显现。全书都含有这样的意思——即那些鼓吹各自的“是非观”的人,其实拥有超乎纯粹知性动机和道德动机以外的动机。他们追求的是名誉与声誉意义上的“名”;无论是对道德上的正确还是对知性思想上的威力,这一点都是适用的。那些关于固定化的原则或对立双方的对错问题的争辩,当然不能通达大“道”,因为“道”
从根本上讲是不可把握的。知性思想的争辩关心的是赢与输,而不是关心真理。它仅仅表明,赢方是更为精熟的辩论家。“设想你和我来一场论辩。
假如你驳倒了我,而不是我驳倒了你,那么,你是必定正确的,而我是必定错误的吗?”(《庄子·齐物论》:“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假如另一位争辩者被吸引了进来,他只是在引入第三种观点。只有有灵智的人才能真正适应无数种生活情境,而不带有前提、成见、兴趣的偏向,因为他没有必要去肯定他的自我。在这里,适应并不意味着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凑合过去”(getby)。庄子的“真人”没有任何必要去控制任何东西。
庄子坚决否定政治秩序具有“纠正”(correcting)事物的功能,在这方面,他比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家都走得更远。圣人的观念,或是认为政治秩序具有“纠正”(correction)能力的观念,是以一整套固定的是非观为前提的。
但不管怎么说,他似乎还是把政治秩序作为处于令人绝望、无法拯救状态之中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摆设而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下来。无论善恶,统治者都是人类领域这首发音不协调的交响曲之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然而,与墨子一样,在完全否定政治秩序具有救赎作用时,庄子也偏离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取向,尽管是一个很不相同的方向。
可以肯定,即使在《庄子》那里,仍然存在着一个观念,它表达的是道家“真人”(perfectman,“完善的人”)所具有的巨大的卡里斯玛能力,这种“真人”随时准备变成政治权力的焦点人物。真人(genuinemen)的更高灵智创造出卡里斯玛,吸引着其他的人,就像蜜糖吸引蜜蜂一样。像隐士哀骀它那样的人,不得不对那些云集于他们周围的人民予以挡驾,而被关怀人民的责任搞得精疲力竭的统治者们,则渴望着将政治责任交还给人民。着名的神秘主义者列子,被庄子描写成为(这一点多少有点令人可疑)一位喜欢运用他的精神能力来表现他自己、并想通过他的卡里斯玛巫术来控制世界的人物;即便是他,也为自己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力感到震惊。在他去齐国的路上,经过一家小吃店时,店主人放下其他的事情,抢着过来侍候他。于是他急忙返程,取消了齐国之旅行。然后,他向隐士伯昏瞀人感叹道:
“假如我不能驱散这种内在的精神能力[内诚],那它就会变成一种有辐射力的光线,一旦溢出人的体外,就会压服人们的心灵。”(《庄子·列御寇》:“夫内诚不解,形谍成光,以外镇人心。”)他接着表达了这种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