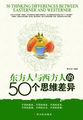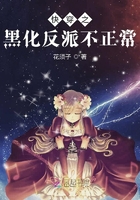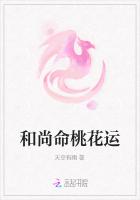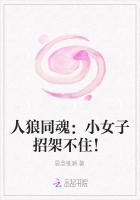团体。它不是把人们的心思集中在更广阔的公共事务上,而是把人禁闭在最大限度地关心其他家庭成员的卑微的欢乐与悲伤的天地之中。由于仅有妻子和儿女相伴,所以几乎没有为知识上的扩展提供任何空间。因而,“公共的”德性只有在公共领域之中才能得到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针对的是柏拉图——对于家庭要善意得多。家庭是发展某些德性和情感纽带的一个领域。的确,在关于父母之爱的评论中,我们听见了类似的回声:
“孩子们对于他们父母的情感(类同于人对神的爱一样),是一种人们对于善的东西、好的东西、高级的东西所具有的感情。因为他们的父母已经赋予他们以最大的祝福——他们给予他们以生命,哺育了他们,当他们到了上学年龄时,又为他们提供了教育。”亚里士多德根据人们之间的一般范畴“爱”(philia),对于家庭的德性和情感进行了讨论,而在人类多种多样的人际联系方式当中,这种德性是介于爱情与友谊之间的某种东西。他的另一论点也同样是与柏拉图对立的:一个好的国家必须由多种联系模式组成,它们的形成来自于不同的原因,但必须依靠爱(philia)而团结到一起。但是,当亚里士多德最终追问自己一个好的社会是如何诞生时,还是转向了政体和那些能够建构良好的法制体系的“政治科学”的大师。家庭和其他种类的人类联系方式一样,也是善的一个来源,但所有这些单独的善只有通过注意到那项“对于其他各项善拥有最大权威和控制权力”的研究——即政治科学——才能得到保证。在考虑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差别的时候,必须多加小心。孔子并没有断言所有实际的家庭都是社会道德的来源。他坦率地承认,在缺乏“道”的社会里,民众的家庭受到剥削和压迫之苦,因而不能指望它们实现家庭生活的道德潜能。在他的时代,统治阶级的家庭生活也出奇的糟糕。因此,他很可能也承认,相当一大部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在家庭的怀抱中学会德性。事实上,他也赞同这种情况只能够通过政治秩序来解决,而且这项任务必须由好人和聪明人承担。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使那些负有权力使命的人变成善人?无论人们发现孔子在对于等级制和权威的实际结构的关注、对于世袭制与功德的关注以及对于国家权力范围的关注方面有多大的灵活变化,对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关注始终构成中心焦点。最终讲来,这一道德品质的形成,仍然不能与其家庭基础分离开来。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最为关注的是在一个为了使得善的效果极大化、以及使得坏的效果极小化的“宪政”(constitutional)法律体系之中的权力和权威的分配问题。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位民主派,甚至也没有使其成为任何单一“宪政”方案的信徒,但它的确在城邦(citystate)
框架范围之内处理了通过结构性的“宪法”(constitutionallaw)控制权力和权威的整个观念。亚里士多德的善人与智者是那些根据自己的“政治科学”去设计尽可能好的宪法的“立法家”。尽管他们无疑都是有德之士,但他们用来创造一种明智的法律结构时首先依靠的是他们的智力。对孔子来说,问题仍然是:人们怎样才能获得甘愿接受“仁”
与“礼”支配的统治阶级?正如《理想国》中的柏拉图关注最好的政府统治一样,负有统治使命的那些人的个人道德修养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然而,与柏拉图正好相反,对孔子来说,这些导致人们正确处理权力和权威的气质倾向和习惯的第一个检验基地,与神圣的家庭制度之间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里暂且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年幼者的社会化问题所要处理的问题是:达到自我意识年龄阶段的人是怎样处理他们的家庭角色关系的?
《大学》断言,在古代,“想要为国家带来秩序的人首先要使其家庭和睦,要使其家庭和睦的人就要陶冶其人格”,据推测这里谈到的是成年家长。
(《大学》:“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一学说在孔子眼中的可信程度又因为他本人的观察而得到强化,孔子观察到,周代的“封建”结构依靠的是遵守王朝谱系的家族忠诚而获得的道德凝聚力,就正如这类忠诚的瓦解与整个周王朝政治体系的瓦解是同步的一样。我们还发现有一位问话者提问:“你为什么不在政府中任职?”孔子作了如下的回答:
“《书经》对于孝谈了些什么?孝——只是孝,并且要为你的兄弟们奉献,这就是在政府中活动,也是在政府中任职。为什么你认为必须‘在政府中供职’才成为参与统治过程的惟一形式呢?”(《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
‘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作出这一回答时,孔子的情绪有点恼怒。很明显,孔子的确想通过“在政府中任职”来影响更大范围的社会。然而,他得出的看法可能是其真实的感受。为恢复政府权威的道德基础所需要的基本品质,将会在家庭关系之中发现。如果说,儒家对于优良行为的“示范效应”
作用具有真实的信仰,那么,和睦家庭的榜样可以把它的影响辐射到周围的环境之中,即使人们不在政府中供职也同样如此。
论政府:《论语》中的“政治”领域
存在着多种理解《论语》的方式,它们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就我们对政治(the“political”)这个术语的通常定义而言,孔子的通见之中是否包含有政治的内容?尽管芬格莱特作了让步,承认孔子含有“政治方面的通见”,但他还是假定,孔子对于政府的基本关怀是“为了呼唤仪式性的政治-社会统一体”。因而,在他的着作中缺乏任何对于政治内容的单独讨论。
阿伦特(HannahArendt)坚持认为,“政治”一词预设了这样一层含义:
公民们在“公共自由”和“公共幸福”的生活之中,完全以伙伴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管理就不是政治而是技术。因而,中国人所说的“在政府中供职”就很难配得上“政治”这一庄严的称号。有点对不起阿伦特的是,事实上,在一个由大国组成的、其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仍然有着举足轻重重要性的世界上,我们还会用这个词来包含所有属于行政管理职能的运作。不管是对是错,我们的确把官僚制的职能包括到对于政治科学的研究之中。
的确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在理想的儒家社会中,即使在行政管理的意义上,统治阶级的先锋队也不是一个“政治阶级”,而是一种通过“神圣仪式”和充分体现在他们行为中的“仁”德精神来把社会团结到一起的牧师。这样的统治阶级的模范家庭关系会自动地将它们巫术般的“德”性辐射到整个社会。这是一种坚决赞成“通过榜样来治国”的儒家教科书式的观点。
的确,当叶公夸耀说,在他的国家,“有一位被人们称做正直的(直)
躬的人,其父偷了一只羊,躬就去作不利于他父亲的见证。”孔子则回答说:“在我的国家,正直观念与此不同。父亲会为儿子隐瞒,而儿子也会为父亲隐瞒。”(《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人们感到,孔子把家庭置于政体之上。这并非意味着他要替偷窃辩护。
而是说,家庭纽带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即使在这么难堪的情况下也必须维护它。“仁”和“礼”的整个神圣结构要以它为基础,正因为这一结构的存在,社会才能维持下来。
然而,“礼”并不仅仅适用于家庭,而且某些最重要的礼只适用于君王、领主以及所有那些与政治秩序有关的人。不过,也许仪式本身就构成了政治秩序的本质,当孔子谈起某种古代皇家祖先祭祀仪式的时候说:
“‘假如人们知道了它的解释,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地容易吧’——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掌。”(《论语·八佾》:“或问褅之说,子曰:
‘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掌乎!’指其掌。”)人们的确感到,某些庄严的仪式带有神秘的、巫术般的意义,这些意义与我们所使用的“政治”这个词的通常意义相距甚远,甚至与之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尽管词源学的解释极其冒险,但当我们转向译作统治或政府的那个汉字(政)的词源时发现,它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与在日常口语惯用法中倾向于称为“政治”的东西,有许多更为平凡的联系。“政”这个词与同音异义的词义“正直”、“正确”(正)有着关联。在甲骨文中,后者常常被用作动词,所描述的是步兵在进攻一个村落。王国维和其他学者假设,它的意义与动词“征”相同,类似于“征伐”(punitiveattack)。它所描述的是一次对于反叛的或者是外国的村落运用武力使其“改正”的征伐。即使在《论语》中,也只出现过一次现在用来表示统治的术语“政”,意义大约类似于“刑法”,“通过刑法来统治人民,使用刑罚来使他们守秩序,他们就会试图躲避[刑罚],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羞耻心。应该用道德的力量引导他们,用礼来使其保持秩序,他们就会获得羞耻感,并进行自我改正。”(《论语·为政》:“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以肯定的是,整个这一段所作的抨击强烈地支持了以精神道德性的力量为基础的政府观念。然而,“政”这一术语之单一的也许还是古旧的用法,却指出了更为古老的含义,这层含义暗示我们:政体的兴起最初与武力和强迫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于中国和对于其他文明同样正确。因而,即使在《论语》
中,“政”(统治或政府)仍然与对于惩罚性力量加以控制的含义有关。即使在《论语》中,这一层更古的含义也存续了下来并仍然在起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一种我们熟悉的观点,它把政府看做是合法性强力的终极例示。
尽管孔子的最高理想的确是以“仁”和“礼”为基础的政府,但却有证据表明,他并没有幻想过一个这样的情境:在那里,强力完全是可有可无的。
他肯定注意过武王用刀剑建立了周王朝,而且他还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当“道”畅通流行的时候,天子就不仅负责“礼”和音乐,还要负责公正的“惩罚性征伐”。只有天子才有合法性的权威,去惩罚不合原则的“封建”统治者,平定文明世界之内和之外的野蛮人。
在孔子生活的世界上,存在着一件悲剧性的事实:没有得到授权的战争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而且在缺少“道”的年代里,又造就了这样的环境,即使是“封建”诸侯也有道德上的义务来发动正义的战争。当邻国齐国的一位高级官员杀死了合法的统治者之后,孔子呼吁鲁国国君进行征伐,以惩罚这一犯有邪恶弑君罪行的凶手。然而,控制着鲁国的三个篡位家族故意拒绝了这个请求。孔子似乎把军事建制的存在看做是必要的与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任何政府的三项必备条件如粮食、武器和人民的信任中的一项,尽管他认为它最不重要。事实上,君子在某些情境里并不能逃避这样的责任,他要对武器使用得是否合理作出判断。
与此类似,尽管孔子清楚地强调过,要尽可能地缩小刑法的作用,又尽管正如上段引文所坚持的那样,只有当它能使人民依照内在化的道德情感行动时,一个政府才能被断定为好的政府,但是如下的这层意思仍然是清楚的:就像军队一样,即便是在好的社会里,“惩罚和刑罚”也是政府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推测,只要社会还没有真正实现道德力量的统治,这些就总是社会必要的组成部分。这就能解释论正名的那一段文字:“当礼和乐不兴盛的时候,惩罚和刑罚就不可能适当。”(《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在“礼”不兴盛的地方,人们不能期望大多数人的行为会接受内在道德情感的引导,因而,甚至连那些具有听从“内在道德领航员”的教导之潜力的人,行为方式也会将刑罚问题“设置”(中,target)为他们的行动目标;只有对那些很明显地不肯接受礼乐影响的人,刑罚才是“恰当的”。人们能够由此向外推演出一个儒家的乌托邦,在那里,强制性的制裁(它是政府的手段)将会完全消失。然而,人们在《论语》中并没有发现诸如此类的外推。
强力在统治中具有合法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政府也明显不只是仪式和榜样的事情。尽管孔子兴高采烈地断言,人们只有履行其在家庭中应尽的角色才能为其统治活动提供模式和范例,但很明显,他的目标是在政府中任职,而在政府中任职就不只是履行仪式性的作用。只有当某些先决的环境条件建立起来之后,仪式和榜样才能影响人民,而这些先决条件只能通过正确的“社会政策”(也许可以这样称呼)才能建立。
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君子也能够保持其自身道德上的坚定性,但对那些既没有机会,而且在很多场合下也没有能力来取得充分自我修养的广大民众来说,情况就未必如此了。人们也许会说,只要人民还在忍受剥削和压迫的环境,就不会对上等人的“榜样”有所响应。人们还应该说,那些表现出不具备“学习”能力的统治阶级的成员也许是不良环境的产物。
关于民众,也有一处清楚的论述,后来在《孟子》中以更明确的方式将它表达得更为清楚了:经济上的保障是群众道德化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因此,我们在中国发现了关于群体生活的“社会学”分析方法的明显进展。
他们的行为从根本上讲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塑造的,但塑造他们的社会环境却是统治者的责任。
当我们在古代文明中寻找那些多少有点与这一社会学观点背道而驰的见解时,也许又要提到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后者是以这一预设为基础的:
普通民众也能从过去的习俗和传统之中汲取足够的智慧,来塑造自己的道德生活,参与城邦的决策活动。在犹太《圣经》中,这一通见展现为一种神圣的诫令,民众完全有能力理解它们,仅仅凭藉其对于上帝的热爱和恐惧,人民便会很理想地将其加以内化并付诸行动;这一通见也表示,存在着一种并不完全取决于统治精英智慧的共同体生活。
然而,根据他个人的经验,柏拉图坚信,普通民众并不具备获得真正德性和城邦幸福的足够智慧,他和孔子一样确信,只有来自社会政治秩序顶层的伦理上和知识上的先锋队进行自上而下的运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事实上,《理想国》中的柏拉图只是在社会学的观点方面比孔子更为一致和更加彻底而已。在《理想国》中,他创造了塑造所有阶层的一整套系统,其中包括统治阶级在内。不仅是群众和武士阶层要由非人格化的运行体系予以塑造和决定,甚至连卫国者阶级本身也不例外。卫国者的组织机构是共产主义化的,他们接受的教育体系十分严厉,这意味着至少就其初衷而言很少依赖自身的个人修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