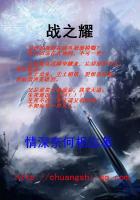临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株木兰花树下。触目尽是如墨的黑色,浓稠而寂寂,不见星,不见月,唯有眼前的木兰花开了又谢,花瓣纷扬而下,花上暗光流转,暗香铺满了他一身。
朝华躺在他的身边,眉头深皱,似醒非醒,像是被魇住了一般。
他探了探她的鼻息,气息若有若无,而她的脸颊甚是冰冷。临衍吓了一跳,坐起身,忙摇了摇她的肩,见其依旧双目紧闭,昏昏沉沉,他便又拍了拍她的脸。
她的发丝粘在脸上,眼睫低垂,似梦非梦,半醒不醒,如一只精致的白瓷人偶。临衍不知自己为何竟有这般离经叛道的比喻,他一手扣着朝华的两腮,另一手往袖中一掏,掏出一根银针。
“那东西没用。九殿下神体加持,凡人的小东西,怎会有用。”临衍吓了一跳,抬起头。
他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场面:他见到玉兰花树枝上有一只巨大的鸟,那鸟单腿而立,羽毛蓝白相间,喙为白色,咕噜噜如琉璃珠一般的鸟眼睛中间有一簇黑色的火焰。它的尾巴长长地拖在身后,木兰花一落地,尾巴便一卷。枝头木兰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生生不息,没有尽头,而那巨鸟被繁华簇拥着,颇有孤零零而君临天下之势。
那鸟居高临下看着临衍,嘎嘎笑了两声,道:“果然传言不假,这小脸,啧,当真神似。”
“……你是谁?”临衍手握银针,另一手护着朝华的头与肩,沉声问道。
“本座名唤毕方。”
毕方?《山河志》中驾着黑龙战车,随侍黄帝身侧,不鸣则已,一鸣则天火燎原的毕方?
临衍满目诧异,毕方见之,嘎嘎笑了两声,道:“现在的小娃娃当真没有见识。本座当年纵横宇内的时候,这天地还清浊未分,而你的魂火,还不知道在哪条河里泡着呢。”它一笑,那细瘦的腿便随着其巨大的身躯一抖,每一抖,那木兰花便抖落得更为厉害。
“……这幻境是你的手笔?你待怎样?”看临衍满脸戒备,毕方跳下树干,一蹦一跳,跳到临衍跟前,其形态刻意,如小丑般荒谬。然而那其白色的喙却锋利如刃,直对着临衍的胸口,试探之意若有若无。
“本座来同你谈一笔交易。若成,你可得本座两千年修为,自此四海宇内,你来去无极,扶摇直上,再没有敌手。如何?”
“……若不成呢?”
毕方闻言,又嘎嘎大笑,道:“你且听本座讲完。不成也罢,本座将你二人困在这四方石的方寸里,你这肉体凡胎,至多支撑十天,至于九殿下么……”它那琉璃珠一样的眼睛咕噜噜一转,长长的尾巴一卷,道:“九殿下不老不死,神魂不灭,想来要比你要更痛苦些。”它此一言,似是喟叹又似幸灾乐祸,阴鸷而又喜上眉梢。
临衍见之心下发毛,面上却更装得沉静如水。
“哦?我凭什么信你?”
“哈,有趣。”毕方闻之,拍了拍翅膀。更多的玉兰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复抽芽盛开,而它其巨大的身躯被一支细而长的鸟腿支撑着,说话之时左摇右摆,更显滑稽。
“你信与不信,同我又有何关系?”
——言下之意,信与不信,但在此间方寸里,都是他的地盘。临衍深觉有理,便也挑眉道:“也对。那你想要什么?”
毕方见他答应得如此之快,甚是诧异。它又拍了拍翅膀,长尾一卷,道:“我要九殿下身上的一件东西,那东西寻常人或许拿不到,若是你么……啧,”它居高临下地将临衍从头至尾,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番,道:“情之一字,当真不合时宜。你说对不对?”
你此言倒更不合时宜。临衍一挑眉,冷笑道:“你怎对我如此信心?”
毕方闻之,嘎嘎笑道:“你且一试,试试又不亏。若你都不行,那这放眼四海,怕就真没人可以做到了。”它一边说,以那宝蓝色翅膀往那花树指了指。
木兰簌簌摇落了一树香。毕方又道:“此间颇为奇特,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这木兰花还只是一颗苗。后来它越长越大,花也越来越多,我本想着,此处终于有了些旁的东西,也便不那么黑沉沉的,也便有了些趣味。”它一顿,话锋一转,道:“后来我才知道,此花没一次开落,这里的灵力便又被消耗了几分。这没一遭花开啊,你猜我在这里一共呆了多久?”
临衍没回话。毕方自问自答,道:“七百八十年。自神界湮灭,我寄身此囹圄之中,整整过了七百八十年!”它哈哈一笑,俯身看了朝华片刻,道:“九殿下这一遭又是生又是死,死里来,生里去,人间自是声色犬马,它又哪里晓得我们这些人的痛苦。”
它以其白喙拨了一下朝华的脸,临衍忙将其巨喙挡了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该怎么拿?”
毕方看它的神色多了几分戏谑,此戏谑令他极为不适。它那小眼睛一转,道:“你可有听说过一件东西,叫天子白玉圭?”
神不是“天”,天有其道,神奉天之道,礼天,礼魂,礼万物。神帝自诩“天子”,“天子”承上天之德,至高无上,以六瑞白玉器统御海内,璧礼天,琮礼地,圭礼东方,琥礼西方,以璋礼南,以璜礼北,安邦定国,承天景命。
昔年九重天的六瑞被封在皇室宗庙里,每到万魂归宁之时,天帝率众神礼天地,人鬼,地示,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事鬼神,谐万物。那天子白玉圭原先由神界太子所执掌,后来神界湮灭,六器不知所踪,再无人得见。
“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侍黑龙,却也听到了些许传闻。自九殿下被神界驱逐,此物便也没人再见过——即便是大礼之上也未曾出现。思来想去,唯有一种可能,这东西随殿下一起,进了轮回境。”
临衍一听,十分诧异,道:“九……朝华是被驱逐的?为何?”
毕方闻言,更是戏谑。由戏谑到同情,由同情再到不屑,它那小眼睛一转,道:“此事你自去问她,吾等可不敢多嘴。这天子白玉圭于你无用,于外头的凡夫俗子亦没什么用,其镇神魂,凝六魄之效,倒可令吾超脱生死,再不被此方寸之境束缚。”
罢了,毕方将长尾一卷,围着那棵玉兰树,来回逡巡,一蹦一跳,似怅惘又似遗憾,道:“吾在此间被困了太久,每天一睁眼,便只有这天,这地,这花与黑夜。听闻外界早已沧海桑田,世殊时异,本座就想看看,这没有了九重天的世界,该是个什么模样。”
它且说且叹,且叹且唏嘘,临衍听之,心觉怪异,又颇有些震撼。
他低头看了一眼朝华,她还在魇着,眉头深皱,神色不安,想来此噩梦颇令其难以招架。
她竟真的活了这么久?那沧海桑田,东隅桑榆,岂不都是一时之事?可百世之寿,乘奔御风,于她却又为何这般孤独?这般……令人心疼?
临衍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本想抚平她眉间的皱,方一抬手,却又在距她眉间咫尺之距的地方停住了。
他思索片刻,抬头道:“你既是神体,想必这小小的一方结界自是困不住你,为何你却定要抢她的东西?这方结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那不受控制的手终究还是点到了她的眉心处。
触手一片凉,她的身体仿佛属于一个死人,他这才想起,原来许砚之早些时候的一番胡话竟有些道理:朝华生死不辩,非人非鬼,或许于其他人来说,此“死”才是她的常态。
这般一想,方才小院中的那一幕便也有了些道理。他想,若自己也这般生死不忌,扶摇直上,想必这一番君子做派,也断不是现在的样子。
毕方见表情有所缓和,心下暗暗生喜。他摇了摇那长尾,道:“神体归神体,在这里待了太久,魂力不可支撑神体之重,出去了也是魂飞魄散,有何意思?”
它眼见临衍神色又松动了几分,心道此局有戏,一念兴起,便也多感慨了几句,道:“这世间能拖着此神体活个六百多年而不魂飞魄散的,便只有九殿下一个。九殿下自小得宠,尤得天帝垂怜,此白玉圭乃皇室至宝,太子殿下将其给了她,想必也是出于一片厚爱。”
它遥遥地看着那忽开忽落的玉兰花,面露得色,眉心一蹙黑火忽明忽暗,道:“你若将那白玉圭取出来,九殿下在凡间还能活个十天半个月,若我给你们腾个位置,在这结界里也勉勉强强能有个十年之寿——神仙眷侣,避世而居,十年,还不够么?”
“……这么说,此结界的时间流转较外界不同,”临衍不动声色地握紧了银针,眼睛清明而雪亮,沉声道:“怪乎不得,那王旭勇在此结界中也不过呆了数月,其修为长进竟这般迅猛,也怪乎不得,他一个菜贩子,得此宝物,竟还懂物尽其用,助其网罗了这许多凡间耳目,”
他一边说,一边缓缓站起身,直盯着那毕方的背影,道:“你令其在此井口层层叠叠地布下结界,哄桐州百姓入局,原来竟从一开始便是打了这白玉圭的主意?”
毕方讶然回头。
临衍一身疏落,无兵刃在手,亦无半分杀气,而他便这样一站,眼如点漆,黑白分明,颇有些天地袖手的气势。这便是了,它陡然想到,那人指挥黑龙战车之时,便也是这般运筹帷幄,这般举重若轻,这般……吓人。
它还没来得及反应,只见方才还在沉沉昏睡的朝华陡然睁了眼!
她指尖霜色稍纵即逝,几根琴弦簌簌飞射而出,在毕方感觉到痛之前,携了杀意的琴弦便早缠上了它的长尾。临衍抓过弦,二人往后一扯,毕方吃痛振翅,那长尾便被此琴弦拧绞着,生生扯掉了它大半截羽毛!
毕方惊怒,一口黑火喷射而出,朝华早有准备,一面水镜陡然在她面前张开,将那黑火尽吞噬。临衍就地一滚,捡起她脚边的晗光剑,长剑在手,一袭白衣,力拔千钧,万夫莫敌。
朝华见其狼狈地抖着那惨不忍睹的尾羽,边抖边跳,实如跳梁小丑,冷笑一声,道:“令一个凡人化形来哄我,你倒真想得出。”
原来她方才与王旭勇同“临衍”一番撕斗,昏昏沉沉,似梦似醒,直到临衍以一枚银针扎进她的后背,她吃痛知下陡然惊醒,方才听下此局始末。
当真是世殊时异,当年神界留下的几根苗,一个个都不想着凭其千年神力造福四海,偏都想着白骨生肌、长生不老;想也便罢了,还都惦记着自己这点残躯残魂与体内的一块破玉,真也就这点出息。
她长袖一震,司命剑在手,白玉兰的花瓣落了一地。
毕方看着她,又看了看临衍,这才反应过来。它阴鸷一笑,道:“王旭勇凡人之体,九殿下这一剑下去,他可有魂飞魄散?”此言既出,临衍也自诧异,瞥了朝华一眼。
朝华目不斜视,冷声道:“你竟关心他的魂火完好?”她言罢,一剑朝毕方砍去。
“他被你困在此方寸数月之久,其凡人之躯,早成了不生不死的怪物。你这番假惺惺地给我设个套,又是何意?!”
此一剑,有天地崩裂,奔雷电泄之怒火。
毕方拍着翅膀斜略过她的头顶,一剑下去,它那宝蓝色的柔亮羽毛则又被削去了些许。羽毛与玉兰花一同纷纷杨落下,一衣香,一衣着了彩色,毕方又惊又怒,张口一簇黑焱朝朝华喷去。
黑焰隐隐有股浊气,朝华一惊之下避闪不及,被那火焰擦过了肩,其黑衣被火焰灼过的地方丝丝冒着黑气。
“……你,竟已入魔?!”朝华捂着肩膀,退了半步,更是怒气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