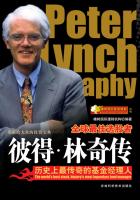汝陵候府。
蔺之儒正在翻阅医书,提笔记录着什么,写到一半,他忽的停住手中笔锋,低头看向那两株醉蓝叶。片刻间,眼眸轻转,不知在想了些什么,直到沙苑唤了他两遍才回过来神。
沙苑容色沉重:“皇上来了。”
皇上?
蔺之儒眉间凝了一层。
因寒冰烈火的谣言,多方势力齐聚龙海,此事与公主有所牵扯,皇上自然也跟着一道去了,后来生出一系列风波,便又辗转去了决谷。
此次回程,两人并未同行,公主竟提前一日至此,皇上,却是慢了一日。
如今公主已恢复记忆,下定决心再去夏朝,不知皇上这边,又是该如何。
搁置了笔,不思片刻,蔺之儒一抬起头,便只见皇甫衍已经跨门进来,他忙起身相迎,低了一礼。
皇甫衍入了房门,瞄了眼沙苑,再看向蔺之儒,免了礼。随即走了几步,瞥见桌上的锦盒,皇甫衍坐在了主座之上,声音悠沉:“听说,你找到了醉蓝叶?”
皇上的消息倒是传的快。
蔺之儒轻一点头。
“说说吧,夏王问你什么了?”皇甫衍再问。
醉蓝叶世间罕见,无处可寻,听闻夏朝赵家因缘际遇得了几株,便日夜照顾悉心栽培,繁殖了些许,但可惜自赵家抄家覆灭后,此物被一些无知的人毁去大半。
蔺之儒一直确信,此物定还有幸存,并且唯一能拿出此物的,天下只有一人。他也很清楚,夏王不会轻易交出这样重要的东西,必定是要以物换物。
而面前这位君王亦非好唬弄之人,这点小事只要一查,便能一清二楚。何况夏王以正门入候府,想不让人知道也难。
蔺之儒也未曾想要隐瞒,微微跪坐在案桌对面,提笔写上了几字。
皇甫衍接过纸条,端详着条子上的字迹,纸条上虽只有潦草两句,却也说的大致清楚:夏王以醉蓝叶为酬,问,清风凝香丸是否可救故人。
故人,故人……
夏王的故人,他当然知道是谁。
他之前一直想不通,夏王亲临龙海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奇珍异宝大可不必,为那寒冰烈火只是无稽之谈,若是为灵丹,更是说不通,夏王何曾是贪恋长生不死之人?
不过如今,他可总算是明白了,心中不免轻轻嗤了一声。
夏朝在皇宫必定也有几个见不得人的耳目,何况他又昭告天下,寻求良方药草,这么大的动静,夏王知晓阮以素病情,也并不奇怪。他奇怪的是,夏王似乎对阮以素仍为上心。
哪怕,这个女子,已在他后宫之中。
皇甫衍略微沉吟思索:“你是如何回答他的?”
蔺之儒给了个回答:“未必。”
“未必?”皇甫衍见着纸条上的二字,重复了一遍这个回答,深皱眉头,久久出神,把写着这两字的纸条拽在手心里,反复揉搓。
他从灵台山回来前,又去了一趟决谷,他知道,寒冰烈火和灵丹都是明皇留与她的东西,她这么大动静去拿,定然是对她很重要。寒冰烈火已落入白衣女子和夏朝手中,但这灵丹……
南宫祤明明想要,待在决谷多日,却碍于脸皮薄,一直不曾开口向白萧笙索求。后来,他去问及灵丹的时候,白萧笙却告诉他,南宫祤走之前也问过相同的问题,而且,灵丹已物归原主。
天下灵药,若连阮以素的命都救不得,岂不可笑。
“你如此回答,模棱两可,夏王未必深信。”说来,皇甫衍心底还是有些担心,若是南宫祤明知不可为而为,非要去夺来一试的话,只怕,她会有麻烦。皇甫衍说道:“她手中有着天下一等的灵丹妙药,此番前去夏朝,只怕危险重重,你的人务必要护她平安无虞。”
蔺之儒动了动眸子,颇为意外。
皇上与夏王皆是白萧笙门下,而白萧笙此人是个难以打交道的江湖人,把灵丹归还于她,绝对不是物归原主这么简单的理由,皇上与夏王两人都知道灵丹在她手中,这不足为奇。
想来,皇上也觉得夏王会夺灵丹。
蔺之儒意外的是,公主也说过,皇上知道她要去夏朝,却无阻拦之意,当下之意应当是默许,她决心已定,他亦是无法阻拦,只有倾其所能助她。
可是,既知危险,为何皇上不自己派人确护公主安危?反而要叮嘱他?
皇上明知公主一直恨其入骨,难道就不怕公主此去夏朝是要与夏王图谋?真的要如此任由公主在夏朝胡作非为?
按照以往,皇上怎会如此放任公主……
皇甫衍望着蔺之儒奇怪且意外的脸色,他又怎会察觉不出什么,若是以往,他定是会派人时时刻刻监视她,更不会让她这般偷偷摸摸名不正言不顺的去夏朝。
他知道,她与蔺之儒的关系非比寻常,就像他给夏朝公主下药,她宁愿遣人来找蔺之儒取解药,也不愿去求他。
他困的她越深,她越是反抗,丝毫不对他服软妥协,他在她心中的地位,甚至连蔺之儒都不如了。
看着那两株醉蓝叶,皇甫衍脸色暗了半截,沉声沉气:“蔺之儒,你的其他小心思,我当没看见,也不过问,但是她的事,你若敢有半点瞒我,我绝不饶你!”
房中有一瞬间的寂静。
静的连沙苑都觉得有点胆寒。
蔺之儒容色一禀,手贴额,郑重扣礼。
似是说,臣不敢。
无论如何,蔺之儒都不会忘记君臣有别。
沙苑一见此,忙是跟着掀衣一跪:“少爷绝不敢欺君瞒上,公主若有何动向,定如实汇报。”
待皇甫衍面带冷色挥袖离去,沙苑这才起身去把自家少爷扶起来,心里又喜又忧。喜的是皇上对丢失解药一事并无问责之心,连提都没提,想来此事对皇上来说并不重要。忧的是,少爷给皇上与夏王的答复,并不一致。
沙苑看着自家少爷松缓了口气,似是一扫雾霾,心定清神,沙苑忽然间想明白了什么,便故作一脸哀愁,说出自家少爷的心声:“我方才还一度担心,皇上这回会不会为了沅妃,又要与公主翻脸。少爷想必也有这番顾虑,要不然,又怎会欺君说出未必二字。”
“莫要胡说。”蔺之儒唇语一动,微微严肃。
“哪里胡说,皇上待公主从来是争锋相对的态度,公主失了记忆,还偏要不顾一切强求公主记起来。皇上对沅妃却是宠爱有佳,寻求天下良药,只为吊她一命,这明眼人都知道,皇上就差为沅妃豁出命去了。”沙苑抬了抬眉眼,却难得笑了一下:“可是,皇上却不问这灵丹是否可救沅妃。”
蔺之儒轻轻动唇:“君王心思,少猜。”蔺之儒回到位子上,轻轻盖上装有醉蓝叶的锦盒,然后唇边微启:“皇上方才进来,面色苍弱,似是身上患伤。”
沙苑是习武之人,皇甫衍一进来便也有所察觉,只是没敢提,如今听自家少爷提起,便皱眉不解:“皇上有伤,为何瞒着,不让少爷知道?”
蔺之儒目色沉稳,唇瓣微启:“这几日,不曾听说有何刺客行刺,夏朝的人自顾不暇,应该不会有机会伤人。”
“难道是……”沙苑有个猜测,但不敢明说,沙苑容色一愁:“少爷,您说,皇上与公主的关系,如今到底是好是坏?”
蔺之儒眉目暗沉,未曾回答。
沙苑一时间竟然有些猜不透,若是说好,两人从决谷回来却未同行,若是说不好,可他看两人的言辞举动,却不似以往。
公主眉眼间虽冷,但提起皇上时,那股恨意怒意不似从前浓烈,而皇上对公主的所作所为,也少了一丝争锋相对,目中减了几分凌狠锐厉,多添了些沮丧颓然。
也不知,两人又生了什么别的争执。
总之还是有些不对劲,明明皇上之前一心想让她恢复记忆,如今得常所愿,反而又不太欢喜。
沙苑想到候府另一座院落住着的人,皇上此次出来,其实是带着沅妃一起,后来因要去龙海,恐有危险,又听闻少爷在汝陵候府,便将她安置在此,直到现在。
皇上有伤,应该是直奔那院子了。
好歹沅妃到底也是会些医术,看些小病小伤倒也无碍。只是沅妃自己的病,一日不松口诊治,越拖只会越严重。
候府院落。
灯色落下,房中早已亮起烛火。
椅榻上,素衣女子旋靠着,手中捏着一本书,但却久久不曾翻页,婢子铺好床褥,打理好一切,才缓步过来,见此一幕,不忍提醒道:“娘娘夜里还是少看些书,仔细伤了眼睛。”
素衣女子醒了神:“你先睡去吧,容我一个人再看会儿。”
“娘娘整日无神,奴婢不放心,还是让奴婢陪着吧,好给娘娘掌灯。”婢子拿起一盏烛火,小心蹲下,伏在椅榻旁,好让女子旁边的灯光亮一些。
素衣女子合上书册,无奈道:“不知情的,还以为我在罚你,行吧,我这就去睡。”
婢子连忙把烛盏放下,接过书册,微微一笑:“娘娘向来体贴奴婢,怎舍得罚。”然后婢女起了身,正想着把书册放回架子上,一回身,却见门口不知何时已站了抹紫衣人影。
婢女惊得半天没句话,直到那紫衣人影走近来,将婢女手中的书册抽走,淡声说了句:“下去吧。”
眼见紫衣人影随手翻了翻册子,一边已经走到了椅榻边,素衣女子亦是惊了惊,已连忙从榻子上起来,想要行礼,却被阻止了。婢女才回过来神,又兴奋又激动的,话语断续道:“奴……奴婢告退。”连忙小跑了出去,带上了门。
皇甫衍将书放到一边:“你以前,不是不爱看这种杂书么?”
素衣女子眉色一敛,此次出宫,一波三折,说是带她出来散心,连朝政都不理,陪她去故地一游,却没想半路他便丢下她去了龙海,她住在汝陵候府,等了多日,难得再见他一次,他却转夜又跑去了灵台山。
她知道,能让他如此心急如焚不顾一切的,天下间恐怕只有一人,这些日子,他一直辗转多地,也一直都是为那个人。
那个女子,跌入雪山未死,消失了快两年。
应该再过不久,那女子是要回来了。
此刻三更半夜,他一回来便入她这院子,素衣女子心底有些意外,何况,他与自己昨日见到的故人,几乎是一前一后,难免让她有所疑虑。素衣女子目光撇向那本杂书,说道:“人是会变的,以前喜欢的,现今未必喜欢,以前所不喜的,如今也未必厌恶。”
他嗤嘲了一声,似是认同这个道理,却又无法想明白,喃喃道:“她以前也喜欢看,但后来,却说这些杂书幼稚无趣,通通给扔了。”
素衣女子皱了皱眉,能让他用这种语气说话,想必又是在那女子处受了什么气吧,素衣女子琢磨了许久,才转了话题道:“这么晚了,你还过来,是要歇在此处?”
他没说话,开始一层层的解开他自己的衣服,直到敞开里衣,肌肤微露。
素衣女子微微一惊,看见他腰腹处缠了纱布,那抹伤,染了深深的红色,女子又诧又忧,上前碰了碰,眉色凝皱:“你这伤……怎么回事?”
他坐在椅榻上,转而又微斜躺着,双目空神,唇白苍弱,没有表情的说道:“给我换药。”
素衣女子容色微急,转身便去翻箱倒柜,拿出常用的创伤药,小心翼翼给他敷上。
她的包扎动作熟练,如是习以为常。
只是这次的伤,似乎比以往重了些,以往给他敷伤至少会同她说几句话,会谈及那个女子,这一次,他却好像很累,什么都不想说,只是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腹口处,旧伤未好,又添新伤。
她看了有些不忍,他每回出去回来,总是伤痕累累,不用想,她也知道,这伤会是怎么来的,天底下有谁能伤得了他呢。敷完药,她轻声说道:“解忧倒是心狠,一点都不心疼,每次都刺同一个地方。”
他动了动,手掌覆在伤处:“她那么恨我,捅这么几下又算什么。”
“你就是太纵容她了。”素衣女子低了低眉眼,试探性的问道:“是不是解忧不肯回来,所以,你们起了争执?”
他未曾睁眼,也不回答她的话。
见他不言,素衣女子只好不再追问,轻叹一声,刚要起身去收拾一下桌上遭乱的瓶瓶罐罐,却不料,还未起身,他突然伸手,锁住了她手腕。
素衣女子看了眼被抓住的手,视线轻瞄,又望向他,很不明白。
只见他缓缓睁开眼睛,与她对视,嗓音醇厚:“听说,昨日有人寻你琴声,误入了这院子?”
她心中一紧。
他刚回来,竟然连这都知道。
昨日那位故人,出现得太过蹊跷,果然是绝非偶然。但她并未与那人多交谈几分,自认为没有差错,没理由惹人生疑。
她禀住呼吸,不缓不慢说道:“那人本是入府祭拜魏老夫人,一时迷了路,他寻我琴声,想必也精通音律。”
他又问:“那人可有惊到你?”
“自然是有。”她将他的手放下,坐在椅榻边侧,笑看着他:“我怎么说,也算是你宠妃,这私会外男,是什么罪?”
他紧紧的看向她,忽然说:“你信我吗?”
“当然信。”素衣女子很肯定,开玩笑般的说道:“回了宫,无论什么谣言蜚语,你会护着我。”
宫中的谣言蜚语日日换新,他怎会有时间理会,她此次随他出来,想必宫中那些女人,不会多给她好脸色。想了片刻,他没有转弯抹角:“既然带你出来,护你也是应当,只是你的病,太医都瞧不出什么,蔺之儒此刻也在候府,你若松口,我随时可让他帮你诊治。”
她笑意的脸容微微一暗。
“还是不愿意?”他沉允出声。
默然片刻,她摇了摇头:“我的病,只是小事,我自有法子。”
他从椅榻上起了身,理了理敞开的衣裳,曼斯条理的将衣服一点点系好,然后弯了弯眉目,对她说道:“你还是不够信我。”
她容色沉重,却说不出话来。
如若他知道她往日身份,会如何看待?还会留着她吗?
她不够信他,也不信蔺之儒罢了,蔺之儒给她开的那个方子,其中一味醉蓝叶,根本不是治她的病所需要的药,而她也知道,当今天下,醉蓝叶只有一个人才会有。
昨日,那位故人出现在此,会不会就是因为这味药?
“再这么撑下去,你会没命的。”他看着她,不是很懂她宁愿不要命,所坚持的是什么。
素衣女子怔凝了半响,从未想过会从他口中说出这样一句话,有这样一丝的关心她,也许正是因为知道他不会强迫她做什么,所以,她偶尔也会有这么肆无忌惮的时候。
她突然欣慰了些许:“我无父无母,从小寄人篱下,从我懂事起,我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这世上,能让我执恋的东西并不多。”
他拧了眉目:“那你现今留恋的是什么?”
她执恋的,与常人并无不同。
就如他的执念是冥解忧,冥解忧的执念,却是另一个人。
她起了身,清然微笑:“想必你今晚要歇在我这,我去给你拿床被褥。”
———————
解忧与燕麒燕嫆叙旧,在他们住处宿了一夜,她深知自己有要事在身,不便多待,燕嫆也只叹了声气,未做挽留。两人又寒暄几句,她才抽身离去,临走前,还不忘吩咐燕麒照顾好自己的妻儿,若有什么仇家为难,可拿她留下的信物去找蔺之儒相助。
望着挚友离开,燕嫆隐隐担忧,想起解忧身上的那些刀剑伤痕,伤口那么深又还未好透,又有那么多仇家,如今又要只身一人去夏朝,那样危险的地方,燕嫆如何放得下心,反手轻轻的抓着燕麒,柔声道:“真希望她能好好的,不要再这样拼命。”其他的,也无法多说了。
而解忧与燕麒燕嫆分离后,不顾身上各处的伤,快马加鞭穿梭于林中,一路马不停蹄,多日后,她再次经过了乌拉雪山,晋国与夏朝的边界。
她骑在马背上,悠悠的看着那白雪山尖,三年前的拢地之战,夏朝险胜,这地方,已经归于夏朝。离开夏朝时,公玉鄂拖带她走的捷径入渡。
可惜,公玉鄂拖不在了。
这次回去,她自然不能偷偷摸摸。
路过门关时,查的很严,比往日多了几排官军看守,前头排了很长队伍,大多都是商户生意之人,拉了些许货物,轮到她时,她递过去一张文牒。
官军查看文蝶无误,但看她的眼神有点古怪,递回去给她道:“关姑娘可以自行进去。”
那官军自她走后,忽然深吸一口气,慌不择已的走到一边,拿出几张画像同她的背影比对,越比对越觉得怪。
那几张画像,有男装有女装,很明显,画的都是她,真是好费一番心思。
但心思多又如何,她明显就没想易容,甚至大摇大摆的,能让人一眼就认出。
官军又瞧了眼旁边挂着的一些通缉令,那上头的画像中,会有通缉名字和所犯何事,而他手中的画像,仅仅只有画像,没有名字没有罪名。
官军咽了咽口水,上头没说要抓人,只说严查此人踪迹,并如实汇报,更重要的一点是不可打扫惊蛇,官军沉了沉:“快去上报,有了此人踪迹。”
解忧牵着马儿一路通行,入境之时,她明目张胆,入境之后,有人鬼鬼祟祟尾随,她是知道的。
行了多日,她辗转来到夏朝王都,立在城门下,望着眼前城墙上的郸阳二字,她竟然觉得,有些许的陌生,她离开的时间不久,短短几个月而已,却已物是人非了。
与关玲珑有关的记忆再次涌入脑海,她在郸阳结识的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隐隐约约的扯痛她的脑神经,她时常提醒自己,关玲珑是关玲珑,关玲珑的所作所为,绝非她可控制,更非她的意愿。
解忧缓步踏入城中。
与此同时,解忧进入的后一息,后面有一名青衣女子行步至城门下,那女子手持长剑,清凌凌的立着,亦是抬头望着城墙上挂着的那两字,久久出神。
这么多年过去,她又来了这个地方,青衣女子想起往事,眸光渐渐变得冷厉:“花忍,如今我要杀人,你还能拦得住吗?”
步入城中,周边热闹非凡,解忧一眼瞥望后头尾随之人,眉头一皱,实是生厌。很快,她弃了马儿,随身进入了一道巷口。
拐了几个弯之后,她便觉得有点不对劲。
后面,似乎有什么响动。
迟疑片刻,她折返回去一探究竟,便在巷子中央,看到这样一幕,那几个尾随她的便衣人早已倒翻在地,不省人事。而巷口中间,站着一抹青衣靓丽的背影,清清临立,落在背后的长发如瀑,随那抹肃杀的冷风似飘似摇。
解忧心中微禀。
这个人……
青衣人影有所察觉,回头,脸容一笑,声音却是轻轻凉凉的:“关姑娘,帮你解决这些鬼祟之人,可介意?”
她倒是不介意,正愁如何甩掉这些人。
只是,有点意外。
解忧横扫一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几条人影,再次确定这几人只是被打晕,还没死。这几个便衣人并非普通百姓,而是训练有素的夏家人,若是她一来郸阳便惹出夏家人命,便是麻烦。显然,青衣女子不知出于何因,仅仅只出手击晕了他们。
人人传说的唐家岭女魔头,竟也会心慈手软,这事挺让她意外的。
解忧处变不惊,望着面前人,只是简简单单道:“多谢唐姑娘出手相助。”
说是多谢,声音却冷的没有一点情调。
她谢的,不是因为给自己解决了麻烦,而是谢这唐问雁没有出手狠辣,把所有人都给杀了。
唐问雁是唐家岭大当家,与唐问雁打过交道的人,上至高堂达官,下至地撇流氓,唐问雁又怎会察觉不出面前这女子眉眼间的冷漠。唐问雁眉头一皱,慢慢走向她:“方才入城,便见这几人尾随于你,你在郸阳得罪了什么人?可要我相助?”
解忧道:“一些小事,不必挂心。”
从眼神中,唐问雁越觉得这个女子,与她之前见过的有所差异,相同的话说出来,有着不同的语调,总给人不同的感觉。
她还记得去年与这女子同谋共取盘山盐矿之事,那女子傲气凌骨,又胸有成竹,更重要的是,那女子话语之间总有一丝俏皮活泼之处,相处一久便觉亲切,见她更是叫着唐姐姐,便是当时这女子有所图谋,她也着实提防不起来。
她与这女子虽非挚友,却好歹相识一场,没想到多月不见,这女子对自己竟如此淡漠,既然这般,自己又何必非冷非热去招惹。唐问雁当即便道:“关姑娘有自己的打算,我多此一举了,告辞。”
说完,便乘风展身,从巷口上飞远了去。
解忧再度瞥了眼地上的人,虽不知唐问雁为何出现在郸阳,但也只当这是个很小的意外,并不多做理会,转身快速的离开了此处。
醉风楼。
解忧对醉风楼熟轻熟路,是从后门直接翻墙而入,一落地,直奔一座宅院。
她刚一进入,便听到亭台上奏出的琴音,亭中似轻纱的帘子随风搅动,将里头人影印的若隐若现,她撩开帘子,双眼对上里头的人,不冷不热的嗓音传过去:“傅公子,好雅兴啊。”
“听闻少主要来,我最近,又作了一首新曲子,可要听听?”男子微微抬头,嘴角的唇瓣勾起,单看那星碎的眼眸,便知这男子相貌绝佳,只可惜,他左脸上半侧,却是扣了半截的枯木面具。
听说,从未没有人看过他长何模样。
他是醉风楼最顶级的男倌,也是醉风楼的二把手,这里的人不知他姓名,都只叫他公子。
解忧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你觉得,我现今有心情听曲么?”
傅公子摇了摇头,他知道,她连夜奔波,日夜兼赶,自然不会闲的来听他奏曲,傅公子望着她微微泛白的唇色:“玉绝一事,我知道少主有怒,若少主心有不岔,想撒气,属下愿意受着。”
撒气?有用吗?
便是把他杀了,公玉鄂拖也回不来。
死了便是死了。
“我要一个答案。”解忧忍住心中的团团火焰,一字一句的厉声问:“你们早有耳目混入夏家,想必知道一些细枝末节,告诉我,人是谁杀的?”
“属下只知消息,不知过程。”傅公子又道:“何况夏家门风森严,我们的人身家背景再如何干净,能混进去一两个已是不易,少主此去龙海的目的是寒冰烈火,是以,我们的人自然必须跟着少主,玉绝被杀当晚,我们未曾在那山庄放眼线。”
“连你们都不知道?”话一出口,她便觉得是她自己想多了。
他们这些人从来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是谁杀的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重要的。他们更不会为一个微末人物的死因去仔细盘查,何况玉绝死因蹊跷,似乎跟夏家有些瓜葛。
这样费心费力的事,他们没有必要查清。
“那玉绝被杀,也绝非我等所愿。”傅公子见她失神几许,心中略有动容,那玉绝毕竟是她一直信任的得力手下,不像他,就是一个工具人,傅公子又接道:“少主切莫太过哀伤。”
她漠然冷声:“你们不喜他跟在我身边,早就巴不得他死,如你们所愿了。”
傅公子有些苦笑,她说的也很正确,玉绝与那些奴桑以前的旧人,虽都被她收服,培养成为她手中一股私人的势力,但对他们来说,奴桑人是外人,总归不可控制。碍于她次次威胁,他们之前一直不敢对玉绝如何。
如今玉绝一死,主心骨便散,那些奴桑旧人十有八九不会再听她受命。
这也算是断了她一只臂膀。
傅公子道:“若非少主放出那谣言,致使局面一发不可控,事情又怎会是如今这样。”
她轻声嗤凝:“便是我不放那谣言,你们也会去拿,你们要的东西,岂能不得手,既如此,何不利用一次。”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们趁她不记得所有事,竟然这样无耻的拿公玉鄂拖威胁她去拿,还在谣言中加上一句不死仙丹,让夏王为之轻狂。
傅公子眉眼稍低,很是想不明白。
明明所有人都尊称她为少主,都知道她才是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可她的所作所为,总是故意与族主背道而驰,而族主对此,却颇为无动于衷,似是随意她造作,但冥冥之中,又总会让她处于下风。
譬如这一次,她几番陷入险境,自己差点丢了性命,寒冰烈火终归被枭鹰羽得到,而她所在乎的人,公玉鄂拖冥栈容却也双双死于非命。
跟族主作对,又如何斗得过。
傅公子像是劝诫:“这一次,少主又一败涂地,还不认输吗?”
解忧眉眼低沉。
认输?
她又输了,上一次输的时候,把整个龙海冥家给搭了进去。
这一次,连公玉鄂拖也没能幸免。
她输的倾家荡产,一步步的成为众矢之的,身边更是没有什么可以支使的人了。她明白,他们只是要她当一个听话的傀儡而已,好好的做一个活着的,能让他们名正言顺的傀儡,她身边其他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可她既然已是孤家寡人,无牵无挂,她又有何后顾惧怕的,怎么可能就此认输。
“傅如。”她抬起头,念出他的名字:“你这一辈子,有过不甘心不认命的时候吗?”
傅如微一敛动。
面具下,看不清是何神色。
“没有。”过了片刻,他答的很坚定,像个忠心一般的奴仆,继而继续劝她:“少主何苦次次要与族主作对?”
她的眼中是怒的,如狂风骤雨:“一个从未与我谋面的人,凭何来掌控我的人生,凭什么干涉我的一切,凭何随意定我身边人的生死,凭什么?”
凭什么?
傅如也不知道凭什么,也许是凭别人强大如翼,而她弱小如蚁。他很早也说过,他只是一个工具人,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来完成上面的任务,不需要的时候,就当个倌人,弹一首又一首的曲子,陪那些达官贵人谈笑风生。
但他知道,少主之位,皇家权位,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趋之若鹫。她的尊贵身份,锦衣玉食,是有些人一辈子都求不来的东西,她却觉得自己被枷锁束缚。
生而为皇家人,这就是她所谓的不认命?
夏王宫。
南宫祤看着手中的人像,微微皱了眉。
这人像,是她曾潜入别院亲手交与他的,她还口口声声说怀疑此人使用易容术冒充夏家暗卫杀了她师父,更怀疑此人是南宫颢的手下。
他一回朝,便即刻让花忍去审查春红楼白水镇抓获的一干人等。
此刻,花忍便正在向他汇报所查之事:“严刑之下,倒也有人招了,此人名为马文石,是江湖杀手,端王以重金相聘,收他于麾下。”
得知结果,南宫祤并不意外,她之前那么信誓旦旦,如今得证,她所言为真。
事情经过也很清晰明了,何元夜巡山庄时,被马文石暗杀,并以易容术冒充,混入了山庄,待时机成熟,便一举杀了公玉鄂拖。
杀了人也就罢了,但那马文石并未及时撤离,而是继续潜藏,在关玲珑回来时,毁证灭迹,一把火烧了行凶之地,抛出了夏家独有的箭标,最后特意留下断后,欲杀关玲珑,反被皇甫衍一剑封喉。
马文石所作所为,似乎一直争对的,都是关玲珑。只是,南宫颢与关玲珑虽有瓜葛,结怨颇深,但也不至于,费那么大心计去杀一个无关紧要之人,甚至还嫁祸给夏家。既然要嫁祸,最后又为何要去杀关玲珑?
思绪麻乱,这让他着实想不通。
南宫颢这么做,是为什么?
“司徒璋何时回来?”
听得南宫祤的问话,花忍理了理蛛丝马迹,原本司徒璋同茱萸私自前往晋国,爷是挺气的,可茱萸一直护着他,说是自己以死相逼要他陪同,爷只好作罢。而公玉鄂拖被杀当晚,司徒璋与茱萸同在山庄,司徒璋一直说山庄并无异常,茱萸也是这般回答,爷当时信了,没有生疑,后来司徒璋因公务自请回朝,爷也应允了。
但没想到,在后续的追查中,有夏家暗卫发现说,司徒璋与那位假何元,也就是马文石有过一次交手,似乎有所争执。
因司徒璋回了朝,这条线索便断了。
花忍心中掐算了一下日子,爷前几日刚回朝的时候,第一时间便要召见司徒璋,但司徒璋却奉司徒夫人之命,去了一趟郁安陈家,至今未归,不得已,爷只好下急召让他归朝。
召令一去一回,也有好几天,花忍道:“应该快了,最迟后日。”
花忍看着自家爷,不觉深锁眉头,心内叹气再叹气,刚离开汝陵候府的时候,爷气上了头,冷言冷语的,说以后她的事不必再提,这让花忍惊了惊。
可没想到,翻脸翻的快。
许是自家爷在路上忽然想明白了什么,一入关,爷便随手画了几张画像,一路吩咐边关将卫,必须严查此人踪迹……
说好的不提呢?
“还有一个消息。”花忍不得不再提:“关姑娘已入郸阳。”
南宫祤紧紧的捏着手中画像。
她终究还是来了。
此次再入夏朝,她会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她那所谓的师父?
还是……
“不过,她入郸阳不到一日,便将尾随的夏家人重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踪迹。”花忍一口气说完,很显然,她这是要明目张胆的跟夏家作对。
南宫祤却是微疑:“重伤?”
凭她那点功夫如何能重伤夏家暗卫,除非有人相助,他一想到那白衣女子,就有点头疼,杀又杀不了,防又防不住。
花忍瞧着自家爷的眼神,突然的沉厉肃然,不是什么好兆头,想来跟自己想的一样,也许是那白衣女子所为,花忍道:“关姑娘既已入郸阳,哪怕掘地三尺,我们必然能找到她。”
南宫祤回身就座,一言不发,过了许久,他忽然道:“你吩咐下去,将夏家眼线都撤回罢,不必再追踪她了。”
花忍皱了眉头,不明白,明明费那么大心思从边关一律严查,就是要知道她是否入关,如今她人到了夏朝王都,虽说已消失无影,若全城盘查,必能查到些蛛丝马迹,可爷反而说不追了?
怎的,关姑娘伤了夏家人,爷这会儿又开始气上头了?
尽管想不通,花忍也无法反驳:“我这就去办。”
夜色。
唐问雁随风轻盈,立在断府屋顶,望着眼前院子里的一切。
断府,断一鸿的府邸。
那院子里,有一个男子身着单衣,在挑剑走招,剑花很轻,男子似乎有什么不对劲,使不出太大的力道,捥了几个剑花,终究作罢。
刚一收剑,便有一小孩儿上前去抱住他:“爹爹,娘亲说你伤还未好透,不能再这么拼命练下去了。”
男子抬头往廊下看去,一位面容秀丽的少妇温婉一笑,朝他点头示意:“方才弃将军入府,妾招待了片刻,房中已备好沐浴熏香,将军快去洗涑一番,换身衣裳见客。”
男子点头:“好。”
唐问雁看着那底下的三人。
真是好一派琴瑟和谐,天伦之乐。
她动了动手中长剑,正欲展身而下,却不料后头忽然传来道声音:“断府有客,姑娘挑一个别的日子。”
唐问雁回首,警惕的看着后面的人。
是个女子,身着白衣,白衣女子背上背着一把剑,却用白布裹着,似是爱惜剑身,又像是不能轻易示人,让人瞧不出那是什么剑。不过,单听这人沉允均匀的气息,离她如此之近,她都未曾察觉不出,便知此人内力不凡。
而这白衣女子知道她要做什么。
唐问雁冷凝一声:“你想阻我?”
白衣女子重复了一遍:“断府有客,姑娘另选他日。”
唐问雁在代渠也是叱咤一方的人物,何曾这样被人当面威胁挑衅过,断府有客与她又有何关系,凭何就要她另挑日子?唐问雁望着气定闲神的白衣女子:“若我偏要今日呢?”
白衣女子眉眼间隐隐透出一股冷意。
断府内堂。
弃瑕前几日才随自己二哥回郸阳,这几天公务堆积成山,忙得喘不过气,今夜好不容易得了空,母亲大人便让他来瞧瞧断一鸿,他很是不明白,断一鸿有什么好瞧的,这不活的好好的吗?
“差点一剑穿心,你也是命大。”弃瑕啧啧称奇,自从在花忍那儿听及那唐问雁的事,弃瑕看断一鸿的眼神就有点奇怪,堂堂女魔头唐问雁,到底是看上了断一鸿哪一点?
甚至不惜如此疯魔。
明明在他看来,断一鸿迂腐木讷又呆,一点都比不上自己,但二哥倒是经常夸断一鸿沉稳,做事细心,不像他粗粗心心的。
那唐问雁也是心够狠,情爱不成,反倒成仇,她到底是怎么下得了手的?
那一剑,是真的想要断一鸿的命。
弃瑕又想起花忍说过的一个比喻,白衣女子比起唐问雁,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若入江湖,何止是女魔头。弃瑕心下一叹气,拿出藏好的几瓶酒,说道:“反正今日无事,咱俩喝几杯,你能喝酒吧?嫂夫人应该不介意吧?”
“无妨。”断一鸿沉沉一声。
弃瑕倒了杯酒:“花忍那么嘴碎,一定跟你说过我的事。”
断一鸿想了想,是说弃瑕痴缠一女子,表白心意不成,还依然继续纠缠的事儿?断一鸿点头:“听过一点,没想到,咱们风度翩翩的弃将军,也终究难过美人关。”
断一鸿记得,花忍时常提起,说弃瑕打架第一,念书倒数第一,性子直来直去的,后来一直跟在夏王身后为伍,倒收敛一点了。众所皆知,夏王身边莺莺燕燕极少,导致弃瑕也染上了不近女子的毛病,后来弃夫人为了弃家子嗣着想,不得已常逼弃瑕和各种表姐表妹见面,岂知,弃瑕更是避女子如猛虎。
能让弃瑕挂念的女子,断一鸿倒是很好奇得嘲。
弃瑕道:“你可别嘲笑我,你的事我也全知道,我还挺想讨教讨教,那美人关,你是怎么过去的?”
断一鸿闷了一口酒:“陈年往事,早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不记得你胸口能被戳这么大一个窟窿?我就不明白,那唐问雁武功再厉害,可你也不赖,怎么可能不偏不倚,正中她这一剑,连避都不避。”弃瑕喝了口酒,把酒一摆:“我看,压根是没过去。”
断一鸿瞥了眼胸口,那一剑极险,伤口养了两月,才渐渐好转,如今一想,还是有些隐隐作痛,断一鸿又抬眸含笑,撤引话题:“还是说说你的白姑娘,她那美人关,你想不想过?”
“不想。”
断一鸿眸色一奇:“为何?难道你不想与她结为夫妻,百年好合,绵延子嗣?”
“等等。”弃瑕听到子嗣两字,忽的抬手阻止,压着酒杯,冷不丁的眯眸望着断一鸿:“你是不是我娘派来的说客?一句两句不离子嗣,好像我断了香火就是罪魁祸首似的,想当年,老太太逼我爹的时候,我爹也是豪迈的说过,便是我娘这辈子无所出,他绝不休妻,绝不另娶。凭何到了我这儿,我娘就忘了当初呢?”
断一鸿很同情的看了眼弃瑕,内心却窃窃私语,所以最后,你祖母才活活被气病了呀,甚至与你父亲闹得满城皆知,这不孝之罪就扣你父亲头上了,若不是后来弃夫人终于有了你,而你这么争气的在朝堂上跟对了队伍,这弃家一族,能像如今这般鼎盛?弃家旁族会对弃夫人谄媚客气?
往大方面来想,他不觉得弃夫人此举有何不对。
断一鸿道:“弃夫人也是深谋远虑,人活于世,不可只自私为己,家火相传,封妻荫子,才是世家大族名存的根本。”
弃瑕却不管这些,听腻了更是烦,所以说断一鸿极是迂腐:“你不是不知道,弃家并非世家大族出身,弃家的地位,是我爹用命拼出来的,同他有没有子嗣没有半分关系,便是我有了儿子,他若不成器,照样不会被重用,弃家一样得完。老太太眼红,想要这样世家大族的名号,让她其他的孙子自己挣去,非得天天逼我娘,还扯上我。”
断一鸿对弃家的事,多少明白一些,老太太是弃瑕祖母,弃瑕父亲身死后,夏晟王念旧,封了弃瑕祖母和母亲做诰命夫人,也没亏待弃瑕,他从小还被破格录取,可去京府书院念书,因一次偶然,遇到了在京府书院听课的太子和夏大公子,从此,命运便与这些人串在一起,形影不离。
不过正因如此,弃瑕忽被夏晟王所不喜,因一次打架事件,赶出了书院,从此弃瑕便没好好念过书,考取功名不可能,却在武名谋了一番出路。夏晟王也说这小子有他父亲几分风范,但终归他与太子走的太近,夏晟王对他的好感度又降了降。
弃家旁支一直不得势,便觉得是弃瑕忤逆夏晟王又被赶出书院使弃家丢尽了脸面,因此埋怨弃瑕母子,多次明里暗里为难他们孤儿寡母,老太太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朝堂变化莫测,太子与端王之争如火如荼,还劝弃瑕母亲莫要站错队伍。
而后,太子成王,弃瑕得势后,老太太和弃家旁支却一改往日态度,纷纷把弃瑕当做全族希望。
“话虽如此,可毕竟弃家一族在朝堂上,如今独你支撑,弃家旁支又无可重用的人,你母亲也是想,念着你与王上情分颇深,若你有了子嗣,也能继续在这朝堂立稳脚跟,这弃家一族才能得以庇护……”
弃瑕打断道:“断一鸿,你今天够婆婆妈妈,我和我娘落魄的时候,他们给过庇护么?凭什么要我的子嗣去庇护他们的子嗣?我娘背着我给他们的庇护已经够多了,人心不足,得寸进尺。”
“这世家大族的名头,几世积累,岂是这么容易挤进去的。二哥这么重用我,因为我做的事他是认同的,我这么听二哥的话,是因为他能让我做我想做的事,封妻荫子,不是我想要的。”
断一鸿也知弃瑕所说并非无道理,这毕竟也是弃家的事,若非弃夫人相求,他也懒得提,弃瑕这人,除了王上,没人能治得了,断一鸿叹了口气。
岂知,这口气刚叹完,便忽的听到瓦片掉落的声响,而且越来越猛。
两人相视一眼,弃瑕快速了拿起搁置的剑,快速急步而出,于是,出来的两人,看到了极为瞠目结舌的一幕。
屋顶上,一青一白两个女子,剑气横飞。
拆的屋顶七零八落,瓦片碎裂。
断一鸿微微拧了眉目,看着那青衣女子,一时间怔了怔。
弃瑕的表情却是又喜又忧又疑,喜的是果然如花忍所说,龙姑娘一直跟着自己,甚至真的蹲屋顶,忧的是,他也知道,她只是为他手中的烈火剑而来,疑惑的是,那青衣女子是谁,她两人为何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