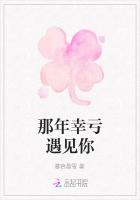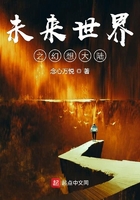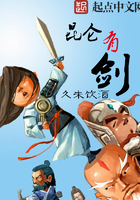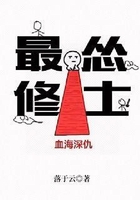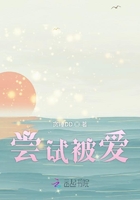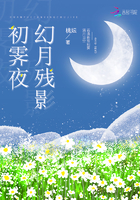■文化传播及其对替代性发展模式的追求:历史线索
倘若新闻客观性是新闻学与新闻实践中的“不死之神”(哈克特,赵月枝,2005),“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则是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当然,这两者一个是正面的宣称,另外一个是负面的批判。正如正面的“客观性”及其相关概念“准确”、“公正”、“平衡”与其对立面“偏见”、“失衡”所组成的规范性矛盾体一样,负面的“文化帝国主义”及其相关概念“依附”、“同质化”、“不平等”、“不平衡”与其对立面“文化多样性”、“平衡”、“独立”、“自主”、“多元化”、“平等”等也组成了规范性的矛盾体。而且,客观性作为一个“知识/权力”的话语集合体有其不同的话语主体、历史演变复杂性以及制度沿革背景,与此类似,“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国际传播领域内“知识/权力”的话语集合体,也有其不同的话语主体、特定的历史演变以及制度变迁背景(Fejes,1981;Tomlison,1991;D.Schiller,1996;Roach,1997)。
割断与修正历史是意识形态运作的重要方式,这在学术和政策层面上都不鲜见。实际上,倘若我们不把19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政策上升史当做某种“全球化新纪元”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尽管诸如“文化全球化”、“混杂性”、“流动”、“创意”等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词汇层出不穷,但目前国际传播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围绕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主题而展开,包括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阐释、修正、批判、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等;而上面提及的联合国两大机构在2005年国际文化传播政策领域内的关注问题与政策诉求,与被全球化话语所边缘化的1970年代“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所关注的问题与政策诉求之间在政策层面上有着更为明显的前后相承的关系。当年有关国际传播秩序民主化的呼吁,与如今WSIS中有关互联网管理民主化的诉求遥相呼应;当年有关国际信息流动不平等的旧问题成为如今WSIS上所提出的“数字鸿沟”新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发表的《麦克布莱德报告》标题所表达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愿望也与如今这个组织的“文化多样性”诉求相辅相成(MacBride Report,1980);而如今被视为对全球化浪潮的批判或逆向行动,亦是过往抵制国际资本主义运动在当前发展的新阶段。正如马特拉(2005:11)所言:“实际上,文化多样性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今天我们却把它当做一个新生事物。对它的历史的遗忘正是‘全球化’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然而,‘全球化’现象的起源却被我们所忽视”。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时过境迁”的重要性,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与话语框架背景和维度的变化。梳理这一变化也许能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一个有益的世界历史背景。
首先,从关注点的角度来看,政治性与文化性突出的大众传媒问题,尤其是国际新闻流动与电视节目流动中的不平衡问题是1970年代“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讨论的核心。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大众传媒宣言》(Mass Media Declaration),强调了大众传媒问题。在随后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中,技术、内容、政策、新闻与文化身份认同等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作为整体性的讨论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整个讨论的中心,而讨论的政治性色彩十分浓厚,因为它意在针对国际传播资源的不平衡分配与不平等权力关系发起挑战,并对跨国公司的商业主义逻辑提出尖锐批评。到了新世纪初叶,大众传媒问题在“信息”与“文化”的机构性和概念性分野中被边缘化,甚至消失了。一方面,主要关注技术问题的国际电信联盟成为世界信息社会峰会的主办者,去政治化了的“信息”范式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广与普及问题成了主流话语的中心。如我在前一章分析2003年WSIS 第一阶段的成果时指出,尽管有“以人为本”的承诺,官方文件的主旋律仍旧体现了技术决定论的思路,更遑论去挑战信息资本主义的统治性逻辑。同时,被美国成功“去政治化了”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公约》的倡导者,与“信息”一样,“文化”概念也被去政治化,在强调不同文化间平等地位的同时,却遮蔽了文化背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倘若“多种声音”理应包括政治和文化声音的话——尤其使人联想起新闻传播中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声音,那么,“文化多样性”的概念却很难使人联想起新闻传播及其所表现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与价值取向,而更多地将其与博物馆文化和被本质化了的少数民族和原生态文化等相提并论。总之,“信息”与“文化”概念几乎消解了“新闻”与“政治”内涵。
其次,以政策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文化帝国主义”讨论中的政策主体与“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第三世界的主权国家,它们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阵营之间,以及由此形成的“不结盟运动”队伍之中。对刚刚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各国人民通过抗争夺取的国家主权是他们在国际上争取文化独立的主要武器。新世纪初叶,主权国家已不再是国际文化传播政策领域内的唯一主体,资本与公民社会力量的角色开始出现。虽然《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公约》的缔约主体是各个主权国家,而且《公约》也旨在维护国家制定并实施有关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政策的主权,以期有效制约跨国传媒企业的商业化活动,以及传播文化中服务与资本利益的贸易自由主义,但是《公约》本身却不得不重申民族国家在文化传播领域内所应拥有的主权,同时支持者将《公约》的出台亦视为主权概念的一次胜利,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主权概念面临的挑战。此外,《公约》把“公民社会的参与”作为重要一条加以规定,并认为缔约方在文化保护中有义务“加强与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及其内部的伙伴关系”。新的超越主权国家作为唯一主体的“多利益主体主义”(multi-stakeholderism)原则在WSIS过程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除了主权国家之外,资本和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成了参与WSIS过程的主体。当然,各方的力量相当不平衡,而对于那些资本和公民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甚至有不同理解和社会建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体认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如我在本书第8章和第9章已论及,公民社会概念本身就极具争议性,而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中与国家、资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同时,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演变也加剧了这一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复杂性(Sparks,2005;Aginam,2005)。公民社会组织第一次与国家、资本携手,建立“伙伴”关系,在国际会议中“登堂入室”,即便如此,这股力量的内部构成却有诸多局限,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代表性,毕竟他们大都来自发达国家,或得到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相关资助。这必定影响他们的政策关注点,导致他们对人权的定义过于狭窄,并无法在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上——即缩小全球信息鸿沟问题和建立更合理的知识产权——更有所作为(Chakrarvatty,2006)。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公民社会力量明显被边缘化,而与国家和资本力量在价值观层面的实质性分歧正是公民社会决定单独发表宣言的真正原因。2005年公民社会宣言的标题《本来应该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无疑传神地表达了这种失望情绪。相比之下,跨国公司的力量更为明显,例如,2003年WSIS日内瓦阶段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已然认识到开放代码软件(open source software)对发展的重要性,针对这一主流认识,微软公司成为2005年WSIS突尼斯阶段会议的赞助商,不但借此一举取得了会议主题发言的资格,而且公司的参加者也从2003年的6人增加到2005年的70人,他们在WSIS官方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扮演了超常重要的角色(Ermert,2005)。这在197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历史上“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话语与1970年代争取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旨在追求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现代化发展模式。当时,国际政治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实质性的对抗,为许多取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想象和现实的政治空间。这里,需要从人类学意义上来理解“文化”。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体系,被视为争取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发展模式和构建新型社会结构的主要场域。在这个激进话语里,“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博物馆里的陈列和少数民族或原生态文化,更不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各国的文化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说,该话语中的“民族文化”,既不在空间上把地理意义的区分本质化(东方对西方,中国产的商业电视剧对韩剧),也不是去历史化和去社会化意义上的“文明”,更不在时间上面对过去,进而把传统文化中压制性的因素理想化,当成国粹来保护(Tomlison,1991),而是强调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相互建构,以及生活方式选择的动态意义与未来意义。因此,“对激进主义者而言,民族文化是未来的东西”(D.Schiller,1996:96),亦即,它是这样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超越了殖民主义和传统社会关系,隐含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
■“民族文化”与文化多样性
具体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话语里的“民族文化”是区别于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阶级文化的正在或有可能出现的新的“人民文化”。正如“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批评者赫伯特·席勒所言,该“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保护是在“与外国或本国统治者的日常冲突和斗争过程中苦心孤诣的结果”(H.Schiller,1976:85)。阿尔及利亚著名反殖民和民族解放文化先驱弗兰兹·范农(Frantz Fanon,1961;1968)更明确地把锻造这样的新“民族文化”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紧密相连,认为这种“民族文化”是殖民地人民反殖民斗争并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的结果。因此,围绕文化而展开的斗争,离不开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为争取自由斗争的最中心地带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转引自D.Schiller,1996:99)。很明显,对范农这样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激进批判者而言,后殖民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培育不仅与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文化息息相关,也与一系列反抗行动密切相关,它们旨在抵制国内压迫性“反动传统主义”的复活,并阻止新的各国资产阶级作为跨国资本的附庸与代理者成为统治性的特权阶级(D.Schiller,1996:100—101)。正是在此意义上,丹·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可以视为一种反抗国内外跨国阶级统治的理论(1996:101)。第三世界的政治家有可能一边在国际讲坛上大谈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一边却在国内建立和维护阶级统治,并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而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也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反帝反资社会运动内部的复杂权力关系缺乏足够认识(Tomlinson,1991),即便如此,简单地把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等同于对第三世界专制政权的支持是毫无道理并缺乏历史根据的,相反,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恰恰包含着对国内国际压制性社会关系的共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追求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统治关系的新型的本国文化,也是英国激进文化批判学者的目标。信仰社会主义的英国文化研究先驱汤姆森(E.P.Thompson)、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尔(Stuart Hall)都密切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以及他们的共同经历,甚至通过成人教育等途径参与到工人阶级文化的培育行动中去。譬如,对于威廉斯(1961)而言,新的“共同文化”以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包括产权关系)为基础,以文化革命的“漫长革命”为目标,后者与经济领域的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密切相关,并相互延续。威廉斯意义上的文化是普通的,是“整个生活方式”,而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社会生活中最关键的分野并不存在于语言、衣着和休闲之中,因为它们趋向一致,而是存在于“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不同观点”之中。威廉斯认为,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反,工人阶级的“主要文化贡献”在于“为实现普遍社会公益而形成的集体的民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