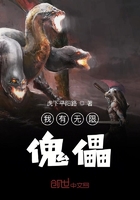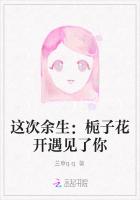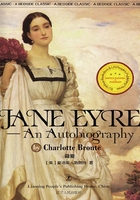第三节 研究夏商西周社会的基本资料和基本理论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人们对于夏商西周社会的认识都只局限于若干文献资料,直到近代以来,随着甲骨卜辞的发现和彝铭资料研究的深入,以及田野考古事业的发展,相关研究的资料才比之于过去而极大地丰富起来。
一、甲骨卜辞
殷墟甲骨的发现可以追溯到清代光绪初年。殷墟一带的农民偶有翻地时而发现甲骨者,但却没有发现甲骨的真正价值,而是视其为废物而用以填塞枯井,也有人将其磨成粉末作刀伤药,亦有作为“龙骨”、“龟版”而售于药材商店者。1898年冬季,山东潍县姓范的古董商贩在豫北一带搜寻到有字的甲骨。【8】并于次年运至北京,售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大得赏识,甲骨文字始为世人注目。1903年刘鹗在罗振玉的支持下,选择所藏一千几十片甲骨拓片,石印成第一部甲骨著录书——《铁云藏龟》。然而,此时的甲骨收藏者尚不知确切的甲骨出土地点。后来,罗振玉经过查访始知安阳小屯一带是甲骨埋藏地。1909年至1911年间,罗振玉三次派人到安阳搜求甲骨和古器物,并于1913年用珂罗版精拓影印了《殷虚书契》,为甲骨文的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1929年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这些以科学方法所进行的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殷墟考古资料,而且得到了不少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甲骨文。这些文字材料后来汇集为《殷虚文字甲编》、《殷虚文字乙编》两书。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在安阳小屯继续发现有甲骨文以外,而且在附近的侯家庄、后冈、大司空村等地也有发现。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南地发现甲骨七千多片,汇集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这本书除在上册刊布甲骨拓本以外,还在下册系统地刊布了释文、索引、摹本和钻凿形态,颇便于使用。据统计,自19世纪末八十多年以来,先后出土的甲骨约在十五万片以上,著录甲骨的书刊有一百八十多种。【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甲骨著录之大成,编辑了具有重学术和使用价值的《甲骨文合集》。此书和《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10】是研究殷商史最重要的甲骨著录专著。
关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用甲骨文探索殷商历史,是从罗振玉、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开始的。早在1914年罗振玉就出版了《殷虚书契考释》一书,王国维则于1917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的先公先王考》和《续考》,通过对于甲骨文所载的商王世系的研究,证明《世本》、《史记》等的相关记载的可靠性。1933年董作宾先生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1】,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并将甲骨文划分为五个时期,“从此凿破鸿蒙。有可能探索甲骨文所记载的历史、礼制、祭祀、文例发展变化。把晚商各期的历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12】。对于甲骨文字考释进行艰苦的开创性研究的,除了郭沫若、杨树达、朱芳圃、孙海波、唐兰等专家以外,用力最多的是于省吾先生。他在1940年至1944年间,先后出版了《双剑誃殷契骈枝》以及《续编》和《三编》,并于1979年经过增删修改,汇集成《甲骨文字释林》一书。运用卜辞材料对于甲骨学和殷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的,首推郭沫若、胡厚宣两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字研究》是郭沫若先生研究殷商史的代表作,而胡厚宣先生研究殷商史的许多著名论文则汇集于《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甲骨学和殷商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有杰出贡献的学者,首推陈梦家和李学勤两先生。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在甲骨断代方面提出和研究了“自组”、“子组”、“午组”卜辞的问题,并且总结了1956年以前的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的成果。李学勤先生的《殷代地理简论》以甲骨文地名的内在联系为线索,系统地考订了殷王朝都邑、田猎区、征人方路线、方国地理等问题,是研究殷代历史地理的专著。当前,研究甲骨卜辞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是孙海波的《甲骨文编》、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和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
除了殷墟甲骨卜辞以外,周原甲骨也是一批极重要的材料。这批材料是1977年春在陕西省周原地区的凤雏村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共有甲骨一万七千多片。其中有字卜甲二百九十多片。周原甲骨发现以前,虽然在山西洪赵【13】、陕西西安【14】、北京昌平【15】等处发现过西周时期的带字甲骨,但数量很少,还不足以用来探索西周的重要史实。而周原甲骨则与此不同,它不仅数量多,而且有不少重要内容。记载了商周关系、占卜祭祀、农作田猎、地理官制、干支月相等大事,对于西周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周原甲骨曾以摹本形式刊布【16】。王宇信先生的《西周甲骨探论》【17】一书不仅将包括周原甲骨在内的西周甲骨摹本聚为一编,而且对西周甲骨的特征、断代、科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一部关于西周甲骨的现阶段研究的总结性专著。
二、彝器铭文
殷代前期的铜器多无铭文,即使有,也仅以几字为限。到殷末时彝铭最长者也不过四五十字。因此,运用地下发掘的资料研讨殷商史须以甲骨卜辞为主,彝铭为辅。但是,周代的情况则大有变异。周代甲骨虽有周原的大批甲骨出土,亦记载了不少重要内容。但其数量和刻辞字数并不能和殷墟卜辞相侔,也无法和周代彝铭材料相比拟。因此运用地下发掘的资料研究周代历史时,则以彝铭为主、甲骨卜辞为辅。
周代铜器有铭文者达三千多件,其中不少铭文内容丰富,堪称鸿篇巨制,足以和文献中的周初诸诰相媲美。西周彝铭,《毛公鼎》497字,《齐侯镈》492字,《留鼎》403字,《散氏盘》357字,《大盂鼎》291字,《克鼎》289字,《史墙盘》284字,《卫鼎》207字,其他如《令方彝》、《师虎簋》、《虢季子白盘》、《宗周钟》等均在百字以上。周代的许多军国大事,如分封授土、赏赐奴仆、征伐献馘、诉讼刑罚、职官任命、地域疆界等,都被勒之彝器,以示永垂不朽之义。正由于铜器铭文是周代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所以它是我们今天研讨周代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利用甲骨卜辞研讨历史是20世纪初年以来的事情,而利用铜器铭文研讨历史则从很早的古代就开始了。《左传》昭公三年载《谗鼎》铭文“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昭公七年载《正考父鼎》铭文“(?)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可见战国时人就曾以彝铭作为修史和教育后人的资料。春秋战国时人视古鼎为宝物,楚庄王曾向王孙满“问鼎之大小、轻重”(《左传》宣公三年),齐侯曾经为索取《岑鼎》而伐鲁(《吕氏春秋·审己》)。秦汉时代寻找周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秦始皇曾经“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史记·秦始皇本纪》)。汉武帝时得宝鼎于汾阴,将鼎“见于祖祢,藏于帝廷”【18】。汉代经学家曾以古代彝铭作为立论根据,《礼记·大学》就曾引用《汤盘》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说明问题。【19】《礼记·祭统》载有《孔悝鼎》的全部铭文,并总结说:“此卫孔悝之鼎铭也。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彝铭为文人所重,于此可以窥见。汉时颇有能释读彝铭者。如汉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鼎献于朝廷。以“好古文字”著称的京兆尹张敞就正确地考释了此鼎铭文,指出“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藏)之于宫庙也”(《汉书·郊祀志》)。南北朝时期,人们对于彝器的性质已经有了许多认识,刘杳曾经向著名史学家沈约说:“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南史·刘杳传》)宋朝时,人们对于彝器尤为重视。“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石林避暑录话》三:十,涵芬楼本)。在广泛搜求的基础上,宋代开始出现彝器著录专书,如北宋时期吕大临编《考古图》,宋徽宗敕撰《博古图录》,南宋时期薛尚功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都汇集了丰富的图像和铭文资料。清代对于彝器的著录和考释有了很大进展。关于彝器图像的有《西清古鉴》、《长安获古编》等,著录铭文的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筠清馆金文》、《攈古录金文》、《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多种。
近代以来对于彝器铭文的著录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在彝铭著录方面,以资料丰富、鉴别仔细、印刷精美著称的,是罗振玉于1937年印行的《三代吉金文存》。全书收商周青铜器铭文四千八百多器,传世拓本大致完备,并且拓本多精品,所以此书一直为学者所重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未能将器形、出土著录、收藏、考释等情况编入,而仅有目录和拓本,所以使用起来颇不方便。另外,此书混入了个别伪器,有些器铭有重出或遗漏若干部分的现象,这些都是在使用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于青铜器研究的划时代巨著是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影印初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原收录251器,1958年增订本增至323器。所收西周时期的器铭以自武成至厉幽的列王为次,东周时器则以吴、越、徐、楚等32国为次。全书以铭文的内在根据为主,参照器物纹饰、文字体例、文辞格调等,对青铜器进行断代和区分国别,并由此而论定我国青铜时代的分期,将其划分为滥觞期、鼎盛期、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等五大时期。全书每一器铭都有释文和考证。此书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20】、《金文丛考》一起,是郭沫若先生关于金文研究的主要成果。对于彝器铭文和形制、纹饰等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还有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21】,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22】,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23】,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24】等。研究器铭的主要工具书有容庚《金文编》【25】和周法高《金文诂林》【26】。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陆续有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出土。如《利簋》、《墙盘》、《秦公钟》、《何尊》、《多友鼎》等。不少专家对这些器铭进行了考释,推进了金文和西周史的研究,汇集成书者主要有李学勤先生的《新出青铜器研究》【27】和裘锡圭先生的《古文字论集》【28】。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编《殷周金文集成》自1984年出版第一册以来,陆续分册出版,这部书集铜器铭文著录之大成,去伪存真,删去重复,注明器铭来源和收藏、断代等情况,并有释文和索引。它的出版为铜器铭文资料的运用提供了很大方便。
三、文献资料
研究先秦史的文献资料,由于时代久远、辗转传抄等原因,所以问题比较多,一般需要进行辨伪和考证,以确定其可靠程度,然后再选择使用。这些文献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尚书》。《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词和追述古代史事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时曾派遣晁错随伏生学习《尚书》。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相传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到不少古书,其中有用汉以前的古文抄写的《尚书》,故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古文尚书》已佚,现仅存篇目,在《汉书·律历志》中有其少量佚文。这部《古文尚书》是否可信,在历代经学家中多有争论。今所见的《古文尚书》为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共25篇。南宋学者吴棫、朱熹等始疑其伪。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尚书谱》,定其为伪作。此后,清代学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罗列一百多条证据,逐一揭发《古文尚书》伪作的来源,后来惠栋作《古文尚书考》加以补充。至此,梅赜所献25篇为伪作,终成定论。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将今文、古文杂合为一编,所以使用时应慎重分辨。《今文尚书》的各篇写定的时代有早晚之别。其中的《虞书》、《夏书》和《商书》的一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人根据传说资料整理而成的。《商书》里的《盘庚》篇当写成于殷周之际,是很有价值的文献。《周书》部分,除《洪范》、《文侯之命》、《秦誓》、《吕刑》等篇写成的时代较晚以外,大部分是西周时期的作品,是研究西周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另外,先秦和秦汉时代的古书里,如《孟子》、《墨子》、《左传》、《吕氏春秋》、《礼记》等,引有《尚书》佚文一百六十多条。这些佚文和《今文尚书》一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总而言之,《尚书》对于商周史的研究,最有参考价值的是《商书》和《周书》,特别是《盘庚》与周初的一系列的诰辞,更是了解商周史事的极为难得的宝贵记载。对于上古历史的研究而言,《尚书》的《虞书》和《夏书》保存了不少古代传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时代悬隔,《尚书》的不少篇章佶屈聱牙,素以难读著称。清代学者孙星衍博采当时经学和小学的研究成果,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是较完备的注释本。
《周易》。《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五千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如王亥“丧羊于易”(《大壮》)、“高宗伐鬼方”(《既济》)、“帝乙归妹以祉”(《泰》)等。《周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易经》的解释,基本上是东周时代哲学思想的反映。《十三经注疏》所载《周易正义》是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合编本。
《诗经》。《诗经》原只称《诗》,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始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诗经》,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经》又称《毛诗》。东汉末,郑玄为《诗经》作《笺》。唐初,孔颖达作《正义》,凡四十卷,共三百零五篇,今《十三经注疏》所载《诗经》即此。《诗经》诸篇时代早晚不一,从周初至春秋中期,约五百余年。《诗经》广泛地反映了先秦时代的社会风貌。《大雅》和《豳风》中的多数篇章产生于西周,叙述了周族起源和周王朝建立及兴盛的历史,反映了周代农业、征伐等社会生活情况。《小雅》是两周之际和东周时的诗篇,主要反映了当时政治废弛、贵族昏聩、民众疾苦的情况。《周颂》和《鲁颂》是贵族祭祀时的庙堂乐歌,《商颂》是春秋时代宋国宗庙祭祀乐歌。《国风》部分主要反映了东周时期各地的社会生活、农业生产、婚姻恋爱和风俗民情。总之,《诗经》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研究先秦史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左传》。相传此书是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所撰写的,但根据内容和年代等情况分析,一般认为它是由战国时期的学者整理加工而编定的。《左传》以《春秋经》的编年为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的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多出十七年。《左传》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它详细、真实地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除此以外,《左传》还对春秋以前的古史,特别是西周史,多有记载。如记羿、寒浞代夏和少康中兴事(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初封邦建国事(定公四年)等均为其他史籍所罕见。现在通行的《左传》版本是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的合编本,为《十三经注疏》所收纳。
《逸周书》。《逸周书》原名《周书》。《汉书·艺文志》载“《周书》七十一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因为它的内容不见于《尚书》的《周书》部分,所以汉代许慎《说文》、晋郭璞《尔雅注》等称其为《逸周书》。今本《逸周书》应当是汉代刘向根据朝廷所藏材料整齐编定的。从文体和内容上看,大部分是战国时人的伪作,也有少数,如《商誓》、《度邑》等是周代作品。或称《逸周书》为《汲冢周书》,说此书得于晋初汲郡魏王冢。但汉魏时人所著书多称引此书,因此它早在汉代即行于世,把它列为汲冢所出古书之一,实属错误。《逸周书》载有许多关于周代史实的资料,如《度邑》、《作雒》记周公营建雒邑事,《克殷》、《世俘》记武王伐纣事等,不少资料为司马迁撰写《周本记》所取材。清代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为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较详备的著作。
《国语》。《国语》共二十一卷,分记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上起周穆王伐犬戎,下至智伯被灭,历时五百多年,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国语》中记晋国事尤多,可见其编纂者搜集了不少晋国的档案材料。因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话,所以一般认为它曾为左丘明所传诵。这部书的《周语》、《郑语》等部分记述了西周中期以后的某些史迹,向为人们所重视。现在流传的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韦昭的注本。
《竹书纪年》(古、今本,以下简称《纪年》)。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中有《纪年》十三篇,述夏至战国时史事,被称为《纪年》或《汲冢纪年》。此书所记史事,不少与正统的文献记载违异,但却与甲骨卜辞或彝铭相合。它所记载的一些史事很有参考价值,如关于商王中宗、共和行政、穆王西行等,均为研讨古史者重视。此书早已亡佚,只在南北朝至北宋时期的古书里存有佚文。这些佚文历经清代学者汇集,称为《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古本纪年》)。另有《今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今本纪年》),可能是南宋以前的人所辑录的,尽管问题较多,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山海经》自古号称奇书,其撰著者不详。今本《山海经》共18卷,其中包括《山经》5卷和《海经》13卷。从其内容上看,这部书并非由某一个人编纂,也非作于一时。《山海经》所记的内容虽然有许多怪诞不经之处,但却蕴涵着我国上古时代的地理、历史、神话、动物、植物、矿产、医药、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对于研讨夏商西周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山海经》记载了不少“国”名。这些“国”,很可能是原始部落名称的讹传,所以能够从中探寻上古时代部落分布的一些情况。《山海经》在西汉时期存有32篇,刘歆校书时定为18篇。古本《山海经》有图,但在流传中图均佚去,今本仅余文字部分。
《战国策》。相传《战国策》是战国时期所辑录的策士、纵横家的言论总集。起初称之为《国策》、《国事》、《事语》、《短长》、《修书》等。西汉末年,刘向校理诸书,删去重复,按战国时期的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的次序,编订为33篇,始称《战国策》。这部书主要记载了战国时的纵横家游说诸国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所涉及的夏商西周史事,也为专家所重视。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有些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还有的内容与之相似,共一万一千多字,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可与《战国策》对照研读。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文献材料以外,其他如《周礼》、《史记》以及先秦诸子书等,也都有不少相关的材料。
四、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
我国先秦时代在文字记载出现以前时期历史的研究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并辅以民族学的资料。历年来,我国已经发现了元谋猿人、北京猿人、金牛山猿人等多处猿人遗址,是世界上猿人资料最丰富的地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也很丰富,所发现的遗址已有六七千处。关于夏商西周时期历史的研究虽然有了较多的文献资料,但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仍很重要。夏墟的探索已经全面展开,且有不少重要发现。关于商周时代的考古发掘,以安阳殷墟、湖北盘龙城、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陕西周原、北京琉璃河等处的发掘最著名。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发现比之于以前时代的有了更多的数量和更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考古资料,多见于《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杂志。专著主要有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2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30】、胡厚宣《殷墟发掘》【31】、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32】等。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保留一些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残余,这些民族学的资料也可供研究时参考。
五、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1929年,郭沫若先生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巨著时,在《自序》中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他还说自己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郭先生的这番话是七十多年前所写的,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能感到它的魄力和卓识。郭先生的这些话至少在两个方面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其一,研究夏商西周史,应当刻苦努力,认真探索,而不要希冀从马列著作中找出可以代替自己研究的现成答案来。限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熟悉和掌握我国先秦时代的甲骨金文资料以及文献资料。恩格斯研究上古社会历史,阐述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依据的主要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欧洲的一些资料。他的阐述不涉及中国社会的范围,这正是经典作家实事求是学风的一个体现。既然经典作家已经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那么,我们就应当尊重经典作家的意见,不把他们关于古代社会的某些具体结论生搬硬套地应用于夏商西周史的研究,而是学习他们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二,研究夏商西周史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郭先生称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其用意应当就在这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我国的先秦史研究提出具体论断,但却为这个研究指明了方向。郭先生在《自序》中说他的研究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的,在1947年写的《后记》中又明确表示他这种研究古史的“方法是正确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着巨大影响,成为我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这个成功与郭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有直接关系。我们的夏商西周史乃至整个古代史的研究,要想有一个大的发展,不仅有史料方面的问题,而且有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就当前夏商西周史研究情况看,我以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的问题,似应引起重视。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典作家对于历史主义有过许多论述。在历史研究中注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时代性,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论述,应当是历史主义的核心内容。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3】,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上所以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与忽略了“历史范围”的问题是有关系的。例如,商代的人祭人殉问题,不少研究者在揭示其基本情况的时候,多忘不了义愤填膺地谴责一番,以期揭示出一幅奴隶主残暴统治的血淋淋的画图。毫无疑问,研究者的这种主观愿望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我们今天又有谁能赞美杀人祭神和以人殉葬的愚昧而残暴的行径呢?没有。不仅今天没有,就是商代以后的历代王朝也都极少有赞美、支持人祭人殉的呼声。然而在商代人祭人殉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据统计,仅甲骨文所记载的人祭人殉数量就至少有一万四千多人。【34】这种情况的出现,适应了商代神权发展的需要,它不仅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对于原始时代的复仇屠杀和部落战争来说,又有某种历史进步性。商代用于人祭者,大部分是羌俘,往往在俘获之后不久即被杀祭。俘虏并不就是奴隶,如果说殷墟祀坑里的羌俘的累累白骨是奴隶被残杀的证据,那么就逻辑论证而言是有问题的。我们对这样的问题需要的不是廉价的谴责或赞美,而是冷静的、科学的分析。在这个分析里,历史主义观点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人祭人殉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它可能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但也可能是原始愚昧的遗存,而在原始社会里则与阶级斗争没有什么瓜葛。对它的历史主义考察关键在于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马克思曾经指出:“关于俘虏的处理经过了和野蛮期的三个阶段相适应的三个连贯的阶段:野蛮期的第一个时期,俘虏被处以火刑;第二个时期——作为供献神灵的牺牲;第三个时期——转变为奴隶。”【35】马克思的这个分析对我们运用历史主义观点考察人祭人殉问题是很有启发的。再如,关于甲骨占卜的问题,研究者往往只肯定卜辞所记载的文字资料,而对占卜则嗤之以鼻,认为那是纯属愚昧迷信的勾当。其实,商代的占卜的性质是比较复杂的,不可将它和现今的巫婆神汉的骗人勾当混为一谈。商代的占卜除了一定程度的迷信性质以外,还反映了某些原始民主精神和维系诸方国诸部族的象征意义,有些占卜还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如果只简单地斥责其愚昧迷信,那是不会对它有全面认识的。商代占卜盛行,几乎每日必卜,每事必卜,对其原因应当从它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上去探索。占卜迷信,不独商代如此,可以说我国古代历史的每个时期都存在这种情况,但为什么于商代独盛呢?显然,如果不做历史主义的分析,那是很难作出正确解释的。
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要求重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恩格斯曾经批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缺乏对事物认识的历史观点,指出:“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36】当然,我国的夏商西周时代不等于中世纪的欧洲,然而在“历史联系”被忽略这一点上两者却有共通之处。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商代文化除了甲骨文字以外,只不过是如同人祭人殉之类的愚昧和迷信的堆积;而提到周代则往往只把其宗法制和近代以来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之一的族权相联系。对于商周文明的具体情况及其在我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则了解甚少,对于商朝文明在世界上古史的地位的认识则更茫然。尽管曾有学者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讨,但毕竟还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熙熙攘攘的人类社会和色彩斑驳绚丽的自然界一样,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人们的认识当然也在发展之中。我们今天来判断史事的是非曲直,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臧否,探讨历史上思想学派的优劣得失,应当用什么标准呢?当然只能用我们今天的标准,不应当,也不可能用某个历史时期的人们的标准,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标准和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不矛盾。举例来说,如果比较和评价今天的玻璃器皿、不锈钢餐具和商周时代的鼎簋盉爵等青铜器,那么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只能说前者远比后者进步和科学,我们谁也不会把笨重的鼎簋摆到餐桌上,谁也不会举起盉爵来祝福干杯。然而,大家都会承认,在商周时代,鼎簋盉爵等青铜器则是最高级、最进步的器皿。我们今天评价商周青铜器,一定会把它放在商周时代的物质文化发展中去评价,而不会以今天的物质文明发展去对它贬低和蔑视。假若我们由此及彼,从而联系到夏商西周史的研究问题,那么,在探讨方法上的共通之处是不难发现的。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7】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38】我们的先秦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如何理解和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十分丰富。它不仅阐述了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而且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大千世界的阶级斗争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绝不是只呈现一种色彩的单调的图画。长期以来。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总以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其实,社会分为两大敌对的阶级阵营那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事情,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39】。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的阶级对立并不是简单的两个阵营的对峙。列宁曾经指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40】。我国古代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的说法是等级制的很好说明。夏商西周时代社会阶级的等级性质十分复杂。如果硬要作两大阵营的划分,显然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关于商代阶级状况的研究中,“众”的身份问题,聚讼多年,迄无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有理解史料的深度和角度问题,另一方面也有把复杂的阶级状况简单化的问题。
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论断。我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还需要做具体分析。阶级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它的各个具体发展阶段,其阶级斗争的作用是不可一概而论的。在阶级出现以后不久,原始氏族遗存还拥有巨大影响的时期,其阶级斗争的作用和影响就不能和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相比拟。就是到了商周时代,其阶级斗争也还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可以说,商周时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以阶级斗争为轴心而前进的,阶级斗争还算不得贯穿夏商周社会发展过程的一条“红线”。马克思说:“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41】根据这个分析,马克思十分强调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的“根本区别”。列宁也曾指出:“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42】夏商西周时代的社会矛盾、阶级斗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并非仅有奴隶对奴隶主的斗争。这个时代的奴隶斗争的作用尽管未必如同古代罗马那样只是统治阶级政治舞台的消极台柱,未必是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估计到左右历史进程的地步。
在夏商西周史的研究中还会遇到国家的产生和初期国家的作用问题。关于国家的产生,经典作家有许多论述。他们强调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43】在这段话里,恩格斯强调了“日益”的意思,表明了国家的产生应该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人以为夏代以前很久就有阶级,因此也应有了国家。这种说法把国家的产生简单化了。实际上从阶级萌芽到阶级出现,以至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期间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同样,从国家的萌芽到国家的产生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那么国家就不会是和阶级同时产生的。国家的产生应当有一个从量到质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萌芽于原始时代,“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44】。从国家权力的萌芽到国家的形成,应当是在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迈进这一漫长时期逐渐完成的。就我国古史情况看,国家何时产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我以为如果把夏代看做这个从量到质的发展过程,似乎是接近历史实际的。就国家的职能来说,过去的研究中,大多注意到了国家残暴性质的论证,如国家机构中的军队、监狱、刑罚等,都有不少专门的叙述和研究。但是对于当时国家机构“缓和冲突”的职能则很少涉及。国家机构的职能是两方面的,一是镇压,二是调节。就夏商西周时代的情况看,国家机构通过调节各集团、各阶层的利益所起到的缓和冲突的作用,远比后代为甚。这个方面的研究应当受到重视。
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历史主义、阶级观点、国家产生等,在理论方面还应当注意到整体观念的问题。历史的整体观念在我国古代早就有了。在卜辞中,殷的中心区域称为大邑商。其四周地区称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或合称“四土”;也称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或合称为“四方”。周人的概念与殷人大略相同,只是有了东国、南国、北国等称谓,或合称为“四国”,并且把“中国”和“四方”相对应。说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民劳》),又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梓材》)。周人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四方攸同”(《诗经·文王有声》)。春秋时代的人继承了商周以来的天下整体概念。例如,孔子的理论中虽然有诸夏与夷狄之分,但他和弟子们仍然有“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广阔胸怀。鄙视周边各族,并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那是战国中期及其以后的事情,然而亦不乏天下一体的概念。“九州同域,天下一统”仍然是历代王朝所彪炳的目标。我们研究夏商西周史应当有一个全局观点,既要肯定夏商西周是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又要看到那个时代“天下”的概念已经以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达而出现。它的范围要比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大得多,只是限于史料记载的局限,我们对于许多部族、政权、方国等还所知甚少。有的还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让眼界开阔些,努力探索那个时代的诸部族、政权、方国的情况,这对于夏商西周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念的确立是有帮助的。
人们常用冥行擿埴来形容学术研究的艰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这个名句曾激励过不少前辈专家对夏商西周史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夏商西周史研究的真正大踏步前进,那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事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和学习的普照的光,只有它才能为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我们的研究中之所以重视理论问题,其原因正在于此。
注释:
【1】李仰松:《仰韶文化慢轮制陶技术的研究》,载《考古》,1990(12)。
【2】李文杰:《试谈快轮所制陶器的识别》,载《文物》,1988(10)。
【3】关于这段话里面的“大道既隐”一句含义的诠释,请参阅本书第五章第—节。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墨子·非命中》引《尚书·仲虺之告》。伪古文《尚书·仲虺之诰》据此云:“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威,式商受命。”
【6】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405~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关于甲骨文字的最初发现情况,陈梦家先生于1953年春,曾在安阳小屯访问以出售“龙骨”为业的村民李成的后人,得知不少重要材料。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2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9】参见《甲骨文合集》,第1册,胡厚宣序,北京,中华书局,1978。
【10】我们下面引用卜辞材料时分别简称为《合集》、《屯南》和《英藏》。
【11】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北平,1933。
【12】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3】参见《山西省洪赵县坊堆村古遗址墓葬群清理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4)。
【14】参见《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3)。
【15】参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载《考古》,1976(4)。
【16】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
【1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8】 《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注引应劭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谓武帝“元鼎”年号由此而来。王先谦《汉书补注》辨此说非是。因为得鼎为元鼎四年(前113年)事。按,虽然应劭说为附会,但汉武帝十分重视周鼎,仍是事实。
【19】郭沫若先生举商戈铭文为例证明《礼记》所载此铭乃是“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之误读。尽管如此,这个记载也还是说明了商代彝铭为汉人称引的情况。(参见《汤盘孔鼎之扬榷》,见《金文丛考》,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0】上海,大东书局,1931。
【21】见《考古学报》,第9—14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1956。
【22】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23】见《古文字研究》,第2辑。
【2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5】 《金文编》初版于1925年。由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该书第4版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
【2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
【2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8】北京,中华书局,1992。
【2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31】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3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3】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5卷,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4】参见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载《文物》,1974(8)。
【35】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2页。
【38】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2页。
【40】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287页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6卷,405~406页。
【42】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7卷,7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170页。
【44】同上书,第3卷,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