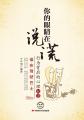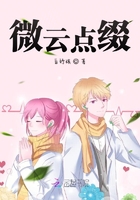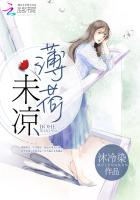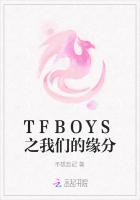第三节 殷商时代氏族封建制的发展
关于夏商周三代制度与文化的承继与发展,孔老夫子曾经有过一段颇为著名的言论。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殷的制度文化是对于夏的制度文化进行“损益”之后形成的。孔子又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所谓的“二代”,即指夏商两个朝代。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夏商西周的社会性质颇有启发。夏商西周的社会制度,总的来说都属于封建制度,但其发展过程中后代对于前代的制度又有所“损益”。我们研究殷商时代氏族封建制的发展,着眼点就在于探讨它是如何对于夏代的氏族封建制进行损益的,看殷商时代在社会制度方面较夏代补充了些什么新的东西,又改变了哪些旧的东西。
一、殷商时代的氏族
殷商时代的社会结构中,氏族的力量比以前有所加强,其影响也更大。甲骨卜辞记载有殷商时代的许多氏族和方国的情况,早就引起了专家们的重视,进行过许多研究。例如丁山先生曾经就甲骨刻辞、卜辞所载诸妇和诸氏的资料进行统计,并且指出:
就现在已经刊布的甲骨文材料看,我们确知商代的氏族至少有二百个以上,待将来海内外所藏的甲骨文全部刊出,再为综合研究,一定还有若干新的氏族发现。这些氏族的事迹,有的常见于卜辞,间有见于经传诸子的传说;并且,他们当时所用的器皿和兵器,自宋以来,出土甚众。我们利用商代铜器的铭文,参验以经传诸子传说,可以说,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17】
丁山先生相当谨慎,他以甲骨卜辞的材料为主进行研究和统计,所以只断定“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其实,就整个殷商时代而言,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即殷商时代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我们说殷商时代的国家组织以氏族为基础,包括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就商王朝而言,氏族为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二是就商王朝以外的诸方国而言,氏族也是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我们先来研究商王朝直接控制下的氏族的情况。
殷商时代的族可以称为氏,史载周初分封诸侯时,曾经分封给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左传》定公四年)。条氏、徐氏、萧氏等氏,自有其“宗氏”和“分族”,可见其氏本身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不会像原始氏族那样只有几百人。商王朝的诸族可以分为“以国为姓”和以职业为姓两类。《史记·殷本纪》谓“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所提到的殷氏、来氏、宋氏等,都是子姓族,被分封以后而以国为姓。前面所提到的“殷民六族”中的索氏,或谓为以制造绳索而著名的氏族,长勺氏、尾勺氏,或谓为以制造酒器而著名的氏族。周初分封的时候,据文献记载,除了分封给鲁公殷民六族以外,还分封给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左传》定公四年)。这七族殷民,陶氏或谓即以制陶著名的氏族,施氏为以制作旌旗著名的氏族,繁氏是以制造马缨而著名的氏族,锜氏是以造釜著称的氏族,樊氏是以建造篱笆著称的氏族,终葵氏是以造锥著称的氏族。这两类氏族在商代社会上的地位可能是有区别的,“以国为姓”的氏族,其社会地位较高;以职业为姓者则是子姓部族中的下层氏族。
对于商王朝的军国大事,子姓的族众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商代前期这种影响更为显著。商汤灭夏是夏商之际最重大的事件,请看《尚书·汤誓》的记载: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篇中所提到的“众庶”应当就是商王朝的子姓族众。商汤在行动之前召集“众庶”计议,“众庶”当即提出质疑,询问为什么“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商汤不得不就此而耐心地进行说明。“众庶”又追问“夏罪,其如台”,让商汤讲清楚夏的罪恶到底如何。当然,商汤作为君主,还是以利诱、威逼两种手段,让“众庶”就范,但是其对于“众庶”意见的重视和向“众庶”所进行的细致解释,都表明当时“众庶”是有很大影响的,令商王不敢小觑。《尚书·汤誓》可以看成当时族众会议的记录,至少是后人依据这样的记录而写成的。商王盘庚迁殷是早商和晚商两个历史时期的分水岭,是对于商族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尚书·盘庚》篇里面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族众的重要影响,据是篇记载,盘庚迁殷时,族众曾经“协比谗言”,质问盘庚“曷震动万民以迁”,于是盘庚不得不召集族众至“王庭”举行会议,细致而认真地进行解释。迁殷以后,“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陈言”,盘庚对于民众的不满情绪继续进行说服。盘庚迁殷时告诫官员们要“念敬我众”。这些都说明了族众是商代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商王对于族众的重视在甲骨卜辞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例如,卜辞中有关于“氐众”的记载:
(1)贞,勿惟王往氐众人。(《合集》34)
(2)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囧。(《合集》10)
(3)贞,王勿令禽氐众伐(?)方。(《合集》28)
(4)……禽于……氐众……宗(?)……(《合集》31)
以上四例都是第一期卜辞。卜辞中的“氐”,同“以”,用如动词,意指召集、命令。第一条卜辞贞问商王前往从事某项事情是否要召集众人随同。第二条贞问王至某地收获黍时是否召集众人。第三条贞问商王是否命令名禽者征集众人讨伐某方国。第四条辞残,大意谓名禽者于某日是否召集众人到宗庙里举行(?)祭。卜辞中还有“以众”的记载,如:(1)丁丑贞,王令禽以众伐召,受又(佑)。(《合集》31973)
(2)壬辰卜,王令禽以众。(《合集》32031)
(3)〔翌〕日壬王其以众。(《合集》26902)
(4)以众王弗每(晦)。(《合集》26901)
上引前两例是第四期卜辞,后两例是第三期卜辞。卜辞中的“以众”与“氐众”的意思相同,亦指召集和命令族众。第一条卜辞贞问王命令名禽者征召众前往讨伐召方,能否受到保佑。第二辞贞问王是否命令名禽者征召众。第三辞贞问逢壬日的第二天王是否召集众。第四辞贞问征召众是否会给商王带来晦气。卜辞中还有“登众”的记载,如:
(1)己酉卜,受贞登众人乎伐……古王事,五月。(《合集》22)
(2)乙亥卜,王其登众,受又(佑)亡灾。(《屯南》1010)
(3)丁未卜贞,王令禽登众伐,在河西岸。(《屯南》4489)
(4)丁卯卜贞,王其令禽登众于北。(《屯南》2260)
上引第一例为第一期卜辞,第二例属于第三期卜辞,其余两例为第四期卜辞。在卜辞中“登”义为征召。第一辞贞问是否征召众人前往讨伐某方国以执行王命之事。第二辞贞问商王征召众是否会受到保佑而无灾祸。第三辞贞问商王是否可以命令名禽者征召众往河西岸讨伐某方国。第四辞贞问商王是否命令名禽者在北方地区征召众。
这些卜辞表明,对于众人的征召多由商王亲自进行,或者由商王委派某人进行,并且要通过占卜来察看征召众人的吉凶,可见商王对于众人是很重视的。从“众”和“众人”与商王的密切关系看,他们应当属于商代的王族或子族。有一条卜辞载“众又(侑)于堂”(《屯南》599)【18】,指众到堂上进行侑祭。堂为商王室举行祭礼的场所,众可以到堂上,足见其当为商王直接管辖的族人。商王朝的族众有许多部分,或者说分支,卜辞记载的诸族众的首领,如禽(《合集》31974)、墉(《合集》31970)、驱(《合集》31997)等,都是殷商时代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相传,西周初年周武王向商王族箕子垂询治国之道,箕子回答的时候就曾经提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尚书·洪范》),认为君主的法则就是要将福佑给予庶民,箕子还谓在决定大事的时候应当“谋及庶人”(《尚书·洪范》)。箕子所谈的治国经验是据殷代情况而言的,认为君主应当和族众的代表人物经常进行磋商。晚商时期孝己曾经告诫商王祖庚“王司敬民”(《尚书·高宗肜日》)。这些言论都表明商代的统治阶层十分重视对于族众的团结,因为商的族众乃是商代社会上“庶人”及“民”的主要的核心的部分。
商王室对于发展王族和多子族的势力十分重视,因为这是与商王关系最为密切的族众。商代的王族在卜辞中多有所见,如:
(1)戊戌卜,争贞,(?)王族令。(《合集》14915)
(2)庚辰卜,令王族比□。(《屯南》190)
(3)甲子卜,争贞,雀弗其呼王族来。雀其乎王族来。(《合集》6946)
(4)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及于……(《合集》33017)
上引第二、四两辞为第四期卜辞,余皆第一期卜辞。第一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从事某项事情。第二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和某族一起从事某项事情。第三例为两条对贞卜辞,贞问名雀者是否征召王族前来。最后一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追击召方及于某处。卜辞中还有“王旅”的记载。“王旅”应当是由王族所组成的军队建制名称,有一条卜辞谓:
王旅其敦人方邑。(《屯南》2074)这是一条康丁时期的卜辞。辞中的敦字从羊从屋室形,王国维释为敦字异文,有伐、迫之义。这条卜辞贞问王旅是否征伐人方之邑。同版还有一条卜辞谓“右旅不雉王众”,可见“右旅”也是王旅。卜辞中有左旅、右旅的记载(《合集》36425、《屯南》2328),可见王旅可能是分为左、中、右三旅的。商代的“王族”应当是商王直接控制的族。
商代王室中未继位的王子及其后裔的族在卜辞中称为“多子族”【19】。商王对于子姓贵族十分关心,经常为其祈祷占卜,在卜辞中就有多例,如贞问子汰田猎之事(《合集》10314)、贞问子目分娩事(《合集》14034)、贞问子渔疾病事(《合集》13722)、贞问子央田猎时坠车事(《合集》10405)、贞问子阱死亡事(《合集》7363)、贞问子雍出巡事(《合集》3123)、贞问子画征伐事(《合集》6209)等。商王还经常为子姓贵族举行禳祭(《合集》535、3202等),以禳除其灾祸。卜辞中有称为子某的贵族90余位,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商王的儿子,但大部分应当是子姓贵族。这些子姓贵族有被封为侯者,如子奠在卜辞中又称为“侯奠”(《合集》3351),子(?)又称为“(?)侯”(《合集》3333);也有的子姓贵族被封为伯者,如子儿又称“儿伯”(《合集》3397),子宋又称为“宋伯”(《合集》20075)。据专家研究,商王朝的“多君”、“多尹”是地位非常显要的官员。【20】假若子姓贵族担任此职,便称为“子尹”(《屯南》341)。王族与多子族关系密切,卜辞里面就有“王族爰多子族”(《合集》34133)的记载。在商代社会上王族与多子族是很重要的社会集团。卜辞载:
(1)……丑卜,五族戍弗雉王〔众〕。(《合集》26880)
(2)丁酉卜,王族爰多子族立(莅)于□。(《合集》34133)
(3)己卯卜(?)贞,令多子族比犬侯凿周(琱)古王事。五月。(《合集》6812)
(4)贞,(?)多子族令比□□古王事。(《合集》5450)
上引第一例为第三期卜辞,第二例为第四期卜辞,余为第一期卜辞。第一辞中的“五族”由辞中的“王众”之称可以断定,此五族即王族。这条卜辞贞问若派五族前往戍守,是否会对王族的族众造成危害。第二辞贞问是否命令王族和多子族一起到达某处。第三辞贞问是否命令多子族和犬侯之族一起去开凿矿石。第四例贞问是否命令多子族和某族一起执行王命之事。卜辞中除了“五族”之称以外,还有“三族”,如“己亥□贞,三族,王其令追召方及于□”(《合集》32815)、“(?)三族马令”(《合集》34136)等,皆为其例。若以“五族”即王族之例为准,那么,卜辞中的“三族”也应当是王族,值得注意的是,王族和多子族参与征伐之事,多见于康丁时期以后的卜辞,这表明王族和多子族在康丁以后实力更强,地位更加重要。
商王朝的王畿地区除了子姓诸族以外,还居住着异姓部族。商王朝对于异姓诸族尽量笼络利用,周灭商以后,周武王所发布的诰命里面所指出的“伊、旧、何、父”、“几、耿、肃、执”等“殷之旧官人”(《逸周书·商誓》),可能都是商的异姓部族的名称。【21】这些异姓部族在卜辞中称为“多生(姓)”【22】(《合集》24141)。有一条第三期卜辞谓“(?)多生(姓)飨”(《合集》27650),盖指商王设宴飨招待“多生(姓)”之事,同版的另一条对贞卜辞谓“(?)多子〔飨〕”,“多生(姓)”与“多子”并列,可见这些异姓部族的首领很为商王所重视。另有一条第二期卜辞谓“多生(姓)射”(《合集》24142),其内容指让“多生(姓)”参加射礼之事。这些记载表明,异姓部族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和“王族”、“多子族”一样也以族的面貌出现于商代社会舞台之上。
族众对商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商王朝是在各族支持下发展起来的,盘庚在迁都时曾经这样向族众讲述他们之间的关系: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尚书·盘庚》)
盘庚明谓诸族的族众和商王的关系可以追溯得很远,诸族的远祖曾经和商先王一起奋斗,同甘苦共患难,所以现在的商王不敢对诸族的族众作威作福、肆意妄为。商王祭祀先王的时候,诸族的祖先也一同被祭祀。卜辞载:
丙辰卜,(?),(?)羊子族。戊午卜,(?)(?)子族。勿(?)子族。戊午卜,(?),(?)母丙。(《合集》21290)
这版卜辞属于第一期,贞问是否用羊为牺牲(?)祭于子族的祖先,是否(?)祭于母丙。从辞例上看,子族的祖先与商王的先妣受祭的规格是一致的。卜辞中还有“(?)子族彘”(《合集》21289)、“又(侑)子族彘,用”(《合集》21287)等记载,都是关于祭祀子族祖先的辞例。这与盘庚所讲“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有某些相似之处,表明殷人除了祭祀商先祖先妣以外,确曾祭祀其他诸族的祖先。盘庚讲他对于诸族有时候也要采取严厉的手段进行处置,但是要经过诸族祖先的同意才行,自己并不敢随便做主。盘庚说: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尚书·盘庚》)
盘庚所强调的是商王在过去曾经得益于诸族祖先的辛劳,诸族的族众又是现在的商王的民众。如果诸族的族众心中产生了作恶的念头,那么商先王的在天之灵就会告诉诸族祖先。这样的话,诸族的祖先就会抛弃那些有作恶念头的族众,不挽救其死亡。如果商王手下有了败坏政治的官员,这些官员总是聚敛诸族的贝玉财物,那么诸族的祖先,就会报告商先王,商先王也会同意给自己的子孙予以惩罚,于是便会降下灾难。盘庚这番言辞里面,并没有把自己摆在居高临下的位置,而是以娓娓动听的语言和平等的地位向族众解释道理。在盘庚看来,商先王和诸族的祖先是平等的,现在的商王和诸族也是平等的。盘庚的这番话,尽管其中不乏官样文章的因素,但是诸族在商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贯的重大影响还是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这影响在,那么盘庚的这些话也就是无的放矢了。卜辞中屡有“王族”、“多子族”、“众人”等“古王事”的记载,见于《合集》22、14912、6813等片。所谓“古王事”,意即治王之事,参与王所命令之事。这些卜辞表明,盘庚所谓的“惟图任旧人共政”、“邦之臧,惟汝众”(《尚书·盘庚》)确非虚语。
晚商时期的氏族已经通过不断地壮大而形成分支。这在商末青铜器的族徽铭文中看得十分清楚。商末和周初的不少青铜器上铭刻有象形性质颇强的族徽,有的族徽上铭有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氏族名号,并且在不同的器物上有不同的组合形式,专家们谓其为复合氏名。专家曾收集了复合氏名的大量材料进行研究,指出复合氏名的意蕴在于作器者以之表示自己的族系,表明自己出身的高贵。例如,单铭“戈”的商代青铜器出土于今安阳地区。关于与“戈”组成复合氏名的青铜器,或铭有与“戈”有复合关系的其他名号的青铜器的情况,专家经研究统计后指出:
记明出土地点者共44件,其中年代属殷代的器物较集中地出土于安阳,及其邻近地(如河北藁城)共30件,占全部44件的68%。而不出于安阳者多属西周早期器(众所周知,西周初商遗民被周统治者按族分赐,各族的青铜器亦由此散布各地)。【23】
这个情况表明,商代的戈氏到了晚商时期已经发展成为相当庞大的氏族,所以产生了许多分支,与“戈”组成复合氏名徽号者就是“戈”氏分支氏族的族徽。戈氏的青铜器有出土于商王室大墓者,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和殷墟妇好墓都曾有所发现,甲骨卜辞中也有关于“戈”的记载,如谓“子戈亡囚”(《合集》32779)、“争贞,(?)王族令”(《合集》14915)等,都表明戈氏与商王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戈氏及其复合氏名的青铜器的出土地点看,可以说戈氏是商王畿地区的一个强大的氏族。
殷商时代氏族的情况还反映在考古发现所见商代墓葬情况中。殷墟洹水北岸侯家庄、武官村以北一带的西北冈,是商代王陵区,所发现的大墓虽然个别的墓道有相互打破的现象,但绝无墓室相互打破之例,可见这些大墓是事先按照一定布局而排列的。这些大墓就是最高级别的王族的族墓。殷墟所发现的中小型墓也以族为单位埋葬。殷墟大司空村墓地,1953年发掘166座,1958年发掘51座,从平面分布情况看,这些墓葬皆以组、群的方式埋葬。1958年所发掘的殷墟后冈墓地的墓葬也成群分布。这些中小型墓葬群应当是商代氏族族葬的遗存。这些墓葬群里面,以小型墓居多,但也有较少的中型墓。大司空村第五群中包括了一座较大的中型墓,后冈的第五群中包括了3座大型墓和两个中型墓。这些情况表明当时氏族首领尽管已经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死后还是和族众成群埋葬,而没有单独游离于氏族墓地之外。
商代氏族制度的发展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是对于祖先崇拜的前所未有的加强。殷人尊神,但在所有的神灵中,以祖先神最为重要。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殷人尽量扩大祖先神灵的范围,凡是能追溯到的对于商族发展有过贡献的先祖都被祭祀。殷人祭祖所用牺牲数量最多,祭祀的次数最多,祭典也最隆重。商代后期还出现了将祖先神灵轮番祭祀的周祭祀谱。这种对于祖先神灵的高度重视,表现了殷人氏族观念的浓厚。从卜辞中还可以看到,商王室以外的其他诸族,除了祭祀商先王先妣以外,也祭祀本族的先祖。《合集》乙组的一条卜辞载:
(?),鸟至。……(?)父庚三牢,又(侑)奚二。(《合集》21538)
这条卜辞载在(?)祭的时候适逢鸟至。卜辞贞问在向父庚祈求禳除灾祸的(?)祭时是否使用三牢为牺牲,是否杀两名奚为人牲。父庚就是其族父辈的先祖神。在诸族的卜辞中,这类神灵见于卜辞记载的还有父戊、祖庚、父乙、妣乙、妣辛等。这些祭祀活动都与商代诸族浓厚的氏族观念有关。
关于商代氏族的情况我们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首先,商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氏族,从商王到各级贵族,以至普通民众都生活在不同等级不同大小的氏族之内。游离于氏族之外者,在商代社会上只是很少的人数。商代的社会生产以氏族为单位进行。其次,商代的氏族在社会上有巨大的影响,商王朝的许多军国大事都需要通过命令氏族来完成。最后,商代的氏族既是社会成员的血缘组织,又是商王朝基本的社会基层组织、商王朝的军事组织以及征收贡赋的基层单位。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对于说明商代社会性质很有作用。族在我国古代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大约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可以找出不少例子说明族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像夏商两代这样,氏族能在社会上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并且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者,则是没有的。不仅如此,夏商两代去古未远,其氏族的特质、组织形式等,与后世的族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以上这些,便是我们断定夏商时代为氏族封建社会的理由之一。
二、封建制在殷商时代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夏代社会性质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孟老夫子关于贡、助、彻的那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这段话里面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孟子·滕文公上》),殷代与夏代田赋制度的区别就在于“贡”与“助”的差别。这一点,正是封建制在殷商时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作为田赋制度的“助”,其基本点是力役的征发。孟子谓“助者,藉也”(《孟子·滕文公上》),可见殷代的“助”就是藉(籍)田之法。《孟子·滕文公》篇的“助”字,本当作“耡”。《说文》载:“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税也。从耒,助声。《周礼》曰:‘以兴耡利萌。’”《说文》所引的“殷人七十而耡”就是《孟子·滕文公》篇之文,可见在东汉时期字还作“耡”。《说文》还有一个“耤”字,谓“耤,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从耒,昔声。”古代的学问家多谓耤、藉、耡等皆一义,指借民力以耕种公田。关于“耤”字,段玉裁注谓: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赵曰:“彻者,犹人彻取物也。藉者,借也,犹人相借力助之也。”按,耤、耡二篆,皆称古成语,而后释其字义,耡即以耤释之。耤税者,借民力以食税也。【24】
他所说的“借民力以食税”,正道出了助法的实质。《孟子·滕文公》篇的“助”,就是古代的“耡”,亦即“耤”。孟子谓“助者,藉也”,是很正确的。
十分宝贵的一点是关于“藉”的生产方式在卜辞中有所记载。卜辞关于征发某族之人藉(籍)田的记载也有不少,例如:
(1)舌伊侯藉。(《合集》9511)
(2)辛丑贞……人三千藉。(《合集》32276)
(3)壬午卜,(?)贞,乎□藉。(《合集》9508)
(4)贞,乎雷藉于明。(《合集》14)
上引第三例为第四期卜辞,余皆为第一期卜辞。第一辞的“舌”在卜辞中有告义,这条卜辞贞问是否通告伊侯之族前来藉(籍)田。第二辞贞问是否征集某族的三千人前来藉(籍)田。第三辞的乎后一字不识,这个字又见于《合集》586,亦为呼其从事某项工作之辞。从“乎”在卜辞中的文例看,其后一字当为人名或族名。这条卜辞大概贞问是否命令某族前来藉(籍)田。第四辞的“雷”为族名,卜辞里面有“雷妇又(有)子”(《合集》21796)的记载,可见雷应当是与商王室有婚姻关系的一个氏族。这条卜辞贞问是否命令雷族之人来到称为“明”的地方为商王室藉(籍)田。卜辞中还有“雷藉在明受(?)(有)年”(《合集》9503)的贞问,可见“雷”是常替商王室藉(籍)田的氏族之一。这些辞例表明,各族常被征发,出动劳力为商王室耕种田地。在殷墟宫殿区内属于王室贵族的一个窖藏圆穴里面,曾经发现了400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集中堆放。【25】这些石镰应当是供诸族的人员前来为商王室的田地收获谷物时所用者。
除了征发诸氏族藉(籍)田以外,商王室还命令自己的族众藉(籍)田。卜辞载:
(1)丙子卜,受贞,乎藉于□受(?)(有)年。(《合集》9504)
(2)丁酉卜,(?)贞,我受封藉在□年,三月。丁酉卜,(?)贞,我弗其受封藉在□年。(《合集》900)
(3)己亥卜贞,王其观藉延往。(《合集》9501)
(4)庚子卜贞,王其观藉(?)往,十二月。(《合集》9500)
(5)王勿藉……(《合集》17407)
这些都是第一期卜辞。前三条卜辞中所空之字从女从自,为地名,应当是商王朝的重要农作区,还有一条卜辞谓“(?)藉于□”,亦贞问在此地藉(籍)田能否获得好收成。后三条卜辞皆贞问王是否亲自前往视察藉(籍)田。藉(籍)田是一项重要的农事,所以商王要亲往视察。从前引第二条卜辞里面“封藉”的记载看,藉(籍)田可能包括着耕地作垄之事。
无论是征召诸氏族的人力藉(籍)田,抑或是命令商的族众藉(籍)田,所藉(籍)的田地皆为商王室所有。这种藉(籍)田的方式,正合乎“借民力以食税”之义,就是对于族众的劳役地租的征发。这种征发,按照孟子所谓的“其实皆什一”的说法,实际上占去了族众十分之一的劳动成果,当然,在藉(籍)田的时候,其所被占的劳动成果是以劳役的形式所付出的。
族众在商代社会生产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卜辞记载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材料,例如:
(1)……王大令众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
(2)……(?)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合集》5)
(3)癸巳卜宾贞,令众人□入羌方垦田。贞,勿令众人。(《合集》6)
(4)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囧。(《合集》10)
(5)丙戌卜,宾贞,令众黍,受(?)(有)〔年〕。(《合集》14)
(6)贞(?)小臣令众黍。(《合集》12)
(7)丁亥卜,令众□田,受禾。(《合集》31969)
上引除了最后一例为第四期卜辞以外,余皆为第一期卜辞。第一、二两例,辞例相同,皆贞问商王隆重地发布命令让众人“协田”是否会有好收成。“协田”,可能是以耦耕的方式翻耕土地,与藉(籍)田相类。第三两辞为对贞卜辞,其中的“裒田”,据专家考证就是开垦荒地。【26】这条卜辞贞问是否命令众人前往羌方开垦荒地。第四辞贞问商王是否亲自前往征召众人至囧地种黍。第五辞贞问命令众人种黍是否会获得好收成。第六辞贞问是否委派小臣命令众人种黍。第七辞贞问命令众人从事某项农事能否多收粮食。在卜辞中,“田”多指田猎而言,然而这条卜辞中“田”与“受禾”相连,故知其亦指农事。这些辞例都表明,“众”、“众人”是商王室田地上的主要劳动力。
商王室的农田耕种采用征召诸族的族众“藉田”、“协田”、“裒田”等方式进行,已由卜辞材料所证实,那么各族内部的公田——亦即贵族所掌握的田地是否采用征发族众劳力的方式进行呢?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商代诸族是否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存在呢?卜辞保存有这方面的一些极为宝贵的材料。甲骨卜辞中有一部分非王卜辞,迭经专家研究已经可以确定其为商王室以外的诸族的卜辞,《合集》将其单独排列,并且分为甲、乙、丙三组。在乙组卜辞中,有一版谓:
丁(?)丑卜,我贞,我役藉于尸。
我尸藉今春。(《合集》21595)
辞中的“我”指贞问者本人,实即乙组卜辞的“子”,即非王室的贵族。辞中的“役”盖指征发族众服役之事。这版卜辞贞问是否征召族众于今春到称为“尸”的地方藉(籍)田。这版卜辞证明,商王室以外的诸族内部也是采用“藉”这种生产方式的。属于乙组的卜辞有“受今秋麦”(《合集》21586)、“余受禾”(《合集》21747)等记载,属于丙组的卜辞里有“正受禾。长受禾”(《合集》22246)等记载,都表明诸族有自己的农业经济,其生产活动应当都是采取“役藉”一类方式的。《合集》所列出的甲、乙、丙三组卜辞,其中不仅记载了诸族农业生产的情况,也有关于诸族畜牧、田猎等的记载,虽然其数量不多,具体含义还有待深入考究,但是诸族拥有自己的各种经济,在这些卜辞材料中还是可以肯定的。属于丙组的一条卜辞谓,“庚戌卜,朕耳鸣,(?)(?)于祖庚,羊百,(?)(又)用五十八(?)母□……今日用”(《合集》22099)。辞中的“朕”是占卜者,即氏族贵族的自称。他耳鸣有病,便要用百只羊(?)祭于祖庚,还要用58只羊(?)祭于先妣之称母某者。辞末的“今日用”盖为验辞,指此事已经付诸实践。一次祭祀要用如此之多的牺牲,其族内的经济应当是较有实力的。诸族一般都与商王室保持着关系。有一件商代末期的铜鼎铭文载“子易小子□王商(赏)贝”(《奇觚室吉金文存》2·1),子为部族首领,将其所受商王赏赐之贝赏赐给其族内的小子某人。可见商王对于诸族的贵族是不敢怠慢的。
卜辞所载“众”及“众人”的身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商代社会性质的认识。认为“众”及“众人”为奴隶的研究,常常举出卜辞中关于“丧众”的记载为证。我们先来看看关于“丧众”的卜辞记载:
(1)……卜贞,众乍(作)藉,不丧。(《合集》8)
(2)己亥卜贞,藉不丧众。其丧众。(《合集》61)
这两片都是第一期卜辞,皆贞问藉(籍)田之事是否会“丧众”。除此之外,卜辞中还有些单独的贞问,如“贞,我其丧众人”(《合集》50)、“贞,其丧众”(《合集》63)、“其丧众”(《合集》32003)、“其丧人”(《合集》1084)、“不其丧众”(《合集》65)等,都没有说明具体的事项,只是表示对于是否“丧众”或“丧人”之事的关心。在卜辞中“丧”屡作地名使用。“丧众”的辞例与作地名使用者不同,其所表示的含义是相当重要的,商王对此颇为关注。《说文》谓“丧,亡也”,又谓“亡,逃也”,能否据此而言“丧众”指众不堪劳役的负担而逃亡呢?看来,不好这样说。理由在于释丧为逃亡是战国秦汉间人的理解,在商周时代并不作如是观。商周时代的“丧”盖用如失去之义。
关于商代“丧”的用如失去之义,在卜辞中可以找到下面两个证据。其一,《易·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经专家考证此即先商时期的王亥之事,义指王亥曾经失羊于易之地。卜辞谓“丁未卜,王贞,□不惟丧羊,□若”(《合集》20676),于省吾先生指出此辞“当指放牧为言”【27】。丧羊即羊走失,可证商代“丧”用如失去之义。其二,卜辞有“允丧师”(《合集》32914)的贞问,于省吾先生指出与《大盂鼎》的“古丧师”“词例相仿”【28】。后世文献中也有关于“丧师”的记载。《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此丧不当作死或逃亡解,亦为失去之义。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交战时,晋卿士季感慨于晋军主帅无威,谓“丧师无日矣”(《左传》宣公十二年),亦为失去军队之义。这两例卜辞与后世文献对勘,可证商代的丧并不作逃亡讲,而是用如失去之义。
在较早的文献里面,“丧”也不作逃亡讲。《易·坤》卦辞“东北丧朋”,马注“失也”。《诗经·皇矣》“载锡之光,受禄无丧”,朱传“能受天禄而不失”。春秋时期,人死为丧之义习用,此外丧亦常用如失去,如《左传》僖公五年载郑文公不参加诸侯之盟,欲逃归,郑大夫孔叔劝他,谓不与盟将被讨伐,届时“病而乞盟,所丧多矣”,“丧”即指郑国之所失。《左传》所载“丧车”(成公二年),即失去战车;“丧列”(成公十六年)即失去行列;“丧陈”(襄公五年)即失去陈国支持;“百工之丧职秩者”(昭公二十二年)即百工之失去职位和俸禄者。是皆丧用如失去之例。商代社会上有一些奴隶身份的人,如臣、妾、奚等,在卜辞中也有记载,但从不与“丧”相连。卜辞言所“丧”者仅众与人,另有两辞谓“丧工”(《合集》97),若丧为逃亡,则首先应当有“丧臣”、“丧妾”之类的记载,可是在卜辞中却从无发现。这一点对于考虑“丧众”的含义应当是有启发的。
总之,卜辞和文献两个方面的分析都表明,商代的“丧”用如失去之义,犹后世所谓的丧失。丧用如逃亡之义者为后出,卜辞里面的“丧众”当非指众逃亡。卜辞的“丧众”,其义当谓失去众,实际上是指失去众的支持。所云“众乍(作)藉不丧”意即进行藉(籍)田之事不会失去众的支持。“不丧众”,意即不会失去众的支持。关于“丧众”、“丧人”的卜辞说明众人在商代社会上地位相当重要,众人的舆论和意愿为商王和其他贵族所十分关注。卜辞关于“众”的记载表明众在商代社会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劳动者,作为氏族成员,其意愿具有相当大的作用,这与《尚书·汤誓》所载商汤耐心地向“众”解释伐夏的原因、《尚书·盘庚》所载盘庚不厌其烦地向“众”说明迁都的理由的情况,完全合拍。关于“丧众”的卜辞还表明了商代氏族首领与族众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首领须得族众的拥戴。卜辞载:
(1)戊午卜,宾贞,禽不丧众。(《合集》39481)
(2)……贞,并亡灾,不丧众。(《合集》52)
(3)贞,长其丧〔众〕。(《合集》4564)
(4)贞,钺其丧人。(《合集》1083)
(5)己亥卜贞,弜不丧〔众〕。(《合集》54)
上引皆第一期卜辞,辞中所提到的禽、并、长、钺、弜等都是商王朝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都是著名的氏族或部落首领而任职于商王朝者。商王关心他们在族众中的影响,故而占卜贞问他们是否“丧众”,即是否失去族众的支持。
商代社会上族众是最主要的劳动生产者,社会上也有一定数量的不同名目的奴隶,但是奴隶在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卜辞资料表明商代社会上,有一部分“众”属于商王室直接控制的民族,另有一些则属于商王族以外的氏族。作为商代社会上主要劳动者的众和众人,都是在氏族组织之中者。他们被命令参加藉(籍)田等农事,是其力役地租的一种付出方式。由此也可以推测,在各族内部,氏族的公田,也要靠征发族众来耕种收获,这种方式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商代的劳动者是否都拥有七十亩土地,现在很难证实,但孟子之语毕竟不能抹杀。商代的“众”即使不一定有七十亩土地,也当有归自己耕种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其上的收获归自己所有。唯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出力役耕种商王室的土地和本氏族的公田。氏族封建制在商代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商王朝的国家组织形式的完善及其对于氏族控制的力量都比夏代增强,从而使不断增强的氏族力量成为商代社会的有力支柱。二是商代已经出现了比较典型的劳役地租剥削形式,文献所载的殷代的“助”,卜辞所载的“藉”、“协田”、“裒田”等事,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质,与夏代具有较多原始民主遗存的“贡”的方式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