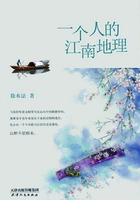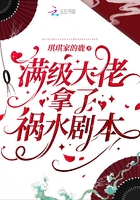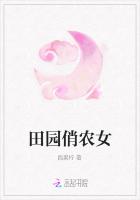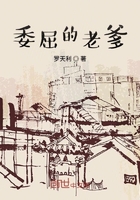现今社会, “老师”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称谓。在一般社会交往中, 对年事稍长或者觉得比自己地位、学识较高的人, 都可以称为“老师”, 而不用考虑对方是否真的在学校里任教, 也用不着考虑对方是否真的与自己有师承关系。
但在三十多年前, 我们生活的年代, 可没有现在这种习惯。那时候, 对于与我们共同工作的长者, 在对方的姓氏前面加个“老” 字, “老张” “老李” 一叫,就算是挺尊重的称呼了。现在看来, 这种称呼未免太随便了一些, 然而, 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 这些长者的分量, 一点不比“老师” 差。如果说有一点差别的话, 仅仅是我们没有张口叫他们一声“老师” 而已。
从1967年到1977年, 我在北大荒工作了整整十年。在这十年当中, 起码有七年时间, 从连队的报道组到团里的宣传部门, 我有幸参与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工作。回首当年, 之所以走到这条路上, 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但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是我遇到了几位没有叫过“老师” 的老师。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在他们的助力之下, 我才在自己的生活轨迹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第一位老师姓甄, 名科。我们都叫他老甄, 有时候跟他没大没小地开玩笑,也喊他老甄科。老甄是八五二农场真正的元老, 据说, 当初铁道兵八五零二师从朝鲜战场回国, 奉命到完达山一带建设农场, 老甄是第一批勘查小组的成员。我们八五二农场(我们来农场大半年后, 成立兵团, 农场改称三师二十团) 方圆数百里, 几乎每一个生产连队, 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农场的老职工们, 背地里管他叫八五二的“活地图”、“活档案”。“文化大革命” 前, 老甄科从总场调到我们三分场, 担任副场长。随着运动的深入, 老甄很快就靠边站了。听老职工们说, 他家庭出身不好, 只能靠边站。但老甄不是主要领导, 平时人缘又好, 还没有被打倒。
老甄个子不高, 身形消瘦, 脸色也不大好, 看上去绝对不是那种身强体壮的人。有时候, 他还戴副眼镜, 讲话的时候喜欢眯缝着眼睛, 慢慢腾腾的, 话也不大多。但在私下里, 他又是个特别健谈的人。老甄经历丰富, 当过兵, 去过朝鲜, 搞过创作, 还写过书。但老甄最吸引我们的经历, 是他自作主张, “想方设法” 去了一次苏联。有一年冬天, 风雪特别大, 老甄他们几个到中苏界江(可能是黑龙江, 要不就是乌苏里江) 附近执行公务。冬季的界江, 双方就在主航道中心线上堆上一连串雪堆, 雪堆顶上再插上一把蒿草, 作为两国的分界线。正值年轻力壮时的老甄科忽发奇想, 顺风把皮帽子扔了出去, 并有意让皮帽子落在苏联一侧。天寒地冻, 数九寒冬, 总不能光着头站在零下三十几度的荒野里吧? 就这样, 老甄靠自己创造的机会, 大模大样地一边捡帽子一边到苏联“走了一圈”。
或许是见多识广的关系,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了冲击, 可他并不是特别在乎。和他在一起, 天南海北地聊, 确实是一种享受。他爱人胡大姐也是北京人, 为人特别热情。知识青年到他们家里, 又吃又喝, 有说有笑, 真像是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不知不觉地, 和很多北京知识青年一样, 我也成了老甄家的常客。碰到休息日, 去分场(后来改称“营部”) 逛逛, 一定要去老甄那里坐坐。后来, 老甄被分配到我们16连“协助” 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落实干部政策的措施), 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 我被安排当了16连的报道组组长。
虽说置身在可以胡思乱想的年代, 说心里话, 在进入报道组之前, 对我来说, “新闻” 这两个字还是挺神秘的。除了在学校写过作文, 根本没想过要把自己的什么“作品” 放到铅字印刷的纸张上。
老甄是多年摇过笔杆的人, 自然成了我们报道组的指导者。
跟老甄学写文章, 倒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他把这事情说得十分简单, 一要看报纸上的文章是怎么写的? 二要轻轻松松地写, 想到什么写什么, 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
这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可是十分费力。
记得有一次, 《兵团战士报》的编辑老赵到连里来, 老甄领着我们和赵编辑座谈。谈着谈着, 议论出来一个题目, 老甄催着我赶快写出来, 让赵编辑直接审读。我急匆匆回到宿舍, 就着黯淡的灯光, 很快写出了这篇稿子。没想到, 稿子送到赵编辑手里, 不出三分钟就被“枪毙” 了。老甄和我简单谈了几句, 要我回去再写第二稿。凭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头儿, 不出十分钟, 我的第二稿完成了。
但第二稿的命运和第一稿没有任何区别。接下去, 老甄又要我写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和第六稿。结果呢, 六篇稿子, 都没逃脱被“枪毙” 的命运。
出现这样的结局, 我并没有感到丝毫气馁。为什么呢? 关键在于老甄的态度。他始终笑呵呵地对待我, 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 甚至连一点生硬的口气都没出现过。在整个过程中, 他只是告诉我稿子有什么毛病, 但绝不建议我应该怎样怎样写。他说, 我就是要憋你一下, 让你自己把自己引导出来。写好当然好,写不好就不好, 没什么关系。
老甄的轻松态度, 并不意味着放任, 该管的时候他一点不放松。在我们的稿子基本成型后, 他要戴着眼镜, 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的仔细检查。那时候, 我们连队宿舍的灯光, 是一连串36伏的灯泡串联而成的, 灯光暗淡不说, 还总是一闪一闪地变换着亮度。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或是写信, 没有耐力可真不行。老甄伏在灯下改稿子时, 眼光极度聚焦, 恨不得一头扑到字里行间, 那股认真劲儿,让人特别感动。当然, 更使我们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认真, 而是他帮助我们、为我们纠正笔误的艰辛努力。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是他将我写的“手捂着疼痛的胃” 改为“手捂着疼痛的腹部”。当时, 看到他改过的字迹, 我就暗暗警示自己,一直到老, 也不能忘记老甄改的这两个字! 这倒是真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 差不多三十七八年了, 在我的记忆中, 依然清晰地留着当时的印记。
第二位老师姓甘, 名叫甘宗棠, 很是斯文的名字。
老甘和老甄的年龄差不多, 而且也是经历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所不同的是,老甘属于现役军人, 一身绿军装, 红领章、红帽徽, 精神头儿要比老甄足。这也是当时的社会氛围造成的。现役军人到农场, 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占据了农场各级领导的主导位置, 当然要比农场的老干部风光得多。听说, 不少老干部很是愤愤不平。因为, 论起参加革命的资格和功绩来, 他们或许更占优势。但他们之间的种种感情上的纠葛, 和我们知识青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下地干活的农工(后来被称为兵团战士), 谁当领导都是一样, 所以, 与现役军人交往并成为忘年交的速度和进度, 完全等同于与农场老转业军人的交往。
老甘是师部宣传科的干事, 但我们很少喊他“甘干事”。一是“甘” 和“干”
连起来喊, 别扭; 二是他也喜欢我们喊他“老甘”。和老甘接触, 很容易判断出他的身份: 这绝对是一位政工干部。他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 和颜悦色, 说着说着就“呵呵” 地笑出声来。老甘的面孔白白的, 头发有些卷曲, 还有点发黄, 一脸络腮胡子, 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外国友人” 的影子。有时候, 我们也会拿他的相貌开开玩笑。
很让我们佩服的是, 老甘身为现役军人、领导干部, 但他没有架子, 一点不像“官”。他在我们农工宿舍间串来串去, 和我们一起说笑、一起聊天、一起唱歌、一起开玩笑。若不是那一身色彩鲜明的军衣, 你会很容易把他误认为连队的老职工(当然, 除了他的肤色: 老甘太白了, 而且总是晒不黑)。
宣传科的干事, 当然是笔杆子, 少不了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老甘与我们报道组的接触, 也就更多一些。老甘他们这些现役军人, 特别是政工干部, 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特别会分析问题。挺不起眼的事情, 让他们一讲, 会冒出很大很大的道理, 时常把我们讲的目瞪口呆。但是, 你又不能不承认, 他们讲得确实精彩, 而且确实有道理。
有一段时间, 老甘到我们连蹲点, 正好赶上兵团在抓勤俭节约, 连里也闹得热火朝天, 出现了很多好人好事。连里领导要求把这些好人好事宣传出去, 我们报道组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写写黑板报, 我们的能力没有问题, 但要给《兵团战士报》投稿, 还要争取见报,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更让我们为难的是, 连里出现的大量好人好事, 很零碎, 事情都不大, 很难展开去写。
这时候, 老甘领着我们细细地琢磨开了。他要求我们一件一件地把那些好人好事摊开, 再一件一件地进行具体分析, 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 抓住他们的特点。三番五次地“过滤” 之后, 我们突然发现, 不少事情都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而现在看到了!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一下子想明白了。在宣传勤俭节约的过程中, 大家发挥主观能动性, 以前看不到的, 现在看到了; 以前没有想到的, 现在想到了; 以前没有做到的, 现在做到了。
抓住了思想发展的脉络, 原先看上去细碎的材料都被用上了, 稿子也就写出来了。而且, 很快被《兵团战士报》采用, 刊登在挺醒目的位置上。
老甘的欢快活泼同老甄的沉默稳重一起走进了我们报道组的生活。
第三位老师姓杨, 单名一个“钫” 字。
当然, 我们对他的称呼也是一样: 老杨。
老杨瘦瘦的, 个子很高, 眼睛大而有神, 黑黑的眉毛特别长。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很多, 头顶上的发丝已然不多, 绝对是前辈式的人物。初次见老杨, 好像是在1970年。兵团要出版一本文艺通讯集(后来又叫报告文学), 组织了一帮年轻人来干, 我有幸被选了进去。老杨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但当时可没这么叫)。
我们这一帮人中, 可能数杨成春年纪最大, 我们两个是一个团的。此外, 还有二师的张猷辉、五师的方存忠, 以及熊道衡、迟英杰等十来个知识青年。虽然, 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级报道组的成员, 在报刊上都发表过作品, 可是,对于写文艺通讯(或者说“报告文学”),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然而, 在和老杨的逐步接触中, 我们心中的“底” 竟然慢慢地“坚实” 起来了。
老杨教我们写文章, 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一篇报告文学,从素材整理开始, 确定主题、完善结构、细节安排、人物刻画, 他是一点一点地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 细得不能再细。文艺创作需要生活, 而我们这些年轻人恰恰在这方面非常“欠火候”。老杨的生活历练当然比我们丰富得多, 他时常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多年积存的生活素材抖搂出来, 为我们不成熟的作品“雪中送炭”, 增添活力。等到文章写出来, 我们惊奇地发现, 除了字是自己写出来的,文章的字里行间, 分明可以看到老杨挥洒的那么多的心血。
老杨身体不大好, 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哮喘, 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咳嗽, 严重的时候喘气都困难。他又是个烟瘾很大的人, 手指头熏得焦黄。有时候, 看着他一边抽烟一边咳嗽, 还一边给我们做辅导, 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慢慢地, 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老头儿的一些身世。老杨原先是相当有名的编辑, 参与过《志愿军英雄传》的编辑工作。流传很广的长篇小说《苦菜花》, 是他帮助作者完成的。当然, 这些都是别人无意中泄露给我们的。老杨从来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 即使我们一再追问, 他也只是一笑置之, 不承认, 也不否认。
应该说, 当时的我们, 简直连文学青年都算不上, 根底实在是差。老杨带着这样一干人写东西, 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我们从来没见老杨发过急, 更没见他生过气。他简直是手把着手教我们写东西。文章写成了, 老杨满脸是笑, 但在发表的文字旁, 却不见他的一丝痕迹。
后来, 我还参加过兵团举办的其他写作班, 多次承受到老杨的殷殷教诲。据我所知, 兵团的业余作者中, 已经出名的梁晓声、李龙云、陆星儿、肖复兴, 还有一大批没有出名的像我这样的人, 都曾从老杨身上得到过恩惠。我相信, 大家都会永远地怀念老杨。
老杨是一位难得的终生为他人甘作人梯的好人。
现在, 我也到了老杨当时的年纪, 每当读到《道德经》中“善利万物而不争”、《论语》里“不伐善、不施劳” 等章句, 我都会想起老杨。
写到这里, 还有些意犹未尽的味道。十年的北大荒生活, 遇到的老师不止这三位。而半师半友的朋友更多, 像比我年长一点的贾宏图、黄海, 比我稍小一点的曹焕荣、张持坚、陶杰等人, 都给过我很大的帮助, 在这里一并说声“谢谢”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