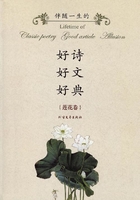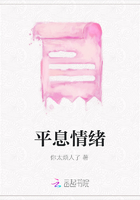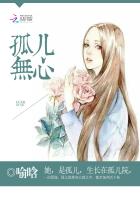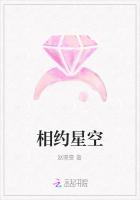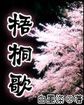当沈从文“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国民族身体里去”时,是为了“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从这种角度上去看,所谓的精神还乡首先是一种有意的文化原乡追寻。在这样的还乡中,作家思考的是现代进程中民族的存亡与断续,寻找的是民族生存和延续的理由。其实,这样的精神还乡不仅仅发生在现代中国,这是每一个后发型现代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意识形态。正如西方学者麦凯南所说:“现代性对其他社会文化安排最终胜利的最好表征不是非现代性世界的消失,而是它在现代社会中人为的保存与重建。”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文学中的这种精神还乡其实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体现。通过想象或现实中文化家园的寻找和重建,表示对现代性种种举措的一种反弹和自卫。因此,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他们刻意渲染的有意的乡愁,与其说是对本原的怀念,不如说是对前路的惶惑”,其所关心的是“诸如国家认同和民族整合之类的问题”张汝伦:《乡愁》,《天涯》1997年第1期。。
说到这里其实关系到对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态度的思考问题,对于这个庞大的话题的细致辨析显然不是本书所能完成的。不过,因为这个话题的理解对我们现在审视的还乡寻找至关重要,又是我们讨论中所不能回避的。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激进主义思潮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保守主义的潜流一直似断若续地绵延着。从《东方杂志》到《学衡》再到新儒家,不管他们的文化面目上有多大的差异,但其对现代性的态度——那种重建民族文化传统和国家认同的努力,一直是和激进主义思潮相对存在的。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现在讨论的回归和寻找文化原乡的现代作家与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多少的联系。但有一点我们应当看到,即使激进主义者的文化态度,在近现代中国史上也是不断分化和演变的。以对文化传统而言,同样也经历了从摒弃式的批判和清算到建设式的清理和重建的转变,像许地山1935年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对理想中的中国文化“自觉、自给、自卫”的期待,无疑反映“五四”后许多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不要说周作人、胡适,就是30年代的鲁迅也已从建立以实践为基础的这一伟大历史工程的需要出发,反观历史,重新发现与肯定中国长期被湮没、否定的“埋头苦干”的传统。在这种普遍的文化“清理”思潮中,传统文化也相应地由一个整合体而被离析成许许多多的侧面,与此同时,像沈从文、艾芜、端木蕻良等写作视野中的边地文化的价值也被重新发现和肯定。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与对文化传统清理、选择和重建相较的另一面是对现代化,尤其是对其重要文化表征都市文化的批判和审视。应该说,对民族文化传统由清算到清理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对都市文化的态度似乎与此构成了一个逆向的反复,经历了由欣羡、赞美到诅咒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都市文化”在近现代中国同样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在沈从文、芦焚眼中的都市文化和刘呐鸥等眼中的都市文化无疑是大异旨趣。不过即便在施蛰存这些诗人的眼中,工厂的烟囱,这个工业文明的象征成了“在夕暮的残霞里,/从烟囱林中升上来的大朵的桃色的云,/美丽哪。烟煤做的,透明的,桃色的云”。都市不仅是工业文明的象征,同时也给诗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一种近乎迷狂的“快速的节奏、幻变的色彩、嘈杂的音响和肉欲的气息”的沉醉和兴奋。但是诚如有人指出的,这种“都市风景的赞美只维持在一个小圈子里,而都市疾病的诅咒却逐渐蔓延开来”。像《火灾的城》这首诗写到:“从你的隧道望了进去,/在那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我看见了无消防队的火灾的城/和赤裸着的疯人们的潮。”这样,因为病态都市的体验,使得人与他的生存环境——都市脱节,从而使置身都市的人产生了一种无所归依的悬浮感、漂泊感,在现实世界里,当“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从对现代都市的讴歌、沉醉走向对现代都市的诅咒和摈弃,现代作家纷纷在精神上踏上一种回归古典田园的还乡之路。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还乡寻找心灵的憩息之地,正是那种人在现代都市体验到无边的孤独和深刻的疏离之后向传统和古典回归的“反弹和自卫”的心理反应。在这里故乡、乡土中国适逢其时成为“城”之外的“乡”。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心理反应和前面讨论的对文化传统的清理、选择和重建某种程度上是互为因果。而沈从文这个乡村少年一踏进都市就陷入生活的窘境,都市对他的敌意无疑孕育、生成了他对都市的敌意。都市的异乡人使“乡下人”立场和姿态的选择显然是蕴蓄“反弹和自卫”的强调。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沈从文写作《边城》的心理动因了。沈从文反复申说他所倾心关注的是“我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7—59页。,而与此相对的都市,都市的所谓教育、理论则为作家所诟病和厌弃。因此,就像汪曾祺指出的:“‘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值得指出的是,为何现代中国作家在现代大都市里体验了孤独和疏离却没有像西方现代派那样走向抗争、堕落,或者是抗争、堕落之后的毁灭,而是义无反顾踏上反抗与逃避的还乡之路。这和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之子”身份的认同和确认密切相关,这中间典型的像鲁迅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是对大地、故乡、母亲的皈依。李广田的《地之子》里写到:“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我爱着这地面上的沙壤,湿软软的,/我的襁褓;/更爱着绿绒绒的田禾,野草,/保姆的怀抱。/我愿安息在这土地上,/在这人类的田野里生长,/生长又死亡。/我在地上,昂了首,望着天上。/望着白的云,/彩色的虹,/也望着碧蓝的晴空。/但我的脚都永踏着土地,/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我无心于住在天国里,/因为住在天国时,/便换掉了王国,/且失掉了我的母亲,这土地。”可以这样说,现代中国作家中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作家微乎其微,当他们侧身都市,当他们思考民族的出路,文化的中兴,这种乡村背景无疑规定了他们反抗、逃避与皈依的方向。因此,沈从文认为:“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这样的温爱源于“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7—59页。现在看来,像沈从文这样选择精神还乡,其意义就在于相对于都市,“乡”“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还乡的过程中,作家完成了文化的臧否,同时也寻找到生命存在的依据和根源。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寻找与发现,也许存在着主动与被动、情感与理性的差异,但应该说,同样都汇集到对我们文化传统的价值的发现和重估之上。
但是,尤其要廓清的是这种文化的反顾和寻找与“复古”派、“国粹”派的抱残守缺有着本质上的界限。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都采取了“向后看”的姿态,但恰如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爱国者虽偶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因此,沈从文同样强调他的精神还乡书写对于民族未来的意义,“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是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7—59页。
沈从文的还乡是自觉的文化还乡。“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下一个空壳”,“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之后,于遥远的边地,别出一片新的世界。关于这种自觉和这个世界,沈从文给友人的信中写到:“我这时是觉得生活在我只是一种苦事,若是事势许可,能够返到苗乡去住真是幸福,不可讳的是我真已近于落伍人,大都会生活使我感到厌倦;就是写文章,也只是回到乡下去好,因为要明白中国,也只有在老国民去一处过日子才是事。”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而“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习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离远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一部分的生命的腐烂”同上书,第63—64页。。就在写这封信的前两天,沈从文将湘西世界称为“我的世界”,他写到:“……我的故事就是《龙朱》同《菜园》,在那上面我解释到我生活的爱憎。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学的世界;我太与那些愚暗、粗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习,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我爱悦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沈从文:《〈生命的沫〉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作为都市文明的对照面,这样的世界虽然联系着遥远的湘西——沈从文那大地上的故乡,但在写作中,沈从文却似乎有意让自己从这样的世界淡出,而这世界自顾自地呈现出来。相比较而言,废名还乡从事的工作类似于一种“文化考古”,在细致的钩沉后进行文化的甄别,省略了一些,同时也放大了一些;遮蔽了一些,同时也彰显了一些。就像朱光潜说:“废名的人物却都沉没在作者的自我里面,处处都是过作者的生活,小林、琴子、细竹三个主要人物都没有明显的个性,他们都是参禅悟道的废名先生。”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因此废名的世界虽然不刻意去强调和自己故乡的联系,但却一切皆着上“我”的色彩。所谓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其后来的衍生和异变的状态。与沈从文空间移置中的回归寻找不同,对照着文化的原初状态,废名的选择和省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还原和净化,去掉文化衍生过程的遮蔽和附着,让我们回到那“不应当忘却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中去。虽然这样的生活随着“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面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00—102页。,但仍然可以像废名这样借助书写在纸上溯回我们文化的原乡。极端地说,在废名的文化意识中一直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文化发展观。他曾经说过:“延陵季子挂剑空垅的故事,我以为不如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美。嵇康就命顾日影弹琴,同李斯临刑叹不得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未免都哀而伤。朝云暮雨尚不失为一篇故事,若后世才子动不动‘楚襄王,赴高唐’,毋乃太鄙乎。李商隐诗,‘微生尽恋人间来,只有襄王忆梦中’,这个意思很难得。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此间乐,不思蜀’,或者因为这个原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我尝想,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儿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掐失好些好看的字面。”废名:《中国文章》,《世界日报》1936年1月6日第37期。这种俱往溯古的文化发展史观显然和“五四”后的文化未来主义和进化史观构成一种奇特的反差。从这种意义上说,废名的写作中其实隐含了“反文化”、“反现代化”的因子。相比较而言,当沈从文呈现着湘西的“过去伟大处”和“目前堕落处”时隐含的也是类似于废名的文化发展观,但不同的是在沈从文的视野里还有一个遥远的未来被想象着、期待着,成为其艺术世界的又一时间维度。
《边城》和《桥》这两部作品,沈从文和废名都存在一种寻找乌托邦的寄托,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无论是《桥》还是《边城》,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中国古典“世外桃源”的仿写。据刘明华的研究,中国的桃花源包含着这样一些因素:“首先,作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桃花源又是一个人人自食其力,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桃花源民风淳朴,质朴无伪”,“桃花源是人类社会隔绝的乐土,又是大自然的一个神秘天地。”刘明华:《大同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21页。按照这些指标,对照《桥》和《边城》的世界,沈从文和废名为读者提供一个桃源梦境的企图自不待言了。只不过从写作策略上,《桥》是更多在时间上回归到我们文化的原乡,似乎当我们从生活的现在返回原初,走过这座“桥”,抵达的就是我们文化的根源;而《边城》则侧重从空间上把文化和灵魂的故乡推向“湘西边境”,这世界的“边境”和我们生活的都市世界神奇地并置,它们却有着自己的时间与应对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的意义世界。“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是那些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这个小城中生存的,各人自然也一定皆各在分定一份日子里,怀了对于人事爱憎必然的期待。”“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一些人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若有多少不同处,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也更于糊涂一点罢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现代桃源梦境的书写,“难逃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意识形态兴味。与其说原乡作品是要重视另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不如说它展现了‘时空交错’的复杂人文关系,意即‘故乡’乃是折射某一历史情境中人事杂错的又一焦点符号”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6—227页。。因此,对沈从文和废名来说,既要致力一个文化的原型——桃花源的复制,同时又必须提供外在文化压力的理由。所以《桥》的下篇展示时,小林已经不是在私塾中提笔在水壶上写“程小林之水壶”那个小林了,是走了几千里路还乡、可以出口成诵莎士比亚名句的少年公子了,而《边城》的最后则提醒读者:“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圯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相比较而言,废名的《桥》贯穿着有变迁流逝而没有进化意义的时间意义,通过闯入桃花源的现代知识者对桃花源的皈依,书写了一个现代的文化神话,一个关于“故乡”“幻”得的现代神话。而沈从文对桃花源的仿写和复制似乎更多现实的期许。如果说,《边城》由于空间的错置,使人几乎相信了这样现代桃花源现实存在的可能。毕竟,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样的文化“边境”可能会遗存下来。但是仔细阅读沈从文的《边城》,会发现作家的思考似乎还不只是对都市和边城参照中进行简单肯定与否定。事实上,在作家的写作视野中,“边城世界”自身也存在文化的并置、参照和权衡,这无疑使作家的文化选择复杂起来。文化后来的衍生与异变的状态和文化的原初状态在《边城》中纠缠在一起,小说中翠翠的出场显示在边城世界里生命的原始和本真的素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但一切皆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表面上看,在小说中打破他们安静平凡的生活的是大佬溺亡的隐痛,渡船和磨坊比较中潜藏的担忧,但和这种影响生命个体前途的偶然事件相比,左右边城整个世界和未来的则是一个更具有破坏力的大时代正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边城》这种渗透和破坏也许还很难察觉,但“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因为商人的需要,水手的需要,这小小边城的河街,也居然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脚楼的人家”。因此,《边城》的“边境世界”自己的内部也时刻处于一种矛盾和紧张状态,这个曾经用来质疑与瓦解现代和都市世界意义的“边境世界”,自身也时刻面临质疑与瓦解。“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了。”作家诉说着小儿女的乐与哀,弦外之音却是一个精神还乡者心灵深处难以言说的乐与哀。在其后《长河》的写作中,沈从文则进一步将《边城》的桃源梦境向时间的长河挪移,以至于作者最后抑制不住地叹惋:“《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已经成为过去,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显然,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经历了文化原乡和精神故乡的“幻”得与“幻”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经营着“故乡”的文化神话,废名得到的是“天上的花园”,而沈从文失去的是“地上的花园”。而且有意味的是《桥》和《边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还乡的灵魂之旅安放在小儿女的故事和心事的讲述中。值得指出的是沈从文一方面书写着“幻”失的“薄薄的凄凉”,“《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汪曾祺:《又读〈边城〉》,《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100页。。但另一方面却走向对生命创痛体验之后的体恤、宽宥和忍耐,就像《边城》最后,“过渡时有人问及可怜的祖父,黄昏时想起祖父,皆使翠翠心酸,觉得十分凄凉。但这分凄凉日子过久一点,也渐渐淡薄些了”,“时候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应该说,废名、沈从文的写作对于30年代的“京派和北方作家群”是有启发和示范意义。“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这使得“京派和北方作家群”群体症候似地启动文化或精神的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