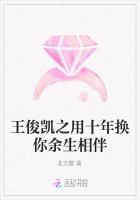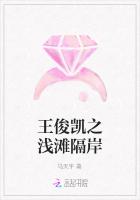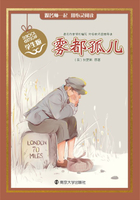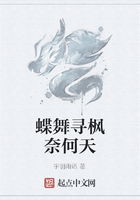从原型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学的还乡母题同样溯源于回归土地、回归母体子宫的原始思维和意象,但中国文学的“还乡”传衍过程中,发育出“归”的世俗、伦理的“还乡”和“游”的精神性“还乡”,特别是“归”的世俗、伦理的“还乡”更是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而西方文学的还乡母题在后世的传衍过程中,却是和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摩西五经”中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叙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哥珊出走回归祖宗雅各的故乡迦南的旅程,是相当成型的“还乡”书写。不仅如此,在《圣经》中对于此岸的家乡和彼岸的家乡有着明确的区分,《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而,所谓“还乡”在西方文化中就具有了此岸和彼岸、世俗和精神的双重性,而且彼岸的、精神的故乡和家园从一开始就凭借神的预予确立了它的优越性。这中间奠定了西方还乡母题书写基石的是奥德修回乡的旅程。
天神们在奥德修已经在海上漂游了10年之后,决定让他返回故乡伊塔克。在《奥德修纪》这部伟大的史诗的一开始就这样写:“且说所有其他英雄这时都已离开战争和海洋,逃脱凶险的死亡命运,回到了自己家乡;只有奥德修一个,苦苦怀念着归程和他的妻子,却被那有魔力的女神吕蒲索洞主留在她的山洞里,要他同她成亲;但岁月流转,上天注定奥德修回到伊大嘉的一年终于到来,只是他回到亲人中间的时候,还免不了要受些艰难考验。”《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这时奥德修在家中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已经长大成人,出去打听他的长期失踪的父亲的消息。伊塔克的许多人都认为他10年不归,一定已经死去。当地的许多贵族都在追求他的妻子佩涅洛佩,佩涅洛佩百般设法拒绝他们,同时还在盼望他能生还。奥德修在这10年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独目巨人吃掉了他的同伴,神女喀尔刻把他的同伴用巫术变成猪,又要把他留在海岛上;他又到了环绕大地的瀛海边缘,看到许多过去的鬼魂;躲过女妖塞壬的迷惑人的歌声,逃过怪物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最后女神卡吕普索在留了奥德修好几年之后,同意让他回去。他到了菲埃克斯人的国土,向国王阿尔基诺斯重述了过去9年间的海上历险,阿尔基诺斯派船送他回故乡。那些追求他的妻子的求婚人还占据着他的王宫,大吃大喝。奥德修装作乞丐,进入王宫,设法同儿子一起杀死那一伙横暴的贵族,和妻子重新团聚。对于这部史诗和《圣经》的关系,弗莱在他的《批评的剖析》中指出:“《奥德赛》开创了另一种回归史诗的传统。这是一个浪漫故事,描述一位英雄经历了千难万险,在关键时刻回到自己新娘身边,赶走了那些恶棍:但我们对它的主要感情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意识,基于我们对自然、社会、法律和理所当然的主人自己对房产的重新占有和接受。《伊尼德》的回归主题则有所发展,是回到一个人的新生。其在‘新特洛伊’的终点就是由英雄的探寻所更新和改变的始点。基督教史诗把同样的主题带进更广阔的原型关联域。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圣经》囊括了前述三部伟大史诗的三大主题:《伊利亚特》中城市的毁灭与失陷的主题。亚当和奥德修同样是一个愤怒的化身,因为他超越了做人的界限,触怒了上帝,因而被赶出家园。在这两个故事中最有代表性的情节是吃了为神准备的食品。像奥德修一样,亚当是否能重返家园取决于神的智慧对神的愤怒的安抚(在荷马史诗中海神波塞冬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对宙斯意志的妥协;在基督教赎罪故事中上帝与世人的妥协)。以色列人把诺亚方舟从埃及一直带到希望之乡的福地,同样,伊尼亚斯把所有家当都从陷落的特洛伊城带到永恒地建立起来的新特洛伊城。”〔加〕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有了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看清楚还乡母题在西方文学中的传衍脉络。在这里,隐含了西方文学还乡母题的两个重要秘密:其一是“逃亡”、“漂泊”和“还乡”的对举出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丽·萨克斯的研究专家艾哈德·巴尔曾经对奈丽·萨克斯全部作品的高频词作过统计,并和《圣经·出埃及记》比较发现了两者的平行关系,这些词是“逃亡”、“告别”、“避难”、“逃亡者”、“异国”、“故乡”、“回乡”、“乡愁”、“返回”等,他的研究固然是为了揭示奈丽·萨克斯作品的宗教性,但借助他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还乡”常常联系着“逃亡”、“告别”、“避难”,这样的传统,《圣经》提供了写作的原型,并且延伸到20世纪文学写作中〔瑞典〕萨克斯:《逃亡·译本前言》,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其二是“还乡”往往还联系着自我的复归,弥合和过去的断裂,重新回到他过去那种童年的记忆或者是那种集体无意识当中去,而这样的回归和完善又和磨难纠结在一起,就像卡吕普索对执意还乡的奥德修所说的:“你能预料到要经历多少苦难才能还乡……”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能发现这两方面其实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逃亡”、“漂泊”的分离与背井离乡,然后是在现实、回忆与想象的还乡中重新找到自我。因此,我们进一步发现在中国当“游”的精神性还乡被挤向边缘,“归”的世俗性、伦理性还乡成为主流时,东西方还乡已经存在着巨大的分野,和中国文学的还乡母题常常止步于人伦、亲情和血缘相比,西方文学的还乡母题对于人的存在与走向的终极话题更为关注,在人伦、亲情和血缘的暌违与弥合之外,强调形而上的心灵的断裂与复归,即便是现实的、世俗的还乡往往也隐藏着象征和隐喻性。从弗莱研究中文学史意义对传统的不断回归而言,所谓“一种后来的模式最强烈地反对紧挨着的父辈的模式,但却在较小的程度上回归到祖辈的模式的某些标准上去”〔加〕诺思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第49页。。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文学的还乡母题在一个恒定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不断的同构和复制意义上回到《诗经》所凝固下来的传统,而西方文学的还乡母题却在自身文化语境的演进和更嬗中,在互文、互释意义上在回到史诗和《圣经》的传统。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对于《奥德修纪》戏仿的例子。《尤利西斯》借用古希腊英雄“奥德修”的故事,把古希腊英雄在海上漂泊10年终得还乡的故事予以现代化。乔伊斯在书中精心构思安排了《奥德修纪》中相对应的结构模式,把《奥德修纪》中的24章缩为18章,对应三个还乡行动的角色18小时的心路历程,象征性地展示“现代英雄”还乡的磨难。甚至每个章节和每个主要人名、地名,都用《奥德修纪》中的人名、地名来隐喻。久经考验、多智的古希腊英雄奥德修的海上历险,变成了现代“尤利西斯”、小市民布卢姆的都柏林街巷中的无所事事的漫步。这样在和《奥德修纪》互文、互释中,乔伊斯的现代还乡之旅,凸显的是神性消退、英雄末路时代现代人的平庸和卑微。而昆德拉的《无知》也可以在和《奥德修纪》的互文、互释中看取现代世界去国又还乡之后,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值得指出的是东西方还乡母题不仅在基本主题上二水分流,而且在中国文学中还乡母题和诗性抒情传统密切联系着,并没有在叙述传统中展开围绕还乡母题的丰富的母题构成和组合,相反在西方文学中,从一开始“还乡”不仅就和“流亡”、“自我复归”结合在一起,而且着重于还乡延宕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这样的“时间化”模式为叙事的充分发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考察西方文学的还乡母题,文艺复兴以及其后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就是从这一个阶段开始,时代又为还乡母题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就像有研究者指出的:“文艺复兴是一柄双刃剑,它开启了近现代的人性解放以及人性堕落之路,导致了人性的分裂,同时也导致了一个二律背反,即‘精神家园’的生长和失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浪漫主义思潮在欧洲各地兴起。在谈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滋华斯时,勃兰兑斯曾经指出:“华滋华斯的真正出发点,是认为城市生活及其烦嚣已经使人忘却自然,人也已经因此而受到惩罚;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了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纯朴印象的灵敏性。”〔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徐式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应该说,华滋华斯的出发点也几乎是当时所有欧洲浪漫主义者的出发点,只不过是英国浪漫主义者在对城市生活和物质文明的批判中重回自然,而德国浪漫主义者却在体验着“失却诸神”的内心分裂中,思考着“还乡”的必要性,这在诺瓦利斯那儿是“哪里没有了神灵,魔鬼就出来统治”的精神荒原,是“我们这是去哪儿”的迷惘,是“总是在回家呵”的灵魂复归(《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在荷尔德林那儿则是“我寂然一身,但祖国之父,/你就在我头上,超然于云雾之端!/呵,万能的苍穹!/还有你们,大地与光明!/你们三位一体,永恒无极,/宰割万物,施与慈爱。/那把我紧系于你们的丝带永不断裂。/我自你们溢出,/追随你们而浪迹他乡,/现在,我已饱阅人生,/又与你们,与欢乐的神明同返故园。”(《致流浪者》)他们共同认为“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页。。那么,人类怎样才能返回到与神灵同在的原初和故乡呢?海德格尔在分析荷尔德林的《返乡——致亲人》时,认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返回,他先前而且也许已经长期地作为漫游者承受了漫游的重负,并且已经向着本源穿行,他因此就在那里经验到他要求索的东西的本质,然后才能经历渐丰,作为求索者返回。”〔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第25页。在“漫游”、“求索”中,“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同上书,第31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不仅是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写作的《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还乡行动的角色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的还乡之路同样也是“漫游”、“求索”之路。“漫游是为了展示漂泊的游子在回忆中返回家园,并非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我完善,所以还乡行动的角色经历的只是在从无家可归到重归故里的‘过渡年代’。”李伯杰:《“思乡”与“还乡”》,《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研究中,我们发现德国浪漫主义者还乡母题的处理过程中还乡和对于故乡的理解其世界图式是建筑在西方神学世界之上,无疑这也证明了还乡在西方文学中常常是一个富有宗教色彩的文学母题。值得指出的,虽然这里的还乡在神学意义上展开的,但所思考的却开启了近现代技术文明时代人类“精神家园”失落和重返的现实命题。
由进化论演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使社会变迁和发展中的进步与落后的命题凸显出来。哈代在处理还乡母题明显渗透着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达尔文主义使哈代笔下英国农村的消亡有了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小说《还乡》中,还乡行动的角色克林不满故乡爱敦荒原的落后,还乡办学,最后以失败告终。在这里还乡者和故乡环境之间的隔膜和不适成为哈代对他失败原因的合理解释。但不是所有的问题纳入进化论的图式都能得到合理的阐释,而且即便能够解释的一些问题,从理智上认同它的合理性,落实到情感认同上又是一回事。因此,一方面,20世纪人类的家园不断遭遇技术进步、战争、动乱的毁弃,同时频繁的移民、迁徙、文化交流、冲突使整个人类体验着“在他乡流浪”的家园失落;另一方面,人类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家园的怀念,对故乡的回归,而不断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这中间,都市和乡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成为还乡母题书写中引人注目的主题内容,应该说这样的因为文明冲突而引发的还乡母题的运用和书写几乎在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中都有所体现,这就使得还乡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话题联系在一起,哈代的还乡母题处理是一种角度,但不是20世纪世界文学还乡母题的全部。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20世纪还乡母题另外的发展状况。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文学中出现以阿勃拉莫夫、扎雷金、别洛夫、拉斯普京等为代表的“农村散文”派的写作。对于这群作家的主题、风格和创作手法,美国学者乔治·吉比安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新趋向》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对简朴、古老的俄罗斯乡村生活方式进行探索的作品构成了一类重要的文学……农村作家中有:阿勃拉莫夫、阿斯塔菲耶夫、别洛夫和久负盛名的拉斯普京,以及受人爱戴的电影演员、导演、短篇和长篇小说作家舒克申。……他们哀叹城市、技术文明导致了人性的丧失,但也描述乡村生活的落后。他们提高了俄国农民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们并不掩饰农民的落后特性。他们暗示,灵魂的拯救在于回到原始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中去,或者就如他们所说,存在于俄罗斯乡间‘德高望重’的幸存者中间……这些人的心灵中保持着古老的、朴素的、民族的品质。……”薛君智:《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6—77页。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家回归到乡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科技的进步,就像拉斯普京所说:“随着几个世纪来农村习惯完全被破坏,农村的伦理风尚也被摧毁(而农村一直是人民伦理基础的贮藏所),这件事当然不能不反映在文学之中。”《文学报》(苏联)1977年3月16日;彭克巽:《苏联小说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281页。就手段和主题而言,“各种不同的作家……以‘复旧’为手段……就主题而言,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到过去,如重新构思作者本人或作品人物的童年或青年时期的历史材料或事件(强调往日已经过去);把过去作为探索的对象,为现在挖掘其重要意义;或集中于从遥远的过去幸存下来的事物(如古老过时的行为、思想和说话方式)。……” “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下,这代表了一种明显的转变;偏离进步的、前进的、直线发展的时代的旧框框(官方的思想)——偏离一切目的论,倾向强调过去与现在相联系的时代感。”薛君智:《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第80页。
20世纪中期,印度的边区文学兴起。对于印度的边区文学,有研究者指出:“印度独立后,伴随着梦想的破灭与新价值观念的迷惘,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开始‘寻根’。印度是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度,乡村是这种农业文明的集中体现,作家回归于乡村生活的主题,企图从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展示上来揭示传统文明在当今社会中的命运与前途。因此,从这一时期边区文学中反映出来的并不单单是乡村世界的风俗人情画面,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积淀式分析……在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普列姆昌德等作家就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把印度的希望寄托于农业文明传统的发扬光大之中。印度独立之后,美化乡村并以乡村来对抗城市的倾向在边区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石海峻:《20世纪印度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本着这样的目的进行创作,边区文学作家的“还乡”、“寻根”以及他们笔下的乡村就有了一种“文化寓言”的意味了。像帕尼什沃尔纳特·雷努的《肮脏的裙裾》所写的比哈尔邦东部的普尔尼亚是作家的故乡,但作家在初版“序言”中却提醒人们,这部小说,“此书名为《肮脏的裙裾》,是一部边区小说。故事的发生是普尔尼亚。普尔尼亚是比哈尔邦的一个县。“这里面有花也有刺,有红粉也有尘埃,有檀香也有污秽,有美也有丑……我不能回避其中任何一个。”〔印〕帕尼什沃尔纳特·雷努:《肮脏的裙裾·初版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对于20世纪迁延至今的世界范围的还乡母题书写,就像安德森的研究所揭示的,虽然民族主义的没落以及国际交通、资讯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大大超过往日,但这并不会因此促进泛国际主义;相反的,由于资讯与交通的进步,人虽身处他乡,他的认同行为却透过象征的还乡,而变得更加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