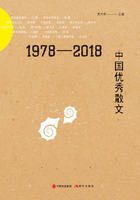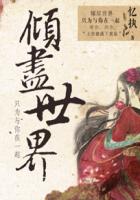急遽变动时代·两发重磅炮弹·冯牧还有茅盾
蔡:《收获》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就刊登了你的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那时候《收获》刚刚复刊不久。你那么早就在《收获》上发表作品,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冯:我是写“伤痕文学”的第一拨人,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走上文坛的那一批人,新人。这批作家基本都以写“伤痕文学”开始的。我在一九七七年以后一直在朝内大街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里住着。我写历史小说,第一部《义和拳》出版了,《神鞭》也出版了。那时北京文坛正处于寒冷的秋天,秋寒季节中。各种说法都有,很紧张,也很兴奋。觉得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解冻开始。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否定,作家完全凭着勇气写作。凭着勇气写作,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当时非常不容易。那时候我写了一个小说,就是《铺花的歧路》。《铺花的歧路》最早不叫《铺花的歧路》,叫《创伤》。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写的,是写红卫兵的小说,那时候比较敏感,但是我的角度正好和当时控诉红卫兵的相反。我是用一个红卫兵忏悔的角度,带着同情的角度来写的。一般人可能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整个家让红卫兵给毁了,被砸得粉碎。我们那个楼,整个楼都被洗劫了。我一直想写这么个小说。红卫兵连着三天抄了我们一条街。抄完之后拆了房子的地基,把所有的人拉到街上斗,整整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家是首当其冲的第一家,一条街的第一家。我们家是比较有名的家,在天津租界的地区。但是相反,我会从人性的角度,站在红卫兵的角度,也不是站在同情的角度,来写那么个小说。可是,就是这么个小说,在当时是不被接受的。而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编辑室)编辑部里就变成个麻烦。编辑部的几个负责人都认为这个小说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而且是指责毛泽东,因为我前面一段话是写毛泽东的,当时被认为是个很危险的小说。我是一九七八年写的,《当代》还没有创刊。我那时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把历史小说放下了,因为整个时代变化了。那时候刘心武的《班主任》刚刚出来,很敏感。一种被压抑的欲望一下子爆发。爆发就看谁有勇气。大部分人都要观望一下。一种政治上的激情冲出来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争论非常大。还出现了很多笑话。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的孩子,在出版社里面挨个给送报纸,送到当代文学编辑室,当代文学编辑室正在为我的小说争论起来。他一听,从屋里跑出来,满楼大喊,说:“冯骥才犯错误了!”那时全都知道了。我当时住在出版社后面的一个作家写字楼里,很简陋的房子。作品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搁浅了。
蔡:你写出小说,本来是打算在他们那里发表的吗?
冯:出版。当时《收获》还没有复刊,《当代》也没有创刊。就搁浅了。在这前后,卢新华的《伤痕》出来了。卢新华的《伤痕》比我的小说写得晚一段时间,等出来以后,“伤痕文学”起来了。“伤痕文学”起来以后,我的小说题目就要改了。后来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在《小说家》上。他说如果当时冯骥才的小说发出来,恐怕就要叫“创伤文学”了。当时就是这么个阴差阳错的时代。那时代的变化非常急遽。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一九七八年的冬天,韦君宜的意思是想让我的小说迅速通过,就提出了三部小说:一个是我的《铺花的歧路》,一个是上海的作家竹林的小说《生活之路》,还有一个是孙颙的小说,三个中篇小说拿到北京和平宾馆去开个会讨论,实际就是文学思想、文学动态务虚会。那时候还没有“新时期文学”的称呼。《生活之路》是写一个女孩子被强奸后来自杀了的小说。出版社刚接到的时候,害怕,不敢出。我说,我认为非常好。那时候写悲剧都根本不可能。而且,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最后也自杀了。后来就改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是北京想通过,想借助一种力量,就在那个会上,把茅盾请出来了。韦君宜说,冯骥才,你把这个故事讲给茅盾同志听听。我就上主席台,坐到茅盾身边,把我的小说一口气讲了二十分钟。那时候年轻气盛,也不在乎。茅盾非常仔细地听我讲。印象非常深。听完以后,他当时就表示支持。但是,自杀,他说,你可以再考虑。他说,我不是说人不能自杀。他说,是可以自杀。但是,是不是人物性格发展的,他必须自杀,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实际上更好,更有力量,更有感染力。后来改了一下那本书。韦君宜说,茅盾同意了,出就出吧。就在这期间,李小林找我要稿子。她听说这个会,听见这件事情,她马上拿走。她一看,就觉得很好。因为《收获》复刊后的第一期没有“伤痕文学”,第二期才有,第二期就我的那篇和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两个小说一块出来,就等于是两发重磅炮弹。小说出来以后,《收获》杂志社就接到一封匿名信,说我们是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是“解冻文学”。那时候就是这样,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文化大革命”没有否定。他们认为我们的小说绝对是反面的东西。从那会儿开始,我很佩服李小林。李小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家里没有电话,我是到邮局去接的。我和《收获》的关系超出了作品和出版的关系。没有什么作家想成名啊,要多少稿费啊之类的想法。就是对时代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是时代的激情,这种激情是碰撞出来的。就是一种同志式的关系,在一起很激动。这种精神很牢靠,是一种纯精神的,跟时代联系在一起。
蔡:你的作品是《收获》发表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给你出版了吗?
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得稍微晚一点,因为图书渠道比较慢。《收获》第二期出来之后,我紧接着就给《收获》一篇《啊!》。《啊!》这个小说要比《铺花的歧路》厉害多了,而且更成熟了。后来冯牧对我的小说不是很满意的。冯牧是在好几个会上讲,说《啊!》这个小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正面人物。
蔡:思想还受到“三突出”原则的禁锢,受到“左”的思潮的束缚。
冯:他说,有正面人物,这个小说会更有积极意义。后来在好几次小说获奖的会上,冯牧都要讲那样的话。等到真正小说评奖的时候,当时评委会的几个人都希望把这部小说评成一等奖。冯牧也觉得这个小说写得不错。他说,他被震住了。但是,很遗憾,这个小说没有一个正面人物。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局限。他们就是这么考虑问题的。但冯牧也很了不起。他说,不要一等奖,我们评成一等奖,上面就要看,看了就麻烦了,弄不好就把这小说拉下来了,还是放在二等奖吧。他们就把我的小说放在二等奖的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把我的作品埋在里面。
蔡:我们刚才谈到《铺花的歧路》经过了一番修改,小说结尾,主人公没有自杀,在沙滩上犹豫着,终于被爱情的力量拉回来。这样,确实有更值得回味的东西。
冯:茅盾是个作家,他给你提问题,是贴近你的作品和人物提的,是从艺术上提的,而跟任何政治上的要求没关系。
好作品习惯给《收获》·搞现代派·自由的状态
蔡:你的作品主要刊登在哪些刊物上?
冯:我的小说绝大部分都给了《收获》,都是中篇。个别的也有给别的刊物的。但是主要的,比较重要的,都在《收获》上。
蔡: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还有像《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短篇《炮打双灯》,有一个散文,写冰心的,叫《致大海》,我读了之后很感动。看来你的重要作品确实大多在《收获》上发表。
冯:我都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好的小说,只要是写得不错的,我一般都给了《收获》。要是给了别的刊物,作品本身好像也觉得不对劲。另外,写完以后,只要觉得这个作品好,我马上就想到了《收获》。而且,散文只要写得好,我马上就想到给《文汇报》的笔会。我觉得,我好像跟这一报一刊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这主要还是跟人接触的关系。跟小林,跟肖关鸿,有关系,他们的气质很好。他们的人格都很好。他们的思想立场、他们的艺术眼光,都非常好。好像好朋友一样,我写完了,就愿意给你看看。有时候很长,肖关鸿宁愿用整版发出去。
蔡:除了《收获》、《文汇报》之外,你还有哪些重要作品发在其他刊物上?
冯:那都是很零碎的。你比如天津的《小说家》,给过两个中篇,包括《神鞭》都是给它的,编辑的关系比较好。后来编辑调走了,就不再给了。我这人特别私人感情化,编辑要是特别好,我就愿意给他稿子。可能是小林在《收获》呆得长,就一直给她。当然要是小林今后不在《收获》当主编了,也还是会给《收获》的,毕竟和《收获》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的。
蔡:你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收获》发表作品,一直到去年,还在上面发表了两个作品,这种交往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看来已经成了长期的、不可动摇的关系。
冯:要是有一天《收获》真正给关闭了,给停了,那我这只鸟不知该往哪里飞去。
蔡:跟你联系比较多的就是李小林吗?
冯:我就跟小林一个人联系。我在别的刊物也发过一些不错的,比如《上海文学》,发了我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我跟周介人的关系很好。因为我当时在《上海文学》发过一篇《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最早我们几个人,还有李陀,搞现代派。去年我在法国住了两个多月,正好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媒体都说,高行健最早是现代派,问和我、李陀的关系如何?后来张辛欣在美国还说,高行健的事情,你们不知道的可以问冯骥才和李陀。好多人还跑来问我。当时我们搞现代派有两个想法:一是希望艺术上有一个自由的空间,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二是打破教条主义。就是要向教条主义冲击。这里冲不了,就向那里冲,拼命要把它冲开。那一代作家很有精神,比现在的作家有责任感和精神。现在的人有时很轻视责任感,觉得责任感是给自己背了个十字架,觉得完全可以不这样。但是,要是没有这种精神,你的作品不可能有大的激荡。那时候非常自觉。
蔡:你不仅是个作家,而且还是《文学自由谈》的主编,根据你的体会,你觉得一个刊物的主编或者主持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冯:我觉得眼光、视野非常重要。对作品的眼光,对文坛的看法,对稿子的选择,还有理念。现在刊物太多了,你要想刊物跟别人不一样,要从理念体现出来。只能别人去学你,但你不能学别人。《文学自由谈》强调几条非常清楚:第一,只谈不论,不要论的东西。论的东西交给《视界》,交给《读书》,交给《当代作家评论》。我们只谈,更自由的方式。但它又不是随笔。它有时候几乎就是一次谈话,更轻松、更自由。这里面可能有非常多的锐气,用论很难到达的。有些擦边的东西就可以错开。比如我们上一期发了一篇关于骂那些对高行健作品批评的文章。我们今天这个刊物的待遇,一般作为理论的东西,在其他刊物可能很难发表,可能要惹麻烦,在我们这里一点问题没有。说白了,你说实话在我那里有一个好处,因为我的特殊身份,我是非党人士,比较自由一些,谁也不好太怪罪于我。另外,我希望能够把文学评论或者文艺批评写成一些比较自由的文章,一种比较自由活泼的方式,就是解放文学批评文体。这是我的想法。现在的批评文体跟我们古代的不能比,而且太模式化了。模式化限制了我们的思想。人所做的一切最后都限制了自己,我们要不断解决模式问题,实际上就是不断解放我们自己。要把批评文体解放出来。所以《文学自由谈》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我说的是开玩笑的话。但是,我说,可以用自由的方式。另外,我非常主张文章。我觉得中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文章写得很漂亮。写文章很漂亮,就是行文很好,非常讲究文字。现在人运用方法的能力差多了,可能是因为欧化的关系,可能是我们的思想跟西方交流,我们被同化了。思维被同化了,造成我们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也有可能被同化的迹象,有时候不太讲究单个字的运用。去年我写了个小说《俗世奇人》,我就非常注意单个字的使用。每个字很讲究,但它不像写诗那样讲究。又要让它口语化,这做起来非常难,看起来很舒服,很流畅,其实做起来非常难。我主张《文学自由谈》里的东西,不像写随笔这样那样做文章,又要让它口语化一些,有时候非常见灵感,有时候又有锐气,也有很好的思想片段。对我来讲,有影响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整个的理论所完成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片段的思想,很漂亮有灵性的片段,有创造力的发现,对人也有影响。我有时候很主张刊物往这一方面倾向。所以,刊物给人感到很灵动。也有一种看起来没什么意思,翻一翻又感到很有意思。就像我们在溪边走,忽然一看很漂亮,再认真看,也很平淡,就那样的感觉,一种很自由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文学自由谈》有三句话:文学自由谈、自由谈文学和文学谈自由。实际来讲,最后想达到的目的还是自由,就是一种自由状态。因为我不可能什么都解决,因为我们不是当权者,我们也不是执政者,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文章、文风、文化行为来影响人。我觉得给人的影响是一种很自由状态。就像我去年在德国演讲的时候,大使馆里一个人问我对余杰怎么看,对王朔怎么看,我说,他们最积极的意义就是给文坛多一点空间。我说,如果他们没有,那么空间就小一点。别的意义谈不上。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这样,他给文坛带来的意义远远大于他的作品本身的意义。他们属于这样的人。
接巴金衣钵的人·视野和眼光·思辨历史
蔡:你跟《收获》的关系非同寻常,跟《收获》的李小林交往尤其密切,那么请你对李小林做出评价。你认为《收获》的主持人李小林是个怎样的人?
冯:我觉得一个好的刊物,真正是我们说的文坛上最重要的刊物,实际上它自己的历史就是当代文学的历史,它自己的作品也应该是当代文学的一种选本,我觉得《收获》就达到这样的。因为它的选本跟《中华散文》、跟《小说月报》这样的选本不一样,因为它发作品,它的选择是靠对作家的选择,对作者开始的选择,而不是发表完作品之后的选择。一开始你没有很宽的视野,你就是这些作者。它需要什么?我觉得它需要非常好的眼光。李小林有很好的眼光。首先,这个人的思想立场很纯正,我很敬重她。她可能受巴金的影响太深了。我觉得她是一个接巴金衣钵的人。真正接巴金的思想和精神衣钵的人是李小林,而不是别人,不是哪个作家。我对巴金这人很敬重。我很敬重他一点是,他从来不到作协去领各种费用。我有时很固执。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当天津文联主席,我到现在坚持一条:我所有出差的火车票、飞机票、各种费用,我除了工资以外,别的钱我一律都不拿。我自己定了一条:我出差住旅馆,坐飞机、坐火车,打电话,我所有出差的钱,我从来不向他们要。因此,我很敬重巴金。爱屋及乌吧。我觉得李小林是一个真正接巴老衣钵的人,思想非常纯正。她有很强的文学敬业精神。她的气质、素养都很好。她对稿子非常认真。我只要给她一篇稿子,很大的麻烦就是她不断地要来电话。她很严格,跟一般的编辑不太一样。一般的编辑,你给他稿子,他如获至宝,而她就认为一个字不能错的。李小林是不一样的,她非要和你讨论,大段地给你提意见,甚至还要建议你修改,她的意见,有些我觉得非常好。她的这一套程序很严格。
蔡:你所有的作品都是李小林做责任编辑?
冯:她给我做三审。一审、二审、三审,到最后,都是她。
蔡:她在你的创作中还起过哪些作用?
冯:我经常跟她通电话,聊个天。我现在给她稿子并不多,因为我做别的更多。这两年我对城市比较感兴趣,这些跟《收获》没什么关系。平常跟她打电话,谈谈一些想法。有些稿子不合适的,我也不给她。因为我知道李小林要哪一类稿子。
蔡:她要哪一类稿子?
冯:小林要的是纯文学的稿子。小林比较偏严肃的,太诙谐幽默的东西没法用,跟她的气质不相符。有时候我写得太幽默的,我就得考虑考虑,但《俗世奇人》,我还是给她。因为我在《俗世奇人》的文字里也讲到了,她肯定能看出来,我相信她有眼光。所以,李小林很不容易,因为各类的小说她都要能看到。她有时看到我这类稿子,有时看到棉棉的稿子,各类她都能看,或者是余华那种。每个人都不一样。另外一些大作家的稿子她也退过,但李小林没有跟我退过稿。
蔡:去年《收获》开辟“走近鲁迅”专栏,你那篇《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引发了一场较大的争论。请谈谈你创作这篇文章的背景。另外编辑部是怎么跟你谈他们的设想的?
冯:“走近鲁迅”,李小林早就跟我谈过,她希望我写一篇。我早就跟她说过我对鲁迅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对鲁迅的“国民性”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写《神鞭》、《三寸金莲》的时候,想的就是“国民性”。《神鞭》,我想写的是国民劣根性中顽根的那一面,劣根里面本身还有顽根的一面。《三寸金莲》里面,我想写中国文化的顽根,再往深处找找,就是中国文化是要把一切畸形的、变态的东西都强加给人变成一种美。它变成一种美以后,你就很难再打破它的规范。比如,这个脚,它把一种天然的东西变成人为的,通过人为的,把它强加给你。最后,它把它变成一种变态的东西,但是它还说是一种美的。然后你也认为它确实是美的,那么你就难以再走出来了。就像“文革”期间,我们确实认为那时候很辉煌很伟大,我们走出来很痛苦啊。为什么说“文革”厉害?它是两极拥有,它既把人的卑鄙的丑恶的自私的调动起来,它把善良的忠义的勇敢的也调动起来了。它在两极都占有,你逃不出去的。三寸金莲本身是中华民族灵魂的象征。它把脚缠成那个样子,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美的,必须要遵循。所以中国人最痛苦的是放脚的时候而不是缠脚。放脚是全民族的痛苦,它挣脱不出来。改革的时代特别像放脚那样,所以我写了《三寸金莲》。直到现在,还是有人没有看懂,还是说冯骥才喜欢缠脚。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真是太笨了。而且我们的文化批评界也是太笨了,都没有想象力。我觉得文艺批评最关键的是想象,你对作品的想象。你连作家的想象都到不了,你的作品更没有想象。所以,我一直关注鲁迅的国民性,但是国民性的来源是有问题的。后来我又读了很多翻译过来的著作,关于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的影响,特别近代史那一段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传教士这一段。因为天津这个地方很像上海,面临着西方的东西。西方人的东方观,我也比较关注。包括张艺谋的电影,张艺谋的电影背后有一种强烈的西方人的东方观。我说张艺谋陷到西方人的绝对背景里,张艺谋不是有意识的非要陷进去,他是为了在西方获奖,他的这种目的非常明确。因为他在国外拿了奖,在中国他才威风。有这种比较浅的意识,最后就被西方人拉走,陷入到他们的东方观里。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原点上去,看鲁迅的国民性是怎样产生的。鲁迅是伟大的,因为他要唤起中国人觉醒。但是鲁迅同时又有个问题,他跟毛泽东一样,他的马列主义是从外边拿过来的。所以鲁迅当时拿来的东西是从传教士手里拿过来的。因为鲁迅想看当时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他想解决问题,他想斩断古老的精神锁链,但他的思想武器从哪里来?正好西方提供给他一个传教士的角度,这个角度他发现的是对的,那确实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国民共有的一种文化性格。但是鲁迅拿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把西方的问题掩盖了。所以,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讨论一下。那应该不应该叫做对鲁迅的批评呢?我认为应该。但是什么叫批评呢?我认为批评就是一种思辨。我这是对鲁迅的思辨。与其说是对鲁迅的思辨,不如说是借鲁迅来思辨历史。
蔡:你的用意并不像外面争论的那样,说你是对鲁迅的否定。
冯:我觉得那太幼稚了。还是那句话,现在中国人太没有智慧了。我这里充满了对历史的思辨和文化判断,充满了哲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的东西。他们都没有看出来啊。太幼稚了!那真是一种无聊的狭隘的浅层次的东西。我根本没法说话了。不在一个量级上。
蔡:这种情形下,沉默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实际上,从你文章的语气、内容的全文看,你对鲁迅还是充满了景仰之情的。你也不过讲出了你的一些想法,你是在探讨一种精神根源,与否定鲁迅,与所谓的贬鲁根本不一回事。没想到你的用意,《收获》的用意,竟会这样被扭曲了。《收获》原本打算把“走近鲁迅”多开一年,也难以再进行下去了。我们的文化批评界还是有一种极不正常的心态存在着。
冯:就是国民性产生的思想原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找到以后,实际上是想认识西方人的东方观,这对我们的现在很有意义。我们先不说这种功利性的一面,从更深远的意义讲,就是思辨意识,我们要把这个混乱的历史给理清了。至于对鲁迅的评价,这是另外一个事情。说实在的,鲁迅已经有评价了。就是有了评价,我们也可以拿出来重新讨论。人就是这样,有时候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人为什么活着,最简单的问题,有时候你要拿回来重新想,要拿出来想清楚,不要稀里糊涂到老了,人为什么活着最后忘了。可能小时候还想清楚了,老了反而忘了。所以有时候要回来重新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鲁迅伟大,究竟在哪儿?也许我们原来认为的鲁迅伟大恰恰是错误的。
蔡:你的想法我可以理解。只是批评界的某些人设置了一个先入之见,说你是在否定鲁迅,什么拥巴(金)反鲁(迅),然后把你的想法往他们的圈套里引。我觉得有些滑稽,有点投机,甚至有点卑鄙。我们一碰到鲁迅这样的高大形象也不能进行心平气和地平等讨论,这也影响了我们对鲁迅这个人的理解和判断,实际上也不利于鲁迅精神的发扬光大和深远传播,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冯: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我不理他们。我做好自己的事情。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
文化责任感·保护遗产·自发的“伤痕文学”
蔡:你近年对敦煌文化、对城市古墙旧街颇为关注,而且已经出版了几本书。我想问一下,你写这类文字的意图和构想是什么?
冯:我现在觉得一个关键的问题基本上还是对抗现代化的负面。我认为现在中国人在稀里糊涂的现代化过程中,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破坏得太严重了。所以,我给《文汇报》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化责任感》。我说,我们这些作家,如果讲责任,过去更多的讲的还是社会责任感。但是,我忽然发现,文化自身也面临着危机。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有一种文化责任感。我对敦煌的兴趣是多方面的,跟这个问题没关系,包括对汉唐历史的兴趣,包括对佛教东渐的兴趣,另外对壁画样式的兴趣。我对敦煌的兴趣太广泛了,因为敦煌有太多我的兴趣点。我跟一般写小说的作家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文化兴趣特别多。直到现在,我还在做敦煌轶画的研究。比如敦煌藏经洞被斯坦因拿走的一千件唐宋绘画,我就特别有兴趣,因为这一批绘画的数量远远超过台北和大陆故宫博物院唐宋绘画的数量。所以对这一部分的研究影响了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应该做一个比较。这些具体的暂且不说了。近些年我们的现代化速度太快了,文化受到的危害特别大。从现代化的步伐来看,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它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比如北京的风沙都已经吹到奥迪汽车里了。不能不考虑了。但是没有人考虑,很少有人考虑人和环境。但是,我就想中国这个民族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是个比较实用的民族。我们不是精神至上。
蔡: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缺乏虔诚心,缺乏畏惧和禁忌,这就存在着破坏性和可怕的因素。的确有太多值得我们思索和反省的事情。
冯:中国人没有精神寄托,很可怕。我们没有执著,没有侠气,都没有了。这时候我就想起敦煌早期伯希和从藏经洞拿了东西之后,一九〇七年拿了之后,一九〇八年又回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展览之后,罗振玉、陈寅恪这批人一旦知道中国在西北敦煌有一批五万卷的文书是被西方人拿走了,这批人基本就披星戴月般地奔波,救火一般地想到敦煌,想抢救这批东西。然后像向达、刘半农等这批知识分子都是用自己的费用到法国、英国的图书馆,用毛笔字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一抄就是几百万字。他们基本都住在小破旅馆里,我都去看过了。他们不断地向清政府呼吁,然后用车去把这些东西运回来。奋斗了那么些年,然后敦煌学才建立起来。这批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宋庆龄讲过一句话,中华民族几百年来在中外各种矛盾中没有垮下去,就是每个时代总有一批知识分子活得明明白白。他们是精神至上,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迷乱了。你不觉得问题挺大的吗?知识分子没有赤胆忠心,没有激情,而且没有真诚。太精熟了!
蔡:我觉得都活得像蝼蚁一般的,很可怜。这又怎能希望他们去主动承担责任和使命?
冯:所以,我在抢救天津老墙的时候,那些墙要拆掉,我拿自己的稿费出来,几十万拿出来,请一百个摄影家,整个调查完之后,然后一条街一条街拍照。去年我去抢救天津最早的商业街的时候,那里的文物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结果都捐到博物馆去了。这些人下去,一方面是拍照,一方面是录像,然后一家一户地对原居住民调查这条街的口头记忆。不断地跟政府谈,政府不同意,我就发表言论。最后市委书记火了,指令报纸封杀我,不许发表我的言论。我就在大街上演讲。有一次我给老百姓签名。老百姓有一千三百人。签完名,老百姓都沿街贴上大标语,都要保护我。就这样,把那条街的主要建筑保护下来了。我觉得关键不是保住一两间房子,关键是用一种文化精神启迪和影响一代民众,让他们有文化遗产。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文化遗产,城市是供使用的,没有精神价值,不享受城市的文化精神。我们跟巴黎人没法比。巴黎是只修不改的城市,两百年的房子不动。他们享受这座城市。我们是乱拆一气,都让那些官员们发了财了,让他们显示他们的政绩。每个城市都夸耀自己的好,实际上都为显耀他们的政绩,为他们升官发财。你别到处光破不立,只是为显示自己的政绩,老百姓实际获利不多。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示我们每个知识分子的价值。知识分子有两个价值:一是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最有价值的意见都是不同的;还有一点是知识分子的前瞻性。
蔡:你谈到这些,我想起读了你的作品的感受。我觉得你的作品当中包含了两种情怀:一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强烈关注,表现出对宏观历史事件和现实境遇的人文关怀;一是对民间气息,对世俗百象的体味和通达,体现出一种形而下的感悟。前者如对“文革”的反思,对鲁迅的国民性的文化思考;后者如《神鞭》、《阴阳八卦》、《俗世奇人》那样,充满了鲜活灵动的民间生机与活力。当然,有时,对宏观的考察、对文化的思考与对百姓人生的咀嚼、对民间气息的理解是融为一体的。《三寸金莲》之类的作品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挖掘出深刻的文化命题,《一百个人的十年》也是从普通人的视角来反省民族的悲剧这样的大问题。
冯:很感谢你。你说得很对。文化学中年鉴史学派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地域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就会形成一种心态。过了一个时期,心态就消解了,变成了另外一种心态。比如上海三十年代有一个心态,现在人虽然很迷恋上海的三十年代,但现在的心态已经跟三十年代不一样了,是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上海三十年代的心态只有在三十年代表现最强烈。小说家主要是写人的,可以用一群人来记录时代的心态,从历史的横剖面来记录整个时代的集体的文化性格,通过这些人物的性格来认识时代的特征和人物的所想所为。现在的时代没有民间英雄。因为所有的民间英雄都被劳模化了。他们被硬性规定为劳模了,没有民间的英雄了。我写的小说时代,民间里有泥人张,有绝技的;有霍元甲这样的人物。街坊、邻里都住着各式各样的奇人。老百姓都很崇拜他们。他们都有自己的尊严。这种社会充满了活力。但是我们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我们还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往往一个人好,非把你弄成很糟不可。马俊仁不是出成绩了吗,最后舆论各个方面非把你弄得一塌糊涂不可,直到把马俊仁弄臭了为止。没有英雄的民族,就是没有精神的民族。
蔡:你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几乎一开始就选取了对“文革”的否定这样的题材,很自觉的,充满了激情,这是虚构的小说;另外,你还专门用纪实、实录的方式,写下了《一百个人的十年》,仍然继续对“文革”进行清算、清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文革”题材如此感兴趣?你的精神资源是从哪里来的?
冯:首先,我是“文革”的一代。“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二十四五岁。“文革”结束的时候,我是三十五六岁。我的成长期主要是在“文革”里。所以,我承受了“文革”的苦难。而且,我也目睹了“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变化,太剧烈的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民族几代人都在“文革”里面滚动着。我刚才讲了,“文革”利用了我们民族所有的劣根性,也利用了我们民族所有的优长。从文化的层面讲,“文革”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利用了。我觉得最伟大的统治者就是能够利用一个民族的弱点。但是,“文革”把优点和弊端都使完了。从文学本身来讲,“文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舞台和一笔财富,实在是太丰富了。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写出一部真正更深入的反映“文革”的作品。我还有一个使命。我应该再写一部长篇,写“文革”。因为我正是“文革”的经历者。如果我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才十几岁,我可能看得没那么透彻。我那时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已经看了很多书了。结束的时候,我三十五六岁。现在我不到六十岁。这样的经历,我应该把“文革”写出来。我一直在想,怎么写,从哪个角度写。我是“文革”的受难者,而且是在“文革”中开始从事文学的。那时,我是秘密写作的。我压抑得很强烈。我的文学创作跟“文革”紧紧关联。另外,我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特别提到过巴老的“文革博物馆”。我觉得,中国最应该建立的是“文革博物馆”。历史的灾难可以变成财富。我们现在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最大的历史灾难变成最大的财富。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对“文革”都回避了。我现在觉得“伤痕文学”运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文学史里面是非常独特的,它没有任何拘束,没有任何官方的因素。那时官方躲在一边,让你自己爆发的,跟“文革”刚开始的情况完全一样。“文革”刚开始也是官方躲在一边,让你自己爆发,形成一种力量,然后把刘少奇冲垮了。“伤痕文学”刚开始,官方也躲在一边,一爆发把华国锋给冲垮了。冲垮了之后,需要收拢,“改革文学”就出来了,《乔厂长上任记》出来了。所以,我说《乔厂长上任记》是“伤痕文学”的反动。因为《乔厂长上任记》最投官方的主旋律的胃口,官方的权利把整个的“伤痕文学”都导入政治的轨道上去了。“伤痕文学”就夭折了。但是,在那个短暂的时期,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能量,而且显示了文学的批判功能。所以,不要谴责“伤痕文学”粗浅,都是控诉。“伤痕文学”可不是一个被政治利用的东西。尽管政治需要这个东西,但它是民间自发的。所以,“伤痕文学”的价值,我们远远没有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