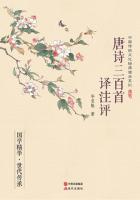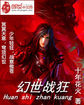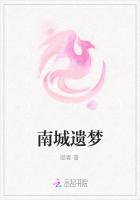一、 现有学科理论的缺憾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法国学派。法国学派是以实证性的影响研究为其基本特征的,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是法国学派最根本的特征。法国学派奠基人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要使比较文学研究落到实处,就必须加强实证性的科学精神。梵·第根也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而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声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
法国学派的学科定位是摆脱随意性的比较,追求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比较文学的研究是在不同的国家文学体系之间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建立的是以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三大理论为主的研究大厦:流传学研究的是一个文学现象在另外的文学体系中获得的影响与传播的状态;媒介学研究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影响得以形成的中介方式;渊源学是在起点不明确的情况下所作的研究,是追本溯源的研究方法。可见,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是实证“关系”,而不是“比较”,属于文学外部的研究。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二阶段是美国学派。美国学派倡导“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实质上就是丢弃“比较”,而只谈“关系”。美国学派恢复了曾一度被法国学派丢弃的“比较”,打破了法国学派强调的事实联系的自我限制,将没有实际影响与关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以及艺术、宗教、历史和哲学)之间进行比较。它重点关注的是文学性,即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价值与规律,所以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它用文学的美学价值取代了法国学派倡导的文学实证性的影响关系,突出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是既重视跨国也重视跨学科的特点。
目前,几乎所有从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都以为,有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就是一座完美的大厦。事实真的如此?研究结果证明,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即使有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我们仍然不能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
首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他们是求不同中的同: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这种“求同”的理论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比较文学的基本事实和客观规律。因为法国学派所强调的以“国际文学关系”为核心的“影响研究”,其变异性要大于类同性。即便是在美国学派强调的以“类同性”为共同规律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变异现象。
我们承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同源性”、“类同性”是“可比性”的基本立足点,但我们要郑重提出,变异性、差异性同样具有可比性,而且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立足于差异性这个基本点而提出来的。变异学探讨的是完全差异的对象是否存在可比性的问题。变异学的根本理论认识是,异质性也是可以比较的。同源中包含了变异,因为同源的文学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和文化层面都会产生变异,这就是异质性的体现。事实上,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求“异”的问题。然而“异”是两个学派都没有注意的重要问题。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都没有从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对异质性和变异性加以考虑和总结。
二、 影响研究的特点与面临的困惑
法国学派提出比较文学就是研究国际文学关系史,坚持实证性的科学精神正是法国学派的突出个性,但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也同时包含变异的问题,因为当一国文学传到另一国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
实际上,国际文学关系的两大支柱应当是实证与变异,也就是实证性的国际文学关系与变异性的国际文学关系。对于实证研究,我们可以作如下分类:诗歌的实证关系研究、小说的实证关系研究、形象学的实证关系研究。对于变异研究,我们也可以作如下分类:翻译的变异研究、语言的变异研究、接受学的变异研究,等等。
在法国学派的研究中,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只突出了实证性的一面,即只注重研究存在着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而忽略了变异性的一面。法国学派不但回避谈论审美判断与平行比较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在影响研究中存在着的变异。这是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两大缺憾。其中,放弃“比较”,忽略文学审美的缺憾,被美国学派所弥补,而变异性的缺憾至今仍未解决。
法国学派提出国际文学关系时,一直强调实证性和科学性,但是在具体从事影响研究时却遭遇了很多无法实证的困难。比如,运用实证方法就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而且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经提到了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这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的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有能够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表面注重的是有事实关系的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其实早已突破了实证性的研究。卡雷于1947年出版了《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 1800—1940》(巴黎布瓦文出版社出版)。他的学生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设置了“人们眼中的异国”一章,借以专门讨论形象学问题,这是最早的一部对形象学研究进行确认的概论性著作。卡雷与基亚的努力,使得法国学派打开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那就是他们直接进入了对“形象学”的研究,但是他们依然不承认“形象学”是非实证性的。可事实上,法国学派确实是在运用实证的、科学的方法从事着非实证、非科学的对象性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是不属于法国学派所倡导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畴的。
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形象学应该属于变异学研究范畴。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以形象学研究的“词汇”、“套语”为例,中国人将美国人称之为“美国佬”,将日本人称之为“日本鬼子”,这些就是中国人对美国人、日本人的集体想象的体现。正因为它是一种变异性的集体幻象,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集体想象,而非实证性事实,所以产生变异是必然的。变异学中的形象学对想象的强调,从“再现式想象”上升到了“创造性想象”层面,也就是说他者的形象不是再现,而是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混合而成的产物,客观存在的他者形象已经经历了一个生产与制作的过程,是他者的历史文化现实在注视方的自我文化观念下发生的变异过程。
可见,在文学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的因素的作用下,被传播和接受的文学会发生变异。如果说影响研究根本目标是求“同”(可实证的同源性),那么变异学研究探求的基本特征就是“异”(不可实证的变异性)。变异学追求的是同源中的变异性。
三、 平行研究的特点与面临的困惑
目前,很多比较文学概论教材都认为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发明的,准确地说应该是美国学派恢复了平行研究。对此,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法国学派否定了平行研究,认为“平行”不是比较文学,凡是不涉及“关系”之处,都不是比较文学,“比较”的方法被后来的美国学派所恢复。
第二,美国学派提倡平行研究的原因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是讲究审美性的。法国学派仅仅强调文学外部的实证性研究,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性特征,这直接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非审美性。文学研究中必然伴随着审美性因素和心理因素,而这是实证性关系研究所无法证明的,这个缺憾恰恰被美国学派弥补了。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一方面比较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同;另一方面是将文学与诸如艺术、宗教、哲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作比较。当然比较的两者必须具备可比性,从中总结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学发展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
第三,美国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有比较诗学、类型学、主题学、文体学和跨学科研究。主题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相同主题的不同处理,它研究的范畴包括母题研究、情境研究和意象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平行研究中包含主题学,影响研究中也包含主题学,这种现象体现了平行研究中也必然包含变异关系的研究。
第一次在比较文学史上提出“主题学”术语的是法国比较文学家哈利·列文。他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的重要建树是“主题学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法国学者保尔·梅克尔于1929年至1937年间编辑了一套主题学丛书。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韦斯坦因在其专著《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单独开辟了“主题学”一章,弗朗索瓦·约斯特在其专著《比较文学导论》中详细地论述了主题学。
主题学到底是属于影响研究还是属于平行研究?事实上,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既含有影响研究注重文本外部关系的因素,也含有平行研究注重文本内部审美性的因素。所以,平行研究中的主题学、文体学等研究内容,也是属于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
美国学派并非完全排斥影响研究,它批判的是对文学进行纯粹的实证考察,主张应该将实证研究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结合起来。何况,两种研究范式在某些内容上是呈交叉状态的,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就是为何在美国学派的主将韦斯坦因和雷马克的著作中,都有对影响研究的阐述。
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只讲文学关系,美国学派恢复了比较,表面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似乎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已经出现了困惑,使得体系出现了不完满之处。具体表现在:有人提倡比较文学无边论,又有人提倡比较文学应该有边界。比如,韦勒克等人就提出什么都可以用于比较。在他们看来,比较文学、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等都是注重研究审美性的,比较文学就是探讨全人类文学的共同审美性。它可以跨越很多边界,包括文明的边界,从而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文学,以至于韦勒克认为可以将比较文学边界无限扩展,甚至可以直接将比较文学改称为“文学研究”。因为这些都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探讨人类共同的文学规律。正如韦勒克所主张的,“将全世界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语言上的区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去“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可见,他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学科边界,成了比较文学无边论。与此相反,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应该有学科边界,而且韦斯坦因也认为跨文明的比较是不可能的,不应该将比较文学的边界扩大。对此,韦斯坦因批评道:“我以为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在领域的力量。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不是不够,而是太大了。”韦斯坦因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研究的对象会过于庞杂,何况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太大,无法进行追求类同性的平行比较。显然,无论是韦勒克还是韦斯坦因,他们的主张虽有差异,但都在比较文学的“求同”之上进行研究,这证明了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的。
从“求同”的思想意识出发,不管是韦勒克还是韦斯坦因,都没有认识到比较文学的变异性实质。美国比较文学界两种对立的观点反而揭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面临的一个危机,而这种危机美国学者却恰恰没有看到:那就是只注重求同。韦勒克是主张“大同”,即全人类都可以“同”,而韦斯坦因只承认“小同”,即西方文化的“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异质与变异性。
美国学者之间的论战,反映出的核心问题有:其一,他们走不出比较文学“求同”的思维模式;其二,欧美学界的某些前沿理论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塞义德的《东方学》一书,就是从差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他阐述的道理是西方人研究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这个运用学理方式加以研究的观点,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的话语霸权导致的结果,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很明显,塞义德并没有从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来深刻地认识这点,而更多的是从话语霸权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他认为,是西方的话语霸权决定了西方处处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东方,他没有认识到东西方文化是存在异质性的,也就是说,双方既有可通约性,又有不可通约性。这是西方以塞义德为核心的学者们对东西方文明差异性问题认识的局限性。
四、 变异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
以上例子说明了,美国学者在运用平行研究看待问题时往往会忽略异质性的问题,这使得比较文学面临着危机,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存在着重大缺憾,即缺乏变异学理论的指导。
一般情况下,比较文学学者不会想到一个问题,即平行研究中也存在着变异问题。因为,我们在通常情况下所讲的变异是影响研究中的变异。但是,当我们进行平行研究时,两个毫不相关的对象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相汇了,双方的变异因子从交汇处产生了,这就是平行研究中的变异问题。不同的文明在碰撞中产生变异,这种变异涉及了文明差异的交集。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平行研究中的变异,最根本之处是体现在双方的交汇中,是文明的异质性交汇导致了不同文明文学的变异。
平行研究中的变异,突出之处体现在话语变异上。可以说,中国与西方原本都有一套独立的文学话语体系。比如,以浪漫主义为例。湖畔派诗人提倡的浪漫主义,注重的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正如华兹华斯所说,“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味的情感”。华兹华斯在《写于早春》这首诗中这样写道:“穿过簇簇樱草,在树阴下, /长春花已把它的花环编成; /我有个信念:认为每一朵花/都在欢享空气的清新。”柯勒律治在《查木尼山谷日出颂》中赞叹道:“啊,高峻的布朗峰! /阿芙河、阿尔维伦河在你山麓下/咆哮不停;但你,最威严的形体! /高耸在你沉静的松海当中, /多么沉静啊!在你的周围和上空。”这两首诗赞美了充满欢乐的大自然以及诗人对自然界一草一木的感受与爱怜之情。从这两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浪漫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和诗人的主观想象力。若以此浪漫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中国的古代诗歌基本上都可归入浪漫主义范畴之内,因为中国的古诗都是重情的,都是“发乎情”的。正如白居易对诗的定义,“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但事实上,中国诗并不是浪漫主义可以完全概括的。所以说,被冠之以“浪漫主义”的所谓中国浪漫主义,绝不是西方提倡的浪漫主义。一种事物从一个国土传播到了另一个国土,必然会生成新的事物,这就是变异。也就是说,西方话语进入到中国,虽然其主要架构仍然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但在中国国土上,这种话语已经产生了变异,已不再完全是西方的了。比如,“禅宗”已不是印度佛教,而是印度话语与中国话语结合后发生变异的结果。
对文学作品而言,“理论”就是一个“话语”,文学理论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换句话说,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总结出的基本规则,再用这套规则来指导文学创作。关于“话语变异”,我们可以引进塞义德“理论旅行”的观点来加以说明,也就是说一种文学理论话语从一个国家“旅行”到了另一个国家以后会产生变异。当代的“理论旅行”基本上是从西方到东方,东方基本上是在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西方的理论话语到了中国以后,产生了两方面的话语变异:一方面,在知识谱系上,西方文论几乎整个地取代了中国文论。现当代的中国学术与文学研究几乎都是照搬西方的文学和理论,导致我们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都是西方式的。新时期,中国极力地引进、介绍西方的文学和理论,海德格尔、卡夫卡、哈贝马斯等西方文学家、理论家几乎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中国学术很难有自己的创新。渐渐地,我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处于“失语”的状态了。我们没有站在自己的话语方式的基点上对西方文论进行为我所用的改造,而是全盘照搬西方文论。另一方面,西方理论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问题。西方的文论话语必须与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相结合,我们应站在中国学术规则的立场上选择性地、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才能真正地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论话语的“失语症”现状。要理解“西方文论中国化”,首先应注意文学理论的“他国化”。由于面临不同的文化背景与语言翻译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具有某些中国色彩。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就必然会面对一个吸收、选择、过滤、误读与变异的再创造过程。其次,要使西方文论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就需要西方文论自身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学术规则和话语言说方式相结合,加快中国文论自身的创造力。
西方文论的引入导致了中国文论的整体“失语”。自从我在1995年《东方丛刊》的《21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一文中提出“失语症”的问题后,就引发了学界长达10年的论争。对“失语症”的认识,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我们需要重申一下“失语症”的两点内涵:其一,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失落;其二,汉语文化现象本身的现代转型。事实上,“失语”也属于变异的范畴。“失语”是一种现代性变异,即中国理论自身的变异。“失语症”是中国文论追寻现代性的一种症候体现。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变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古代文论的现代化努力。古代传统文论在现代性文论面前失去言说自我意义的途径,所以古代文论呈现出了在西方现代性文论中的被动转化和在自我传统文论基础上的积极建构。第二是现当代文学艺术整体否定了古代文论的意义建构方式,而整体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话语范式。现当代文学艺术所呈现出的这一趋势就是现代性的变异。第三是以西方文学范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这种解读方式造成了对古代文论真实意义的曲解。第四是全社会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多重否定。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语言的变革。中国古代文论素有“言不尽意”的话语言说方式,但从20世纪初语言发生变革,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人们在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接触中逐渐淡忘了自身的话语模式,使得我们对中国传统经典文论的品读渐趋陌生。
另外一种话语变异是中国文学理论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出现的“激活”问题。也就是说话语在变异中被“激活”后会产生新的东西,这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这种“激活”是在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启发下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再发现,也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和承续。首先,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其次,从中国文化特征入手领悟本土传统文化典籍的精神特质。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西方文论的碰撞中站稳自己的脚跟。最后,在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中国文论应以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来言说当今的学术问题,展现中国文论自我的魅力。这正是话语言说的创造性的体现。
可见,中国文论话语要实现现代性重建,就要在坚守中国传统文论话语言说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和融会西方文论的精髓,才不会让西方文论话语成为中国文论意义建构的方式,达到本土与他者的良好结合,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
比较文学话语变异最典型的个案,就是中国学者提倡的“阐发法”。在整个当代中国,学者们都形成了一个基本思路,即用西方文学理论(或是西方话语言说方式)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与西方理论都产生了变异。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西方理论改变了中国文学。比如,用浪漫主义解释《诗经》,解释李白、屈原等;运用现实主义解释杜甫、白居易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得中国文学产生了变异。其二,西方理论在与中国文学的交汇中也发生了变异。比如,我们在运用西方的浪漫主义阐释中国诗人李白、屈原时,西方的浪漫主义理论也发生了变异。在进入中国之前,西方的浪漫主义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讲述的浪漫主义为准,强调诗歌表达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这在前面已有所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而中国在讲述浪漫主义时则更突出它的理想、夸张等方面的内容。可见,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二者在碰撞中都产生了变异。整个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都是在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的文学作品,它既使中国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变异,也使西方的理论产生了变异。中国文学理论自身产生的现代性变异包含了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其中积极意义是变异成为两种异质文明“杂交”的前提。
当代学者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认为西方文论具有普世性。我们认为,西方文论确实有自己力所能及之处,但也有自己力所不能及之处。前一种认识体现了西方文论的普世性,后一种认识体现了它的不可通约性。但是,“阐发法”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中西文明的碰撞,碰撞的结果正如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提到的,“对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之间不同的信仰、假定、偏见和思考方式,给予适当考虑之后,我们必须致力于超越历史和超越文化,寻求超越历史和文化差异的文学特点和性质以及批评的概念和标准。否则我们不应该再谈论‘文学’( literature),而只谈分裂的‘各种文学’(literatures);不谈‘批评’(criticism),而只谈‘各种批评’(criticisms)”。负责翻译此书的杜国清这样评论:“在谈论文学时,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将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而只能谈论个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
可见,“阐发法”是自觉地意识到了差异性,并且主动地、有意识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种自觉的异质文明之间的互相阐发。它是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作品,同时用中国文学作品来检验、校正西方理论。“阐发法”成为中国当代变异学跨文明研究的第一个突破,也是跨文明研究从自觉的、异质角度出发的突破口。
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就是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下催生出来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结果。文明冲突中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大于共同性,而异质性与变异性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表现形态,也是跨文明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异质性是跨文明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变异性在跨异质的文化中也是存在的,在跨文明研究中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限于篇幅,此不赘述)。所以,在“求同”思维下从事跨文化研究是会面临诸多困难的,而变异才是现今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该着重研究的内容。
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包括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和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六个方面。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科支点是变异性与文学性,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在交流中出现的变异状态,它重点在求“异”。例如,文化过滤是指在文学的交流与对话中,接受者因为自身文化背景的因素而有意无意间对传播方面的文学信息进行选择、删除、改造和移植的现象。文化过滤就是一种文学变异的现象,而由它所带来的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则是文学误读。
我们说,在尊重法、美学派的学科理论时不得不重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整个比较文学学科是缺乏变异性研究的,而文学变异学研究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是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比较文学变异学弥补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重大缺憾,开启了一个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尤其是开启了跨文明比较研究的新历程。因为,在人类文学史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学新质,也使得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得以凸显出来,而不同文明的比较、对话与交融,将是人类文化交流的更高阶段。
在此之前的所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是从求同性出发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了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现在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变异学”。变异不仅仅是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较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更是一种文化创新的重要历程。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将对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新华文摘》2008年第5期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