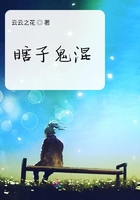从昨天开始,汪精卫就神经不安,心绪不宁。有时候,胸口好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难受,喉咙好像喘不上气来,心跳得很慢,简直像要寿终正寝似的。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病,是习惯性的心情悲痛到了极点所致。每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变得十分暴躁,肝火特别旺,动不动就发脾气。
早饭后,他像骨头散了架似的躺在睡椅上,对陈璧君说:“你打电话告诉春圃,要他通知在京的常委来我这里开个会。”“开常委会研究什么问题?四哥!”陈璧君是中央监察委员,又是他的第一夫人,她有权过问。“研究为我开追悼会,我要死了!”汪精卫大发无名火。陈璧君怔了片刻,知道丈夫心情不好,强忍着任性的脾气,勉强笑着说:“何必这样呢?四哥!我了解一下会议性质,好让春圃通知常委携带有关情况到会呀!”
“什么都不带,只带屁股,带耳朵,带嘴巴!”汪精卫还在生混账气。陈璧君痛苦地摇摇头,心里沉沉地走向电话机,给陈春圃打电话。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八个常委除了任驻日大使褚民谊、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陈公博以外,在南京的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杨揆一、何世祯先后赶来了。他们熟知汪精卫的夫妻生活习惯,知道每月的上半个月他与陈璧君住在一起,都驱车来到汪精卫官邸的东楼小会议室。徐珍以汪精卫的秘书身份列席常委会,中央代理秘书长陈春圃也列席参加。
“今天开个常委会,讨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南京国民政府还能够维持几天?”汪精卫满脸忧悒神色,说话粗声粗气,说到最后两个字特别加重语气。说完,脸色冷如冰块。
他的话如同一颗残酷的炸弹爆炸,震得大家的脑袋发麻,心脏发颤。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知说什么好。一个个像受了惊的牡蛎那样把口闭得紧紧的。房间的气氛好像一阵惊雷过去,显得格外寂静。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希望陈璧君和徐珍发言。陈璧君能说什么呢?她把丈夫刚才说的话与那句“开追悼会”联系起来分析,只知道他很烦躁,但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她感到眼前的一切都仿佛是一张曝光不足的照片,慢慢变成了黑乎乎的一片。徐珍呢?已经十天没有与汪精卫在一起生活了,她对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有种陌生感,还有点不安和胆怯,犹如一个上了舞台不能立刻进入角色和意境的蹩脚演员。
不知是受既得利益驱使,还是为了感恩戴德,平日不大发言的何世祯倒首先开了口。他说:“大凡伟大人物都善于警钟长鸣和防患未然。这正是委座的伟大之处。依愚见,委座的话绝不是泄气,而是鼓劲,绝不是打退堂鼓,而是吹冲锋号,是要我们正视现实,战胜困难,迎难而进!”他瞟了汪精卫一眼,见他愁眉舒展,进一步恭维说:“有委座掌舵,只要我们利析秋毫,曲突徙薪,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防止一切危险,达到励精图治之目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任何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他从汪精卫脸上的表情判断自己的话很投机,继续说下去:“我没有多大本领,但有颗对委座的赤胆忠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委座给予我的是大恩大德!为了实现委座的伟大主张,就是抛头颅,洒热血,我都在所不惜!”
营养学家研究,蜂蜜抹在嘴唇上也能被人体吸收。大概甜言蜜语也有这种神奇作用!汪精卫觉得何世祯将一颗白璧无瑕的心捧在手掌上,感到亲密无间,感到输出爱的重要和获得爱的愉快。他激动地说:“感谢毅之兄对我的理解,感谢毅之兄对我的支持!”他身上继承了祖先自我调节的遗传因子,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许多。
房间里死一般沉寂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请委座指破迷津,眼下有哪些问题不可忽视?”周佛海觉得气氛不同了才这样提问。
“诸位是中央常委,是过来人,也是当事者,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汪精卫稍微平静的心,又被周佛海的提问搅得乌七八糟,不得不正面答复。他说:“在苏州地区,准备活埋的四百多个新四军家眷被共党分子弄走,有三十多处碉堡被炸毁,在巡逻路上经常发生地雷爆炸事故,近来又有一百五十多个清乡干部被暗杀!昨天上午,裕仁天皇接见褚民谊大使时说:‘这是对苏州地区的清乡试点工作的莫大讽刺。’我们好受吗?”他两眼注视着大家脸上的表情,似乎在看他们好受不好受。
他们是长在一根苦藤上的瓜,当然都不好受。
他十分难过,接着说道:“在江苏、在海南、在广西、在福建的沿海盐场那么多的盐工闹事,周先生亲自带人去平息过,可是,如今闹得更凶了!莺歌海的盐工竟敢用汽油烧毁四艘日本盐轮,灌河口的盐工上山打游击,专与保卫盐场的日军、和平军为敌,北海盐区的盐工把前往运盐的四十多个日本船员丢到海里活活淹死;金井和将军头两个盐区的盐工已经罢工一个星期了。昨天下午,褚先生从东京打电话告诉我,近卫首相感到很恼火,说‘南京政府连盐工闹事都对付不了,未免太软弱无能了。’我们好受吗?”
大家脑袋里像灌满了铅,重得脖子支撑不住垂在胸前,活像一批正在接受审讯的罪犯。
“在大冶,那么多的铁和铜被老蒋的部队运走,使四个日本朋友死于非命,使整个矿业公司处于瘫痪!畑俊六总司令指责我们‘平日对矿工和冶炼工教育不严’,说我们‘过于相信周成哲’,心里真不是滋味!”汪精卫很痛苦,痛苦得心在滴血。
“在南昌,六家中日面粉业联营厂的仓库,在九月十八日晚上同时被炸毁,损失二十八万四千多斤面粉!小仓大藏相批评‘守护面粉的和平军都是木雕菩萨’。唉!真难受。”他满脑子浓得化不开的悲伤感情,“四天前,周先生接到日本大藏省书记官德田卓仁先生从武汉打来的电话,才知道武汉纺织业联营的九个厂出了大问题!德田先生说老蒋手下一个少将参谋冒充和平军师长,捏造周先生的亲笔信,骗走了三个多月库存的棉布和棉纱,还把赵毓松先生和他的三夫人,把联营厂总经理市川东升先生和他的续弦夫人带走了!现在,他们的生死不明。昨天上午,小仓先生接见褚先生时说:‘请贵国政府自己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要我们反躬自省嘛!”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尊严,拳头不能自制地在胸脯上连捶三下,“这样下去,势必失去日本政府的同情、支持和援助!所以,我才提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请诸位思考:我们这个中央政府还能维持几天?”
沉默了。沉默所具有的意义,有时比雄辩还雄辩。这种难堪,表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悲痛、仇恨和警惕。大家的心如同一只被小偷窃走后扔进垃圾箱的钱包那样空空荡荡,正常的思维能力陡然停止,仿佛只剩下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现在,我只想出家当和尚!”汪精卫说,“或者,做个沙漠中的孤游者,自由自在走自己的路,横走直走也好,走东走西也好,想走就走,想歇就歇,无人干涉,无须商量。”他悲观已极,其声凄不忍闻,其状惨不忍睹,在座者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都觉得心在隐隐作痛。
可是,要做自由人容易吗?贝多芬老人说得十分明白,要获得自由须付出生命和爱情。绵羊总是成群结队行走,只有雄狮才敢于独来独往。在座的常委们缺乏贝多芬说的那种勇气,自然没有雄狮的气质。因此,当中华大地金瓯破碎,狼烟遍野,几度江河流血,无数英雄饮弹时,他们成了软骨虫而被人牵着鼻子走。先生们都是从最高学府走出来的,有的人还喝过洋水,这些道理都懂。然而,不管他们的本意如何期待,也不管他们心理上已经如何悟得透彻,最后还只能委曲求全,过黄鳝躲在罐子里的生活。因为他们有种向往,或者说是幻想和希望。人只要有了精神支柱,就能容忍一切,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坦途还是逆境。
“南京国民政府万岁!”周佛海振臂高呼一声。
大家一怔,以审视神经病患者的眼光审视他。
但是,周佛海的神志是清醒的,若没有清醒的神志,不会激起如此由衷的祝愿。他接着说:“委座问我们的新政权还能维持几天?不是几天,也不是几月几年,而是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无需否定,我们的确面临许多不利于巩固和发展新政权的困难,面临许多不顺心的事,乃至受到许多不公正的指责,但我们有委座掌舵,就能够渡过一切惊涛骇浪,绕过一切险滩暗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达到繁荣富强的理想彼岸,使国父创建的三民主义伟大学说永放光芒!”他犹豫片刻,还是把想说的都说出来,“我认为,日本政府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至少可以说是推卸责任。”
“我完全同意周先生的看法。”陈璧君为了激励丈夫,进一步引申说:“负责苏州地区作战和封锁任务的是日军第十三军所属三个师团,兵力够充足的了。要说出了那些问题是‘对清乡试点工作的莫大讽刺’首先是讽刺日本军队!每个盐区都有大批日军担负强化治安的任务,要说‘软弱无能’,也是日本军队!守护大冶矿业的同样是日本军队,他们才真正是‘教育不严’呢!”但她不能不承认:“当然,说守护南昌各面粉厂的和平军是‘木雕菩萨’,我们甘领甘受,因为那里没有一个日本兵。武汉各纺织厂发生的问题的确很严重,要我们反躬自省,我们也诚恳接受。”按常规,在常委会上陈璧君和徐珍无发言权。但常规只能约束芸芸众生,对一切特殊人物则一文不值。徐珍紧接着说:“我不完全同意君姐的观点。南昌和武汉,各驻扎了日军一个师团的部队,那里的面粉厂和纺织厂出现的问题,难道他们没有一点责任?”
“那就请二夫人出马,赴东京兴师问罪去吧!”陈璧君板着面孔冷笑一声。她不像往常那样称“珍妹”而称“二夫人”,就带有鄙视意味。
徐珍没有把她看在眼里,反唇相讥:“如果委座和诸位常委派我去东京一趟我愿意去,虽不能说是兴师问罪,但也能把情况说清楚,你说是吗?尊敬的一夫人。”
“成什么体统!”汪精卫瞪了陈璧君一眼,过了好一阵才瞪了徐珍一眼,不免失之偏颇,“这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会,不是汪兆铭家里的家庭会!”
“好了,好了,责任问题不必深究了!”周佛海从中打圆场,“现在,问题都摆出来了,今后该怎么办?还是请诸位发表高见吧!”他面向汪精卫,“委座的意见呢?”
看汪精卫的脸色,他仿佛刚从崇山峻岭踏进千里平原,心情豁然开朗了。他没有直接回答周佛海,却是泛泛而谈:“刚才佛海兄高呼万岁,表达了中国一切志士仁人的心声!毅之兄刚才的发言富于哲理。是的,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暗极即光明啊!我坚信,有在座诸位做南京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我们一定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巍然屹立,也一定会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姿态屹立在日本朋友面前,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感到我们是大有作为的友好邻邦,进而依靠我们,支持我们!”他的喜笑颜开,与一个小时前的愁眉苦脸判若两人,“我同祥认为,日本朋友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但我们可以从正面去理解,把它当作鞭策和动力。”他感到自己言词陈旧,论调空泛才煞住,笑了笑,说道:“我不必多讲了,其实这些道理诸位都懂。好,请诸位按照周先生的意见发表高见,我们如何迎难前进?”
对于汪精卫的多愁善感,喜怒无常,能屈能伸,能方能圆,变化多端,人们只能惊异于一个十分复杂的中国造就出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人物,惊异于一个远未成熟的中国,造就出这样一个似乎过于成熟的政治人物。
“我提点不成熟的意见,求教于委座和诸位常委同志。”梅思平说,“我们的敌人是老蒋和共党,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和不同的对策予以对付。前者虽然势力很大,也与我们势不两立,但是,毕竟他们与我们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有着最基本的共同语言。我们之间还有某种默契,在某些方面是明斗暗合。近几个月来,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和平军摩擦大大减少,在许多地区保持互不侵犯的和平局面,军统也停止了对我们的中央委员的行刺。这些事实证明,我们与重庆的关系正在逐步改善。因此,我们不必把主要兵力对付老蒋。”他为自己能先于其他常委提出这种见解而高兴,“而后者,力量虽然不那么大,但不能小看,因为他们无孔不入,十分狡猾和凶狠,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与我们毫无妥协的余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所以,建议将和平军的主力部队放在各个日军占领区,对付共党新四军的所谓抗日根据地。同样的原因,建议把特工总部的主要力量用在侦察和暗杀潜伏在我们管辖地区的共党地下组织。”他进一步分析说,“在清乡试点地区出现的种种严重恶性事故,无一不是共党分子干的!各个盐区的盐工闹事,而且越闹越凶,其祸根子也是共党。只有把共党彻底消灭了,我们才得安宁。”
“你的意见很好,祖芬兄!”汪精卫说,“下午三点召开军委常委会,把兵力重新部署一下,春圃你现在就去通知,把会议的中心议题告诉他们,好让大家运筹帷幄。”他面向周佛海,“至于把特工总部的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事,请你具体部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