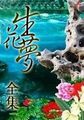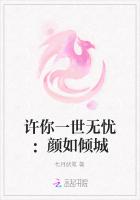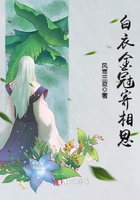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鲜明特征。
小到一个女人的发髻花式、袖口宽窄,大至一个政体的意识形态、价值趋向,凡俗如市井闾里流行的方言俚语,高贵如王公贵胄间崇尚的风靡时好,环肥燕瘦,各有所钟。
是人参与并改变了生存的时代,改变了的时代又反过头来影响人。它给这个时代里的一切打上烙印,最终将带有时代独特印记的文化以符号形式永远存档,醒目标定。
如同文学,由汉赋,而唐诗,再宋词,再元曲,到明清为笔记小说;也如同书法,由秦篆,而汉隶,再魏碑,再宋楷。随着时代的不同,文学与书法相应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达样态。历经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的系列嬗变之后,当历史的车轮由元及明滚滚而来,这个全新时代的学术风潮会再次改变吗?
答案是肯定的。
心学,将成为一面赫然的学术旗帜,猎猎飘扬在明朝的学术天空。
从宋代程朱理学转型到明代心学,有两个人功不可没,其一是陈献章,另外一位是王阳明。他们二人在明代心学中的位置和作用,很像宋代理学中的“北宋五子”之于朱熹,前者是领航,负责发轫,肇起,推开一扇门;后者是中坚,负责承继,光大,在综采大成中将其推向全盛,使之蔚然成风。
《明史·儒林列传》中讲得很清晰:“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撰《明史》的清代作者虽然高举程朱理学为正朔,将陆王心学视为异端,但他却客观陈述了心学在明朝“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以及“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的巨大学术影响。
开启明代心学新航的陈献章,就这样桨声欸乃地从理学晨雾中划水而来。
一.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白沙里(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号石斋,别号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门渔父、南海樵夫、黄云老人等,因曾在白沙村居住,后人又称其白沙先生。生于公元一四二八年,明宣宗宣德三年,卒于公元一五〇〇年,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耕读世家,父祖皆无显名。其祖父名字颇像二十世纪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的那位著名农民,名陈永盛,号渭川。和陈永贵不同,陈永盛“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其父名陈琮,号乐芸居士,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过着和大多数乡间文人一样的悠闲的隐居生活,二十七岁便英年早逝。
我曾经在叙写周敦颐的那篇文字中思忖过:一代大儒的成长,是否必须以幼年失父为代价?何晏冲龄丧父,后由继父曹操调教培养;韩愈幼年父母双亡,其兄将其抚养至大;孙复父亲早亡,独与寡母相依为命;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再醮,继父为其完成学业提供生活保障;周敦颐少年失父,母亲与舅舅将其抚养调教至大……陈献章也经历了这种人生的不幸。
而且,他更为不幸,甚至与父亲陈琮彼此连面都没见过。
作为遗腹子,陈献章自出生之后便为孤儿,从此与他二十四岁的寡母相依为命。陈献章幼时一直体弱多病,他自称“无岁不病”,全是在母亲含辛茹苦、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才不至于夭折,乃至“至于九岁,以乳代哺”。一个九岁大的孩子,仍在吮吸母亲干瘪的乳房,这的确少见。
特殊的成长氛围,极端的生活环境,使得陈献章深知母亲的艰辛与不易,自懂事之日起,他便对母亲敬爱非常,极为孝顺。《明史·儒林列传》中说:“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彼有一念生,此即一感应,这就是母子连心。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及。”孟郊曾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绵密缝制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游子吟》,千年传唱不衰。陈献章也有一篇诉说母子情深的散文,尽管知道它的人不多,但其文学感染力比孟郊的诗作更强,更催人泪下。
公元一四八三年,明成化十九年,五十五岁的陈献章为避盛气凌人的吏部尚书尹昊,向朝廷称病,请求归家事母。在上书给明宪宗的《乞终养疏》中,他这样写道:“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拳拳孝母之情,溢于纸上,令人闻之落泪。朱见深皇帝读后大为感动,不仅准许他归家奉母,另外还特别封他为翰林院检讨。
表现在少年陈献章身上的不仅是明理懂事,孝敬母亲,更为突出的是他聪明早慧,资禀异常。《明儒学案》中称他“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当陈献章刚刚读《孟子》一书,接触到其中的“天民”概念时,年幼的他为之慨然说:“为人必当如此!”
如果你的记忆力不是太差,应该记得还有位儿童也曾在他的人生初年说过类似的话。幼而颖悟的朱熹刚接受启蒙教育,当老师授以《孝经》时,他粗粗一看后即在其上题写道:“不若是,非人也!”
幼小的陈献章与孩提时的朱熹所共同表现出的人格禀赋是:亲近经典,志向远大,立意宏远,执意践行。
陶渊明曾蓄素琴一张,上无琴弦,每当心中意至,辄取下虚拂一番,以造心中之趣。陈献章梦中也曾自拊石琴,其音泠泠然绝美,梦中有人对他讲:“八音中唯石难谐,子能谐此,异日其得道乎?”醒来后,陈献章以为得到神启,于是为自己起别号为石斋,胸中慨然有承继圣贤之意。
正统十二年,公元一四四七年,二十岁的陈献章应广东乡试,考中为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中副榜进士,进入国子监读书。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岁的他偶然间听闻到抚州崇仁的康斋先生大名,遂不远万里,跋山涉水,一路追寻到崇仁,投其门下,向拒不出仕、困处乡间、怡然自得在家读书课徒的吴与弼先生虚心请教。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看来,这首悠扬而抒情的歌不光今天的人会唱,旅途中奔波的古人大概也会常常哼起吧。其间大不同的是,今人千万里追寻的往往是金钱或女人,而古人苦苦追寻的却是知识与学问。
二.
吴与弼相当不简单。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他与同时期另一位儒学宗师薛瑄,俱为明初朱熹之学的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
《明史》中这样说他:“与弼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响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中岁家益贫,躬亲耕稼,非其义,一介不取。四方来学者,约己分少饮食,教诲不倦。”
他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是“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宦官势力在明朝十分强大,几乎祸害了有明一代的整个朝政,佛教势力同样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这两种势力当道,于吴与弼而言,就失去了走出家去治平天下的先决条件,只能老于林下。为此,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明代宗景泰年间,再到明英宗复辟后的天顺年间,他屡被推荐,但一直拒不出仕。
天顺元年,明英宗朱祁镇赐玺书,赍礼币,征吴与弼赴阙,授他左春坊左谕德,面对殷勤备至的皇帝,他仍然摇头拒绝。明英宗纳闷了:“闻处士义高,特行征聘,奚辞职为?”他回答道:“臣草茅贱士,本无高行,陛下垂听虚声,又不幸有狗马疾。束帛造门,臣惭被异数,匍匐京师,今年且六十八矣,实不能官也。”英宗不许他辞职。最后吴与弼请求“以白衣就邸舍,假读秘阁书”,以普通百姓身份入馆,翻阅秘阁之书。明英宗说:“欲观秘书,勉受职耳。”两个月后,吴与弼以病重为名请归。明英宗只好遗憾地放老先生返乡,而且“赐敕慰劳,赍银币,复遣行人送还,命有司月给米二石”。
吴与弼秉承朱熹的学术理念,认为“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强调个人苦修,要人通过读书穷理的“集义”功夫,达到“涵养德性本原”。同时,他还持程颐的“敬义夹持”思想,提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即通过内敬和格物致知对人自身“浣洗”,从而陶冶出“莹澈昭融”的达理通性。
吴与弼在他的《日录》中强调:“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他与程朱一样认为,学者要常存警惕之心,克制非分欲念,因而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他非常重视“主静”,提倡在静坐与夜思中实现心灵的通透、达悟。
“澹如秋水贫中味,和若春风静后功。”这是吴与弼所写的诗联,正可当作他为人的真实写照。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他:“先生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及夫得之而有以自乐,则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此正孔、颜寻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动之间,悉归平澹。晚年出处一节,卓然世道羽仪,而处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于道,其能如是?”他为吴与弼所画的人格肖像是:“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吴与弼所创的“崇仁之学”主静主敬,主张在“静观”中反求于“吾心”,实为明代王学的发端。
吴与弼一生授徒,桃李繁多,门人学生中声名最显著者为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谢复、郑伉等人。胡居仁以“主静”标宗,开启了“余干之学”。“余干之学”的另一代表人物为娄谅,他则是王阳明的老师。以此而论,陈献章实是王阳明的师叔。
由此可见,吴与弼已经于不自觉中,和会了朱熹与陆九渊的思想。他的存心以涵养本源与主倡静思冥悟的修养方法,将在他的弟子陈献章、娄谅身上结出心学的花蕾。
而这朵花蕾又将在明代中期,通过王阳明的发扬光大,绽出心学的奇葩。程朱理学也将从此式微,代之的是心学的异军突起与广泛播扬。
无疑,陈献章将以其“江门之学”成为理学的终结者和心学的发端人。
三.
陈献章出生之时,从皇觉寺蒲团上站起来,跑出庙门闹革命的安徽凤阳农民朱元璋,已经建立大明政权整整六十年。
元亡明兴的六十年来,程朱理学一直高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领之位,以无可争辩的官方学说备受历代朱姓皇帝推崇。
《明史·儒林列传》概述道:“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想望风采,而誉隆于实,诟谇丛滋。自是积重甲科,儒风少替。”
早在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朱元璋就下令在科举制度的乡、会试中,一律采用程朱理学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使得程朱理学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二程与朱熹享有无限尊荣地位,连孔子、孟子都望尘莫及:“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
洪武十七年,朝廷再次诏告天下: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颐、朱熹及其弟子的注解为准绳。并规定,文章须据以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八股文由之兴起。被称为“制艺”的八股文章,目的性极强,即代圣贤立言,严禁个人自由发挥,而且还有着严格的体例和字数限制。
永乐十二年,公元一四一四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组织编纂以《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为内容的三部《大全》。一年之后,编纂成书,明成祖为之亲自作序,并颁行天下。
三部《大全》所辑内容均为程朱或其门人弟子解释儒家“六经”、阐述性理之学的著作,因而可以说三部《大全》实质上是程朱学派学者的著作汇集。它的刊布,标志着程朱理学已经从原来的民间私学完全上升为官学。
程朱理学思想一统全国,成为系统而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最高准则。此后,明朝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儒家经典先前的一切古注,只认定程朱理学为唯一学术依据。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的圣典。
程朱理学的官学化、独尊化,以及科举考试的唯一依据化,这些无疑都使得程朱理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提高到一个历史空前的地步。当然,这附带着也给儒学的自身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桎梏。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学术永远不是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它有着很强的开放性与待完善性。任何学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自身持续的质疑,众口一词,唯斯为大,其结果只能让本属开放的学术封闭起来,让流动的思想凝滞、僵化起来。
被奉为至尊的程朱理学,已经处于这样的尴尬困境了。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是这样总结理学被当成圭臬之后,给明朝初期学术与思想界带来的贻害的:“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
程朱的影响到处存在。那些一头钻进《大全》去猎取功名富贵的读书人,许多都成为无益于国家、社会的废物,而钻营成功者,则蠹国病民,行同窃盗。更为严重的是,其他文化领域,如戏曲、小说、曲艺等艺术领域,也深深地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迹,而且越到后来,它的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锢的消极作用也越为明显。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从明朝建国伊始相继走出的一系列大儒,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他们虽然学问做得很好,学名远播,但他们的学术独创性却极少,基本上全为承袭并株守程朱学术思想,属于自己的学术思想贡献均相当可怜。
如开创“河东之学”的大儒薛瑄,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广大区域,为北方朱学宗主。他就认为,经过“北宋五子”发端,儒学发展到朱熹这里已经成为极致,登峰造极,属于当今学者的事只有一样,那就是照着先辈所说的去做就够了,“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恭行而已”。
有这种思想和认识的,又绝非薛瑄一个人,在明初诸儒的集体学术认知里与他们的为学方向中,这种思想普遍存在,随处可见。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登到绝顶之上“览”过之后,还能干什么呢?若不是在绝顶之上逗留,便只有走下坡的路了。
当程朱理学被奉为绝顶之学后,那么儒学必然从此落入止步不前或每况愈下的境地。
四.
儒学发展史的舞台上,陈献章适时登场。
公元一四五四年,二十七岁的陈献章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来到了江西崇仁,进入吴与弼个人创办的小陂书院,从此全面接受吴师的教导。
关于他在小陂书院的学习生活,《明儒学案》中有则趣闻:“陈白沙自广来学。晨光才辨,先生(吴与弼)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声曰:‘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又何从到孟子门下?’”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在小陂书院睡懒觉而被老师批评的特殊经历,陈献章一生之中对书院的兴趣,远不如师弟胡居仁那么强烈。
胡居仁自崇仁小陂书院归家之后,颇为热心书院事业,先后在余干创建礼吾、南谷、碧峰三所书院,直至成化二十年去世。这中间还两度应聘到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而且写下了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之后,对学林影响最大的另一著名学规《续白鹿洞书院学规》。
陈献章恰与之相反,他离开崇仁返乡苦读十年之后,在家乡先后讲学于碧玉楼、江门钓台、嘉会楼、小庐山书屋,但他的讲学场所从来不以书院为名。成化十七年,他还态度颇为坚决地辞却江西提学请他主讲白鹿洞书院的聘职。观其行状,他似乎始终对“书院”抱有成见,很不以为然。
其个中真正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吴与弼的那一次呵责,陈献章后来在与友人的一封书信中透露出了原委:“仆年二十七,始发愤从吴聘君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老师无所不及,学生却不得要领,始终感觉于学无补。
所以,跟随吴与弼学习仅一年之后,陈献章就离开小陂书院,回到故乡江门白沙村。他在小庐山麓之南建起一间书舍,题名“春阳台”。自此,他在“春阳台”中伏案读书,潜心悟道,足不出户。
还是在那封信中,他讲了返乡后自学中的苦恼:“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
问题的根源找出来了,原来是此心与此理没有契合!心与理始终相见而不相爱相契,彼此不能相印,这自然使得书本上的圣贤说教与自我内心所悟不能谐振。最后,他找出了妙诀——静坐:
“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涣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盖以吾所经历,粗有实效者告之,非务为高虚以误人也。”
既然学问所得在静坐,通过独自静坐进而“见吾此心之体”,那么当然对不谙此理的书院是要看不起的了。
也因此,后世学者往往否定陈献章与吴与弼之间的学承关系,认为吴与弼的学说完全秉承的是宋人成说,而陈白沙的学说则是离此矩矱,心悟而得,独辟蹊径,自成一派。
黄宗羲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崇仁学案》中为吴玉弼打抱不平:“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言心,则以知觉而与理为二;言工夫,则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故必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而后为学问之全功。其相传一派,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於戏!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其实,这正像二程所言自己的学问全是悟来的一样,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思想撇不开老师周敦颐的影子。陈献章的心学溪流,源头也正是自吴与弼那里汩汩流出。
五.
十年磨一剑。
公元一四六五年,明成化元年,紧紧关闭了十年的“春阳台”门户大开,里面走出了学已大成、吾道自足的一代儒学宗师陈献章。
因白沙村位居西江入海之江门,故陈白沙之学被称为“江门之学”。
“江门之学”的最大特点是不株守旧学,富有独创性。与一般恪守朱学传统的明初学者不同,陈献章注重独立思考,提倡怀疑精神:“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同时,他还强调为人为己之辨:“为学莫先于为己、为人之辨,此是举足之第一步。”正是这种主独立思考、倡质疑的学术贵疑精神,使他在朱熹的学术体系中冲破藩篱,从而使明代儒学从理学实现了向心学的转身。
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确为恰当之论。
在陈献章的宇宙观与自然观中,人的来源与世界构成皆在二气之相感。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道和天地一样均为至大,“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这种以道为天地之本的观念,接近朱熹以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不同的是,陈献章没有把道看作独立于万物之外的绝对本体,而是提出了万事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独特认知:“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进而引申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本论观点,直追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论调。
如此,陈献章提出了“以自然为宗”,进而提出他的为学之法——“静中养出端倪”。通过静坐,然后悟得心体,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就与朱熹所提倡的读书穷理、格物致知为学之法大不相同。不再汲汲于格物与读书,也不必依循他人的说教,包括孔孟程朱在内的一切先圣之言与心体比较而言,均处于次要位置,因而欲为学,就须“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
他描绘了通过静坐,求得“吾心之约”后的心灵极为洒脱空旷的审美至境:“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夫以无所著之心行于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曾点活计,鸢飞鱼跃,通过静中涵养而直达天理,这既是陈献章的学术特征,也是他的学术理想。
《明儒学案》这样总结陈白沙的学术特点与历史地位:“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远之则为曾点,近之则为尧夫,此可无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与文成不作,则濂、洛之精蕴,同之者固推见其至隐,异之者亦疏通其流别,未能如今日也。”
陈白沙的心学,表面上看非常接近佛门禅宗之义。他提出的“以无所著之心行于天下”超功利审美境界,就与禅宗所倡的“荡相遣执”十分相似。与陈献章同时代的高僧梵琦,就特别强调心本体的重要性,认为心中本具一切,只要护持,觉悟此心,即可得道成佛,“无理外之事,无事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无物外之心”。
因此,他的学说引来学界不小的诟病,许多人认为其学近禅。黄宗羲为之分辩:“或者谓其近禅,盖亦有二,圣学久湮,共趋事为之末,有动察而无静存,一及人生而静以上,便邻于外氏,此庸人之论,不足辨也。”
其实,陈白沙自己这样说过:“禅家语,初看亦甚可喜,然实是笼统,与吾儒似同而异,毫厘间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贵择之精也。如此辞所见大体处,了了如此,闻者安能不为之动?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无归宿,无准的,便日用间种种各别,不可不勘破也。”
也许,真理是相通的,只是它表达在了不同的学说之中。一个欲发佛家之真如,一个想致儒家之良知,同途却异归。
牧人与狼都喜欢羊白白胖胖,但谁能说他们想的是一回事呢?
六.
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三十八岁的陈献章离开家乡学馆,再次来到京师,复游太学。
原因是翰林侍读学士钱溥的一封信。钱溥在信中说,明宪宗刚刚上台,正要复礼施教,整顿朝纲,为此劝他进京考取功名,为国家效力。
然而,皇帝朱见深并非一个英主。《明史》称他:“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受其宠爱的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当然是陈献章后来一再辞职的最主要理由。
其时,国子监祭酒为邢让。而邢让是陈献章的同年,在公元一四四八年,他们曾一同走进考场,只不过,陈白沙考中的是乙榜,邢让却考中甲榜,进士及第。
十八年的光阴挥洒之后,邢让成了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陈白沙却还是个游学于国子监的旁听生。面对山村老师陈献章,邢让没有将眉毛挑到脑袋顶上,而是有意要察看一下陈献章的学问,再做推荐之念。于是,他即兴让陈献章提笔来和南宋大儒杨时的《此日不再得》诗。
“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绩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行己慎所之,戒哉畏迷方……”杨时的这首诗很长,也很出名,曾作为治学格言教育了一代代由宋及明的读书人。
陈献章当然对之耳熟能详,他不假思索,援笔而成一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
“能饥谋艺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负奇气,万丈磨青苍。梦寐见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义利分两途,析之极毫芒。圣学信匪难,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养,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辞固秕糠。俯仰天地间,此身何昂藏。……顾兹一身小,所系乃纲常。枢纽在方寸,操舍决存亡。胡为谩役役,斫丧良可伤.愿言各努力,人海终回狂。”
全诗体格雄健,音律开朗,寄寓哲理,议论义理,写得奇瑰跌宕,情理交融,更因其中深邃的治学之思,宏大的体道之想,深深折服了邢让。邢让为之连声惊叹:“龟山不如也!”并“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
因邢让的这一称赞,朝中为官的一大批知名学者如罗一峰、章枫山、庄定山、贺医闾皆恨相见陈白沙太晚。给事中贺医闾甚至在听到邢让“扬言于朝”的当天就“抗疏解官”,辞官不做,改为恭恭敬敬跟随陈献章做学生。
随后,在邢让的推荐下,陈献章进入吏部当起一个抄抄写写的司吏。但因性格耿直,为人端方,得罪了礼部侍郎尹昊,备受其陷害与暗算之后,四十二岁的陈献章决定返回家乡。
江门沙白如玉,那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大明朝廷中少了一位下级公务员。
岭南却迎回一位旷世的学术宗师。
七.
“江云欲变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凉夜一蓑摇艇去,满身明月大江流。”这是陈献章一首抒发自己胸臆的诗作,名为《偶得示诸生》。
取名“偶得”,实是久伫于胸;举之向学生展示,也是自己对自己的倾诉。
那便是他为人为学中始终抱持的一个理念——以淡远的襟怀,澄明的心境,以静应变,万化自然,如此才不失自然的真趣,才能永葆自己的高贵人格。
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罗一峰充满敬意地说:“白沙观天人之微,究圣贤之蕴,充道以富,崇德以贵,天下之物,可爱可求,漠然无动于其中。”
而黄宗羲却从中看到了另一种悲壮或崇高:“信斯言也,故出其门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其高风之所激,远矣!”
他的衣钵传人湛若水便是证明。
湛若水,字元明,弘治七年从陈献章游,从此不乐仕进。母亲命之出,乃入南京国子监。参加会试时,考官抚其卷叹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遂以甲榜第二名进士及第,后来,他成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历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嘉靖初年,入朝上经筵讲学疏,向昏聩的嘉靖帝直言不讳地进谏:“陛下初政,渐不克终。左右近侍争以声色异教蛊惑上心。大臣林俊、孙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为寒心。亟请亲贤远奸,穷理讲学,以隆太平之业。”
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基础上,提出了“万事万物莫非心”的观点,认为“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内矣”,同时他警告学者:“舍书册、弃人事而习静,即是禅学。”黄宗羲认为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是王、湛之学各树门户的标志,而且也是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与发展。
其实,湛若水的这个学术观念仍然来自陈献章。陈白沙曾在予湛若水的信中写道:“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
湛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祀陈献章,足见他对其师的高山仰止之情。
公元一四八三年,明成化十九年,广东布政使彭韶、总督朱英集体向明宪宗举荐陈白沙:“国以仁贤为宝,臣自度才德不及献章万万,臣冒高位,而令献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宝。”于是,陈献章又被召至京城,令就试吏部。昔日曾与陈献章心存芥蒂的权臣尹昊,此时为吏部尚书,为此,陈献章辞疾不赴,最后用那篇情文并茂的《乞终养疏》感动了宪宗,被授翰林院检讨而归。
回乡途中,走到南安时,南安知府张弼对陈献章先拜官而后辞,颇不以为然,认为这和他的老师吴与弼完全不同,有沽名钓誉之嫌。陈白沙回答道:“吴先生以布衣为石亨所荐,故不受职而求观秘书,冀在开悟主上耳。时宰不悟,先令受职然后观书,殊戾先生意,遂决去。献章听选国子生,何敢伪辞钓虚誉?”
一个听从自己内心召唤,率意而为的人,因其言行不合乎世俗逻辑,故最易为世俗所不容。进而,歪曲与诬蔑,造谣与诽谤,便接踵而至了。
陈献章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
但他有自己的应对之策,那就是以平常之心待之。
萧伯纳镌刻在茶壶上的自警之语是:“他们骂了,让他们骂去。”陈白沙所持的信条是:“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牛自为牛,马自为马。”
举世加誉,赞扬声连,于我何干?
万夫所指,批评接踵,关我甚事?
在《论学书示学者帖》中,他告诫门人弟子:“诸君或闻外人执异论非毁之言,请勿相闻。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须隐其姓名可也。人禀气习尚不同,好恶亦随而异。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见得是处,决不至以是为非而毁他人。此得失恒在毁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毁之人,言之何益!”
诲人不倦、力创新旨、唯务履实的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给他送米一石,他却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
耕读自足,致力讲学,粗衣敝履,饭粝蔬豆,却始终甘之如饴。将生活简约化,将人生简单化,将灵魂丰厚化,就这样他终老此生。
公元一五〇〇年,弘治十三年,他以七十三岁之龄卒于家中。
“飞云之高几千仞,未若立木于空中与此山平,置足其巅,若履平地,四顾脱然,尤为奇绝。此其人内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气浩然,物莫能干,神游八极,未足言也。”他曾经要求学生朝着这个方向修炼,渐至臻境。
观陈白沙一生行迹,他确实已经抵达了这一胜境,令人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