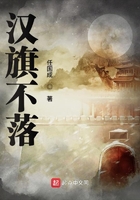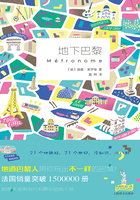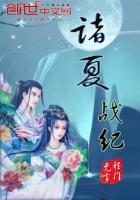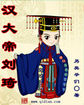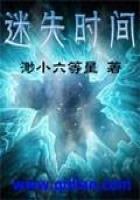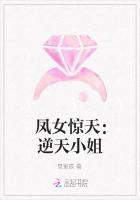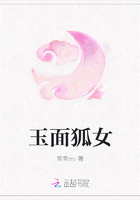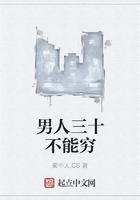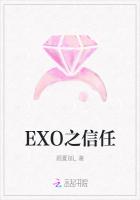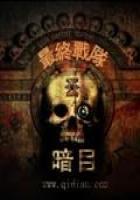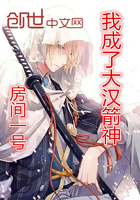《史记》校读研究与史实考证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2006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词语考证
訾永明的《“三户”考》(文史杂志/2006/03)认为,“三户”出于《史记·项羽本纪》,是范增游说项梁时引用楚南公的话,但自晋代以来,对它的理解却众说纷纭。其实“三户”不仅是楚国地名,还是楚国申息之师的戍地。而申息之师是楚国在公元前682年灭掉申国、息国后所设的地方武装,其装备和战斗力应远低于楚国的正规军。《史记·项羽本纪》中,范增游说的背景是项梁率军渡过江东,听说首举义旗的陈胜已死,并且秦朝章邯的大军将至,便召集诸将在薛地商议对策,这时范增用楚南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话来游说。这里的“三户”指驻扎在三户的申息之师,意思是即使楚国仅拥有战斗力极弱的地方武装,但灭亡秦朝的也一定是楚国,他以此来反映楚国人民对暴秦的痛恨,坚定项梁反秦复楚的信心。
杨传凤的《“暗渡陈仓”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02)引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洁修著《汉语成语考释词典》(1995年版),针对书中提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语来源《史记》,刘邦与楚将章邯作战等,提出三个问题探讨:一是是否有“明修栈道”这一事件;二是章邯的身份;三是应该用“度”还是“渡”。结论:“明修栈道”的最早语源应是宋元时期的小说、戏曲,而与《史记》、《汉书》无关;章邯此时的身份是“雍王”,而非楚将;应用“渡”而非“度”。
卞华成的《“刀笔吏”的由来》(语文知识/2006/12)认为,汉时竹简、木牍是最经济、最主要的文字载体,用毛笔书写。由于竹简、木牍宽度较小,所以当古人因写错而需要修改时,就要把写错的地方用刀子刮去,然后重写,这样刀子就派上用场。一个称职的古代文员,刀和笔是必备的工具。长此以往,“刀笔”就成了这些人的代名词。
马达的《“始作俑者”考异》(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06)认为,成语“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自汉赵歧为《孟子注》,到新中国建立之初,乃至建国后,一直被人们所苟同,用法也几乎一致。文章依据我国田野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和传世文献的“考异”、分析,指出孔子对“人殉”历史了解的局限和赵歧所作注释的错误,认为“始作俑者”并非是指所谓的带头做某些好事的人,此成语明显不合时宜,也不宜再用。
孙熙春的《〈史记〉中的“刁斗”与“刀斗”辨析》(沈阳大学学报/2006/06)认为,《史记》的不同版本中存在着“刁斗”与“刀斗”的两种写法。究其原因为所依据的底本不同,其根本原因为“刀”与“刁”是古今字、通假字。提出在同一《史记》的文本中,无论使用“刁斗”还是“刀斗”均可,但混用是不科学的、不妥的。
刘鸿雁的《“韦编三绝”别释》(江海学刊/2006/01)认为,“韦编三绝”是个常用成语。通常的看法认为“韦”指熟牛皮,此处用缀连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来形容孔子读《易》次数之多。后来就用“韦编三绝”来形容读书勤奋。各种词典对“韦”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目前可见的出土竹木简都是用丝绳或麻绳编连的,尚未见到用皮绳编连的竹木简实物。现存文献中也未见有用熟皮编简的记载。文章认为,“韦”当通“围”,表环绕义。“围编三绝”指的就是环绕竹简的编绳断了多次。从“韦”、“围”在《史记》、《汉书》中的使用情况来看;汉代“韦”通“围”的情况比较常见。从竹简的形制来看:多数简册是直接用丝绳或麻绳将单支简逐次连结在一起的。除此之外,还可在简札的上端穿孔,再用编绳串连成束。从产生误解的原因来看:“韦”指熟皮是一个通行义。尤其是放在名词前面,修饰名词表示事物的性状。如韦弁、韦带、韦衣、韦沓等等。而且比较常见的竹简都是由几道编绳编连成册。于是后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韦编”就是指编连竹简的皮绳。
晏鸿鸣的《谈“目眦尽裂”中“裂”之字义》(修辞学习/2006/02)认为,鸿门宴“目眦尽裂”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文中:“樊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释“眦”为“眼眶”;高级中学课本《语文》也释“目眦”为“眼眶”;其配套《教学参考书》释全句为“眼眶都裂开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也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也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下称《郭古》,认为“眦”是“上下眼皮结合的地方”,即“眼角”。可能因为限于体例,未能展开深入阐述。刘钧杰《樊哙的眼睛应当怎么裂》(见《语文建设》)提出了两个论据:一是眼角是“眼睛的结合部”,“牢固程度差”。二是古书书证有《灵枢经》“锐,内眦”注“眦者,睛外之眼角也”等。上述观点都将“裂”理解为“完整处的破裂”,但现实生活中从未见人愤怒得瞪破眼眶或眼角的,因为从生理上讲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对“裂眦”理解和注释的错误,根源是人们一直忽视了“裂”字的一个义项。《汉语大字典》指出“裂”属于方言词,意思是“物件的两部分向两边分开”。即“张开、分开”。这样我们知道,汉族人其中特别是男子眼部的皮褶较多。而当人发怒的时候,体内及外形会发生一些变化,其中眼部由于眉部耸起、睑板内收而眼裂增大,这必然导致眼内、外眦的张开。由此看来,“裂眦”实际上就是眼角张开,也就是眼睛瞪大。而“目眦尽裂”就是眼角完全张开,换句话说,就是怒目圆睁。
吴晓燕的《关于〈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引绳批根”》(绥化学院学报/2006/04)认为,通过古文献《汉书》、《汉书补注》及《汉语大词典》、《辞源》等工具书,求证了《史记》的“……引绳批根……”句的标点及“引绳批根”的结构及本义。结论:一是中华书局版的标点是正确的,人大版的标点是错误的;二是对“引绳批根”的解释,人大版、中华书局版及以上所查相关资料大意是相同的,即“比喻合力排斥异己”。不同的是对这个词的内部结构及本义的解释。认为“引绳批根”引申为合力打击、排斥。
李宝通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新解》(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认为,左丘明姓名来源失载,单姓、复姓说均有疑。左丘明当以义命名,即“佐孔丘明史”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可释为“佐孔丘明史而有失明细,于是有《国语》之继”。左丘明并非盲史官。《左传》可称《左氏春秋》、《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甚至《春秋传》、《春秋古文》乃至于《国语》合称《春秋》、《国语》,但却不可称《国语》或单称《春秋国语》。
付丽敏的《“马童面之”并非“马童仔细观看项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6)认为,《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的“面之”有不同解释,传统说法中,有解释为“背对项羽”的,也有解释为“面对项羽”的,肖振宇则坚决否定了传统说法,提出“仔细观看项羽”的新解,并认为“根据字义、文义和语言规律”,此论新则新矣,可是根据对词语意义、上下文义辨析以及语言使用规律分析,笔者觉得此说有悖于词语意义和语言使用规律,传统解释才更合理。
陈子谦的《“天府”新解》(天府新论/2006/05)认为,“天府”最早的含义是指天帝居所,它与文祖、世室、明堂含义相同。“府”者物之所藏,“天”者尊之爱之,视所藏之物如“天物”,由此而有了掌管财物的官职,并生出职掌而兼聚敛之义。由天然府库而得“天府”之名,因地域之富饶、山川之险峻而名为“天府之国”。秦汉以降,记“天府”和释“天府”者,大多着眼于“富等天府”,有时也扩展到地域之广袤和险要,《战国策》、《史记》、《汉书》、《晋书》等史著,莫不如此。“天府”或“天府之国”的美称原指“关中”,即今陕西省。其专属于四川,始于陈寿的《三国志》和常璩的《华阳国志》。《三国志》所说的“天府”,还没有完全包括今四川的版图,《华阳国志》则径直以“蜀”与“天府”相等同。长期以来,“天府”一词作为精神之渊默、沉潜和学问之富有、精深等方面的含义,少为人知,以至于湮没无闻。某些最现实又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化本位论者,其实守住的只有“天府”即“天堂”。
风俗研究
肖振宇、郑秀真的《〈史记〉风俗习性的记写特点》(民俗研究/2006/03)认为,《史记》对人的风俗习性的记写,不同于对人物和其他内容的记写,有着其自身的记写特点。一是分传记写。在《匈奴列传》中,记写了匈奴人的风俗习性。在《大宛列传》中,通过张骞之口,记写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身毒等国人的风俗习性。在《货殖列传》中,记写了关中、三河、燕、齐、鲁、三楚等地人的风俗习性。通过在不同的列传中,分别记写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们的风俗习性,这样就把复杂的风俗习性化为简单,相对集中地表现出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鲜明的风俗习性特点,便于人们认知和把握。二是细粗结合。如《货殖列传》中先比较详细地记写了关中、三河、郑、卫、燕、齐、鲁、梁、宋、三楚、颍川、南阳等地人的风俗习性。关中汧、雍以东至河华、华人,“好稼穑,植五谷,地重,重为邪”,人多善于经商;长安人,“益玩巧而事末”等等。《史记》采用粗略总括和详细具体相结合的记写法来写风俗习性,不仅从不同层面和视角交代了全国大小不同地域错综复杂的风俗习性,而且还能够使人比较清楚地看出各地风俗习性自身特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三是揭示原因。《史记》注重对风俗习性形成原因的揭示。如在《匈奴列传》记写匈奴人的风俗习性前,传中先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驘、駃騠、騊駼、驒騱。”这里所写的匈奴早期历史、地理方位、多见和奇特的物产是匈奴人生活的人文和自然条件,正是因为这些人文和自然条件原因,造就了匈奴人的独特鲜明的风俗习性。《史记》以其独特的方式方法,记写了作者生活时代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性,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面貌、性格特点。
张文华的《〈史记·货殖列传〉与风俗史》(理论学刊/2006/05)认为,《史记》从风俗史角度入手,考察《货殖列传》对全国各地社会风俗的建构之功及其在中国风俗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全国各地社会风俗予以理论性总结,初步建构起了社会风俗史的体系。其具体工作可体现在风俗理念、取材、谋篇布局、贯通古今的考察四方面。《货殖列传》以列传形式记载社会风俗,在中国风俗史上有重要地位。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对全国各地会风俗作了总结,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同时,奠定了《汉书·地理志》撰写社会风俗的基本格局。司马迁分区叙述各地风俗的模式直接为班固所取法,拉开了风俗史写作的序幕,启发和推动了后世对风俗的关注和对风俗历史的研究。
石朝江的《苗族:“神州”土著》(贵州民族研究/2006/06)认为,根据史学家的研究及考古发现,苗族的祖源故土就在中国,即苗族为“神州”之土著。神州,即中国。《史记》曰:“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苗族发祥于中国长江、淮河流域,曾北渡黄河挺进中原腹部,并形成名曰“九黎”的部落联盟。“九黎”集团率先开发了“神州”本部。
历史地理研究
张可辉的《“五湖”考释》(中国地名/2006/12)认为,太湖为吴中胜地,颇多异名,如震泽、具区、洞庭等等,也有五湖之别称。然而历史上也有观点认为五湖并非太湖,亦不在太湖之内;又或认为五湖是指太湖周边五大水湾;便是宗五湖为太湖别称者,亦因太湖何以名五湖而争论不已。历史上太湖以五湖为名确是曾有的史实,而参订各家之说,虞翻《川渎记》、王士性《广志绎》之以为太湖派通五道者极是。
张可辉的《太湖异名考》(兰州大学学报/2006/03)认为,太湖为吴中胜地,颇多异名,如震泽、具区、洞庭,也有三山湖、湖亭、姑篾。太湖的异名记载着太湖的变迁、太湖的社会情况、自然环境,以及历史上人们的相关语言、认识等。太湖异名表现出形状定名、特征定名及吴越古族语言性的特点。
潘发俊、潘竟虎的《西汉玉门关地理位置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02)认为,《史记》和《汉书》十见玉门关,通过逐条分析、综合判断,得出结论:西汉玉门关在“石门周匝”酒泉嘉峪石关。这座汉关的位置在北朝、唐、五代、北宋的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
张国硕的《晋南“夏墟”考》(中原文物/2006/06)认为,夏王朝包括夏代晚期的都城皆在豫西地区,晋南地区不存在像安阳殷墟那种都城废址性质的属于夏王朝的都邑故址;文献所记的“夏墟”应该是泛指广大区域而非专指某一地点,整个晋南地区皆应该属于“夏墟”之范围;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的原因是由于商王朝灭夏之后夏族聚居晋南所致,“夏墟”即夏族聚居区;晋南地区被称作“夏墟”只能说明商代和西周初年夏族曾聚居于此,其与夏族的起源和夏文化的渊源没有必然的联系。
李绍连的《黄帝部族活动的北线地域》(中原文物/2006/01)认为,黄帝部族是新石器时代活动于中原地区的主要部落族团,这一族团的历史创造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向文明方向发展。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资料,该部族历代的迁徙路线已较为明确,并且其活动的北线地域很可能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山山脉南麓一带。
郝导华的《杞国史地考略》(中原文物/2006/01)通过周代杞国史地的对比研究,论证了周代杞国不宜再分为“殷杞”、“周杞”或是“夏杞”、“夷杞”,而应该把杞作为一个国家来时待。并认为,杞国殷时在山东,周武王分封到今河南杞县,西周中晚期又迁到山东诸城一带,齐桓公时为淮夷所患,向齐南、鲁北一带迁移,而后与晋国关系密切,再后又向鲁国西部或是南方迁移,战国时为楚所灭。
苏海洋《秦国邽县故城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06)认为,邽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县之一。检索历史文献,关于邽县故城的位置,有六种(类)不同的记载。除《水经注》记载的今天水市区内的邽县故城外,其余诸说均误。邽县得名于邽山。邽山西起今天水市区西北20公里的凤凰山,东南至今天水市区北边的营房梁,北至渭河,南至罗峪河。邽县原为邽山东南脚下(今天水市区)的邽戎邑。考古资料亦证明春秋早期今天水市区内可能有城邑存在。结合历史地貌调查和考古资料分析,初步推断:《水经注》所说的“上邽故城”大约在今天水市区耤河以北、弥陀寺巷——仁和里——尚义巷一线(北魏罗峪河故道)以东、邽山以南,它可能就是秦国邽县故城。
李海俏的《关于圜阳地望所在》(文博/2006/01)认为,过去对汉惠帝五年(前190)在陕北南部设立之圜阳县治方位的一般提法是在神木境内秃尾河下游。对此诸家曾多次提出疑义。经考证圜阳县治应在绥德境内四十铺左近。
李毓麟的《秦汉布山古城考》(中原文物/2006/01)根据古今有关史志、文献资料、地理特点、实物依据及实地考察,桂平是汉布山县地,县治就在今桂平市蒙圩镇新德古城村。
张泊《上郡阳周县初考》(文博/2006/01)考证秦汉上郡阳周县认为,秦汉时期,阳周曾是上郡所属的一个县治,然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阳周县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悬念和谜团。秦大将军蒙恬奉始皇帝之令修造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最终却被二世胡亥囚禁于阳周,加害于阳周。汉武帝北巡曾在阳周城南的桥山之脉祭祀黄帝。在两汉之间它突然神秘消失,而在北魏时又被重新设县,不在陕北却到了今甘肃正宁,从而引发出一系列中国历史地理名著的失误。一直到今天,诸专家学者仍然对它的地望各执一词,各持己见。在对史念海和王北辰的观点进行辨析后,认为阳周地望位于秦长城线上,又临近秦直道,芦河依城而过,南有白于山。而阳周城的神秘消失,则是因为王莽穷兵黩武,匈奴的攻杀掠抢,加之连年灾荒,民不聊生。
神秘文化研究
吴象枢的《〈史记〉与神秘文化因缘浅论》(唐山学院学报/2006/02)认为,《史记》与神秘文化的因缘,一是由于史官文化的母体是巫官文化,二是由于作为百科全书性质的《史记》,会收录那个时代很有影响的神秘文化;而且神秘文化是被司马迁当做一项政治内容载入《史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了较多的神秘文化现象,有《天官书》、《封禅书》、《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专篇,另有《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主要谈征兆灾异及神仙方道,《宋微子世家》中也有长篇的对神秘文化观念的论述。《史记》中有关神秘文化方面,除理论论述的内容之外,就其神秘文化的情节,笔者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共有307例神秘文化。从这些数据中可明显看出,《史记》中的神秘文化记载,相当一部分是应帝王及重臣的需要而出现的,同帝王之事及社稷兴衰有直接联系,政治色彩很浓。同时司马迁也想借神秘文化以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于司马迁的主体原因和神秘文化本身在当时的普遍性和政治地位,《史记》中记载了大量的神秘文化现象,今天的史家或文学研究者,对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能回避,也不应因为对神秘文化本身价值的否定而对它曾经存在也加以否定。广泛的现实证明,神秘文化是研究古代文化时无法回避的一个方面。在今天重新探讨神秘文化,其目的,不是信仰它,更不是发展它,而是因为当你不懂得神秘文化这一脉系时,就难以理解古代主体的进步的传统文化。这正如当今的文字学家研究甲骨文一样,并非为了把甲骨文推而广之成为大众化的书写字形。
吴象枢的《对〈史记〉中梦占的思考》(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6/01)认为,《史记》中记载了一些梦兆情节,司马迁对这些梦兆迷信的预示意义没有否认,而且由于梦占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司马迁也把梦兆当做实现“究天人之际”写作目的的手段之一。据统计,全书共记梦的情节23处,从梦者来看,梦者都是帝王及皇宫贵族,司马迁没有把一个纯粹的平民之梦记入《史记》。从梦的内容来看,《史记》中的梦都有重大意义,都关系到国家大事,可归为圣人或贵人前兆之梦、梦兆得人、社稷安危梦兆、凶梦体四类。梦占活动同国家政治有密切的联系。龟占、易占、梦占三者,其功能都是“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梦作为政治舆论的一种工具,由于梦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严重的虚构成分。梦是主观性的东西,《史记》及以前的史籍中记下的梦,其客观真实性如何,应该说是很难判定。从事情的前后过程中,不难看出其中的梦是一种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孙娟的《〈史记〉感生神话与司马迁表现艺术》(唐都学刊/2006/03)认为,《史记》记载了商、周、秦始祖和汉高祖的感生神话,其中商、周、秦的感生神话都以经典为依据,但都简略;而刘邦的感生神话则详细、系统,与他的史学思想相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经历了历史神话化的过程,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神话历史化,但又在其中设下了微言大义。后世不察,以此为书写历史著作的模范。
杨建军的《后稷感生神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6/04)对《诗经·生民》记叙周族始祖后稷感生神话的某些词句作了考释,并认为《史记·周本纪》中的后稷感生神话不同于《诗经·生民》中的后稷感生神话,是另一异文。《周本纪》的“巨人迹”与“马牛”,便是司马迁对异文的采摘。可惜那个录有异文的文献没有流传下来。
胡钢、田富强、池芳春的《〈史记〉预测文化研究——以人物品鉴为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6/05)认为,《史记》中有关人物命运预测的部分史料能够应验,是有深刻原因的。预言者科学的观察与研究、罗森塔尔效应的作用以及流传中的附会与选择,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些史实。将司马迁笔下自我品鉴及他人品鉴的相关史料贯通起来,可以窥见其“究天人之际”良苦用心之一斑。
史实考证
叶永新的《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新探》(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认为,目前史学界对于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楚汉双方的决战不是垓下之战而应是陈下之战;也有学者认为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本是同一次战役。通过对史籍有关文献记载、作战规模和性质、参战人员、作战经过、作战地点和作战结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知,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是分别存在的客观事实;陈下之战是刘邦所率汉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一个转折点,垓下之战则是楚汉双方的大规模最后决战。
张箭的《战国长平之战赵降卒被秦坑杀数新探》(齐鲁学刊/2006/04)认为,战国秦赵长平之战的结局,传统说法是赵军全军覆没,战死者5万,投降被俘者40万,降卒全被秦坑杀。但按常情,参加长平会战的秦军数至少应与赵军数持平,这样便也有45万。指挥长平会战的秦军主帅白起承认这次战役“秦卒死者过半”。因此按常理赵军在战败投降前也应死者过半。是故投降被杀的赵降卒数最多不过20余万,甚至可能只有14万多。
罗培深的《论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虚构》(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04)对于《史记·项羽本纪》中垓下之战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项羽到乌江边上后不是不肯过江,而是无法过江,不得已而自刎身亡。当项羽逃奔至乌江边,遇乌江亭长驾船在江边守候,欲渡项羽过江,而项羽拒绝,最终只将坐骑送走。本文认为这段描写应为作者的虚构,不是历史事实。主要理由有四:没有旁证、乌江亭长是否确有其人、情节过于巧合、乌江亭长的行为不合常情。司马迁虚构的原因在于因李陵一案而受到牵连,遭受了仅次于死刑的宫刑。这对他是极大的耻辱,这种内心极大的痛苦在司马迁的心中,终于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心理。这种复仇是通过《史记》的著述来完成的。在司马迁的笔下,汉家统治者受到贬损,如写刘邦的虚伪、狡诈、残酷等。
李绍明《“禹兴西羌”说新证》(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3)从阿坝州近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考古学新资料,茂县和汉川花灯戏中歌颂大禹唱词,以及重庆云阳新近出土的东汉景云碑等说明《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确有依据。
张应桥的《西周卫国国君康伯懋事迹考》(文博/2006/06)考证了西周卫国国君康伯懋的事迹。康伯,名懋,是西周成康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卫国第二代国君,卫康叔元子,“八师”统帅。传世文献和金文均记载有其事迹。文献中又称其为康伯、王孙牟、康伯髡,金文中称其为伯懋父、康伯。他生前曾统帅“殷八师”又称“成周八师”南征北战,东讨西伐,为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曾以司寇的身份主持官员之间的讼事等政务。死后葬于卫国墓地,即今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地。
张宗云、郭永远的《老子故地孝义村考》(光明日报/2006/01/23)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和故地遗迹考证,老子避难在鲁国的栖身之所,以及后来的隐居之处都是山东省平邑县柏林镇孝义村,老莱子即老子。老子的大半生都在孝义村度过,孝义村应是老子故地。
黄崇浩《屈原是否到过赵魏两国》(光明日报/2006/05/12)从研究合纵连横、屈原外交活动和理解屈原作品特别是《离骚》的主旨的角度考察,认为《史记·赵世家》“楚、魏王来过邯郸”这句话不该被忽略。屈原不仅使齐,而且可能使魏、使赵。楚怀王十六年(前313)“楚、魏王来过邯郸”,是继怀王十一年“楚怀王为纵长”之后的又一重大外交事件,是六国合纵活动的延伸。《史记》将“楚、魏王来过邯郸”一事置于《赵世家》而不是其他“世家”,正是司马迁“互见法”叙事的一个例证。“楚怀王为纵长”,理当受邀前往。魏受秦的间谍张仪暗中播弄,虽貌似摇摆,实则恨秦,故亦在受邀之列。
对于我国牛耕始年约有以下诸说:州大学历史系王星光从我国各地远古时代石犁的出土,和世界牛耕出现的比较,把犁耕和牛耕加以区分,阐述了黄帝时代已有牛耕的可能,到商周时期不能广泛应用的原因;沫若据甲骨文的“犁”字考释提出牛耕在商代已经有了;杨宽提出春秋战国之说。陈全方、陈馨《西周甲文中的牛耕》(农业考古/2006/04)认为,学术界对我国牛耕始年的看法还是有差别的,但认为在殷代已出现牛耕是大部分学者的意见,而对西周有无牛耕,且都未提及。近年来在研究周原考古队发掘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宫室(宗庙)建筑基址西厢房11号窖穴出土的大批西周甲骨文中,发现其中第23片明确记载了牛耕之事。并认为,我国商周时期的牛耕问题是值得从多方面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帝研究
孙锡芳的《〈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02)认为,《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谱系,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从现存文献记载归纳出的四种五帝谱系来看,其基本框架是一致的,只是个别世系略有差别。从民族学的角度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五帝之间并非直系血缘的父子、子孙关系,而是氏族、部落发展过程中的分裂与分化。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周及徐的《“炎帝神农说”辨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认为,“炎帝神农说”流行两千年。然司马迁《史记》无此说,且查检先秦汉初的20多部文献,言神农或炎帝50多处,神农与炎帝皆不相混,二者的时代特征、重大的行为和事件皆判然有别,是神农与炎帝为先后不同时代之人。“炎帝神农说”源于汉代刘歆,其《世经》以上古帝王世次附会五行说,捏造了“炎帝神农氏”。传统的“炎黄子孙”的说法也是沿袭了“炎帝神农”在前、黄帝在后的错误。若依史实,只当是“黄炎子孙”。
张维慎的《关于周人女始祖姜嫄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04)认为,后稷本是其母姜嫄参加社祭后与某个姬姓男子野合而生,而史籍载为“履大迹”、“履大人迹”、践“巨人迹”,完全是出于儒家崇圣心理而对野合的巧妙掩盖;为了更神异其事,乃曰“履帝迹耳”,因为当时尚无“帝”、“上帝”的概念。姜嫄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当时盛行普那路亚婚(即外婚制),民“知母不知父”,因而后稷被其母姜嫄抛弃,既不是因为他无父而生,也不是因为他要接受图腾仪式的考验,而是因为他出生时“胎生如卵”(带胞生),形体异常,古人以为妖异而不祥,所以被抛弃。
魏嵩山的《虞舜行迹地望辨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04)认为,据古史记载与民间传说,古人以所居地为姓,虞即虞山,今晋南中条山区东段当是舜的原籍所在。今豫东鲁西地区曾为有虞氏部族迁居,今济南市南历山很有可能为舜所耕。今运城市、永济县虽分别有鸣条陌和苍陵谷,但志书不言舜死葬于此,当地亦无此种传说,不能因为肯定《孟子》而否定《山海经》与《礼记》诸书记载,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鸣条当是苍梧九疑山中地名,今湖南永州宁远南九疑山当为舜所终处。舜死以后,后裔尚有分封,其地在今河南虞城、河南淮阳和山西平陆等地。
人物考证研究
于智荣的《“范雎”称名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6/02)认为,战国后期,秦昭王时的宰相,被奉为应侯的范雎的名字,史学著作和史论文章或作“范睢”或作“范雎”,文章认为应作“范雎”,理由一是作为人名用字“雎”和“且”古籍中互为异文;二是据古人名的用字规律,“睢”当为“雎”之误;三是清乾隆五十年,黄易等人于山东济宁嘉祥县紫云山得范雎之像,字作“范且”。
王振中的《姜太公是山东土著姜姓吗——与焦安南、李建义二位先生商榷》(新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01)认为,有人认为姜太公是山东土著姜姓,甚至是山东日照市人,出于对《孟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一系列典籍相关内容的误解,有的属于疏漏,有的属于偏颇,但更深的原因,还是受了家乡情结的制约,把姜太公的避居之所,提升到了祖居的地位。
李和山的《荀子生年及游齐时间汇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6/02)认为,荀子的生年及游齐时间,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对荀子游齐时间的看法各异。通过进行综合比较诸家说法,逐一剖析各自由来,根据《荀子》原书和史实,断定荀子游齐时间为齐襄王六年,并推断其生年约在齐威王三十年。
赵金炎的《兵圣孙武的籍贯与奔吴内情》(海内与海外/2006/02)认为,孙武的籍贯是山东广饶。孙武奔吴的原因是齐国内部四族矛盾激化。孙武奔吴的路线,据清代在今济南市东之济水旁(即今小清河岸边)出土孙武私人印和孙星衍撰《家吴将印考》所证实,孙武是从齐国乐安(今广饶草桥)乘舟顺济水经济南东而奔吴的。
贺金峰的《陈胜故里方城考》(开封大学学报/2006/01)认为,依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记载,结合笔者实地考察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故里,在今河南省方城县境内。
杜长印的《庄周故里新探》(中国历史文物/2006/02)认为,“濮渠之侧”、“曹濮之间”的李庄镇李庄集村一带,是庄周为蒙漆园吏、著书立说的主要活动地区。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在庄周垂钓濮水之处建庄子钓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庄子钓台,为南华观的庄子庙村一带,是庄周故里。
白国红的《晋文公“五贤士”考》(山西师大学报/2006/02)认为,晋文公即位前曾有过19年的政治流亡生涯,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但是,由于他身边始终有一批忠实且颇具能力的追随者,所以他历难弥坚,流亡生涯反而成为他政治磨炼的课堂,为他最终归国即位、称霸诸侯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其追随者中,为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是“五贤士”,他们的忠贞、才干不仅成就了晋文公对君位的追求,而且还塑造了春秋一代霸主。考证得知,晋文公“五贤士”当为: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胥臣。其中,赵衰、狐偃、贾佗三人更为突出,在出亡途中就受到所经诸国君臣的赞誉,被称为“卿材三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晋文公“五贤士”以他们的忠贞、才干塑造了春秋一代霸主。
杜玉奎的《曾子故里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6/05)认为,曾子故里南武城,即春秋之武城,鄫世子巫避难之所在,所处之费为子游所宰之费,“居武城”“处费”均在其故里,而非做宾师。据先秦秦汉史料及历代名家考论,确证曾子故里南武城,即今山东省平邑县南武城。
步如飞、郑晓华的《子夏里籍考》(管子学刊/2006/04)认为,子夏是孔子得意弟子之一,晚年到西河教学,开创了著名的“西河学派”,为魏国的军事政治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关于其出生地,众说纷纭,文章通过史料对比和考证,证明子夏是卫国温人,他到西河教授并不是回到自己的老家。
(韦爱萍 杜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