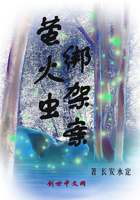陈近南站在郑锦身边的六步之遥,手握着那张相思木冰蚕弦强弓,一瞬间额角已渗出了细汗,感觉三十多年人生从未有过的紧张。
世子现在已被他看成是复明的最大希望,所以他绝不允许有半点意外损失!
即使郑锦已告诉他不会有什么事,陈近南依然不完全放心。所以他要站在可迅速反应的距离,帮助郑锦一起感受白衣狂僧飞箭的轨迹和杀气!
如果真的轨迹有异杀气突现,陈近南将已最快的速度飞出手中的相思木弓,或者以微曲紧绷的身体借力地面为弓,射出自己挡住那致命的一箭!
但是如果白衣狂僧并没有取郑锦性命之阴谋,而真正只是在为银子比赛,只是要射落郑锦的帽子,那他陈近南冒然出手则会破坏比赛的公平规则,坏掉世子的信誉,也可能会让世子失掉招揽一个奇士的机会。
如果真有凶险,出手慢那么一点点也可能要遗憾终身!
出手还是不出手,什么时候出手,只在那十分微妙又相当重要,相当难把握的一瞬间!
而那个白衣狂僧似乎也明白陈近南的艰难处境,故意迟迟不出手,消耗他紧张的神经。
陈近南已不觉内衫汗湿。
关心则乱!陈近南不能不关心,他只能以最大的定力让自己不要乱。
所以这场郑锦和白衣狂僧之间的危险玩命游戏,最紧张的不是当事的两个人,反而是一旁的陈近南!
郑锦不紧张,因为他自信可以躲得过对方如果有杀气的那一箭!或者说他更自信的是白衣狂僧那一箭根本不会有杀气。刚才他和白衣狂僧一个扮信陵君一个扮侯赢演的一出礼贤下士似乎两人都很有默契感,而白衣狂僧掀起帽沿两人目光相碰那一刻,郑锦也觉得似有相通感。
言语很多时候会骗人,但目光更多时候是泄露本心。
只是你为何迟迟不出手呢?
你在等什么?你不需要瞄准都能一发两中,为何现在要瞄准这么长时间?
难道你忽然没自信了?
郑锦干脆闭上了眼睛。
忽然,箭来了!
那么风驰电掣,也那么从容不迫。
却没有感觉到一丝杀气。
因为郑锦感觉自己的印堂、面门或者咽喉都没有一丝感到危险的警觉,没有一丝被压迫的不适。虽然那飞速而来的铁箭头形成的尖锐恐怖湍流只高出印堂那么一点点!
只是感到头上那顶带着蒙面恶僧汗酸味的帽子就要被飞落的畅快感,以及头上的青巾和发丝将要重见天日重获自由的那种飞扬飘逸感。
箭头触帽顶,一道有形有质的湍流激起,像一道平流而射的瀑布,将那顶汗酸味帽子冲走,冲了好远好远。
郑锦的身体像旗杆一样纹丝未动,青巾黑发像旗帜一样自由飘扬。
啊!
啊!啊!
……
黑压压一片跪在地上的将士们全都蹦起身,举枪举刀兴奋欢呼起来!
为白衣狂僧的绝妙箭术欢呼!
为他们世子的安然无恙欢呼!
更为他们世子的守信和神勇欢呼!
一旁紧张了大半天的陈近南也轻松了起来,就像洗了桑拿然后被美女全身按摩了个遍的轻松,轻松得让他向来一丝不苟一脸严肃让所有洪门特务看了都害怕的脸上也露出了平易可亲的笑容。
他忍着没出手,他的世子也没动,彼此安好,他一会后可以回家去坐在窗下泡一壶铁观音慢慢写簪花小楷画雪竹寒梅图了。
只是那白衣狂僧,那一千两银子,还微让他有点肉痛。
一千两银子,可以又从弗朗基人手中买100支燧发枪,或者可以造300多张柘木弓,还可以买1200石大米,为3000多个战士们换一套夏天凉爽新装,但现在……那狂僧真是狮子大开口,一个秃驴要那么多银子干啥?世子开始也不知道讲一下价的……
陈近南微摇头叹息一声,只好去准备今天比赛要发的赏银了。他既是郑成功尊称的陈先生,也是郑军财神爷。因为洪门控制的各支商业船队以及各地商业据点现在是郑家军队最大的财富来源,而他是洪门的总舵主,要钱不找他找谁?
“陈军师,那个,今天要多搬一点银子来啊!”郑锦特意在后面喊了一句,陈近南却似乎没有听见地没有回头没有回答。
************
晚明的江南繁华风流中,有一个好学早慧的神童,他的名字叫祁彪佳。
祁彪佳的爹进士祁承爜酷爱藏书,家中藏书楼“澹生堂”的藏书为江东之冠,小彪佳从小几乎在书堆中爬滚长大。六岁那年,一向静如处子的小彪佳被几个不怀好意的大叔们抱着放到高高的树杈上调戏,出了一个“猢狲上树撒童尿”的对子让他对,要对着了才肯放他下来。
小彪佳抹了一把眼泪,不屑地哼了一声:“飞虎在天啸苍云。”
众大叔惊愕拜服。从此小彪佳也被众人称为祁虎子。
祁虎子爱读才子佳人类的诗赋戏曲闲书,但考试做八股文也很厉害。
11岁时就被当时的大儒刘宗周收为关门弟子,然后13岁成了秀才,17岁成了举人,20岁又中了进士。
祁虎子考试很厉害,断案也很厉害。
21岁成了福建兴化州的推官(管理刑狱诉讼的官职,相当与宋代的判官),众奸吏豪强欺他年少,狼狈勾结,为奸作科,但所作案件无论巨细都逃不过他法眼,被他如狄仁杰般神明判决,如包黑子般严惩不贷,上任三月,众奸服帖,再无人敢欺他是嘴上无毛的小白脸。
祁虎子断案猛,打人也很猛。
他在苏、松巡按的任上时,三吴一带有一个叫“天罡党”的**组织,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还有众多小啰啰,扰乱市场次序欺凌百姓拦路劫财强抢民女无恶不作,前几任巡按都无法自理睁只眼闭只眼,祁虎子不知怎么有一天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108将都抓了起来,历数其罪,然后在大庭广众下将坐前四把交椅的“及时雨”、“玉麒麟”、“智多星”、“入云龙”捆绑了起来,用杀威棒一一亲手杖杀了,打得鲜血染红了他儒雅的白色襟袍,其余的天罡地煞们都跪在一旁一个个吓得股栗不已。在祁虎子最后竟仁慈地放了剩下的所有人后,众人叩头不已,天罡党从此也就烟消云散,吴中百姓们也都拍手称快。
祁虎子敢对小将下狠手,也敢对最高官硬碰硬,执法如山。
当时深得崇祯帝倚重宠信的首辅是宜兴人周延儒,周延儒在朝中弄奸作威,他的家人亲族在乡里横行霸道,强夺民田,仗势欺人。以至于民怨沸腾,将周家的祖坟给扒了。祁虎子既没有纵容放过扒祖坟的不道德行为,也对周家仗势欺人的亲族依法严惩不贷。
然后祁虎子就被罢官赋闲了,在家闲了八年。
在他赋闲期间,家乡绍兴曾发生大水灾,官府这个时候赋闲了。无一官半职的祁虎子却没有闲,他拿出几代积累的家财,与老师刘宗周一起分区救灾,设粥厂和药摊施粥给药,饥者饱之,病者药之,死者埋之,深山穷谷,无不亲历,所活数千人。
1641年,朱明王朝已处于最后的风雨飘摇中,祁彪佳这个时候又被朝廷征招出来做官,虽然有些不满,虽然夫人很反对,但祁彪佳还是走马上任了。
1644年,北京城破,崇祯上吊,祁彪佳被南明福王政权授予兵部侍郎一职,夫人苦劝他不要接,但祁彪佳最终还是接了。李自成部下的几个降将贼性不改,到处劫掠扰民,祁彪佳一边抚恤南逃难民,一边对降将恩威并用。当骄横跋扈的高杰将要暴动作难时,祁彪佳一叶扁舟过江奔赴高杰的大营,对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镇之以威。高杰天不怕地不怕,连李自成的老婆都敢抢,一时却被单枪匹马的祁彪佳折服,声称公在一日,杰决效鞍马之劳。
可没多久,祁彪佳又被南明的首辅阉党首领马士英给罢职了,悍将高杰再无人可慑。
祁彪佳再次赋闲在家,夫人却高兴极了,以为他再不会离家而去了。
祁彪佳爱藏书,爱读书,也爱吟诗作画。画的山水画清幽旷远,雄秀苍茫,深得元代山水大师倪瓒、黄公望的神髓,其他所画花卉竹石,随意点染,无不风趣高逸。他夫人也有与他相同的琴书诗画爱好,梦想与他一起再不问世事,专心在家共同探讨交流,相伴到老。
可是很快,1645年5月,扬州城破了,南京城也破了,乌烟瘴气的南明朝廷也亡了,清廷也同时下了易服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王学殿军一代大儒刘宗周绝食而死,祁彪佳这时却受到了清廷的出仕邀请,许以高官厚禄。
祁彪佳没有出仕,没有剃发易服,也没有躲入深山。
他留下了纸绝笔书:“图功何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然后深夜自沉入家中梅墅寓园梅花阁前的水池中。
这一年祁彪佳只有43岁,他夫人商景兰刚入40岁,他们的五个子女还有两个未成年。
商景兰是原吏部尚书商周祚的长女,名动江南的才女。商景兰刚入16岁那年嫁给了长她三岁的神童祁虎子,一时被传为“金童玉女”的佳话。成婚25年,他们一直伉俪相偕,琴瑟和鸣,也成了夫妻恩爱相敬,风雅高逸的佳话。
为何祁彪佳要抛下这段佳话,抛下未成年的子女,选择自沉?
前世的郑锦对此一直有些不理解,但现在似乎有些理解了。
前世看那些演康雍乾时代的辫子戏时,以为那种将前一半脑袋剃光,然后在后面一半留发,再将发结成一条拖与身后的大辫子发型就是清朝一直以来的发型,后来才知道错了。
历史的真相是,这种还不算太难看的大辫子阴阳头发型其实是乾隆死后嘉庆朝以后才被逐渐允许留的。以前150多年神州大陆的男人除皇帝外唯一合法的发型,一直是以鞑子入关前的野蛮鞑子发型为标准,也即“金钱鼠尾型”——头顶的头发要被剃得只留下头顶铜钱大小的一圈,后面再留几咎,编成鼠尾巴大小的辫子,像墙头草般摇晃于脑后。
士可杀不可辱,对于刘宗周和祁彪佳这样的人,他们是宁可死也不会去剃那种侮辱性的头的!更何谈剃了头去在满清鞑子面前下跪称臣称奴才。
祁彪佳也不屑与躲进深山老林。
那样他一家人都会跟着他在深山老林受苦。
或者那样清廷终要到处搜捕不放过他。天下之大,已没有桃花源。
现在他自沉明志,不仅是悲哀地感到复国无望以死殉之,也是保护他妻儿家人。
他殉国自杀了,他的夫人和家人会得到世人的尊重,可以再不会被清廷骚扰地在故园安静生活下去,那里有他家传世园林的幽美清旷,有传世藏书楼的丰富文化,有琴棋诗画的高情逸趣,他们会继续在那里好好活着,延续祁家和商家两代书香世家的文脉和尊严。
如果祁彪佳怕死,逃入深山老林躲着清廷苟活,这一切都将死去。
如果祁彪佳怕死,剃发下跪入仕新朝,祁、商两家的尊严折辱,文脉也可能要中断。
没有如果,祁彪佳终究是祁彪佳,在清廷的聘书到来的那一天,他就果断地自沉了,给他家人既留下难忘的悲痛,也留下继续尊严活着的空间,留下文脉,留下以身作则的气节典范。
或许还有最后一条路,那就是祁彪佳留家人在故园,而自己一个人出家,去披袈裟做和尚或戴黄冠做道士。
然后他每月或者每年偷偷回家和夫人子女相见相聚一次。
大概这条路才是他夫人商景兰最期望他所走的,既不出仕新朝屈身辱节,也不用生死相分阴阳两隔。
也许祁彪佳也在这条路面前犹豫过。出入佛老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一种常见的行为,无论是在精神修养上还是在为人处世上。在这种国破山河残的时候,更是很适合的选择。但或许是祁彪佳对儒家的信仰比较深,他最终还是没有在关键时候拿佛道两家作僻难所,生为儒,习为儒,死为儒,正衣冠着儒服自沉而死。
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死得很伟大,不过认为自己做了一件相对简易偷懒的事。
“图功何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
既然不能生而图功反抗,那就以死反抗。你不是要请老子去做官么,**的鞑子,老子宁死都不跟你合作。
这就是现在郑锦所理解的祁彪佳为何最终选择了去死。
在国破民族将亡的时刻,总要有人以死反抗,也要有人活着反抗。对前面一种的刘宗周、祁彪佳、袁枢、文震亨等等等之人,对后一种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等等等之人,还有对先反抗被抓再去死的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张同敞等等等之人,郑锦都同样的尊重敬佩。
他们的以死抗争,决不合作的精神气节,已超越了对朱明王朝的效忠,保卫的不仅是世代生存的家园,也是一个已传承两千多年民族的文化和尊严,为的已不是一家一姓朝廷的兴亡,而是汉人江山传统。
可惜他们的力量还是太弱小了,他们不过是一群秀才、书生,在朱明王朝大厦将倾的时刻,他们都是毫无一官半职的,毫无一军半卒的被赋闲之人。
所以到现在,1661年,鞑子入关的第十八个年头,依然神洲陆沉,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到光复的希望,没有光复的信心。
郑锦坐在五老峰上的一块岩石上,背对着黑沉沉的神洲大陆,望着海岛远方升起的一线日出光明,回头对身旁的祁班孙笑了笑:“你是个只秃了头却不戒酒肉的假和尚吧?”
海风吹动祁班孙白色的僧衣剌剌,却半点吹不动他光秃秃的头,一点没有郑锦那种宽袍大袖古装长发的飘逸感,虽然他人长得很神采俊秀,一点不愧其父母“金童玉女”的称号。
“我娘舍不得我离家去做和尚,早就给我定了一门亲事。”祁班孙望着远方海天相接处的日出云霞,良久才答了一句。
“那你现在成亲了没?”郑锦又问。
“成了。”祁班孙简洁回答。
“那祝你幸福。”
“世子真的准备不光复不成亲?”
“说出去的话能收回么?”
“那祝你坚持。”
又欣赏了一番海上日出的壮丽景色后,郑锦对祁班孙正式邀请道:“加入我们的队伍吧,我们一起赶走鞑子光复大明,完成你爹的遗愿。”
祁班孙一会沉默后,拣了一块石头扔到海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大朵浪花。
“世子可否先答应我一件事?”
“何事?孙郎尽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