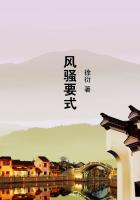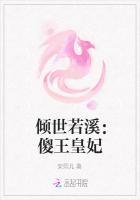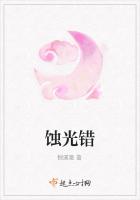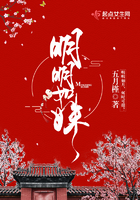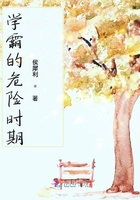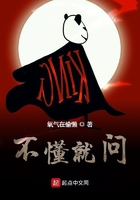良知是造化之精灵,吾人当以造化为学。造者自无而显於有,化者自有而归於无。吾之精灵生天生地生万物,而天地万物复归於无,无时不造,无时不化,未尝有一息之停。自元会运世,以至於食息微渺,莫不皆然。如此则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原是变动周流,此便是学问头脑。若不见得良知本体,只在动静二境上拣择取舍,不是妄动,便是着静,均之为不得所养。以上(《东游会语》)
当下本体,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拟议即乖,趋向转背,神机妙应。当体本空,从何处识他?於此得个悟入,方是无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纤毫力中大着力处也。
近溪之学,已得其大,转机亦圆。自谓无所滞矣,然尚未离见在;虽云全体放下,亦从见上承当过来,到毁誉利害真境相逼,尚未免有动。他却将动处亦把作真性笼罩过去,认做烦恼即菩提,与吾儒尽精微、时时缉熙,工夫尚隔一尘。
良知一点虚明,便是入圣之机。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不为旦画牿亡,便是致知。盖圣学原是无中生有,颜子从里面无处做出来,子贡、子张从外面有处做进去。无者难寻,有者易见,故子贡、子张一派学术流传后世,而颜子之学遂亡。后之学者沿习多学多闻多见之说,乃谓初须多学,到后方能一贯,初须多闻、多见,到后方能不藉闻见,而知此相沿之弊也。初学与圣人之学,只有生熟不同,前后更无两路。假如不忍觳觫,怵惕入井,不屑呼蹴,真机神应,人力不得而与,岂待平时多学,而始能充不忍一念便可以王天下?充怵惕一念便可以保四海?充不屑不受一念便义不可胜用?此可以窥孔、孟宗传之旨矣。
忿不止於愤怒,凡嫉妒褊浅,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过,皆忿也。欲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转转,贪恋不肯舍却,皆欲也。惩窒之功有难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将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惩心忿,窒心欲,方是本原易简功夫,在意与事上遏制,虽极力扫除,终无廓清之期。
问:“伊川存中应外、制外养中之学,以为内外交养,何如?”曰:“古人之学,一头一路,只从一处养。譬之种树,只养其根,根得其养,枝弃自然畅茂。种种培壅、灌溉、条枝、剔叶,删去繁冗,皆只是养根之法。若既养其根,又从枝叶养将来,便是二本支离之学。晦菴以尊德性为存心,以道问学为致知,取证於“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以此为内外交养。知是心之虚灵,以主宰谓之心,以虚灵谓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说误之也。涵养工夫贵在精专接续,如鸡抱卵,先正尝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点真阳种子,方抱得成,若是无阳之卵,抱之虽勤,终成毈卵。学者须识得真种子,方不枉费工夫,明道云:“学者须先识仁。”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机。种子全在卵上,全体精神只是保护得,非能以其精神功益之也。”以上(《留都会记》)
耿楚侗曰:“一念之动,无思无为,机不容已,是曰天根。一念之了,无声无臭,退藏於密,是曰月窟。乍见孺子入井,怵惕恻隐之心,动处即是天根,归原处即是月窟。才搀和纳交要誉恶声意思,便人根非天根,鬼窟非月窟矣。”先生曰:“良知觉悟处谓之天根,良知翕聚处谓之月窟。一姤一复,如环无端。”
有问近溪守中之诀者,罗子曰:“否否。吾人自咽喉以下是为鬼窟,天与吾此心神,如此广大,如此高明,塞两间,弥六合,奈何拘囚於鬼窟中乎?”问:“调息之术如何?”罗子曰:“否否。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息安用调?”问:“何修而得心和?”罗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顺父母,心斯和矣。”先生曰:“守中原是圣学,虞廷所谓道心之微,精者精此,一者一此,是谓允执厥中。情反於性,谓之“还丹”,学问只是理会性情。吾人此身,自顶至踵,皆道体之所寓,真我不离躯瞉。若谓咽喉以下是鬼窟,是强生分别,非至道之言也。调息之术,亦是古人立教权法,从静中收摄精神,心息相依,以渐而入,亦补小学一段工夫,息息归根,谓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气和、形和世儒常谈儱统承当,无入悟之机。”(以上《答楚侗》)(此可见二溪学问不同处。近溪入於禅,龙溪则兼乎老,故有调息法。)
良知者,性之灵根,所谓本体也。知而曰致,翕聚缉熙,以完无欲之一,所谓工夫也。良知在人,不学不虑,爽然由於固有,神感神应,盎然出於天成。本来真头面,固不待修证而后全。若徒任作用为率性,倚情识为通微,不能随时翕聚以为之主,绦忽变化将至於荡无所归,致知之功不如是之疏也。(《书同心册》)
良知二字,是彻上彻下语。良知知是知非,良知无是无非。知是知非即所谓规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谓悟也。
乡党自好与贤者所为,分明是两条路径。贤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从人转换。乡党自好即乡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毁誉为是非,始有违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观人,先论九德,后及於事,乃言曰“载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观人者,不在事功名义格套上,惟於心术微处密窥而得之。(以上《云门问答》)
良知不学不虑。终日学,只是复他不学之体;终日虑,只是复他不虑之体。无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尽便是圣人。后世学术,正是添的勾当,所以终日勤劳,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会,穷其用处,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话。(《答徐存斋》)
尹洞山举阳明语庄渠“心常动”之说。先生曰:“然庄渠为岭南学宪时,过赣。先师问:“才子如何是本心?”庄渠云:“心是常静的。”先师曰:“我道心是常动的。”庄渠遂拂衣而行。末年,予与荆川请教於庄渠,庄渠首举前语,悔当时不及再问。予曰:“是虽有矫而然,其实心体亦原如此。天常运而不息,心常活而不死。动即活动之义,非以时言。”因问心常静之说。庄渠曰:“圣学全在主静,前念已往,后念未生,见念空寂,既不执持,亦不茫昧,静中光景也。”又曰:“学有天根,有天机,天根所以立本,天机所以研虑。”予因问:“天根与邵子同否?”庄渠曰:“亦是此意。”予谓:“邵子以一阳初动为天根,天根即天机也。天根天机不可并举而言。若如公分疏,亦是静存动察之遗意,悟得时谓心是常静,亦可谓心是常动,亦可谓之天根,亦可谓之天机,亦可心无动静。动静,所遇之时也。”(《南游会记》)
问:“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个知,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行有本体,有工夫,如眼见是知,然已是见了,即是行;耳闻得是知,然已是闻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个知,已自尽了。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无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说能爱、能敬。本体原是合一,先师因后儒分为两事,不得己说个合一。知非见解之谓,行非屐蹈之谓,只从一念上取证,知之真切笃实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即是知。知行两字皆指工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为立说,以强人之信也。”
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以上《华阳会语》)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良知是天然之则。是伦物所感应之迹。如有父子之物,斯有慈孝之则;有视听之物,斯有聪明之则。感应迹上循其天则之自然,而后物得其理,是之谓格物,非即以物为理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物者因感而有,意之所用为物。意到动处,易流於欲,故须在应迹上用寡欲工夫。寡之又寡,以至於无,是之谓格物,非即以物为欲也。物从意上,意正则物正,意邪则物邪。认物为理,则为太过;训物为欲,则为不及,皆非格物之原旨。(《斗山会语》)
邓定宇曰:“良知浑然虚明,无知而无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权法;执以是非为知,失其本矣。”又曰:“学贵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面承教议,知静中所得甚深,所见甚大,然未免从见上转换。此件事不是说了便休,须时时有用力处,时时有过可改,消除习气,抵於光明,方是缉熙之学。此学无小无大,无内无外,言语威仪,所以凝道。密窥吾兄感应行持,尚涉做作,有疏漏。若是见性之人,真性流行,随处平满,天机常活,无有剩欠,自无安排,方为自信也。”定宇曰:“先生之意但欲此机常行而不住,常活而不死,思而不落想像,动而不属安排,即此便是真种子,而习气所牵,未免落在第二义。”(《龙南会语》)
人生在世,虽万变不齐,所以应之,不出喜怒哀乐四者。人之喜怒哀乐,如天之四时,温凉寒热,无有停机。乐是心之本体,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失之则哀,得之则乐。和者,乐之所由生也,古人谓哀亦是和,不伤生,不灭性,便是哀情之中节也。(《白云山房问答》)
良知之主宰,即所谓神;良知之流行,即所谓气,其机不出於一念之微。(《易测》)
良知本顺,致之则逆。目之视,耳之听,生机自然,是之谓顺。视而思明,听而思聪,天则森然,是之谓逆。(《跋图书》)
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彼视世界为虚妄,等生死,为电泡,自成自住,自壤自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万变轮回,归之太虚,漠然不以动心,佛氏之超脱也。牢笼世界,桎梏生死,以身徇物,悼往悲来,戚戚然若无所容,世俗之芥蔕也。修慝省愆,有惧心而无慼容,固不以数之成亏自委,亦不以物之得失自伤,内见者大而外化者齐,平壤坦坦,不为境迁,吾道之中行也。
心迹未尝判,迹有可疑,毕竟其心尚有不能尽信处。自信此生决无盗贼之心,虽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贵之心与决无盗贼之心一般,则人之相信,自将不言而喻矣。(以上《自讼》)
昔有人论学,谓须希天。一士人从旁谓曰:“诸公未须高论,且须希士。今以市井之心妄意希天,何异凡夫自称国王,几於无耻矣!愿且希士而后希天,可驯至也。”一座闻之惕然。
诸儒所得,不无浅深,初学不可轻议,且从他得力处效法修习,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学》“格物无内外”《中庸》“慎独无动静”诸说,关系大节目,不得不与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无忌,恣口指摘,若执权衡以较轻重,不惟长傲,亦且损德。
见在一念,无将迎、无住着,天机常活,便是了当千百年事业,更无剩欠。
千古圣学,只从一念灵明识取。当下保此一念灵明便是学,以此触发感通便是教。随事不昧此一念灵明,谓之格物;不欺此一念灵明,谓之诚意;一念廓然,无有一毫固必之私,谓之正心。此是易简直截根源。(以上《水西别言》)
良知灵明原是无物不照,以其变化不可捉摸,故亦易於於随物。古人谓之凝道,谓之凝命,亦是苦心话头。吾人但知良知之灵明脱洒,而焂忽存亡,不知所以养,或借二氏作话头,而不知於人情事变,煆炼超脱,即为养之之法,所以不免於有二学。若果信得良知及时,只此知是本体,只此知工夫,良知之外,更无致法,致良知之外,更无养法。良知原无一物,自能应万物之变,有意有欲,皆为有物,皆为良知之障。(《鲁江别言》)
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人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就论立言,亦须一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拟,皆小技也。(《曾舜徵别言》)
思虑未起,不与已起相对,才有起时,便为鬼神觑破,非退藏密机。日逐应感,只默默理会,当下一念,凝然洒然,无起无不起,时时觌面相呈,时时全体放下,一切称机逆顺,不入於心,直心以动,自见天则。(《万履菴漫语》)
问:“白沙与师门异。”曰:“白沙是百原山中传流,亦是孔门别派,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乃景象也。缘世人精神撒泼,向外驰求,欲返其性情而无从入,只得假静中一段行持,窥见本来面目,以为安身立命根基,所谓权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论语默动静,从人情事变彻底炼习以归於玄,譬之真金为铜沿所杂,不遇烈火烹熬,则不可得而精。师门尝有入悟三种教法:从知解而得者,谓之解悟,未离言诠;从静中而得者,谓之证悟,犹有待於境;从人事炼习而得者,忘言忘境,触处逢源,愈摇荡愈凝寂,始为彻悟。”(《霓川别语》)
从真性流行,不涉安排,处处平铺,方是天然真规矩。脱入些子方圆之迹,尚是典要挨排,与变动周流之旨,还隔几重公案。(《示丁惟寅》)
人心一点灵机,变动周流,为道屡迁而常体不易,譬之日月之明,往来无停机而未尝有所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