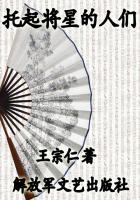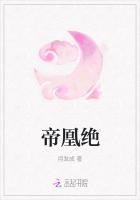——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隐含读者”问题的探讨
儿童文学是按读者区分出的文学类型,按理应特别关注读者的特点和读者接受作品的方式,但事实却有些相反,谈儿童文学的人很少是真正从读者的角度切入、很少对读者的接受心理进行认真地分析和思考的。原因是,人们谈儿童读者只是将其视为一个被动的接受群体,给儿童写作文学作品只是把社会、成人认为重要的东西往他们脑子里灌,把现成的东西往某个容器里灌是不需太了解对象自身的特点的。虽然偶尔也说些要了解儿童的接受兴趣接受能力的话,但一般出自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即在不改变教育内容的条件下作些教育方式上的调整;二是为着作品发行量上的考量,要求顺应甚至讨好小读者的兴趣和能力。但他们所说的兴趣和能力大多是以生物年龄为主要依据推导出来的,是相对客观和固定的,说来说去,也多是儿童的思维是直观的、好奇的、万物有灵的,所以喜欢热闹喜欢趣味喜欢听故事等等。可是,儿童是建构出来的,儿童的兴趣、能力等也是建构出来的。将儿童文学理解为以少年儿童为主要隐含读者的文学,这个隐含读者是作家设定的,他们与其说是读者的代表不如说是作家的共谋者,是作家的“托儿”。但设定又不能完全脱离现实读者,即如马克思说的,既要考虑“主体的尺度”,又要考虑“物种自身的尺度”,使儿童文学中的隐含读者显出复杂的状况。其中最引人兴趣的,就是认为儿童文学中存在着双重隐含读者的议论。
关于儿童文学中双重隐含读者的讨论在西方已很有一些时日了。佩里·诺德曼在《儿童文学的乐趣》中说:“许多理论家都认为儿童文学文本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们拥有两种隐含读者……儿童文学文本拥有‘一真一假两种隐含读者。儿童作为儿童文学文本的法定读者,并不能完全理解文本,对文本来说,儿童更多的是一种借口,而不是其真实的读者’(左哈·夏维特语——本文作者注)。换句话说,儿童文学文本隐含的真正的成人读者比法定的儿童读者懂得更多;文本要求成人读者所掌握的知识和策略库,是法定的儿童读者无法拥有和达到的。”芭芭拉·沃尔在《叙述者的声音:儿童虚构文学的两难》中对儿童文学的接受者进行了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但认为“文本内发言的都只是叙述者,而他(她)所面对的听众,也永远只是受述者而非作品的隐含读者”,这样,作者就把“隐含读者”转变成了“受述者”,将双重隐含读者问题变成了双重受述者的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说,沃尔的说法具有较多的可操作性,因为受述者和叙述者相对,出现在叙述行为层面,而隐含读者和隐含作家相对,出现在作品意蕴的层面,前者比后者较易感受和把握。但这二者毕竟是不同的。王立春的《毛绒绒的梦》(“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你了/我的孩子……”),受述者是“我的孩子”;傅天琳的《月亮》(“妈妈你走了多久我记不清了/你走了我天天晚上趴在窗口念月亮……”),受述者是“妈妈”,她们都不是隐含读者。我倾向继续沿用隐含读者的概念,但具体使用中会参考沃尔的论述。
双隐含读者的最常见的表现是一篇(部)作品既适合儿童也适合成人,即中国人说的“老少咸宜”。“老少咸宜”是从效果的角度说的。能产生这种效果,从文本的角度说,很可能就是同时将“老”者和“少”者作为自己的接受对象,在文本中设有双隐含读者。这有些近似沃尔所说的“双受述”。但沃尔所说的“双受述”是“同一文本有时以儿童为受述对象,有时以成人为受述对象”,窃以为这种现象较难把握,即使有也是少数。“老少咸宜”的情况却是大量的。《海的女儿》表现处在低级存在状态的人为获得较高级存在所进行的挣扎和奋斗,是既适合儿童、少年也适合成人的。中国的《西游记》,如果不特别考虑其文字上的难易,不特别考虑其内容上的某些社会讽刺,不特别考虑其“三教合一”的宗教含义,只注重其成长主题,也是既适合成人也适合儿童的。还有大量的民谣、童谣、民间故事,特别是与儿童生活较为贴近的部分,如三兄弟、三姐妹、三个教训、三个愿望、童养媳、孤儿后母等,大多也是老少咸宜、既适合成人也适合儿童的。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隐含读者”不是具体的个人,也不是某一现实的读者群体,它是文本内作者为读者设置的一个理解作者意图的位置,如诺德曼所说,是一个“知识集”。不同的“知识集”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有界限也不会是刚性的,可以互相重叠、互相渗透、互相融通、互相改造,“老少咸宜”突出的就是“儿童”和“成人”两个“知识集”间共同的部分。如“成长”,不仅少年儿童,就是成人,也存在着一个成长的问题,虽然二者成长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这样,当《海的女儿》《西游记》等作品在较为抽象的层面表现成长时,儿童和成人便成了共同的隐含读者,“老少咸宜”的现象便出现了。
“老少咸宜”可以说包含了“老”“少”两重隐含读者,但也可以说,在这类作品中,“儿童”和“成人”完全重合在一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年龄作为隐含读者设置中的一个因素被极度的淡化甚至被忽略了,是“双隐含读者”的一种特殊情况。所以,我倾向将“老少咸宜”拿出来,不在儿童文学“双隐含读者”的讨论中做过多的关注。本文讨论的“双隐含读者”只指隐含读者中同时包含了成人与儿童、儿童和成人又有明显区别因而有“双重”感觉的那种叙述。这在儿童文学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彼此间还有许多差别。
最显见的双重隐含读者有时并不是由文本自身的题材、主题、作者与读者的对话需要等引起的,而是出于文本外的一些考虑。《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条目曾说,作家们都知道,虽然他们为孩子写作,要将书卖出去,要顺应儿童的兴趣,讨小读者的欢心,但掌管钱袋毕竟是他们的父母,是大人,所以,在说服孩子的同时也要说服他们的父母,让他们的父母、大人也喜欢上自己的作品。为了钱,作家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人设定为作品的隐含读者。如在作品中表现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主题,代父母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和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甚至讲一些大人都觉得有趣的故事等等,使大人觉得钱没有白掏。这或许是最俗气的例子,但类似的以文本外的原因在儿童文学中设定成人隐含读者的情形并不鲜见。比如,一个作者写一篇稿件往一家儿童文学杂志投稿,或写一部作品到出版社寻求出版,他是只考虑读者还是要同时考虑到诸如具体杂志的风格、编辑的兴趣爱好、当前社会的价值取向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而这些多是成人性的。20世纪50年代,陈伯吹先生说过两段很有名的话,意思说审读儿童文学作品,要站在儿童的角度,用儿童的眼睛看,用儿童的耳朵听,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否则,发表出来的作品,成人叫好儿童却不理会。这是对编辑说的。但所以要对编辑说是因为它在编辑那儿是一个问题,即编辑审稿时容易把自己作为成人的思想、情感、审美观念带到审稿过程中去。编辑作为成人的思想情感会影响到审稿活动,延伸开去,会不会影响到创作者?不少作家都说过,他们写稿,是要考虑编辑、揣摩编辑的意图的。更重要的是,编辑是具体的个体又不只是具体的个体,在很多时候,他们是某种权力意志、政策路线、审美思潮、大众习俗的代言者和执行人。在中国,审稿首先看政治标准,作者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和读者见面,就必须首先理解、把握政治上的标准、尺度,让自己的作品为那个标准和尺度所认可,即在某种程度上将那个标准和尺度作为作品的隐含读者。我们很难将这个标准和尺度具体化为某个个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不会是一个孩子。“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歌,叫《唱支山歌给党听》,党是“山歌”的隐含听者。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儿童文学都是唱给党听的“山歌”。又是面对孩子又是唱给党听,或唱给执行党的意志的编辑听,自然就出现了儿童和成人出现在同一文本的“双重隐含读者”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方也存在,只不过出发点可能有些不同而已。利普斯说:“纯正的儿童文学并不存在。那些为青少年读者创作的作品,往往是为作者本人或为编辑们而写的。他们通过对作品文本的投入,通过市场将这些作品传播到青少年读者当中,从而获得其预期的利益。”近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也在向这个方向靠拢。
但此类儿童文学中的成人隐含读者形象毕竟还是基于文本外的一些因素设置的,当作者根据文本自身题材主题审美理想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将成人作为隐含读者引进儿童文学时,儿童文学中的双隐含读者形象便变得较为内在,成为作品有机的构成部分。最常见的就是那些以儿童、儿童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也以儿童为隐含读者,但事实上主要为成人写、以成人为主要隐含读者的作品。如叶圣陶写于五四时期的《小白船》《克宜的经历》等,以儿童、乡野人的单纯、质朴反衬现代都市人的腐化、堕落、退化,主要对话者显然是和隐含作者一样对单纯、质朴等审美范畴抱热烈欣赏态度的成人,但作品以儿童、乡野人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儿童为主要观照视角,内容也对儿童有益,艺术表现也契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儿童应该也是文本的隐含读者(事实上我们也一直是将这些作品作为童话、儿童文学来看待的)。差不多同时,周作人力主童话、儿童文学即“原始人之文学”,“儿童”“原始人”“乡野人”同为童话、儿童文学、原始人文学的隐含读者,虽然作者将他们归入同一“知识集”,但原始人、乡野人中的成人毕竟也是成人,和彼时彼地的儿童不可能完全没有区别。虽在某些作品中同为隐含读者,但彼此间总还是有差别的。英国人布莱克的《天真之歌》、日本人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周作人20世纪40年代写的《儿童杂事诗》,都可以作如是观。
与此相近的是一些作家以自己的童年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人们一般称这些作品为童年小说、童年文学。童年小说是现在的“我”写的童年时的“我”的故事,是人物兼叙述者,是第一人称事后叙述。由于同一文本中出现两个“我”,在不同文本里,两个“我”的距离、思想情感关系等互不相同,形成童年小说一些不同的特点。一些童年文学侧重现在的作为叙述者的“我”,是从成年人的视角回忆自己童年经历的事,现在的成年人的身影较为明显,作品中的隐含读者也主要是成人,主要属成人文学,如鲁迅的《朝花夕拾》、萧红的《呼兰河传》、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另一些童年文学侧重童年的经历时的“我”,视点在故事内,主要写童年时自己经历的或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如任大星的《湘湖龙王庙》、林焕彰的《回去看童年》、吴然的《铜墨盒》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一般都有双重隐含读者。前者以成人为主,儿童为辅;后者以儿童为主,成人为辅。两类作品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从内容上说,它们和我们上节说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也无明显的界限。一些写童年、将童年作为一个美学对象予以赞颂的作品不一定有作家生活的影子但多有作家情感体验的成分;一些写作家自己的童年生活的作品在回忆中都经过时间的虚化、过滤、重组,从自己个人当初的经历中升华出来,获得超越的普遍的意义,已不复是当初自己经历时的面貌了。这时,阅读这些作品,读者无须汲汲于作家个人的生活背景,只需从文本出发,体味其中面对成人和儿童或主要面对成人或儿童的意趣。双重读者的影像在这儿也不是十分分明的。
设置双重隐含读者,更多的还是既写儿童也写成人、将儿童和成人放在一起表现但彼此在趣味情感成长愿望等方面却又不尽相同的作品。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有儿童也有成人,儿童和成人同处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虽然具体的文学作品可以主要写成人而不涉及孩子或主要写孩子而不涉及成人,但二者间的联系肯定是无法割裂的。当作品主要面对儿童和成人重叠较大的那部分生活如主要写学校和家庭时,儿童和成人的身影都会凸现出来。于是,同一作品,就有既对儿童的内容也有对成人的内容;甚至同一问题,对儿童和成人,却有不同的含义。由此形成既对成人也有对儿童、儿童和成人同时成为文本中的隐含读者但对各自的意义却不完全相同的作品。特别是在时代发生转折性变化、人们的成长观念分歧、作者面对主流成长观念进行抗争的时候,文本的这种特征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如程玮的《白色的贝壳》,作品中的作家伯伯忘记了和孩子们的约会,见了孩子又撒谎说自己去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使孩子们突然窥视到成人心灵中并不光明的一角。在孩子,是对成人、成人世界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在成人,面对孩子们的真诚则需一种诚实的反思。作品是为孩子们写的,但对成人有更现实的意义。陈丹燕的《黑发》《上锁的抽屉》《女中学生之死》,表现在新时期到来时,一些少年在启蒙意识的引领下开始主体意识的觉悟,要从成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引起个人和群体、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女中学生之死》中,敏感而脆弱的宁歌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表现这种冲突时,作者写了少年们在面对社会的规训、修剪时表现出的惊悸、慌张、不成熟,但作者更多批评和拷问的却是成人。一种缺少关爱的生存环境,一种冷酷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学校、老师为了升学率不惜摧残人的个性以致身体,社会在少年彷徨痛苦时没有施以援手。人人似乎都在关心宁歌,没有人是杀害宁歌的凶手,但一朵还未绽放的花朵就这样凋谢了。“宁歌是黎明以前爬到这七层楼上跳下来的。那时候大人们在哪儿?男人和女人为了自己的希望累了一天,睡着了……他们没醒。”无声中饱含着悲愤,包含着对社会的控诉和抗议,显然也希望这女孩的死能使一些大人从睡梦中醒来。“他们没醒”,这是一种状态的描述,也是一种呼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人应是这篇儿童小说主要的隐含读者。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利普斯认为:“绝大多数儿童文学主要是由成人来阅读的,尤其是图书管理员、教师和孩子的母亲。”话说得有些绝对,但其中包含的道理还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更深层次,就是一些典型的、从表面上看纯乎只写给少年儿童、只以少年儿童为隐含读者的作品,其实也可能是双重叙述,有着一个成人的隐含读者,包含了与成人对话的内容。佩里·诺德曼说,“一个社会对儿童的观念是一个自我满足的预言”;“成人真正相信的不是儿童天真无邪而是儿童应该天真无邪。”如果我们相信诺德曼,将隐含读者看做一个“知识集”,这个“知识集”自然不是单质的,而是包含了许多内容的集合。就儿童这一“知识集”而言,能力、兴趣、成长需要应是最重要的。而它们无疑都对象着成人的意志、是经过成人修辞的。能力首先指一般的阅读能力,但不只是阅读能力,除阅读能力外,还有把握文体惯例的能力,再造艺术形象的能力,理解生活经验的能力,感受不同艺术美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主要是经由成人塑造的,打着成人的思想情感烙印是显而易见的。兴趣似乎带有较多的个性特征,更多与人的先天因素有关,但其实也主要是社会、成人塑造的。旧时的儿童爱听老奶奶讲狼外婆的故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爱看革命小说,现在的儿童爱玩电子游戏,这些表现在儿童身上的兴趣有多少是与生俱来或由儿童自己决定的?成长需要更主要是由社会和成人决定的了。儿童的能力、兴趣、成长需要主要是成人设定和塑造的,儿童作为一个“知识集”主要是社会和成人设定和塑造的,文本中的隐含读者自然也是社会和成人设定和塑造的,反映着成人的观念和理想。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儿童是像“风景”那样被颠倒着发现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人们从对象中发现的东西常常是自己放进去的东西。这样,儿童文学文本中设定的成人隐含作家和儿童隐含读者的对话,一定程度上成了成人与自己的对话,是成人自己对未来的希冀,是对自己心目中另一个自我的塑造,这或许就是佩里·诺德曼和“许多理论家”都认为的,儿童文学文本拥有“一真一假”两种隐含读者、“儿童作为儿童文学文本的法定读者,并不能完全理解文本,对文本来说,儿童更多的是一种借口,而不是其真实的读者”的原因。如孙幼军的《小狗的小房子》,写两个拟人化的幼儿的一次带游戏性的经历,画面简洁,色调明媚,是较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品。可是,孩子们的单纯、稚拙、天真、美好,不是同样可以使成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吗?特别是那些处在现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中、被各种各样的争斗搞得疲惫不堪的人们,看到孩子们的单纯美好,不是如发现一块生命的绿洲、有一种重回精神家园的喜悦吗?在这些儿童身上,不也对象着成人的理想和对未来的渴望吗?如此,一篇看似“单叙述”、看似只为儿童甚至幼儿创作的作品,其实也有成人隐含读者的身影。这显然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就所有儿童文学文本即儿童文学这一类型而说的,和芭芭拉·沃尔所说的“单叙述”“双叙述”“双重叙述”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二者间绝不是没有联系的。
在同一作品中,又是面对儿童,又是面对成人,有儿童和成人双重隐含读者,可从年龄的角度说,人群不是由成人和儿童两部分组成的吗?既然同时包含了儿童和成人,那就是面对社会全体,为什么还要提出包含了儿童和成人的“双重隐含读者”的问题呢?“儿童”和“成人”合起来固然就是全体的“人”,但将人分成不同的群体,却不只有“儿童”和“成人”这样一种分法。按性别,可以将人分为男性和女性;按职业,可以将人分为工人、农民、学生等;按国籍,可以将人分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等,如此推延,每一种分法都包含、暗示了不同的内容。不说一些儿童文学面对全体读者而是说一些儿童文学包含了“儿童”和“成人”双重的隐含读者,就暗示作品表现的是儿童的问题或成人面对的与儿童有关的问题,如《女中学生之死》表现的就是一个儿童的成长及成人如何对待儿童成长中出现的各种困惑、迷茫、惊悸的问题。儿童和成人是一对矛盾。在许多问题中,儿童为一方,成人为另一方,当文学表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同时涉及儿童和成人,但涉及的内容却是有所不同的。在《女中学生之死》中,孩子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成长中修剪、打击、挫折的问题,成人面对的是儿童在成长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们自己如何做的问题。由于同一作品中出现了不同的隐含读者,二者的要求有重叠但又不会完全相同,创作时就有一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有的处理得好,有的处理得不好。比较常见的缺陷是自觉不自觉地偏向成人,使儿童文学成人化。虽然诺德曼说儿童文学中有一真一假两个读者,真实的读者是成人而不是儿童,但要真的主要为成人而写,那就是成人文学而不是儿童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