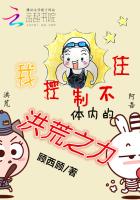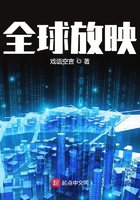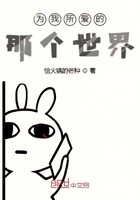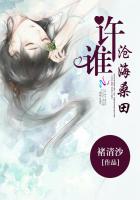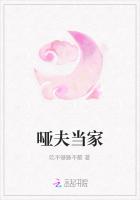程颐主张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性静而情动。程颐在回答吕大临“夫子以赤子之心为已发者,而未发之时谓之无心可乎”的问题时,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论道篇》,《河南程氏粹言》卷一)即认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就是“寂然不动”的“心体”;发而皆中节的“和”,就是“感而遂通”的“情用”。也就是说,“未发”是就心体性言,“已发”是就心用(情)言。这样未发、已发,其“心一也”,是心之体、用而已。不过,“伊川后来又救前说曰:‘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朱子语类》卷六二)。这样,其观点就变成“已发为心,未发为性”,与前边所论形成矛盾。此后胡宏(五峰)明确提出“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五峰学案》,《宋元学案》卷四二),这一观点对朱熹早期的心性论发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三十七岁时提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的思想,此被称为“中和旧说”,因当时是乾道二年(1166,丙戌),故又称“丙戌之悟”。朱熹在四十岁时(1169,己丑),又形成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曾说:“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于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发见处。”(《朱子语类》卷五)但朱熹此时悟到若以心为已发,则心仅为用而难为体,这就与其所主性静情动、心主宰性情之说难以贯通,并悟出心亦分体用。
他说:“只是这个心自有那未发时节,自有那已发时节。谓如此事未萌于思虑要做时,须便是中是体;及发于思了,如此做而得其当时,便是和是用,只管夹杂相衮。若以为截然有一时是未发时,一时是已发时,亦不成道理。今学者或谓每日将半日来静做工夫,即是有此病也。”(《朱子语类》卷六二)即在思虑未萌时,情未发,即为“心体”;思虑已萌时,情既发,此为“心用”,强调不能把心之未发、已发截然分开。可见,朱熹此时对心之体用关系已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心兼体用、已发未发。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则统摄性情,注意到了心、性、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中和新说”(也叫“己丑之悟”)。朱熹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如果认同“旧说”,承认“心为已发,性为未发”,那么其修养工夫就可能只在“已发”上用功,只注意明显的意识活动,而忽视“未发”时的涵养。如主“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心统性情”,那么就会既关注“未发”时的主敬涵养,又关注“已发”时的格物致知,从而与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工夫论相衔接相对应。
在朱熹那里,致知与涵养的关系也表现为知与行的关系。对于知与行的关系,朱熹明确主张知先行后、行重于知。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在这里,主张知先于行,注意到对事物的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从本原上说“行”先于“知”的道理,不过他强调“行”重于“知”则是有合理性的。同时,朱熹注意到知与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如目与足的关系一样。但朱熹所说的“知”,更多的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识,对道德本心的体认;所说的“行”,也不同于今天所说的实践,而更多的是指对伦理道德的践履。
服务于伦理道德的践行,是其知行观的出发点和归宿。
朱熹在修养工夫上,主张“主敬涵养”,强调既要涵养于“未发”之时,也要涵养于“已发”之际。他说:“只是涵养于未发,而已发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于静而无得于动;只知制其已发,而未发时不能涵养,则是有得于动而无得于静也。”
(《朱子语类》卷一一三)即如果只注意“未发”时的涵养,到“已发”时就可能难以控制。相反,如果只注意“已发”时的控制,而不注意“未发”时的涵养,那么到“已发”时就难以收拾。总之,二者必须兼顾,不可偏废。所谓“主敬”,按照朱熹的说法:“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就是要心存敬畏,常存一种恐惧心态,也就是“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朱子语类》卷一二),亦即收敛身心,不使放纵,使心中时常有一种警觉而不外驰,从而达到一种澄明宁静的心理状态,这又叫“常惺惺法”。“主敬涵养”一说经朱熹倡导后,对理学的心性修养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四,“道心”、“人心”与“存理”、“灭欲”。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被称为“十六字心法”。这里提出“人心”、“道心”一对概念,后经由二程始重视并大力宣传,此后成为宋明时期理学家普遍关注和讨论的一个命题。二程说:
“人心私欲也,危而不安。道心天理也,微而难得。”(《心性篇》,《河南程氏粹言》卷二)“道心”是对天理的体认,故“道心”即道德本心或天德良心。在二程看来,“心与道浑然一也”,如果一个人“放其良心则危矣”,即放逸掉道德本心,就会被感性欲念所控制,于是就危殆了,这就是“人心”。所以“人心”就是个体对情欲的意识,其表现就是私心、追求欲望之心。二程是以天理解释“道心”,以人欲解释“人心”,并把二者对立起来,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四)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有所发挥。他说:“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朱子语类》卷六二)又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朱子语类》卷七八)意思是说,心只是一心,都有知觉的活动,觉于义理者就是“道心”,觉于耳目之欲者则是“人心”。也就是说,“道心”是指人的道德意识、道德本心;“人心”指人的感性欲望。朱熹认为,心的虚灵知觉都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中庸章句序》),所以会有道心与人心的区别。也就是说,人都是禀受气以为形体,又禀受天理以为其本性。出于本性的理,形成人的道德意识;根于血肉之躯的气,则产生感性的情欲,所以说“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朱子语类》卷六二)。由于道德意识常潜存于人心灵的深处,故精微;而感性情欲如不加控制就会流于恶,所以就危殆。朱熹这里把道心与人心对立起来,从而也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了。道德修养就是用道心去克服人心,用天理去抑制人欲。由此,朱熹主张要“以克人欲、存天理为事”(《朱子语类》卷三一),“在天理则存天理,在人欲则去人欲”,如果“理会得天理,人欲自退”(《朱子语类》卷七八)。总之,“遏人欲而存天理”(《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下》),正是二程、朱熹理学的伦理目的所在。
心本论与心物、知行之辩———从陆九渊到王守仁在朱熹创立其理学体系的同时,陆九渊也在进行着自己的理论思考。据说他在少年时就不满于程颐的一些言论,曾说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六)的惊人之语,这事实上也是他所建立心学体系的基础。陆九渊后来创立了与朱熹理学旨趣大不相同的心学体系,这一体系在明代进一步被光大,并涌现出以王阳明为集大成者的心学理论。历史上将二者并称为“陆王心学”。学者们常把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分歧的根源,追溯到程颢与程颐的思想差异,以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学,而程颢则是后来心学的源头。诚然,二程在思想上确有差异,如程颐比较注重外在的知识,在方法上强调格物,而程颢则注重内向的体验,轻视外在的知识。但是二者在理学的根本点上是相通的,其差异仅仅在于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和修养方法方面,尚不具有引起此后学派分立的根本动因。
一、朱陆之争与心学体系的初步建立
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分歧是在鹅湖之会上公开暴露出来的:“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指陆九渊、陆九龄)
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六)鹅湖之会上的这种分歧,被概括为在为学之方上是以“尊德性”还是以“道问学”为先的问题。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再加以博览;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泛观博览然后归之约。于是二陆即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讥朱熹格物致知的渐修工夫为“支离”,而称自己的发明本心为“易简工夫”。鹅湖之会不欢而散。此后,他们还以不同方式进行过辩论,其论题也已超出“为学之方”的范围,如曾围绕着“无极而太极”、义利关系等问题发生过争论,从而也暴露出二者在世界观、道德修养论等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本体论上,朱熹以“理”为最高本体,陆九渊则以“心”为最高本体。
朱熹认为“理”是最高本体,虽然“心具众理”,但“心”与“理”并不即是一。他强调主体的“心”应该服从本体的“理”,“理”是可以离开人“心”而存在的观念性实体。陆九渊也讲“理”、“道”,但他却把“理”、“道”与“心”同一起来。他说: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认为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理”是直接合而为一的。
这样,“理”就被安置在人的“心”中,“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与李宰(二)》,《陆九渊集》卷一一)。“心即理”是陆九渊的核心命题,在陆九渊看来,“理”不能超越主体,而是由主体“心”所统摄,这样,“心”比“理”、比万物就更为根本。陆九渊所说的“心”,不同于朱熹的知觉之心,而是指“本心”,即先验的道德理性。他认为,孟子所说的“非由外铄”、“我固有之”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德良心,就是“吾之本心”(《与曾宅之》,《陆九渊集》卷一),而一切不道德的行为,说到底是因为“失其本心”。显然,陆九渊认为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就只有“我”和“我”的理性———“心”,宇宙万物也不离我的“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四),这样整个客观世界就被主观的心所吞噬。陆九渊提出的“心即理”,后来成为心学的基础性命题。所谓的“心即理”,无非是说本心即理,不仅一切皆由心所统摄,而且包括伦理道德原则等在内的一切主观精神,都与宇宙之理直接同一,“本心”成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这是其心学体系的基点。
第二,在为学之方上,朱熹主张“即物穷理”,而陆九渊则主张“切己自反”、“发明本心”。朱熹认为“心具众理”,但人心常为物欲所蔽而不能自明,因此必须通过格物的积累工夫,才能“豁然贯通”,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即体证到“天理”的境界。所以朱熹认为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方法失之简约,陷于空疏,主张人们应该先“泛观博览”。陆九渊则认为“理”实为“吾之本心”,“我固有之”、“非由外铄”,因此无须到“心”外去“格物”,只要“先立乎其大者”,即努力确立和扩充自己的道德本心,通过“切己自反”的内省工夫,就可使“理”“存于心”而“自明”,这叫“发明本心”。陆九渊由此认为朱熹“泛观博览”的方法失之“支离”。可见,陆九渊追求的仍是“天人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他所说的“存心”,其实质内容仍是传统的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他说:“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故“存之者,在此心也”(《与李宰(二)》,《陆九渊集》卷一一),这样,所谓的“切己自反”,就主要成了“存心去欲”的道德践履,与理学的性质和主题相合。陆氏认为朱熹为学“支离”,表面上是方法的不简易,实际上是朱熹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根源是人的本心。由此,二者在工夫论上就发生了分野:朱熹主张“即物穷理”、“主敬涵养”,陆九渊则主张通过“静坐”而“发明本心”,这叫“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五)。故陈淳说:“象山教人终日静坐,以存本心,无用许多辩说劳攘。”(《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八)
朱、陆的论争是理学内部的思想分歧。从思维特征上说,朱熹比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立,而陆九渊则比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两派意见既有不同,所以在此后的思想发展中,“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象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八)。虽然两派在本体论、为学之方、修养方法上有诸多不合,但是正如黄宗羲所说:“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同上)不过,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在当时较之程朱的理学体系要单薄得多,因而无法与朱子学相抗衡。随着程朱理学在元、明时期日益官方化,陆学也渐趋于沉寂。
二、以主体“致良知”为核心的王守仁心学
在明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泯然无闻”三百余年的陆九渊“心学”此时又重新出现了活跃的局面。经陈献章、湛若水等人的提倡,在明代中叶社会的严重危机中,出现了旨在挽救明王朝的统治,以“破心中贼”为己任并足以能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黄宗羲说:“有明学术,白沙(陈献章)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一○)
阳明心学是作为统治中国思想界几百年的程朱理学的对立面出现的。程朱理学官方化的直接后果,一是理学家的经注、名言、语录成了士人获取高官厚禄的工具,浮虚和空疏的风气愈加蔓衍;二是造成了思想界陈陈相因、墨守师说的僵化局面。理学本来是要启发传统伦理道德的自觉的,然而朱子学后来导致的僵化教条之风,却使知行脱节、言行不一,人们“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结果“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人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以下只注篇名)。所以,王阳明疾呼“今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与黄宗贤》),其心学正是为“补偏救弊”,即补朱子之“偏”以救时势之“弊”而发。
王阳明早年也是笃信程朱的,后来他对程朱理学发生了怀疑并转而归向陆九渊。王阳明对朱子学的怀疑,是从体验“格物致知”,因“格竹”失败而开始的。
他二十一岁时曾“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为了体验朱熹所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遂对着亭前竹子做“格物”之功,然却“沉思其理不得”
(《年谱》),未有结果,但此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后被贬官贵州龙场,仍常“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一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这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他认为朱熹以“格物”来“穷理”,实际上把“格物”与“天理”分为二事,于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年谱》)。从此,王阳明便与程朱“格物”说决裂,由“外心以求理”转向“求理于吾心”(《传习录中》)的“圣人之道”,提倡“心理合一”、“知行合一”之旨,阐发心学理论,实现了从“理本”向“心本”的转变,晚年则专讲“致良知”,使其以道德实践为宗旨的心学体系臻于成熟。
从王阳明思想发展的逻辑看,其心学体系由三个依次提出、相互联系的命题构成,这就是“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如果说“心即理”、“知行合一”是其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立言宗旨”,而“致良知”则是贯穿其全部学说的中心观念。
1.心即理
王阳明把“心即理”称为他的“立言宗旨”。“心即理”固然是为“补”朱子“析心与理为二”之“偏”而提出的,同时也是针对当时学风空疏、言行不一的“时弊”而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