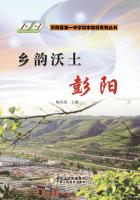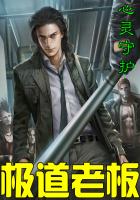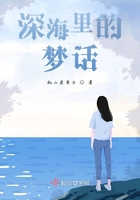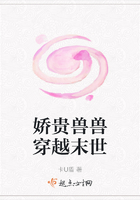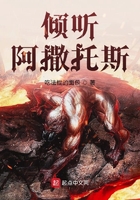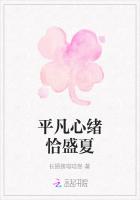以亲身经历作为作品的情节基础是“萨米亚特”的特点,哈维尔的剧本《观众》,瓦楚利克的小说《捷克梦之书》,也都写到自己在底层的经历,生活的日常性及其悖谬。这一点使人联想到源于18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诉求:艺术的本真性在于通过亲身经验,形象地表现生活。但是,浪漫主义思维认为价值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人们唯一面对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今天,在许多人眼里,这种思维的实际效果仍然与政治压迫夹缠不清。“萨米亚特”作家恰恰在这点上有所不同。他们保留了中世纪的信仰背景,把价值看作一种超验的事实,认为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造的。自传性叙事代表了一种个人主义理念,以及从个人角度观察世界的重要性。而相信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世界,又使他们得以拒绝任何主观的建构理性和浪漫主义激情,坚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经历了“布拉格之春”,作家们带着惊愕的眼光,看到自己的国家又一次被掷进一个荒诞的世界。在奥匈帝国统治下,19世纪捷克作家曾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这些前辈相比,“萨米亚特”作家的视野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宽广,他们着力刻画的是个人在极权社会里的存在境遇,自我的疏离与异化,因而可以称为一种个人现实主义的创作。
卡勒尔·佩克的小说《乔治先生》写了一个孤独者,这是一个内心与社会分离的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独自住在公寓里,富有的美国妻子远在国外,每月都给他寄钱来,但当妻子要他出国时,他的平静生活却被扰乱了。过去他想出国,得不到批准,如今他不想出去了,他们又催他赶快办手续。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一天的活动:很晚才起床,刷牙洗脸,喝咖啡,想着天花板上的污渍。然后穿过街道,漠然地看着发臭的运河,在熟悉的小店买报纸和雪茄,在小吃店吃快餐。然后又是回家,喝咖啡,看报,睡午觉。在酒吧里,他遇到一个喝醉的女人,把她带回家。结果她吐了一床,惹得他大发雷霆,半夜里把她无情地赶走。第二天,主人公又在酒吧里喝了不少酒,最后突然发病死去。
这人物让人想到加缪的《局外人》,但却没有加缪作品中那种对绝对的激情。克里玛曾说,布拉格像它的现代史上几位总统的死一样,像它曾同时诞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大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一样,充满了悖谬。人们常常把“萨米亚特”文学看作是卡夫卡式的写作,但它其实也是哈谢克式的写作,如特勒弗卡、邦德、乌德和佩克等人的作品,都属于那种典型的捷克小说,即捷克哲学家哈耶克所说的“悲伤的欢笑”。
普鲁恰日科娃的《来尝一尝》,同样写了一个道德麻木的故事。一个女人怀孕之后,痛苦地躺在房间里,她的男友却一走之,去了国外。通篇故事都是她与妹妹的对话,她在房间里的活动,她与男友在电话里的通话。而那个有家室的男人始终没露面,只是给她寄去一张明信片:“这儿的啤酒不错。来尝一尝吧。我爱你。”然后又打电话邀请她出国,并且抱怨这个国家不自由。这篇小说与佩克的小说一样,都是很平常的故事,冷漠而不夸张的叙述,通过一种荒诞的眼光,审视那些灰色世界中的个人。在所谓“正常化”时期,犬儒主义和道德腐蚀成为社会的突出特征。当局为了表面的稳定,强制宣传制度认同和民族认同,但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真正面临的危机却是自我认同。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生活有何价值,即使他们的内心是真实的,他们的行为也永远是被动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有损尊严的事实变成了个人的宿命。
许多作者都在作品中有意显示出社会的背景,以此表明人性的缺失并非与时代无关。极权社会扭曲了人性,而扭曲的人性反过来又支撑着这个社会。然而,正如克里玛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文学家当然要描写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冲突,却不应当必然地假设这个世界比自己更坏。大多数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生活在谎言中,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着承认它的东西。尽管人们内心什么都不相信,但表面上人人都很顺从,甚至似乎和当局达成了一种游戏规则——至少大家要装作互信的样子。于是,基本道德的崩溃构成了每个人的现实。通过小说的形式,作家们探索了人性最深刻的本质。
“萨米亚特”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但一些作家也复活了捷克的传统小品文。这种夹叙夹议的文学类型,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国内外事件及自身状况加以叙述和评论,在恰佩克时代就很流行,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哈维尔、科赫特和克里玛以及其他作家都经常采用这种形式写作,但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家还是瓦楚利克,小品文的形式到了他又有了新的发展。作者虽然常常写的是政治题材,却并没有放弃美学关怀。在他笔下,朋友间的趣事,咖啡馆的谈话,传讯室的交锋,安全人员的蛮横,都生动有致,很有一种讽刺、冷漠和顽强的风格。哈维尔曾说,瓦楚利克的小品文“创造了一种原创的形式,在其中他的个人思考、他的观点和经验与主题论述融为一体,并被重新巧妙地安置到艺术的细小结构中,其效果远远超过读者对这一文类的期待”。读他的作品,读者不但会觉得其中的政治思考发人深省,那些描写人的细节也同样使人感到愉悦。
比如,《妖魔》讲述作者在咖啡馆遇到一个天真的伊拉克游客,他们谈到阿拉伯神话里那个宝瓶和妖魔的故事,讨论如果妖魔再跑出来,怎么把它弄回去。他们又谈到旅游,那个伊拉克人说,他去过许多地方,发现布拉格比雅典更自由。这番话使作者哭笑不得,但他不禁又想到,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也许自由的观念会显得更加繁荣,因为在那里,人们更能体会到生活目标对抗制度目标的力量,正如文章最后所说,妖魔又跑了出来,但“妖魔只能在上空盘旋,就像它在荒漠的沙丘上飘浮,却不能改变沙子的本质”。在《发言人的葬礼》中,作者本打算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却接到警方的传唤,并被带到警察办公室。两个警察坐在旁边聊天,也不来询问他。作者为了消磨时间,只好一边阅读一本讨论捷克民族性的书,一边想象着葬礼的情形。书中内容与葬礼想象交织在一起,意味深长。葬礼结束,警察宣布他可以回家了,当作者赶到墓园时,只看见空荡荡的墓地。作者最后写道:“你不可能真的错过一个葬礼,只有活着的人你可能错过。”作者善于把感情内敛在冷静的叙述中,然后在结尾笔锋一转,引出一个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哈耶克称他的作品代表了“将政治升华为文学的东欧写作”,确实是精当之论。
瓦楚利克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萨米亚特”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文学,瓦楚利克像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为此,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作家失去了太多的个人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社会边缘化。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出版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热烈鼓掌,通过向“萨米亚特”表示敬意,那些在胡萨克时期获得巨大好处的人,一夜间就撇清了自身与政权的共谋关系。在座的作家契卡洛娃本想站起来,质问出版商为什么现在才说出这话,但最终她还是忍住了。也许,这就是“萨米亚特”作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其名著《论出版自由》中,曾经这样说道:
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20世纪的捷克作家再次践行了这一信念,他们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
浮出水面
上世纪50年代,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写了一部科幻小说,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官方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作是犯罪。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过上岸上的生活。多年后,另一位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在文章中引用了这个故事,并把它作为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的一个隐喻。
萨米亚特这个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西文词语。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实行过书报检查制度,这种制度显示了统治者对思想的垄断,要由权力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事实上,检查制度常常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力。三百多年前,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就曾表示,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与恶的能力,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弥尔顿此文的副标题便是“论未经英格兰议会许可而出版的自由”。与弥尔顿一样,苏联、东欧知识分子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变化的时代,其萨米亚特写作正是对弥尔顿出版自由主张的拥护。这些作者同样坚信,没有人能代表自己作出对善恶的判断,发表个人言论是人的天赋权利,包括未经许可而出版的自由。就像巴兰察克说的,一个生活在水下的人想浮出水面,是因为他的肺受不了,他想要呼吸。
有的研究者把苏联30年代政治反对派的著作也归入萨米亚特,但更多研究者使用这个词,主要还是指50年代以后出现的那些民间地下出版物,他们的言论已经突破了正统的意识形态框架。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对权力的渴望和维护。权力者深知一切精神生活最终都会导向自由,将所有出版机构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书报检查制度比任何时代都要更加严格。1965年,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官方迅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以重刑,此后作为一种抗议,大量的手稿、打字稿冲破检查制度的封锁,开始广为传播,很快成为苏联社会一种充满活力的、非官方的文化现象。像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人,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索尔仁尼琴并在1967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自50年代起,东欧各国就不断发生反抗体制的事件,诸如东德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等。经过多年统治,斯大林体制越来越暴露出极权本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思想也遭到严密禁锢,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众从最初的乌托邦迷思中醒来,开始为自己争取自由。这些反抗最终都遭到武力镇压。新的统治层上台后,往往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异见作家、学者被送进监狱,或失去公职,作品遭到禁止。直到1976年8月21日,瑞典外交部长斯万·安德森提起八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还这样说道:“这是民主和自由的一次失败。同时它显示出极权社会的不人道。公民们要求更多地参与决策,要求选择的自由,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全副武装的坦克和监狱。而且直到现在人民还被迫沉默。”然而,正是这种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戳穿了政权早期许诺的自由谎言,催生了萨米亚特的表达方式。
在一次访谈中,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回忆起捷克萨米亚特的产生。70年代初,一批遭禁的作家开始每月一次在他的寓所聚会,这些作家朗读自己的新作,并把作品手稿打出来装订成书,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不久,其他的人也仿效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还有爵士音乐、流行音乐和民俗音乐的拥护者,以及拒绝由官方出版作品的年轻作家。”写作的范围也从文学扩大到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波兰萨米亚特则是始于70年代中期,1976年,波兰第一份未经审查的文学刊物《记录》诞生,波兰最著名的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担任编辑,并时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此外,一些不能公开出版的著述也采用了地下出版的形式。匈牙利萨米亚特同样是始于这一时期,诗人米克罗斯·哈拉兹特早在1973年就通过这种方式出版了其著作《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遭到逮捕和审讯,而80年代初杂志《讲述者》的问世更是推动了萨米亚特的发展,这个杂志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哈拉兹特和哲学家杰诺斯·基什。东欧各国的萨米亚特作者还常常互相关注和支持。如在1977年,东欧各国知识分子就曾签名抗议捷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签署者的审讯。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很快也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克里玛后来解释道:“有一个东西使萨米亚特跟捷克其他文化完全区别开来:它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两者之外。”回归自由的思考与写作,这也是所有东欧国家萨米亚特作品的共同特征。
在一个审查制度的文化里,每个人都被迫过着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即使有时能公开发表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但由于预先考虑到要面对审查,作者的表述仍然会被迫含糊不清,甚至夹杂着必需的谎言。巴兰察克曾写道:“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甚至甚于审查官的红铅笔。”这样的损害常常导致作品主旨与作者意图相左。久而久之,作者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发表的东西就是自己原初的思想。语言本身也受到了伤害,在那些公开的文字中,诸如自由、民主、人性等都变成了毫无实义的虚构概念,苏联学者雷达里赫曾把这种现象称为语词的“功能性虚构”。词语与真实脱离了关系,人们失去了称呼事物真名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人们渴望对现实有更直接的表述,渴望真实。萨米亚特的形式改善了写作者的心灵环境,使得作者能摆脱审查与自我审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使得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其主旨,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内心交流,并最终表明压制人类思想和言论的任何企图都是无用的。正是在思想的表达和语词的还原方面,萨米亚特成为生活本身的捍卫者,促成了东欧各国人民的心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