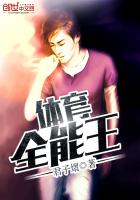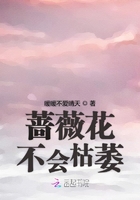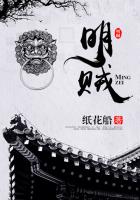——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
一、孙中山“革命”研究的“后设”诠释问题
陈锡祺先生在50年代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究起于何时以及如何而产生,这是今天学术界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页75。无论数十年来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述如何车载斗量,近年孙中山研究新潮表明,陈先生所提的问题仍具时效。“革命”的意义与时俱进,因此对孙中山的革命遗产的诠释,与不同思潮相激荡,投映出不同时代欲望的镜像。但长期以来,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缘起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问题的症结,我认为,却与一些基本史料的理解和使用有关,且史家未能在“革命”的历史性及其“后设”的诠释性之间作有效的区别。这里涉及一系列有关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简言之,语言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历史的“再现”与“叙述”中语言、修辞、风格等所起的“中介”功能,如何对待思想话语形成过程中的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语言的中介作用常常同历史再现或历史叙述所声称的“真实”产生张力,而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离不开新旧“形式”的交替嬗变,它既为历史主体所创造,也时时制约着主体的主动性。
本文通过对孙中山在1897年前后与“革命”话语关系的释证,说明他接受日本人的影响而正式自称为“革命党”,不仅促成传统“革命”话语的某种现代转折,对此后中国革命产生巨量的影响,也提出一个有关孙氏文化抉择上戏剧性转变的饶有兴趣的问题。自英伦被囚、遭港督驱逐之后,他不得不将反清基地从香港移向日本,这本身在政治上蕴涵着对于西方的失望,而在这当口他对“革命”口号的接受,说明这失望更属文化上的。尽管他深受西方教会文化的熏染,且他的伦敦被难,置死地而后生,亦直接受惠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和绅士文明,然而他所接触的英语世界在滋养他的“革命”精神方面,殊缺乏文化上的“源头活水”。孙中山自称“革命”,是受到当时喧腾于日本朝野的“支那革命论”的诱惑,或许更重要的,这唤醒了他埋藏内心深处的有关“汤武革命”的秘密梦想。这一传统“革命”话语同他的其他革命思想的脉络交织在一起,固然奏出在中国革命场景里不可或缺的“暴力”主调,其蕴涵的实际诉求亦包括——政权的法定性与“革命”传统的本土性。
我的结论并非依靠某些石破天惊的新材料,而主要是建立在对现有的有关史料的辨析和推断上。学者普遍认为,由于缺乏新材料的发现,对于辛亥革命以前,特别是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孙中山研究,较难获得突破。见桑兵:《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中山大学论丛·孙中山研究文集》,第4集,1986,页126。早期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画像,罗家伦、黄季陆的《国父年谱》代表一种倾向,即以孙中山自述“有志于革命”,“始决倾覆清廷”为根据,强调他暴力反清的一面。这也是台湾的孙中山史学的主流。另一个主流启自于70年代末重新起步的大陆孙中山研究,以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为代表。对孙氏革命思想之源的诠释,侧重他倾向“共和”的思想脉络。力主“共和革命”为孙中山早年思想主线的,参桑兵:《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页126—228。如果说以往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起源基本上以“后设”观点的诠释方法入手,本文首先将“革命”处理为一种历史性、物质性的语言现象,从探索语源的方法入手。在提问上我想另辟蹊径:孙中山从何时开始使用“革命”一词?其使用过程中的历史境遇是怎样的?主客体之间形成怎样的关系?这一考释方法遵从传统考证学的实证性,但与之相区别,即把“革命”视作一种“话语”,通过具体的时、地、人,追踪“革命”一词的流通环节,在更为深广的文化思想的背景和脉络中探寻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考虑的因素包括人的动机、性格及其集体无意识,到理论话语的生产过程与社会条件等。在当今流行于欧美学界的有关文本、文学乃至文化理论中,“话语”(discourse)这一概念犹如万花筒,其歧义难以得到恰当的描述。其基本含义是对话,包括言说与书写形式、其表述或再现的场域,于是涉及社会条件,即所谓“境遇”(context),又涉及意义、诠释等范畴。但始自60年代末,福柯(MichelFoucault)的“话语”理论不仅以“欲望”和“权力”的范畴界定话语,亦将欲望和权力带进话语的场城。他不仅强调言说者的主观欲望,更强调约制言说者的权力机制(institution)与再现程式(convention)。自60年代初,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事物的秩序》中,对西方16世纪以来的文明构成即所谓“知识话语”进行了质疑、解构的历史追踪,书中所隐含的“权力”主题,显然在1968年的未遂“革命”之后,浮现于福柯的“话语”论述的前台。关于构成话语意义的机制似乎更趋复杂,体现在“技术运作过程、机构、一般行为模式、传播和散发形式以及教学形式中”(“HistoryofSystemsofThought”,1971)。
的确,福柯所描绘的话语主体并无多少自由,甚至他所追踪的“知识话语”历史,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运作与构筑。自我为一定的技术、学术场域所规范,在书写话语的同时,亦为话语所书写,他不自觉地受到一系列话语规则、符码、程式的操纵,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是“作者”并不重要,因此也可称作“死亡”。
“话语”突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亦突出了人的主体为语言所构筑的事实。福柯对从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的人文科学话语的历史状况的“考古学”表明,文化的秩序也是言词的秩序。在“求真意志”(thewilltotruth)或“求知意志”(thewilltoknowledge)的趋动下,话语者所运作的是一种“排斥机制”(asystemofexclusion),即排斥所有不符合话语规则、符码、程式的可能,最明显的莫过于对于“疯狂”言行的界定与控制。
福柯被称为“后结构主义者”,因为他自觉意识到自己与现存知识话语的吊诡关系——在揭示知识话语的生成“迷思”时,自己既是这一话语机体的历史延续,而自己的文本再现——必然作为一种知识话语——与历史话语的权力机制应当形成怎样的关系?在福柯那里,我们可找到结构主义的思想成果。如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是一种结构,意义在结构中呈现,语言构成具随机性,然而一旦形成,便具有不为人所左右的文化程式。但福柯不像结构主义者那么乐观,即以为只要发现一成不变的结构,便万事大吉。在描述西方人文科学话语与主体意识的历史形态时,他强调的是历史的断裂与多样性。福柯并非意在提供一种新的历史叙述,他的叙述文体的本身师法尼采和马拉美。与他的非线性、非理性、非因果性、非境遇性的历史叙述相一致,他有意使他的历史文本诗化,试图以“疯狂”语言逃脱甚或颠覆现有的话语权力网络。
本文所谓的“话语”虽在很大程度上折衷于福柯,然而照怀特(HaydenWhite)的说法:“如果说福柯无意于将单个专门的科学著作或集合的著作同它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境遇联系起来,那么他对于将它同它的作者的联系更缺乏兴趣”(“FoucaultDecoded,”1978)。我的释证方法远非激进的,相反的我要说明的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短时间里,“革命”话语通过几个思想舞台的“要角”的传播,却呈现了迅速整合的进程;同时他们也受到传统和现代技术机制的操纵,而在社会思潮的背景上,当大众由惊骇于“革命”转向欢呼“革命”,意味着迷狂已被穿上理性的语言外衣,这些要角也是被牵线的傀儡而已。
这里提到的“时、地、人”,是考证术语,如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所表述的。暂不论他的“古典”、“今典”等“通解”的“释证”方法,他的“忽庄忽谐,亦文亦史”的历史诠释,在语言使用上与福柯有异曲同工之趣。《柳如是别传》并非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这也不单是一种评传,也是诗的诠释(原书题为《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且不说陈寅恪仍坚持他的“背时”的书写风格,也不论“著书唯剩颂红妆”所引起的有关作者伦理与专业的异议或非议,此书的叙述风格具有强烈的象征姿态,蕴涵着他对中国史学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反思。
《柳如是别传》中大量的考证文字作为正文,从传统的诠释谱系来看,将疏解、评注与原典融为一体,与中国史传或小说评点传统相涉,亦引起如狄尔泰(WilhelmDilthey)所说的作者与传主之间的主体表现的有趣问题。而这里陈寅恪先生违背的是现代历史的书写规范,亦即着意摆脱他曾经接受的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所笼罩的欧洲现代史学传统。如果说,陈先生早期的史学实践表明一个经受现代训练的历史学家,那么他的《元白诗笺证稿》表明他的治学兴趣更潜入民族的情感史与心灵史,而对史学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更趋向“象征”特征,虽然在以诗证史方面上未完全摆脱实证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柳如是别传》似是以史证诗,在严格遵循考证方法的同时,并不回避他主观的动机。陈寅恪晚年的史学取向无疑有其政治性,但其意义更是文化上的。由《柳如是别传》所示的对史学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反思,与福柯始自60年代的改写史学模式,殊具“普世”性。
对于孙中山与“革命”话语之间关系的考释,大部分是对孙氏与“革命”的有关材料的清理。这只是孙中山研究中一小部分,然而毋庸讳言,是最重要的部分。辨明他在1897年与现代“革命”结缘,并不否认他在此前有可能接触到“革命”思想,亦不止于辨正孙中山“革命”时刻表的误差,更不打算将他的革命源起约化为一个话语问题。本文更关注的与其说是孙中山个人革命思想的缘起,不如说是他和那个在20世纪之交迅速成形的现代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实即将他个人的作用与“革命”话语形成之间的关系,作一种辩证的、历史的考察。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必须以其使用“革命”一语为标志,但弄清“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后设诠释意义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孙中山研究中无可回避的课题,也有利于将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处于一种更为客观、批判的观照之中,有利于体现历史学的现代性。
孙中山研究中语言问题一向存在。他在1923年作《中国革命史》,开头云:“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这里自述“革命源起”,对官方史学撰写民国史,无异于一锤定音。尤其是中山自述《有志竟成》中说到1885年之后他在香港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便进行反清宣传,所谓“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按:《有志竟成》原为《孙文学说》第八章,后被单独抽出,置于《国父全集》之首,题曰《自传》。。这“四大寇”故事,经过后来陈少白、冯自由、罗香林等人或回忆、诠释与研究,成为孙氏最富英雄色彩的“革命”传奇。孙中山在生前多次谈到他自己的革命源起,但从不讲清楚。在上面自述中“鼓吹革命”,“非谈革命无以为欢”等语,造成一种历史错觉,似乎他在当初的反清言论中,“革命”这一字眼已经出现。作为一个政治家,孙中山考虑的并非历史的真实。问题更在于,这在客观效果上勾画了一个“革命”先知先觉的自我画像,意味着他始终是“革命”的创造者。“革命”口号仿佛自天而降,其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历史过程被遮蔽。如果按照史实,孙氏的早期反满活动,曾接受会党的“光复”口号,或传教士的“造反”的译语,则蕴涵某种主体的被动性。
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由于严峻的政治现实,孙中山研究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最典型的莫过于罗家伦等人编的《国父年谱》,其中孙氏的《有志竟成》和《中国革命史》理所当然地被作为叙述的主体。那些含糊其辞的自述“昌言革命”等语,都被当作坚证的史料而加以征引。一方面,由于孙中山遗体的缺席,年谱的叙述本身不仅必须成为他生前“革命”的见证,也必须成为以“反共复国”为宗旨的“革命”载体。另一方面,对于孙中山“革命源起”的自述的绝对尊重,也即表示睹其文而聆其音,其文体获得了遗体的同等意义。因此在铸塑一个“天纵之圣”的“国父”形象之时,《国父年谱》本身也呈现为一个纯粹的首尾一贯的“革命”叙述体。
30年代中据陈少白回忆,1895年广州暴动失败后,他同孙中山亡命日本,见日文报纸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氏遂自称为“革命党”。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35年初版,1956年再版),页12。稍后,国民党史家冯自由作《革命二字的由来》一文,将陈氏的说法加以引申。冯自由:《革命二字之由来》,《逸经》,第1期(1936年),页29。这样的说法对于孙中山自述产生某种抵触,因此《国父年谱》对于这条材料断章取义,也就不足为怪。重要的是,陈、冯的说法所包含的对“革命”一词历史性的语言意识,以及将孙中山“革命”历史化的意向,在台湾的孙中山史学中不绝如缕,且形成挑战的潜流。如吴相湘、周弘然从“革命”的翻译或使用角度提出问题,尤其是罗刚的《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初稿》之作,旨在颠覆《国父年谱》。他在1889年谱中涉及“四大寇”时,指出“其时尚无‘革命’口语,四人所谈者,均为反清造反之事,亦只相聚密谈,不能公开昌言”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初稿》(台北:正中书局,1988),第1册,页220—221。。他在《罗编国父年谱纠谬》中,公然提出:“为国父作年谱,并非国父所言,全不可变更,反非国父亲身经历之事,为事后追述者,或因记忆有误,或因未及考证,间有错者,自应更正。”罗刚:《罗编国父年谱纠谬》(台北:正中书局,1962),页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