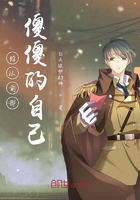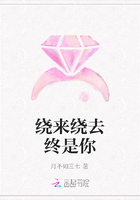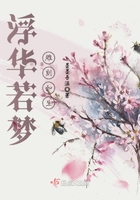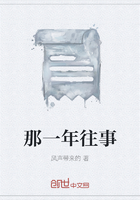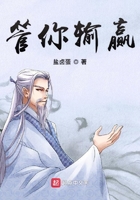《庄子》的《天下》篇总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历述先圣以来,至于己之渊源”。首述儒家学说的渊源和主要内容,批评其“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致使“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认为儒学使“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痛陈儒学的迂腐害世,混淆是非,表现了儒道鲜明而尖锐的学术对立。次叙墨家学派“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批评墨翟禽滑厘之说“其意则是,其行则非,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再叙宋尹文之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批评其“为人大多,其自为大少”。再叙前期道家之说“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批评彭蒙、田骈、慎到等人不懂得什么是“道”学,“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再叙关尹、老聃学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极力赞赏老聃之“道”,可谓“至极”,称道老聃其人“古之博大真人”。最后称述庄周自己的学说为“寂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为什么庄子在排列当时的学术流派之成就与地位时,首述儒后未说己?因为儒家思想首先是道家人物最要打倒和批判的东西,它们乱世害人;而自己的道家学说渊自深远,博采众长,王夫之先生认为庄子“以己说缀于其后”,是为了“表其独见独闻之真,为群言之归墟”,如此首儒后道,儒道遥相对峙,从而见出两家之为主派在当时首尾呼应的争鸣辩驳之情。那么,《庄子》寓言与儒学之关系已如前述,它与道学之关系又如何呢?本节拟作简单的探讨。
一 《庄子》寓言与道的内涵
儒家学说对于现象世界的认识拘限于对已知的现实世界的存在性作出合理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只承认现实世界应该是这个样子,即类似于那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类的存在主义哲学,所以,他们极力维持现实世界特别是现实社会的现存秩序,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论来看,儒家是保守的,甚至是复古的、法先王的守旧主义者。与此相比,道家思想以其开放性、辐射性思维要穷根究底关于世界和现实社会的本源以及宇宙天地、人间万象的未来走向,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理想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是个什么样子,世界按照一种什么方式或规则在运行、发展和变化着……所以,他们对现实社会和现存制度多做否定性的认识甚至试图做出多方面的改造与变革,现象世界中的一切万有,都应该从某种生成发端学的高度得到解释,从而提出了他们“道”为万物之母的“道德”学说。那么“道学”之道有哪些基本内涵呢?我们从《庄子》寓言中来寻找答案。
《庄子》寓言凡涉及“道”的有(举其要):《齐物论》篇“庄周梦蝶”,《养生主》篇“庖丁解牛”,《德充符》篇“豚子食死母”,《大宗师》篇“南柏子葵问道”、“子贡问孔子道”,《应帝王》篇“浑沌之死”,《胠箧》篇“盗亦有道”,《在宥》篇“黄帝问广成子道”,《天运》篇“东施效颦”、“孔子问道于老聃”,《秋水》篇“庄子钓鱼濮水”,《至乐》篇“庄子鼓盆而歌”、“鲁侯养鸟”,《达生》“佝偻承蜩”、“津人操舟”、“吕梁丈夫蹈水”、“纪渻子养斗鸡”、“梓庆削木为鐻”、“工倕旋盖规矩”,《田子方》篇“奔逸绝尘”,《知北游》篇“孔子问老聃道”、“东郭子问庄子道”,《寓言》篇“罔两问景”,《天下》篇“慎到弃知”、“田骈学道”、“关尹老聃”等等。统计发现,在涉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相关学科领域的《庄子》寓言中,反映道家“道学”文化的核心实质问题的寓言在数量上最多,这个现象体现了《庄子》寓言有所侧重、以己为本的特点。对上述寓言进行反复研究,我们发现,道家思想关于“道”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界关于道家之“道”的多种义界与解释都始终在这三个方面上打转转而争论不休。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对这种争论做一个大胆的“了结”,以祈教于方家。
《庄子》寓言所揭示的“道”的第一个方面的内涵是“道”为宇宙万物之母,“道”是产生天地万象的本体性的客观存在。
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东西,是产生物质世界的根源,《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是说,道产生浑然不分的统一体(一),由这个统一体产生阴阳二气(二),再由阴阳二气产生新的统一体(三),这个新的统一体就是形态各异的众多物质,再由这个新的统一体产生天地万物(万)。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气”的形成与变化,亦即气(阴阳)也是由“道”产生的,同时,气也产生天地万物,是产生天地万物的一个元素。受这个宇宙生成论的影响,庄子认为“道”就是天地万物、宇宙自然的母体,是现象世界得以形成的根源,他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庄子这番话阐述了五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认为“道”是一个本体,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形态,是万物之母,即所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
其次认为这个“道”作为本体,其特征是可以不断地传承下去,即所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再次认为“道”具有无穷的超越性,即所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再次认为“道”具有笼盖时空的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神秘性”,即所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最后阐述“道”作为本体的实用价值,任何人得之都可受用,比如“黄帝得之,以登云天”。
为了给这个产生宇宙万物的“道”以一种观念形态的评价,庄子用“气”来替代“道”的生成特性,认为气是产生万物的基本因素,气的变化决定着世界万物的产生和发展。他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的意思是,虚而无形的道产生气,气又产生有形的物质。庄子又说:“伏羲氏得之(指”道“—引者注),以袭气母”,成玄英疏曰:“气母者,元气之母,应道也。”气与道,同质而异名,同为万物之母。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由气产生,也就是说充斥在天地宇宙之间的就是气,所以他又说:“游乎天地之一气”,“通天下一气耳”。成玄英对“天地之一气”注疏为“阴阳之气”,又统称为气,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人也是由这元素变化而来的,所以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宣颖曾注云“万物之生死,总一气也”,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亦即由道产生的。
了解了上述庄子关于“道”的第一个方面的内涵有如此多层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来把握具有这些内涵的《庄子》寓言了。
《知北游》篇有一则“孔子问老聃道”寓言: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女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女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
这则寓言,虚构孔子向老聃问道的情节(类似情节与人物的寓言在《庄子》一书中凡6见),老聃向孔子讲述“道”的本质内涵,基本上覆盖了我们在上面涉及的五个层面,而其中心旨意则是阐述“道”的本体论、生成论意义,即寓言末尾所说的“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万物源源不断而生都是依靠“道”,“此其道与”四字情不自禁地流露了老聃对“道”的精辟概括之意。有意思的是,凡6见孔子与老聃关于“道”的寓言,通过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来辩难“道”的内涵和主旨,而孔子始终居于蒙昧下风的地位,体现了庄子道家之“道”对于孔子儒家之“道”的绝对胜利,反映了两种学术思想对于世界现象的截然不同的理解与优劣,儒学之被道家蔑视,儒学与道学之争的情景,于这些寓言中可见一斑。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几则寓言透露的当时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以便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判。
再来看《大宗师》篇“子贡问孔子道”的寓言:
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待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人之生死,万物之变化,都是由气来决定的,“造物者为人,游乎天地之一气”;“气”又是由道产生,万物得其道,则万物得其为万物,犹如鱼得其水,故相忘乎江湖,人得其道,故相忘乎道术。庄子这种“气”为万物之形成要素的“气”论思想,造就了他对待事物生死成败的开朗而又科学客观的生命理念,生为气之聚,死为气之散的思想,对于为人类在生死面前做出坦然从容的抉择提供了一条乐观向上的路径,使人们能从烦杂苛重的名利观中摆脱出来,对于在痛苦中挣扎和备受挫折的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指出了释放忧愁的方向。庄子在面对自己妻子的死亡时,就是这么达观放旷的,请看“妻死鼓盆”的寓言: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人的生命这个实体,是由气决定的,“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万物的形成、发展、变化都决定于气,因此,气的终结,也就是生命的死亡,这是很合乎逻辑的科学发展、必由之路,故面临死亡时,又有什么可忧惧担心伤感的呢?纠缠于死,是“不通乎命”的表现。乳猪见到母猪死了,知道是精气耗尽了,所以坦然从容地离之而去,“豚子食死母”寓言有云: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豚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
“使其形者”,就是指的形成豚子之母的“气”,气既绝,则其母即死,故豚子弃而走之,不再纠缠于死者之前,更不为之伤心掉泪。动物尚且深晓“道”的奥妙,洞察“道”的隐微与妙用,作为儒家圣人的孔子当然比动物(猪)要聪明得多,他当然也就领会“道”的玄妙了。道家思想的庄子又在这里重重地教训和讽刺了一把儒家的先知先觉。
综上所述,宇宙万物之形成,人类生命之生死,都是由“道”或“气”来决定;同比类推,人类外在的功名、富贵、显达、势位、权利、情欲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在如此种种面前,又该持取怎样的态度呢?对此,孔子也曾经非常迷惑和茫然,所以又曾向老聃问此之至道: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慄,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恩、怨、取、予、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王夫之说:“天地人物之化,其阴其阳,其度其数,其质其才,其情其欲,其功其效,好恶离合,吉凶生死,有定无定,变与不变,各有所极;而为其太常,皆自然也。因其自然,各得其正,则无不正也。”如此说来名位富贵利禄仁义,也是自然而然的,故要“因其自然”,如此则能“各得其正”。什么是自然?自然者,道也,常也,因自然就是因常道。道产生这些富贵利达,人类只能顺其自然,不能强为之求,否则失其常所。
在上述寓言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道家之“道”的决定作用,于是也就推断出“道”的无所不在之品质,这是庄子学派合乎宇宙天地之生成逻辑的思维走势,这一点在《知北游》篇“东郭子问庄子道”的寓言里有集中的说明: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女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在这里,庄子以形象的深入浅出的寓言说明“道”除了具有产生宇宙天地的广大与超越之品性,又包含在有限、平凡乃至细小低下的万事万物之中。从思维方式上讲,联系“道”作为本体、宇宙之源来看,庄子是把本体与现象、无限与有限、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巨大与细小、超越与平凡之间的关系、对立与差异做一种相对同一的考察,以示对现象世界的理解与把握。东郭子对庄子的这些哲思无法理解,甚至觉得不可思议,是由于他割裂了普遍规律与个别现象之间的必然内在联系,是一种孤立、静止地观察现象世界的形而上学。
《庄子》寓言所揭示的“道”的第二个方面的内涵是,“道”是宇宙万象、万事万物之所以成其为然的内在必然性和合乎规律性与逻辑性,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支配世界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精神,如果违反了“道”的这个规定,现象世界不但不会被人类所认识,相反,在一定时机与场合下会受到它的惩罚。执行这个“道”的规定性的最佳方法是“顺物自然”。这个理念在《庄子》寓言中,通过如下篇目来体现:“庖丁解牛”、“浑沌之死”、“黄帝问广成子道”、“东施效颦”、“妻死鼓盆”、“鲁侯养鸟”、“佝偻承蜩”、“津人操舟”、“吕梁丈夫蹈水”、“梓庆削木为”等等。其中“庖丁解牛”对“道”的第二个方面的内涵概括得最具综合力: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则寓言故事不只是对文惠君的养生之道有所启发,我们认为它对于人类一切的行为和办事都有巨大的借鉴意义。人们办任何事情都要按规律办事,只有首先遵循规律,承认必然,最后才能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所谓遵循规律,就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顺物之性,依物之理,办事才能游刃有余,达到预期的效果。人类必须喜好“道”的规定性,办事的技巧,所谓熟能生巧,都是在深入了解和把握事物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的一种熟练与自如。“庖丁解牛”所昭示的必须遵循规律这个总原则在人类生活、生产中又是怎样具体落实的呢?对此,《庄子》寓言又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许多细小分工上予以落实。首先体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上。我们来看这方面的几则寓言。
《则阳》篇有“长梧封人”寓言: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君为政焉勿鲁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终年厌飧。”
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作物的种植,一定要按照土壤特点、种作要求以及其他生产条件来进行,违反了农业生产规则只能受到歉收甚至颗粒无收的惩罚,长梧封人的生产实践就是明显的例子。以此移植或借鉴到政治统治上来,也要遵循治政的规则,不能违背农时和人心。
农业生产要按规律办事,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我们来看手工业的情形。《达生》篇中“梓庆削木为”寓言是这么说的:
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
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作为乐器的制造,要使器皿奏出的音乐有巧夺天工之妙,关键在于根据乐器的发音特点寻找符合要求的制作材料;而乐器的精妙又是一件制作者的心灵设计必须与客观外界的环境条件达到非常默契的“遇合”之事,这样制作出来的物器才能如鬼斧神工。所以,寓言中讲的“以天合天”就是制作的规则,这是不能违背的。将这种手工制作的经验借鉴到艺术创作之中,就是要求创作者的精神与灵魂去感应自然造化的内在质性,达到创作主体与客观对象的统一融合,即所谓主客为一,艺术作品才是上乘之作,才是融和着精灵与神志的精神产品。
违反创造精神产品的原则,人为地添加一些违性的行为举动,只能带来相反的结果。在美的创造中给人完善的审美感受是不能离开美的对象本身的“质性”的,“东施效颦”的失败和没有引起人们的美感,只是增添了欣赏者的恐惧,其原因就在这里:
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其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如果不顺物之性去雕刻对象,不但不能使雕刻收到成效,相反会使对象世界变成一片衰败,甚至失却对象世界的生机与活力,北海之帝与南海之帝就曾品尝过这种苦果: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世间一切作为,都必须因任自然,强其所为,为者必败,这是天经地义、不可易换之理。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之所为,把一个浑沌之帝活活弄死,就是违反了因任自然之道。无独有偶,鲁侯养鸟以违背鸟之生存习惯和生存方式的办法去驯养,只能使鸟悲愤地死去:
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人类在改造世界、改造自然,与对象世界作斗争的过程中,不遵循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后果,常常令人不寒而栗;反之,如果一旦认识和把握了规律,客观世界特别是自然界就会造福人类,特别是造福于人的生命之健康、体质之提高和寿命之长久。因此,《庄子》寓言对于人类养生、养神规律之探讨,也是富有成效和启迪人智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取养生之道。下面简单列举《在宥》篇中的“黄帝问广成子道”和《达生》篇中的“吕梁丈夫蹈水”以及“桓公见鬼”寓言稍作说明。
“黄帝问广成子道”云: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闻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
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地。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
道家学派在对待人类生命问题上,比儒家更注重关爱生命本身的价值。体现在生命理论比儒家繁富而有系统,注意个体健康和生命的长寿,而且指出了许多养生、养身、养神、养命的方向与方法,对于后来以关爱生命为本位、追求长生不老的宗教——道教的产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建立了许多理论原则。这则寓言主张生命应该以清静守神为养生之要,强调人体的感觉器官不要为利欲所动,同时反对多思好知,要求守一抱道,这对后来道教主张守住人的体内神灵启发很大。这些养生规则和理论,无疑对人类的生命文化贡献卓著。
生命的修养和安顿,还在于遵守顺命之性的原则。生命内在的情性、质性、禀性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生命都要顺性而行,这样,有形的生命躯壳就能健壮,寿命就能长久,“吕梁丈夫蹈水”寓言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而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吕梁丈夫蹈水养生强身之道为何?王夫之解之曰:“养之从容,而守之静正,则将不知其所以然而与物相顺,不知所以然而顺乎物者,此万物之所终始而为命之情也。守之而乃顺乎物之所自造,则两间虚骄之气敛于其所移以成始,而兵刑之害气永息于天下,吕梁亦安流矣。”养生亦在乎“顺乎物”,就如蹈水之顺乎流一样,性命之性必顺之,性命才能长久不败。
人类在养生上应特别注意精神的作用,精神支柱往往是生命保持活力的决定因素,如果精神涣散则会招致身体的灾祸与病痛,所谓人要有一种精神,不但是强调精神对于事业的重要,更强调的是对于健康的重要。“桓公见鬼”寓言说的就是精神专一对于桓公的作用:
桓公田于泽,管仲御,见鬼焉。公抚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公反,诶诒为病,数日不出。
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夫忿畜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
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邱有,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由于桓公精神散失,魂不附体,导致呆痴迷笑之病发作。也由于他全部的心思在称霸诸侯方面,故精晓其心理病症者虚拟委蛇之鬼以对症下药,使其精神又聚集到身体上来,迎合其心理爱好而谎称见委蛇之鬼能实现称霸之愿,于是桓公之病不到半天而痊愈,精神的回收和凝聚又治好了他的病,所以王夫之说:“神不凝者,物动之。见可欣而悦之,犹易制者;见可厌而弗恶,难矣;见所未尝见者,弗怪而弗惧,愈难矣。乃心一动而神不守,且病其形。夫物之所自造,无一而非天。天则非人见闻之可限矣。而以其习见习闻,为欣为厌为怪,皆心知之妄耳。心知本无妄,而可有妄;则天下虽无妄,而岂无妄乎?使人终身未见豕,则不知豕之可以悦口,而且怪之矣。知天下之无所不可有,则委蛇之怪犹豕耳。故神凝者,不见天下之有可怪,因不谓天下之无可怪。霸者自霸,怪者自怪。志一于霸,则怪亦霸之征也。无所容其忿畜之气,而纯气周流浃洽于吾身,出入中央,举无所滞,怪不能伤,而形全矣。”汉代枚乘《七发》里楚太子的病也像桓公一样是如此生,如此愈的。
《庄子》寓言所揭示的“道”的第三个方面的内涵是,“道”是庄子孜孜以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和生命理想,是一种对于社会、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超越。
老庄思想基本上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联系体。老子主张人类社会在生存环境和个体存在上返璞归淳,复归自然,强调外在至上、神秘玄奥的“道”是一种绝对的超越与主宰,人类只要驾御了“道”就能超越自然、社会和自身。庄子在老子这种超越观念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和强调生命的自由以及个体精神的自主,主张人类摆脱一切对生命的束缚,达到一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命崇高之境。
庄子追求的这种生命境界,通过我们反复诠读《庄子》寓言发现,这种境界的实现需要经过等是非、齐生死、心斋坐忘、物我为一三个环节,最后达到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的为人标准,从而实现绝对的自由。
首先是对纷纷呈呈的现象世界、物质社会和利欲现实等是非、齐生死。事物的大小、多少、成毁、寿夭、生死、美丑,社会的穷达、贵贱、尊卑、高下……都要等量齐观,所谓“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用“同者”来观察社会世界,就是用具有普遍本质的“道”来观察世界,以道观物,则万物一齐,就无所谓大小、多少、贵贱、美丑、生死、贫富、穷达之别,“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样,人类一旦没有了这些富有等级差别的概念,就能平心静气,无牵无挂,无束无拘,慢慢地向逍遥自由之境迈进,最终找到生命的归宿。来看下面的寓言:
狙公赋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狙公为什么能将众猿的心态从怒调节为喜?因为他掌握了齐是非的标准,以“七”这个不变的等量去安排“三”和“四”的顺序,总量不变,齐一的标准不变,以此来判断事物,事物就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因此也就消弭了许多是非怒气而归于和顺安宁。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也是如此。天地万物的总量不变,只在万人之中的分布不平衡而已,如果想通了总量在众人手中,不要计较你我之间的得失多少,那么社会就和平安处,无所谓是非曲直之争,所以庄子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非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只有“彼是莫得其偶”,泯灭是非差异,达到齐一道通的境地,就能应于无穷,了无人生烦恼挂碍,这就是“道枢”,是人生得道的关键和枢纽,是生命存在的至上法宝。
人类对生死也要等量齐观,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死如一,因此也就能视生如死,视死如生。“孟孙才处丧”寓言就是这样说的: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心中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耶?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戾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孟孙氏处丧,不问死生,不辨先后,顺物之化,泰然面对发生的现实,有一种安时处顺、安命处惊而不变的达道之态。人生达到了这种哀伤不入、欢乐不形的无所作为之境,就没有什么解脱不了的痛苦,人生的自由也就指日可待了。
上述等是非齐生死只是庄子为人生追求崇高理想所设计的理论原则,或者说是一种理论上要探讨的可能性。而要将这种理论作为指导实现人生最高境界的有效原则,还必须考察具体的实践方法和实践路径,否则这种理论将是空中楼阁。对此,《庄子》寓言亦有很好的构建和创造。“心斋”和“坐忘”的修炼操持就是两种最好的实践措施,也就是说,“心斋”和“坐忘”是实现庄子人生理想目标和最高生命之境的行动内容。
先来看《人间世》中“仲尼心斋”寓言:
颜回(问仲尼)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
再来看《大宗师》中“颜回坐忘”寓言: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综合上述两则寓言来看,“心斋”和“坐忘”是两种人类生命修养的工夫,它们注重于人格内在的修炼,是一种内省的工夫,“心斋”强调一个“虚”字,即心虚而与万物通,然后能通万物,能容纳万物,虚怀宽广,不计较名利权势富贵生死等等。在道家思想里,虚为万物之本和道德之至,老子说:“虚怀若谷。”因此,虚的修炼,既是一种工夫,也是一种境界。“坐忘”强调一个“忘”字,忘就是忘却一切功名利禄,是是非非,恩恩爱爱,即达到“离形去知,同于大道”之境,这也是与“道”相依为命的修养工夫,可见,“心斋”和“坐忘”殊路而同归,都是要达到通晓“道”的境界,两者在修养方式和目标指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坐忘”的范围有些分类的属性,主要包括忘物、忘我和物我两忘三层范畴。其中物我两忘是“坐忘”的最高形态。这三层范畴之“忘”,庄子也曾经有形象的寓言予以说明:
南柏子葵问乎女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柏子葵曰:“道可得学耶?”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
这个寓言是讲修道体道的程序和原则的,也是个体在生命修养中要完成和实现的程序与目标。这个过程包括: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无死生等环节。对比一下,这里的几个环节与“心斋”、“坐忘”中的忘物、忘我、物我两忘是相对应的,其中,外天下、外物相当于“忘物”;外生、朝彻相当于“忘我”;见独、无古今、无死生相当于物我两忘。因此,生命修养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体道的过程,“道”也就成为一种追求的境界,一种物我同一、天人一体的理想之乡,一条通向逍遥、达到自由之境的神与物游的内省之路。
通过了“心斋”和“坐忘”两个实践和操持环节,已经领略了体道带来的理想色彩,当主体与客体融合为一、天人相与为和之时,已是物我不能分辨之际,这时,人的生命之光就开始达到“物化”之境。因此,庄子追求人生自由、实现逍遥远逝理想的第三个环节——“物化”——升华的表征就呈现眼前。这有《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寓言为证: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在这则寓言里,认为物我可以融通契合,消解和泯灭了物我的界限,物我不分,不知有物,也不知有我;物转化为我,我也转化为物,物我转化交感,胡蝶与庄周(我)都冲破了自我的界限,双方都达到一种冥合为一的自由逍遥之境。这就是物化之境,也就是无所待、无所依从的绝对自由之境,庄子所谓“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自在地“游心于物之初”,“浮游乎万物之祖”,“游乎四海之外”,都是指的达到一片心灵开放、精神自由的净土境界。
经历了上述三个环节之后,得道的主体,作为精神的人就会是一个尘世间都无与伦比的至善至美的真人、至人、神人或圣人。这里的异名的四种称谓,其实都可以归结为具有同一含义、同一实质的理想人格或理想人物,更多的情况下,庄子称之为“圣人”或“神人”。作为“圣人”的概念,是与儒家反复指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人”内涵完全不同的,道家圣人具有下面一些特点:一是“圣人法无贵真,不拘于俗”;一是圣人“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一是圣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一是圣人“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归结到一点,圣人就是一种与道合一、守道而终,抱道而归的理想人格,他逍遥自在,卓尔不凡,非人世间的常人所能想象。下面几则寓言所描写的理想人格,就是这种达到了握道境界的“道”的化身。
一是《逍遥游》中“藐姑射之神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这简直是一个把握了“道”的真谛,驾御着“道”的帆船在宇宙天地之间任意遨游的神仙形象,他对世间的繁琐事务一概不闻不问,徜徉在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园,外物莫能伤害他,任何雷霆巨变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惊恐,他是那么泰然自若,那么神奇万能。后来道教所追求向往的神仙,就是藐姑射之神人,就是奇特无比的能人,就是绝对自由的仙人。
另一则寓言就是《大宗师》中的“真人”:
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事,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再明白不过了,“真人”就是胸怀至道、假于至道的得道之人。
还有一则寓言,同时出现在《齐物论》、《达生》、《秋水》等篇中,这就是“至人”: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人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其自行也,忘乎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这三则寓言所描写的至人,与造物者(道)为友,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绝对逍遥自由,任何危险灾难于他无所伤害。
总之,“道”通过齐是非、等生死、心斋、坐忘、物化的运作过程,最后达到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的理想人格,体现了“道”作为一种高尚境界和逍遥自由的美好追求,从而使庄子的道的内涵达到最完美的人格价值和最艺术化精神化的审美观照,因此,“道”赋予了道家文化乃至中国民族文化最上乘最亮丽的内容。
二 《庄子》寓言与清静自守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考察先秦道家的渊源和学术思想特色时指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卑弱以自持”,这是对老子的哲学思想和为人处世原则最精辟最准确的概括。老子强调以至柔克至刚,不要为天下先,主张以静制动,以卑旺尊,以下胜高,处处要求“示弱”。为了人类自身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老子提出要谦虚为怀,“虚怀若谷”,要排除外界与杂念对于人心的干扰,要保持人的心境处于一种虚静状态,即所谓“至虚极,守静笃”,这是个体体认宇宙之“道”和实施道法的最佳方式。怎样保持“虚静”呢?老子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主静的办法,对道家思想和道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这两个方法是:“塞兑闭门”和“涤除玄览”。
所谓“塞兑闭门”,是指不用耳目聪明去感知外物,摒弃人体感官的感觉行为,人世间庸俗的名利、爵禄、权势、酒色都无所动于眼、耳、口、鼻、心,人终身不忙忙碌碌地为外物所牵累,所谓“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启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所谓“涤除玄览”,是指要消除自己心中的一切思虑、一切歪门杂念,让心灵有如明月朗照一样明静洁亮,没有半点污垢尘埃,洗涤了一切的世俗邪妄,所谓“至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这也就是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提升的“疏瀹五脏,澡雪精神”,保持人心灵的虚静空明。
庄子在继承老子上述道家思想以静为本的处世哲学的基础上,更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宁静与自由,包括虚静状态的心灵清静和灵魂的解脱。
庄子虚静状态下的心灵清静,其实质是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虚静”的艺术精神。我们纵观《庄子》寓言,有一组数量不少的作品从三个方面来阐释这种清静或虚静的人生艺术,从而确定人生自持、自守的信条与原则。这三个方面就是静笃之美的观照、凝神于一的生存技巧和逍遥自由的生命艺术境界。对此,徐复观先生指出:“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艺术性的生活”,无疑指出了庄子的处世原则是比老子形而下的生活态度提升得更审美化和精神化的,是一种灵魂的升华与净化。
首先来考察静笃之美的观照。
《人间世》中有“心斋”的寓言: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
《大宗师》中有“颜回坐忘”的寓言: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
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
它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这两则寓言所蕴含和宣传的主旨就是那种不关人事纷呈的利禄、嗜欲、富贵、名誉等等累人系心的庸俗之为,内心保持一种虚豁空达的宁静与安详,是一种与大道融通的“集虚”之境,它摒弃了知巧与欲壑,是一种心之“虚静”,是从世俗的成见欲望中的一种解放和解脱的工夫。这种虚静的心理状态,是人生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正如业师张毅先生所说:这种“摆脱个人成见和欲望桎梏的虚静之心,也就是超越一切差别对立而能涵融万有之心,这样道家讲的虚无之道,才在人的现实生命中有了根据”。这种心斋、坐忘的虚静之心,我们认为是一种对个体现实生活的艺术升华,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观照,对此,徐复观先生总结得好:“中国文化,总是走着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内收的一条路。庄子即把老子之形而上的道,落实在人的心上,认为虚、静、明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使心之虚静明的本性呈现出来,这即是道的呈现。人的精神由此而得到大解放……庄子的虚静明的心,实际就是一个艺术心灵;艺术价值之根源,即在虚静明的心。”可见,庄子所强调的虚静,既是道学文化心灵自持、灵魂自守的重要表征,也成就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同样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理:以空明、虚静为美。
其次来考察凝神于一的生存技巧。
当人类的生存不能摆脱现实的处境时,更要求人的精神和灵魂集中于“静”的状态,保持精神的专注、心灵的凝聚,倡导用“神”去感知世界,达到与“道”融通的“朗彻”之境,从而提升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来看几则相关的寓言对凝神于一的诠释。
《达生》篇有“佝偻承蜩”寓言: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
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这个承蜩的佝偻丈人,屏声静气,全神贯注于对象世界,“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这是一种以虚静之心来考察世界的生存处世方法,他的心与物(蜩)冥合为一体,既是一种美的观照,更重要的是一种生存艺术,一种神会冥通于生活之道的艺术技巧。对此,徐复观先生指出:“但若仅止于此,而无技巧的修养,则只能对蜩翼作美的享受,并不能作‘承蜩’的美的创造。若技巧的修养不是根据于这种美的观照的精神,则其技巧亦将被拘限于实用目的范围之内,而难由技以进乎道,即难进入于艺术的领域。‘用志不分’,是以美的观照观物,以美的观照累丸(技巧之修养)。‘乃凝于神’之神,是心与蜩的合一,手(技巧)与心的合一。三者合为一体,此之谓凝于神。”佝偻丈人正是“将此虚静之心凝注于对象上而物我两忘,进入无差别的审美精神境界。但凡能技而进乎道的艺术创造,是巧而忘其巧,创造而忘其为创造,把有限的生命投入主客一体的无限的自然造化中去。心与物冥而手与心应,是一种巧夺天工的艺术境界”。
同篇中还有“梓庆削木为”的寓言:
梓庆削木为,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
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滑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梓庆为的经验在于“必斋以静心”,即通过一种虚静的心理练养工夫,使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任何削木为以外的私心杂念,专注于所从事的客观对象,然后加手于事务之上,得心应手就成为一种生活艺术的技巧,正像轮扁斫轮一样,“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之妙,善用之则一技而疑于神,合于天矣。反要以语极,唯‘用志不分’而已”。庄子所一再宣扬的凝神用志,无疑对人类生存的态度、生存方法、生存力量以及所从事的生存内容都注入了指导性内涵,给人类生存的文化层面的价值体系放置了一个沉稳而必须把持的天平,启迪着人类的生存理念。
至于《养生主》中“庖丁解牛”寓言所述庖丁动刀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同样是强调精神贯注,精神的流程在从事人类生存的职业时必须达到一种艺术的高度,而且庖丁的解牛艺术还是一种超越了一般生存技巧的“达于道”的高度完美的创造美的精神活动,因为他“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已经完全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艺术性的、审美性的表演,这就体现了庄子把现实的生命与艺术的生命结合起来的至善至美的道家追求。
最后来考察逍遥自由的生命艺术境界。
虚静的审美观照,凝神的生存技巧,都只是生命存在和延续的方式与手段。生命存在的归宿或者说最高境界是什么?庄子及其虚构的寓言作品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刻地思考。由于庄子为代表的后期道家哲学的终极目标是保护自己的精神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追求心灵的宁静与精神的解脱,因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绝对自由——逍遥游成为他们生命境界的最高最理想的形态。对此,业师张毅先生指出:“以虚静为体的人性自觉,落实在艺术人格上,可以用一个游字来概括,一部《庄子》即以逍遥游开宗明义。‘游’代表的是独立的艺术人格和自由解放的精神状态,一方面要消解实用的观念,自己决定自己,同时要自己不与外物对立,以达到彻底的和谐。”那么,庄子所设计的逍遥游之境要怎样才能达到或实现呢?我们来翻开《逍遥游》中的一系列寓言故事就可得到答案。
逍遥游是一种无所依凭、无所借助的绝对精神自由,因此,首先必须消除有条件、有限制、有依赖的“游”,即打开枷锁,才能放出自我。故否定“有所待”的自由是首当其冲的事,“列子御风而行”是必须推倒的自由:
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是否就很赞赏鲲鹏高飞九万里所获得的自由呢?它的自由是: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显然,这种自由是不符合逍遥游的要求的,因为它是有所待,有所依靠而得到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王夫之对此解说得好:“水浅而舟大,则不足以游,大为小所碍也。风积厚而鹏乃培之,大之所待者大也。两言‘而后乃今’,见其必有待也。负青天而莫之夭阏,可谓逍遥矣;而苟非九万里之上,厚风以负之,则亦杯之胶于坳堂上也,抑且何恃以逍遥耶?”所以鲲鹏之飞不是逍遥之游。
打倒了有所待的自由,接着就树立无所待的自由。那么什么是无所待的自由呢?那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游”,是超越了一切外物和自我的自由,这就是逍遥游。所以,还必须做到忘物和忘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什么是忘物?无功、无名是忘物;什么是忘我,无己是忘我。下面就是阐述忘物忘我的寓言: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尧想把治理好了的天下交给许由,这是不贪功的高洁行为;许由不接受这天下而代替尧,这是不求名的亮丽节操。贪功名者,自然受功名之累、琐务之羁,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言。因此,要逍遥游,必须摆脱和消除世俗的功名之心,特别是被儒家学派所道德化了的声誉功名之邀,一直在束缚人类心灵的自由。只有无求功名如藐姑射之神人者,才是逍遥自在的: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造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
不以天下累己之心,不以万物伤己之神,不以世事劳己之力,逍遥游遨于四海之外,达到吸风饮露、日行万里的神仙之境,当然是绝对自由的人生,最美最善的人生。这是一种忘我忘己的境界,一种主体精神与天地四海融为一体的和谐朗彻之境。当然,忘我忘己的另一方面,还包括我虽为我所有的“使然”,但最好是忘却那有所用我的“作为”一面,下面一则寓言就是忘己的这个意思之表达: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痈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斧斤,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主张无用,反对作为,这也是一种忘己无我的逍遥,“以无用用无用,无不可用,无不可游矣”。
综上所述,庄子上述寓言所追求的逍遥自由的生命境界,是一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的精神活动,它要求顺应和驾御自然界复杂的规律,摆脱和超越客观世界和现实环境的所有限制,随心所欲地在广阔的宇宙空间遨游飞翔,这无疑是庄子道家学派在厌恶了现实世界的种种丑恶之后做出的心灵选择,为当时乃至以后想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找到一条退让和摆脱之路的穷困窘迫之士指出了方向,从而成为历史以来隐士阶层得以回应的绝好范本,这也注定了逍遥自由思想在中国士人文化中拥有广大空间的良好命运。
要之,《庄子》寓言所体现的道家清静自守的虚静精神,把“虚静作为与天地生命精神往来的工夫,同时也以此作为人生的本质属性,并且以为宇宙万物皆共此一本性,所以贯通宇宙人生而与天地万物冥合,乃以虚静为体之心所必然达到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由此构成了道家文化虚静精神的全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