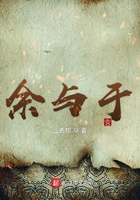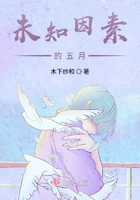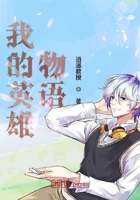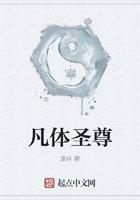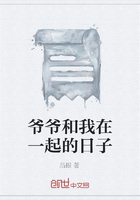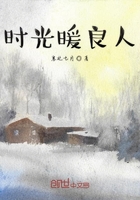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界的怀疑态度主要是针对教会权威,重塑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的活动也是在批判教会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最终无可避免要把矛头指向被教会奉为一切思想和知识来源的《圣经》。作为整个怀疑主义的一部分,历史怀疑主义同样要去质疑《圣经》所叙述的历史和《圣经》本身的历史,而新的史学观念、尤其是世界史观念则在围绕圣经历史的种种争议中成长起来,圣经文本批评更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另外,中国古代历史在欧洲掀起巨大波澜,根源就在于它同圣经历史有冲突。由于这些原因,在正式叙述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记载在欧洲惹起的风波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在欧洲自身的文化和知识脉络之下,《圣经》的根基已经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对《圣经》的批评总体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性的批评,一类是历史性的批评,前者揭示出圣经观念在认识论上的矛盾,后者则显示圣经观念的事实基础不可靠,并描述所谓神圣观念实际上如何起源于世俗社会并逐渐被神化。这两个层面的批判与前文所说依据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寻找知识确定性的两种努力分别对应,其结果是互相呼应,从形而上与事实层面共同弱化了《圣经》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我们重点要看对《圣经》的历史性批评,哲学性批评仅择要而言。
第一节 哲学性批判
18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哲学家和启蒙运动文学家莱马路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1694-1768)从认识论基础上对《圣经》所作的批评极具代表性,他被认为是对正统教义进行激进理性主义批评的先驱者。莱马路斯因其自然神论观点而令人无法忘怀,他坚持人类的理性能够达到一种比启示宗教更确定的宗教。1727年莱马路斯被任命为汉堡高级中学(或预科学校)的希伯来文和东方语言教授,他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一个文化中心和学术界与艺术界聚会的场所。1754年出版的《论自然宗教的基本真理》(Abhandlungen von den vornehmsten Wahrheiten der natürlichen Religion)是他首部重要哲学著作,从自然神论的立场讨论宇宙观问题、生物学-心理学问题和神学问题。在1756年的《理性学说》(Die Vernunftlehre)中,他同基于启示的传统基督教信仰作战。莱马路斯穷20年之力撰写了许多哲学论文,汇为《为上帝的理性的仰慕者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ür die vernünftigen Verehrer Gottes),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通篇主旨认为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教义通过理性就可以获得,而无需启示原则的帮助,这种理性宗教比启示宗教更完美。但莱马路斯经深思熟虑后至死没有发表这部作品。后来,莱辛从莱马路斯的孩子们那里获得该作品的残稿,于是1774-1777年在他自己的《历史与文学》(Zur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中以《匿名者文稿残篇》(Fragmente eines Ungenannten)为名发表。莱马路斯文稿片段一问世便引起一场同时激起自由派和保守派非难的争议,莱辛因而也卷入他平生最激烈的一场辩论。其实莱辛对莱马路斯的激进观点采取一种调和立场,但神学家仍将这些出版物看作对宗教正统性的严峻挑战,因为莱马路斯拒绝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那么莱马路斯在这部生前不敢出版的作品中究竟对哪些基本信条构成威胁呢?
莱马路斯的理性宗教可以说是理性主义范式在宗教里的表现形式,他抨击正统基督教时的基本立足点是:在宗教里运用理性主义范式是正确的,而且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本于此,他全面批判原罪说和启示观念。
莱马路斯认为原罪说是对理性能力的一种诋毁,否认理性在人类宗教生活中有能力实现人类的目标并且有充分的自足能力。人类理性在宗教生活里已经消亡的观念,蕴含了基督教这样一条教义:把信仰建立在历史上面,并且在信仰的指引下“将理性囚禁起来”。而让理性屈从于信仰是对人类尊严的玷污,也是基督教不宽容精神产生的根源。莱马路斯进而对《圣经》作出一系列仔细阐释,指出《圣经》中并没有关于“原罪”的信条,是圣经学者把它冒充上帝的要求教授给人。他想表明,在《圣经》中理性不是让人类“颓败”的东西,而且亚当犯下罪孽正是由于他没有理性认识。
莱马路斯对启示观念的批判依据这样一种逻辑:上帝能够向人类揭示的无非是形式和实质上普遍的事物,即类似理性真理的事物,而精神力量存在于人的理性领悟能力之中,因此获得上帝启示的唯一工具是人类不借助外力的理性力量。也只有这样,理性的启示才可能有普遍的意义,即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理性人类都有发现上帝启示的工具。因此,他认为基督教启示说没有依据。
莱马路斯依据他的理性宗教观念提出,《圣经》作为提供上帝启示的源泉本身充满矛盾,因而完全没有历史的可靠性。以《圣经》为上帝启示的中介,实则表达了关于上帝的知识源于历史,且关于上帝的真理由历史传递这样的观念,但莱马路斯认为上帝的真理作为普遍真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上帝给予的启示不可能是面向所有人的启示,通过历史给予的启示由于自身具有历史性而必然总是具有个别性,且总是受到条件制约。所有这些条件与理性真理的普遍性、必然性以及无条件性这些性质都是对立的。因此,《圣经》作为启示中介并不可靠的原因之一就是,《圣经》传达的启示不具有普遍性。这种非普遍性的一个表现是时间的限制,如果有关人类获救的必要真理在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时间获得或者说可以在那时获得,则生活在那个时间之前的所有人类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必要的真理。然而既然上帝本性善良,理应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所以拯救真理经由历史传播的观点就自相矛盾。表现之二是空间的限制,如果民众中只有某些人直接得到启示并且向其他人传递启示的内容,那么事实上其他人得到的就不是神性的启示,而是对接受过神性启示之人的见证,这种见证十分不可靠。此外,即使上帝通过历史给予人类启示可以看作是可能发生过的事件,但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并非人类为了获得精神幸福而应具备的宗教必要性。在这里,莱马路斯对《圣经》启示的蔑视乃是基于对历史传递的真理的蔑视,这正是“理性主义者”在理性真理与历史真理间持绝对对立态度的表现,是立足“理性主义者”的共同逻辑来抨击传统基督教的认识论错误。
莱马路斯还对《圣经》有过深入研究,揭示出其中有关启示的历史传说不可靠,这构成《圣经》不能作为可靠启示中介的又一个原因。莱马路斯竭力表明《圣经》中的历史传说、尤其是那些关于神迹的传说是不准确的,例如他否定除创世以外的所有奇迹,包括童女诞圣婴、耶稣复活、基督复临等奇迹,还努力研究过耶稣的生平,把他勾画为传播一种关于理性的宗教的凡人。莱马路斯这种做法实则显示出启蒙运动对《圣经》的普遍看法——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文本加以严格考证。但莱马路斯在否认《圣经》所载史实的可靠性时,主要着眼点仍是依据理性主义范式对真理的规定而否定整个基督教,也就是说具有短暂性、时间性特征的事物不能向人类阐明存在必然的、永恒的、普遍的也即理性的核心,不能用来传递宗教真理。换而言之,传统基督教的实质恰因其历史性而不可信,《圣经》中的历史史实至多能够表明某个具体事件可能曾经发生,但既然上帝是理性存在的本原,上帝的启示就不能经由具体的、历史的事物而应经由普遍的、必然的真理显现出来。
在莱马路斯这样的理性主义者眼里,只有理性宗教才充分可靠,理性宗教是唯一能够展现理性主义范式的宗教,理性有能力发现有关上帝、世界以及人类的一切必要的和充分的概念,而且也有能力以这些概念规范人类的活动。基于对理性宗教的推崇,《圣经》中不包含某些被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关涉宗教真理的教义,这成为质疑《圣经》作为启示中介可靠性的再一个理由。比如,永生对于一个人道德生活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但《旧约》不包含永生的教义,因此它显然不可能是提供上帝启示的可靠来源。
从莱马路斯的思想可以知道,对《圣经》的哲学性或形而上的批评归根结底就是揭露《圣经》和教会教义的非理性性质,指责它们是对人类理性精神的蒙昧和愚弄。
第二节 历史性考察
一、古物研究惹出风波
圣经研究的大观由古物搜集者的行为即可体现:在文学的、物质的、或活语言的脉络下解释圣经文本。而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在17世纪初重新出现在欧洲学术研究的示意图中,这对有关《圣经》的学术研究产生特殊意义,圣经研究的上述三个层面在撒玛利亚人研究中同时具备,属于最好的情况。撒玛利亚语启发一些古物研究者自认找到了古代犹太文明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联接纽带,另一方面《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Samaritan Version of the Pentateuch)引出了对现存《圣经》版本的评价问题。这两种研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就目的而言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和确切勾画圣经历史与古典历史间的关系。质而言之,撒玛利亚人进入欧洲人视线,使欧洲人以为得到了证明基于《旧约》的历史观的有力证据。然而事情发展下去的结果却不完全如人所愿。
首先觉察到撒玛利亚文化代表着文化从东向西迁移中的一个环节的是前面提过的16、17世纪之交的荷兰学者斯卡利杰。斯卡利杰对古代历法感兴趣,他正是首先因为历法而研究撒玛利亚人,由此而引起对拉比语(Rabbinic Hebrew)犹太文明的更广阔的兴趣,他同样感兴趣的是撒玛利亚人保存了古代希伯来文字母表,此字母表亦被腓尼基人(Phoenician)使用。斯卡利杰进一步推论,所谓“腓尼基字母”在亚伯拉罕时代被迦南人(Canaanite)使用,并被作为古代希伯来人的字母对待,后来字母经过变化仍在撒玛利亚人中被庄重地使用。这一情况暗示出,研究撒玛利亚人的语言可以有助于揭示出腓尼基是圣经历史与古典历史之间的关键纽带。斯卡利杰还第一个发觉关于古代犹太人和古代希腊人的故事在撒玛利亚人的历史中相重叠。培赫继承了斯卡利杰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趣,也抓住了斯卡利杰的这一提示去理解圣经历史与古典历史的关系。培赫在1628年开始对撒玛利亚人产生兴趣,他一再强调撒玛利亚人与埃及人间的联系,这年秋天的一封信里满纸谈论关于希腊人、科普特人(Coptic)和撒玛利亚人关系的理论,表明他将比较语言学视为发现和精确建立古代地中海东岸社会之间联系的钥匙,他希望理解撒玛利亚语同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间的关系。在培赫的时代,人们正在开始把撒玛利亚人作为一部新近构造中的世界历史的一员,培赫基于他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将撒玛利亚人定位为古希腊罗马世界和圣经世界间的一座桥梁。培赫和斯卡利杰及其他古物搜集者的目标是为欧洲文明的起源提供一个有文献证明的描述,在他们的努力下,《圣经》关于古代东方的叙述现在可以同《圣经》所反映历史时期之后的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公认历史相接合;并且古物搜集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构造共同叙述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融合古希腊罗马世界与古希腊罗马之外或非欧洲世界的方式,事实上就是统一在《圣经》和基督教的道德、宗教与社会模式之下。这两点都是近代早期的重要学术发展,前者提供了对西方文明之东方起源的证明,后者帮助系统构造以《圣经》为基础的世界历史图景,为传统观念提供了有力支持。
正是在此影响下,17世纪欧洲有关近东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埃及学)达到一个高潮,且千方百计证明它们与欧洲文明的渊源;也是在此影响下,17世纪的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关于人类最初历史唯一可靠的叙述就建立在《旧约》之上,《旧约》摹画出最初的世界历史图景,所有民族理论上都可以将他们的谱系上溯至古巴比伦和诺亚的一个儿子,而普遍史学者们的工作就是通过比较任何民族的古代年鉴或记录同《旧约》这唯一可靠叙述的符合程度来测试其真实与否。直到17世纪末,莱布尼兹仍坚持,古代遗迹、古代历史以及距欧洲人最遥远的民族的历史对于证明宗教真理是绝对必要的,“除教义的优越性外,我们的宗教还由于它那完全是神的起源,所以有别于其他所有不能以任何方式相接近的宗教。通过一些经过确切证实的古代作家的著作,使这些伟大的真谛得到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明,这可能就要运用最细微和最深刻的考证办法了”,这正是被那个时代古迹研究带给历史领域的动人成果鼓舞所致。然而,“恰是构造神圣历史所取得的战果导致神圣历史在所有苦苦思量有关人类过去之研究的怀疑论下禁不起推敲”。
除撒玛利亚人研究造成的影响,《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的出现使一些学者开始挑剔作为标准希伯来文本的《马索拉本圣经》(Hebrew Masoretic texts/Massorah),加剧了17世纪有关各《圣经》版本权威性的争论,在此过程中因需进行文本考证与批评,《圣经》文本的历史性因素日益突出,而各版本的神圣权威性无形中都被削弱,这不仅对圣经批评这个研究领域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上古史问题之酿成争论也至为关切。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撒玛利亚人就使用一部希伯来律法的副本,写以古希伯来文,但有些地方有变体。公元前2世纪,它被逐字逐句译为撒玛利亚文,这就是《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早期教会的一些教父曾引用它,但它到17世纪初期始为欧洲所知。1616年,一位意大利旅行者瓦勒(Pietro della Valle)在大马士革弄到一部《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手稿,从此为西方所知,1628-1645年在巴黎出版,1654-1657年又于伦敦出多语对照本。《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与《马索拉本》相比有6000处差异,而其中有近1/3与希腊文《七十子译本》(The Septuagint)相同。这些变异其实只有少部分是名副其实的变异,大多是信条(dogmatic)、注释、语法或仅仅文字书写的不同。但无论如何,这些差异已足够让许多学者认定它比《马索拉本》优越得多,《马索拉本》是公元6世纪由马索拉学士(Massoretes)确定的希伯来文改进本和标准本。而这又引起学者们对当时教会钦定使用的《通俗拉丁文本》(The Vulgate)的权威性展开争论。
为明白争论如何由此及彼,我们必须先了解《圣经》几个基本版本的渊源关系。《七十子译本》习惯上被认为是公元前285-247年间由七十位亚历山大城学者自希伯来文《圣经》译出的希腊文本,它是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一个译本,且产生的时间非常早,因而在文献考证上意义非凡。《七十子译本》首先被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接受,逐渐扩展到所有使用希腊语的地区。犹太人在基督诞生前长期使用它,即使基督时代,犹太人也认其是合法文本,在巴勒斯坦甚至被犹太拉比使用。《七十子译本》后来成为东部教会的钦定版本并一直保持。大约在公元2世纪出现以《七十子译本》为基础翻译的《旧拉丁文本》(Old Latin,又称Vetus Itala),此版本被长期作为西部教会的通用版本,直到被《通俗拉丁文本》完全取代。《通俗拉丁文本》是公元4世纪末由圣哲罗姆(St。Jerome)编订,他因为修订《旧拉丁文本》而确信西部教会需要一个直接译自希伯来文的新版本。圣哲罗姆在390-405年间从事这项工作,他从希伯来文译出正经《旧约》,从阿拉伯文译出次经《多比传》(Tobias)和《犹滴传》(Judith),此外还借助当时意大利尚存的原始希腊文本、残存次经、《以斯帖记》(Esther)和《但以理书》(Daniel)的部分修订《旧拉丁文本·新约》。圣哲罗姆使用的希伯来文本是比较晚出的版本,差不多就是后来《马索拉本》的母本。圣哲罗姆的新版本经历从4世纪到13世纪的漫长路程才逐渐取代《旧拉丁文本》确立地位,其名称“通俗拉丁文本”是13世纪所定。16世纪,特兰托公会议宣布它是教会的权威版本,规定只有《通俗拉丁文本》可以作为“公开朗读、讨论和争论时的权威版本,没有人胆敢或设想以任何借口拒绝它”。这道声明在不贬低希伯来文本、《七十子译本》或其他任何流通版本并且不禁止以前版本的同时,称许《通俗拉丁文本》并责令将其作为一个没有教义和道德错误的版本在公开和官方场合使用。
碍于教会势力,17世纪的人不会直接质疑《通俗拉丁文本》的教义权威,但随着《圣经》的文本批评学的发展,尤其是《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对《马索拉本》的权威性构成直接挑战,与《马索拉本》有同源关系的《通俗拉丁文本》便可以在文本批评的角度被质疑,那些早于《马索拉本》的希伯来文《圣经》各译本的文献价值被意识到,学者开始提出《通俗拉丁文本》的文本价值比《七十子译本》和古叙利亚文本《伯西托本》(Peschitto,Peshitto,Peshito)逊色。《七十子译本》的支持者指出其与现存希腊文副本间的一致来证明希腊文本与《马索拉本》间的差异不是誊写的错误,而是七十译者使用了比圣哲罗姆所能看到的或17世纪学者仍能获得的手稿更古老的希伯来文手稿,自公元前3-2世纪到公元6-7世纪之间,希伯来文本一定渐渐出现许多文本的讹误、添加、遗漏或顺序错置。《马索拉本》的支持者则以所有现存希伯来文本都彼此一致来证明《马索拉本》的可靠。关于《七十子译本》与《马索拉本》材料可靠性的争论与中国上古编年史的争论密切相关,因为到底是采用从《七十子译本》中计算出的世界年代体系,还是采用得自《马索拉本》的世界年代体系,影响到在相信圣经历史正确的前提下接受还是拒绝中国编年史。这是后话,在此只需要明白,《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在一个充满怀疑、强调证据的时代呈现在欧洲人眼前,助长了对《圣经》进行历史性检验的风气,通过揭示出《圣经》尤其是《旧约》各版本间的差异而削弱了它作为天启之书的神圣性。
二、为《圣经》作者困惑
斯宾诺莎在1670年出版的《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是运用历史学方法解释《圣经》经文原始文献的先驱之作。他提出,流行的解释《圣经》的方法是错误的,神学家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威而非经书真意,以《圣经》原文来附会自己的虚构和话语,并且由于迷信使然,人们梦想《圣经》中藏有极深奥的秘密而疲于探讨这些背理的事。斯宾诺莎对神学家的批判和对《圣经》真理的理解是由他对宗教真理的理解来决定,这已不消在此处论述。但斯宾诺莎在批判之外,试图建立解释《圣经》的真正方法,他称这种方法与解释自然的方法差不多——弄清事物的来历并根据某些不变的公理推出对现象的释义。他提出的第一条根本原则是,解释《圣经》不能预立原理,只能讨论《圣经》本书的内容,也可以讨论非理解力所能理解的以及为理智所能知的事物,这是一种类似实验方法的态度。第二条则是,由于《圣经》主要都是些故事和启示,这些启示本非人类所能理解,所以关于《圣经》内容的知识都只能求之于《圣经》,也就是说证明《圣经》中有纯正道德信条只能从《圣经》中分析,证明上帝的神性不能借助奇迹,若要信从预言家则必须先证明他们有一片向善之心。这条原则表明斯宾诺莎认为解释《圣经》只能依据内部证据。第三条原则,这是具体研究《圣经》内容时的一条普遍法则,凡我们没有十分看清楚的,就不认为是很可信的《圣经》的话。这里强调避免以主观偏见歪曲文本原意。
在这些原则之下,他介绍研究《圣经》的内容或历史到底要解明什么,也就是具体操作方法。第一,了解《圣经》各卷写时所用及著者常说之语言的性质与特质。这样就能把每个句法和在普通会话中的用法加以比较研究。第二,把每编加以分析,将每编内容列为条目以备查阅,并把模棱两可和晦涩不明或看来互相矛盾的段落记下来,明白或暧昧是指按其意义从上下文推论出来的难易程度而言。这样做旨在了解《圣经》本书究竟说了什么,不强使原文意思附和研究者的理智和先入之见。第三,《圣经》某句话的历史必须与所有现存的预言书的背景相关联,即,要追究每编作者的生平背景,写作的原因、时代、对象及语言;还要考察每一编的历史经历,诸如版本、普及程度、为何会被归入《圣经》;最后弄清现在公认为神圣的各篇如何合而为一。经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辨别哪些话是律令,哪些又是道德箴言,辨别箴言的价值,书的伪篡情况。斯宾诺莎以为,只有将圣书诸篇经过这样的考察,明了它们的历史,才能够进入第二阶段的工作,去研究预言家与圣灵的心,去了解《圣经》的真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斯宾诺莎的方法中包含着十足的历史考证精神,在他的时代,将历史考证运用于世俗文本的研究已屡见不鲜,但他却宣称这是解释《圣经》唯一正确和适当的方法,他将《圣经》的神圣性面纱彻底抛弃不顾,那么不难想到这种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将造成前所未有的震撼。
《旧约》中有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早就被人们察觉,前基督教时代已经引起争议,早期教父也时有讨论。比较明显的难题包括,摩西作为《五书》的作者,有可能在《申命记》(Deuteronomy)中写出他自己的死亡和被埋葬吗?当太阳只是在第四天才被创造,人们怎么能衡量创世的“天数”?按斯宾诺莎所说,西班牙犹太人学者埃兹拉(Abraham ben Meir Ibn Ezra,1092-1167)应当是首个认为《摩西五书》非摩西所作之人。埃兹拉在《申命记》注释中暗示,《摩西五书》是晚于摩西许久的人所写,摩西所写的书与此不同,他提出六点请人注意的事实,主要是书中用第三人称并提到摩西死后的事件和地名。但埃兹拉不敢公开表示意见,斯宾诺莎却在《神学政治论》中以埃兹拉为基础,以他自己的历史考证法为依据,全面重新评价关于《摩西五书》起源的传统说法甚至《圣经》的价值。他本人是犹太人并且是希伯来文化专家,在这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圣经》文本的语言、作者和翻译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圣经》许多篇章的精确含义一贯被人怀疑,人们对古代语言知识的缺乏先天存在且无可救治。而且,无法为这些篇章标注日期,也不知道谁写了它们或不能确定哪些人的名字与它们相联系。也就是说人们研究《圣经》原始文献时既失去历史根基,又欠缺历史脉络,斯宾诺莎称自己只能根据一定的方法作一个推测性研究。他指出,可以确定的是,《旧约》记载了一群古老、原始、无知之人的历史,谈论奇迹是他们在理解自然方面无能为力的表现。奇迹原是对一些自然事件的错误阐释,出于宗教动机和预存成见而将其与道德性后果相联系并被强调。《圣经》不去真正解释事情而谈论奇迹,是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使人的理智信服,而在于用最能感人的方法吸引人的想象力。或者说,《旧约》体现出古代散文夸张的“东方式”文体,叙述者把官觉上实际所得的印象同他们的意见、判断相混淆,这意味着至少有些奇迹应该被象征性地解释,而非照字面解释。他还主张,《旧约》中先知们的灵感仅能在他们的道德教义和实践教义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他们的实际信仰只是那些适合他们所处时代的信仰,却并非在哲学上有重大意义。经过这样剖析后,剩下来可归为《圣经》首要价值的是它作为道德箴言的价值,类似于那些独立的人类理性可发现的箴言。
斯宾诺莎还明白和系统地论证《摩西五书》非摩西所作:第一,《五书》的作者基本以第三人称指摩西,并明确介绍他的详情,从这样的叙述方法和故事上下文可知非摩西本人叙述自己。第二,书中不但叙述摩西死时情景,还把他和以后所有预言家比较。第三,有些地名与那些地方在摩西生前的名称不同。第四,文字叙述到摩西死亡之后。凡此种种说明《摩西五书》是摩西身后许多时代的人所写,摩西也曾有著作,《五书》有引,但与《五书》非常不同。不仅如此,斯宾诺莎还一一考证出《旧约》其他篇目非通常以为的作者所写,它们都是辑纂之书。他甚至还论证出,《旧约》并非天启之书,马卡比人(Maccabees)的时代以前还没有圣书的经典,事实上是殿宇修复时代(Period of the Second Temple,538 B。C。-A。D。70)法利赛人(Pharisees)选择了《旧约》各书并让世人接受它。不过斯宾诺莎认为,从各书的题材和叙述风格的一贯性以及都是在书中事情发生很久之后编纂来看,这些书出自一人之手,这一点有待后人去纠正。斯宾诺莎关于《圣经》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必定要被视为洪水猛兽,尤其是他否定奇迹的态度成为人们诛伐的焦点,《神学政治论》被很多人目为“由一个叛教的犹太人和魔鬼在地狱里编造出的”工具。有此前鉴,斯宾诺莎1675年完成《伦理学》后便有意未在生前出版。
与斯宾诺莎不折不扣的激进怀疑主义相比,法国奥拉托利会士理查·西蒙对《圣经》的批评只能说是研究初衷与最终效果间“意外”地南辕北辙。西蒙原打算通过对《圣经》进行历史性研究来驳斥新教,因此当他着手工作时,得到博絮埃主教的支持鼓励。然而当西蒙的研究结果《〈旧约〉批评史》(Histoire critique du Vieux Testament)1678年出版后,却大大震惊了博絮埃主教,以至他立刻销毁书版禁止流通。西蒙的研究揭示出《旧约》中有许多重复、混淆和年代倒错,反映出它所由以编辑成的更古老的文献已不复存世。比如他发现《创世记》对洪水的叙述简单却重复罗嗦,因此总结说:“非常可能的是,如果是一名作者写了这部作品,他将用少得多的词解释自己的意思,尤其是在一部历史作品中”,这就是说他由此得出与斯宾诺莎一样的结论——否认摩西对《五书》的著作权。尽管西蒙在另外两个主要观点上与斯宾诺莎有不同——他没有质疑奇迹,并坚持由文本性质产生的解说问题在天主教会的惯例中和权威下有明确的解决办法,而且西蒙其实是罗马天主教会权威的捍卫者,但就因为他否认摩西的著作权,已被一些读者目为斯宾诺莎主义者,并遭遇博絮埃主教的禁书令。博絮埃主教认为西蒙的《批评史》关心的是细枝末节,《圣经》的主旨显然不需要靠这种危险的卖弄才学来理解。然而正是这些被叫做“细枝末节”的历史考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攻击力,因为西蒙的研究表明《圣经》作为历史都不可信,那么它作为神学基础还能可靠吗?其实博絮埃这样的正统派应该深深地感觉到了历史方法的威胁,所以才如此神经紧张。不过西蒙的书在被禁毁之时有一些副本已经流通,而且1685年又在有出版自由的荷兰再版。但不管怎么说,被列上黑名单使西蒙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他后来只能躲藏起来暗中写作,有学者认为本来这位语言学和圣经历史批判主义的奠基人在17世纪末应享有可与贝尔、洛克匹敌的声誉。西蒙著作的最早读者之一、学者兼外交家施邦海姆(Ezechiel Spanheim)在1679年指出《〈旧约〉批评史》的最终影响在于,它通过暴露出《旧约》文本中关于人类、历史的和语言的难题和弱点而颠覆了《旧约》的权威,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也被认为具有同样效果。
斯宾诺莎和西蒙成功地唤起人们注意到需对《圣经》采取学术态度,尽管他们的读者对这一过程和结果感到害怕。他们所提出的这类涉及《旧约》的疑问和难题在很长时间里似乎极难处理,除了思想观念制约之外,还因为圣经研究需要更多常人不易掌握的技巧。斯宾诺莎便提醒人们,运用他设计的方法研究《圣经》存在如下一些困难:1)需要彻底了解希伯来文,然而古时说希伯来语的人没有留下字典、文法或修辞学等任何可以指示此种语言原则之基础的工具,所以无法追寻希伯来语的历史;而且希伯来语还有一些特有的性质和构造,导致语义暧昧不明。2)需要知道《圣经》各书的来历,然而各书的来历往往无法求得,并且也不了然这些书写作的原因与时代,不知道这些书的传承演变经过。3)现存这几部书已经不是原来写作时所用的文字,有的是从其他语言译成希伯来文。所以,直到1750年之前,无论是斯宾诺莎和西蒙的追随者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罕有人具备能与他们匹敌的足够学识,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圣经批评的发展进程。
18世纪初期,圣经批评取得一些进展,比如英国自然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柯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也提出了圣书篇目(ural canon)的有效性问题,为近代圣经批评的产生打下一份基础。他1724年出版《论基督教的根据和理由》(Discourse of the Grounds and Reason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prefixed by An Apology for Free Debate and Liberty of Writing),否认《旧约》预言了《新约》中的事件,断言所谓基督实现了《旧约》预言的说法全部是“次要的、隐藏的、寓言式和神秘主义的”。1726年,他出版《受尊敬的文学预言系统》(Scheme of Literal Prophecy considered),在书中的一份附录里坚持《旧约·大卫书》是伪造。但关于摩西的著作权问题,到18世纪后半叶才有重大突破。1753年,路易十五的御医让·阿斯特鲁克(Jean Astruc)在布鲁塞尔出版《关于摩西撰写〈创世记〉一书所使用的原始回忆录之推测》,终于在斯宾诺莎和西蒙的疑问之上更进一步,第一个从《摩西五书》中分辨出两种风格不同的记述,其一称上帝为埃洛希姆(Elohim),另一种则称上帝为耶和华(Iahév,Jéhovah)。前文提过莱马路斯在18世纪中后期通过对耶稣生平的历史研究而否定了耶稣的神性,他指出所谓“耶稣复活”是他的门徒制造出来的,耶稣死后,门徒将其尸体偷走藏匿以便宣扬耶稣复活的说法。从否定奇迹、运用历史方法对《圣经》进行批评性研究并由此颠覆《圣经》权威而言,这也是对斯宾诺莎和西蒙的继承发展。莱马路斯和他的同时代人已经认为,《福音书》的记录比起《旧约》要相对可信,因此耶稣的生平需要在严格筛选和掂量关于《福音书》的证据后从中推断和拼接。
但在17世纪末,斯宾诺莎和西蒙将《圣经》作为历史文本对待还属大逆不道,因此反驳他们和捍卫《圣经》的作品排成了队。然而鲜有欧洲学者掌握了两位作者所展示的古代语言知识或西蒙对残留手稿的知识,也没有人能够直接回应斯宾诺莎关于《圣经》诸书的写作日期和著者的问题。事实上,就连博絮埃也必须承认,《旧约》诸书在古代遭到更改。而这一点随着《撒玛利亚文摩西五书》现世,人们开始比较希伯来文、希腊文、撒玛利亚文诸文本并发现许多差异,早已是不争之实。于是对斯宾诺莎和西蒙的回答趋向于如何捍卫《圣经》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而不管它曾经遭受什么样的改动。比如斯蒂尔林弗里特(Edward Stillingfleet)在指斥斯宾诺莎和西蒙否认摩西写作《五书》时坚称:上帝已经保护了《圣经》文本的完整,且一份公开文献不可能遭受了重大改变而不引起公众愤怒呐喊。而这实际是他1662年就提出的老调。又如于埃对这两人观点的答复是:当一本书在自公开发行以来的所有年代里一直都被相信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一部历史当它所记录的事实也被其他同时代作家或生活年代接近事实发生年代的作家所记录,它就是真实的。这一类回答就是明白斯宾诺莎和西蒙的观点而又没有能力对付他们的学者通常采用的论据。很显然,斯宾诺莎和西蒙运用历史方法对《圣经》文本进行的批评研究严重挑战了神圣历史的传统轮廓,而17世纪对神圣历史具有同等破坏力的还有中国上古编年史以及受中国民族和美洲民族启发而产生的“亚当之前人类说”,这些留在后面介绍。在对《圣经》文本的考证研究这个领域,除了像斯宾诺莎和西蒙这样对《圣经》的历史性提出疑问,17世纪还有很多人以运用历史证据证明《圣经》为目的,他们也将研究世俗文献时发展起来的关于“事实”的概念、检验证据的方法等等用于研究《圣经》,结果如何呢?
第三节 证明《创世记》
17世纪,由于《圣经》遭遇各种挑战,也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普遍对包括神圣历史与世俗历史的古代历史比较熟悉,因此遥远的过去比中世纪更能引起讨论的热情。但是除了一些怀疑论者,大多研究古代的人都以一些被认为不容质疑的推断和限制为起点,其基础性认识是,相信《圣经》是真实的历史,相信《创世记》是最古老的成文文献。因此证明《圣经》所载的历史成为17世纪一件令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尽皆全神贯注的工作,而且证明活动主要是围绕《创世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直接证明《创世记》中的一些事件或细节以巩固《创世记》的可信度,另一方向则是用《创世记》的记载与异教徒的古代传说相印证以证明《创世记》是关于人类最初普遍历史的记载。这两种证明事实上暗合了研究世俗主题的学者关于内部证据与外部证据的区分。前面介绍过的古文书学的奠基人马比隆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通过文献批评和历史古迹研究世俗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套考虑证据的方法,比如关于任何文本的证据都可分为内部证据(如宪章的语言风格)与外部证据(如对宪章所安排的土地转让行为的独立确认)两大类,又如通过对证人的可靠性加以验证而确定证人所报告的事件是否可信。这些由研究世俗主题的人发展起来的对证据的考虑渐渐被学者们运用于圣经研究。
一、内部证据
处理世俗文本的历史学家往往自开始就对文本的真实与否持开放态度,要根据检验的结果下结论。而捍卫《圣经》的学者则从心里认为《圣经》无可指摘,恰恰违背了斯宾诺莎所说的“不预立原理”的基本要求,所以他们虽移用了历史批评的规则,却没有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他们主张《圣经》文本需要证实,只是想运用这些已得到公认的批评规则为《圣经》的真实性穿一件坚实的铠甲,满足这个时代喜好“证明”的风气,也封牢怀疑论者的口。
波义耳不仅是实验科学的先驱之一,也是率先将证据批评规则运用于圣经研究的自然哲学家之一。他在1661年的一篇论文中处理内部证据,涉及的是《圣经》经文的语言风格和文体问题。他认为,圣经散文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虽然没有同等古老的文献来帮助理解希伯来语言和文化,但《圣经》本身包括了对普通士兵、牧羊人和女人的未加文饰、发乎自然的评论;因此,它的风格显示出十足的诚实、报告的及时性、并且文本中没有后来的篡改。波义耳下结论说,因为《圣经》是打算让所有时期的各种人理解,文本并没有为它的受众而被简化,这更说明它是诚实和坦率的。波义耳的分析与后来斯宾诺莎评论圣经文章具有夸张的“东方式”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然而波义耳的方法对《创世记》却不大适用,斯宾诺莎和西蒙先后论证《创世记》中有很多晦涩、罗嗦、篡改之处。
内部证据也包括对作者的证明:他是否目击了他所描述的事,他是个公正的人吗?讨论基督奇迹目击者的文献比较多,这其中既有明显的神学原因,也可能因为《福音书》的作者被认为已确知。所以当斯宾诺莎否认耶稣复活的奇迹时,必定会惹怒许多人。但分析证人的方法用于《创世记》就有很大困难,因为没有人曾目睹创世,摩西也没有目睹过大洪水。对此,捍卫者就只能转移视角,以《创世记》是一部公开文献作为它无可质疑的理由。比如斯蒂尔林弗里特1662年出版的《神圣的起源》(Origines sacrae,or a Rational Account of the Grounds of Christian Faith)通过研究《摩西五书》的性质和完整性,说摩西所报告之事件牢牢嵌于希伯来人的历史和信仰之中,它们众所周知,也为众人相信,因此不需质疑。从前文可知,斯蒂尔林弗里特在反驳斯宾诺莎和西蒙时又老调重弹,而于埃的两条论据与他几乎如出一炉,他们归根到底是以仰赖信仰和“普遍赞同”原则为依据且对此不加证明,然而这样的认识论前提正是怀疑主义所怀疑和历史研究要破除的内容。所以说,持先入之见的《旧约》捍卫者们在运用证据批判法上既不彻底,也无法有效维护自己。
有一些作者讨论信息传递的准确性问题,这与证人考察同样属于通过检验传播通道来核实事件。捍卫者的观点是,在亚当和摩西之间没有多少代,因此口头传递的信息——尤其是与世界历史关系重大的事件——的准确性大体能够保障。随之而来又产生确定最早的书写如何发明的问题。同一时期在对古罗马起源的考虑中也存在类似争论:少数人认为关于罗穆卢斯(Romulus)时期没有书面证据可依,因此他的故事应被当作神话拒绝;其他人则争论说存在直接的证据,或者这是一个传统看法,因而可以信赖。1722年,巴黎金石与美文科学院院士普吕(Lévesque de Pouilly)坚持罗马历史的头400年是“不确定的”,因为所有叙述都只依赖口头习惯说法,他说:“当历史仅信任人的记忆时,它们在所有后继传达者的口中被改变”。普吕在这里明确否定了口头传递的可靠性,这种观点传扬开来必定会波及《圣经》,但学院其他成员拒绝该结论,理由竟然也是公开文献的公信力,即李维(Livy)同时代的受过教育的罗马人读者对李维《罗马史》的叙述没有争议。普吕在答复中坚持相信传统说法仅仅是“对我们不知来源之事的流行传言”。但他也作出些让步,承认一些传统说法如果涉及重大、公开和相当简单(易于记忆)的事件,可能在一般轮廓上颇为准确,例如广泛流传的关于世界是被创造和现在所有陆地都曾经被覆大水的说法。但丰特内尔1724年出版《论神话的起源》时却没有一点退缩,对口头传递进行了简要明确的攻击。
在关于内部证据的讨论中,还包括各种具体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寻找有关大洪水的事实,比如大洪水发生的地点和持续时间、诺亚方舟的制造和迁移,细分下去,诺亚方舟中的动物数量都自成一类问题。由于欧洲人开始熟悉此前尚不知晓的美洲、亚洲和澳洲的动物的种与属,因此如基尔谢和威尔金斯便列出那些被认为是杂交而不需要出现在方舟乘客中的动物。所提出的问题诸如,袋鼠怎么做到不在阿勒山(Mount Ararat)和亚洲东南海岸之间留下任何后代就迁移到澳洲?一些特有的美洲物种如何横穿大西洋?可以想象人类能找到方法横越大洋,但这么早的移民显然不会携带如响尾蛇这样的有害动物。所有这些解说都是郑重其事的,学者们没有要指摘怀疑摩西的意图,而是相信如果能以一种看似合理的方法填补细节将巩固《创世记》的可信度。勒·佩勒蒂埃1700年出版的《论诺亚方舟和黄鼠狼》就是一个例子,书中论述了许多奇特问题,认为确定它们就可以证实诺亚方舟的制作原料、能量、形状、组装方式以及在其中容纳的生活必需品和动物的数目、世界洪水持续的真实时间等。英国学者约翰·韦伯在论证中国语言是世界原初语言时,也对这些细节问题表现得格外有兴趣。然而对大洪水的讨论越深入,它是世界性洪水的论点便越难自圆其说,比如动植物分类学家约翰·雷便认为关于动物移民问题的答案如此可疑,使他不得不去质疑洪水是否世界性的。除了考虑大洪水的内部证据遇到困难,在以中国有关记载为外部证据证明大洪水的世界性时也最终导致相反的结论,大洪水问题是中国上古史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犹希迈洛斯主义
在17世纪的普遍认识中,《创世记》是最古老的文献,这便意味着无法找到关于这些最早篇章的更确凿的独立证据,因此确认《创世记》的真实性就需要寻找其他方法,而最常见的方法是将异教徒的古代传说作为外部证据来印证《创世记》中关于人类起源和初民历史的记载。这种方法既可以说是在证明《创世记》,也可认为是在相信《创世记》的先见之下用《创世记》来解释其他民族的历史,而后者的意味其实更浓厚一些,这就是17世纪圣经研究中运用“外部证据”时的陷阱。斯宾诺莎尽管深知研究《旧约》所需的历史基础天然薄弱,却坚决反对在《圣经》之外求解《圣经》,但他的同时代人能这么严格地在圣经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态度的,少之又少。
17世纪的欧洲人在努力寻找关于遥远过去的事实,这种愿望使他们复活并改进了自希腊人时代就有的犹希迈洛斯主义传统。犹希迈洛斯主义是以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00年的希腊作家犹希迈洛斯(Euhemerus)之名命名的一种神话阐释理论。古希腊斯多葛(Stoic)派哲学家创立了一种有影响的象征式(allegory)传统,他们坚持地中海人民的各个地方神都象征着同一个被神圣地规定的自然命运。斯多葛式的象征强调命运的角色,因为所有人都要服从命运,所以命运能够成为不同国家人民的共同纽带。斯多葛式道德诠释后来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关于神的神话事实上是以一种崇高的形式代表了伟人的行为。犹希迈洛斯受斯多葛派学者这种观点的影响,将东方文化中解释普遍流传之神话的一种古老方法系统化,他主张神学有一个尘世的源泉,众神原本是英雄和征服者,他们赢得了臣民们公认的尊敬而被他们的人民神圣化了。犹希迈洛斯的历史象征与希伯来式象征论(typology)恰好相反,希伯来式象征论从唯一上帝的全能性中寻找神的起源,而犹希迈洛斯从人类的国王和英雄中寻找神话传说中众神的起源。犹希迈洛斯的方法体系问世后广泛传播,在关于神话阐释的历史上有着特别的和持久的影响,早期基督徒尤其借助它来确认自己的信仰,但他们采纳的是一种修正式犹希迈洛斯主义,据以说明异教徒的众神不是真正的神,只是因为拥有功绩而在人类中享有超凡地位的人,古代神话集充斥的仅仅是人类虚构的故事。这样,来自古时异教徒而又具有文化权威性的神话就可以被吸收到基督教体系之下,同时又将神变成普通的人而消除其宗教含义。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神话阐释方面没有发展出新的理论视角,仍由象征式的阐释和犹希迈洛斯主义式的阐释居主导地位。需要注意,这两个时期犹希迈洛斯主义主要限于在古典神话或其他异教徒古代神话之内运用,而且文艺复兴时期强调的是它的审美意义。
17世纪的欧洲学者重新拾起犹希迈洛斯主义,却与前此做法有很大不同,他们旨在利用这种理论来沟通《创世记》和异教徒神话。古希腊的犹希迈洛斯主义意图指出神的起源,即他们曾是真实的人。17世纪的犹希迈洛斯主义紧紧抓住这种理论指示的神话中隐含历史性意义这一点,意欲反其道而行,想指出人的行为受神指引,认为将神话加以适当解码,就可以帮助重构古代统治者与其他杰出人物的历史。更进一步,古代异教徒的神话就是对《创世记》所载人类最早历史的碎化和歪曲。因此,以《创世记》为指引可以还原异教徒神话的真实所指,反过来这些神话又可以作为外部证据证明《创世记》。17世纪后半叶,神学家、评论家和诗人都倾向于对古代文学进行犹希迈洛斯主义式的解释,指出其中的寓意,古代诗人和哲学家不仅是圣贤,并且因为具有某种直觉预感而能更好地理解自然法则;同时他们通过传说搜集到许多诺亚洪水之前族长神学的残余,因而也均为犹太教—基督教真理的保证人。这些传说是在诺亚洪水之前300多年时由诺亚和闪(Shem)保留下来的,并通过诺亚的子孙们不断巩固和扩展,直至荷马时代前后。但这些诗人和哲学家有时也受到“魔鬼”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模仿魔鬼的教义。所以必须剥掉这些神话中传达魔鬼教义的表象,才能成功地理解其中固有真理,而古代诗人被正确解释后,实为真正的先知。
于埃1679年的《论福音书》是犹希迈洛斯主义的代表作。于埃希望通过证明上古史的事实来证明《圣经》,他的基本论据是,所有民族都是继犹太民族之后才出现,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埃及人、希腊人或罗马人的神话中寻找犹太人经书的踪迹或追回已遭磨灭的记忆。如果这些古代民族都认识犹太文书籍,那么他们对摩西也就应有一定了解,因此如果能在那些代表他们神祗的文字中发现某些特点可以使人联想到摩西并证明他们已将摩西神化,再加上他们是大地上继犹太人之后的最古老民族,他们最古老的历史就是他们的神话,那么由此便能证明摩西及《摩西五书》的古老程度。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极力证明所有民族只信仰唯一一尊上帝,也不在于证明各民族拥有与基督教伦理相似的一种自然伦理,而应该证明所有民族都得到了摩西的教义,有些迹象尚保留在他们的神话中。为此,于埃竭力将许多古代人物确认为异教徒记忆中的摩西,摩西是埃及的泰特(Theuth),是腓尼基人的塔奥图斯(Taautus),是希腊人的赫耳墨斯,是罗马人的墨丘利(Mercury),也是高卢人的特乌塔特(Teutatés),他还是酒神巴科斯(Bacchus)和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既然摩西以不同面目出现在古代各民族,那么关于摩西的教义自然传播于古代各民族之中,根据“普遍赞同”原则,这足以证明摩西的古老性。
看过于埃处理西方古代民族的手法和目的,就不会奇怪将有那么多人把中国的上古帝王对应为《旧约》中的族长。而揭去古代神话的表象以显现其内在真谛的思路和做法,与在华索隐派耶稣会士大同小异。其实“索隐派”起先就是欧洲17世纪这一批醉心于揭示古代神话寓意之人的专称,后来才移植到白晋等人身上,在华索隐派与欧洲犹希迈洛斯主义者有着类似的理论渊源,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
显然,犹希迈洛斯主义在17世纪重新流行不是古代犹希迈洛斯主义的简单复活。古希腊犹希迈洛斯主义关于神的起源的观点无疑有一定真实性,历史证据或人类学证据都可以说明,但即使如此,现代比较宗教研究者也并不将此当作关于神之起源的唯一可接受解释。而17世纪的犹希迈洛斯主义者就有些太过离谱,犹希迈洛斯主义原本只是指出神话具有真实的历史渊源,17世纪的欧洲人却将这个历史渊源唯一地规定为“圣经历史”,认为所有地方的神话都反映出圣经历史的影子,这是偏见之一。与此同时,他们把基督教文化以外的传说看作神话加以犹希迈洛斯主义式的解释,却偏偏不对《创世记》和其他圣经故事运用这种解释,先天地以为《创世记》是真实历史而非神话,别的传说则一定是神话而非真实历史,这是又一处偏见,也即奉行双重标准。17世纪的犹希迈洛斯主义同古希腊的犹希迈洛斯主义相比,囿于狭隘的圣经历史观念而失去了合理性,它更是对希伯来式象征论的继承而非对古代犹希迈洛斯主义的复活,它更接近基督教神秘主义理论喀巴拉而不是古代犹希迈洛斯主义。
但我们今天认为是偏见的,在17世纪许多学者那里还是信条,对世俗文本能进行娴熟历史性批评的人未必想过要将这种态度严格地运用于《圣经》文本。例如马比隆最重要的继承者蒙弗孔(Bernard de Montfaucon),他是中世纪希腊文古文书学的创始人,但他与他的大多同时代人一样,完全不能做到将《旧约》作为一部历史材料对待。马比隆和他的主要同事们被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身为僧侣的特殊地位所限制,故而尽管他们在文献批评方面成绩卓著,却仍不能与近代历史学家媲美。所以,17世纪对《圣经》的“证明”归根结底是一种姿态,对很多人来说,它不证自明。就连普吕这样质疑口头传递准确性的学者,也不能摆脱犹希迈洛斯主义,提出应该用异教徒的传统说法来证实《创世记》的头几章。他说异教徒的文献具有非独立性,因为一般认为它们来自于可上溯到诺亚甚至亚当的传统,但它们还是可以被看作“外部”证据,因此要仔细审查各种异教徒资料(包括中国编年史书、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古希腊和罗马神话),以从中确认创世、大洪水、希伯来人族长的业绩、及各种特定的基督教信仰,这还要求对异教徒的证据进行想象的和灵活的解释。尤其是大洪水传说,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这不会是各地地方性事件的巧合,而必定证明了《摩西五书》的真实性。毕竟,直到19世纪,新教徒大学的教授们才享有不必一一证实《圣经》细节为历史事实的自由,从而能够将《圣经》诸书置于历史背景下考虑。直到这时,对《旧约》的研究才真正发生变革。
不过,以维护《旧约》神圣性为主旨的17世纪犹希迈洛斯主义者同样可以给《旧约》的神圣性造成危险,尽管这并非于埃们的本意。犹希迈洛斯主义者固然是对《旧约》和异教徒神话持双重标准,但通过他们对《圣经》和神话进行这样的接合,却也很好地向读者暗示出《圣经》中包括神话。同时,对神话进行这种弹性处理,也启发一部分人将神话当作自然过程的人格化,而这与斯宾诺莎视《旧约》中的奇迹为遭希伯来人误解的自然事件十分接近。虎克是这条道路上的先驱之一,他提出许多神话事实上是指地震。丰特内尔多次再版的《世界的多样性》宣称,是自然过程造就了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而古代的人因为无知或“爱好奇迹”相信这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作品。
三、自然证据
事实上,引入自然的证据在很长时期内并不必然破坏《圣经》的权威,反会被以为是对上帝杰作的见证。所以,以自然过程解释神话不过是为犹希迈洛斯主义的流行形式增加一个细节,丰特内尔关于直布罗陀海峡的观点会在18世纪初成为老生常谈式的论调,热忱的犹希迈洛斯主义者巴尼尔(Antoine Banier)会在1739年的《根据历史解释古代神话和传说》(The Mythology and Fables of the Ancients,Explain'd from History。)中允许一些神话有自然过程为基础,有犹希迈洛斯主义倾向的普鲁舍(No?l-Antoine Pluche)在1739年的《宇宙的历史》(Histoire du ciel)中也将一些神话解释为自然过程的人格化。而且,地质学、生物学方面的自然的证据还曾一度被认为是证明世界性大洪水的更有价值的证据,因为自然提供了唯一符合方法论者发展出的挑剔规则的证据,自然不会虚假,且独立于任何人类对其运行的叙述。自然证据一度大受《圣经》捍卫者青睐的关键原因在于,当时无论科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必须在宗教限制之下考虑问题,除去一些肆无忌惮的激进者,社会的一般期望仍相信《圣经》将被证明是真实的且不会与自然提供的证据冲突,就如同莱布尼兹对历史古迹将证明宗教真理胸有成竹。
结果,1665-1750年间几乎所有的自然学家(naturalists)都使用短的地质时间表,以配合神学家所强加的编年学限制,即人类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相等,都是不到6000年。在这种给定的框架之下,地形学家(geomorphologists)只能接受“灾变”动力学来解释地表特征的形成,火山喷发、地震、洪水、酸雨、山崩和海岸线变化等等使自然界在短时期内就成为现在的模样。这样,自然学家不仅不排斥《圣经》年表,有些人还明确捍卫它。比如有人提出地球沉积岩外层的主体部分是自大洪水时代以来“逐渐”积累而成;有人设想陆地在大洪水之后很长时期内埋藏在深海之中,由于大海向赤道方向退却才逐渐显露出来。又如化石也被作为大洪水的有力证据,有人断言自大洪水以来有充裕的时间供生物体石化;虎克干脆在实验室里进行快速石化树枝的试验,并称自己发现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的一块地方可以于12个月以内在不破坏形状的情况下把木头和其他非石质的物质变为石头,人们由此得出结论,将实验室时间稍微延长些,对自然就足够了。
然而亦如对古迹的深入研究将使莱布尼兹的期望逐日成空,来自自然的证据最终也在《圣经》捍卫者中间引起更多惶惑不安。科学家们虽然普遍在运用地质学证据考虑世界的年龄时会将上帝当作一个必备因素,却并非所有人都会将《创世记》的真理当作一个真命题,个别怀疑论者将会把自然证据的运用引向反对《圣经》的方向。17世纪末的自然学家伍德沃德宣布他将通过考察自然的证据来审视摩西,并且只如对待李维或希罗多德那样对待摩西,这意味着他认为摩西的文本必须被审查、评价和确认。同样是化石,18世纪的法国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盖塔(Jean-étienne Guettard,1715-1786)与虎克等人的认识截然不同,他说在法国中南部多姆山省(Puy de D?me)火山群中发现的化石与《旧约》中的年代体系相冲突。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批评考证法在中世纪历史研究和古代历史部分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极大成功,但在与《圣经》有关的研究中却踌躇不前。原因有多种,对《圣经》进行批评研究的结果将令人心浮动甚至具有危险性;圣经研究要求更多技巧,而大多有知识的人达不到;还有波义耳和斯宾诺莎指出的,几乎不存在能够帮助学者处理世界上最古老书籍的资料。然而重要的是,17世纪后期的人,无论是能冲破成见约束奉科学方法为至上的人,还是因证明《圣经》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而焦虑紧张的人,都明白《圣经》必须如其他文本一样通过确认。换而言之,这时期关于证据的概念发生变化,“《圣经》不再是自然的向导,而自然成为正确解释《圣经》的一把钥匙”。总之,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只要将《圣经》推上历史批评与考证之路,这就给质疑正统神学的怀疑论者以更多机会和理由,这对《圣经》的神圣权威衰落而言就是一条不归之路。17世纪后半叶和18世纪前半叶,立意批判《圣经》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对《圣经》从求证到怀疑再到否定却是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有赖于科学精神之确立、科学方法之完善、以及证据之增加,这个过程又成为启蒙时代思想变革的一个稳健而强劲的推动力。
中国上古史正是在这个时代活跃在欧洲社会舞台之上,如果说启蒙时代的思想变化是这舞台上的一出大戏,中国上古史则主要是在此剧中关于圣经批评的重要一幕里出场。所以,中国上古史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历的风光必须置于欧洲的舞台背景下方能准确定位,这也是本书不避冗长之嫌铺叙欧洲的时代与知识背景的原因。欧洲人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正是随着他们对《圣经》的认识而变化——先以之证明《圣经》,继因之怀疑《圣经》,再借之批判《圣经》,从而使那段被耶稣会士所歪曲的中国上古史在启蒙时代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上古史也是帮助欧洲人重新理解圣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新证据。而作为证据,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资料本身也必须经受这个时代的证据检验规则的考量,耶稣会士叙述的准确性问题因此被部分地觉察,并进而促成“汉学”这个学科诞生。可见,中国上古史又可作为窥探启蒙时代欧洲知识与思想变革之“豹”的一枚“管”。本书期望着在布置好欧洲这个舞台环境、安排好各幕各场的顺序之后,读者对中国上古史在其中的表现自有会心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