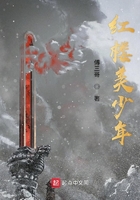老北京,俗称“四九城”。“四”指的是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个城区,“九”指的是内城的九个城门。
“东富西贵,南贱北贫”,这话大体上把握住了北京城四大块的特征。东城之所以“富”,是由于仓库多;西城之所以“贵”,是因为王府多,有清初八家********及“世袭罔替”的亲王府;南城所谓的“贱”,因那儿是汉民居住区,多属“下九流”;北城之所以称为“贫”,是由于德胜门一带有很多外地盲流。
本书说的事,大都发生在南城。
至今,从宣武门往南走不多远,有一条街,叫南横西街。街名拢共四个字,居然给出“南”和“西”两个方向,不仅把外地人弄糊涂了,就是当地人解释起来也颇感吃力。其实,清代那会儿,这条街叫西横街,当地人则简单的称为横街。
晚清时,横街有个门脸儿朝北的肉铺。不大,有个两丈多长,里面是肉铺的标准陈设,一趟硬杂木柜台,营业时,柜台上铺着刚刚切得的猪肉,分为大块儿和小块儿,还有猪身上各个部位的肉。柜台后面是个木架子,架子上有俩大铁钩,钩挂着两三扇猪半子。
肉铺看起来是中规中矩的,但铺名起得随意,就像没过脑子,随口叫了个“老朱肉铺”。那时的商业是粗线条管理,店名当然由老板说了算,只要不出大格,爱叫啥叫啥,官家不抻茬儿。
老朱肉铺的小老板姓朱名贵,有个三十多岁,长了张倭瓜脸,脖子粗,个子矮。胖乎乎的,皮肤白白净净,像个娘们儿。他的眼睛总眯缝着,就像没睡醒,显得有点迷糊。如果街上有俩人问路,而他正好在旁边,或许会指着他说:“要不,咱们问问那个矮胖子去。”
可但凡知道这个矮胖子来路的,都会避他几分。回避并不是怕,而是不愿意和他有瓜葛。至于个中原因,稍后就会揭底。
论起朱贵的籍贯,如果搁到现在,当地派出所得给他核发北京市户口本,而在清末那会儿,他算直隶人。他家所在地,如今算北京市远郊区县,叫门头沟区。他住的村子依傍永定河,村里副业是给进香者备伙食,由于进香伙食以素食为主,所以村名叫斋堂。
朱贵是同治三年(1864)生人,十岁那年,父母患了急症,没挺几天,双双身亡。打那之后,他跟着叔叔学杀猪。杀猪不用搭本钱,只需要一把屠刀。通常情况下,东家管屠夫一天的酒饭。杀一头猪的酬劳大概是一个猪头、一串猪大肠和三斤腰花肉。
斋堂那边至今保留着几个碉楼,一圈城墙。墙里仍住着些居民。据老户人家自述,过去这里是兵营,他们是旗兵的后代。那么,深山里为什么要建座兵营呢?明代后期,明军与清军隔山海关对峙,大明朝廷的臣子脑瓜相当死性,认准了一条:清军如若从关外进犯关内,就得通过山海关。没有想到,清军压根就不这么玩儿。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在位时不断对明军作战。明末,皇太极钻空子,率军从北面绕过山海关,钻进京西大山里,经斋堂,钻出山沟,向东掩杀到北京西郊,差点得手。明朝躲过这一劫,从此对京西斋堂一带不敢懈怠。
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破关,爱新觉罗·福临那年才六岁,在八旗兵簇拥下,入主紫禁城。“太上皇”多尔衮尽管日理万机,在百忙中也没有忘记,在斋堂左近建兵营及碉楼,驻扎军队。
晚清,清军作战能力远不如太平天国战争中崛起的团练。团练由汉人组成,是经过严格训练,后勤保障充分的民兵。在一个时期内,朝廷重视湘军与淮军,不怎么把清军八旗当回事。八旗部队由满洲旗人组成,按说与朝廷走得更近,但清军官兵知道,自己在朝廷那儿没面子,破罐子破摔,又懒又馋,猪送上门了,都懒得宰。朱贵跟着本家叔叔给驻扎斋堂的清军供应猪羊,把杀猪这活儿揽了下来,由此与驻扎斋堂的清军混了个脸儿熟。驻扎斋堂的清军人数不多,最大的官儿叫千总,千总手下有个笔帖式。笔帖式专干抄抄写写的活,属兵头将尾。斋堂驻军的笔帖式叫杨门拴,中不溜个头,中不溜面庞,什么都中不溜。他看上了闷头闷脑的朱贵,经打听,朱贵二十五岁,偷鸡摸狗之类事一概没有,而且没有父母,也没有成亲,想做什么事,自己就能拿主意。杨门拴不由暗喜,这正是他要找的那类人。一天,老杨试着问朱贵,想不想在北京找个活儿?朱贵当即露出典型的乡下人反应:到北京能拿多少钱?杨门拴回以三个字:拿薪俸。拿薪俸?朱贵一听就蒙了,只有官差才拿薪俸呢。老杨浅浅一笑,给你找的那地儿,就是吃官饭的。朱贵问,薪俸是多少?老杨回答更绝,比我多。比您拿的还多?朱贵简直不敢相信。老杨接着说,与你年龄相仿的比,你拿的是他们的三五倍。在朱贵那土得掉渣儿的脑袋瓜里,干活儿发饷银俸米,而且拿的银子是般对般的三五倍,做梦也梦不到这等好事,立马就答应了。
杨门拴说:“有条件。”朱贵忙问:“啥条件?”老杨答:“到北京给一位爷当义子。”朱贵心说,这算啥呀,不就是叫人家爹吗。回家跟叔叔婶婶一说,老两口有啥说的,相互努了努嘴,向外一甩胳膊,这事儿就算齐活。
几天后,朱贵随着杨门拴出山,进了北京城,没有去客栈,而是来到一家肉铺门前。初来乍到,朱贵懵懵懂懂的找不到北。后来才知道,这家肉铺铺名为“一枝梅”,位于南城的横街。到了肉铺的门口,杨门拴紧了紧裤腰带,绷着脸说:“你在外面耐心等会儿,我先进去一下。”说完就进门了。
“一枝梅”肉铺的掌柜,看样子有个五十来岁,后来朱贵才知道他姓霍,大伙儿叫他“霍爷”,叫顺了嘴,他的名字反倒不怎么提了。据老街坊说,当年的霍爷可神气啦,块大膘肥,大嘴阔腮,满脸横肉,俩大眼珠子瞪圆了,就像张飞的豹子眼。
一年前,霍爷得了一种怪病,不痛不痒的,只是吃不下饭,日渐消瘦,终日恹恹地躺在床上。他知道,自己挺不了多久,唯一愁闷的是膝下无子,成天想过继个儿子。
杨门拴喜滋滋地进了屋,跟霍爷叨咕了几句。说是从北京大西边儿的斋堂挑的,没爹没娘,也没娶媳妇儿。这样几方面条件都凑齐了,难找。最紧要的是,他是个杀猪的。正是听了最后一条,霍爷的豹子眼瞪圆了。
“杀猪的好哇。”霍爷边想着边说:“杀猪的对动刀子见血这些事儿不怵,而且,对‘咔嚓’一声响,就拿走一个大活物的命,也不怵。”
“那就是他啦。”杨门栓想了想,又说:“这小子,既不傻也不笨,但是长得那样儿嘛,不大精明,有点儿呆头呆脑的。”
霍爷一挥手,“门栓,在刑部里,凡是干我们这事儿的,就没有一个好看的,长得仰头竖脑的,还看不上我这行呢。”
杨门拴再没二话,旋即出门,领着朱贵进屋,不介绍,就一推朱贵的后脖颈,高喊一声:“跪下。”朱贵立马就扑通跪下了。
杨门拴踢了他屁股一脚,“跪下就完啦?往下该干啥啦?”
“砰、砰、砰”,朱贵连着磕了仨响头。
杨门拴喝道:“往下该叫什么啦?”
朱贵一抬头,高声回答:“义父!”
杨门拴最后喝道:“忘啦?义父是你的什么人?”
朱贵铆足了劲,扯着脖子,喊了俩字儿:“亲爹!”
“哎。”躺在炕上的霍爷应了一声。
普天之下,最为简洁的过继手续,放俩屁的工夫算完事了。转眼间,朱贵成了南城横街上霍爷的义子。随后,义父向新收的义子简单介绍了家里情况,说自己还有个女儿,今年十八岁。说到这儿,神差鬼使的,朱贵居然抬头看了看,只见门框边倚着一位姑娘,高挑儿丰满,长得挺好看,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漫不经心地瞭了他两眼,而后一扭腰身,闪了。
转天,朱贵在前门外大街溜溜地转了一天,繁华景象令他瞠目结舌。高大的城墙、热闹的市肆、琳琅满目的货物,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他见识到了京师的模样,昏了头,一门心思想留下来。过了两天,杨门拴领来俩穿官衣的,看样子,这俩人是霍爷的熟人,自打进门后,对霍爷就特别的客气,阐明此行只办一件事。
杨门拴和俩着官衣的打开一张纸,说是契约,逐一读条款,首要一条是操持霍爷的老行当,只要把霍爷的老行当接过手来,日后就能娶霍爷的女儿为妻,还能得到霍爷的“一枝梅”肉铺。
朱贵读过两年私塾,不傻不笨。契约上的几条都听清楚了,不太放心,拿过来看罢,差点拍着屁股跳起来。哈!天上掉下一张大烙饼了。这等好事,不要白不要;谁要让这样的机会从眼前溜掉,谁就是大傻蛋。至于契约上写的继续操持霍爷的行当,操持就操持呗,大不了就是杀猪呗。之前,朱贵没有签署过任何契约。穿官衣儿的把蘸墨毛笔递到他手上,客客气气地说:“朱先生,请您在这地儿签上您的姓名。”仅这句客气话,就让朱贵美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他舒展两下臂膀,随即拿起笔,刚要签字,抬眼一瞥,见霍爷的女儿正往屋里张望。这两天,朱贵已弄明白了义妹妹的概况。她叫霍小珍,年纪比自己小七岁;脾气挺柔顺,不大吭气儿;模样儿就甭提了,那盘儿,那条儿,要哪儿有哪儿。只要在这张纸上写上名字,那么好看的丫头,沿街的肉铺,用不了多久,就都成自己的了。他没有片刻犹豫,活动活动右手,而后歪歪扭扭地签上自己的尊姓大名。
按照穿官衣儿的要求,接着还得按个手印。不是食指蘸着红印油按,而是满巴掌涂满红印油,使劲地向下一拍。俩着官衣儿的拿着有朱贵巴掌印的契约,满意地吧嗒吧嗒嘴儿,走了。当晚,霍小珍进了朱贵的房间,惊得朱贵从炕上腾地蹦了起来。
她对朱贵说了平生第一句话:“我爹让你到他屋里去一下。”
霍爷平日里不爱说话,身体好的时候,就三棍子打不出个屁,身体垮了话就更少了,一天到晚,安静地躺在炕上。这个晚上,病中的霍爷冲着朱贵开腔了:“笔帖式杨门拴是我多年的老哥们儿,为人忠诚厚道,我托他帮我找个传人。他当个事儿办了,处处留心,就这么着,在斋堂搜罗到了你。”
朱贵恭恭敬敬地问:“义父,我到了您家里,干些啥呢?”
霍爷说:“杨门拴对你所说的那些,无一字是虚言。你到了北京后,安顿下来,有一份差事,活儿不重,每年只忙活几天。有饷银俸米拿着,而且饷银不少,是你般大般小当差的三五倍。”
朱贵问:“什么差事,能拿这么些银子?”
霍爷反问:“不寻常的差事。你自己想想看?”
朱贵并没有认真想过,尝试着回答:“……杀猪。”
“得得得,边儿去!”霍爷不屑地一撩巴掌,“凡是拿薪俸的,就没有干杀猪这行的。再说,你也不看看咱这是哪儿。京城,乡下不能相比。乡下的地不值俩钱儿,而在京城,只要地段好,就是寸土寸金。我这‘一枝梅’肉铺在南城,不敢说是寸土寸金之地,也是个寸土寸银。杀猪挣那几个小钱,能买这么好的地段开铺子?”
朱贵问:“那您是干什么的?”
霍爷说:“我要是照实说出来了,别吓着你。”
朱贵殷勤地说:“义父,您就说吧,儿子听着呐。”
霍爷想了想,微微摇摇头,慢慢悠悠地张了嘴,却还是那句话:“我要是照实说出来,别吓着你。”
朱贵不敢怠慢,瞪圆了眼珠,静待下文。
霍爷说:“要说我的行当嘛……是使唤鬼头刀的。”
“使唤鬼头刀?”朱贵懵懵懂懂地问:“使唤鬼头刀干吗?”
霍爷轻轻吐出俩字:“砍头。”
朱贵心里一惊,以为听错了:“什么什么,义父您再说一遍。”
霍爷依旧慢慢悠悠地说:“砍头。”
“砍什么的头?”朱贵紧着问。
霍爷斜了他一眼,“人头。”
朱贵当时就吓晕了,“咕咚”坐到了地上。
话说开了,霍爷不再回避,盯着他说:“听懂了吗?我干的行当,不是砍猪头、牛头、羊头,而是砍人头。你以为霍爷就是个横街卖肉的,错啦!我操持的是刽子手行当,在菜市口法场砍人头。”
朱贵魂不附体似的呆在那儿,像是吓傻了。
霍小珍手脚麻溜,凑过来,展开姑娘家软软的小巴掌,“噼里啪啦”地左右拍着他的脸蛋子,而后又掐人中。摆弄了一阵子,他逐渐缓过神儿,被搀扶到椅子上坐下,恍恍惚惚地继续听着。
霍爷盯着屋顶的老木柁,兀自说着:“北京这地儿,讲究子承父业。你想啊,皇上传位太子,以下的王爷,统统世袭罔替。科举走仕途的另当别论。其他:当兵的、做大买卖小生意的,手艺人、工匠、剃头、拉媒跑纤儿,甚至乞丐,都子一辈孙一辈地接续。大伙儿都这么着,就别说我这行了。我爹从我爷爷手里接过鬼头刀,又传给了我。我没出息,没儿子,养了个闺女。菜市口刽子手是父子相传,一茬儿接一茬儿,横是不能打我这儿断了,于是把你找来。先收你当义子,再让义子接过鬼头刀。明白了吗?”
朱贵沉重地点了点头,“我听明白了。”
霍爷说:“这事儿,先前没有跟你挑明。是因为……”
还没等霍爷说完,朱贵就嘟囔起来,“老杨要是事先告诉了我,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离开斋堂。”
霍爷苦笑了一声,“砍人头这个行当,你要是想起来心里犯堵,可以不干,腿长在自己身上,找个茬儿就溜了。但是,你白天签的那东西,按着你的巴掌印儿,那可不是个普通契约,而是生死文书,带连坐。你要跑了,你在斋堂的叔叔婶婶可就得进大牢了。”
朱贵一听这话,吓得浑身直哆嗦。霍小珍过来,不但不好言安抚,反而使劲一戳他的脑门儿。朱贵刹那间愣住,下意识地摸了摸刚才被纤细指尖戳的地儿。
在古典小说中,常用七尺八尺这类模糊语言描述彪形大汉的个头儿,而“尺”在不同朝代有不同标准。清末的人,不用尺量身高,兴站一块儿比。霍小珍比朱贵高出半头。
自从朱贵进了霍家的门儿,很少听过霍小珍说话。除了伺候老爹,进进出出忙活外,几乎就听不到她什么动静,像个既孝顺又规矩本分的孩子。而在这时,她露出了本色,像憋屈了多日,就要憋不住了,张嘴就是大糙话,而且嗓门拔得挺高。
“这两天儿过的,可把姑奶奶给憋屈坏了。”这是她的开场白。
朱贵一愣,眨巴眨巴眼儿,好像从来就没有见过霍小珍。
霍小珍叉起腰,“嘿嘿嘿,你小子是叫朱贵吧?”
朱贵迷迷瞪瞪地点了点头。
霍小珍打量了对方一会儿,那神情仿佛在看一只肥猫,而后咧了咧嘴开贫道:“朱贵,本姑娘从来就不在相貌上挤兑人玩儿。而对您这号的,我得说说了。您有空儿不妨撒泡尿照照自己那模样,就您这三寸丁的个儿,就您这张迷迷糊糊的二傻子脸,有模有样的大姑娘凭什么嫁您这样歪瓜裂枣的半残废?嗯?”
霍小珍一开骂,让朱贵想起了在斋堂那边村里的那些老娘们儿撒泼,那叫吓人。哟嚯,这两天居然没看出来,霍小珍原来也是个会撒泼的主儿。
霍小珍愈发来劲了,坐了,支起二郎腿,“没想到吧。估摸着你想不到我是这号的。听着!霍小珍我从来就不是盏省油的灯。再说啦,在菜市口操持砍头营生的老爹也养不出个文静女儿来。”
朱贵不知如何应对:“义妹妹,我……”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义妹妹是个什么样的人!”霍小珍高声说:“就你,山沟子里一个镚子儿没有的穷小子,我爹好端端的‘一枝梅’肉铺为什么让你承接?你想过吗?还不就是为了我爹的事儿有人接。昨儿个,你还是个斋堂臭杀猪的,今天,连女人加营生的就都到手了,你还想怎么着,还不知足吗?”
“知足知足,我一百个知足。”朱贵向霍爷和霍小珍连连作揖,“义父、义妹妹,你们得容我想想。因为这不是别的事儿,是砍人头哇!虽然我是从山沟出来的,也知道七十二行中,刽子手是最造孽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没人肯沾这个边儿的。”
“砍人头怎么啦?砍人头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霍小珍腾地站起,直着脖子嚷嚷:“砍人头跟砍猪头砍羊头砍牛头有啥两样?不一样的只是人脖子比猪脖子牛脖子细,还容易砍呢。再说啦,人头又不是天天儿砍。有个词儿你懂吗,什么叫‘秋决’?一年到头下来,就冬至前后那几天去菜市口法场砍头,其余日子你该干吗就干吗。”
朱贵还是没有太弄懂,急忙问:“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一年下来,就冬至前后那几天有差事?”
霍爷半闭着眼,“大概就是这样。不管是什么犯人,如果不是特殊情况,都是秋后问斩。也就是冬至前几天。”
“噢。是这样的。”朱贵盘算起来,而且嘀咕出声:“合是一年下来,就那几天犯膈应。那么……那么其他日子呢?”
“剩下的日子你就在家里杀猪,不愿意见人的话,就在小院儿里待着。都随你。都随你,都随你还不行吗……”嘟囔了几句,霍小珍不再嘟囔了,低头想了想,低声骂了一句,看她那口型,不是在骂别人,而是在骂自己,而且骂得挺悲怆。随即,她啪啪抽了自己俩嘴巴子,不是在作秀,因为抽的时候挺使劲。
再笨也能看出来,这丫头在酝酿一种情绪,一种可怕的情绪。
果真如此。霍小珍忽地站了起来,一扬脖子,逼上了一步,随即就亮开了嗓子:“朱贵,你小子知道不?按照你今天签字拍巴掌的那份儿契约,打今儿个起,就算接了我爹砍人头的行当。往后的事你知道不?往后我就得嫁给你。往后的日子什么样的,知道不?你就美美地过吧,怎么美,知道不?我白天打理肉铺;晚不晌儿,你坐在炕边,我得给你打洗脚水,把你的臭脚丫子洗干净,伺候你上炕。然后我得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上炕,还得岔开腿候着,岔开腿候着是什么意思,知道不?就是让你个混球随便儿捅,只要不来月事,就每天每天地让你干。你还想怎么着,你还想怎么着,你还想怎么着哇!”
朱贵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溜光水滑的大姑娘,居然会说出这么糙的话来。而且,话中捎带着的那见不得人的乐呵事儿,会让她说得如此地慷慨昂扬,如此地大义凛然,而且如此悲哀、悲愤和悲戚。
他不由自主地抬眼看看她,那红扑扑的脸蛋儿,那媚媚的单眼皮儿及婀娜的腰身,不由“咕咚”一声,咽下一大口口水。
霍小珍一眼就看穿了这小子的花花肠子,一股火登时就蹿了上来,纤纤细指戳着他的脑门儿,高声说:“杀猪的朱贵,你支楞起耳朵听好喽,本姑娘现在郑重其事地请你去办件事。”
“办事?”朱贵愣了愣,“你让我办什么事?”
霍小珍说:“听着!你出了家门儿,满世界撒着欢儿去打听,横街这片儿,霍爷的女儿霍小珍,从模样到身条,够不够拔份儿,能不能震倒一大片,能不能拔得头筹?”
朱贵紧着应付,“义妹妹肯定拔得头筹,肯定拔得头筹。肯定!”
“谢谢啦,难得你这样的二傻子也明白。但是,但是!横街最棒的妞儿是给你备下的吗?嗯?横街的头号美人儿是候着斋堂来的臭杀猪的吗?嗯?”霍小珍愈发来劲儿了,歪着个脑袋,右手拇指斜着向后一晃一晃的,“左近方圆,从法源寺前街到法源寺后街,从糖房胡同到教子胡同,从北半截胡同到南半截胡同,你可着劲儿去打听打听,有多少爷们儿在打我的主意。我对他们并不是不动心,有好几个纯爷们儿让我走过脑子。而眼下,为了我爹的差事有人接续,许给了你个三寸丁。就你这号的,居然敢得了便宜卖乖!”
经过这一通数落,朱贵心里也盘算好了:“霍小珍,我听明白了,也想明白了,照这么说,是我对不住你了。”
他这一改口,她的心里顿觉委屈。“……你对不住我?”
朱贵赶忙说:“是呀是呀,我对不住你。”
霍小珍的眼眶里泛出泪光,尽管一忍再忍,还是抽泣起来,“你没有对不住我,用不着对我赔情道歉。是我对不住人家,我该给人家赔情道歉。天呀,人比人,气死人。你这样的,撑死了就是个矬地炮。而教子胡同的刘大江,说出来你别不爱听,高出我多半头,而你呢?不信咱俩现在就比比个儿,你肯定比我矮多半头。请你用你那猪头算算,多半头加多半头是多少?横是人家比你高出一头多,你得略微抬起脚尖儿,脑瓜顶将能够着他的下巴颏儿!”
朱贵垂下了头,真的自愧不如了。
“而且,而且,而且……”霍小珍愈发来劲儿了,“而且刘大江中举啦!听清楚没有?人家是个举人,准备考进士呢!哪个女人不想腻味在这种大男人的大怀抱里。我就对你这二傻子实话说吧,刘大江瞄上我不是一两天了,刘家托媒婆上门提亲多少次了,我爹都没点头,就是为了等着认个义子接承他的事然后再娶了我。刘大江刘大江刘大江……小珍对不住你了。”她捂着脸跑了出去。
朱贵斜眼看着霍小珍跑出去,心下主意已定,表面却傻头傻脑地伸出胳膊比划,高出自己一头还要多的那个人的个儿到底有多高。
霍爷看在眼里了,叹了口气:“朱贵,刚才小珍说的,可全是真的。头些日子刘家托的媒婆还来了呢。”
朱贵的胸脯大起大落了一阵子,猛然间嚷起来:“义父!我现在就算完完全全的、彻彻底底的答应您了!我赶明儿练练手,您再教教我,我一旦觉得差不多了,就上法场砍头,砍人头!”
霍爷说:“你答应得这么痛快,是不是有条件呀?”
朱贵顿了顿,“……是有条件。”
霍爷问:“什么条件?”
朱贵嗫嚅:“我砍下第一个人头后,霍小珍就嫁给我。”
霍爷正考虑如何回答时,霍小珍揩着腮边的眼泪,一撩门帘又进来了,把她爹的嘴一捂,“爹,你不用说话,我来回答他。”
霍爷和朱贵都不再吭气,盯着霍小珍,静待下文。
霍小珍手指点着朱贵的鼻头,大声说:“就你这号的,甭提什么狗屁条件。我霍小珍虽然是个娘们儿,但是,我这娘们儿比你这爷们儿好说话,想事比你想得明白。你个山里钻出来的穷小子,二十好几了,估计还没尝过腥味儿呢,肯定想女人想疯了。行啦。行啦行啦。你只要答应当我爹的传人,就用不着等到砍下第一颗人头。你只要甩出句爷们儿话撂在地上,听着!明儿个,我就可以嫁给你!”
霍爷的眉毛略感惊讶地一抬,吃力地撑起半边身子,笑了笑,“小珍,你就不怕这小子先娶了你后变卦?”
“我怕个啥。”霍小珍斜睨着朱贵,“斋堂来的臭杀猪的,你小子给我听着,我就是嫁给你了,枕头边儿也会时刻放着把剪子,你要是变卦了,我会咔嚓一剪子剪了你的命根子!”
不由自主,朱贵垂下头,挠着后脑勺,偷偷乐了。
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老刽子手霍爷向老街坊郑重宣布,收斋堂来的朱贵为义子,接他的班,并把独生女儿霍小珍嫁给他。几天后,霍家操办婚事。别看霍爷操持的行当不好听,左邻右舍少有往来,但是都知道,他人厚道,卖肉准斤足两。当天来的街坊邻居不少。新郎和新娘原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用抬花轿,只是在肉铺跟前没完没了的放炮竹,“噼里啪啦”地响了一个时辰。
洞房就是霍小珍的闺房。平日,朱贵都不敢往房间多瞅一眼,有事经过这个房门,耸耸鼻子,能闻到里面飘出一股淡淡的幽香。而在这个晚上,他被几个毛头毛脑的小子连推带搡拥进了屋。
人都走了,霍爷关门睡了,轮到新郎、新娘独处了。别看朱贵今年已二十有五,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童男子,连梦遗都不清楚是咋回事。从山沟里到京师,他初来乍到,原本对新娘不大把牢,对她的底细有点二乎,以为备不住她早就被附近的混球儿——比如她总挂在嘴上的那个刘大江开过苞了。但这时发现,别看霍小珍嘴里啥都敢掏,一到动真格的,那种羞涩,那种紧张,比自己还厉害。
朱贵从来没有经过女人,但是在斋堂时,公猪和母猪交配,他可见多了。公猪是从后面爬到母猪背上干事。山里人把猪的交配动作称为“骑”。他模模糊糊地知道,男人和女人行房事好像不是“骑”,而是面对面地干。
朱贵摸索着按这个要领去做了,自己先脱了衣服,而后就背过脸去,等着霍小珍慢慢脱。但是,霍小珍害羞,脱到内衣,就不动了。朱贵回过头看了看,热血冲顶,难以自制,扑了上去。
十八岁已算成熟女人了,就像个长满了汁液的大蜜桃儿。色令智昏,这话一点也不假。朱贵在昏头昏脑之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强项”。不大不小的猪,也就一百多斤重,和人的体重差不多,驯服一头活猪,在他是小菜一碟。而且,煺毛后,才会发现,猪其实也白白净净的,和人皮肤的颜色差不多,不仅如此,猪的躯体和人的躯体,摸上去,手感其实也差不多。杀猪前,活猪会哀嚎着拼命挣扎,义妹妹是个活物,却一声不吭的,任凭他摆弄。他把杀猪的本事略微使出了一二,干得挺麻溜,几下子就把义妹妹剥得一丝不挂了。而后,他把吓得哆哆嗦嗦的新娘子小心翼翼地摆在炕上,接着就俯身上去了。
往下该做啥了?对了,听村儿里的混小子们说过,干这事儿之前,得先亲嘴儿。他的嘴唇儿使劲往前嘬着,忙忙活活地找女人的嘴,四片唇很快就贴在了一起,渐渐地相互吮吸起来。
往下就是干最为当紧的。他抖擞精神,一阵子胡乱比划,那东西居然就入门了。开始,她有些疼,还往外使劲推了几下,接下来就进入了状态,挺舒坦,哼哼唧唧的挺逍遥。
完事了。他从她身上下来,刚翻过身去,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霍小珍羞涩地交给他一块白绸子,上面沾着血迹。
这下,他心里有谱了:这媳妇儿是崭新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