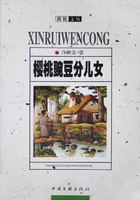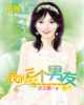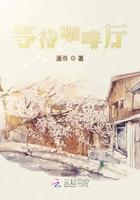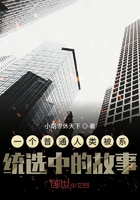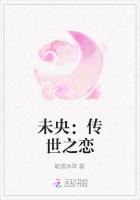近现代学人把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象地比喻成“酒”与“瓶子”的关系。晚清文学改良运动,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都积极倡导“旧瓶装新酒”,即用新材料来填充旧的文学体式,以此来显出文学的近代性(现代性)特征。而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则极力主张“新瓶”装“新酒”,用胡适的话说,文学革命就是为了建设“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他们既反对“旧瓶”装“旧酒”和“旧瓶”装“新酒”,也反对“新瓶”装“旧酒”,他们把这三种形式都当成是非现代性和伪现代性的东西。因此,“五四”前后新文化派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这一派内容与形式的取用和搭配之上。周作人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现在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还是旧思想;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转;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象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那可更古旧得厉害,好象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之外。”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胡适则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屑一顾,他说:“现在的小说,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笃,遂订白头之约……而大妇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生抚尸一恸几绝’……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故不值一驳……”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他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之所以在中国文坛的盛行,主要是因为国内缺乏“高明的文学方法”,也就是缺乏对“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发现、占有并加以整合的具体操作规范。鲁迅则讥嘲“鸳蝴派”语言的陈旧和题材的俗套:“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淌牌’‘吊膀’‘拆白’,什么‘噫噫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吁嗟风风雨雨’‘耐阿是勒浪覅面孔哉!”鲁迅:《有无相通》,《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1年1月1日。“五四”时期新文学派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是零打碎敲式的,并没有集体性地对之加以攻伐,而且当时“鸳蝴派”小说正值鼎盛时期,在普通民众中很有市场,几乎是独步于当时文坛,这一派小说家们也许觉得新文化派的批评势力尚小,还不足以动摇他们的存在根基,因此没有人站出来与之辩驳。
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文学研究会为主体,新文学派对“鸳鸯蝴蝶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批判,这一次批判是整体性的,因而比“五四”前后攻势猛烈得多。文学研究会主张艺术“为人生”,如郑振铎所云:“我们要晓得文学虽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像之美来感动人,但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泻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8号,1922年5月11日。因此,他们立足于文学承担着伦理与道德重建任务的思想角度,来着力批判“鸳蝴派”的“娱乐”论、“消遣”论。茅盾在批评“鸳鸯蝴蝶派”时指出:“他们小说里的思想,也很多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作者自己既然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并且他们大概缺乏对于艺术的忠诚……在他们看来,小说是一件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这种“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就是“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郑振铎不仅称“鸳蝴派”为“文丐”(西谛《消闲?》),还认为他们简直就是“文娼”:“我以为‘文娼’两个字,确切之至。他们象‘娼’的地方,不止是迎合社会心理一点。我且来数一数:(一)娼只认得钱,‘文娼’亦知捞钱;(二)娼的本领在应酬交际,‘文娼’亦然;(三)娼对于同行中生意好的,非常眼热,常想设计中伤,‘文娼’亦是如此。所以什么《快乐》,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西谛(郑振铎):《“文娼”》,《文学旬刊》第49号,1922年9月11日。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会还对《礼拜六》刊物的广告词“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有人认为这是“文学事业的堕落”:“世间竟有无耻的文学者,情愿卖去了自己的人格,拿高贵的文学,当做消闲娱乐满足肉欲的东西,还怕人家不知道,更在报上登起广告来,说是‘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蠢才(胡愈之):《文学事业的堕落》,《文学旬刊》第4号,1921年6月10日。叶圣陶则称:“这实在是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圣陶:《侮辱人们的人》,《文学旬刊》第5号,1921年6月20日。
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批评、指责和谩骂,“鸳鸯蝴蝶派”并没有等闲视之,而是作了及时的回应与辩驳。他们本着创作自由的观点,来回击文学研究会对他们的批判:“小说作者若努力于创造作品,将他心中所深信而不疑者抒写陈述出来,那么他的作品里,一定含有个性。个性是作者创造的自由,不但自己应该尊重他,批评家与社会也当尊重此点。”张舍我:《创作自由》,原载《最小》报第6号,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因为文学创作是自由的,所以不应该有“新”“旧”之界限:“为着文学前途,那么只要作品进步,无论这作品是何人做的,都应该提倡,不必把新旧的界限放在心里,不必把人我的界限放在心里。现在攻击他人的先生们是不是如此?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如此。”胡寄尘:《一封曾被拒绝发表的信》,原载《最小》报第8号,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小说很有销路的时候,文学研究会对他们所作的指责和谩骂,实在有“同行嫉妒”的“嫌疑”星星:《商务印书馆的嫌疑》,原载1922年9月1日《晶报》,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此外,“鸳鸯蝴蝶派”主张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是“寓教于乐”,并以此为根据为他们所说的“消遣”和“娱乐”的思想观念作了辩解:“我以为专供他人消遣,除消遣之外,毫无他意存其间,甚且导人为恶,固然不可。然所谓消遣,是不是作‘安慰’解?以此去安慰他人的苦恼,是不是应该?且有趣味的文学之中,寓着很好的意思,是不是应该?这样,便近于消遣了。倘然完全不要消遣,那末,只做呆板的文学便是了,何必做含有兴趣的小说。”胡寄尘:《消遣?》,原载《最小》第3号,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尽管“鸳鸯蝴蝶派”对文学研究会的批判作了一定的回应,但老实说他们缺乏有说服力的理论家,也未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理论,因此他们的回驳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文学研究会对“鸳鸯蝴蝶派”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当时直接承借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余威,而且也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茅盾、郑振铎等,后来亲自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工作,他们是历史的制造者和书写者,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力,这样,“鸳鸯蝴蝶派”就只能咽下被历史淘汰的苦果。关于此中的机妙,我们可以征引刘禾的下述言论来阐述之: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旺完全依赖娱乐市场,其报酬或多或少是由大众消费决定的。而五四作家则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评论和文学史写作这样一些体制化的做法,来着力于生产自己的合法性术语。理论起着合法化作用,它以其命名能力、引证能力、召唤和从事修辞活动的能力使象征财富和权力得以复制、增殖和扩散。“五四”作家和批评家凭借这种象征权威而自命为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同时把其对手打入传统阵营,从而取得为游戏双方命名和发言的有利地位。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0页。
文学创作的两种现代性的争执——新文化派“血和泪的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消遣娱乐的文学”最后是以新文化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的。“鸳鸯蝴蝶派”从此成了以后所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股反动的逆流。
与“文艺大众化”擦肩而过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成立,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左联”成立之后,讨论和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大众化问题,而这次讨论中,很“大众化”的“鸳鸯蝴蝶派”却并没有进入讨论者的言说视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左联”所谓的“文艺大众化”的具体含义到底是什么?有关此问题的讨论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具有显在的大众化审美特征的“鸳鸯蝴蝶派”没有作为他们讨论研究的基本对象?
在1931年“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明确写道:“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立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语)为原则,同时也须达到这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原载《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从这段决议中我们不难看到,“文艺大众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任务和目标而被提出的,提倡“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的大众文学,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当时许多新文学作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他们就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文艺大众化所涉及的内容与形式上的问题等等,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谈到艺术的基本属性时,沈端先引用前苏联文艺家乌拉奇米尔·依里支的话说道:“艺术非为着民众,为着几百万勤劳的大众,——就是工人农民而存在不可。……艺术的根底,应该深深地埋在民众里面……艺术,非使大众爱好不可。艺术应该和他们的感情,思想,意志结合,而使它昂扬起来。”沈端先(夏衍):《所谓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而对于“大众”对象的确认,这些作家是旗帜鲜明的,他们认为这里所指的“大众”并不就是“全民”,而“应该是我们的大众,——新兴阶级的大众”王独清:《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所谓“新兴的阶级”,就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这样,文艺的大众化也就变成了“无产文艺的通俗化”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由此可见,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并不是在文学艺术的雅俗共赏这样的审美框架内讨论问题,而是让文学成为政治斗争和文化宣传的附属品。诚然,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当救亡压倒启蒙的时候,扩大文学的政治化功效是情有可原的,但30年代是新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救亡的形势并不如一些作家想象的那样严峻,文学的审美探求仍应该成为新文学的主要目标,持续了整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一直在文学的政治化框架内思考文学的问题、寻求文学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存在极大的偏误的。再者,“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所称的“大众”,仍然是一个假想的读者群,并不就是现实层面上的大众,如果真的达到像当时一些作家所期待的那样“使大众能整个地获得他们自己的文学”,那么“大众化”可能实现了,而与此同时,“文学”也随之消亡了。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比如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与40年代的“讲话”与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之间的联系,“左联”的成立和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负面影响,可惜这些问题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得到深入的阐释。
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作家显然对文学的设想过于理想化了,他们指责20年代的新文学是“过于投合智识份子读者的脾胃的”洛扬(瞿秋白):《论文学的大众化》,《文学》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大众文学,就是“要用劳动群众自己的语言,针对着劳动群众实际生活里所需要答复的一切问题,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刊》创刊号,1932年6月。。在讨论过程中,只有鲁迅还显得较为客观和冷静,他说:“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鲁迅:《文艺的大众化》,《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0年3月。鲁迅的目光是敏锐的,其思想也是深刻的,寥寥数语之间,已经点到了“文艺大众化”的要害,如“全部大众化”的非现实性,有可能与“政治”结盟的内在隐患,等等。也就是说,鲁迅早已意识到“文艺大众化”口号的局限性和弊病,意识到其中的政治性话语蕴涵,鲁迅所意识到的这些后来都在中国文学的实际中得到验实。
本来谈文艺的大众化,“鸳鸯蝴蝶派”是绕不开的参照和模本,因为他们的作品恰好就在大众化方面比“五四”新文学要做得成功。但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它不是站在文学如何做到雅俗共赏的审美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站在文学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非文学角度来探讨问题,这样,作为此前被新文化派批判的“鸳鸯蝴蝶派”自然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了。如果说,“五四”前后的文学论争中,“鸳鸯蝴蝶派”还有插嘴的机会的话,那么,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这个与他们密切相关的话题,却根本轮不到他们发言。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和运动的这种情形,说明了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已成了这个时期现代性追求的基本表现形态,也从一个角度交代着“鸳鸯蝴蝶派”已经被历史遗弃的客观事实。
在世纪末的文学反思中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