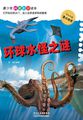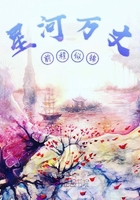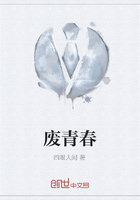——四川大学徐新建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
徐杰舜(以下简称杰):徐新建教授今天很高兴在相思湖旁采访您,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科背景。
徐新建(以下简称新):今天接受您的采访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多年同行和朋友问的对话,另外则是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系列访谈的参与。我觉得这个系列访谈已逐渐成为国内相关学界沟通、互动的品牌。我对它的组织者心怀尊重。在我看来,创意、组织和策划是学术表达的另一种方式,亦即古人所谓“知行合一”的体现。
杰:我们这个访谈已经采访了30个人了。包括了海峡两岸三地的各个有关方面的人类学家。包括具有国际权威声誉的李亦园院士,但是也有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像当时刚刚毕业的孙九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所以李先生认为我们这个访谈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方李莉认为这是中国人类学的族谱。所以我很想把这个访谈继续做下去。你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回来。而且又是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所以今天就想请你把你的学术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
新:我个人“走向人类学”的经历,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小时候喜欢音乐,先学竹笛后学提琴——学五线谱、拉西洋曲。现在看来,似乎很早就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转变。“文化大革命”期间没书读,但普及“样板戏”的需要却给一代人提供了投身艺术的机会,同时也在闭关自守的封锁中留下了“洋为中用”的空间。考上大学后,改行学中文,兴趣又转移到文学和理论,同时开始关心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方的比较。这时,“文学”成为继“音乐”之后我的第二个梦。当时的校园文化很活跃,我们办刊物、搞沙龙,还以(19)77、78和79级的同学为主成立剧团。我当导演,每学期都排演话剧,其中一些很“先锋”,还得了奖。最后又拍电视剧作为毕业论文,在为学科与专业的合理性而力争说服导师方面,费了不少口舌。那个时候对艺术期望很高,认为国家的兴旺在于文艺的复兴,人生的志趣在于审美。朋友们之间流行的一句话是:“一百个拿破仑抵不上一个贝多芬。”
杰:那你怎样转向人类学的呢?
新:毕业后我分配到文化部门工作,然后考进社会科学院。经历从机关到基层、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向,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了解海外的前提下立足本土,于是研读比较文学并逐渐走近人类学。
机关的两年,对我来说等于在“上层建筑”里获得一段亲身的观察、体验,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分层、权力的作用和书生的幼稚。那时对天天都要接触的一个事物体会很深:文件。我们在大学里曾花费大量时间学文论。然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文艺实践来讲,从深处影响文艺运转的其实是文件——文件传达国家的文艺政策、规定社会的精神方向。比起学者们费力撰写的大量表面文章,无论“推动”还是“阻挡”,文件都更直接地左右了中国民众的文化生活。
1985年进人贵州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职业上来说,就变成了职业的文学研究者。贵州地处西南,是多民族省份。我们的研究必须面对本土,面对地域性文化和多民族传统,同时还必须关注现实。在所谓的“学科意识”方面,我们不像大学,不崇尚纯理论,反感空谈,侧重对当下“活文化”的研究,倾心于“经世致用”。这一点使我在后来很容易跟叶舒宪提倡“破”学科产生共鸣。因为我们既关注学科、学理,但更看重对其的突破和超越;以社会问题和历史进程为对象,而不是以学理为归宿,更不以学科为牢笼。在这方面,比起其他的现有学科来,人类学似乎更具有“科际整合”以及“知行合一”的特点和优势,所以就吸引了我们向它走近。
举个例说,在贵州研究苗族文学,涉及文学、少数民族文化,涉及贵州的地方史、民族关系史,每一方面都涉及不同的学科;如果孤立地分开来做,不仅做不好,还可能使对象遭到肢解和割裂;只有把这些学科打通,你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分析和描述苗族文学。其他如研究傩戏也好、侗歌也好,甚至研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涉及多学科的关联整合。所以在贵州,在西南,地域性的文化特点促使人们在学术研究上所形成的特点,首先就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意识和心态。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面向田野。这个面向是必然的。在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里,你的第一手材料,显然不是来自于文献。并且我们也不以制造理论为第一目的,丽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去研究现实。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常年在基层走。贵州81个县,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这81个县你至少要走完一半才能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者而言,能背多少书都没用,“走向田野”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走了也不觉得稀奇,不值得荣耀。在那个圈子里,你要是没走过田野,根本没有发言权。这样,“多学科”和“走田野”就把我们的研究与人类学很自然地连接起来。
杰:你那个时候走向田野的感受很有意思,我们有些学生一进入人类学这个学科,就问我人类学为什么要做田野?不做田野行不行?我说不行。看来你最后进入人类学跟你必须走进田野有关系。
新:对。而且我们回过头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大学的田野观跟研究机构的田野观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大学好像是社会里的文化孤岛,在里面可以系统地学文学、学历史、做中外比较,但所依据的几乎都是文本,可以说是在图书馆里观察“文本中国”。可是真正的中国在哪里?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在贵州、四川、云南……这样的省份里,贵州又是什么?贵州就是那些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是省城贵阳、遵义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你只有从生活的本貌上认识这些具体事象,你才可能谈论中国,才可能谈对中国的研究。
所以我发现在两个阵营里面谈田野,彼此的田野观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学里谈田野,多半是附加的,是专业和理论的“锦上添花”,而不是务实求知的必然要求。所以一些关怀现实的老师们不得不苦口婆心地劝告学生“走向田野”,但收效甚微;如今竟还从一些学校听见“告别田野”的呼唤。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样的话之所以由“学院派”喊出,是因为他们的中国是一个虚拟的中国、符号的中国和主观的中国,与现实隔了一层“文字的皮”。与此不同,另一种非学院派的田野观要求的是以现实为本位、学科为工具,自觉地在田野里寻找自己的学术生命、学术起点和学术皈依。
在贵州社会科学院的日子里,我和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贫困”与“发展”的反思。1987年,我们在贵阳组织了一次“东西部中青年理论对话”,就当时很吃香的“梯度理论”展开辩论。针对发达地区主流话语中的“单一经济学”眼光,西部学者强调“地域”、“民族”与“人文”、“历史”的意义。那时我们经常说起的书有王小强的《富饶的贫困》和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后来到新疆做“对外开放”课题,又发现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从中获益不小,对作为地理、文化和历史构成的中国“西部”,有了更为深入的体认。
当时的“梯度理论”,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分成三个梯度,东部沿海作为第一梯度,中部地区第二梯度,西部第三梯度。该理论主张把最好的资源、最好的机会投放到东部,使整个中国分梯度发展,西部的前途要等东部发展以后再说。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国家性的最大资源其实就是中央政策的发布与实施,政策代表权力;不同量级的权力,产生不同量级的效应。这样,当国家权力向东部倾斜,比如给一个“特区政策”,那里马上就被激活,被权力圈化的地区就产生出资源倾斜的效益。而在权力资源分配极为不均的社会里,这样的发展却是以把其他地区定为“次要梯度”,从而牺牲当地民众的平等竞争机会为代价的。这样做的后果会导致地区差距的拉大,由此可能导致一些震荡。所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一批西部的学者提出“反梯度理论”,反对按不均等的方式划分和发展中国。
当时参与论争的人很多,话题也不少,既讨论经济,也讨论文化,还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怎样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保护。大家都以问题而不是理论为主,以现实参与而不是学科分类为重。在这种经验中,我觉得学院派的学术和田野观跟实践派是不太一样的。关于这一点,论争并未结束,今后还会有对话和交锋。我在这里旧话重提,是想提请一种关注,即关注人类学作为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的两重影响。人类学的特点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文理打通、文史哲打通,传统和现代、理论与应用以及东西方的打通。
杰:有意思,“五重打通”。
新:这是一个方面。与走近人类学有关,值得一提的还有参与一套丛书的组织和撰写,就是“西南研究书系”。云、贵、川三省的一群中青年学者跟云南教育出版社合作,发起出版关于西南研究的丛书,其中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怎么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来认识西南,按族群与文化的自身区域来做研究。比如说对待侗族,我们不想再像以往那样仅把其分割在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诸省边地做生硬拼凑,而是把它视为跨省关联的整体。对其他如“父子连名”和“舅权制”等文化事象也期望亦然。在这套书中,我们计划研究的问题有西南地理、西南历史、西南文化、西南民族以及西南宗教、西南与中原等。我承担的《西南研究论》,就是总论。我认为丛书是一种大文本,一套丛书的作者是一个群体,集体书写。这种“大文本”的书写应该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思想。所以编委会觉得应该有一个总序来贯穿所有的专题。大家集体讨论,最后委托我写。我写了8千字的总序,获得大家一致通过后又发展成专著。当时是咬着牙写出来的,无论功底还是积累都不充分,但有激情,比如呼唤“西南学派”,呼唤“从西南认识中国”,呼唤“与世界对话”等等。很多话言犹未尽,也还有很多需要再完善的地方。那时也常读人类学的书,但忙于现实参与,读了就用,顾不上深入和系统,不过对于有关东西方的差异以及双方理论术语的平等互动等问题,已有所质疑和反思。比如我们追问说:在对待“萨满”与“巫师”、“仪式”与“跳神”等的对举时,为何要用前者说明乃至取代后者?难道只有前一种说法才代表普世性的知识?总之疑问不少。
杰:后来呢?
新:后来在1992—1993年考进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一年。该中心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办。中外学员一同学习、生活,由美国教授给中国学员讲“国际关系”、“美国历史”等课。那一年我们有很多对话和研讨,提高了英语,也开阔了眼界。我还在历史教授指导下,做了一个学期以印第安文化为主题的“独立研究”。不过最主要的收获是面对面地感受西方人的思想和习性,听他们发表对中美文化的看法、对世界秩序的观点,其中包括介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
再后来调到了四川大学,阴差阳错,卷入到了“学院派”的阵营。到四川大学之前我和萧兵、叶舒宪、彭兆荣等几位朋友发起做了一件事,让文学与人类学相连接,在1996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长春年会上,倡导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到四川大学后,与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的基础联系起来,成立了“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如今又有了文学人类学的博士点。四川大学在成都,也在西部,是教育部在西南的重点大学。我在那里边研究、边上课,分别教授比较文学和文化人类学,在学科上朝人类学方向又走近了一步。
杰:从你这个背景来讲,你是搞文艺的,进到文学,再从研究机关转到学院。你具有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你的经历非常丰富,跟一般的直接从学院到学院,经典人类学、科班人类学有点另类。但是这种另类丰富了你的经历。你是否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着重谈一下你是怎么进入人类学的。
新:这样的进入有两条线,一条是经历,一条是学理。第一条线,从艺术走向文学,从文学走向理论,又从理论走向田野……最后就走向了人类学。从学理上分析的话,可以说是人类学的品位和特点,使我们这些从事地域和族群文化研究的学人走向了它。因此一方面是我们走向人类学,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走向我们。人类学从西方引进以后,需要“落籍”,需要本土化,即要由本地的学术主体对它再认识、再接收。在这方面,工作在基层的学者们的努力特别重要。如果说早期前辈的翻译引进功不可没的话,基层人员的实践操作也不容低估——是他们使外来学科和理论在中国本土生了根、结了果。在这点上,我特别赞成讨论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最近以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引起同行的关注。但我觉得还有许多层面需要深入展开。比如同为中国范围,西方人类学引进后的“本土化”路程和演变,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就很不一样。表面看都在“走向人类学”,但背景、目的、重点及方法却各具特色。这不值得比较分析么?
杰:你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价值。我们访谈的题目就定为“我们走向人类学”,你同意吗?
新:这我当然同意。反过来看,“人类学走向我们”有一个学科发展史的问题。它起源于西方,经过殖民时代、后殖民时代,然后从西方走向非西方。这里面又有一个值得回顾的过程。在早期的时候,是西方人士,包括学者、教师、传教士、外交家,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把人类学带人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对他们有用。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主动走向人类学,早期的前辈包括蔡元培、吴文藻等,扮演着“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角色,视人类学如希望的“火种”一样,孜孜不倦、前仆后继地加以介绍和引进。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学对中国有用。
从中国近代史的过程来看,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看,在人类学的路上已走过了几代人。我们的“走”,标志着另外一个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际上是在延续当年的“双重走向”。在如今全球西化和反西化的过程中,人类学需要进行学理与实践两方面的对话。一方面,全球化过程需要来自人类学的声音;另一方面,人类学本身又需要来自不同文明的声音。人类学需要走出西方,在非西方世界的再传播和再改进中完善自身学理,以承担在文明碰撞的世界里重释“人为何物”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