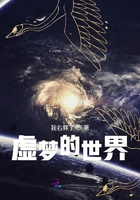的确,施先生有狂放的一面,可那是一种内心的清高,一种不为外界所动的自我评判;他不会以此去争外在的待遇,更不会因为他人的评判的高下而忿忿不平。——他自己有底。所以他只止于自嘲,也乐于自嘲,因为在自嘲中,他已表达了对不合理的现象和思维的批评。他所看重的是这种自嘲的资格,而并非出全集的资格。
此事当然怪我,因我在谈话时说得不清楚。可谈话刊出后,有几位年轻朋友不觉得这两句话里存在什么区别,这就使我意识到,对施先生的这种精神实质,实在还有阐发的必要。
现在,当我写完这几句文章的时候,我真正发现,这种清高和狂傲的不同,正显示了一种大文化人的境界。时到如今,狂傲者比比皆是了,清高者则日渐稀少,争名争利者日见其多,能平静自嘲者则几成罕物,这就更显出了施先生的可贵。
(写于二〇〇三年末)
9、“枕流漱石”亦可通
从《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读到薛理勇先生《沪西的“枕流公寓”》一文,颇见情趣。文中引《世说新语·排调》中“孙子荆”一节,说“枕流漱石”本应是“枕石漱流”。记得前几年也曾在晚报上读到短文,说人名中常有“漱石”者(如今人有饶漱石等),其实是跟着古人弄错了,应是“漱流”或“枕石”云。《世说新语》中确有王武子的反问:“流可枕,石可漱乎?”其实,只要转换一下主语,当真是“流可枕,石可漱”的。枕流,不是指人在枕流,而是水中的石头枕流,石在水中,枕流二字,可谓曲尽其妙。漱石,也不是人去漱石,是穿石之水过而漱之。所以,自“枕流漱石”一语出,从此便难以从口语中消除,自晋唐以降,正确无误的“枕石漱流”说的人少,不尽合理的“枕流漱石”用者益多——只因其将“水中石,石中水”的情景,描绘得太传神了。而孙子荆当初想要归隐,说自己将“漱石枕流”,也未必真是说错了,倘若理解为,他不想像现在这么生活下去,而想要到远离市嚣之处,当一块枕流之石,或当一湾漱石之水,以石“砺齿”,以水“洗耳”,恐怕也是说得通的。只是听者王武子较为拘泥,觉得他说错了;而记者刘义庆也只想到欣赏他的急对,却不曾意识到他前面的话其实也已超越了常人的思维。
(写于二〇〇五年初春)
10、《读书》文风之我见
在二〇〇七年的下半年,由《读书》杂志换帅一事,引发了关于《读书》文风问题的争论,许多报刊都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对近十年来的《读书》,黄裳、舒芜、范用、朱正、何兆武、沈昌文、陈四益等,都提出了批评。好多年前,我还曾亲耳听到过柯灵、冯亦代等老先生的相似的批评。虽然我至今认为《读书》仍是中国最重要的杂志,这一地位并未因文风而动摇,但我对它后来的文风演变,也是颇为不满的。本来,这本杂志创刊之初,一是领思想界风气之先,二是以其美文着称。但十年前,自从换了年轻的主编后,选题上逐渐加重了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探讨,文章上专业论文的成分日益加重,专业术语多起来了,叫嚷“看不懂”的读者也多起来了。而趣味性、文人气,被编者看成是与学术性不易相容的东西,被逐步淘汰,老一辈文化人的隽永的美文也明显减少了。面对批评,辩之者称,进入九十年代,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和世界性的问题推到面前,它们不同于那些文艺问题,它们本来就是迫切的、艰深的,怎能要求他们再像过去那样去做好看的文章?
于是,我想到了“五四”以后的那几代学人和他们的文章论着,他们又何尝不是面对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种种迫切的难题?他们的研究,也深入到了大量艰深的学术领域,其中也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但他们的文章,仍能写得一清如水。现在随手即可举出的,就有:
胡适与冯友兰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
吕澂关于印度与中国佛学源流的梳理;
赵紫宸的基督教研究;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古建筑学研究;
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理论;
顾颉刚、江绍原与钟敬文的民俗学;
费孝通的社会学与人类学;
贾祖璋的生物学;
陈原的地理学;
自赵元任到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
知堂以至舒芜的妇女问题研究;
顾准、孙冶方的经济问题研究;
马寅初的经济学与人口理论;
……
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这都不局限于文学艺术,但这些作者无一不有“文人气”,他们的文章也无一不具真性情,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自如地运用“谈话风”,把学术文章写得一清如水——事实上,他们都是“文章家”,他们的文章都能当作散文读。
这样看来,新一代中的不少学人,之所以不能写出像前辈那样的美文,主要还是未能充分认识“五四”以后中国文章优美可贵的新传统。他们多为留洋的博士(其实老一辈学人中也不乏西方名校博士),他们所学的是国外学院派论文的论证方式,但他们“入乎其内”,却未能像第一代学人那样“出乎其外”,在面对中国大众,面对像《读书》那样的非专业的杂志时,他们还是只能以行业内的方式说话,这就不能不留下遗憾。
(写于二〇〇七年冬)
11、顾彬的棒喝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成了二〇〇七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当年三月之初,因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邀请,我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一起,与专程赶来的顾彬先生做过一个“三人谈”。因为是面对面的交谈,使我对顾彬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我发现,他对中国文学确是热爱,但这与他对自己个人的事业的热爱是休戚相关的。他对媒体(包括中西方各媒体)的关注度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敏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因为翻译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而成为西方媒介追逐的对象;但近年来,他在西方说话没人注意了,翻译或评论中国文学作品也很少有人过目,他感到了无可忍受的寂寞。我在对话时分明感到了他内心的焦躁,也很能领会他对于八十年代“过去的好时光”的无限留恋。
事实上,尽管顾彬用的是“全盘否定”的口气,但有些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甚至可说是一针见血的。比如,他批评中国作家:“你们过去(指“新时期”以前)听领导的话,现在听市场的话,你们自己呢?自己在哪里?”又比如,他看不惯中国作家的高产,看不惯当代作品语言的粗糙和内涵的苍白:“你们三个月就可以写一个长篇,一年可以出好几本书;而一个德国作家,一天最多写一页,再加上修改,一本三百页的书,至少要写三年。”还有,他认为,版税高,获得巨量财富,未必是一个作家的光荣,在德国,出一本书是一件大事,好作品带来的荣誉决不是高额的版税所能相提并论的。——我以为,这些话,值得每个中国作家深思。
当然,我并不同意他的“全盘否定”。由于他一再以鲁迅为例,我特意指出,即使在鲁迅时代,能与鲁迅相比肩的作家,其实也是并不多的。他首肯,但强调:“可毕竟还是有。”于是我说,在当代作家中,能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语言的个性化和文学性上极为用力的作家,也还是有的。我举出了我心目中的作家和作品,在场的同济师生和许多校外德国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顾彬后来也承认,他的说法有片面性,但他说:“必须有人先提出一个文本,你们才可以补充,纠正。我就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人。”此外,我还指出,正像俄罗斯文学有普希金传统和果戈理传统,中国文学也有鲁迅传统和周作人传统,顾彬先生现在只注意到了鲁迅传统;另外,中国的真正的纯文学主要是诗与散文,不同于西方文学主要是小说和戏剧,顾彬不明白“中国的思想在哪里”,这与他没有更多注意中国那些较高层次的、出于大家手笔的散文、随笔有关。顾彬对此未多置词,虽说他用德文写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我想,这可能已涉及到他的盲区了。
当我们开始熟悉以后,顾彬皱着眉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你们都不肯干苦活,让我这样的老头子写。我是外行。”我知道那最后四个字不是他的真心话,但我忽然觉得他很可爱,就笑说:“你是劳动模范,向你学习。”他不无得意地点头道:“可以这样说。”这是后话,此处略去不表。
陈思和在发言时,指出八十年代的创作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关注,与那些作品触及了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有关,那时文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而现在的文学已不存在这一功能。这使我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美学家李泽厚说过的话:“文学如果脱离社会,过于自我,一味向纯艺术发展,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走向衰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也许与顾彬及李泽厚先生有某种共识,那就是:至少有一部分文学,应深刻地、锲而不舍地关注当下的重大社会问题。
当然,已经走过的路不能也不应白走。近二十年来作家们的种种文学探索,决不会是没价值的。回头去看当年的和更早些的“问题小说”,不难发现,在国难当头,或拨乱反正之初,作家有满腔的的愤怒与激情,急切而不能已于言,问题意识往往强过文学情怀,这就难免出现“思想大于形象”的倾向;而一旦以问题意识作为文学的第一标准,又易于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所以,近二十年来的文学探索,不妨看作对于过去教训的一种反拨。今天的许多作家已经明白,现在的文学,已不可能担当解决社会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的重任——但难以担当并不是不要关注,即使只为着文学的自救,也需要真诚而深刻的问题意识。
是的,真正的文学不能脱离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它不能只是躲在象牙塔里自梳羽毛;但它的关注点又不只是现实问题的提出或解决,它要透过现实以感悟更为旷远幽深的人性——它不能跨过(或远离)现实,而要在表现现实的同时实现文学的超越。这是当今中国文学最需关注的大题目。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得感谢顾彬先生的棒喝。
(写于二〇〇八年初)
12、我与《解读周作人》
要说走上文坛的时间,我大概不算太短了。最近有一位当代文学史家,在一本专着中列出了我早年的两篇半小说(其中一篇与人合作)的题目,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的朋友谢泳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及了我当年写过《女采购员》的事。而我自己,的确很少谈起这些作品,这不仅因为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大成问题,严格地说,它们还真算不上是自己的作品。那时个人被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框架内,从构思到落笔,都是在一层层的帮助和把关下进行的。虽然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一点独创性,甚至留下一点点真生命,但实在微乎其微。
进入新时期后,我在《小说界》、《文汇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中短篇,也曾出版过一本小长篇,但都不成气候。当时小说创作日新月异,新起的作者个个呼风唤雨,令我十分佩服。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赶不上了。与此同时,我在评论上的特点(如果真有的话)开始显露出来,那就是:因为有过很投入的创作实践,略能体会作家的甘苦、成败和用心;因为对中外古今各类作品都有浓厚兴趣,有一定的阅读量;二者相加,便偏重于鉴赏的批评,以艺术分析为根柢,爱从审美中发现或提出问题。这样,我的写作重点就由创作慢慢(很不自觉,也很不情愿地)转向了批评。我与友人合写过一部论着《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印数高达十几万,曾得到许多批评界师友的肯定。但我觉得,还是不成气候。
到底什么是“气候”呢?说实在话,我倒不在乎外界的评判,也不过于关注名气大小,但我觉得,一定要写出自己的东西,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创见,而且要能真正推动某一方面的创作或研究(哪怕只是一点点)。从七十年代到整个八十年代,从创作到批评,我出了五六本书,发表了大约一百万字的作品,有的文章被选入一些重要的选本,当时学术地位很高的《文学评论》也登载了我的长篇论文……但所有这一切,我认为,都还是在作准备——从最初发表作品到那时,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代气氛有了明显的改变,许多作家、评论家都想静下心来,写一点更为稳定,更为深沉,更为独立的东西了。我也在这时下了决心,要把酝酿了好多年的两本学术性的专着写出来。一本是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即后来出版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另一本是关于现代文学的,即《解读周作人》。可以说,这是我很长一个时期来,最感兴趣的两个题目。写这两本书,把我的创作体验、阅读经验、理论思考,以及对文学的挚爱之情,全都调动起来了。两部稿子,写了两三年,真正动笔的日子,大概各在半年左右。当然我还要上班,主要用的是业余时间。但我的心是完全浸在书稿的进程中的,有时写到晚上两点钟,因为兴奋难抑,还会到外面去走一大圈。我真正体会到,原来,批评与研究竟和创作一样,也需要灵感,需要激情,需要调动生活和思想的积累,也会有许多潜意识的推动,会“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总之,那也是一种生命涌动的过程,一切创作的乐趣,它全都有——至少写这两部书时,我感到确是如此。
先写完的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而先出版的是《解读周作人》。如果我现在这点小名也能算“名”的话,那这本《解读周作人》,也许可算是我的“成名作”。
一九九四年八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解读周作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很快,从各地报刊上陆续看到了近三十篇书评;直到近年,还常在网上读到年轻朋友有关此书的讨论,论者大多不相识。张中行、谷林、黄裳、锺叔河、黄宗江、冯亦代、金性尧、钱理群、倪墨炎、止庵、黄开发等知堂散文的爱好者和研究者,都对我有过热情的鼓励。范培松先生在其《中国散文批评史》中,将这本专论放入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舒芜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的书评《真赏尚存,斯文未坠》,影响则更大。此书当时仅印三千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我的十几种小书中,它一直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十余年来索书者不断,其中有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专家,更有急需此书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我的存书越来越少,当我实在无能为力时,只好请他们到图书馆去复印。这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书的印数和影响,有时并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印了十几万册的书,其影响远不能和这本只印过三千册的书相比。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好在,在初版十三四年之后,这本小书终于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我很珍惜这一机会,将书稿修葺一过,并增补了四篇附文:《知堂的回忆文》、《梦一般的记忆》(谈知堂译作《如梦记》)、《乐感文化、俗世情怀与希腊精神》(周作人与张爱玲、周作人与李泽厚的比较研究)和《〈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其中最末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是专为这次再版补写的,此前从未发表过。有了这些附文,我对知堂散文及思想、艺术的探讨,也许会比较地趋于完整吧。
(写于二〇〇七年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