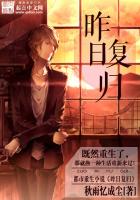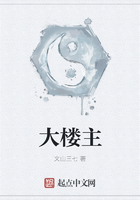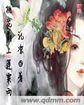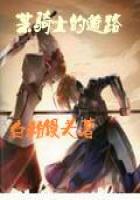人文学者可以培养出世界级物理学家,世界级物理学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由来已久。对学生过早地实行专才教育,很容易把他们培养成会说话的奴隶、不会思考的机器。这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国家的不幸。我过去以为,这是内地教育的一大失误,最近读《吴大猷文录》(《大科学家文丛》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看到这个问题在台湾也出现过,只是由于吴大猷等人及时发现并全力纠正,才没有酿成大错。
吴大猷是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他在海外工作多年,于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话对于那些把海外学者看得比本土学者更吃香、把自然科学家的意见看得比人文学者更重要的人来说,也许有较大的说服力。
吴大猷出身于广东番禺的一个书香世家。他幼年失怙,十几岁随伯父去天津求学,二十二岁毕业于南开大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在老一代物理学家饶毓泰和叶企孙推荐下,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马仕骏、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在许多场合谈到吴先生对他们的影响,一九五七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恩师、致谢。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大猷长期旅居海外,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后期,他才定居台湾,这也是大陆同胞对他不大熟悉的缘故。回到台湾以后,他看到岛内大学的学科设置越来越细,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窄,而人们对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却趋之若鹜,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抢得先机,出人头地。这使他深感忧虑。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大声疾呼,希望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一九七六年六月,他以《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为题,在《民族晚报》发表文章说:科学的要义是追求真理,科学的内容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智慧,“是‘知识和智慧’不可分的一体。片断个别的知识,如缺乏了各种知识的融会关系,则不构成科学”。可见对于任何人来说,假如他受的教育太狭窄太专门,就只能掌握一些“片断个别的知识”,而不会通过了解科学的全貌来增长智慧。这种人很可能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书簏。
针对人们过分看重实用的倾向,他告诉人们,科学家投身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都来源于纯粹的求知,而不是为了实用。另外,针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已经存在的鸿沟,他提出三点意见:第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有一个人文与科学合一的文明”;第二,在科学界与非科学界之间,必须沟通思想经常交流;第三,要达到这种沟通与交流,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
当时的台湾社会,也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潮所笼罩,许多人上大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面对这种倾向,吴大猷告诫大家:“教育的目的,不只限于知识的传授,尤其是高等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思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吴先生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是将人文学与科学间的鸿沟盖接起来”,这种“盖接”,不是一种表面的点缀,也不是“在文学院加一二科学课程,在理学院加一二人文课程”,而是要在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上进行重大改革。拿吴先生的这个观点来衡量,近年来内地大学的“文理沟通”,恐怕还是所谓表面点缀,算不上一种全面“盖接”。因为这种文理沟通,还局限在“提高学生素质”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教育学生思考”的高度。前者的立意是为我所用,后者的出发点才是为人本身。
一九八二年,吴大猷以《科学、技术、人文学》为题,在《民生报》分三次刊登长文,进一步论述三者的关系。他说,科学和人文学是人类文明的两个方面。就科学而言,由于“高度专门化”和大量使用深奥的观念和术语,它已经“成为极少数专家的私有花园”。这样一来,连那些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也很难对科学有个基本了解,即使是受过专门教育的人,对其他专业也是隔行如隔山,根本不知道人家说啥干啥。于是,几乎所有的专业工作者都处于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这充分说明人类文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个人的生命体验,都非常有害。他强调,人类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沟通起来的时代,而这种沟通的任务,只能由教育来承担。不难看出,近年来有些人一再强调所谓专业教育、技术教育的重要性,显然是要重复人家走过的弯路。
在这篇文章中,吴大猷还对纯粹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作了比较。他说如果把科学比作一棵树,那么纯粹科学就是树根,应用科学就是枝叶,技术科学就是花果。假如只想着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那就好像不顾树根枯朽、只想着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一样,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纯粹科学的探索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由的环境,这种环境应该由大学和学术性研究机构提供;二是要有一批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博学深思、颇具想象力的学者和青年。这两个条件比大楼、仪器、图书、经费等物质条件更重要,是造成学术研究气氛的关键。这与梅贻琦先生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观点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吴大猷先生更重视学生,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文章结束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没有纯粹科学的国家……将永是落后。”
一九八三年,《中国时报》以“人文与自然科学应如何均衡发展”为题,对吴大猷和******进行采访。他们二人是国际知名的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再加上当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失衡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对话。对话中,吴大猷进一步分析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的区别。他强调:研究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动机很单纯,只是为了求知,根本不考虑实用,也不追求商业性利益;但后者却不是这样。应用科学是利用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对具体的问题或目标进行探讨;技术科学则是把应用科学得到的原理、方法用在更广泛的实际问题上。按理说这本来是老生常谈,为什么吴大猷还要反复强调呢?这说明当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甚嚣尘上的时候,人们反而在常识问题上容易出错。正因为如此,吴大猷批评台湾当局“只重视下游的技术,忽略上游基础科学”,在经费分配上也总是应用科学大于纯粹科学、自然科学大于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紧接着吴先生又谈到通才教育。他介绍说,哈佛大学在一九四六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使没有学过科学的人也能对科学有个基本的了解;二是要让人人都知道,不断研究创新是美国科学精神之所在。这个委员会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零零碎碎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要使人们对科学有基本的了解,最好的办法是借助于通才教育。吴大猷说:“通才教育可使学生未来发展时,能有一种宽广的基础,使得念科学的人,也能了解、欣赏人文知识。同样的,念人文的人,如果对科学有清楚的了解,将来如果进入政府机构,在从事政府决定时,就可避免发生偏差。”
这次采访中,******也谈到在台湾和世界各地出现的一些情况,与如今大陆面临的困境极其相似。他说:“我国传统教育的毛病是偏重于通才、不重专业。现在的情形恰好相反。由于社会趋于专业化,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职业才有保障。因此,哪些专长易于找到职业,大家便一拥而上。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台湾,美国、苏联等地,亦复如此。例如,目前各国都有许多男女,纷纷学医、法律与电脑。这纯粹是一种以职业为主导的教育取向。这种取向,有予以自觉改变的必要。”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取向呢?余先生的意见是:无论你学什么专业,都应该对专业以外的学科具备必要的常识。只有这样,你“才有资格做一个完整的现代人,并具备综合判断的能力”。他认为,这些问题涉及考试与教育制度,要彻底解决虽然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也应该作些努力和尝试,“否则就会产生一种流弊,亦即造成一种所谓‘对很多事情知道得很少,对很少事情知道得很多’的‘专家’。这种专家只有很狭隘的专业或纯技术观点,却无法妥善处理专业以外的重要问题,甚至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最让人感动和钦佩的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吴大猷总是站在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反复强调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他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类陷入一个贪婪的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其中最明显的是生态环境破坏和犯罪率不断增高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靠人文科学来发展人类的智慧,控制并克服人类的贪欲。
他主张让人文与科技“融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一个文化,着重的是需要改变人类的教育,使习科技的不成为‘机器人’,习人文的了解‘科技’的性质”。对于这个问题,******先生补充说,企图用科技来解决科技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这对于那些总以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应该有醍醐灌顶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吴大猷已经年近七旬,但仍然担任台湾科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这一年年底,他在台湾“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所谓科学精神,乃是科学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尽管它原本并不是为了实用,但它却是一切技术的“根”。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发展工业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引进”的模仿阶段,而应该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与此同时,他认为激发青年学生对科学的兴趣,是中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大学联招”(类似大陆高考)存在的问题,使中学教育出现三大偏差:一是课程设置太偏,二是文理分科太早,三是学业负担太重。这就是使大多数学生在学习中只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不能理解知识的奥秘和科学的真谛,从而对科学丧失兴趣。为了纠正这些偏差,吴大猷成立了“人文社会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一方面主持高中教材改革,一方面组织教师培训,进一步提倡通才教育。
一九八七年,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吴大猷先生在接受《台大研讯》采访时又说:“三十年前我来台湾时学生的求学志向都很高,很多有志于基础科学,求学的动机也比较单纯,现在进大学的竞争依旧很激烈,但是很多学生对学术兴趣并不高,只在图个资格。”
吴大猷所说的三十年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他回台湾讲学的时候。当时他在台湾大学讲学四个月,可谓座无虚席,盛况无前。他觉得这里的学生比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学生还要好。吴大猷回台湾讲学是胡适促成的,后来胡在信中对吴说:“你此次在台教学四个月,最辛苦,最负责任,所以最有成绩。所谓‘成绩’,不在班上那几十个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在你所引起的青年学人的求知向学的热诚……”(《胡适书信集》第一三一二页)这些话胡适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讲学之后,吴大猷还向台湾当局提出一个发展科学的全面计划,可惜因********日趋紧张,这个计划曾一度中断。
胡适与吴大猷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他们的交往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是一九四七年,胡适曾给白崇禧、陈诚二人去信,提议在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把这方面的第一流物理学家集中起来,“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在这封信中,胡适列出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人,认为这九个人“可谓全国之选”。这件事虽因内战未能实现,但也可以看出吴大猷在学界的地位。当时吴大猷正在国外,他代表胡适与正在英国的“张宗燧谈数次,使其决来北大”。(《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二八九~二九三页)张宗燧是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儿子,他回国后,不仅没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反而因为父亲在朝鲜战争期间被打成美国特务而受到牵连,并终于在“****”中自杀身亡,为历史留下沉痛的一页。
二是一九六二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当时担任院长的胡适因为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等四位海外院士都能回台湾出席会议,心里非常高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胡适在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八九八~三八九九页)出人意料的是,也许是过于兴奋吧,胡适话音刚落,就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因此这段话也就成了胡适的临终遗言。它告诉人们:在我国,人文学者可以培养出世界级物理学家,世界级物理学家又大力提倡人文教育,这其实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遗憾的是,随着胡适、吴大猷等人的离去,这个传统被中断了。因此尽快恢复通才教育的传统,才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最好出路。
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