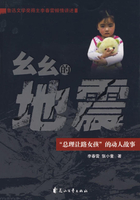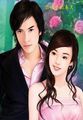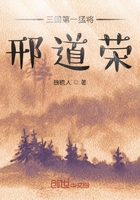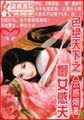对于一八九八年发动保卫德雷弗斯上尉运动的那一群人而言,“知识分子”一词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富有强烈道德动力的作家,用通俗的语言向一批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群体讲述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一九八七年,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敲响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和这个阶层的丧钟。该书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左拉当年的《我控诉》,不过左拉控诉的是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政权,而雅各比则是声讨脱离现实的当代学术和当代学者。雅各比认为:社会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目前的美国知识分子,多半以私人身份露面,他们的书只是为同事写的,圈外人很难读懂;他们的批评文章,受界限分明的学科所制约。一个大学教授的“社会性”或“公共性”很难超出大学校园。主宰知识生活的是一批学术专门家,而不是一批深知世故的通才。对此,雅各比哀叹道:“激进的社会学家成百上千,就是没有一个威尔逊。如果西部边疆的开拓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告一段落的,文化边疆的开拓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结束的。”
知识分子的历史真的结束了吗?
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是谁呢?
学术与意识形态
学术与意识形态的纠结,在东西文明诞生之初便是一大问题。东西方不同的处理方式,决定了双方迥异的知识谱系。
以希腊文明为例,希腊哲学显然不是纯粹的哲学。哲学家的目的是:一、了解人及其宇宙的本质;二、确定人与宇宙的关系;三、为人类寻求明智而美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希腊哲学发展出四大领域: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希腊人的伟大天才在于,他们能够认识到安定和进步可并存。在他们看来,一个合理的、协调的、稳定的、而且相对自由的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完全可能同时发展。正是这种毫无偏激和具有社会责任感前提下的个人自由精神,表明了希腊人明确的现代性。
我认为,希腊文化的精髓在于学术与意识形态互相尊重。学术不必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刻意干涉学术自由。学术的自由,是广泛的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伯利克里曾经在公民大会上讲演道:“我们享有的自由适用于日常生活,我们并不互相猜忌,倘若我们的邻居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并不责备他……雅典市民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并不忽视公众事务。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国家的人不单并非无害,而且无用;虽然只有很少人能制定政策,但我们全部可以判断政策的优劣。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是政治行动中的阻力,而是达到明智行为的必要措施。”这段话切不可等闲视之,它所阐述的原则,完全可以作西方政治史和学术史的基石。
学术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无自由则无学术。中国似乎只有意识形态史,而无学术史。儒学自诞生之初便被“国家化”,取得独尊的地位后,自身的思想活力便完全丧失了。中国的学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暴露出它作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知识形态的全部弱点。在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天人合一”,这种“合一”乃建立在对自然顺应的基础上,因而自然主要不是作为人类探索、认识和作用的对象,而是顺从和依赖的对象。这种“天人合一”与当代环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人却错误地将它当作一块批判西方、拯救世界“新大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生命境界。相反,中国文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到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厘定上,从孔孟、老庄到魏晋玄学,到佛教禅宗,到陆王心学,是一条从本心获取欢乐的重要线索,追求一种超稳定感的人生哲学。这样,中国传统学术缺乏与现代文明接触的“科学理性”,囿于无所不在的“伦理理性”,最终沦为官方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奴婢。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没有根本动摇“六经”的神圣地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六经完全抛在一边呢?
过去:否定或怀念
我想往八十年代,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未班车。最近,肖全出版了他的一本摄影集《我们这代人》,包括了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的文化精英(当然,更优秀的若干人士可能无法还处于露面的状态),我能从照片上捕捉到他们昔日飞扬的神采。
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份,只有“五四”一代人能与他们并肩而立。他们有三个宝贵的特点:一是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二是不屈不挠地参予历史的热情,三是对“知识分子”身分的空前自觉,他们希望在短暂的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知识分子数百年的历史使命。于是,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相反的命题,并置于同一时代的呼号之中。
我拒绝那些嘲讽、指责、否定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的声音。九十年代,充满恶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是一批冒充“先知”的“后知”,通过蔑视别人所承担的苦难来示自己的高明,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太高明。一边享受着前人用鲜血换来的财富,一边指责前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妥,这未免太无耻了。把无耻当新潮,把赏玩当优雅,把怯懦当聪明,确实是九十年代学术界的新景观。
新潮学者们很喜欢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杰姆逊,那么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杰姆逊在《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惟一主义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新潮派吮吸着西方的乳汁,却恶毒地责骂替他们肩起闸门、放他们跑到光明里去的前辈。他们把过去的事件“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其目的不过是替自己在历史上“叙述”出一个“崇高人位置”,而自身实在不那么“崇高”,便只好用“打倒崇高”来证明自己的“崇高”了。
我们薄情寡恩地对待十年前的先行者们,美国知识界却对本世纪初的纽约文化人悠然神往,充满了思故和怀旧的情感。
二十世纪三四十和五十年代,在纽约有一批围绕在《党派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如菲利普·拉夫、爱蒙德·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艾尔弗莱德·卡津、欧文、和丹尼尔·贝尔,他们形成了纽约知识分子的核心,这批人以桀骜不驯著称,他们的文体为“自由作家的锐气、孤高自傲和穷追猛打”的结合。
《党派评论》重视思想观念,重视在发行量少但读者层次高的刊物间发起论争,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称《党派评论》为“美国知识界的喉舌”。他们喜欢写散文;虽然题材广泛,要求偏高,但没有晦涩的术语。这些文章是专家专心致志写的,却又有反对专门家的心态表露,评文论政,得心应手,文未点题,得出道义上的结论。他们似乎在永无休止地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美国面临的一系列政治挑战,引起的共鸣,反过来又给这些作家以一种远为广泛的影响。他们是一批重视其冷眼旁观的地位的反对派人物,对常规的智慧总要表示不同意见。卡津指出:“即使内心同意也要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跟着主流文化走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豪说:“异化是我们引以自豪的自我评价。”
那些能够称之为“金本位”的著作,即使绝版了,但是受到尊重,如威尔逊的《开往芬兰站》、特里林的《自由的想象力》、卡津的《故国情怀》、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扶夫的《形象与观念》。他们提出的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以此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他们成为辉煌的回忆,被多得不可胜数的传记和回忆录赋予了某种神圣的色彩。
否定与回忆,两种不同的面对过去的姿态,揭示着两种不同的现实。
知识积累与公共参与
美国学者罗伯特·S·博恩顿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一篇论文《新一代知识分子》,向我们勾勒出美国知识界的另一幅图景:在知识分子纷纷退居学者讲席的时候,美国出现了一批继承纽约文化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有趣的是,他们的主体由黑人和犹太裔组成。这群新一代知识分子中,有诺贝尔奖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普利策奖得主戴维·利弗林·刘易斯、散文作家斯坦利·克劳奇,以及威尔逊、盖茨、胡克斯、卢里、贝克等,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群落。他们认为,在吸毒成灾,经济萧条、犯罪猖獗的中心城市里痛苦呻吟的“那些人”,是“自己人”,知识分子不能丢弃他们。
这个道理已经超越政治和政策,“和我们当中最穷困的人打交道是必要的,这是一种道义的必要性。如果我们美国人经受不了这个考验,我们就辜负了作为”山顶城市“的自我形象,就当不了全世界自由和希望的灯塔。”
我敬佩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知识的欲望与对精神和思想自由的欲望是同构的。知识的积累,同时也是自由的积累;文化的耕耘,最终开出了民主的鲜花。
反观中国,千年以降,“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倒也说得头头是道,但是知识积累越来越多,不仅没有打开一眼自由的甘泉,反而成为“自由之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汗牛充栋,却成了堵塞泉眼的大磨盘。问题出在哪里呢?
中国的知识倒是一点一滴地积累的,中国的士人倒是热心参加公众事务的。但是,积累知识的过程中丧失了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追求,参与现实的过程中丧失了对自身人格独立的捍卫。于是,知识便沦为既非形而上,也非形而下的“伪学术”。殷海光先生说得好:“自古以来儒门最大的弊端是与现实权力粘合。任何教条,即令再好,与现实权力粘合久了,便容易被权力压变了形,或者失了原味。儒门严于阶级上下之分;讲究‘定于一尊’;主张‘尊王攘夷’,掀起浓厚的权威主义的气氛。这些要素无不合于君主的胃口,很容易用作治理万民的建构框架。所以,儒宗终于战胜了佛老,取得了统治的地位。”殷海光先生打蛇打准了七寸,中国学术的病根就在此处。
找到了病源,顺流而下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了。本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本该具有的超越文化反省态度,一直被“文化救国”、“思想革命”等实质性的运作所遮蔽。新创或引入的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橘生淮北为枳,依然笼罩在儒学支离破碎的神光圈里。因此,一种普通性、持久性价值关怀的文化规范体系,迟迟未能成形。到了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这一“缺席”到了令人焦灼和绝望的程度,没有人回答得了“知识分子何为?”的问题。
个人在参与公共生活的同时,又必须保持完整的“个人性”。一旦“个人性”丧失,参与便毫无意义,个人便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因此,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强调了他的三个不可撼动的立场:第一,反对任何闭合的思想体系,即反对用存在于本身之外的某个可用理性解释的实在来解释生活和人本身;第二,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第三,强调试图在世界上做某事的个人所具有的自由和责任。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道德规范,人必须完全用自己对上帝的信仰指导行动,而无须首先确保自己行动的正确性。
那么,在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该用什么来作为自己的“指南针”呢?
权力的怪圈
没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权力迷恋到了变态的地步。我将其概括为“奴隶的法官情结”。
中国的“圣人”比小脚女人还多。“圣人”不是民间承认的,而是朝廷册封的。既然朝廷可以册封,也可以一脚踢开,如“亚圣”孟子就被明太祖朱元璋请出圣庙,吃不成冷猪肉了。原因何在?因为孟夫子太善养“浩然之气”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是想造反吗?即便是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在“天子”们的眼里,也不过是个奴隶工头罢了。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在《上亲制日讲义序》中有板有眼地说:“联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每念厚风俗必先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化民成俗之药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近于唐虞三代文明之治也乎!”道出了其尊孔的秘密:用几块冷猪肉来换取天下太平,何乐而不为呢?
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却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圣人”,充当起“小民”的法官来。会吟几首歪诗,会凑几篇大赋,便有了决定别人命运的本钱,这是什么逻辑?我最讨厌那些声称处于当事人利益之外,能以普遍性口吻言谈、代表上天的律令,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的人物。例如不食人间烟火的新儒家诸大师,我只能敬而远之。他们自己人格分裂却死死抱着一元论的传统儒学不放——人性善理论、诚明内省的修养方法、天人合一的道德理想境界,全是扯淡。所谓“回归祖辈的文化”或“复兴先秦儒学”,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者的梦呓。
我觉得福柯的理论似乎更适合于中国——这是一个灵魂被权力压扁了的民族。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当奴隶当到了麻木的地步。其实,真理哪能外在于权力呢?福柯说:“哲学的问题是有关我们是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哲学完全是政治的和历史的。它是内在于历史的政治,是同政治不分隔的历史。”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我们也无法求助于客观规律,无法求助于纯粹的主体性、也无法求助于完整的理论。我们有的是已使我们变成现今这个样子的文化实践。要想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只能搞现实的历史。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去把真理从权力中解脱出来。在人文科学中,所有这些企图似乎都仅能为我们社会中的监督和技术趋向提供催化剂能量。相反,应该去做的是使命名这种实用的诠释在权力范围内起不同的作用。
拥抱孤独
在一个什么都可以销售的彻底的社会,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否终结?看似绳索越来越松,知识阶层的独立性却一代不如一代。博恩顿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在为自己取得学术精英世界和主流传媒的中心地位时,难道放弃了社会知识分子传统的反对派立场吗?他们通过报刊专栏和电视访谈节目已经获得广泛承认,但是那种传媒像过眼烟云,他们是否会给后人留下十分充实的作品呢?他们是不是无意中把文化领域的原则斗争换取电视“夜谈”专题的露面机会呢?由于社会知识分子接触主流文化的机会更多,他们是否已变成更重要的思想家了?还是只不过更有名气了?
这是一个权力泛化的时代。权力不仅仅归结于政府、政党,而渗透到每座建筑物的根基里。一部电视肥皂剧、一段广播歌曲、一张新闻报纸、一本消闲杂志、一个街头广告牌,全都是权力之网中的一部分。在这样背景下,知识分子必须更加警觉地对待权力的任何侵犯——已经变得温情脉脉的侵犯。
卡津是第二代俄罗斯犹太移民,与美国本土知识分子相比,他充分地享受了犹太主义中的文化相关性和知识边缘性,“它对我来说似乎有一种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拟的反馈作用。”卡津认为,犹太人生活的局外性是“问题的核心”。他写道:“我拥抱孤独……我把孤独当作创造未来的呼唤。”
孤独是出自本心的情绪,以孤独的心态去参与公众生活,这是知识分子再生的必由之路。丹尼尔·贝尔十四岁就在街头散发政治传单,这丝毫没有降低他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的学术水准。因为他的内心是孤独的。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孤独应该是自由的同义词。美国的大众文化从来不会听知识分子的话。梅尔维尔、福克纳、享利·亚当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威廉·詹姆斯、杜威和埃默森都曾多年在历史垃圾箱里苦熬,最后才被重新发现,重新被列为经典作家——也许最后又会被遗忘。如果他们能持久占据舞台,那是因为他们在变化多端的复杂局面中提出了未来知识分子还须思考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因为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包含着需要终生孜孜不倦运用想象思维来解开的矛盾和填补的空白。
知识分子是不会终结的。我可以对所有的问题都持悲观的态度,但惟独对这个问题保持仅有的一丁点的乐观。丹尼尔·贝尔写道,“学者在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找到自己的位胃,然后再一块一块地添砖加瓦,犹如在绘制一幅复杂的镶嵌画。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经验,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自己的特权和无权出发,并用这些敏锐的感受来审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