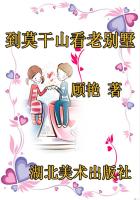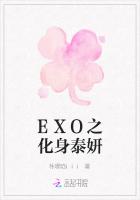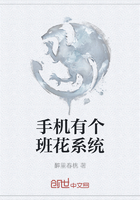曼弗雷多·塔夫里
从皮拉内西(Piranesi)的作品开始,来对先锋派和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这无疑有点挑衅意味。然而,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针对皮拉内西的《监狱组画》(Carceri)*所做的非同寻常的研究,让我们有机会来确证我们的论文,从而去平息那些怀疑者的困惑。皮拉内西和苏维埃电影导演之间表现出的是一种直接的关系;这里,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检验这一关系的某些突出特点。
1939年4月,爱森斯坦致信杰·雷伊达(Jay Leyda)道:“我预计完成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埃尔·格列柯与电影》(El Greco y e Cinema!)……估计大概26000字(!)都用来说明,在过去的西班牙大师的艺术中,究竟存在着多少电影的东西!……这真是有趣!(C’est Piquant!)”但事实证明,这篇文章完成得相当艰难,因为在1941年8月,这位导演再次致信杰·雷伊达道:“我终于要结束这篇关于埃尔·格列柯的文章了。与此同时,我正在将我关于格里菲斯(Griffth)和不同艺术中的蒙太奇历史的一篇长文翻译成英语。我还有可能再写一篇研究艺术史中的特写(close-up)理念的论文。”
爱森斯坦对艺术史的好奇,当然不算什么新鲜事。他在不断地为其电影诗学寻找历史合法性的过程中,也在对艺术史进行着探索。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坚持认为,新电影语言的先驱尤其应包括格列柯和皮拉内西这样的人。1尽管这二人的作品所包含的母题很容易就能同蒙太奇理论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感兴趣的却是爱森斯坦在分析格列柯的绘画,或拆解、重组皮拉内西的《监狱组画》时所运用的操作方式。
本章附录的那篇爱森斯坦论皮拉内西的文章,实际上和前文所引的写给杰·雷伊达的信有关,该信出自俄国出版的爱森斯坦作品全集第3卷。这两篇文章通过一种特殊的批判式分析技巧联系起来,该技巧的基础,即爱森斯坦所说的“曝光”(explosion)或“迷狂的变形”(ecstatic transfguration)。
换句话说,爱森斯坦集中分析的两个作品—格列柯的《托莱多城的风景和平面图》(View and Plan of the City of Toledo)(1604-1614),以及皮拉内西的《黑监狱》(Carcere Oscura)——都“动了起来(put into motion)”:它们都剧烈地作出反应,这是其内在形式张力被完美曝光的结果。后面我们将追溯这一独特的批判式操作(critical operation)的特殊过程。但我们首先必须指出,这种分析方式和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并非没有联系。实际上,爱森斯坦自己曾宣称,“蒙太奇是镜头曝光(explosion of the shot)的阶段”;而且,在《爱森斯坦课程》(Lessons with Eisenstein)中他还说,“当镜头中的张力达到极致而不能再增加时,镜头就曝光,分裂成两个分离的蒙太奇片段。”
于是,对爱森斯坦来说,镜头和蒙太奇不能被当作相互分离的领域对立起来,而必须被看作是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它在“从数量到质量的辩证飞跃”中实现了自身。
在这一点上,人们会发现这种蒙太奇理论和某种文学理论之间具有一种密切关系。后者就是,泰恩雅诺夫(Tynjanov)在1924年以后所详细阐述的“文学作品其组成部分间的动态综合”(dynamic integration of its components)的统一性理论。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此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去观察,爱森斯坦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得格列柯的作品,且尤其是皮拉内西的作品,丧失了它们本来的自律性,把它们从隔绝状态中驱逐出来,从而成为理想系列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也即成为了一个电影片段(cinematic phrase)中的数个单一画面。
因此,通过皮拉内西这个特殊例子,来分析苏维埃导演的批判方法能为我们的认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从而阐明18世纪的蚀刻家同爱森斯坦这样的历史先锋派传人之间的奇特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这篇关于皮拉内西《监狱组画》的文章写于1946—1947年,在该导演去世前不久。)
显然,爱森斯坦认为,在整个《监狱组画》系列中,由彼此分离的作品片段(disconnected fragments)所构成的整体,属于一个连续镜头(sequence),这建立在“知性蒙太奇”(intellectual montage)的基础上,根据他自己的定义来说,也即建立在“并列冲突的知识动因上,它们一同出现”(juxtaposition-confict of intellectual stimuli which accompany each other)。
爱森斯坦对皮拉内西在《黑监狱》中所描绘的建筑元素强行曝光,这是对原蚀刻画的组合方式的残忍施暴。也就是说,爱森斯坦佯称,由意象及其对其批判式静观(contemplation)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某种地球之力(a telluric force),颠覆了皮拉内西《监狱组画》系列的所有作品,使它们活动起来,猛烈地煽动它们,将它们简化成等待全新重组的片段。在这样一种智力操作(mental operation)中,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一种源于俄国未来派所有经验的分析技术;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蚀刻画的元素,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具体化(reifcation):最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它们被压缩成一个没有句法结构的符号系统。
然而,不止如此。由于爱森斯坦在字面意义上激活了曝光,所以我们也面临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语义变形”(semantic distortion):皮拉内西那些物质性的构图元素经历了一次意义的改变,其中原因在于,原先将其绑缚在一起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剧变。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尤其对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而言,语义变形已经把恢复语言的原始功能—即纯粹的交流—当作了自身的主要功能。以同样的态度来看,爱森斯坦对皮拉内西的《监狱组画》所施与的暴力,可以被解释为试图让蚀刻画自身说话,超越通常归属于它的含义。换句话说,爱森斯坦对18世纪那个世界的涉足,似乎产生了这样一种环境,它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供连珠炮式的插科打诨的演员去胡乱颠倒。这一环境类似于卓别林(Chaplin)的电影—这位苏维埃电影先锋的“大暴君”(Lord of Misrule)。但是,还是让我们检验那些通过解读爱森斯坦的文本而得来的主题,继续我们的分析吧。
首先我们发现,《黑监狱》各元素的曝光,用爱森斯坦自己的话来说,采取了消解(dissolution)的形式。这意味着爱森斯坦将元素自身解释成处于潜在运动中的形式,即使这种潜在运动被人为冻结了。因此,“迷狂的变形”技术加速了这一潜在运动,刺激它,将它从形式的阻力中释放了出来。
然而,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因为在18世纪的蚀刻画中,形式已经被认为是“消解的”(dissolved)了。爱森斯坦敏感地察觉到了《黑监狱》中,对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坚持是怎样和“表达方式的分裂”(fragmentation of the means of expression)平行而动的。吸引这位苏维埃导演注意的正是这一分裂。他通过自己虚构的“曝光”(imaginary“explosion”)所加速的,正好就是有机结构的相关法则同有机结构各形式元素的瓦解(disintegration)之间的冲突。
爱森斯坦在其分析的过程中,最终借用了一个结论性的模型。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让《黑监狱》“动起来”(setting in motion)的观念,在作品中唤醒“客体的反抗”(rebellion of the objects)、“符号的置换”(displacement of the signs)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最终的模型中找到根源。“符号的置换”是什克洛夫斯基的隐喻5.《黑监狱》同《监狱组画》第一版之间的比较,为爱森斯坦指出了方向,即将其虚构的曝光所释放的片段和剩余物(residues)聚集到一起。
换句话说,爱森斯坦在皮拉内西青年时期的蚀刻画中所感受到的,仅仅只是形式功能所具有的神秘的约束力(a hermetic bundle of formal functions),虽然这其中包含着皮拉内西成熟后那些更为实质化的改革的种子。爱森斯坦打算解开的正是这种束缚(bundle)。皮拉内西在《监狱随想组画》(Invenzioni capricciose di Carceri)和《监狱组画》第二版的构图中所采用的程序(procedure),爱森斯坦完全借用过来,并且以一种暴力且完全知性的态度,把它运用到对《黑监狱》的曝光之中。
爱森斯坦难道不也通过敏锐的批判性直觉,意识到了《随想组画》(Invenzioni capricciose)中,皮拉内西所消解的不仅仅是各自的形式,也是它们的“客体性(objectuality)”吗?(爱森斯坦也认为,更准确地说是,“客体被消解为物质性元素的再现”。)
因此,爱森斯坦从已经确认的结果出发,从《监狱组画》中开放的连续镜头(open sequence)中撷取出一个静态的电影画面(frame of flm),而这种静态的电影画面是由皮拉内西的《黑监狱》呈现给他的。或者可以说,皮拉内西的《黑监狱》来自于《监狱组画》中开放的连续镜头(open sequence)。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强迫理想的画面参与到《监狱组画》动态的、主题的连续性中。而这一连续性正是《监狱组画》的特点所在。于是,由曝光所激发的“迷狂的变形”就有了这第一层含义:随着它将1743年的蚀刻画和第一组《随想组画》之间的空间(empty space)填上的同时,它使《黑监狱》的潜在意义得到了增殖。就像对格列柯那幅画一样,爱森斯坦在《黑监狱》中,也运用了批判式操作。实际上,这一操作和那些同巴特(Barthes)或杜勃罗夫斯基(Doubrovsky)式的新批评(nouvelle critique)最终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是相类似的。在爱森斯坦看来,皮拉内西的作品是一种多层次化的素材,它需要人们对其形式成分进行分割和增殖的操作。
爱森斯坦将《黑监狱》中的静态含混(static ambiguity)称为“无害性”(inoffensiveness)。他将《黑监狱》的这一“无害性”解释为一种挑战。这样一来,针对它的批评就必须采取一种暴行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位俄国导演毫不犹豫地—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说法6—“剥离掉”皮拉内西蚀刻画的“所指”,“在作品的第一语言上”附加上了“第二种语言,也即,一个连贯的符号体系”。这一体系被引入进来,成为一种“受控的转变,服从于视觉环境;它必须按照已定的法则,来转变它所反映的一切对象,并一直这么走下去。”
巴特和杜勃罗夫斯基不承认他们的批评方式同形式主义传统有直接联系,7这个无关紧要。爱森斯坦和巴特的批评似乎都做不到这一点—通过深思熟虑来构成一种文本所具有的真正的增殖的含混性(multiplication of the ambiguities),且特别是这样一些含糊性,它内在于原始语言学素材的组织之中。所以,爱森斯坦在《黑监狱》中所探讨(explodes)的,是皮拉内西强加于形式结构和客体消解之上的伪平衡。爱森斯坦的迷狂的曝光所攻击的正是这种虚假的平衡(falsity of the equilibrium)。在这个被分析的作品中,对皮拉内西的批评倾向于揭露隐藏在作品中的有力的化合作用。这一批评的结果,就是再次遮蔽了将《黑监狱》同随后两版《监狱组画》区分开的中性空间。因此,爱森斯坦的解读所制造出的“语义的陌生化效果”,呈现出一种突发性的形式。但我们还须走得更远一些。通过使皮拉内西作品中潜在的变形法则(principles of the formal distortions)达到悖论的程度,爱森斯坦促使该蚀刻画的形式组织,对“形式反抗”(rebellion of the forms)这一共同行为所造成的压力作出反应。
于是,对作品的批评成为一种关于作品自身的操作。(The criticism of the work thus becomes an operation on the work itself)但是显然,只有当作品的语境和批评家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共鸣的时候,这才成为可能——在我们这个例子里,批评家特别着迷于动态地解读皮拉内西的形式组织方式。
因而我们不难看到,爱森斯坦关于《黑监狱》的批评中,有些东西极为类似于20世纪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他关于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断裂蒙太奇(discontinuous montage),普多夫金(Pudovkin)的史诗蒙太奇(epic montage),格里菲斯的平行表演技术(parallel action technique),以及像“字母表中无法改变位置的字母”一样的镜头理论(theory of the shot)所做的批评。8爱森斯坦在1929年写道:
镜头决不是蒙太奇的元素。
镜头是蒙太奇的细胞。
就像细胞在其分裂中形成另一种秩序的现象一样,有机体或胚胎,在镜头前辩证地跃过另一侧(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ialectical leap from the shot),就产生了蒙太奇。
那么,通过什么来表现蒙太奇,并继而表现它的细胞—镜头呢?
通过碰撞。通过相互对立的两个镜头的冲突。通过冲突。通过碰撞。
在我面前放着一张压皱的黄纸片。上面写着神秘的记号:“连接—P”和“碰撞—E”。
这真实地勾绘出了关于P(普多夫金)和E(我自己)之间关于蒙太奇问题的激烈较量。
然而,爱森斯坦走得更远,并且,在其理论研究的革新中,他逐渐将蒙太奇的形式当作意象的结构,将蒙太奇自身当作“客体的结构法则”。10“吸引力蒙太奇”(montage of attractions)所具有的有计划的间断性,以及一般而言历史先锋派—从未来主义到“古怪演员工厂”(FEKS,Factory of the Eccentric Actor)—所赖以建立的彻底让人震惊的论述,被爱森斯坦对于作品所做的完全结构上的考虑所取代,在此,基本上得到恢复的是文本的概念和价值。通过脑力劳动(intellectual work),爱森斯坦采纳了新民粹主义者(neopopulist)和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两者兼备的意识形态立场—它们随着苏维埃头两个五年计划的启动应运而生。对这一个人化意识形态立场的质疑,爱森斯坦的回应是,把先锋派和现实主义进行暧昧综合。(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及“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仅仅是恢复古典的建造法则,该法则为艺术品重建有机性—它是对于历史和世界的总体幻象。)
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感兴趣的是去弄清,20世纪的30-40年代,爱森斯坦试图将哪些先锋派实验保留下来,以作为最适合于他研究的东西。蒙太奇法则曾一直同刺激公众这一主题联系在一起。11但是,在苏联,1928年以后,公众的主题被迫摆脱掉自身所有的一般性,必然具备一种直接同新功能相挂钩的特殊性。处于转变中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被召唤起来在区域经济规划的范围内执行这一新功能。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所经历的危机,必然为1924-1930年间里意识形态具有的形式(物质的、具体的)所影响。我们一旦承认十月革命环境下的脑力劳动只是对“社会委托”(social mandate)的回应,就不可能忽略这种意识形态。
对爱森斯坦而言,公众的意识形态必须经过新具象主义(new representationalism)的过滤。早在1934年,他就承认他受惠于马戏场、音乐大厅、狐步舞、爵士、卓别林:这些东西也成为那些已被未来主义和“左派”表现主义用来建立美学刺激(aesthetic provocation)与公众之间全新和谐关系的基础。但之后不久,爱森斯坦自己注意到,在“小丑的彩衣”之下,(它“首先遍布在节目的所有结构中,最终进入整个生产方式”),甚至在19世纪的文化传统中都存在着更深的根源。他同样也谈到交叉剪接(cross-cutting)的方法:他所引用的例子绝非偶然地来自于《包法利夫人》中的一个场景。在该场景中,福楼拜(Flaubert)将演说家在楼下广场中的演讲,同艾玛(Emma)与鲁道尔夫(Rudolph)之间的对话交替进行。13在福楼拜的文章中,爱森斯坦看到:
(交缠的)两条线索,主题相同,一样单调。内容被升华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单调性,通过一连串的交叉剪接和话语游戏达到其高潮,而意义一直有赖于这两条线索的并置。
爱森斯坦对《监狱组画》的兴趣,就来自于这一分析所隐藏的概念。这位苏维埃导演在皮拉内西、福楼拜、莱奥纳多(Leonardo)的《洪水》(The Deluge)和格列柯那里,看到了两个对立面的综合:一方面,是先锋派和形式主义的经验主义,从这些例子来看,它们似乎在历史上都得到认可;而另一方面,是确认文本整体性(totality)特征,拯救其有机性,以及坚持(动态的)形式上的结构主义。
但这似乎否定了历史先锋派的一项基本断言:破坏艺术作品(work of art)这一概念,以及消解形式,有助于在对立的空洞符号之间形成某种断裂的蒙太奇。在五年计划的最初几年之后,某种类似的、具有暧昧自主性的语言学体系,不再发挥作用;它经不起新的俄国公众的直接检验,他们满脑子都是社会主义作品的意识形态。绝非偶然的是,在完全放弃了构成主义的传承之后,维斯宁(Vesnin)、布罗夫(Burov)甚至Vopra小组的追随者(最开始是Alabyan和Mordvinov)这样的建筑师,都会被无产阶级史诗洗脑。这一史诗具有一种在新未来主义和“20世纪”形而上学之间徘徊不定的特定形式结构。
实质上,1934-1937年间,安德鲁·吕尔萨(Andr Lur?at)这样的建筑师在苏联所做尝试与之相同。我们在卢卡奇(Luk cs)的理论中发现了对这一现象最为充分的表述。对卢卡奇而言,问题在于将资产阶级的形式传统推到极限边缘。对吕尔萨或爱森斯坦来说,事情也是这么回事。
实际上,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传统似乎才能逃离19世纪的冲突——对总体性的渴求与在极度异化中垮掉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困境。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有机性和团体有机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绝对不会完全实现的。
但应指出的是,对爱森斯坦来说,“知性电影”的程式,决不意味着对电影结构的内在动力的否定。这一内在动力是有机性的:爱森斯坦分离开其张力,他用“知性蒙太奇”(intellectual montage)去吸引观众,从而使观众参与到图像建构的动态过程中来。
于是,导致爱森斯坦分析皮拉内西作品的,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实际上,在分析“随想组画”的结构时,他特别关注于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一个独有的冲突。这就是“客体的危机”(crisis of the object),它与对单个元素的形象特征的保护正相呼应。并且,“客体的危机”,因其扭曲性和空间贯穿而遭到18世纪蚀刻家们的激烈指责。爱森斯坦写道:
一块石头或许已经“移离开”另一块石头,但它已经保留了它所表现出的“石头的”具体性[predmetnost]。一块石头或许让自己被一根棱角分明的木椽贯穿,但石头和木椽所表现的“具体性”(concreteness)还是丝毫无损地保持下来……客体本身的具体的现实透视性,其真正的再现性品质,在哪里也不会被破坏。
爱森斯坦敏锐地发现了皮拉内西赋予客体的模糊维度(ambiguous dimension)。就《监狱组画》中所涉及的问题而言,这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它关系到形式有机性(organicity)的命运:“第一次飞跃——超越了客体的精确轮廓的界限,这些客体进行着(构成客体的)几何形式的游戏——我们有塞尚(C zanne)……下一步——则是毕加索(Picasso)的出现。客体—这个托词[povod]—现在已经消失。”
从皮拉内西开始,经由塞尚,最终到达毕加索:先锋派的连续性从而得以确定。也就是,从皮拉内西的客体的危机开始,最后到客体的消失。但爱森斯坦向前更进了一步,因为,他热衷于在先锋派的源头处反映出(mirroring)先锋派自身的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克服”。理所当然的,他在其论述(discourse)中插入对结构主义建筑的草率攻击,谴责它低估了图像(image)的特殊作用。因此,在爱森斯坦看来,《格尔尼卡》(Guernica)也会是这样一个作品—通过对痛苦的回返,先锋派变得有历史性(becomes historic)。并且,在这个作品中,毕加索超越了完全主观的时刻。在这一主观性的时刻,“他不知道从哪里去攻击那些导致社会的“事物秩序”(order of things)混乱的东西;他在《格尔尼卡》中的幡然省悟之前,只会去攻击“事物”(things)和“秩序”(order)……之后,他就看到了罪恶及其“最初起因”潜藏在何处,在什么东西里。”
我们对这一关于《格尔尼卡》的解读有兴趣,是因为它也清晰地呈现出,爱森斯坦对皮拉内西的“提前发生的”(anticipatory)作品所作的评价。爱森斯坦从一种(极为可疑的)破坏性的、达达式的角度来看立体主义的毕加索。在他看来,皮拉内西同立体主义毕加索一样,也扰乱了“事物”和“秩序”,因为,他无法直接攻击“事物的秩序”。但正是这种形式的变形,这种对世俗规则的扭曲,这种“作为极端事件的建筑”,吸引了爱森斯坦的注意。此外,爱森斯坦还强迫自己从这种痛苦中汲取纯技术的元素:我们应当注意,他是怎样将皮拉内西的楼梯“升向未知之处”,同电影《十月》中克瑞斯基(Kerensky)攀爬的那段重复母题进行比较的。但也要注意到,他是怎样将《监狱组画》中典型的空间叠置和贯穿,同《旧与新》(The Old and the New)和《恐怖的伊万》(Ivan the Terrible)中镜头的建构进行比较的。在这两部电影中,演员特写,被用来同“此类舞台透视绘景(scenography as such)”的空间作对比。这一特写“曝光”于所展现的空间之外。正是在这一点上,爱森斯坦的辩证法—它不断地对其理论话语重新洗牌—无法隐藏住电影所预设的政治任务这一内在难题。
爱森斯坦将皮拉内西的构图法同他在中国、日本的直幅风景画中所发现的构图法相比较,认识到了处理对立综合(synthesis of opposites)的两种不同方式。在东方艺术之中,他坚持认为,存在着一种“寂静主义(quietism),它试图通过把一方消解为另一方来调解对立”。但是,在皮拉内西的作品中,存在着关系极度紧张的并置的双方,我们不得不“将它们相互刺穿”,并将它们的破坏性的活力推向极点。
但是,一旦我们在连接起《监狱组画》和《格尔尼卡》的红线中,发现了这种过度强化矛盾的方法,那么,形式的痛苦和伦理及政治义务之间的这样一种对比,在那个“幡然省悟”的毕加索的作品中,就真的无可非议地存在着吗?在皮拉内西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观主义,能在什么程度上,真正同那些诸如“知性蒙太奇”和“声音对位法”一样严密的形式构成技术相比拟呢?毕竟,在皮拉内西的作品中所看到的那种让人着迷的形式对立结构,难道不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极不可缺的一部分吗?
在这一点上,运用皮拉内西(或格列柯,或福楼拜)来证实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之间的亲缘关系,难道不是显露出一段意义极为含糊的过程吗?这些正是爱森斯坦避而不答的问题。事实上可以说,他晚期的文章,包括他关于《监狱组画》的文章,就是为回避这些问题而写的。
实际上,最终我们发现,尽管爱森斯坦很愿意发现先锋派不合时代的、乌托邦的特征,但是,他对历史先例的竭力搜寻,仍倾向于证实先锋派所特有的语言学工具。这些历史先例能够证明,在再现性价值的恢复和形式结构的自主性之间进行理论折中,是合理的。
然而,我们决不能被他对“知识分子电影”(intellectual cinema)的抽象特征所作的自我批评所误导。显然,在关于《监狱组画》的这篇文章中,他从皮拉内西到《格尔尼卡》所追索出的路,事实上是一个封闭的圆。他从《格尔尼卡》返回到《监狱组画》,返回到它们形象上的无限潜在可能,返回到它们对冲突、毁灭和记忆失误(lapsus)的夸张强调。《监狱组画》不是返回的终点,因为,在它背后是爱森斯坦自己,他背负着他的全部的语言学负担,同他自己辩论。
先锋派丧失了其乌托邦潜力,也丧失了它准备再度征服语言完满性的意识形态,它只能落回自身;它只能探索自身的发展历程。充其量,它也只能认识到自身起源的暧昧性。
这正是爱森斯坦此刻通过将皮拉内西神秘的《监狱组画》系列带至现在,从而将其“完成”所发生的事情。“被迫相互刺穿的”形式的冲撞,既属于皮拉内西,也属于爱森斯坦,这位苏维埃导演在寻找一种历史连续性,这将为他的语言学研究赋予一种并非昙花一现的体制上的涵义(a non-transient,institutional sense)。
因此,返回起源还包括对语言暧昧性的探索。从皮拉内西到爱森斯坦,在这一变迁中,形式的扭曲,秩序和混沌之间的辩证法,陌生化技术,它们都只不过表现为“素材”,并且是完全可以任意使用的素材。
在读到爱森斯坦将自己的电影系列与皮拉内西的构图法相比的那段时,我们很难不想到艾申鲍姆(Boris Eichenbaum)的基本宣言:
日常用语的机械性,对声音、语义和句法间的大量细微差别毫无触动—但在文学中正是这些东西大行其道。舞蹈是由那些非日常步行的动作所构成。虽然艺术的确借用了日常事物,虽然将日常事物用作素材,但它是为了赋予日常事物以一种意料不到的诠释,或将日常事物置于一种新的语境,一种明确变形的状态之中(例如怪诞风格[grotesque])。
爱森斯坦选择皮拉内西的“否定的乌托邦”(negative utopia)作为其类比的术语,他用这种方式隐喻性地宣称自己忠实于形式主义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他第一次真正表达了“先锋派的辩证法”。因为这个原因,他对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反法西斯的”承诺的参考,把一个(就其明确的讨论方向而言)显然并不和谐的母题,引入到文章组织之中。正因为如此,爱森斯坦避而不答如下终极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证明,在严格的学科思考之外,求助于史诗和痛苦(它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殊要素)是正确的呢?
事实上,这整篇文章都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是以一种晦涩的方式。求助于史诗通常体现出一种怀旧之情。爱森斯坦将他自己的作品同皮拉内西的研究相比较,同伟大的19世纪小说的有机法则相比较,揭示出了他所怀旧的对象:对他而言,现实主义—先锋派的继承人—回头观望,并不再为英雄年代里的资产阶级暧昧性流下一滴眼泪。
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建筑史学家
(译者:胡恒)
注释:
*译注:关于后文将陆续提到的皮拉内西的“监狱”系列作品,我们有必要预先做一些区分解释。Carceri,统一译为《监狱组画》(carceri为“监狱”一词的复数)。Invenzioni Capricciose di Carceri,统一译为《监狱随想组画》,简称Invenzioni Capricciose,统一译为《随想组画》。Carcere Oscura,统一译为《黑监狱》,该单一作品并不属于《监狱随想组画》,而属于《各种建筑作品》组画之一。
1.在爱森斯坦的作品中,他不断提及埃尔·格列柯和皮拉内西的作品。参见他在《感觉的同步》(Synchronization of Senses)一文中关于《托莱多城的风景和平面图》一画的详细分析,见Jay Leyda编辑和翻译的《电影感》(The Film Sense)(纽约,Harcourt,Brace&World,1942年),第69-109页;原始版本为“Vertikal’nyi montazh,stat’ya pervaya”,Iskusstvo Kino,第9期(1940年),或参考皮拉内西的构图技巧,“built from the movements and variations of counter-volumes”,见《形式和内容:实践》,同上书,第157页及其后;原始版本为“Vertikal’nyi montazh,stat’ya tret’ya”,Iskusstvo Kino,第1期(1941年)。《埃尔·格列柯》和《皮拉内西,或形式的流动性》两文见爱森斯坦作品全集第3卷,Izbrannye proizvedeniia(莫斯科:Iskusstvo,1964年),分别见第145页及其后,和第156页及其后。
2.3 。S。M。爱森斯坦:《爱森斯坦课程》(Lessons with Eisenstein)(纽约:Hill&Wang,1962年),第124页;第一版为Na urokach rezhissury S。Eyzenshteyna(莫斯科,1958年)。请注意,之后所引段落遵循了前面参考的皮拉内西《监狱组画》(Carceri)的动态构图。
4.S。M。爱森斯坦:《蒙太奇方法》(Methods of Montage)(1929年),见《电影形式:电影理论文集》(Film Form:Essays in Film Theory),杰·雷伊达编辑和翻译(纽约:Harcourt,Brace&World,1949年),第82页。
5.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走马》(La mossa del cavallo)和《散文理论》(Sulla teoria della prosa)(都灵:Einaudi,1976年),尤其是第12页及其后,第24页及其后;原始版本为O teorii prozy(莫斯科-列宁格勒:KPYR,1925年)。在什克洛夫斯基的基础文本中所建立的客体的“陌生化”(making strange)或“非熟悉化”(defamiliarization)理论,必然导致将诗歌阐释为“受阻且拐弯抹角的语言”。
6.见罗兰·巴特:《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erite)(巴黎:Du Seuil版本,1964年),第64页。
7.事实上,杜勃罗夫斯基所否认的联系,是同Anglo-Saxon批评的形式主义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对我们的论点来说,极为重要的是,《新批评》(Nouvelle Critique)关于“作品的第一性”(primacy of the work)的陈述:“每一个美学对象都是一项关于人类计划(human project)的作品。”杜勃罗夫斯基:《法国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 in Franc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06页;原始版本为Pourquoi la nouvelle critique:Critique et objectivité)(巴黎:Mercure de France,1966年)。
8.爱森斯坦:《电影的第四维度》(The Filmic Fourth Dimension)一文,见《电影形式》(Film Form),第65页;原始版本为”Kino Chetyr?ch izmeeniy”,Kino(1929年8月27日)。他写道:“电影画面永远不会成为不可改变的字母表中的字母,但必须一直保持为一种多义的表意符号,这是因为表意符号需要其特殊的意义(signifcance)、含义(meaning),甚至发音(pronunciation)……只有结合那些分别指示的解读或细微含义—对准确阅读的指示—才可以将基本的象形文字并置一旁。”(同上书)。关于这个主题,见M。Levin的“Ejzen?tejn e l’analisi strutturale”一文,Rassegna sovietica,第2期(1969年),第102-110页;原始版本为”S。E?zenshte?n I problemy structural’nogo analiza”,Voprosy literary 2(1969年)。另见爱森斯坦的《迪金斯、格里菲斯和当今的电影》(Dickens,Griffith and the Film Today)(1941-1942年),见《电影形式》(Film Form),第195页及其后。
9.《电影摄影术的法则和表意符号》(The Cinematographic Principle and the Ideogram)一文(1929年),见《电影形式》(Film Form),第28页。
10.例如,可见“Montazh 1938”一文,Iskusstvo kino,第1期(1938年)。
11.关于这些主题,参见本书中“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The Stage as“Virtual City”)一章。有意思的是去比较一下,爱森斯坦对皮拉内西的狂热,以及年轻的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1929年左右,在未出版的笔记中对皮拉内西的严厉谴责:“Toutes les reconstitutions de Piranèse,plan de Rpme,et compositions funambules qui ont terriblement servi à l’école des Beaux Art:que de Portiques,de colonnades,d’obelisques!C’est fous,c’est atroce,laid,imbecile。Ce n’est pas grandiose,il ne faut pas s’y tromper”(勒·柯布西耶,勒·柯布西耶基金会,bo?te B。N。,1919年左右)。这段评论证实了勒·柯布西耶对先锋派所持有的极其一贯的否定态度,这同他热衷于歌颂节制且典型的希腊艺术,热衷于劳吉耶(Laugier)的城市理论形成了对比。
12.参见阿尔伯托·罗萨(Alberto Asor Rosa)的《革命与文学》(Rivoluzione e letteratura)一文,Contropiano(《反平面》),第1期(1968年),第216-236页,以及“Lavoro intellettuale eutopia dell’avanguardia nel paese del socialismo realizzato”一文,见(多人合著)《建筑、城市、社会主义:从1917-1937年》(Socialismo,città,architettura:Urss 1917-1937)一书(罗马:Offcina,1971年),第217页及其后。关于这些主题,还可以参见本书中“走向‘社会主义城市’”(Toward the“Socialist City”)一章。
13.爱森斯坦:《从戏剧到电影》(Through Theater to Cinema)一文,见《电影形式》,第12-13页;原始版本为Sovetskoe kino,第11-12页(1934年)。
14.同上,第14页。
15.Boris Eichenbaum:《电影风格的问题》一文,选自Herbert Eagle编辑的《俄国形式主义电影理论》(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1981),第57页。原始版本为Poetika kino(莫斯科,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