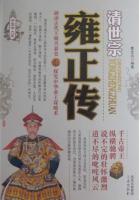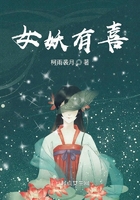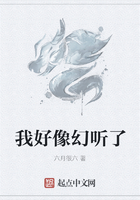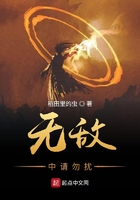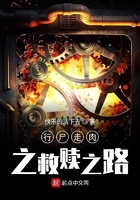高向明
抗大学习生活
1938年春节前后,我在柳青的带领下来到延安,进了抗大四期的女生队学习。这个队的学员绝大部分来自蒋管区和沦陷区,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来的大中学生,年龄在20岁上下,个别人年纪稍大,也不过30岁,还有一个年仅15岁的小妹妹。办好入校手续,便领到一套崭新的灰色军装和绑腿、皮带等。大家立刻脱下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兴奋地穿上军装。转眼间,从一个文质彬彬的女学生变成了飒爽英姿的女军人。
我们队的定额是120人,分为3个区队,每个区队有4个班,每班10个人,睡在一盘大炕上。队长叫赵琳,指导员叫吕瑛,我所属的区队队长叫丁俊雅。每天鸣号吹哨,集体作息。早晨,在响亮的号声中起床,接着整理内务,被子整整齐齐地叠成有棱有角的方块,横竖要成为一条直线。然后,排队到延安东门外的河滩跑步、操练;最后在延河里洗脸回营。刚刚解冻的延河还残留着冰碴儿,开始用冷水洗脸直打哆嗦,以后就慢慢习惯了。
学员每顿饭前,先列队唱歌,而后由队长或指导员讲话。吃饭不限量,但有时间规定,吃稀饭13分钟,吃干饭10分钟。规定时间一到,值班的区队长便吹起哨子,不管吃饱吃不饱,都得马上放下饭碗。
每天上午,学员排着队到府衙门大院,或延安师范大操场,或东门内小广场,或清凉山下上大课。几百名男女学员席地而坐,边听讲边做笔记。课程是马列主义概论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下午各班开学习讨论会。队里有教育干事,实际上是学习辅导员,负责解答学员们提出的疑难问题,或者把问题分类整理送给主管的教员。学校每周组织学员劳动一次,多在星期六。有时往返二三十里,到南门外七里铺的山沟里背柴,有时到仓库里背粮,要不然就清扫住房和院子。文化生活也很活跃,学员编墙报、排演节目、练习唱歌,遇到节日,就要开晚会,各队都得拿出自己认为满意的节目去表演。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乐趣,活动排得满,几乎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星期天很少休息。
每队都有中共党支部,指导员就是支部书记。1938年是党大发展时期,学员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后,毕业时80%以上都被吸收入党。1937年9月,我在开封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以进抗大一个多月后,就由吕瑛、丁俊雅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个多月以后,抗大四期四大队在清凉山成立了两个女生队,我转到其中的七队继续学习。同年7月,我又调到柳树店抗大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从4月到10月,我先后换了三个地方,总共在抗大学习了17个月。
难忘的岁月
1938年的深秋季节,党组织决定把培养理论干部的抗大政治教员训练队合并到延安马列学院。我们队的60多人,经过考试,由队长于丁带领,各自背起背包,迈着矫健的步伐,从延安东郊的柳树店搬到北郊的蓝家坪。蓝家坪在延河西岸,背山面水,一片沙土平川,山上几排窑洞,山下一溜平房,多幽静的学习环境。
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张闻天同志兼任院长,副院长是著名的经济学家王学文同志。学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身经百战的红军长征干部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经过白色恐怖考验的老同志,其中有些还是很有资历的红军指挥员和地下党的领导人;另一部分则是抗战前后入党的知识青年。这些人绝大多数在入校前都经过抗大、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中组部训练班以及中共党校的短期学习。
学院共开设六门课程,专职教员在延安是一流的。副院长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吴亮平讲马列主义基本问题,艾思奇讲哲学,杨松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陈昌浩讲西洋革命史,陈云、刘少奇、李富春分别专题讲党的建设。
最幸运的是,我在马列学院听过几次毛泽东的报告。此前,我在抗大也听过毛主席的报告,那是几百人坐在广场上听的,没有麦克风,毛主席浓重的湖南乡音,有些话我听不太懂,而且离得太远,看不清毛主席讲话时的表情。1940年1月,毛主席冒着严寒,从他的住地杨家岭步行前来马列学院。我接受抗大听讲的教训,早早就在离讲桌很近的地方占了一个位置。毛主席讲他刚刚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他共讲了三个半天。毛主席神采奕奕,声音洪亮,语言生动,讲话中不断打手势。他深入浅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详尽地作了阶级分析,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即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此外,毛主席还曾作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报告。
刘少奇同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主讲《党的建设》,言简意赅,很有吸引力。时过几十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个底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说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坚持斗争,一直到死为止。简而言之,“底”就是奋斗到死。
此外,学校还请一些从前线、敌后的蒋管区回延安的负责同志作报告。周恩来报告《国内外形势与大后方统一战线》,朱德报告《形势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报告《华北战场》,彭真报告《关于晋察冀形势》,董必武报告《关于大后方形势》。总计一年多的时间,马列学院组织专题报告共有50多次。这些报告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而且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是我一生中听报告最多的年代。
1939年春天,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整个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马列学院的员工也在几十里以外的山上开荒种地。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同志们就摸黑扛着镢头上山,午饭是送到山上吃的,傍晚太阳落山才返回。劳动中,大家不顾风吹日晒和雨淋,手上磨起血泡,身上沾满汗水和泥土,不叫苦,不叫累,不嫌脏,力气大的帮助力气小的,男同志帮助女同志,满山遍野,一片欢腾。大家把劳动场地当作课堂,在劳动中既锻炼了意志,又增长了生产知识。由于马列学院生产成绩优异,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除了开荒种地以外,学员有时还到40里外的崂山背柴,到仓库背粮,在河滩种菜,女同志节假日帮厨。
开展大生产运动后,生活明显改善了,每个星期可以吃到一次猪肉和馒头。每人一年发一套单衣。同学们没有替换的多余衣服,夏天到延河里洗澡,先把衣服洗好,晒到石头上,晒干穿上再回来。三年发一套棉衣,要交旧领新。洗衣服没有肥皂,用烧过的草木灰过滤的碱水代替肥皂。刷牙没有牙膏或牙粉,以食盐代替。
我们在马列学院的生活无忧无虑,无牵无挂,除了学习之外,很少想到别的事情。当时实行供给制,吃穿用全由学校供给,连女同志用的卫生纸也是发的。学校每月还给每个学员发两元津贴。发了钱后,全组同志把钱凑到一块,到学校隔壁的机关合作社,大吃一顿。星期六晚上,大家结伴到延安城里的小摊上,喝一碗热气腾腾又香又甜的江米甜酒散鸡蛋。蓝家坪离城7里路,往返14里,一路上说说笑笑,很高兴。时间来得及的话,还顺路拐到延安北门外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魏传统家串个门。有时到老乡家买上几斤陕北大红枣,用搪瓷杯炖在炭火盆上,吃起来另有一番滋味。有时到书店买上几本廉价书。总之,要想方设法把这为数不多的钱花掉。那时候,钱对我们好像没有多少用处,一月29天口袋都没有钱。
我们的生活既严肃,又活泼,充满了乐观主义情趣。逢年过节学院都组织文艺晚会,内容各种各样、丰富多彩。有话剧、京剧、唱歌、舞蹈等。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丁玲、陈波儿、孙维世、王大化都在学校学习。由陈波儿导演、萧三翻译的话剧《马门教授》在学院和中央党校演出后,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那个年代,我们还经常看苏联的原版电影,《夏伯阳》、《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保卫察里津》……百看不厌。看片子和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密切相关,作为学习的辅导材料。
第一次放映《列宁在十月》,刚好周恩来同志从重庆返回延安来学校看电影,大家鼓掌欢迎周恩来同志做翻译,他毫无架子,立即站在大操场上的一个凳子上,用响亮的声音,给大家翻译片子的内容。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原来素不相识,但在朝夕相处的紧张学习中,结下了深情厚谊。彼此极为亲切,不是兄弟姐妹,胜似兄弟姐妹。同志之间,谁有了困难,全靠大家来帮助。节假日,女同志忙忙碌碌地为男同志拆洗被褥、缝补衣服,男同志帮女同志打草鞋。有人生了病,也是同志们互相照顾,陪着上医院,到食堂打病号饭,甚至端屎倒尿。
光阴似箭,历史已经飞越了半个多世纪,但马列学院的那段生活,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清凉山的日日夜夜
1940年6月,马列学院三班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基层工作。先后担任过县(富县)县青救会主任、延安县柳林区二乡民办小学教员、米脂县城关区的乡文书、杨家沟完全小学教导主任。
1946年6月,我重上清凉山,开始到《解放日报》社,以后转到新华总社工作。报社和通讯社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是一个机构。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在新闻单位呆了50年,清凉山对我来说,同样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地方。
我到延安以前是一个中学生,语文基础和文史知识都比较差,对新闻业务一窍不通,到《解放日报》以前做基层工作,工作岗位变动后,一切都感到陌生。一起工作的同志,除少数人做过几年新闻工作外,大多是从各单位调来的年轻人。他们的情况和我差不多,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新闻训练,业务不熟悉。怎么办?学习。在战争年代,受条件限制,根据地没有那么多专业学校培养干部,只有边学边干,干中学,学中干。因而学习和练基本功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幸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学习,热爱新闻工作。那时候,大家都没有家务拖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在工作和学习上。我们的学习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学理论、政策和思想修养;二是学习新闻业务和各方面的知识。前者主要靠日常的政治学习;后者来自三个方面——领导上的及时指点、老同志的身传言教、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
我被分配在采访通讯部,经常到中央和边区机关以及附近的县里采访。大量的工作还是修改通讯员的来稿,给通讯员写信。那时给报社投稿的通讯员有数百人,几乎边区的每个县、每个单位都有通讯员。
我们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经常要在夜里工作,照明设备很差,是盏很小的油灯。小油灯光线很暗,还老跳出灯花,冒烟。我们用的是马兰草造的粗糙的稿纸,没有自来水笔,没有圆珠笔,只能用蘸水笔或毛笔。墨水则是用紫色颜料冲的,而颜料还是从边区外面买的。外出采访,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全是步行。经常是花在走路上的时间远远超过采访的时间,我们的工作还常常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民是靠天吃饭,我们是看天行事,下大雨,下大雪,那出不了门,山路又陡又滑,太难行走。中央和陕甘边区的一些机关在延河西岸,报社所在地的清凉山在延河东岸,每天都有人过河采访、开会或办事。延河上没有建桥,冬天延河结冰,人们就从冰上通过,春秋天过河走蹑石,最伤脑筋的是夏天,要水过河。延河驯服的时候,像一个温柔文静的少女,一旦咆哮起来,简直像一头凶猛的野兽。夏季延河经常发大水,河水漫过腰部,会游泳的人不多,事先约好的采访活动就不得不临时改变。新华社的发报台设在延安北门外美军观察组的旧址。每天编辑部编好的稿子,先由译电员记成码子,再由通讯员过河送到发报台发出。延河涨水的时候,我看见一位勇敢的通讯员把稿子顶在头上水过河。
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们还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清凉山机关在东郊罗家坪有一处生产基地,主要种蔬菜。我们还在窑洞前种了西红柿、辣椒、豆角等。山上缺水,对水特别珍惜。为了留下洗脸水浇灌自己的小菜地,洗脸从来不用肥皂。有时同志们还提上打饭用的半截铁桶,顺着印刷厂的石板路到延河里汲水浇菜地。
1947年春天,国民党集中23万军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同年3月19日,我军辙离延安。早在敌人进攻之前,延安的中央和边区机关就做了周密的备战准备。疏散人员,转移物资,携带不了的坛坛罐罐和书籍等则埋在山坡坡上。幸亏个人物品不多,一声令下,说走就走。
《解放日报》派我们三个人成立了驻绥德通讯处,开始住在绥德城外西山寺的地委机关,和地委报社的同志一起办公。战争爆发后,一直随地委机关行动,前后转移了许多地方。有时离敌人很近,围着一座大山转来转去,就像捉迷藏一样。我们情况熟悉,群众基础好,敌人一出动,立刻有人送信。敌人则到处碰壁,士气越来越低。
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敌人一个整编师,结束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并从此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4月22日,我军收复了延安。气焰嚣张的敌人只占领延安一年一月零三天,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节节败退,一蹶不振。
敌军占领延安后,《解放日报》转移到瓦窑堡,于3月27日出了最后一期便停刊。新华总社的同志,一小部分人由范长江带领,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绝大部分同志由社长廖承志带领,东渡黄河,前往太行。我继续留在陕北,于1948年6月随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边区群众报》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回到延安,三上清凉山。
回到清凉山,我们修复了惨遭国民党军队破坏的《解放日报》社旧址,粉刷了原来的窑洞,重新安上门窗,清扫了脏乱的环境,重建家园。我们又在这个熟悉的山头上重操旧业,日日夜夜,采访编稿,出版报纸,向新华总社发电讯。
彭德怀同志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1949年5月20日解放了西安。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报社的同志分期分批前往西安,迎接新的任务。
6月10日,我告别了曾经学习、工作和生活了11年的延安。